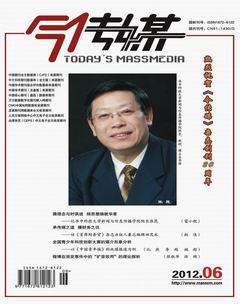大众传媒在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分析
刘燕影
摘要:大众传媒作为科学信息自由交往的传播空间与手段,在由“对技术统治的批判”和“专业知识的民主化”两方面组成的科学民主化的进程中,扮演着科学情景视窗、科学-社会媒介、科学讨论广场以及政策议程推手的角色。随着科学传播模式以及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发展,大众传媒将成为科学技术体系与公众互动有效介质,并将促进冲突性知识管理机制的形成,不断推动科学民主化的进程。
关键词:大众传媒;科学传播;科学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122(2012)06-0022-03
20世纪以来,科学事业突飞猛进,同时也促进了全球的经济繁荣。而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广泛渗透性,引发了许多吸引大量公众关注和参与的科学——社会问题,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专家之间的纷争,让这一过程充满政治性,科学民主化被提上议事日程。大众传媒在这种变化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将知识传播给公众,对其进行选择、强调,并在它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对其进行修整[1]。从近几十年发生的核能、疯牛病、转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化等科学问题来看,当今的科学民主化仍缺乏对冲突性知识进行有效管理的机制,在科学民主化的进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并将担当其应有的角色。
一、科学民主化讨论
科学民主化大致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对技术统治的批判”,当科学以客观、可信的面目示人,以专业知识造福人类的同时,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的一种专有权利,从而威胁民主进程,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二是“专业知识的民主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知识不被看作是更优越的,而被看作是不明确的、危险的和不完全的。在科学内部,科学的政治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专家们已经不是中立知识的代表,他们可能只是在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辩,科学理性遭到怀疑,民主参与成为一种选择。
“对技术统治的批判”,是对科学主义进行理性批判的自然延伸[2]。技术统治论或专家政治是科学主义或技术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和特殊运用。技术统治论者认为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专家群体,才有能力在与科学有关的政治决策中发表意见,承担政治责任,科学的民主化甚至有可能妨碍科学决策的形成。事实上,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中,训练有素的科学专家除了专业素养以外,也许并不具备超常的政治判断力。
“专业知识的民主化”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益凸显。发端于西方国家的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等社会运动,对科学的异化及其社会影响首先提出质疑。随后,公共领域的科学技术争论和风险问题日益增多,诸如“疯牛病”、“转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化”等科学信用问题的出现,使得公众对科学产生了信任危机,公众的关注和参与愿望不断增加。而近年来,由科学引发的社会风险,甚至出现了所谓“风险的风险”,科学家也产生了焦虑,唯恐被投入到民主的暴政之中。
科学的民主化已经成为可能,科学民主化的实践已经在开放社会中萌动。哈贝马斯认为,开放社会的纲领首先是要求科学信息的自由交往。科学传播为这种自由交往提供了条件,成为科学民主化的一种介质。科学技术体系和公众的互动在科学传播的空间展开,成为科学民主化的主战场。
二、科学传播与科学民主化
科学传播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从学者们对科学传播的研究中大致可以看出,科学传播因科学的发展,其内容、特点不断丰富和更新,早期的传统科学普及被认为是强调科学知识的单向传播,公众往往处于某种“被科普”状态。二战后,科学因其对社会的影响被重新评估,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对科学的怀疑和批评开始出现。为此,20世纪8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它倡导科学共同体、教育系统、大众传媒、产业界、政府和博物馆,根据自身的特点,积极投身到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中,旨在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促进国家繁荣、提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90年代,则出现了“优化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与社会”等等新议题,科学咨询、共识会议、圆桌讨论和参与性技术评估等更加开放和互动的传播方式被采用。
一般认为,科学传播有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和民主模型等三种模型。中心广播模型也即传统科普,被认为是国家或政党立场,强调自上而下命令、教导;缺失模型是科学共同体立场,强调自上而下的教育与公关,“知”与“信”并重;民主模型则被认为是公民立场或人文立场,公民接受义务科学教育,就科学技术事务可以参与协商,强调“知”和“质疑”[3]。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各自却也都具有科学民主化的内涵,或者说对科学民主化都有积极的意义。
其中的“民主模型”是英国公众理解科学专家约翰·杜兰特在继20世纪60年代提出“缺失模型”之后建构的重要科学传播模型。它强调公众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决策,与科学家、政府间进行平等对话,从而实现科学传播。“民主模型”预示着科学传播理论正从大众传播理论的一个子集,向着摆脱“科学+传播”的简单框架,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方向发展[4]。民主模型倡导对话和协商,公众成为科学事务和科学决策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公众讨论和冲突解决机制为解决科学产生的社会的、伦理的甚至政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科学传播模型来源于科学传播的实践,打破知识鸿沟和权力鸿沟同样需要实践的空间。从科学传播与科学民主化实践的空间看,除了科学机构、工业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科技政策领域外,还有明确致力于科学传播的空间,大众传媒就是其中一种。大众传媒包括图书、杂志、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尤其是网络等新传媒技术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有效的互动平台。按照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思想,大众传媒的科学传播范式在于它不仅是展示科学的平台,而且就此形成了科学的公众形象。
三、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大众传媒角色
科学共同体和大众传媒,是有着不同旨趣的两个群体,科学是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工作,创造知识,接受同行评议。大众传媒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提供娱乐和信息,新闻记者用新闻的语言转述科学知识。基于发行量和收视率的需要,新闻性是主要的追求目标。因此,就科学的一般性质和媒体的需求而言,科学的知识体系并不是新闻的最佳来源。此外,也还存在着媒体对科学文化的偏见、科学家和记者在时间尺度、优先次序和客观性等问题上的差异[5]。
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观点,当科学成为新闻时,专业媒体或许还可以从提供战略性专家知识入手,大众传媒则往往采用“轰动性”和“骇人听闻”模式。然而,大众传媒的角色并非只是“猎奇的”和“肤浅的”,在科学传播理论日益成熟和丰满,科学传播多种模式并存的状态下,大众传媒的视域變得广阔,形成了多种层次的科学传播,比如从教育背景来理解的知识层次;从商业和政治背景来理解的实用层次;将科学理解为文化实在和资源的文化层次;以及在“民主社会”中理解和使用科学的公民层次。大众传媒在不同的传播层次和科学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科学情景视窗、科学——社会媒介、科学讨论广场以及政策议程推手的角色。
(一)科学情景视窗角色
就大众传媒的新闻、宣传、教育和娱乐的内容属性来看,科学情景视窗主要以传播知识为主,也起到通报信息的功能,向社会报告科学进展。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中心广播的作用。据中国科协统计,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我国公众获得科学信息的主要渠道。2010年,我国公众从不同媒体获取科学信息的统计如下:电视85.7%;广播24.6%;报纸59.1%;图书刊物34.6%;网络26.6%[6]。值得一提的是,网络渠道在2005年的数据为6.4%,显示出很好的发展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