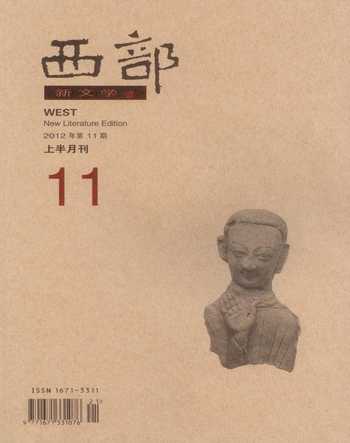一个德国文人对美国的沉思
冯强
1937年新年前夜,托马斯·曼写信给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信中他回忆说,很长时间以来,他竭力不■德国政治的浑水,远离是非,以避免将其与德国文化的联系,最重要的是与德国读者的联系置于危险的境地。然而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他的祖国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迫使他打破沉默。他无法在退隐到孤独的文化存在中蹲守。如果说纳粹政体给了他教训的话,那就是他终于洞见到,文化不可能与政治毫无干系,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也须共存”。就在一年前,“出于令人同情的动机”,波恩大学剥夺了其曾在1919年授予曼的荣誉博士学位。之后,哈佛大学重新授予了他被剥夺的头衔。“不管他是作家还是民主人士,美国都将成为对他礼遇有加的国度。”(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而在1918年一战接近尾声时,曼的《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还宣称“民主和德意志精神水火不容,德国文化和德国军国主义根本就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曼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更,但无疑,文化和权力的关系贯穿了他思考的全部。这一关系在德国向来有两大传统:一是1813年随着俾斯麦的普鲁士战胜法国,德国转变为文化国家,从此“文化与权力并肩生存,政治国家和文化国家成为一体” 。布克哈特、尼采等思想家则相反,前者认为“权力与文化是分离的,是文化的敌对力量。权力有其自身要素,而且这个要素究其本质就是罪恶”,后者认为“对权力的追逐与袒护会导致文化的日渐丧失。文化发展首先归功于政治的长久衰落” 。一战时的曼站在俾斯麦一边,《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的目的就是“反驳在德国权力和文化不可能融合的观点”,彼时的曼“沉浸在德国浪漫主义的咒符中”,对“‘罗马的西方和‘大洋对岸屹立的崭新国家所安享的民主进行了猛烈抨击”。
四年之后,曼却在柏林的贝多芬礼堂发表《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说,力图挽救岌岌可危的魏玛共和国。他在其中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能成功地在共和、民主以及德国浪漫运动之间建立联系,是否我就能够同时使我们国家中那些顽固不化、争吵不休的人更容易接受共和?”他试图论证,德国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传统和民主思想并不相悖。他在浪漫主义世界观的深处发现了共和主义的影子,以诺瓦利斯为代表,曼从中发掘出德国浪漫主义中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双重倾向。另一方面,他试图厘清美国民主理想的浪漫之核,此时他想到的是美国诗人惠特曼。在惠特曼那里,曼发现了世界主义的另一面:个人主义。“我歌唱自我,歌唱每个独立的个体/然而却用民主的词汇,大众的语言”,在惠特曼的诗歌中,民主和审美合二为一,成为乔纳森·福蒂斯丘所谓的“民主美学”。曼的这次演讲以惠特曼的《民主远景》为主要援引资料,后者宣称法律的制定和投票选举都不足以赋予民主以生气,民主需要真正触及“人的心灵、情感及信仰”。这一点确实会触动以对抗法国启蒙运动起家的德国浪漫主义者的心灵。在他们那里,“启蒙的基础不是理性思辨,而是与身体政治有关的涵盖一切的情感和欲望”。
不夸张地说,对政治和性尤其是政治和男同性恋的关系的认同是曼接受惠特曼民主思想的主要原因。惠特曼兼民主和浪漫色彩于一身,对同性恋关系持赞赏态度,“并且认为同性恋在民主国家真正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不可或缺”。他在《民主远景》中这样写道:“强烈而深情的同志关系,男人和男人之间私密而热情的爱慕——这虽然有些难以界定,却存在于思想深邃的救世主的经验与理想的深处,世界上的每块土地、每个时代莫不如此。这似乎在告诉我们,如果这种关系能在社会习俗与文学中得到充分发展、促进和承认,那么这些国家未来中最重要的希望以及最令人信服的安全感便会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惠特曼一样,曼有同性恋倾向。他本人也一直在思考这一倾向在他的写作中和整个社会中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早年受Hans Blüher的影响,曼的同性恋观有强权化和贵族化的特征,厌恶女性,强调男性的阳刚之气和男性的特权,这使他将同性恋和民主对立起来,认为同性恋是男权社会的现象。彼时的曼掩藏起自己真正的性取向。在《德意志共和国》中,Blüher的影响仍旧存在,但是曼已经有意识地以惠特曼的观点与其对峙。在惠特曼那里,同性之爱“根本上说是民主的、和平的,是向着不同国家之联合与不同个体之联合的双重演进。惠特曼为曼提供了超出德国浪漫派将爱和死联系起来的思路……经由惠特曼,曼开始接受内在于和外在于自我的‘女性观……对惠特曼的阅读使曼的观点从贵族到民主、从对身体的厌倦到对身体的欢庆,使他认识到同性恋同样可能蕴含着最高意义上的道德功能……使他可以想象一种虽基于身体却仍然神圣的爱,一种根本上同性恋的却仍然可以于此通达社会责任的爱,一种肯定生命甚于死亡的爱” 。
然而问题是,一个民主制度初步完成的国家如美国,相比尚未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对身体政治的强调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效果。如果我们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对“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区分将民主划分为“第一民主时代”和“第二民主时代”,前者是个体权利的制度化时代,后者是个体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对自我和制度本身进行双重反思并进一步改变制度和自我的自反化时代,我们就会发现德国的问题是它在文化方面的超前性,它在一个相对较好的制度尚未建立之前就发动了明显凌驾于现存政治之上的文化革命,却缺乏一个足够支撑起这种文化的政治底座。简言之,在尚未进入“第一民主时代”的前提下强行推进“第二民主时代”,以文化代替政治、僭越政治,最后的结果却是政治对文化的替代和僭越。
让我们从本书的书名《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说起。沃尔夫·勒佩尼斯将这种 “德国诱惑”界定为“一种认为文化是政治的高贵替代物的思想,尽管这也许并不见得是更好的政治形态”。德国人区分了“文化”和“文明”,前者是德国特有的,后者则用来贬抑英法等欧洲主要强国。这种思想在曼的《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中有代表性的阐述:德国的传统思想体现在“文化、灵魂、自由和艺术上,而不是文明、社会、选举权和文学”,因此,“德国人永远不会爱上民主政治,原因很简单,他们本来就不喜欢政治,而且备受谴责的‘独裁主义国家永远是最适宜的、德国人最习惯的,也是他们从根本上渴望的国家形式”。勒佩尼斯判断说:“文化是政治的替代物,这是贯穿在德国历史中的普遍思想——从十八、十九世纪魏玛的辉煌岁月,到二十世纪末两个德国的统一。”他在本书中接受了某位向导的引领,“从他的一生中,从他遗留下来的书信中,可以看到,对政治和文化的‘德国姿态,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以不太适当或自相矛盾的方式,得到了最撼动人心的表达,其诚实程度经常令人痛苦不安,并且总是带着反讽的态度。这个人就是托马斯·曼”。
根据我的讲述,曼似乎是从不屑于民主转向热情拥护民主的。其实不然。和惠特曼一样,曼的思维方式典型属于第二民主时代。即使是《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这样的著作,也是以反讽的方式表达民主——反讽本身是一种深刻的民主形式——失去睿智和忧郁气质的保守主义会沦落为简单而强硬的原教旨主义,用曼自己的话来解释,即“反讽是知性主义的一种形式,反讽的保守主义是一种知性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形式与效果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冲突,因此很可能,它在与民主进步对抗的道路上便促进了民主与进步” 。但是,正如勒佩尼斯指出的,“在一部支持德国例外论、反对可鄙的欧洲民主标准化的著作中,他的这种表白不仅很是怪异,而且相当危险”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前面提到的,在解放政治尚未完成的时候,在每一个具体个体的权利尚未得到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生活——这种生活往往体现于某种独特的语音语调等等不能被制度规定的情境当中——其中精致和难以言传的部分往往会被粗暴地忽略而蜕变为简单的意识形态,最终为一种不正当的政治形态所利用,这也是曼和惠特曼最主要的语境差异。
无论如何,《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毕竟代表了曼促进德国文化和西方政治和解的努力,虽然和解并非易事——“托马斯·曼对欧洲遗产的巨大影响一开始持勉强接受的态度,后来渐渐转变为热情支持,这个过程贯穿了整个和解进程。”这一转变明显表现在曼前后两次不同的流亡状态上:罗姆大屠杀之前,他回避公开指责纳粹的政体问题,并且在谈到“流亡”时心存鄙夷:“他讨厌‘流亡一词所包含的怨恨的氛围,坚持认为自己处于流亡者的圈子之外。他觉得自己不是避难者,只是一个迫不得已离开国家、到国外居住一段时间的德国公民。他一直念念不忘返回德国。”大屠杀之后,他感到有必要和德国发生的事情划清界限,“于是流亡成了一种可行的、可接纳的生存方式。托马斯·曼在他的日记里总是提到,他如今必须写点政治宣言或声明之类的文章了。对他来说,艺术和生命总是无法分开:他越来越像梦想家约瑟了——在流亡过程中转变成对政治深负责任感的人” 。
对政治的敏感让曼的文化态度更加务实,对德国和美国的比较让他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文化和政治间的深层关联。“一战后,美国民主曾促使托马斯·曼称赞德国共和;二战后,这位德国人对文化所持的浪漫观点又促使他增加了对美国政治所做的批判。”在一篇为1942年12月10日在纽约举办的诺贝尔颁奖晚宴准备的演说中,“他表达了他的期望——他希望整个世界迟早会‘美国化。他补充道,这种‘美国化是在‘某种基本的道德意义上,而且‘华盛顿的和平会在全世界成为风尚” 。而到了1950年代早期,随着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肆虐,他则“希望欧洲能在正在升级的美国与苏联、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中以第三种力量出现”。曼对美国的态度类似于歌德,“既能对美国表示敬佩,又能同时保留对欧洲的骄傲”。
文化和政治之争被搁置起来。“二战之后,让文化凌驾于政治之上的那种高度兴奋感在德国已成明日黄花。当阿多诺把任何在经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之后还想写诗的企图称为残忍时,他表达的正是这种观点。然而经历过奥斯维辛的保罗·策兰所写的诗歌却无论如何不能称为残忍——因为他的诗歌反映了文化的无助,而非权力的无助。”权力的本质不是罪恶。如果没有权力来进行制度性的配置和安排,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这本身即是更大的恶;权力也并非天生善良。如果没有分权、没有监督,权力堕落为极权,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同样会遭到侵犯。因此我们要问一句,权力是什么样的权力?文化又是什么样的文化?如果我们以生命个体的基本权利为鹄的,那么权力必定是一个多元的权力格局,文化也必然是一个可以容忍他者和差异的多元文化。文化和权力虽然是殊异的范畴,但它们在第二民主时代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可分享性。文化的可分享性可以用萧伯纳对苹果和思想的著名区分来解释,权力的可分享性可以用阿伦特对“权力”和“暴力”的区分来解释。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发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真的很特殊吗(或者,中国真的很特殊吗)?未必。从西班牙、法国和爱尔兰的历史看,将文化视为政治的替代物并无多少特殊之处,它反而是政治尚不成熟国家的普遍状况。以文化的名义来抵制资本主义文明,或者以权力架空资本主义文明对社会平等和个体权利的强调(存在一种“权贵资本主义”吗?),都是对文化和权力的滥用和误用。“战后德国的历史转折点不是在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而是在1948年进行货币改革的时候。促使社会发生改变并最终旧貌换新颜的不是罪孽深重的良心,而是新的货币政策。” “欧洲没有像历史学家兰克曾经预言的那样,发展为神圣的统一体,而是像企业家兼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在一战结束时已经预言的那样,成为以利益导向为基础的经济共同体。”煤炭和钢铁而非文化成为欧洲联盟的开端和支点,专业的管理人员代替知识分子有条不紊地经营着。人权的问题已经成为共识并得到制度性的切实保障,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似乎已经终结。“作家与诗人不再声称,他们的角色是先知和预言家,为世界政治提供真理;他们应该承担作家兼公民的角色,在积极参与琐碎的政治工作于政治建设中体验骄傲与愉悦”,而“一旦崇高的道德姿态成为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作家和艺术家就能够以清醒严肃、冷静务实的态度为民主服务”。这样一个结果肯定是曼所欣慰的。
栏目责编:舒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