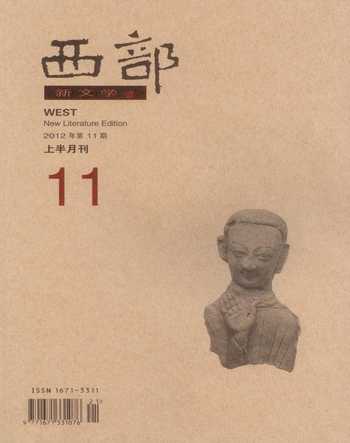巴扎里的时间
王敏
集市荒芜了,还有小店铺,苍蝇
孩子们追逐它,远远的地平线
茅屋在枣椰林打呵欠
——阿卜杜勒·瓦哈卜·白雅帖:《乡村集市》
最初,“BAZZAR”(巴扎/芭莎)仅仅指向巴扎自身,除了具备物理空间的功能外,它不会是别的东西。今天,巴扎更多地和时尚联系在一起,既是因为一本享誉中外的时尚刊物取名为“时尚芭莎”(BAZZAR)的缘故,也是由于坐落于新疆乌鲁木齐市二道桥的地标性建筑——大巴扎驰名于世的结果。就前者而言,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讲,巴扎是波斯语词汇,原是突厥语族采用的一个处所称谓,历史上,突厥人在与汉族的贸易接触中,这个处所称谓也被译介过来,根据汉语的译音,遂有巴扎、巴札、巴札尔、把撒儿、把咱儿、八栅尔、巴匝尔、把杂尔、八杂、八杂尔、八栅等音译出现于史料中。随着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日趋繁荣,“巴扎”这个词的音译经由行旅商人的口耳相传,开始流行于欧洲大陆,并再沿着新时期的贸易往来,从海上丝绸之路回传,最终跳脱出其原有的处所概念和地域束缚,跃迁为一个当代时尚符号的集合名词。
无论古今,巴扎(集市)在维吾尔族的日常生活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场所,与维吾尔族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维吾尔族或者穆斯林生活的全部传统方式都是在连接城镇与乡村或者绿洲的巴扎里形成的。将维吾尔族乃至整个穆斯林社会描绘成一部城镇的历史,或者说从城镇生活的日常细节中把握维吾尔人的行为规范和观念意识已是老生长谈了。中世纪的穆斯林早就说过,城市有两个焦点,星期五的清真寺与市场。可见,清真寺与巴扎在穆斯林世界中的显要地位。而若是将巴扎与清真寺相比,前者在维吾尔人的心里具有更强的世俗性与日常性,对此,维吾尔人有不少民谚,如“去巴扎找幸福”、“离巴扎近一些,麻扎远一些”等等,都与巴扎有关。如此说来,一个典型的维吾尔人一生的大半时间可以说都是在巴扎以及去巴扎的路上度过的。因此,梳理、分析维吾尔人在巴扎上的时间对于概括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考察维吾尔人的文化心理,便显得格外必要。
维吾尔人的巴扎文化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时间的文化,一种在巴扎日上可以用时间对诸多行为进行铭写、修订的模式和系统,正如黑格施特兰德所说,文化其实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无形中蕴含在物质世界中的时间的主要修订体系”。探究巴扎文化,实际上就是透过巴扎的空间屏障去看巴扎上的时间集合,揭示这个集合背后隐含的模式和体系。简言之,考究巴扎文化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出巴扎里的“隐形时间”,分析巴扎文化的关键则在于能否再现巴扎里“隐形时间”的文化模式。
巴扎与约定的时间
巴扎日是被建构的时间。维吾尔人的巴扎有着严格的时间周期,通常按星期排列,以七天为一个时间轮回,每一天都能成为一个巴扎日。因而,不同的地点处所,可以拥有同一个巴扎日,而在同一个地点处所也可以有多个巴扎轮流出现。例如,以新疆墨玉县的巴扎日为例:星期二是墨玉县的奎牙乡、英也尔乡、喀瓦克乡等三个地方的巴扎日;星期四是托胡拉乡、喀尔赛乡、乌尔其乡、吐外特乡等四个乡的巴扎日。县城里的巴扎大多在星期日,而乡村里的巴扎是除了星期天以外的其他日子。可见,巴扎日本质上是一个经集体协商约定好的时间,巴扎是维吾尔人集会的一个时间约定。问题在于,巴扎作为一个时间约定,是与谁的时间约定?
在笔者看来,巴扎首先涉及到与农牧民的时间约定。这主要可以从巴扎的市值差异与周期规律考察发现。一般而言,夏秋两季,巴扎的市值较高,持续时段较长,而秋冬两季市值较低,持续时段较短。也就是说,在巴扎上,一年内5月至11月的商品交易额处于上涨期,而11月至5月的交易额则处于下跌期。考究这个市值起伏规律性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巴扎的市值起伏与农牧民的收支情况有着直接对应的关系。因而,巴扎其实是与农牧民农忙季节的一个时间约定。
其次,巴扎涉及到与安拉的时间约定。在真主“安拉”的启示中,多次提到自食其力、经商就业的重要性。先知穆罕默德在创教传教的过程中,更是始终把造福民生的经济生活放在首要位置。的确,穆斯林一向有重商济世的传统,穆斯林商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究其缘由,主要与伊斯兰教主张教商合一的理念以及先知穆罕默德从商的经历有关。在伊斯兰教看来,经商是受真主喜爱的职业,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原因在于商人需要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巴扎中经营贸易,作为使者的穆斯林商人在经商的同时可以完成安拉托付的传教任务,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古兰经》中,真主安拉启示道:“我在你之前所派遣的使者,没有一个是不吃饭的,没有一个是不往来于市场之间的。”而伊玛目安萨里对正统的穆斯林商人的宗教操守提出过非常严苛的七项规定,其中有一项便是要求穆斯林商人在“集市上常记安拉,常念颂主清净词与颂主独一词;集市上疏忽大意者之间记念安拉更为优越”。可见,巴扎日其实是维吾尔人作为穆斯林对安拉尽忠的一种时间约定。
第三,巴扎涉及到与礼拜的时间约定。在南疆的城镇,很多巴扎就在清真寺周边展开,这主要是为了方便维吾尔人在做礼拜之日,或者朝拜麻扎之后能够顺便逛一下巴扎。因此,很多巴扎日其实是在礼拜日形成的。比如墨玉县托胡拉乡的巴扎便是在礼拜日这一天形成的。相传,很多年前的一个主麻日(星期五),人们在路边的清真寺做礼拜出来,突然看见一个人手里拿着两只鸡站在清真寺前。有一个人问他:“卖不卖鸡?”手里拿着鸡的人说:“卖。”于是这笔关于鸡的生意便算成了。从此这个乡被称呼为“托胡拉”(鸡),人们也就默认般协定每个星期五在这清真寺前做买卖。日久天长,随着饭馆和馕坑的日渐增多,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巴扎。因此,有的巴扎实际上是与维吾尔人礼拜日的一种时间约定。
巴扎与受控的时间
一个巴扎的受控时间是与维吾尔人的工作时间紧密相连的,这种受控时间指的是在巴扎日可以被使用、分配和交换的时间。如果说,巴扎的约定时间更多地指向过去,那么巴扎的受控时间则是在言明当下,是一个现在时的进程,是巴扎的过去时间与未来时间的中间状态。具体而言,这种受控时间在巴扎上主要表现为维吾尔人经营买卖的时间、开张生意的时间、讨价还价的时间以及展示手艺的时间。
1.经营时间
假设一个维吾尔人与一个汉族人同时在巴扎上经营买卖,他们二人对经营时间的认知恐怕是有差别的——至少在经营时间的起点和终点上是迥然不同的。一个汉族人可能会起早贪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准时营业,按时收工,在经营买卖时始终有着强烈的“时间包袱”,而一个维吾尔人则不然,他们对经营时间有着在汉族人看来是随意,在他们自己而言是恪守宗教操守的认知。根据伊玛目安萨里对穆斯林商人提出的七项法则第五项来看,一个正统的穆斯林商人不应太在意经营时间的紧迫性,“不应过于留恋集市和生意,即不要成为第一个入集市最后一个出集市者,这属于可憎行为”。造成一个汉族人对经营时间紧迫性的在意与一个维吾尔人对经营时间紧迫性的不那么在意的原因,在于二者背后迥然不同的文化指令。一个维吾尔商人在使用经营时间时,受控于其所信奉的穆斯林文化给出的指令,他的经营时间是一种散点模式,这造成了他在经营时间段的任何一个点上都能随意出入,而一个汉族商人的经营时间则是一种位移点模式,这要求他必须把握好经营时间段落的起点和终点。
2.开张时间
仍然是假设一个汉族人与一个维吾尔人同时在巴扎上做买卖,他们二人对生意开张时间和持续时间也有着差异认识。当然,在重视生意开张这一点上,二人完全是有共识的,他们都无比在意第一笔生意,认为第一笔生意决定了一天的买卖走势。只不过,一个汉族商人会将第一笔生意的顺利成交归结为运气,而一个维吾尔商人则会将其归结为胡大的示意。紧接着,二人在开张时间段落的差异便会体现出来:一个汉族商人会认为生意开张了,便需要更加勤奋地做事,他会积极地活动起来,例如勤奋地记账,积极地张罗生意,表现出做事的状态,以示开张。而一个维吾尔人则表现得不那么勤奋,他甚至根本不会去记账,至多数数钱,他会有时冥想静坐,有时观望、祈祷,在他看来静坐祈祷也是一种做事状态,也是对开张时间的重视。毫无疑问,决定一个汉族人和一个维吾尔人对开张时间差异认识的仍然是其背后不同的文化心理。一个维吾尔人在分配自己的开张时间及其持续状态时,更多会考虑对真主的敬重,他的开张时间是一种静态的时间模式,在处理时间的流逝这一点上,他通过静坐、祷告向真主致谢,表达了对生意的重视。而一个汉族商人对开张时间的分配则是一种动态的时间模式,他认为只有动起来才能证明自己在做事,不辜负辛苦开张的好运气。
3.讨价还价时间
在巴扎上,一个维吾尔人与一个汉族人对议价时间的处理也是完全不同的。通常情况下,汉族人的议价模式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买卖双方都有各自隐蔽的高限与低限,卖方毫无疑问是要索要高限的,买方则自然而然要追求低限。讨价还价的时间里,双方都执着于发现对方价钱的上下限,同时又不暴露自己可以接受价钱的上下限。所以,一个汉族人的砍价时间是双方优越感的博弈时间,在意的是最短的时间内是否能多砍几成。而一个维吾尔人在议价时,买卖双方是没有上下限的,他们更多地是依靠彼此共识的环境条件来判断,或者说更多依赖对买卖商品在巴扎中的一般实价来判断。对于全民信教的维吾尔人而言,合法的买卖一定是接近实价的买卖。《古兰经》中对此有明确规定:“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暴利。”穆罕默德也强调:“买主与卖主只要未离开行商之处皆可自己经营,倘若他们在买卖时说实话,不隐瞒商品和钱币的缺陷,则他们的买卖定会兴隆。倘若他们隐瞒商品和钱币的缺陷,买卖时讲假话,兴隆的买卖定会毁掉。”([埃及]穆斯塔发编:《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与此同时,穆罕默德还特别提醒信众,凭撒谎来使其货物畅销的商人,在复活日不会蒙受真主的惠顾,真主也不会给他纯洁,而且还将遭到痛苦的惩罚。
由此来看,一个汉族人在讨价还价的时间中享受到的乐趣和展示出来的智慧,在一个维吾尔人看来则会是全然相反的一面,甚至会感到置身险境。对于一个汉族人而言,巴扎中讨价还价的时间恰巧是接近真实的时间,买卖双方在议价时持续的时间越长,则越能接近商品真实的价格。而这种观点在一个维吾尔人来看则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对他们而言,讨价还价的时间有类似欺瞒的时间的嫌疑,买卖双方在议价时持续的时间越长,则越背离商品原有的价格,甚至会完全超出卖方对商品行情的认知,即越接近一种虚假的时间。
试想当一个汉族人将自己议价时间的模式带入到一个维吾尔人的议价时间模式中,便会导致一些麻烦。在巴扎上,经常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当一个汉族人在购买维吾尔人的商品时,往往在没有进入议价时间时,就会被要求接受商品的成交。在汉族人看来,他不过只是对有兴趣的商品张口问价,距离其真心购买还缺少一个讨价还价的时间准备。而在维吾尔人来看,问价却不购买本身便是不真诚的表现。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存在于汉族人与维吾尔人之间,而是普遍地存在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需要指出的是,在他们的讨价还价中(一个维吾尔人与一个汉族人),涉及到的不仅是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更是一种时间与另一种时间的交换,一种隐形文化模式与另一种隐形文化模式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时间越过货物成为了商品自身,双方争夺的都是时间而非货物。
4.手工艺时间
巴扎日上还存在一种隐形的可被交换的时间,即维吾尔人手工艺品制作的时间,或者说巴扎上的维吾尔人展示传统手艺的时间。巴扎上有大量的维吾尔人的手工艺品,在这些工艺品的现场制作中,工艺品内含的传统时间被创造成了一种商品得到了展示,并具备了可以交换的价值。我们经常在维吾尔人的巴扎上看到类似的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如玉雕、腰刀、日用铜器、木器、陶瓷、首饰、花帽、地毯、艾德莱丝绸等种类繁多的手工艺品。这些工艺品(包括维吾尔人的传统饮食)受惠于一种维吾尔人的民间的传统时间,或者说过去时间,并在巴扎的现在时间中期待得以向未来时间兑现现实利益。也就是说,保留在这些手工艺品中的过去时间变成了现在的维吾尔人兑现未来的商品。简言之,现在时间里手工艺品的买卖实则是一种过去时间与未来时间的交换。在这种交换行为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维吾尔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换言之,在维吾尔人手工艺品的交换中,起控制作用的是传统时间里的文化身份,祖辈的文化遗产。过去构成了对等待未来利益的一种控制。手工艺品里封存的过去时间,或者理解为消逝的时间实际上参与了“现在的未来”,即过去由于现在的需要而超越了未来、控制了未来。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保留于现在的过去是我们的前辈超越的遗产。思想、传说、文字记载、神圣建筑物和艺术;发明、宇宙论和机构;如今已经覆盖地球以及周围空间的通信网络;全部都是过去的人们与其未来关系的丰碑。通过它们,我们的前辈超越了其自身的存在,超越的方式不同于保存记录,不同于只是拥有过去。最好把这种过去理解为过去的未来”。
巴扎与多重时间
以上我们对巴扎中隐形时间的探讨都是在一元时间集合里的探讨,即对一次只做一件事的时间集合里隐形时间的分析。然而,在巴扎日,还存在一种多重时间的集合,即一次做多件事的时间集合。打个比方,如果说巴扎上的一元时间集合是一种专心的时间集合,那么巴扎上的多重时间集合则是一种“不专心”的时间集合。其实,巴扎日的产生就是一种多重时间集合的结果,最初巴扎的出现正是维吾尔人做礼拜之余顺便集会一下的产物。
当巴扎上的维吾尔人在使用一元时间追求利益之外,若是还能关注一下有多少时间可以被分配于交际、休闲、分享、期待时,就会产生多重的时间。因而,相对于一元时间而言,多重时间是一种空闲时间,是一种期待被获得与拥有的时间,这种时间能够在单一时间集合之外再次划分巴扎中维吾尔人的群体、层级和角色。具体来说,这种时间的多重形态在巴扎上的主要表现为闲聊时间、“背地克”时间和“档奇”时间。
1.闲聊时间
巴扎上经常可以看到几个维吾尔人聚在一起,三三两两,闲话家常。甚至有些时候,店主可以在经营时间的关键时刻,挤出时间来消磨。当一个汉族人正在为一天计划要完成的交易量费尽思量时,一个维吾尔人可以在开张生意之后便投入到闲聊或者交际的时间中去。对于一个汉族人而言,他会很容易接受时间便是金钱的观点,这是因为,他笃信在同一时间内只能做好一件事情,这种认知使得他在集市上只能专心关注于自己的生意,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一个集市日的计划去安排行事的时间顺序,尽量避免分散注意力导致将做生意这件单一的事件分散来做。他会认为工作便是工作、休闲便是休闲、聚会便是聚会,一如上文分析过的,时间的线性特征在他做事的进程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对他而言,时间会因所从事的活动不同发生断裂,这种时间观念的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单一时间文化。与之相反的是,在一个维吾尔人来看,他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可以顺便完成多件事情,并且这些事情在同一个时间集合里都能和谐相处,互不干扰,时间在他这里没有发生断裂,只是由一元增生为多重形态,这种时间观念的背后隐含的恰恰是一种多重时间文化。巴扎上维吾尔人的闲聊时间,观看斗鸡、摔跤等娱乐时间恰恰反映出他们时间的多重性。
2.“背地克”时间
维吾尔巴扎上有一类专门为说和价钱而存在的人,叫做背地克(bedik),他们斡旋于卖者和买者之间,调节价钱,促成交易。需要点明的是,“背地克”绝不同于“托儿”,同样作为买方与卖方之间的中介,“托儿”无需调和买方和卖方的关系,他存在的价值恰恰体现在离间双方关系上,而“背地克”的存在则是为了调和买卖双方的关系,并以此来获得自己的优越地位。也就是说,在巴扎上,“托儿”是不荣誉、不合法的一种身份角色,而“背地克”则是一种可以合法存在的角色。如此说来,巴扎日上专门有一种时间是属于“背地克”时间。这种时间在坚持单一时间文化的民族看来也是十分奇怪的,因为单一时间文化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文化,或者也可以说是追求效率的文化。持这种文化观念的人会认为“背地克”时间在巴扎时间里是多余的一种时间,是减低效率的时间。
但是维吾尔人却认为“背地克”时间是增进族群情感、强化族群向心力的一种必要时间。《古兰经》中经常被穆斯林引用的一句话便是:“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还要求:“如果两伙信士相斗,你们应当居间调停。”“信士们皆为教胞,故你们应当排解教胞间的纷争。”由此可见,对于穆斯林而言,任何利益冲突都不能离间信众或者说族群内部兄弟姐妹间的感情,一旦出现利益之争,同族人有义务进行调停,帮助排解。从这个角度看,“背地克”在维吾尔巴扎中的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背地克”时间之于维吾尔巴扎日而言也便是一种必要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穆斯林巴扎里,有一类被称作“马赫塔西卜”的人,即市场监督官,他们能佩剑出入巴扎,他们的作用在于监督巴扎中是否有有违伊斯兰教教义的行为,并代理真主执行劝善戒恶的职责。这类人在巴扎中的时间与背地克在巴扎中的时间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展开一种共享伊斯兰教义的时间。他们的角色身份也具有趋同性,都是以宗教教义为依据,通过这种代真主而言的“压倒性的施予”来获取自身的优越地位。
造成以上两种对待“背地克”时间截然不同态度的原因恐怕在于,坚持一元时间文化的人从事的是一种“我”的生意,而维吾尔人的文化强调的却是一种“我们”的生意。“对于伊斯兰教来说,金钱并不违反道德或被鄙视,但它应该有利于社会。事实上,《古兰经》提出金钱和地上所有的资源一样都属于神,人类的责任是让它为集体带来成果。带利息的借贷是被禁止的,资本收入则不是,因为它要冒一定风险:生产性投资是被鼓励的,因为它为增加财富和福利作出贡献。会被谴责的是,把神的用来给集体的金钱积攒起来或挥霍掉。致富是正当的,甚至是被鼓励的,但条件是要创造财富(因此禁止投机和纯凭偶然的赌博),而且致富不能是个人行为,应该是集体的。”([法]米歇尔·苏盖 马丁·维拉汝斯:《他者的智慧》)
3.“档奇”时间
维吾尔人的巴扎日还有一种属于“档奇”(dangqi)的时间。“档奇”是档(dang)的主人,而“档”则是维吾尔人在巴扎上存放畜车的地方,相当于百货商场里的地下停车场。“档奇”时间也就是档奇”们向赶巴扎的人收取费用的时间,很多“档奇”们自身在巴扎中也另外拥有摊位。“档奇”们在巴扎中也是一个阶层,他们拥有合法的地位,比如,在巴扎上多年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自然而然具备了在他(她)的名字后可以加上“档奇”的资格,如买买提“档奇”、迪丽努尔“档奇”等,这就跟工作多年的教师可以获取相应的教师职称的道理一样。与此同时,这也表明“档奇”时间会是一种对未来利益要求回报的投资时间,这种投资将“档奇”时间变成了一种资源,一种值得等待的时间。“档奇”们在这种必须经历的时间中,将曾经使用过的时间转化成了“一种体现服务价值的资源”,换言之,未来在“档奇”们等待的时间中取得了现实的合法地位。
巴扎日中的“档奇”时间是一种可以期待,并在将来可被拥有的时间。“档奇”的合法称谓赋予准“档奇”们一种理想远景,使得他们愿意等待,愿意在巴扎日的交易之外分配出一些时间用来等待。这种等待正是魏格特曾经指出的一种“文化赋值型等待”,它通过把现存的权力有效化、合法化,进而划分出一个社会的阶层,实现时间对社会的重组和分化。
总之,巴扎的多重时间集合与单一时间集合间最大的不同便在于,多重时间是一种闲余时间,是单一时间的剩余价值,它与商业利益无关,而与人们的心情满意度有关,是可以选择、可被拥有的时间,因而也是一种相对超前的时间。
巴扎上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时钟和日历时间的范围,也超出了我们一般概念理解中显性的时间范畴。在巴扎上,“时间是一个生活事实,并且是存在之根本。”(参见景天魁 朱红文主编《时间与社会理论》)它几乎涵盖了维吾尔人日常生活与文化心理的全部要素。在这个汇集了单一时间与多元时间集合的时间里,同时又散落着许多隐形的时间子集,它们所体现出的规约性、受控性与多重性深刻地折射出维吾尔人独特的巴扎文化:一个混杂了单一时间文化与多重时间文化的文化,一种族群共同体文化以及教义共享的文化,一种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相互交织,个体文化与族群文化彼此交融,过去、现在和未来可以并置的文化。
维吾尔人的巴扎日由于其本质是对周期性时间过程的坚持,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一种逝去时间的回溯,这也无形中反映出维吾尔人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厚古薄今——即通过将巴扎日本质化,实现对无法回避的过去时光的缅怀,并总是试着参照过去意图去重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文化无疑起到了主导作用。对此,阿拉伯文化学者格扎维埃·勒巴克曾做过深入分析,她认为在伊斯兰传统中,“流逝的时间被看做是撒旦为了使我们抛弃我们真正的本质、远离神圣根源并走向遗忘的工具……如何能改变世界而不让世界被扭曲?如何能推动发展而不远离自己的根源?”她还认为“世俗的时间是逃避的意思:正如河流远离它的源头,时间使我们远离我们的根源。与此相反,神圣时间则与世俗时间进行斗争,帮助人们追溯过去,帮助人们想起他的来源,并找回他的根源”。(参见格扎维埃·勒巴克《了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