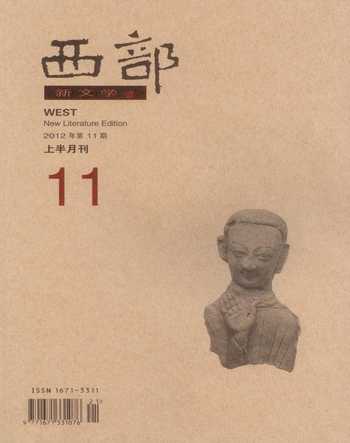飞越大西洋
卡洛斯·富恩特斯 朱景冬
今年秋天圣地亚哥·费尔古松老师逝世时他女儿卡塔丽娜给我们打电话,为了实现她父亲的愿望,他将被葬在英国韦尔斯大教堂里。她还说,希望他的学生和林肯餐厅的新老食客能够把他送到他最后的住所。她不是把这件事强加于任何人。这仅仅是一个友好的请求,一个感人的愿望。我们没法估计会有多少人去为他送行。我们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询问:“喂,你去参加老师的葬礼吗?”再说了,这个时节谁也不会出门旅行,除非是出公差,或者为了及时把自己的墨西哥比索取出来。我们的情况却不同:作为欧洲和美国的建筑学会会员,《建筑法典》的撰稿人,洛杉矶和达拉斯的一些引人注目的住宅,马约尔湖畔阿罗纳城的阿达米博物馆和波兰、匈牙利若干饭店的建造者,我们属于墨西哥的那种从业人员,应该在国外建立一个基地,能够毫无顾忌地随意购买自己的飞机票,而且是头等舱,就像费尔古松老师习惯说的那样:“我只坐头等舱旅行,不然的话,我宁肯舒服地呆在家里。”
可是现在,他要和卡塔丽娜一道旅行了。只是这一次他是躺在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上的一口棺材里。而我们,得首先乘法国飞机去巴黎,密特朗政府建议我们在那里的阿内城堡附近创办一个国际会议中心。那座城堡,不错,本属于一个古老的墨西哥家族:一位浪迹异国的墨西哥人的遗产。此人有时是被流放国外,有时是自愿流亡,有时只是为了完成不局限于祖国本土的职业性的和艺术方面的任务。在飞越大西洋的旅行中,我们一面翻阅一本关于英国大教堂、中世纪的世界旅行和文艺复兴的书(在书中,人的宗教热情和精神推动着人们怀着巨大的努力、迎着比我们遇到的大得多的困难去进行更频繁的旅行),一面回忆十二世纪的僧侣兼旅行教育家胡戈·德·圣维克多的一些名言。对他来说,满意地呆在自己的祖国、在祖国感到舒适的人不过是一个柔弱的新手,而在许多国家觉得舒适的人则达到了一个非凡的高度,但是完美只属于觉得自己能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流亡的人。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敬爱的圣地亚哥·费尔古松老师就只能属于前两种不完美的情况了。而我们,他的学生——卡洛斯·玛利亚、何塞·玛利亚·贝莱斯兄弟,也许就只能和他分享那种不完美了。尽管我们两个很清楚,我们并不是为了不舒服的流亡而旅行: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是去埃雷达德·马特奥斯夫人安排的一个具有悲喜剧色彩的、立有十字架的山丘顶上去;另一个是去一个这样的地方:那里没有一个人,连那里的居民也对它不满意。何塞·玛利亚去的是一个举行圣典的地方,卡洛斯·玛利亚去的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地方。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彼此讲述我们各自的经历。对每个人来说,真正的流亡就是我们离开对方,何塞·玛利亚变成一个远方的“我”,卡洛斯·玛利亚变成一个遥远的“你”。
如果说我们对这段历史能够有所理解的话,那就是在一切地方——格拉斯哥、墨西哥城、弗吉尼亚、维琴察——建造一所房子,从而仁慈地、尽职地或艺术地完成建筑任务。有人将去那所房子里居住。居民们将向建造者们要求麦金托什家族向费尔古松要求过的东西和地下修道院的亲属们向卡洛斯·玛利亚要求过的东西,还有堂娜埃雷达德·马特奥斯向处女和儿童要求过的东西。请你照管我们吧。从现在起请你全力看护我们吧。请你发发慈悲,不要抛弃我们。创造的界限是什么呢?没有一位艺术家不曾在其内心深处想过这个问题,他担心创作活动不是无偿的,不是充分的,而是会在居住在一所房里、读一本书、欣赏一幅画或观看一场戏剧演出的人们的苛求中继续下去。个人的创造天赋会到达哪里呢?从哪里开始和别人分担义务呢?在纯粹的“我”身上消耗的、被取消了的强有力的“我们”的唯一作品也许仅仅是孕育过但从没有产生过的作品。房子就在那里。甚至未出版的书仍然保存在抽屉里。我们贝莱斯兄弟虚构了一个纯粹是设计的、纯粹是臆想的世界,它只是存在于思想中。但是在这种先验论的世界上,却充满了死亡。这就有点像我们分开后发生的情况。
我们丧失了“我们”。现在,当我们在大西洋上空旅行时,我们真希望重新得到它,竭力避免提起发生的事情。卡洛斯·玛利亚从没有讲过他跟着狗穿过新古典主义大门时发生的事情;何塞·玛利亚也从没有提过在堂娜埃雷达德·马特奥斯的小房子里发生的事情。只剩下两件无声的东西作为分开后的经历的见证:一件是看守人赫罗尼莫·马特奥斯的小屋顶上的木头十字架,那是卡洛斯·玛利亚离开修道院时安放在那里的;另一件是作为一种诱惑、一种纪念、也许是因为某种醒悟而被丢在我们家何塞·玛利亚的双人床上的新娘嫁衣。我们的家位于西班牙公园对面的努埃沃·莱翁林荫大道旁。那条大道是我们的父亲修建的,它又干净又美丽,是1938年墨西哥对美国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一个纪念。但是,我们却失去了能够把我们各自的经历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小瓷青蛙。也许现在我们正秘密旅行,去寻找那件既联系着我们对卡塔丽娜的爱(一天下午她在她父亲的浴室里一丝不挂),又联系着摩洛哥大街上的那家秘密修道院的东西。某种东西能够把这两个地方联结在一起,从而也能把两种经历联结在一起吗?对我们来说,麦金托什在格拉斯的家没有什么意义。
也许在浏览英国的大教堂的图片时,实际上我们是在头脑中追忆我们在跑马场移民区的真正家庭。这仿佛是为了补偿因寻找一个暂时的藏身处而从墨西哥飞到巴黎花的十三个小时。然而,在运载我们的铝质母腹中却存在着比我们成长的、一动不动的大地上的家庭中更危险的事情。
一位我们认识的女士、墨西哥国的副部长,手里拿着一瓶用沾湿的餐巾纸裹着的马提尼,紧张而又无精打采地在头等舱的通道上踱步,这样抱怨说:“我觉得我是在这架飞机上出生的,我也将死在这上头。街角到了,下车。”她叹息了一声,一口气把鸡尾酒喝光,然后用嘶哑的声音说,“这是在这儿下车的唯一东西,我的同胞们。”
说这句话时,她望着我们笑了笑,我们整齐地坐在那里,喝着我们的饮料,拿着我们的艺术书。她指的是什么呀,我想。她大笑一声,把后背转向我们:她特地为长途旅行穿了一件阿迪达斯牌粗呢运动上衣、玫瑰色长裤和一双网球鞋。我们望着韦尔斯大教堂的剪刀形连拱走廊的图片,那幅图片虽然不是最精彩的,但却是最引人注意的。而教堂中殿深处的两个石孔展现的透视图,可以和一架飞机的内部结构相比,但也令人想到原始山洞:这是既保护我们但也监禁我们的藏身处的两个入口。波音747的马达声让人什么也听不见,像一只生活舒适的猫发出的最大叫声。家庭是藏身处,而不是牢房。在我们家里,我们的父亲教会我们并让我们喜欢使我们变得幸福的东西:建筑、世界和它的两个领域:自然界和人类。我们的父亲辞世后,我们掌握了圣地亚哥·费尔古松为我们重上的课程:我们不能重新回到纯粹的自然中去了,因为它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为了生存下去而开发它;我们命中注定要采取人为的办法,注定要伪造一种不让我们遭受折磨、保护我们而不吞噬我们的大自然;这就是建筑学的使命,或者说复数建筑学的使命。我们一面议论一面迅速翻阅着约克和温切斯特、伊利和索尔兹伯里、达勒姆和林肯的光荣形象,这个世界的王国中最光荣的名字。有着很长中殿的大教堂,任何流亡和信仰的游行队伍都可以从中殿通过;讲道台既宽敞又让人感到紧张,在台上可以练习世界上最灵活和最富创造性的演说,那是用英语进行的演说;然而在这种光辉的建筑旁边,展示着样式繁多的、朴实的、雕塑般的高塔的轮廓,庄严而好客的坎特伯里寺院和奇切斯特寺院的宽大手臂。满载着灵魂的豪华远洋轮船,诗人奥登写道:具有石头般的船头。
这是圣地亚哥·费尔古松为死亡而做的选择,因为如果决定他的肉体死亡的时刻不掌握在他手里,那么,确定他的精神死亡的权利当然应该属于他。他总是对我们说,这种死亡恰恰是生命的来源。没有一种生命不是来自死亡,没有一种生命不是对我们之前的死者的补偿。艺术家或情人知道这一点;其他人不知道。一位建筑学家或一位恋人十分清楚,他们的生命是死去的人给的,所以他们懂得爱,并以那么高的热情进行创造。他们自己的死亡则是那些加快感受我们以我们的前人或后人名义所作的事情的生命的来源。这是我们贝莱斯兄弟为我们敬爱的圣地亚哥·费尔古松老师所做的安魂弥撒。如果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只剩下对我们的私人大教堂的怀念,那么它就既不是山洞,也不是飞机,而是一所房子,一个家庭,里头堆放着童年时代的东西、玩具、冒险图书、对我们来说小得不能穿的衣服、长毛绒熊、没有气的足球照片。我们说过,我们的当建筑师的父亲路易斯·贝莱斯有一个外号叫“底片”,因为他的皮肤是黑色的,他的头发是白色的,这样,在看他的照片时,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应该恢复他的本来面目——白面孔、黑头发。相反,我们的母亲是金头发,白面孔,她的底片肯定全部是黑色的,也许没有做任何修饰,只有眉毛仔细地进行了描绘,再就是嘴上的唇膏。她在困难地生下我们这一对双胞胎后死去。我们,是玛利亚·德·拉·莫拉·德·贝莱斯的儿子,所以我们取了我们死去的母亲的名字。
女副部长又打断了我们正在做的和正在思考的事情。她用快活的声音优美地喊道:“快起来,我的同胞们,把窗帘拉开吧!我们就要到彭哈莫了,它的炮塔已在那里闪光了。就是这座城市,由于有黎明的光辉和我们脚下圣米切尔山修道院的景色而让我们眼花缭乱。”
我们从布列塔尼进入法国,将在巴黎逗留两天,星期天在韦尔斯相会。我们兄弟俩彼此望了望,都想起了卡塔丽娜。她正在那里守着父亲的遗体。
“卡塔丽娜正在那里和她父亲的遗体一起等着我们。”何塞·玛利亚说。这时,放荡的女副部长醉得面红耳赤,还在唱《现在》这支歌。无疑她是想用一支她年轻时代的颂歌庆祝她来到了巴黎。
“她丈夫呢?”卡洛斯·玛利亚问,“华金·梅尔卡多呢?”
“他的意见不重要。卡塔丽娜和她父亲的意见重要。”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闭上你的嘴,夫人。”
“你说什么?没教养的,我要调查你。”
“那你就调查把。我决不服从你那个该死的官僚集团。”
“好吧,她的意见不重要。她父亲的意见重要。”
“他死了。”
“可是你和我没有。我们两个,她会选择谁呢?”
“她父亲是我们的情敌,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我一直知道那个下午卡塔丽娜曾和谁做爱。”
“现在你和我不应该成为情敌,你同意吗?”
不知道他们二人是谁要求对方同意。这时飞机已开始在夏尔·戴高乐机场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