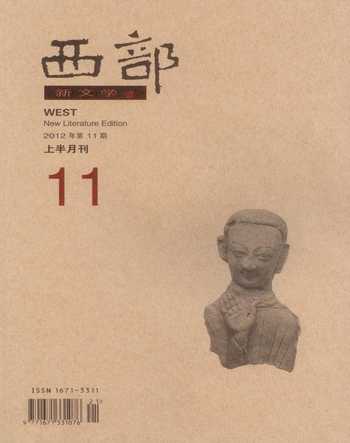光影手记
郑亚洪
它生来为了阳光存在
一切起源于一盘水果。Y买了杨梅、荔枝、李子等水果放在玻璃茶几上,我把一颗杨梅放入嘴里,在杨梅的甜味与酸味碰触到舌尖的瞬间,我想起去拿照相机拍照。外面的阳光刚刚把房间唤醒,书呀,唱片呀,樱桃木地板呀,窗帘呀,差不多在室外逆光下苏醒过来,蓝天在屋顶上方显露出来。早在多年前,我刚得了数码相机,给房间的角角落落拍照片,如音箱、兰花、书架等都成为被摄对象。我不想拍出气势恢宏的画面,那不是我的所长,我喜欢一种偶遇的阳光打在事物表面,玲珑剔透,光滑嫩洁。在这一瞬间前事物不过普普通通而已,下一瞬间仿佛换了面孔,尤其是被相机定格的画面,连阴影部分也呼之欲出,分外可爱起来。你等了那么长时间是为了等阴影到来,密实的、有重量的、生气勃勃的阴影,它生来为了阳光存在,为了它而到来。在未摁下快门之前,事物存在着,书在书的位置上,地板归地板,谁也不见得有融为一体的倾向,可是有了光的投射,便有了阴影,事物就变得神神秘秘起来,阴影产生出叙事,将有一个故事发生。你不知道里面隐含着什么,会有什么东西会发生,你等着下一个即将发生的瞬间,朝它们举起相机。咔嚓完毕后,看显示器上的画面,不像刚才的“实景”啊,有点油画般的效果。你不信,地板照样是地板,书照样是书,没有一样见得神奇。谁在说谎?说谎的是你的相机!有人把小说家称为说谎的人,我觉得拍照与写小说一样,你看“风景如画”的照片、“油画般”的照片、“幻影重叠”的照片,人间有它们的真实吗?哪一个不是在说谎呢?说谎的艺术很可爱,它让人暂时忘记了身边的困扰。
有一年夏天,我在新疆乌鲁木齐游览观光,完全被伊斯兰教的建筑所吸引,拿着卡片机拍遍了乌鲁木齐可以找得到的清真寺。就在与它告别的时候,一座典型的伊斯兰教风格的清真寺出现在我前面,红砖白底绿尖塔,四座笔直向上的宣礼塔围绕着中央穹形大屋顶,屋顶上方镶嵌着明月和星星。我如见到真主安拉般地满心虔诚,虽不信教,依然被它独特的气质所打动。为了拍到好视角,得爬到另一座屋顶上去,宣礼塔下的一位维族老人居然同意了,当我踩在软绵绵的毛毡屋顶上时,心中嘀咕,别让我摔下来,我必须和星星,和月亮、清真寺一道去做。拍完了,这照片就永留在我书房里。
中和巷
五年前,刚有卡片机,独自一人拿着它在巷子里试新机,对老旧的房子格外感兴趣,原来我住的小镇上还有许多可以怀念的旧事物。有些破败不堪,有些看上去丝毫没有美可言,可它们到了镜头底下就有了非凡表现。拍下来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实际存在的,但它们不是我看到的东西那又是什么呢?难道实物与照片之间存在另一个非常态吗?就拿这条叫中和巷的古老巷子来说,我不知道几次走过了,这次当我拿了单反刻意去拍地主屋的时候,情况都变了。四点钟的太阳过滤掉了很多事物,留下在相机镜头里善于表现的东西:浮雕、门廊、墙头草、剥落的墙灰、“办证”字样、掉了漆的窗、芜杂的电线、太阳投下的影子,没拿相机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注意。巷子太窄了,拍不了整座地主屋。我敲开巷子里的一家住户,想说服他们让我到阳台上去拍,那人毫不犹豫地拒绝,只好作罢。一个老人看我拍得如此投入就问,你是报社记者?我笑笑说不是。另一个留有艺术家气质长发的年轻人似乎懂我心思,退在旁边不影响我拍照,我报以微笑。
造船厂
照片上的事物越新奇,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就越大。造船厂集新奇、视觉冲击力为一体。其一,造船器械庞大,几十米的龙门高高竖立,一律单颜色油漆,橙黄的、海蓝的,一只悬吊的机械手在高空飘来荡去,你看不见操作的人,不由得畏惧(因看不见人而产生的畏惧心理),所以造船厂能撼动人心。其二,造船厂办在海边,地域空旷,海面场景同样可以摄入,比方说洋面上行驶的货船,海滩上的花贝壳。在造船厂拍摄,既有宏大叙述,又可捕捉到微观细节。乐清造船厂靠海修建,打造轮船为业曾辉煌过一段时间,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时候黄华一家造船厂拿来上百页的英文说明书让我翻译,光一个零件就费了千字说明。乐清造船厂多为民营企业,如南岳的中欧造船厂、黄华的田欣造船厂,在船老板看来,造一只船的利润空间远大于柳市的电器行业,他们忽视了造轮船跟海洋气候一样瞬息万变,尽管人类出海几千年依然捉摸不透海的脾气,今日出海风和日丽,明日难说不来场暴风雨。造船厂造在海边,其命运完全决定于陆地,2008年的金融风暴给造船业以致命的打击,一艘轮船完工周期漫长,获利空间远抵不上物价上涨因素。在中欧造船厂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巨大的空壳企业,黄华田欣造船厂却是另一番繁忙景象,他们围绕一艘万吨级轮船像蚂蚁围着饭粒模样焊接船体。我时常在摄影画报上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头戴蓝盔的工人正在给一艘轮船上油漆;或者工人拿焊条对准轮船铁板焊接,他的前面火花四射。摄影家捕捉到了诗情画意,加以大肆渲染,让看照片的人觉得造船业的工人是幸福的。在田欣造船厂看到工人爬上操作台工作,忍受太阳曝晒,当我举起相机的时候,我其实是将粗砺不堪、桀骜不驯的场面凝固下来,我的EOS镜头充当起打手的范儿,努力让被摄场面变得规规矩矩。从这个角度说,难道我不也同样走了画册摄影家的路吗?
大烟囱
大烟囱成为历史已有多年。它立在西门城乡结合部,结合部为农村包围城市处,城市脏乱差最集中、城管部门不愿意管的地方,也正是这个原因废弃许久的大烟囱才得以在西门继续生存。话说回来,二十多年前的1980年代语文教科书上画着工厂、大马路、戴安全帽的蓝衣工人正是学子们追求的城市风貌。去年冬日的一个下午,我偶然看见大烟囱,几十丈的高度,黄褐砖瓦烧制一体,烟囱里没有烟雾喷出,光这块头就让人产生时光倒流的感觉,一下子回到了语文教科书。当天天气灰蒙蒙的,灰蒙蒙的烟霭和背后大山的影子就这样包围着大烟囱,我爬到了附近一居民平房的屋顶,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对准它,光线的原因始终拍不出好片子。早上约摸五点半光景,我醒来,想起了西门的大烟囱,立即驱车,赶在太阳保持着早晨的热度之前。我在西门一带找来找去竟然找不到那大烟囱,原先的位置上新楼房林立,莫非大家伙被拆除了不成?我不死心,在西门老氮肥厂里找到了它的替身,也是个大烟囱,但此烟囱绝非彼烟囱,到底是哪一个下午造成的美好印象,在我脑海里已定格为“西门大烟囱”。我在氮肥厂四周转悠了很久,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拍摄,无奈四周的楼房建筑粗鄙凌乱,连双脚都难以搁下,只好作罢。
洪宅下的老人
我完全出乎意料地来到了集贤巷洪宅。洪宅共有前后两进大屋子,前退屋在千秋巷,后进屋在集贤巷,洪宅横跨了南北两条巷子。巷子里的一位老人告诉我说,每当我拿起相机的时候,会吸引很多人,尤其在清晨这么早的时候,问我的多数为老人,一是他们起得早,另一个原因,除了老人外,年轻人不屑于住这么老的破旧房子。有人上前来问,你是旧城改造的吧。他们几乎想都没想就问,因为上半街的一些房屋曾在旧城改造的讨论中,后来改造不成了。也有人问,你是搞文物的吧?我看你拿着相机,专门找老房子。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很有耐心地说,我随便拍。或者说,我没有什么目的,拍着玩。我这样回答是为了让他们对我不起戒心,我可以随意地进出他们的房屋了。在乐清老城,从一条巷子出入到另一条巷子,一个颇有面积的井字形院子朝你打开,你以为走错了地方,来到了他们家里,其实这个空间既是他们的生活空间,又是公共场所:按照叔伯排行的顺序依次排列着上间、厢间、边间,地位井然有序,一副井水不犯河水的模样,生活得其乐融融。被单拿到院子里晒,锄头、扁担、镰刀、畚箕、扫把、筛子等农作工具在地上放着,在墙上挂着,你觉得它们混乱,生活的味道却扑面而来,他们的院子不像商品房里藏着掖着的。女人捋起衣服奶孩子,陌生男人进来也不躲闪。我到的宅院主人姓洪,宅里的一位老人告诉我洪禹平先生年轻时在厢间里住过。在洪宅大屋檐底下坐着两位老人,从年龄上看阿婆稍长阿公几岁,所以她看起来比他迟钝一些,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说话的内容与昨日发生的事有关,如子女忘了带给她衣服,忘了吃降血压药丸,等等。刚刚过去了一夜,他们谈论起来如同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他们问问题或回答问题的时候语速缓慢。他们这样说着话的时候,院子里的上午的阳光一点一点地盛大起来,屋檐投下来的阴影也越发浓重了,连滴水瓦片的瓦齿都在地面上投射了个遍!在这个当儿上,另一位老人在照屏下的一个小菜园里拾掇着什么,这位老人比屋檐下坐着聊天的老人年纪要小些,她弯腰下去,以致我看不清她的脸孔,我不知道她的犹疑的影子是深埋在泥土里,还是已被太阳晒干了。
徒步穿过北大街
北大街是乐成镇唯一一条没有被改造的街道(原先有四条街:北大街、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最早是一条商业化街道,十年以后东大街西大街也终于没落了,向“旧城改造”投降。被迫?也许自愿。北大街起始于南大街最北的供销社,止于公安西路上的人武部大院,一条宽约四米、长五百米的街道,两旁旧式民居,有的是木制结构,因年岁已久也完全倾斜了(其中有两间被一场大火吞噬过仅留下烧成黑炭的梁柱),有些牢固点的是青砖建造的,显示出五六十年代公社的风格,在乐成镇算是有历史感、沧桑感的建筑了。
这一次我穿越北大街往北去毫无目的,它与我二十七年前第一次穿过街道到达乐清中学有何不同呢?我至今回忆起当年从南大街的印刷厂出发,向北经过消防队、邮局、医院、新华书店、国营理发店,再向北穿越北大街是在一个下着雨的夜晚,在现实中它没有下雨,在我的回忆中,我的第一次徒步穿过北大街永远笼罩在夜和雨水之中。独自一个人的夜晚,为了去一趟新考入的中学,我在北大街长长的屋檐下走着,手里举着雨伞,时不时地闪进伞内的雨水、脚底下石阶上积累起来的雨水很快弄湿了解放鞋。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到达乐清中学,它在西山脚下,学校很大,有很多新奇的建筑。我在乐清中学念了六年书,一般从南大街转入环城西路,较少走北大街,因为那里拥挤,现在的北大街仍然拥挤、纷杂,有很多商铺,这些商铺往往就是北大街居民的住宅,他们靠做点小本生意来维持生计,在繁华的南大街看来这些店铺那么不起眼,有些店铺一天到晚没有一个顾客光顾,店门口坐着几位老人,在太阳光和凉风中打着瞌睡,他们剩下不多的年月在幽暗的北大街中度过。我在南大街的印刷厂住了八年时间,在东门住了二十二年时间,四条街道北大街最少接触,倒常常沿着金溪银溪河畔走,金溪银溪自北向南分列在北大街两侧,两条溪流中间民居繁衍。北大街东侧分列着后双箭巷、中元巷、千秋巷、太平巷、开元巷、担水巷,在西侧分列着广善巷、箫台巷、崇贞巷、仓桥巷、迎合巷、崇礼巷、拦诗巷。每一条巷的名字朝代味特浓,从民国上溯到清,到明、元,进而宋唐南北朝,最后抵达王子晋时代乐清古县城发生的山系——箫台山。如果你赶在傍晚时分从北大街巷子里走过,你会听到点灯的房子里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扒拉着米饭,他们的厨房对着巷子开,你往往见到这样的情景:一男子吃过晚饭,心满意足地端着一个盛了清水的陶瓷碗往嘴巴里灌水。九十年代以前北大街一带居民称为最本土的乐清人,他们说乐清城关话,乐清话土音里总有一个a和e的音(汉语拼音字母念法),他们把“书包”说成“书ba”,“教室”说成“gase”,如果说话的人是年轻女子,她们带了城关人特有的傲慢气质,说起乐清话来把每个字咬得很准,吐字清晰,像县府里常有的机关作风一样。这样说话的人一定是正宗的乐清城关人,很可能来自北门,就是北大街一带了。九十年代以后城关的重心向南移动,城关以外的人口大量流入,白象人、柳市人、虹桥人、大荆人纷纷入住乐清,他们的方言混杂在乐清话里,乐清话渐渐失去了好听的a 和e的音,但你若在北大街随便哪一条巷子里一站,满耳a和e的土音又回来了,不过说乐清话的大多是上年纪的老人了。有时候,我常想,为什么北大街不能像有些城市的街道对城市产生影响呢?如杭州的清河坊,南京的中山路,上海的淮海路。说穿了北大街乃一条衰败了的街道而已,它连一座值得留恋的建筑都没有,破落相的老房子在时间之河里越发不堪。我记忆中在北大街尽头有一座老教堂,便赶去看,教堂完全翻新修建,连一点宗教的痕迹都没有,对面有一座民居改造成的佛堂,基督和佛仅仅隔了四五米的距离!这在小说或电影中不可思议,在北大街却完完全全存在,带了点荒诞的味道。存在得很有理由,因为佛堂表面涂了很扎眼的黄金颜色,似乎向对面的教堂示威。走完教堂和佛堂,北大街结束了。到夏天开始的时候,整条北大街在大太阳底下暗淡了许多,我想着那些倾斜的老木屋在太阳光的暴晒中变成深灰、榫头般老旧,我想象着它们会随时着火,城市上空突然升腾起来的火灾警报声,它们是不是预示着北大街朽木上的霉味在腐烂,连同我的过度的担忧、耗蚀和惊惧?
龙舟
龙舟成为摄影常见主题大概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龙舟是项水上运动,既见风景,又见人,动与静相结合;其二,龙舟属民俗活动,一条河流,几十条龙舟,万人空巷,不啻于一次民间狂欢。我在端午节那天曾正儿八经地拍过龙舟,都不满意,因为岸上看龙舟的人多,当局为防止观者不慎掉入河里,拿了竹栅栏把河道两岸封了个严严实实,连个立足点也找不到。吃过了端午粽子和酒,划龙舟者一个个卯足了劲儿,准备在水上大显身手,龙舟咚咚咚咚一路飞驰,场面虽大,却乱。我倒有一张拍于端午前一个星期的照片,颇感满意。那天下午,我从别处拍照收工回来,一只龙舟行于水上,舟上约摸二十人左右,他们大概拉出来训练的,服装就不那么统一了,有些人穿了背心,有些人索性光着上身,使劲儿操桨的人不多,有几位举桨在水中,怅然望着岸上的人。总而言之,这是一支军心涣散的龙舟队,连锣鼓敲起来也那么有一下没一下的,我举起了相机,连光圈速度都来不及调试了。我举起相机对准他们,龙舟上起码有一半人回过头来探望岸上拍照的我,他们似乎在意了,锣鼓声整齐了许多,划桨力度加大起来,船舟飘一般飞驰。照片拍下来后我拿到电脑里试看,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是当天傍晚时分的光照合适,太阳光打在划龙舟人身上,连他们的手臂肌肉都显示得清清楚楚,用力的、松弛的,毫发毕现;岸上其他景物都安静下来,河面更加安静,看不出来是片水域,却恰到好处地将龙舟反射到河流上。我见过不少摄影家拍下的龙舟场面,不是太刻意表现其动作规划整齐,就是水花四溅,人物过分虚,他们就像到了舞台上涂了浓脂的丑角,看见的不是活生生的脸孔,而是死去的人。
这里,黄昏边,我开始
光从晚六点开始好起来,而且越来越好。光的好,从单反角度来说,就是柔软。大太阳底下光太硬,刺眼,不过大太阳也可以出光影效果,当作别论。周三上白云尖以来,已连续三天拍云,周四下午五点钟在云鲤路上,周五到洞头拍云。台风“米雷”今日下午北上浙江擦海而过,它没有带来暴雨,倒给天空造就了辉煌的云,抓住这个台风时机,下午再上茗山逐云去。三点到半山腰,边走边拍,停停走走,这过程云也跟着变化,开始时大团乌云纠结,大有暴雨一场的气势,到四时西北方向原先有个蓝色天眼似的“大洞”越来越亮,太阳时时从云边上探出头来试探台风,太阳出来的时候,抱团的乌云就被打散了,墨黑的变雪白,雪白的变成水汽散开飘走,任何强大的云团都敌不过太阳。到茗山顶,风一下子刮起来,从四面八方吹,人被吹得东倒西歪,相机被风刮得差点脱手飞去。与风搏斗了十来分钟,风渐渐小了,茗山对岸的各色山脉也换了姿色,暗紫的变成了深蓝,太阳出没在西北边的云层里,天空的油画效果浓烈起来。我来到了小天坛底下,上次拍“空椅子”就在这里取景,一把椅子摆在朝向对岸山系的走廊上。现在走廊堆满了工地上的杂活,铁锹、沙土、编织袋、瓦石,整个一大工地的模样,令人欣慰的是一辆小手推车停在了上次的位置上,从云层间出来的阳光也那么准确地投射在了地面上,除了环境杂乱点,此情此景几乎是去年“茗山空椅子”的翻版。上帝有时候垂青于重复,不过换了个布景而已。我感叹。从茗山上下来,柳川平原变得大好起来,一半在阳光下,一半在阴影里,随着天空云层跑动或变化,柳川平原的阳光和阴影部分也在移动,田野倒灌了河水,阡陌交通,美舍俨然。
下到地面后,太阳照样热烈,台风“米雷”估计北上日本海了,我们再去七里港逐云。造船厂单反过几个回合,港区码头倒头一回来,从万吨级轮船上卸下的集装箱从地面一直堆积到了天边,庞大的集装箱顿时引起了好感,因为看着它们新鲜,箱体五颜六色的,用各式英文字母标识。它们堆在海边,海是另一种巨无霸,广袤而无垠,如果失去了作为衬托的轮船或码头,单一的海枯燥得很,偶然有艘轮船驶过,海面上景况完全变了。集装箱、码头或者龙门吊,这些都是巨大的,能使我们产生一种应有的强烈力量,就是崇高的感情,从它们的大想到人类的渺小,于是用单反表现它们,一种康德所谓的“崇高的感情”就在相机里产生了。这些还不能使我满意,我还要“优美感情”。优美是什么呢?优美就是太阳慢慢地下山了,它的光柔和了,它的柔和的光打在人类的器物上,器物就变得优美起来,几艘泊岸的轮船镶了金边儿,龙门吊把它的剪影合乎时宜地投在了海面上,大海是崇高的,有了龙门吊剪影的大海则是优雅的。与我一起拍片的马叙从集装箱区里走出来,他意犹未尽地举起相机朝天空拍了几张。我已坐在汽车里了,他朝汽车跑来,我则举起了相机对准他,意想不到的人物就出来了。马叙身后是叠得很高的集装箱,箱多得压迫人,幸好有天空,有变化的云层,阳光帮了忙,他跑动,太阳光把他的影子投在了集装箱上。一个拿相机跑动的马叙,从集装箱堆里跑了出来,他的影子在移动,优美出来了,尽管这分优美有刻意打扮和装饰的成分,于是优美有了深度,使人颤栗(人摆脱了物)。
从七里港集装箱码头出来,阳光一路好似一路,坐在车里的我看着窗外逝去的景物,都被一一打上了阳光,这条路我曾走过了数十次,今天才看到最好的景物:路边树,田野,农舍,广告牌,电线杆,一路路看过去,一路路消逝,光在城郊结合的边缘地带达到最佳,一个私家别墅群。“石头投下影子,清晰如月亮表面的物体”,特朗斯特罗姆在诗歌里说。这里,黄昏边,我开始。
山中慢时光
幸好有起起伏伏的山和格外难走的泥路,被我们称为“小瓦尔登湖”的黄村水库才显得格外幽静、无人打扰。到达水库时天色已晚,乌云密集布满水库上空,大片大片的浓雾被大风吹来东拉西扯,从一个山头钻出迅速占领了另一个山头,早些时候还看得见眉目的小山不一会儿消失在雾气里,暴雨即将奏响。山里的暴雨没来由的急速,没来由的阔大,令我们猝不及防。一把伞撑开了倒在堤坝上,如果不是手快,就被大风刮进水库里了。雨伞掉进水库里。是一个动词的开始。我们掏出酒、猪蹄,坐在堤坝上喝酒、吃肉,诗人拾来翠绿的松针丢入烧沸的锅里,第一杯水诞生了。一条瀑布从大坝的开口处流出,水流声伴随着我们扎下的营地,直到我离开营帐去山顶上的一座砖房子时,瀑布声音在狭窄的山谷里更加响亮,雨也更大了。在砖房子里我很快入睡,醒来时才十一点光景,回忆起在山上,还有人睡在大坝上面的帐篷里,便了无睡意。风从打开的窗门缝里吹进来,呼呼地响,离房子远一些的山谷里风来得更凶猛,带着大雨,急速跑过去,一忽儿又停掉,风走走停停,停下来时,外面的虫子叫唤得更起劲。多么奇怪,这些秋天的虫子还在叫唤,它们不知道藏在哪片树叶下,无需半点遮挡,生命力依然顽强,而且深夜是它们最喜歌唱的时刻。我,远离了城市,睡在砖房子里,有门窗,有床铺,可身体不适了,手脚时冷时热,隐隐地抵抗着周围。风吹过来,我赶紧拉起被单,比起外面歌唱着的秋虫我是那么不堪一击。黑暗中我开始想念起家里温暖的灯光,想念时常喝的甜南瓜汤,哦,这美妙的甜味! 它让我空空的肠胃更忙碌起来。我甚至无耻地想着一个人。病了吗?我只不过在晚上喝过一点酒,在水库里游过泳,躺下睡着了,连梦也没有。醒来,醒着,我多么想继续睡下去,可我在陌生的砖房子里躺着,身上盖着陌生的被衾。几个小时前,我根本不知道要来这个水库,接下来的六七个小时我只能在这个砖房子里,我是自愿地被禁锢在水库上面的。山上的时光比人间缓慢。我要的不是这缓慢吗?它来了。可是我真的不要这该死的慢时光了,我期盼着天快点亮起来,期盼着掀开被单,轻松地迈出房间来到水库坝上。睡在坝上的朋友发来条短信:闪电像被单一样覆盖了我。比起他来,我多么安稳。他接触到的闪电比我猛烈,因为只隔了道薄薄帐篷,在蓝色的营帐上闪电写着字,大概只有诗人读出其中的含义。雨水紧跟着来到,噼里啪啦打在帐篷上,渗到帐篷防水布下面,它们已没有地方再渗入了,营帐在扎下之前就做好了防水准备,连条小虫子也钻不进来,他们是安全的,与我在砖房子里一样安全,风暴雨水就在边缘地带了。
次日早晨,经过一夜风雨的水库像一位性事后的少妇,慵懒、缱绻。用水库里的水洗脸,烧一锅热水,吃下去一碗煮面条,慢慢地体验水流到脸上、拂在手上、喝进肚子里的感觉。堤坝造得有些年月了,因为水库没有多大用处,无人来管理,上面长出的芜草,芜草就茂茂盛盛,有的没过了膝盖。堤坝对着一个喇叭形的山谷。更远处是雁荡山,上面洒落着大大小小的水库、堤坝。雨季后的水库是充盈的、丰腴的,大坝也很稳固,但没有一个水库能与眼前的黄村小水库相比,因为它是被遗弃的,它躺在深山处,高高地躺在我思念它的喜悦里。我在堤坝上来回走动,从一丛草走向另一丛草,毫无目的。早晨的慢时光!水库上的慢时光就一点点被消耗了,对面小山头后面躲着初升的太阳,原先缠着的雾纱渐渐升腾起来,与阳光交错辉映。一只水蜘蛛从水面上跑过,它浓密的蛛网撒在水面上,网住了山谷的慢时光。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小学学生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