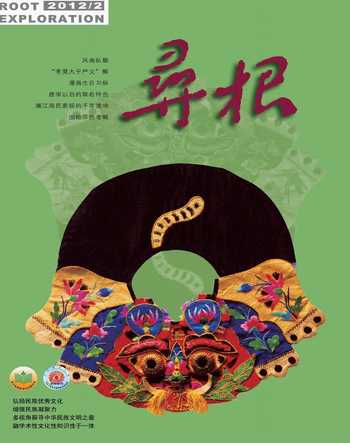“孝莫大于严父”解
汪文学
儒家文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重孝道,儒家文化就是以孝为中心的文化。虽然墨、道、法等诸子百家并不完全否定孝道,但是,相对而言,儒家却是最重孝道的,并把孝作为一切道德的根本属性,如《论语·学而》载有若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三才》说:“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圣治》载:“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虽然儒家学者讲孝道,并不局限于父母与子女之间,而是着眼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并将之推广到社会,作为人的一种社会行为进行阐释(钱世明:《说忠孝》,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学者讲孝道,主要还是侧重于子女对父母的孝敬,而且尤其强调儿子对父亲的孝,如《孝经·圣治》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孝经》及传统学者为何如此强调子女对父亲的孝,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讨论传统学者缘何特别强调儿子对父亲的孝敬?首先应当明确的是父母在传统家庭中的地位,分清父子和母子关系的不同特点。在传统中国社会,父亲被界定在外部世界,由此导致父亲对儿子和儿子对父亲的不切实际的角色期待,又因彼此对对方角色期待之失望,而造成了父子间的疏远关系和对立情绪。与父子关系不同,母子间往往能够融洽相处,如果能够正确解决婆媳关系,母子关系的和谐往往能够保持终身。这与母亲的地位被界定在家庭内部有关。因为在孩子的童年时代,母子朝夕相处,不容易产生那种只有在父子间才可能产生的不切实际的角色期待。或者说,母子间当然亦有彼此的角色期待,但不像父子间的期待那样不切实际。一方面,母子朝夕相处,两者之间构成如朱迪丝·维尔斯特所说的“一体状态”或“根本的联系”(朱迪斯·维尔斯特:《必要的丧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孩子对母亲的感受是熟悉的、具体的;不像对父亲那样,是理想化的、富于神秘色彩的。因此,孩子对母亲的角色期待是切合实际的,不至于像对父亲那样,因理想化的英雄角色期待之失望,而导致疏远、对立情绪。同时,母亲对于孩子是体贴入微的,不会像父亲那样对孩子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与父亲的严厉相比,母亲往往是慈祥的。一般而言,溺爱孩子的往往是母亲而不是父亲,甚至有“家训稍严,而母氏犹有庇其子之恶,不使其父知之者”(《袁氏世范·睦亲》)。与父亲相比,母亲更了解孩子,所以她不会像父亲那样,对孩子产生理想化的角色期待,因而相应的失望情绪也低于父亲。在世俗生活中,当父子间发生疏离、对抗情绪时,母亲顶多是作为一个中间调解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母亲往往是站在孩子一边,与孩子组成同盟军,联合起来反对严厉的、不近人情的父亲。
父子疏远、对立是必然的,母子和谐相处则是常见的现象,这是由父母本身之角色地位及其对孩子产生的不同的角色期待所决定的。《礼记·表记》中有一段话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其云:
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
这段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父母对孩子的态度不同。父亲对孩子是“亲贤而下无能”,即喜欢贤能之才而讨厌无能之子,父亲对孩子的态度有点近乎唯才是亲。这是由于父亲通常把孩子视为实现自身不朽价值的载体,从而对孩子产生过高的角色期待所决定的。母亲则不同,她对孩子“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即贤能之才固然值得喜欢,但无能之儿亦需爱怜。母亲对孩子的这种态度,与她本身的角色地位有关。其二,因父母对孩子的不同态度,从而决定了孩子对父母的情感取向,即“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句话中,“亲”“尊”二字出现了两次,并且都是以尊隶父、以亲属母。尊者,敬也,严也;亲者,爱也,慈也。故《孝经·圣治》说:“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以尊隶父,就是说,孩子对于父亲只有敬,父亲对于孩子便是严,缺少爱慈之成分,故云“父尊而不亲”。以亲属母,就是说,孩子对于母亲是爱,母亲对于孩子是慈,故云“母亲而不尊”。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的区别,在这段文字中讲得非常清楚。
“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这种观点亦体现在《孝经·士章》中: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这里所谓的爱、敬,分别等同于上引《礼记·表记》中的亲、尊。事母以爱,事君以敬,事父则兼爱、敬。君、父同体,以事父之道事君,故事君主敬。事母主爱,故“母亲而不尊”。事父兼爱、敬,之所以提及爱,这正如《孝经·圣治章》说:“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子天性,亦有爱的成分,但父子间爱的成分不仅比母子间少,而且还隐藏得很深,或往往被人们忽略,如扬雄说:“婴犊母怀不父怀,母怀爱也,父怀敬也。”(《法言·问道》)又如儒家学者讲父子关系,往往重孝轻慈,就是一个明证。因为“父子间天然关系固然存在,但不十分坚强”(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8页),即“天性”的成分少,而出于“天性”之爱亦较母子为弱,故曰“父尊而不亲”。
总之,子女之于父母,态度有异,或曰敬父爱母,或曰尊父亲母。这里,有必要厘清爱与敬这两种情感态度的区别。相对而言,所谓“爱”,乃是一种出于天性的诚挚自然之情。所谓“敬”,则是一种在外力作用下的人为之道。考察“敬”字之字形字义,即可明白这一点。“敬”字之初形是“苟”,变化而成“敬”字。“苟”字之本义是恭敬谨慎,其后演变为“敬”字,增加了“攴”符,表示有外力迫使其恭敬谨慎(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4~125页)。这个外力就是礼。敬、爱之别,古人区分得很清楚。如《庄子·天运》说:“以敬孝易,以爱孝难。”扬雄《法言·问道》说:
或问:“太古德怀不礼怀,婴儿慕,驹犊从,焉以礼?”曰:“婴、犊乎?婴、犊母怀不父怀,母怀爱也,父怀敬也。”
“婴犊母怀不父怀”,是出于天性,“母怀”之爱是天性之情;“父怀”之敬是人为之情。“婴犊母怀不父怀”,正表明人之本性是重天性之情而轻人为之道的。刘劭《人物志·八观》亦说:
盖人道之极,莫过爱、敬……然则人情之质,有爱、敬之诚,则与道德同体,动获人心,而道无不通也。然爱不可少于敬,少于敬,则廉节者归之,而众人不与。爱多于敬,则虽廉节者不悦,而爱接者死之。何则?敬之为道也,严而相离,其势难久。爱之为道也,情亲意厚,深而感物。
刘劭这段话,对爱、敬的说明和区分相当准确。就爱、敬而言,爱是敬的基础,建立在爱之上的敬,才是发自内心的敬。在通常情况下,敬有“严而相离,其势难久”的特点,故而需要礼法来维持它、保证它,因而亦往往容易流于貌敬心非。而爱则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的,有“情亲意厚,深而感物”的特点,是一种更适合人之自然本性的情感。所以,它在不需要礼法维持的情况下,亦能自然长久。
搞清了父子、母子关系的不同特点,接下来我们看看古代儒家学者对孝道的界定,及其对父亲角色的态度。考察早期儒学文献中讲的孝道,虽然皆可泛指子女对父母的态度,但在相当多的文献中,则是侧重于指儿子对父亲的态度。换句话说,古代学者通常强调儿子对父亲的孝,而对于儿子对母亲的孝,则往往是略而不论。这大概是因为母子关系是“天然的关系”,是“根本的联系”,无须强调,亦能自然和谐,就像“婴犊母怀”一样,是一种自然本性之流露。而父子关系则不同,虽然在父子间仍然存在着“天然的关系”,但往往因种种原因而容易发生疏远、对立情绪,故而需要特别强调,需要用孝道观念维持其联系。所以,我认为:孝道即父子之道,孝道观念主要是用来维持父子关系的一套思想学说。故《孝经·圣治章》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父亲形象,都以“严”为特征。同时,人们亦认为“但有严父,必出好子”(《课子随笔钞》卷六),“父严而子知敬畏”(《袁氏世范·睦亲》)。为什么古代学者特别强调父亲角色“严”的一面呢?这正如《孝经》所说:“圣人因严以教敬。”也就是说,只有“严父”才能获得子女的“敬”,即父亲因己之“严”而获得子之“敬”。所以,孔子论孝,屡言“无违”,即无违于礼。孝以合礼为原则,而“礼者,敬而已矣”(《孝经·广要道章》)。又《论语·子路》载孔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即孝虽以忠、敬为本,而又特别强调敬,是敬大于忠。所以,孝道即敬道,孝道即是父子之道。
总之,由于父子间因种种原因而容易发生疏远、对立情绪,为了使父子间不至于因疏远、对立而发生根本性冲突,完全变成敌对关系,故古代儒家学者不遗余力地阐释孝道,并以之作为调节父子关系的重要理论武器。孝道即敬道,孝道就是父子之道,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父子间的疏离关系,同时,亦是儒家学者持以调节父子疏离关系的重要思想武器。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学院
——从明代朱鸿《孝经》类编著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