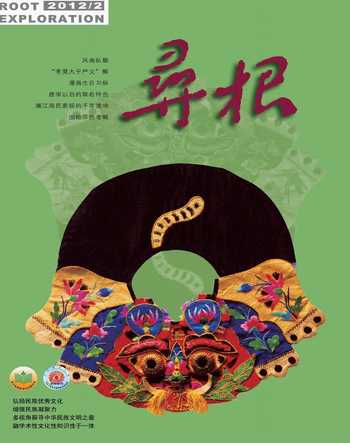浦江郑氏家规的千年遗响
施贤明
一
浦江郑氏自南宋初年同财共爨,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遭火灾而瓦解,共经15世。李静《义门家族的寿命与婚姻状况分析》(《江淮论坛》2004年第5期,第96~99页)据《义门郑氏家谱》估算,郑氏人口在元至大三年(1310年)、至正十年(1350)年、明建文二年(1400年)、宣德五年(1430年)依次是32人、92人、244人、355人,以此度之,天顺三年郑氏人口至少在400人以上。
义门郑氏的同居生活虽然早已结束,但它留给人们的记忆与遐想却不会烟消云散。时至今日,郑氏宗祠仍然静静地矗立在浙江省浦江县东部郑宅古镇。宗祠古色古香、沧桑凝重,正门高悬“郑氏宗祠”匾;旁门坐北向南,檐上悬明太祖敕封的“江南第一家”匾,门前两旁“耕”“读”“忠信孝弟”“礼义廉耻”十个大字斑驳陆离,支撑门厅的四柱之上分别题有“三朝旌表恩荣第,九世同居孝义家”与“文章空冀北,孝义冠江南”,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辉煌的往事。
俗语有云: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庞大的郑氏家族就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家规。
宋濂《旌义编引》载:“(郑氏)持守之规,《前录》五十八则,六世孙龙湾税课提领大和所建,《后录》七十则、《续录》九十二则,七世孙青府君钦、江浙行省都事铉所补,皆已勒石锓版。”“今八世孙太常博士涛复以为三规阅世颇久,其中当有随时变通者,乃帅三弟泳、澳、,白于二兄濂、源,同加损益而合于一。其闻诸父之训,曾行而未登载者,因增入之,总为一百六十八则。”
家规《前录》《后录》以及《续录》撰于元顺帝时期,三者文本只见于永乐刻十卷本《麟溪集》。需要明确的是,宋濂所言《后录》及《续录》条数有误。十卷本所收郑钦《后录》现存62条,第23条之后残佚一页,注云“以下缺七条”,而郑钦《郑氏义门续规序》亦称:“演而绎之,成《续规》,亦六十余条。”(《义门郑氏奕叶文集》卷一)郑钦所撰当为69条;另外,该本所收郑铉所著家规为93条。
自《郑氏规范》损益而合于一之后,大行于时。今所见《学海类编》本《郑氏规范》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据以排印)、胡凤丹辑编《金华丛书》本《旌义编》二卷以及民国重刻本等,所收家规无一例外均是168条这一最终定本。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写道:“家的规模大小是由两股对立的力量的平衡而取决的,一股要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另一股要分散的力量。”(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2页)郑氏家长孜孜以求的便是强化聚居的向心力并削弱可能导致分裂的因素,家规的宗旨即在于此。
心理上的认同是义门聚居的基础。一方面,敬仰与追慕祖宗是凝聚后人的有效力量,祭祀则在礼仪与心理上强化这种认同。《前录》首五则均是言祠堂与祭祀之事,郑钦则继续在细节上予以强调,包括“当用黪淡衣服”等;另外,郑大和仅言宗子“当严扃,所有祭器服不许他用”。《后录》中则有三条规定宗子“上奉祖考,下一宗族”的职责。郑钦意欲重塑宗子这一先祖与后世族人之间的精神媒介,体现了郑氏家长敬宗收族的深度考虑。另一方面,家人唯有孝弟,才能共同营造认同感,和睦共处。《前录》规定:“朔望,家长率众参谒祠堂,毕出,坐堂中,男女分立堂下。击鼓一通,令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凡为子者,必孝其亲;为妻者,必敬其夫;为兄者,必爱其弟;为弟者,必恭其兄。”在祠堂中供奉的祖先观照下反复申饬孝弟之道,郑大和可谓用心良苦。《续录》在听训接受的基础上,通过令人羞愧的惩罚措施不断强化对先祖事迹和家规的记诵,极大增强认知与心理上的认同感:“子弟已冠而习学者,每月十日一轮,挑背其已记之书及《谱图》、家范之类。初次不通,去帽一日;再次不通则倍之;三次不通则分髻如未冠时,通则复之。”所谓《谱图》,当指吴莱后至元元年(1335年)所著《郑氏谱图》,为郑氏历代人物小传。
义门聚居依赖于财富,明初时郑氏家族良田面积底线是8620亩,甚至可能数倍直至十倍于此(毛策:《孝义传家—浦江郑氏家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第228~229页)。如此雄厚的家资无疑是郑氏得以绵延15世最坚实的物质保障。那么,郑氏是如何积累财富的呢?郑大和仅言通掌门户有增拓田业之任;郑钦则首先为儒士不屑道的积累财富正名,“增拓产业,彼则出于不得已,吾则欲为子孙悠久之计”,进而明言,“家长当令子孙以理生财,补助公堂之费”;而《续录》详列义门近二十种职务的职责,不仅农业生产由专人职掌,副业亦复如是(“牧艺之事,当以一人专总其纲”),而且严格规定增拓产业的程序:“增拓产业,长上必须与掌门户者详其物价等,然后行之;或掌门户者他出,必伺其归,方可交易。然又预使子弟亲去检视肥瘠及见在文凭无差,切不可鲁莽,以为子孙之害。”“掌门户者置他人产业,即时书于产业簿中,不许过于次日。”这种变化正是逐渐壮大的郑氏对财富的依赖与诉求日益强烈的反映,也体现出至正末年郑氏家族组织业已定型,对家族资产的营运也日渐规范。
不过,对私有财产的诉求却是不容小觑的导致分裂的力量,这一点相信郑大和早已洞若观火。《前录》规定:“子孙倘有私置田业、私积货泉,事迹显然彰著,众得言之家长。家长率众告于祠堂,击鼓声罪而榜于壁,更邀其所与亲朋,告语之所私,即便拘纳公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论。”郑大和通过对私置产业的严惩来保障义门财富的单一传承,确保绝对的经济均匀性,减少分裂倾向。
二
孝义家风是累世同居的基础与必备条件。孝义行之于家,家庭才能和睦;推之于乡邻,既是义门的自觉追求,也在客观上促成儒士对义门的揄扬与支持,进而得到文官集团背后的皇朝的褒扬与优待,这股力量正是义门累世同居最坚实的外部保障。
郑氏的先祖即有乐善好施的美名。靖康岁俭,同居一世祖郑绮之祖郑淮卖田一千多亩以赈济灾民,以致家道中落。元末至正年间,郑氏同居业已6世,颇具规模,自觉担负起赈济乡邻的职责。《前录》明确规定:“每岁秋成,谷价廉平之际,籴三百石别为储蓄。遇时艰食,依元价粜给乡邻之困乏者。”作为地方有能力的大族,郑氏此举相当于建立了一处小型的常平仓,平价出粜,既可以平抑市场物价,也可解灾民燃眉之急。《前录》又规定建义宅一区、义冢一所,使乡邻无所归者生有所居、殁有所葬。与《前录》仅有三则言及对乡邻的周济与赈济不同,《后录》中竟有十余条家规详述扶困救急之事,内容涵盖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方方面面,这是已成规模的郑氏在道义上的自我修持,也是其立身之基。郑钦首先强调:“宗人实共一艺所生,彼病则吾病,彼辱则吾辱,理势然也。”宗人“其果(裹)无衾与絮者”,当量力资助;缺食者,“月给谷六斗”;“不能婚嫁者助之”;“营义方一区,以教宗族之子弟,免其束”;甚至宗人无后,则“择亲近者为继立之”。至于邻族里党,除了不过问宗嗣之事,余亦有详细规定,“每岁量力以钱五百贯文用以拯(里党)患难之无告者”;里党有缺食者,产子“不问男女,给助粥谷二十五升”等。
《后录》第19条有云:“展药市一区,收贮药材。邻族疾病,其证章章可验,如疟痢痈疖之类,施药与之,更须诊察寒热虚实,不可慢易。此外不可妄与,恐致误人。”以如此谨慎的态度救死扶伤,郑氏真可谓积善之家!
三
郑氏以孝持家,义举推及宗人乡邻,成为士人心目中理想社会图景的映射。于是,士人不吝笔墨,对义门气象的书写浓墨重彩,郑大和裒辑而成《麟溪集》,嗣后时时补益并屡次重刻,这证明人们关于郑氏的记忆并没有随着同居大家庭的崩溃而消逝。社会对儒家伦理、孝义家风的呼唤,郑氏后裔对先祖德业的自豪与追慕,这两股力量使得郑氏成为一种典范的象征与想象:一种道德的象征,一种治家的典范,一幅和谐社会图景的想象与憧憬。
记忆不曾淡去,想象也会与日俱增。民国年间,西学东渐,被一些浸淫于“四书五经”中的儒生视若洪水猛兽,斥之为“自新学横流,异端竞进;自由平等,荒谬绝伦”(民国刻本《麟溪集》卷首黄志琨《序》),便再度祭出义门,重刻《麟溪集》,试图借此归化人心、降服“异端邪说”,终究只能事与愿违。
那么,时至今日,义门郑氏的意义何在?郑氏家规的千年遗响究竟是和谐的乐音,还是迟暮腐朽的丧钟?
郑氏扶困救急是仁义之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孝义—义门的核心价值永远不会过时,它依然是当下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诉求的。
不过,郑氏家规并非全然可取。譬如,郑大和之父德璋主家政时,“每晨兴,击钟集家众,展谒先祠,聚揖有序堂上,申‘毋听妇言之戒”,大和则将此写入家规。此外,郑氏家长对庄妇、媵也有颇多鄙弃之语,以地主士族的优越感俯视妇人与劳动者,无疑是家规中的糟粕。
正如前文所述,一般而言,五世同堂是不分裂的极限。换言之,即便以剔除糟粕的郑氏家规为指导,试图在当下复制一个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仍然是痴人说梦。这种特殊的家庭组织形式很大程度上凭借的是唯心道德的维系,郑氏家规的文本处处折射出义门伦理的艰难。
郑氏家长对“家业之成,难如升天”(《后录》)有清醒的认识,于是不断强化义门的心理认同,并且严格保障绝对的经济均匀性,尽可能减少分裂倾向。除此之外,在细节上补充《前录》的《后录》,满目尽是禁忌;《续录》则严格限制诸妇、子女与姻亲往来,而且规定媵女不得妄出中门,加之前文所言对人、庄妇的限制,体现出郑氏家长在相对封闭的时空中实践这种特殊家族组织形式的努力。细节的规定与禁忌愈多,活动的空间愈封闭,愈呈现出义门伦理的不合时宜与艰难。我们似乎看到,那个精致而又承载着儒家伦理与士人理想的标本在被赏玩,众人啧啧称赞,但构建标本的郑氏家长与族人却不得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