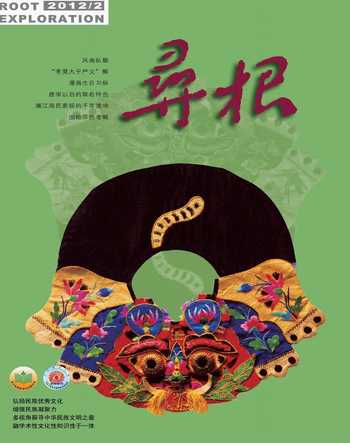彝族旧称“罗罗”与“人化虎”的真相
朱和双
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族旧称“罗罗”(在古代典籍中通常被添加上“犭”),由于读音差异又作“卢鹿”“罗落”“落落”等。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在今四川西昌周边地区及大凉山一带设置“罗罗斯宣慰司”,治建昌路(今四川省西昌市,为古越地),辖今四川大渡河以南,美姑、金阳以西,盐源、盐边以东,金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明洪武中废。元明以来,“罗罗”等名为各种汉籍所习用,比如在《皇清职贡图》中就描绘出各种“猡猡”或“猓猡”的男女人物形象,诸本《百苗图》中也常见贵州的“黑猓猡”“猓猡女官”“白猓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将各种他称统一改作彝族。在汉籍中究竟何时开始用“罗罗”一词指称彝族先民,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在作为特定的族群称谓之前,汉文中出现的“罗罗”是传说中的鸟兽名。《山海经·西山经》云:“(莱山)其鸟多罗罗,是食人。”《山海经·海外北经》又说:“(北海)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如果我们将“青”和“状如虎”作为“罗罗”的共有特征,估计只有黑熊或猫头鹰能符合标准,毕竟“状如虎”还不是虎,虽然猫科动物都可算作“状如虎”,但又不符合“青兽”的特征,因此《山海经·海外北经》所说的“罗罗”更像是黑熊,能“食人”的鸟类估计是因为对虎豹的恐惧幻想所致。不管怎么说“罗罗”非虎恐怕不至于太谬吧!
尽管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活跃于云南楚雄的彝族文化学派,在刘尧汉先生的带领下,对“罗罗即虎族”的命题进行了论证,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转引其观点的著述更是不胜枚举。刘尧汉先生后来在《彝族虎文化》这篇短文中将他的基本结论归纳如下:
彝族自称“罗罗”,女称“罗罗摩”,男称“罗罗颇”,而“罗”意为虎,即彝族自称“虎族”;“摩”意为女,“颇”意为男,即女人自称“母虎”,男人自称“公虎”。此意古籍中早有记载:明代陈继儒《虎荟》卷三说:“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此处所说罗罗,其实也包括凉山彝族。据我在凉山对多位彝老的调查,六七代以前,凉山彝族也自称“罗罗”。元代周致中《异域志》载:“,瓠之种,裳为衣,髻长一尺向上,以女人为首长,曰母总管。”记载的就是凉山彝族的习俗。至于老则化为虎,是认为彝族死后经火化会还原为虎。这是基于图腾崇拜的一种认识,即认为人与图腾物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在彝族地区,以虎为地名、人名的事象比比皆是……而彝族的族称,最早见于记载的是“罗罗摩”,后来才改为“罗罗颇”,即最先是以“母虎族”为族称,后来才改为“公虎族”。这些都透露出彝族的虎图腾崇拜产生于原始的母系氏族时代。
刘尧汉先生在上文中说“彝族自称‘罗罗”,可是除了田野调查材料外找不到任何历史依据。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之“诸夷风俗”条云:“罗罗即乌蛮地……酋长死,以豹皮裹尸而焚,藏其骨于山……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皆此类也……年老往往化为虎云。”这里的“罗罗”是一个地域范围的统称,而且说的是“以豹皮裹尸而焚”,并没有提到虎。
在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中已经用“罗罗”来指称彝族先民,很显然这是一种他称而非自称。据方国瑜先生考证,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中有一个专门用来指称彝族的图画符号,读作“罗罗”,其字形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为“轭”(纳西语读作“罗”,像二牛抬杠之“犁轭”),下半部分则为一人站立状,从整体来看刚好就是人用头部来负重的形象。其实,汉文中的“轭”亦作“”,专指驾车时搁在牛马颈部的人字形器具,引申开来可作束缚、控制解。用头部负重,掌握平衡极为重要,所以此字在东巴文中还兼有“释理”的别意,看来“罗罗”只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在乾隆年间绘制的《皇清职贡图》中,昆明附近的黑白“猡猡”和“罗婺蛮”妇女都用头部来承重,而彝语支民族妇女背负重物的方式基本上也如出一辙。滇西地区的汉族至今仍将这种用头(或颈)部承重的器具称作“罗罗背篓”。
由于受特殊地理环境的限制,彝族先民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生息繁衍一直从遥远的青铜器时代持续到现在。明清汉籍通常都将“罗罗”写作“猡猡”或“猓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种动物,加上后来“图腾崇拜”理论的泛滥,作为一种独特生活方式的“罗罗”完全被人们所忽视。随着田野调查研究的深入,刘尧汉先生的假说首先受到了来自哀牢山区的挑战,因为在那里被旧方志记载为“倮”的族群自称“罗鲁”(这是南华县的称呼,弥渡县自称“腊罗扒”),据说男性称“罗颇”,女性称“罗摩”,“罗”义虎,“鲁”义龙,合义就是“虎龙”。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罗”与“鲁”分别指称“虎人”和“龙人”,两者所不同者仅性别而已,即男的是“虎”,女的是“龙”。尽管这种说法明显受到了“四神”的影响,却也部分地颠覆了“罗罗即虎族”的推测。凉山彝族将蜥蜴称作“鲁”,这种爬行动物在滇国青铜器物上极其常见。就目前发掘的考古材料来看,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漆木箭上已有龙虎相斗的图像,这是云南所见最早的“有麟爪的龙”。
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都出土有“八人猎虎”铜扣饰,清代云南还有“摩察”猎虎图。刘尧汉先生所谓“老则化为虎,是认为彝族死后经火化会还原为虎”的见解,完全漠视大量笔记文献的存在。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篇·补遗》卷四“土司·人化异类”条云:“隆庆间,云南陇川有百夷夫妇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得活鱼六七头,持归烹食之,夫妇俱化为虎,残害人畜不可胜计,百计阱捕,终莫能得。”古来“人化虎”食人,记载中时有之。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北方老妪,八九十以上齿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婴儿,名‘秋姑。”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九“卜思鬼术”云:“建昌有夷尚幻术,彼人葬尸未朽者,至坟所,禹步诵咒,尸即自穴透出,变为牛马,用以充馔,或曳娄而卖之。又三宣慰中有妖术曰卜思鬼,妇人习之,夜化为猫犬,行窃人家。遇有病者,舐其手足,嗅其口鼻,则摄其肉,唾于水,化为水虾,取而货之。”建昌就是今凉山州的西昌一带。康熙“东轩主人”所辑的《述异记》中就有五则“人化虎”的传说。
在《述异记》中也有“人化虎”的记述:“广西有一村民,每日早出晚归,必携死猪羊鹿犬等物至家,以为常。后因其子择日成婚,须猪羊祀神,妻嘱其觅活者为佳,村民有难色。妻遂疑以前之物,皆属偷盗,命子尾其后,觇之。至一山,见其父入岩洞中。少顷,有虎咆哮而出,其子惊悸良久。徐入洞,求父所在,但见一衣存焉,疑为虎食矣。未几虎归洞,而父复出,其子骇甚,因急归告母。村民归家,见其妻色变,遂大言曰:‘吾为汝等识破,今出不复返矣。疾走出门,妻子牵衣留之,力挽其足,竟脱一袜而去。后其子于山中遇一虎一人足也,因思此虎必其父,将为猎者所得,遂遍揭街市云:‘若有人获虎一人足者,勿送官,愿以重价购之。不数月果得而葬之云。此康熙年间,柳州来宾县事,牛哀封使君,其然乎?”传说中不光男子会变成虎,就连老年妇女也能变虎,盖虎亦有公母之别也!在《述异记》中有一则“老妇变虎”云:“康熙四十年,浙东阳县某乡章姓,有一老妇,年已七十余,时时无故他出,辄数日不归,其子窃疑之。一日寻至深山,过土地祠,闻洞中声甚异,入视之。见其母方踯躅变虎,因惊呼从后握其发,持之不释,母以爪伤子面,负痛放手。母跳跃而去,不知所之。数日伤愈,遍求之山中,见一披发虎前行,后从数虎。子不敢近,怅惘而归。传闻远近。”
在中国民间,“人化虎”的传说慢慢地同“神鬼”观念结合在一起,“虎鬼”作为祖灵庇护世人的说法应运而生。清代贵州民间有这样的传说,据《述异记》下卷之“人化虎”云:“人化为虎,贵州最多,妇人即化,男子则不化也。康熙二十六年,贵州定番州上马司土官方名誉之母,独坐室中,忽门外有数虎往来其间,母即神痴,以手据地,坐而攫食,侍者扶掖辄怒之。数日口渐阔,而目竖,突身有黄毛,咆哮欲出外,虎日夕至门候之。一日偶值驰备,跳踉入虎群,就地数滚,变虎而去。三十六年,开州民家一妇,亦如此,已逸入山,尚未全变,其夫与子求而获之,载与具归,饮药医治,月余复为人,今尚在。州守王纪青亲言之。”这则“人化虎”的传说已经明确地将贵州地区的土司和白族(即民家)牵扯进来,并且还说这种特异功能仅仅发生在妇女身上。在“人化虎”的过程中会出现“口渐阔,而目竖,突身有黄毛”的特征,“目竖”即“竖眼”,是人与虎在外形上彼此区别的重要特征之一。毫无疑问,变形的“眼睛”和“嘴巴”都集中在头部,所以“人首虎身”的形象可能更加符合“造神”运动的思维结构,反而是“虎首人身”的形象只可能出现在傩舞中,比如双柏县小麦地冲彝族支系“罗罗颇”跳的“八虎舞”(俗称“老虎笙”)和楚雄市树苴彝族支系“罗鲁颇”跳的“母虎舞”。从称谓上来说,不管是叫“虎人”也好,“虎神”也罢,“突身有黄毛”这一点在傩舞表演中都有体现,只是在原始形态的“八虎舞”中没有“母虎”出现,这与贵州传说的“妇人即化,男子则不化”有些抵牾。江南民间流传的“人化虎”故事多出现在“寺”“洞”“祠”等宗教场所的周围,而西南民族地区流传的“人化虎”故事却多与“土司”有关。清代洱海边的赵州即流传有“人化为兽”的说法。《述异记》下卷之“土司变兽”云:“土司杨姓者,能变三兽,土人知之。至变虎之期,逐家比户,俱闭门不出。欲开城门,彼则望深山腾跃而去,一宿即返,返则仍为人。若变驴,则土人置芗豆草具于通衢,恣啖一饱。变猫不过窃肉食之,须臾则为人云。系祖传世世如此,其变兽亦有定期,故得备之。”在这里土司所变的动物已不限于“虎”,估计是受到了五通神的影响。
在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文化中,作为猛兽的虎是造型艺术的一个基本要素,“人化虎”的传说透露的是对虎吃人的恐惧心理。明清时期的“人化虎”传说有着潜在的传播路线,这是江南汉族移民向西部地区挺进的结果。从元代开始的典籍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类“人化虎”的传说并非“罗罗”所独有,而是一种地域文化现象。
作者单位:楚雄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