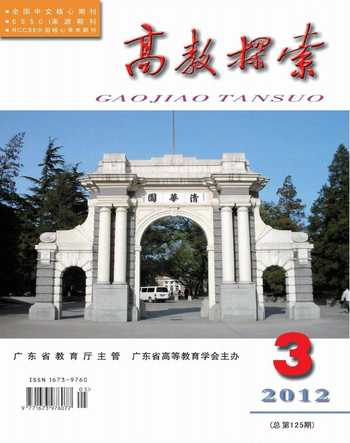后大众化视野中的中国高职教育发展方向
张文格
摘 要:后大众化阶段,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促进高等教育结构转型和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的双重使命。要完成这种使命,必须构建受“市场力量”控制的、竞争性的且对社会需求反应“敏感”的高职教育系统。高职教育目前所面临的生源减少、培养模式落后、财政投入难以为继、就业率低下等困境,致使其必须致力于办学主体私有化、培养目标职业化、学习课程模块化、系统无边界化等发展方向。这关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能否从大众化阶段顺利过渡到后大众化阶段。
关键词:后大众化;高职教育;私有化;无边界化
后大众化作为“人人参与”的普及化的过渡阶段,应对大众化前期急剧扩张带来的危机,进行组织结构变革以及非适龄人口的广泛入学是其基本特征。国外实践经验表明,后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应主要以非适龄人口入学的增长来实现。这将使得高等教育需求发生质的转变,而高等教育系统结构必须为这种转变提供准备。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尚未建立起应对这种转变的组织结构。《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1-2015年)征求意见稿》拟定在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总数达到1390万人,5年内增长425万人。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拟定在2015年高等教育总规模从2009年的2979万人达到3350万。这意味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将全部依靠高等职业教育增长来实现,中国的高职教育体系必须肩负起作为继续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容器”的历史使命。高职教育目前面对的生源减少、吸引力低下等困境,其根源何在?该如何发展才能承担起上述使命?
一、后大众化阶段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新使命
“后大众化”是日本著名学者有本章提出的一种解释高等教育发展新现象的理论。该理论揭示了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增长在未达到普及化之前就出现了停滞和波动,而非传统的成人学生入学率却持续增长。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适龄人口减少,很多院校遭遇生源危机,必须纵向扩大生源市场;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快速变化,使得所有年龄层和社会阶层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大幅增长。在此种契机下,政府开始根据市场需求颁布面向非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政策,甚至创设新的短期高等教育机构来适应此种需求。
美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先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国家。其发展形态是后大众化理论模型生成的源头,其承担扩大参与机会的短期高等教育机构在后大众化阶段经历了极为不一样的发展历程。美国、日本都先后面对生源减少的危机。从1980年开始,美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逐渐下降,其18~21岁人口从1980年的1730万人,下降到1994年的1411万人,14年间减少了319万人。[1]生源的减少迫使位于高等教育金字塔底层的短期高等教育机构通过采取一系列生源拓展计划,将注意力转向招收“新型”学生(少数裔、弱势群体)和“非传统”学生(非适龄人口)。1970年,25岁以及25岁以上的学生在社区学院的学生中所占的比例为27.79%,1990年达到41.88%。因此,虽然适龄人口下降,但是美国社区学院入学人数却迅速增加,从1980年到1986年,社区学院在校生数增加了10倍,从430695人增长到4416882人。[2]日本18岁人口在1992年达到顶峰,为205万人,而2000年降至150万人,2010年则减少到120万人。[3]这种人口的变动给主要依靠私学部门承担大众化和普及化任务的日本高等教育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导致了私立大学的生存危机(尤其是部分短期大学的倒闭)。1997-2003年,有60所短期大学破产或停止招生。2006年,私立大学未达到招生计划的有222所学校,占私立大学总数的40.4%。[4]有学者分析,在大约710所大学中,今后十年间将有大约200所破产,每年将有20所大学破产。[5]美国在后大众化阶段,其短期高等教育机构成功转为以成人学生为主的教育,平稳过渡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日本因其雇佣结构的问题一直以适龄学生为主,致使其高等教育发展始终停留在后大众化阶段。
马丁·特罗曾经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也需要如美国一样创建新型的短期高等教育机构,如把社区学院作为规模扩张的载体。但之后天野郁夫却发现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过程中是以私立高校作为扩展主体,而非特罗所预言的公立大学,于是他提出了不同于“美国模式”的“东亚模式”。美国和日本在后大众化过程中,承担规模扩大任务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共同点是均具有对人们学习需求和就业市场的敏感性,且都以职业教育和实用教育为导向,学习年限短。这两种模式的不同点是,在美国承担普及化教育的机构类型是公立机构即社区学院,其价格低廉,且社区学院与四年制大学道路畅通,以非适龄人口(也包含适龄人口)教育为主;而日本大众化和普及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大学、短期大学、专修学校这些专门以学费收入来运营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学费水平与私立大学不相上下,四年制大学与短期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壁垒森严,以适龄人口教育为主。无疑,美国模式更适应后大众化的需求。
中国的情况不同于上述的“美国模式”和“东亚模式”。中国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我们暂且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异于日本的独特性有:承担大众化任务的主要是公立教育机构(地方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教育);私立教育萎缩,难以承担后大众化或普及化的重任。中国异于美国的独特性有:依赖政府的经费支持,受政府的官僚主义控制,高等教育机构的市场化程度低;学生在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和教育课程之间的流动性差;以适龄人口入学为主。正因为如此,中国大众化了的高等教育系统并没有形成适合规模持续扩大的组织结构和框架。一是特别强的国家意志控制着复杂的高等教育系统,致使大学发展模式单一,缺乏灵活性和对市场的敏感性;二是财政来源单一,即公共财源和学费以外的收入很少,支撑规模继续扩大的财政乏力;三是能够弹性地应对非适龄人口的中学后教育需要、并且能够承担后大众化、普及化重任的高等教育机构尚未成长起来。这种制度和结构缺陷将导致中国后大众化发展之路阻力重重。
所幸,《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1-2015年)征求意见稿》已经明确规定高等职业教育“稳步发展全日制专科教育,积极发展非全日制专科教育”。这意味着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有可能发展成类似美国社区学院的面向“人人”的短期高等教育。这符合当前高等教育结构转型的需要,也与后大众化阶段社会各阶层产生的旺盛高等教育需求相适应。但是,如果高等职业教育要想成为后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容器”,那么其当前面临的生源和费用等等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二、中国模式的高职教育发展困境及其根源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经过十年的快速发展,2009年,全国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院校有1215所,招生313万人,占普通高校招生总数639万人的49%,在校生965万人,比1999年增长了8.2倍。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1-2015年)》等国家战略规划的陆续推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将因势再次进入一个大发展的阶段。
但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因其文化、经济、教育历史以及制度的原因陷入了“中国模式”的困境:(1)生源减少的招生困境。我国18-22岁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2008年达到顶峰,为1.24亿,2020 年将降至8350万人,年均减少340万人。与适龄人口的减少相一致的是,全国高考报考人数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人数1050万后,开始全面下降。据统计,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约为933万,比2008年减少了117万,高考录取率达到了72%。高考报名人数的减少导致高等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开始产生生源危机。即使高职教育的入学分数已经降到了180分,实际上线人数仍无法满足招生计划。随着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减少,这种情况将进一步加剧。(2)面对“压缩饼干”的培养模式困境。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等一直以本科教育为蓝本,只是在难易程度上有所取舍。由于其办学条件(师资、教学设施、资金)和生源不如本科,因而导致培养的“产品”社会认同度低。(3)面对财政来源有限的制度困境。发展中国家,如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经常性平均成本的平均比值为2.53[6],即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需要有更大的投入,但在中国的事实却截然相反,其投入反远不如本科。譬如2009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191.26亿元,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828.22亿元,占83.4%,高职高专学校363.04亿元,仅占16.6%。[7]这与高职学生数基本和本科教育“平分秋色”的状况极不相称。(4)面对“高投入、低产出”的就业困境。大多数高职院校主要依靠学校贷款及学生学费维系。这导致不少学校学费高昂,一般高职高专院校学费已经达到6000-8000元/年,而独立学院、民办院校高职生每年学费均高达万元以上。他们投入更多的资金,获取一张注有“高职”标识的大专文凭,大部分人一毕业即失业,即使就业,其起薪也非常低,一般为1500-2500元/月,且与传统大学毕业生所能获得的体面、稳定、有一定前景的工作大相径庭。以上种种困境导致高职教育吸引力低下,其根源何在?
一是国家教育行政权力的控制使高职教育机构缺乏对市场的敏感性。在中国,由于政府是所有教育机构的投资主体,因此,它们只能按照教育部制定的方向发展。虽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规定要还给大学自主权,但是要还给大学自主权从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提,26年过去了,至今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更别提新近出炉的《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1-2015年)》所提出的一系列指令性数字:“国家级重点建设专业1000个,省级重点建设专业2000个,校级重点建设专业3000个。面向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每年技术服务收入不低于12亿元。各地建设2000个生产性实训基地,开发50个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国家示范(骨干)高等职业院校200所左右,省级示范院校400所左右,100个左右区域(或行业)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这47个数字无一不显示这种教育行政主导发展的趋势,而且这些政策与本科教育政策极度雷同,无疑会继续导致高职教育“本科模式化”和“千校一面化”。由于教育系统外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其面对的市场环境千变万化,而中国政府还继续以行政指令来对教育系统进行直接管理和控制。这导致学校疲于应付和完成上级机构设定的指标,而无暇关注市场,对人们的需求和就业市场反应失灵。
二是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产业结构需求不合拍。2009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分别占总产值的10.3%、46.3%、43.4%,在第一、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者分别是38.1%、27.8%、34.1%。[8]可见,我国仍将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一方面,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已经分别占58%、52%,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2%,在建筑业中占79.8%(根据2006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折算)。但是由于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低、技能技艺水平低,致使我国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只能在较低层次结合,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订单式制造业大国,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环节。这个环节由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支撑,而真正需要大学生的后6个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和零售)则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1比6”的产业生态无法吸纳太多的学术型大学生。“中国的就业市场是一个分割的市场,包括农民工竞争的就业市场、大学生竞争的就业市场,而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技工就业市场,目前正面临严峻的人才紧缺问题。”[9]从理论上讲,与技工就业市场对应的人才需求应由职业教育系统来满足,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一线技能型的人力资源支撑并且能对2、3亿农民工进行技艺技能培训。但是目前我国高职教育仍以适龄人口入学为主,每年招生近300万,培养出来的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型大学生”一方面竞争力不如本科生,另一方面所学专业(专业种类基本与本科等同)和实践技能又与技工就业市场的行业岗位不能有效衔接。因此,其发展陷入尴尬境地。
三、后大众化阶段高职教育发展方向
在后大众化阶段,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促进国家高等教育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双重使命。因此,高职教育面临的困境的化解就显得极为重要。如何构建受“市场力量”控制的、竞争性的且对社会需求反应“敏感”的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呢?根据后大众化理论及其在发达国家的实践,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办学主体的私有化
多年来,我国以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总数的1.5%,支撑起约占世界教育人口的20%,即2.4亿全日制在校学生的教育,通过短短的十年时间又一跃成为世界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其财政负担之重,可想而知。除了为九年制义务教育买单以外,国家是研究型大学、地方本科院校的投资主体,而且正在推广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如果按照国外发展经验,非适龄人口的中学后教育要成为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的半壁江山,那么中国在未来一二十年要承担起大概三四千万非适龄人口的中学后教育。如果由国家来对需要庞大的教育经费的高等职业教育大包大揽,整个高职教育系统只会走进死胡同。教育系统的复杂化和财政困难已经迫使政府权力必须下放,高等教育市场必须进一步开放。允许企业或私人办学,允许赢利教育机构的发展已是大势所趋。近二三十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或正在实施由公共服务品向可市场购买品(trade-able good)的转变。早在1988年,美国总统私有化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称,包括教育市场化在内的社会服务部门之私有化运动,必将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20世纪末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重大事件之一。[10]“1990年以来,私有化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11]1970年,美国高等教育的在校生在私立营利性大学就读的仅占0.2%,即1.72万人,2008年这一数据达到了147万人[12],而同期的四年制公立大学、两年制公立社区学院和私立非营利大学的学生比重则有所下滑。“由于政府是非赢利机构,一般而言,非赢利机构并没有动力去追求效益最大化,因此,其可能更适合举办更加偏向公共产品的学术性普通高等教育;而更加偏向私人产品的高职教育可能更适合由企业或其他赢利机构举办。”[13]在后大众化阶段,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要从重重困境中突围,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私有化之路,将整个高职教育服务中的相当大的部分交由私人企业或个人经营,以实现其对市场的敏感性和灵活性。否则,没有什么办法能摧毁或者至少极大地削弱现存国家教育行政的权力。而摧毁或削弱现存教育行政的权力,乃是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引向市场化,摆脱财政困境的根本条件,也是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组织结构的先决条件。
(二)办学目标的职业化
短期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倾向于职业化可以从美、日短期高等教育机构的转化看出来。后大众化阶段,日本创建的短期大学(以素养教育为主,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中心)由于生源不足不断萎缩,而带有职业主义的倾向的专修学校(结合职业资格、重视实用性教育)却并没有出现升学人数的减少,日本的短期高等教育正以专修学校为中心而发展。而在美国,社区学院的转学教育功能(大学基础教育)也正在逐渐退化。我国的高职教育仍保留着选拔性的教育模式,以录取通过学历评价方式选拔出来的、匀质的高中毕业生为主,并在整齐划一的标准化的教育课程下有效率地施予教育。这种模式适应精英教育和大众化前期教育,属于“僧多粥少”的模式,其特征是“大学选拔符合一定条件的学生,其学习被束缚于建立在一定学科知识体系上的教育课程和学习形态中”[14],大学教育的目的停留在追求知识自身价值或学科内在逻辑的价值和理论取向。随着适龄人口的迅速减少,高等职业教育面向适龄人口和非适龄人口开展开放性入学已经势在必行。这意味着,高等职业教育机构被要求接收具有多样化的学历、学习要求和工作经历的学生,而他们的知识基础、学术资质、爱好兴趣、成才意向与以学科知识、价值为逻辑的教育体系的匹配程度大大降低。因而高等职业教育必须从传统的以学科专业为中心的知识教育转为“促进职业发展,培养职业技能”的职业教育,必须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变化,为学生提供在当前激烈的就业竞争中所需的应用知识和职业技能,并能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帮助其获得学历,提升他们的职业竞争力。
(三)课程的模块化
后大众化阶段,高职教育机构必须将现行的供给教育与需求方的转变联系起来,形成开放的、有弹性的教育计划,为学生提供其亟需的职业发展和技能提高方面的实用性课程。因此,如何针对人们的学习意愿而展开与之相应的应用型知识教育,并提供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目的的“模块型学习课程”,成了当务之急。这种教育课程的特征是,将特定职业所要求的知识与技能设定为一个模块,用2~3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在成人学生可参加的范围内,进行授课。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正是依靠这种模块型课程(modular course)和单元学分积累制(the cumulation of unit credits)运作,课程学分储存在每个学生的成绩单上,并允许相对容易地在同一个学校不同专业领域间或不同学校之间进行转移。这使学生能暂时“脱离”正规教育去工作,也允许学生工作后再回来,或游历后还能重新回到原来的或不同的学校,去重新捡起他学习的课程而不必为必须一次性获得学位而苦恼。这种制度完全适应后大众化对高等教育提出的需求(这种需求鼓励学习的间断和转换),为大众高等教育系统和普及高等教育系统带来了不可忽略的优势。目前在我国,高职教育课程设置完全由国家来决定。而这种模块化课程的设置和调整完全依赖于市场变化机制,即服从于学生和雇主的需求,允许学生因时因地完成学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模块化课程的形成是我国能否构建起适应后大众化需求的高职教育体系的关键。
(四)高等职业教育系统的无边界化
2000年,英国大学副校长委员会(CVCP)和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HEFCE)联合发表的题为《无边界教育事业:英国观点》的研究报告认为,“无边界”已经成为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态势。金子元久认为,在后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系统一方面依靠研究型大学形成高质量核心,一方面依靠短期高等教育机构实现系统的无边界化,扩大高等教育参与机会。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向后大众化的过渡中,由于非适龄人口的广泛入学,学习的边界已经或正在被跨越,传统高等教育的各种边界,无论是观念上的,还是制度上的,都在不断地向“无边界”过渡。“无边界”意味着各种教育空间、教育形式、教育机构之间的渗透和跨越。承担着扩大高等教育参与机会重任的高职教育系统的无边界化所指的“边界跨越”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不同教育机构之间的边界,包括高职院校与普通高等院校之间的边界、高职院校与中职院校之间的边界、不同高职教育机构之间的边界。在中国现行的双轨制下,高职学生不能或很难回归到普通高等教育的轨道,中职升高职的比例也很低。由于高考过独木桥的性质和国家重点投资政策的影响,虽然同是短期高等教育机构,但是却有三六九等,这使得学生在不同高职机构之间的流动也成为不可能。打破这些机构之间的界限是形成无边界化的关键。二是就高职教育的招生类型而言,高职教育应该对三大群体实行开放式入学: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有一定学历基础的在职人群、以农民工为主的弱势群体。三是从举办者角度看,在后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日益被视为个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打破了传统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概念,会出现大量营利性短期教育机构,市场竞争和财政困难将迫使公立机构与私人企业、资本市场之间积极合作,公私界限将不再那么分明。四是人的思想屏障。由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传统的影响,我国一直存在向往大学学位看轻职业教育的倾向。这种意识又与地方政府和大学官员的好大喜功形成互动,导致短期高等教育机构以推动学校升级和扩张为其重要政绩。因此,转变观念是高等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2][3][4][5]卢彩晨.如何应对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下降:美国与日本之比较[J].教育研究,2010(11):102,103,103,105,105.
[6]Tsang M C.The cost of vocational train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1997(18):63-89.
[7]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编撰.2010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M].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4.
[8]王婧. 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规律[J].商场现代化,2011(8):46.
[9]何雪莲, 刘婷. 扩大内需:高等教育之困[J]. 现代大学教育,2010(2):18.
[10]美国高等教育走向市场化[EB/0L].http://learning.sohu.com/20060802/n244578442.shtml.
[12]罗杰·L·盖格, 唐纳德·E·海勒. 私有化与美国高
等教育财政的新趋势[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1):15.
[13]刘大立,李锋亮. 国外成本收益研究与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7(2):120.
[14]金子元久.高等教育的社会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3.
(责任编辑 于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