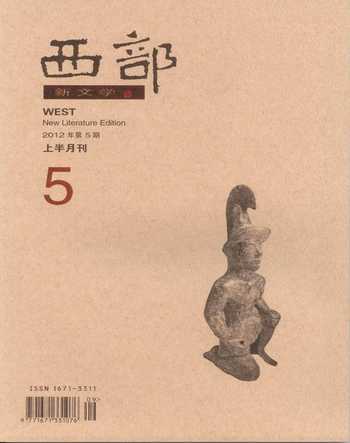一座石头城,一些魔幻事
李玉民
“平川、大路、三圣山、无名的一片片雾气,就连高山本身,从此都沉没在黑暗中,都像史前的庞大动物一样,开始搔自己的身躯,笨拙地打鼻息(我们真难以相信是走向一座高山,因为山的轮廓十分模糊,让人以为前面是一片夜色,只不过更为幽暗一点儿罢了)。我逐渐丧失了任何现实感的概念。我们的行进变成了一种完全盲目的迁徙,一种纯粹的漫步,一种在黑夜腹心的游荡。我感到自己丧失了思索的能力。我思考事情,过分习惯于在一座城市的墙壁之间,在十字街头,或者躲进一间屋里,这些熟悉的地点本身,似乎就能给我的思想理出头绪来,可是现在,远离熟悉的地点,一切变得不仅把握不住了,而且十分残酷了。后面大山的整个山体,几乎压在三圣山上,不慌不忙地咬噬它的脖颈儿。三圣山灵魂出壳了。”
这正是《石头城纪事》所营造的氛围。卡达莱带领读者回到那黑暗的年代,进入他童年——“我”的记忆中的吉诺卡斯特城,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黑夜走在魔幻王国里。
说“魔幻王国”,一点儿也不夸张。“我”的眼睛,连他自己都觉得是团谜,而透过这谜团所见的世间万物,无不具有生命而变幻,丧失了现实感,甚至化为妖魔鬼怪,不时在石头城为非作歹。
首先,这是一座要怎么奇特就怎么奇特的城市,仿佛是在史前,冬天一夜之间出现的。它爬上半山腰,“叫板了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的所有规则”,恐怕是世间倾斜度最大的城市。城里从街道到蓄水池,一切都那么古老,全是石头造的,就连房顶都铺着灰石板,犹如巨大的鳞片。梦一般的城市,永恒存在,锚定在现实中。尤其令人称奇的是,“在这无比强大的甲壳下面,居然还有鲜嫩的生命存在并且繁衍”。
不容易,在这样的甲壳下度过童年,况且又遭逢战乱,实在不容易。好在“我”这双孩子的眼睛,就像两台大功率的水泵,能同时吸入五花八门的形象,而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物、事件,通过记忆的秘密走廊而魔幻化,构成这个奇妙的“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大不过石头城及周围地区,但是好像有一种强大的磁极,从四面八方吸引来古代和现代版的神话、传说、童话、巫术、魔法,各路神仙、各种魔怪、各色传奇人物,甚至吸引来十字军、跛足独行客、意大利飞机、德国坦克……在石头城这个舞台上轮番登场,一幕幕演绎着“我”八载童年生活的经历。
纪德在1889年的《日记》中写道:“真正有趣的是作家看世界的特殊幻象,现实通过作家的眼睛所发生的变异。”
《石头城纪事》的最大特点,正是“我”所看到的世界的特殊幻象,童年经历通过“我”的眼睛所发生的变异。因此,这本书读来很有趣。
卡达莱所经历的童年,从大背景来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从预演到爆发,直到收场的八年。石头城处于多事之秋,人心惶惶,城头上变幻着意大利、希腊、德国等占领军的国旗,全城居民前途未卜,生活在大轰炸和妖术横行的惊恐之中。这样的大气候,特别有利于回忆的魔幻化(或者神话化、童话化):战争与儿戏、历史与现实、幻想与认识,以及传说、谣言、传统习俗等等,全搅在一起;城里发生的事件,无不带有神秘的色彩,城里一些人行为怪异,又都像传奇人物。
这些传奇人物和神秘事件,组成了本书的大脉络。把这些脉络梳理清楚,大体上也就能掌握“我”童年的那些事了。然而,作者在讲述过程中,多条线索齐头并进,反复间断地再现,总保持神秘的气氛。每个事件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每个传奇式人物都以不同的姿态上场,但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每个事件都留下種种悬疑,每个人物都引起种种猜测,差不多直到最后,神秘色彩渐渐淡去,才逐步交代清楚这些事件和这些人物究竟有什么关联。
有一些人物贯穿全书,在文中不时出现,并且带有悬念性,在阅读中应予以特别关注。首先是相当于石头城的记忆和眼睛的老妇人,以“我”的祖母,信息传播者杰乔,专门给全城新娘化妆,总把“全完了”挂在口头的皮诺大妈为代表。最活跃的要数杰乔,她几乎每次出现,都要宣布一个重大事件,她人未到先闻其声:粗哑的喘息。她身上裹着黑色大方围巾,一副躁动不安、忧心忡忡的样子,神秘可怕的事情经她那张嘴讲出来,就活灵活现了,总在身后播种惊慌和不安,让人怀疑她本人就装神弄鬼,用邪术害人。
像沙诺那样的老婆婆,都是传奇式人物。德军开着坦克进城时发出魔鬼一般的隆隆声响,杰莫大婶和沙诺老婆婆在自家窗口,有这样一段机智幽默的对话:
“他们干吗弄出这么大响动呢?没有这样震耳欲聋的闹腾,他们照样可以进城嘛。”杰莫大婶抗议道。
而老婆婆则回答:“他们全都一样,进来的时候,总是大张旗鼓,离开的时候,就一点动静也听不到了!”
他们,指罗马人、诺曼人、拜占庭人、土耳其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最后是黄毛德国人,先后占领过这座城市。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阿尔巴尼亚人民,由恩维尔·霍查带头,组织了游击战争,当地的一些男女青年,包括“我”的小姨,上山打游击去了。消息灵通的杰乔说,恩维尔·霍查正在打一场“新型的战争”,叫做“阶级斗争或者阶级之间的斗争”。祖母谢尔菲杰便大发议论:“应当相信,这个世界离不开战争。我活到这么大年岁了,还从未看到哪怕一天真正的和平。”
作者通过老妇人的口,间接地表达了他对自己的同乡恩维尔·霍查的基本看法,并不完全正面,而本书于1970年在地拉那出版,还是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当政,透露出这样的观点实属不易。杰乔这样断言:“这肯定是一场战争。不过,又不像其他战争。兄弟之间相互残杀,儿子打倒父亲。而这种事,就发生在他家里,在饭桌上。儿子盯着父亲的眼睛,凝视了一会儿,然后对他说,不再认他这个父亲了,就冲他脑袋开了一枪。”
为了证明所言不虚,书中又直接描述了几出“兄弟相残”的悲剧。游击队进城,有一个三人小组按名单惩处“人民的敌人”,他们来到皮匠马克·卡尔拉什的家,以“人民法庭”的名义,宣布处决马克·卡尔拉什父子。卡尔拉什申辩:“我不是人民的敌人,我是个普通的皮匠,为老百姓制作皮鞋。”他女儿也护住他,但是领队的独臂游击队员端着的冲锋枪一梭子打出,三个人都倒下了。恰巧这时来了巡逻队,一行三人,检查了判决书,发现多打死了一名少女,便逮捕了独臂游击队员塔尔,由塔尔的两名同志看守;随后又来了三人,负责审判塔尔。塔尔承认误杀了一名少女:“我只有一只手,右手被人民的敌人剁掉了。我用左手射击把握不住,我未能避开她……”负责审判的人说:“我们理解。游击队员塔尔·邦雅库,你要被处死,因为滥用革命暴力,你要被枪毙。”于是,塔尔高呼“共产主义万岁”,倒在自己同志的枪下。
雅维尔打死阿奸组织的头子——他的叔父阿泽姆·库尔提,第二天,意大利占领军“斗牛狗”式飞机从空中撒下花花绿绿的传单,只见传单上印着:“共党分子雅维尔·库尔提,在家庭餐桌上杀害了他叔父。父亲母亲们,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共党分子是什么东西!”当天晚上,市中心广场上堆了六具尸体,是在狱堡里枪毙的人,尸堆上的白布条写了一行大字:“我们就是这样回答红色恐怖。”到了次日拂晓,广场上另一头又出现一堆尸体,白布条上也写了一行大字:“这就是我们如何回敬白色恐怖。”
下午,二十九年足不出户,已经一百三十二岁的汉科老婆婆,忽然来到市中心广场,分别察看了两堆尸体。有个哭泣的女人问她:“为什么要流这么多血,你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们吗?”老婆婆茫然的目光没有注视任何事物,却似乎什么都看得见,她明确地说:“这世界在换血。人每四五年换一遍血,世界每四五百年换一遍血。这是换血的冬天。”
“我”和伊利尔在一片房舍的废墟上玩耍,看到一张用阿尔巴尼亚语和意大利语两种语言打印的公告:
现正在搜捕危险的共产党人物恩维尔·霍查:三十岁左右,高个头儿,戴一副太阳镜。提供消息协助抓捕他的有功者,可获一万五千列克赏金。谁能亲手抓住他,可获三万赏金。
本地驻军司令官:布鲁诺·阿尔西沃卡尔
这些事件的描述,多了史实性,少了魔幻色彩,在本书中算是例外,但是增添了现实感,同全书的气氛也相得益彰。
像沙诺、汉科这样一些老婆婆,已经跟石头城同化了,身躯没有一点儿多余的脂肪和肌肉,没有什么敏感的部分了,同时也摈弃了多余的欲望,如好奇、恐惧、激动,乃至对美食的喜好,只剩下那么一副恒久的石头城精神。她们对普遍性事物的认识,对“我”了解世界大有裨益。她们往往语出惊人,偶有行动,也锐不可当。沙诺老婆婆隐居了三十一年,有一天突然走出家门,要揍总纠缠她重孙女的意大利军官。别看她浑身皮包骨,青筋暴露,双手却十分有力,一把揪住那军官。意大利军官猝不及防,疼得尖叫一声,怎么用力也挣脱不开,便拔出手枪,用枪柄猛击老太太的手。沙诺老婆婆松开手,又紧紧握住,给那军官一顿老拳,打得他狼狈逃窜。老妇人也有身遭不幸的,皮诺大妈去给一个新娘化妆打扮,在大街上被德军巡逻队逮捕,他们从她口袋里搜出化妆的器具和铁夹子,判定它们与游击队炸坦克的地雷有关,她便被吊死了。她那纤细的身子在风中摆动,胸口挂着一块长方形白布,上面用日耳曼化的阿尔巴尼亚文写着:“破坏分子”。这些场景,都给“我”的幼小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
阿尔巴尼亚是男性主导的社会,话语不多的男人的行为,则引起“我”和伊利尔两个小伙伴更大的兴趣。伊利尔的哥哥伊萨和雅维尔这两个传奇式人物,在本书中占有特殊地位,他们因进行地下抗敌活动,说话吞吞吐吐,行为十分诡秘,甚至引起伊利尔和小卡达莱的误解和猜疑。他们藏有手枪,时常密谈杀人的名单,但迟迟不见行动,伊利尔就认为他们说大话。正巧传来一些青年上山打游击的消息,伊利尔突然质问他们为什么不上山,结果挨了哥哥一记耳光。两个小伙伴很气愤,来到院子,就冲窗口高喊:“打倒叛徒!”“打倒骨肉相残的战争!”
殊不知伊萨和雅维尔刚刚完成一个壮举:焚烧了市政厅,但是他们不露声色。市政厅里保存的产权证书等文件全焚毁了,这就要了富人的命。伊萨指出:“有人触碰财产权的祸根!”富婆玛依努尔太太发疯似的骂街:“这些穷鬼……对,就是这些欠债的人,放火烧了财产证书……是共产主义分子……”
“我”还不完全懂伊萨他们的解释,他的脸贴在玻璃窗上,眼睛凝望乱哄哄的街头,脑海里浮现这样的景象:“土地和房屋,都脱离了证书的支配,开始逃逸,失去控制,分散瓦解了。墙壁倾向于离开地基:下面固定墙壁的百年挂钩,已经断裂了。石头房舍在移动中,往往相互靠拢,发生危险。时刻有可能相互撞击,像发生地震那样坍毁。”每次看到一种现象,或者经历一个事件,“我”因为一时认不清,就会产生奇奇怪怪的反应,以魔幻式的、童话式的奇思异想,来补充他缺失的认识,把他的所见所闻在幻想中重新排演一番。这不仅给全书增添了特殊的魅力,也更真实地反映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判断,从个人好恶到是非辨别,是童年成长的一个漫长过程。卡达莱从童年起,就是这样逐步孕育未来作家风格的主要元素。因此,《石头城纪事》是一部生活入世和文学入门的作品,可以说是构成他的全部创作的基石。
神不知鬼不觉,伊萨的又一次壮举,似乎回答了伊利尔的质疑。这次他打死了意大利占领军驻本城的司令官,正是通缉恩维尔·霍查的布鲁诺·阿尔西沃卡尔。数千户人家的窗口纷纷探出头来,这座城市在观看送殡队列,侵略军的头子躺着走了。敌人疯狂报复,拂晓在市中心行刑,绞死了伊萨和两个年轻姑娘。有人告密了,雅维尔的叔父——民族阵线的头子阿泽姆·库尔提,同马克·卡尔拉什的儿子一起,参加了杀害伊萨的行动。受通缉的雅维尔,当天晚上就去他久未登门的叔父家,假意表示悔改,在餐桌上听他叔父描绘屠杀的过程,随后便亲手枪决了这个凶恶的敌人。
告密者是谁,仍为悬念,也必须遭到惩罚。纳佐婆婆家是邻居,有两个人“我”经常见到,一个是纳佐的美丽的儿媳,另一个是中了邪的马克苏特,纳佐的儿子。纳佐与儿媳时常到“我”家串门,或者在家门口纳凉,“我”受少妇秀美而忧伤的面容的吸引,总爱在附近玩耍,每次看见马克苏特从市场或咖啡馆回来,腋下总夹着一颗断头(“我”的幻视)。马克苏特在文中十数次出现,总是腋下夹着断头这副形象,除了眼珠突出势欲射出去之外,再多一笔也没有交代,显得十分邪恶而神秘。“我”特别憎恶他,就要模仿自己看的第一本书——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中的情节,与伊利尔多次商议干掉马克苏特,割下他的头,用盐渍上。杰乔果然得到消息,说马克苏特是奸细,告发了伊萨,还向德国人提供情报,引德军入城。这个行为诡秘的人,至此真相大白,不待两个孩子动手,他就横尸在家门口。“我”看到尸体上的纸条写着“这就是奸细的下场”,认出那正是雅维尔的笔迹。
这些人物和事件,这样粗线条讲起来,不如看书有趣,因为书中的情节掺杂着大量妖法巫术、神秘的传说,充满了时代感、地域色彩和民族特点。关于邪术害人,老婆婆们也有非常明智的说法。她们根据以往的事例,说明通常在严重事件爆发的前夕,暴风雨欲来之际,人的灵魂开始像树叶一样战栗,于是邪术就要大行其道。无形的手在全城各处置放邪祟之物,都用废纸或者脏布片包着,让人看着会恐惧得打寒战。“我”家的蓄水池中了邪,不再冒泡了,于是全家总动员,雇用淘水工,由街坊邻居帮忙,将池水淘干,换了新水。一种厄运抛到楚特家的房顶,兄弟就反目成仇,无休无止地争吵。本城唯一致力于发明的居民迪诺·齐索,家里也有同样遭遇,要发明特异功能的飞机,计算也被魔法搅乱了。还有一些少女,也发生了可疑的变化,切曹·卡依尔的女儿长出了胡须,阿基夫·卡沙赫的女儿成了“浪货”,肯定都中了邪术,“不可能有别种解释”。总之,全城居民,正如荣格所说的,患了“集体精神病”。
不可能有别种解释,这是作者凭借童年的记忆狡狯的笔法,邀读者同样从童心童趣阅读欣赏,随同“我”及其小伙伴们到各处寻找“巫球”,找见之后欣喜若狂,最后点燃烧掉,再浇上几泡尿。这种儿戏纳入了历史的大环境、大气候、大事件中,就不再是简单的儿戏,可以全面地反映战乱时期民众的心态。预卜未来,也是石头城居民前途渺茫的心理表现。谁家杀公鸡,都要仔细观察鸡骨架,唯恐发生大灾大难。“我”的祖母拿着公鸡骨架子,眯缝起眼睛,冲着阳光转著个儿观察许久,声音低沉地宣布:“战争。胸骨边缘是红色的。战争和流血。”“我”也模仿祖母,午饭后偷偷拿走显示凶兆的鸡骨,跑上三楼独自察看:“冷却的鸡骨托在我的手掌上,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淡红色接近紫色,我忽而觉得它溅上了血点儿,忽而感到它闪耀着一片烈焰的火光。渐渐地,它完全变成了红色,而且在它扁平的部位上,已不再是血滴,而是鲜血的湍流,从高坡冲下来,一路染红了所有东西。”实物,到了“我”的眼下便幻化,模仿大人的行为,在他童年的想象中得到升华。
模仿,是人的天性,更是孩童学习的主要方式。“我”在姥爷家附近的岩洞里,同小女孩苏珊娜拥抱的场景,就是模仿本城发生的一出爱情悲剧。这一悲剧牵连一系列奇奇怪怪的事件和传闻,其余波几乎贯穿全书,成为这部作品另一条重大线索。在这座城市,如果说不管发生什么事,该结婚还是照样结婚的话,那么爱情却始终是禁物。千百年的习俗,并不会因为战争而改变。“我”的小姨勇敢拒婚,上山去打游击了。在“我”家的地窖里躲避空袭时,趁油灯被震灭之机,卡沙赫的女儿同一个陌生小伙子搂在一起。卡沙赫不顾飞机狂轰滥炸,揪着头发将女儿拖到大街上,那个小伙子也赶紧溜走。妇女们都骂那姑娘是“浪货”、“荡妇”,“跟意大利女人一个货色”,而男人们始终跟大理石一样沉默。只有伊萨眼神忧伤,雅维尔从牙缝儿中挤出一个词:“爱情”。这就是对千百年来的禁物——爱情——全城人所持的不同态度。
爱情,既是禁物,就引起孩童本能的好奇。有好几回,“我”对着衣柜镜子,“哈上水汽之后,嘴唇便贴上冰凉的镜面。‘我亲吻的印迹便留在上面,冷冰冰的,毫无乐趣,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在这座城市里,爱情同死亡相伴。再也没人见到卡沙赫的女儿,这事甚至惊动了警察,卡沙赫推说他女儿去了他表兄家,无从查起。在堡垒的塔楼上,“我”同那个陌生青年不期而遇。那个眼神不安的黄头发青年向小男孩打听卡沙赫的女儿的下落,他说在这座城市,有两种方法让怀孕的姑娘消失,“一是用鸭绒被和垫子捂死,二是投进水井里淹死”。最后他还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如果在人间找不到她,我就下地狱去寻找。”已有一段时间,传闻有个怪人,或许一个幽灵,夜间下到街区的水井里。起初老婆婆们猜测,大概是一个名叫朱阿诺的人,在争夺财产中遇害之后化为鬼魂,回来寻找他藏匿的黄金。就在民间闹鬼的时候,当局悬赏四万列克,捉拿焚毁市政厅的纵火犯,第三天夜晚,警察就发现一个人形迹可疑,老远就闻到煤油味,只见那人行色匆匆,手上拎着一只煤油瓶,跟踪了一段路,就把他逮捕,从他身上搜出一盒火柴,肯定是纵火犯无疑了。
拥抱过卡沙赫女儿的青年,就是纵火犯,真是双料的轰动事件。但是作者行文狡猾,并不过多交代和纠缠,由老妇人交谈而轻轻带过。不是他放的火,“夜间他下到水井里,寻找那姑娘”。“夜间,下到水井里?主啊,爱情能把人拖到什么地步!”这个事件似乎到此为止,然而正如书中写的:“发生一个令人不安的事件,总会有一个新的事件来添乱。”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又要排练这出爱情悲剧了。
五六岁六七岁的小男孩,人事未通,对“美人”却很敏感,“我”特别看上了纳佐的儿媳(与爱情悲剧相应的不幸婚姻)、吉卜赛女郎玛格丽特(姥爷家一年夏季的房客),但是,真正能跟他玩在一起的,只有一个叫苏珊娜的小女孩,是他姥爷家的唯一邻居家的姑娘。“我”每次去姥爷家,都会见到苏珊娜,向她讲城里的事,有一回还因为玛格丽特而冷落了她。谁都夸苏珊娜模样长得俊,她轻灵得像蝴蝶或者仙鹤。这次“我”一到姥爷家,就有了感应:“一个年轻的美女发出了警报……是她在飞旋。她的白色翅膀在阳光里闪闪发亮。她在一瞬间现身,仿佛云开从天而降,随即又消失了。”“我”一开院门,果然看见一条铝灰色衣裙。苏珊娜听他讲了讲城里的事,最打动她的,就是阿基夫·卡沙赫的女儿的遭遇。她要求他再详细讲一遍,而她的“眼睛、头发、纤弱的胳臂,全身各个部位都凝注倾听”,最后长叹一声:“这世间出了多少怪事啊!”于是,两个孩子把岩洞当做地窖,开始演练这段爱情故事。“她伸出手臂,搂住我的脖子。她的光滑脸蛋儿贴到我的脸蛋儿上。”一个说:“现在,我被人揪着头发拖走……你怎么办呢?”另一个回答:“我就下地狱去寻找。”这种小游戏排练了好几回,“我”还真喜欢上了:“我从未体会过的一种倦怠,让我时而感到萎靡不振,时而又感到一种翱翔的醉意。”不过,这出模仿的爱情剧的结局却出人意料。
作者自述,在童年模仿的这两出戏,并不是偶然的。照搬剧本《麦克白》中的场景,设谋杀了马克苏特,是他通过模仿向书本学习;搬演卡沙赫女儿的爱情故事,是他通过模仿向生活学习。未来的作家,就是这样培练出来的。
“我”受好奇心的驱使,深入词语王国,逐渐认识了词语王国的专制统治,于是他身上发生了一件怪事:听人重复几十遍的说法或词语,在他的思想里突然产生了新的涵义,摆脱了通常赋予它们的意义。如果他听人说“我的思想沸腾了”,他就不由自主,把一颗脑袋想象成煮开的豆角锅。再如当地一些诅咒的表达方式:“但愿你能把自己的脑袋吃了!”这便引起他的幻觉:一个人两手捧着自己的脑袋大啃特啃,可是他又困惑不解,牙齿长在自己头上,又怎么能啃自己的脑袋呢?常用的语词,在他的头脑里活蹦乱跳,好似群魔乱舞,完全冲破了逻辑和现实的界限。这正应了皮诺大妈“全完了”这句话,全宇宙都分崩离析了,卡达莱必须用聚积了巨大能量的词语,重新创造他自己的世界,也就是本文开头所引的那种魔幻王国。
在“我”看来,一户壁炉的炊烟,就是一种近乎空想的梦幻;就连城市也发起高烧,“我看见玻璃窗瑟瑟发抖,我甚至看见它冒出灰不溜丢的汗水”;夜晚,探照灯亮起它的独眼,它就是独眼巨神波吕斐摩斯……河边那条大路,见证了多少历史和现实的重大事件,也是他幻想的大舞台:“我就是这样,在这条大路上布置了十字军和那个跛足的独行客,同时搅动起一系列事件。我让那些骑士原路退回,让他们的剑和十字架杂乱无序,并且派一名使者突然向他们宣布,有人已经发现了基督墓,于是我看到他们像一个人似的,冲过去要重新打开那座墓。十字军一旦隐没不见了,就是腾地方给跛足的独行客,他蹒跚而行,走啊,走啊,永不停歇。”
抑或这就是卡达莱创造他的文学王国的方法吧?
本书的结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叙述的两章之间,添加两段独立的文字。一是用仿宋体(原文为斜体),以示与正文区别,二是有“纪事”的小标题;仿宋体部分好似剧中人物的旁白,而“纪事”部分则类似画外音。一是作为人物见证,一是作为史料见证,旨在增加可信度与历史感。
久违了,阿尔巴尼亚!经历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估计都还记得,在恩维尔·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朋友。在那个年代,恩维尔·霍查给中国领导人发来一封贺电,就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极大鼓舞;能看上一场阿尔巴尼亚电影,就是一次极高的精神享受了。四十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阿尔巴尼亚的音信,我也只记得那种“鼓舞”和“精神享受”,卻想不起看过什么电影了。这回就像久违的故友重逢似的,我发现了卡达莱和他的《石头城纪事》(当然是这套丛书主编提供的机会),套句俗话,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因而喜爱之情,应当溢于笔端。四十多年前对阿尔巴尼亚的了解,仅仅限于两国的友谊和几个电影镜头;而现在跟随卡达莱,游荡在石头城的大街小巷、堡垒广场,结识战争年代的这些老婆婆、这些青少年,就能重新认识这个极有特点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去掉魔幻色彩,山鹰之国的石头城,也值得在书中一游。
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于1936年出生在吉诺卡斯特城,在故乡读完小学与中学后,进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学习,毕业后由国家派送到苏联高尔基文学院深造,掌握了俄文和法文。1961年,苏阿关系破裂,卡达莱回到地拉那,先后在《光明报》、《十一月》杂志、《新阿尔巴尼亚画报》任编辑。他喜爱诗歌,从中学起就开始创作,1963年发表长诗《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赢得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赞扬与好评。随后又发表了长诗《山鹰高高飞翔》(1966)和《六十年代》(1969),构成了组诗的三部曲。此外,还先后出版诗集《少年的灵感》(1954)、《幻想》(1957)、《我的世纪》(1961)、《太阳之歌》(1968)。这些诗作确立了他作为著名诗人的地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卡达莱的创作转向小说,而且同样丰产。创作的长篇小说有:《亡军的将领》(1964—1967)、《婚礼》(1968)、《城堡》(1970)、《石头城纪事》(1971)、《一个首都的十一月》(1975)、《伟大孤寂的冬天》(1973)及其修订本《伟大的冬天》(1977)。此外,他还出版了数种中短篇小说集,如《南方之城及其他短篇小说》(1968)、《从前的徽标》(1977)、《三孔桥》(1978)、《头脑冷静》(1980),以及儿童文学作品《阿基罗公主》(1967)、《在兵器博物馆里》(1978)和《城堡和毒品》等。
卡达莱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能熟练运用现代写作手法的多产作家,既继承了民族的文学传统,又善于向近现代外国文学汲取新的营养。他的几部主要的长篇小说早已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广为流传。卡达莱已移居法国,他的作品大部分在法国出版了,在法国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石头城纪事》中译本所依据的法文本,是得到作者首肯的优秀译本,能让我体会到原著的精髓。
《石头城纪事》,是卡达莱童年的记忆,截至1944年,其实还有续集,是回忆少年时期的三部曲,背景始终为吉诺卡斯特,写他十二岁至十五岁的经历。总题为《三时段》,包括:《初步写作时段》(1984)、《爱情时段》(作于1986年,发表于1990年),以及《金钱时段》(作于1996年,发表于1997年)。作者假托回忆,展现了各种虚幻(或魔幻),让人全面领略卡达莱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