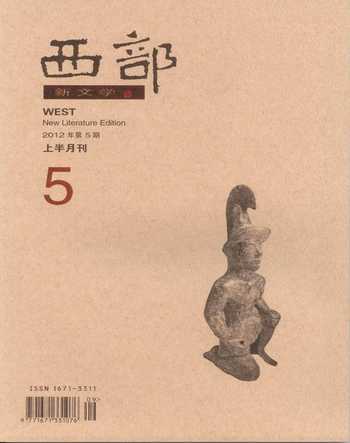西部文学话语的迷思
刘大先
2007年秋天,我和几个朋友在新疆拍纪录片,沿着喀纳斯——阿勒泰——塔城——伊宁——喀什——克孜勒苏——红其拉甫一线迤逦南下。从北疆到南疆,不光是地理风景的差异,也是人情、物事和文化的冲击,那种目不暇给的体验非亲身经历无法言说。新疆是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处,是几大宗教的折冲之地,是世界著名的人种博物馆,是数十种已死或者依然活跃的语言文字的运用之所……此地的丰美和复杂,让本地人难识庐山真面目,让来过的人乱花渐欲迷人眼,让没有来过的人隔岸红尘忙似火。
从喀什驱车至塔什库尔干的路上,起先平淡无奇,路边是荒芜的土冈,满目土黄的苍凉,为了打发旅途的困倦,也害怕司机睡着了,我们开始玩各种提神的游戏。车子逐渐进入高原,漫长绵延的喀喇昆仑山遥遥在望,雪山带来的冷风干燥而凌厉。沿着公路的边上,悬崖之下是一条浑浊湍急的小河,断断续续始终跟随着我们的车。赭红的高山下是布满石头的平滩,灰白的色调中曲折前行着青黑色的河水。我想到了岑参的诗句:“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这个自然而然想起某句诗词的瞬间,其实暗合了一个外来人认识新疆的基本模式——我们总是通过书写来认识一个陌生的地方,无论这种书写是口头的歌谣、故事,还是书面的诗歌与散文,抑或影像的记录与虚构。后来我到新疆的其他地方,在果子沟想到的是闻捷的《天山牧歌》,在奎屯想到的是碧野的《天山景物记》,在那拉提草原涌上心头的是叶舟的《边疆诗》,“那些美,藏在鞋子里,走过边疆。 那些鞋子,藏进灯盏里,放入天山”。文学事实上成了我们认知陌生地方的形式,反过来说,我们所能感知的陌生地方其实是文学和形象的地方。
数年间,我走过青海湖畔的油菜花田,踏过甘南草原的葳蕤花草,登上西藏纳木错湖边的石山,漫步在陕西北角的黄土高坡。这些地方,总是与文学纠结在一起。它们浮现在海子、沈苇、阿信的诗歌中,在色波、张贤亮、路遥、陈忠实、石舒清的小说里,在周涛、马丽华、刘亮程的散文里。“西部”、“文学”和“西部文学”三个词语形成难以割舍的关联。
西部文学是个艰难的话题。写下“西部”两个字,首先就要谦恭地面对自己的浅薄和狂妄。“西部”是什么?它是一块疆域,一簇文化,一种想象,还是一束话语?它是形容词,是名词,还是动词?我们如何观看、凝想、反思它?
“西部文学”是一个无法界定的词语,它如同西部本身一样,从来就是个含混的所在。这个词是1980年代中期,随着西部地区题材的影视文艺作品—— 比如《黄土地》、《盗马贼》、“西北风”的流行歌曲——的轰动一时,而引发出的文学的自觉命名。这样的命名在最初回响着十八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遥远回声,又正应和着国内文化热的浪潮,在寻根的流风中如同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当然,如果从更广阔的背景看,美国西部小说的示范效应则是直接的启发,两者在美学风格、人物类型、主导精神上都有可以类比的地方。而一当“西部文学”发生之后,它就成了一个语词的弗兰根斯坦,自行成为一种具有自动功能的话语。
在西部文学史谱系追溯中,汉唐描写边塞的诗歌被归置为其原初的源头。然而,边塞从来都是随着疆域的变化而伸缩进退的。1893年,美国向西扩张到太平洋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重新创造了美国社会中的“边疆”概念,将原先大陆的边疆推进到太平洋。而中国的“西部”作为边疆也有着自己的盈亏消长。汉代最初的边塞在如今甘肃临洮、陕北榆林、山西雁门关到北京、辽宁凌源一线,过了天山就是西域各国了。唐朝的边境范围扩展,设安西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南直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的辽阔地区,设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广大地带。宋明两代疆域萎缩,1755年,清击败蒙古准噶尔部,“故土新归”,将收复的天山南北地区称为新疆。
1980年代中期热闹的“西部文学大讨论”中所说的“西部”是个笼统的概念,大致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陕西五省,从地理版图看,是所谓的大西北。2000年中国中央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将内蒙古以及原先西南一带的贵州、四川、广西、云南、西藏等都囊括在“西部”之中,此后的论者再讨论西部文学时,地理范围就扩大了,从审美旨趣和基调来说,也更加多样化乃至泛化了。
“西部”的内涵和外延流动不已,西部文学也是如此。“西部”宏大的图景中包含了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因素,这种多元性完全超乎一般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概念框定。丁帆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的西部就仅指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区,这实际延续了西部文学大讨论时的地域观念。其实,实际的文化地理学在有关“西部”的想象和书写中并不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实际上回过头看,1980年代西部文学大讨论中,“西部”被抽象化为一个形而上的存在——尽管从现实历史层面来看,关于西部的认知同萨义德讨论的“东方学”并不具有类似的殖民背景;从话语运行的实践来说,西部倒确实成了“忆念性的不在场”。
“西部”如何诞生?或者说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其发生学的现代全球背景尤为耐人寻味。前现代时期,“西部”所表征的那些空间与文化一直存在于那里,但唯有经过十九世纪 “文明论”的透镜,在文明/野蛮的尺度下,它才如同那些最初的外来者拍摄的底片一样,在内涵各异的显影液下渐渐浮现出黑白分明的影像。
从1876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进入罗布荒原,到1927年德国的艾米尔·特林克勒独行塔里木,域外探险家对中国西部的“地理发现”持续了半个世纪。1900年,斯文·赫定发现被埋藏了一千六百多年的楼兰古城;然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发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和尼雅遗址;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在清理地震后的流沙时突然发现了藏经洞的秘密,从而招来了世界各地的劫宝者:俄国的科兹洛夫,瑞典的斯文·赫定、沃尔克·贝格曼、贡纳尔·雅林,英国的D.布鲁斯、奥利尔·斯坦因、两位外交官的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与戴安娜·西普顿,法国的邦瓦洛特、伯希和、大卫·妮尔以及传教士蜜德蕊·凯伯和法兰西丝卡·法兰屈,日本的河口慧海、大谷光瑞、橘瑞超,德国的馮·勒柯克、艾米尔·特林克勒,美国的亨廷顿、兰登·华尔纳,丹麦的亨宁·哈士纶,等等。这些西方探险者、旅行者目的不一,或者带着拣拾历史碎片和文明断简的祈求,或者带着传教和寻道的理想,或者带着掘宝之梦,或者是作为殖民帝国的前哨和先锋……一批批西来东进,踏上了漫长古道和人迹罕至的旅途,用不同的方式经历了在中国西部广大区域的考察和游历。
尽管这些域外探险者的文化差异和探险目的不同,他们的书写却制约和影响了此后文学书写和文化记忆中 “西部”的构筑以及对西部文明的传播。这个过程颇具东方学色彩,比如维吾尔族的经典《福乐智慧》原抄本今日依然保存于瑞典。然而其意义也并非全然负面,而这些人的行动和书写其实已经超出了游记文学这一狭小的范围,是最早将“西部”的历史时空纳入到全球视野中去的,经由他们的“发现”,吊诡地反转性地促使了中国国内的文化再发现。
正因为最初西部被外来者首先书写,造成了晚近西部书写者长久萦绕不去的主体性言说的焦虑。在“西部”尚未作为一种言说对象树立于二十世纪之初时,星罗棋布于这片广阔土地的人文阜盛而多元,不同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的人群自成一体,交通往来,有各自的言说和书写传统,花儿、柔巴依、哈萨克的歌谣、穆斯林的经卷,纳瓦依、尤素甫·哈斯·哈吉甫、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他们并行不悖,如同驱赶着羊群的风,吹拂在辽阔的西北大地之上。我的同事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翻译过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在其开篇,伟大的歌手居素普·玛玛依唱道:
让我荡漾起歌声吧,
用世上最美的语言。
它是我们祖先流传下的语言,
它是战胜一切的英雄语言;
它是难以比拟的宏伟语言,
它是繁花似锦的隽永语言。
它是我们先祖创造的绝世语言,
它是后人传承的精美语言;
它是如种子般繁衍的语言,
它是让人们倾慕敬仰的语言。
它是我们代代相传的语言,
它是我们辈辈相继的语言,
它是先辈讲述的语言,
它是后人不断传承的语言;
它是人世间最美妙动听的语言,
它是世界上最壮丽辉煌的语言。
无论经过多少世纪,
它都是与我们同生共死的语言。
它是滔滔不绝绵延不断的语言,
它是与世界共生存的语言。
它是超越宇宙的伟大语言,
它是比太阳还要耀眼的语言,
它是比月亮更加明媚的语言。
这样波澜壮阔、大气磅礴的铺陈是无法用排比来归纳的,它是英雄史诗独有的繁复、比喻、夸张、杂沓、赞颂——我在引用时还省略了至少几十句类似的颂辞。中国古典文学的正典系统中,大约只有汉赋才可能有这样的格局。只是这种多元的声音从启蒙文化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于一体的书写模式中遭到了压抑——它们因为无法进入现代西方传入的文類观念中,而不得不成为文学中的“小传统”,西部丰盛的传统文类倒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不得不在外来者的书写中以风情化的格调向强势文化的世界展示自己的面容。
像一切具有辩证色彩的启蒙话语一样,外来者的西部书写在本土滋养了它的逆子。地方性声音在1980年代之后日益生发出一个疑问:从渊始来说,被他人言说固化下来的先验西部,如今如何言说自己?那个先验的西部是个充满浪漫风情和异国情调的神奇地方,不同民族的游牧文化与中原内地的农耕文化和都市文化在此处碰撞、融合,独特的宗教底蕴和不同身份的作家自身所独有的生命体验与个性等诸种因素相互交融,形成了集自然蛮力、超越神性、传奇流寓与慷慨悲情于一体的美学风貌。
然而,很快人们发现,这个抽象的“西部”不过是个玄谈,而关于“西部精神”的总结不过是种人性论的幻觉,其实是现代社会等级秩序的话语霸权下的产物。“西部”还是一个外在于现代世界之外的异质性存在,这种存在之所以是必须的,正是为了树立这样一个他者,而确立现代主流自身的位置。后者可以将西部作为某种多元因素的参照,以彰显自己的包容性和囊括一切的自信,也可以将之转化成可以被自己消费、挪用和榨取文化资本的原材料。
因而,另一种反抗的姿态出现了。“西部的主体”于是成为一个话题,即带有还原论色彩的向西部地域意识的诉求。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这可以算作是对于“被发现”的应激性反应。西部要求在场,书写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是第一个需要剖解的迷思。
在被纳入“西部文学”的早期文本中,比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张贤亮的《绿化树》、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跃动于其间的叙事者与主人公,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角色,带有强烈的启蒙理性的宏大主体色彩,不像后来更多侧重于地方性、民族性和区域性特征的“西部主体性”,而后者则强调前者的空洞与自身的体贴入微。这里涉及人类学上常见的本真性命题,即:是否本土性、局内人的书写就一定高于他者性、局外人的描绘?西部有无一个可以统摄一切的主体?这显然是个伪问题,但是并不妨碍许多人把“西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只是任何一种书写模式的选择,都必然是对另外视角的忽视(如果不是有意遮蔽的话),所以真理从来都是片面的。因此,“西部”如果呈现出了自己的“主体性”,那也必定让人惊愕——那不过是由各种纵横交错的经纬组成的、活泼流变不已的西部已经死去的的尸体,只是人们“从来没见过这么一张颜面如生的死者的脸”。
第二个迷思是常见的“边缘的活力”的说法。在这样的认知范式中,异域、少数族群、从属文化存在的意义在于——“拓展和重构了中国文学的总体结构,丰富和改善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改变和引导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参与和营造了中国文学的时代风气”。“西部”作为边缘,在这样的文化交流话语模式中,往往成为某种特定理念、价值、精神,或者是关于他者性的寓言化代言物。书写者营造出一种真实的谎言,西部在这样的营造中,通常都会变成一个替代性的精神家园或乌托邦——借用异域来表达对自身文化真实性和价值的质疑与反思——西部因而被神话化了。这个不及物的神话,存在的理由是为主导文化提供补苴罅漏的存在,其思想原型是“礼失而求诸野”的悠久传统。
美国西部文学中的灵魂人物——牛仔和警探,成为符号化的偶像,“西部风情”和牛仔、盗贼与警探出没的小镇,成为后来旅游业想象力和物化的源泉。与之类似,在中国的西部话语中,浪漫主义赋予了想象中的荒野和生活以新的意义:它或者成为匮乏的填补,西部充沛的生命元气和蛮荒的力量,为都市化和现代化中的堕落、颓废和城市病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或者成为救赎的源泉,西部的生存智慧、宇宙观和生命观的感悟纾解和拯救了疲乏苍白的东部灵魂;对于西部天地大美的赞叹与认同则充实了杏花烟雨江南和骏马西风塞北的优美、雄浑和崇高。至于它可能具有的龃龉、污秽、含混和暧昧,则被丢掷一边,如果有那也只是作为映衬的辅助性存在。想想张贤亮打造的西部影视城,那是个如何游离在现实与虚构之间让人心驰神往的飞地。
如果从逻辑链条上来说,边缘和中心的二分法内在于主导话语的权力关系。在现代以来文化史的讲述中,边地、边疆和边缘总是被当做一种催化剂或者兴奋剂,在中原文化过于成熟、陷于精致、溺于疲软的时候,那些或游牧或渔猎的边疆兄弟们,以他们天然未泯、刚健质朴的生命力,一轮又一轮地冲击着中原文明,给暮气沉沉的帝国文化带来新一轮复苏的活力。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在彼此血的交融、乳的哺育中牢固地结为一体,长城内外才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故乡。但是,在这样的表述中,边缘从来都是补充,他们存在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证明特定文化所具有的自我恢复能力。何谓“边缘的活力”?难道边缘文化和主流文化从来不都是互动的、流通的吗?所谓的边缘在成为补充之前,难道不具备其自身圆融的价值?是不是如同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它们真的在现代性中不可避免地成了牺牲品,成了“废弃的生活”?它们难道只是在这片次文化的废墟中,我们寻找到可以被现代性回收再利用的碎片?
隐藏在这两种习以为常的西部观念之下的是第三种不那么显著的迷思:“时间的他者”。从“流放者归来”的右派作家的现代性启蒙到知青作家的浪漫追忆,再到先锋派的叙事革命和形式探索,西部文学成名于伤痕和反思文学,曾经的顶峰在于至今依然余脉不断的寻根文学。很大程度上,“西部”是乡土和农牧写作的根据地,现代性与全球化的迷狂似乎只是发生于都市的蝴蝶尖叫。西部似乎是以东部的滞后的、迟到的学习者和模仿者面目出现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迟到的现代性”思路,而西部文学话语中,究其实是全球化与中国西部这样一个普遍时间与特殊空间的置换。
然而空间本身无法增添附加值,如果有也只是沙滩上画的那张脸。西部不具有普遍性正如它不具有特殊性一样,它只是个和西南或者东北类似的地理划分,我们完全可以像命名“西海固文学”一样,命名“北大荒文学”。西部显然无法用“丝绸之路”这样古老的符号化形象加以概括——这里差不多是世界上离大海最远的地方,它就像一块海绵,吸足了东南西北各种各样的文明因子。天竺、波斯、华夏,希腊、罗马,闪米特的两河、希伯来以及后来的阿拉伯,再加上那个动辄就潮水般席卷中国、西亚和欧洲的游牧草原文化,都把它们物质的、精神的底色打在这里。它从来都是光谱复杂、炫人耳目的所在,并向远方,尤其是向东贩运、照耀或辐射。然而,在患了“时差症”的人们眼中,西部成了一面镜子,像乔纳森·费边所批评过的人类学家们一样,中国内地、印度、中东、近东、远东和欧洲的文化在这里寻找自己的面孔,希望照出自己年轻时候的模样。
特殊空间“西部”的时间在上述书写中被否认了与主体时间的同代性,它的时间可能是个神圣的时间、过去的时间、未被驯化的时间,或者干脆静止的时间,而不是习见的世俗时间,当下的时间、进化论的时间。一句话,西部成为了主流时间的“他者”,而无论西部主体与外来者如何汲取活力,都免不了自我殖民化和狭隘化的嫌疑。怀旧总是在事情不发生的地方产生,冯玉雷在《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中写的就是这些在寻找现代性已经不复存在的“失落的文明”的冒险者。然而,文明何曾失落?失落的是人自身。文明就像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有迂回,有回漩,有激流,也会搁浅,并不会停驻在某个隐蔽的角落成为可以被放大镜窥测的化石。
我当然并非要解构“西部”及“西部文学”的存在,只是指出它作为一种话语可能存在的似是而非、南辕北辙的迷思。在那些迷思中,西部文学的幽灵游离在日常、切肤、可感之外,而流行的“重构西部”的话语又总让人想起行政指令似的机械和刻板。再回头读王蒙的《你好,新疆》,或者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反倒会感到一种接地气的踏实感。再抬头读沈苇的诗句:“我用这一首《混血的城》/推翻、改写另一首《混血的城》”、“一个噩梦颠覆一个边疆的夏天/一个夏天颠覆一整部《新疆盛宴》”,“拿什么来修复我们的城/我们的‘美丽牧场?”这是对于西部迷思的重击,凸显的是西部文学真正的力量。西部文学显然未必非要是地方性知识的汇总,本土性意识的展露——当然并不排除它们——它应当是更具有锋芒、包容、超越、及物的性质。2011年5月,我到兰州参加“西部文学论坛”,见到一个藏族朋友,她并没有写任何所谓具有藏族文化特征的小说,是个非常好的当代作家。她集中于都市女性情感的书写,但你能说她的书写不是“西部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写到这里,我又回想到最初去塔什库尔干的夜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窗户没有拉窗帘,帕米尔高原的月光如昼,干燥冰冷的光辉打在屋子里,精神清明,光洁洞烛。坐起来从床上望过去,乌云中间一轮皓月高悬在山顶上,起伏的山脉如同铁一般沉穆,四周寂静无声,仿佛宇宙间唯有我一人存在。心灵在那个时候变得饱满、充实、盈洁,辉煌壮大、无可匹敌,沛然莫之能御。
那样的时刻,并不是什么启示性的时刻,却是一个西部体验诞生的时刻,西部和自我在那时都呈现出澄明的状态。无需洞察,自己呈现。
栏目责编:舒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