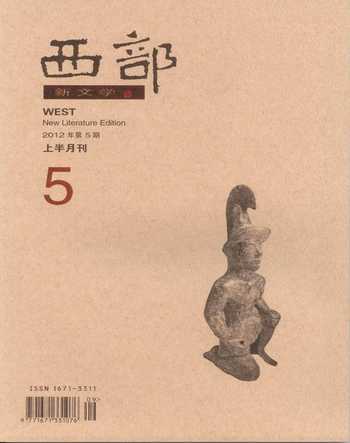冰湖
康剑
你有过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乘一叶扁舟乘风破浪的经历吗?我有过。但不是在大海上,而是在寒风刺骨的喀纳斯湖的湖面上。
这一年的冬季来得特别晚。往年,十月中旬喀纳斯准时要下第一场雪,而今年,到了十月底,老天爷才纷纷扬扬地下起第一场雪来,而且一下就是一场鹅毛大雪,仿佛要把前一阶段欠下的账一次补齐,把喀纳斯湖周围的群山和谷地都严严实实地覆盖上了。
双湖管护站两名留守的护林员还没有来得及撤出,他们被厚厚的积雪围困在了管护站所在的山顶。在喀纳斯,到了冬季,海拔每上升一百米,气温就要下降一度以上。双湖管护站的海拔比喀纳斯湖口要高出一千米以上,现在的温度至少在零下二十度左右。必须要救出这两名护林员,他们的给养已经用尽,而且暴风雪和即将到来的严冬正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清晨七点,天空阴暗,四周漆黑。我们借助手电筒微弱的光,踩着过脚踝的积雪来到湖边。黑暗中,鹅毛般的雪花在手电筒光柱中垂直落向地面。消防队员已经将冲锋皮艇停泊在码头等候我们,发动机发出突突的声音。这时的喀纳斯湖湖水还未达到冰点,湖面尚未结冰,湖水阴冷刺骨,有节奏地拍打着码头和湖岸。
刚坐上皮艇时我们几人还很兴奋,因为从来没有人在这个季节能够荡舟湖上。但当皮艇开到湖面上,我们才发现,越往湖中央走风浪就越大,我们的皮艇简直就像一片树叶,被风浪随意地拍打,而且,随时都有被打翻的可能。要知道,这个季节,人走湖空,所有的游艇都已停泊在岸边,偌大的湖面此刻只有我们这一个的皮艇,若是出现意外,连救生的船只都没有。
为了确保安全,我们选择湖面最窄的出水口处,由东向西,径直穿越湖面,把皮艇开到喀纳斯湖的西岸,沿着湖岸慢慢向着四道湾开去。
天空开始变得蒙蒙亮,湖面上空和四周都是铅灰色,仿佛凝固了一般。深蓝的湖水被沿山谷逆流而上的寒风吹满皱纹,到了近处,这皱纹就成了风浪。逆流而上的山风碰上顺流而下的湖水,就形成了鱼鳞浪,波浪短促而高大,搅得整个湖面像沸腾了的一锅开水,愈往湖心,波浪就愈加凶猛。
喀纳斯湖西岸的一处处湖湾,形成了一个个避风的港湾。就是在这样的避风处,风浪依旧汹涌,我们的皮艇在风浪中颠簸着逆流而上。湖面的波涛被寒风垂直揪起又垂直砸向湖面,皮艇左右摇摆着,被风浪肆意蹂躏。
舵手是个有经验的湖面救生员,他熟练地驾驶皮艇在风浪间穿梭前行。坐在艇头的救生员,他的帽子和大衣很快就被迎面打来的波浪溅湿,随即就结成了一层冰壳。波浪拍打上来一次,冰壳就加厚一层,渐渐地,他头上和身上就背负了一层坚硬的冰的盔甲。
天空渐渐放亮了,但仍旧是雾霭茫茫,水天一色,看不到湖的邊际。皮艇发动机发出的突突声被怒吼的风浪声一阵阵地掩盖,风雪中可以想象我们的皮艇就像一片飘摇的树叶,在这大湖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随时会被淹没。
好在喀纳斯湖左岸一直不远不近地伴随着我们。我们用肉眼测量着湖岸的距离,太近了害怕岸边的浅滩会打坏发动机的螺旋桨,太远了又怕迷失方向遭遇巨浪的袭击。我们的皮艇始终不敢离开湖岸太远,否则稍不留神就会被湖心的引力扯拽到汹涌澎湃的冰湖中央。坐在皮艇上的每一个人都明白,一旦远离了湖岸,湖水就会像怪兽一样毫不费力地把皮艇连同我们一起吞进肚子里。
在惊心动魄中我们谨慎前行,皮艇上没有人敢大声说话。喀纳斯湖西岸的森林和岩石缓慢向后推移。
终于,在朦胧中,我们看到了四道湾岸边用圆木搭建的码头。本来只需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却足足用了三个小时才到达它的终点。回头向湖面的出水口望去,能见度不足一百米,湖面上依旧波涛汹涌。我在内心祈祷,但愿返程时湖面会风平浪静。
四道湾码头的岸边,吐别克村的牧民已经牵着六匹马等候我们很久了。
骑到马背上,我们才真正感受到大地是多么的坚实和可靠。是的,大地是最能让人信赖和依存的地方。再好的轮船,它是在水中行走,难免会有风浪颠簸。再好的飞机,它是在天上飞行,难免会有气流冲撞。这就是为什么在生活中稍有不测,人们会马上蹲到或趴在地上的缘故,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大地是最为安全的。
吐别克村坐落在喀纳斯湖西岸四道湾处一片开阔的林间空地中,这里地势平坦,草木茂盛,居住着八户图瓦人家。随着旅游开发,喀纳斯区域像这样的原始自然村落已经所剩无几了,更多的村落开始被商业化搞得不伦不类,人心也变得惶惑不安。但这里的村民远离尘嚣,与大山为伴,与湖水共眠,与林木花草同度充满生机的四季时光,过着世外桃源般的清静生活。物静则心静,心静则无欲。试想,处在闹市中的人们,怎能求得心静又如何能做到无欲呢?
天空虽然依旧飘着雪花,但吐别克村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烟火的温暖,我们暂时忘却了刚才在湖面上所经历的一切。看到木屋顶上升起的缕缕炊烟,我们知道图瓦人又开始了他们冬季平静生活的新的一天。女人们生火做饭,男人们去牛圈撒草喂牛,然后一家人围坐在桌边,喝着香喷喷的奶茶,吃着自家的烤馕,谈论着今年冬天的雪是不是会比往年更大一些的话题。这种生活延续了几百年,如果没有人来打扰,他们还会如此这般地延续下去。
马蹄踏在雪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这声音传向四周的山林,又在寂静的山谷间回荡开来,吸引了村庄里的几只土狗从四处狂叫着向我们奔来。狗们跑到跟前见是本村的马驮着我们,没有了吠叫的兴致,于是就摇着尾巴跟随我们进了村子又护送我们出了村子。
吐别克村离双湖骑马走需要两个小时,从双湖再爬上山顶的管护站至少又要两个小时。冬季的喀纳斯白天只有短短的七八个小时,如果不抓紧赶路,我们很有可能也会被困在双湖站,那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谁也不知道明天的喀纳斯湖风浪会不会比今天的还要大,甚至难以预测湖面会不会出现冰凌。
策马扬鞭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从吐别克村到双湖一路慢坡,我们骑的几匹马几乎是比赛般地在林中穿行。从双湖到达山顶的保护站垂直高度至少有七八百米,坡度平均在三四十度,随着海拔上升, 山坡上积雪也在不断加厚。几匹马非常不情愿地在羊肠小道上趟雪盘山而上。
越是往上走,风雪越大,气温也就越低。马不得不走走停停,打着嘶鸣,像是告诉我们脚下的路途多么艰险。
到达山顶的双湖站,已经接近下午三点钟。几匹马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浑身上下都已湿透,结满了寒霜,必须休息半个小时才能往回赶路。当牧民向导将几匹马拴在背风的林子里,我们跟随着两个被救援的护林员,踩着厚厚的积雪来到居高临下的管护站前。
这是一个位置绝佳的观测点。管护站建在山顶一处凸起的山崖之上,站在管护站的门前,周围的群山林海尽收眼底,这样的地形有利于观察周围的林区动态。夏秋两季,是喀纳斯林区护林防火的重要时期,而到了冬季,厚度超过一米以上的积雪则为喀纳斯区域提供了天然的护林防火屏障。明显的四季交替,也使森林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正因如此,喀纳斯山林的春季才那么青翠,夏季才那么浓绿,秋季才那么妖艳,冬季才这么凝重。
此刻,站在高高的山崖之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笔法硬朗的水墨画。喀纳斯的山川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泰加林脱去了秋季艳丽的服装,一派青衣素裹。起伏的山峦和黑色的森林勾勒出了一层层极富韵律的粗犷曲线。这曲线由近及远,逐渐淡出,及至最远,与阴霾的天空连为一体。寒风把喀纳斯湖的水气和天空中漫散的雪花向我们脚下的山谷吹来,于是,山谷间风起云涌,雾气随寒风涌动。我们的眼前,一会儿雾气弥漫,一会儿云开雾散。就在这云开雾散间,双湖一次次或清晰或朦胧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见过春夏交替的双湖,它被翠绿的山林环抱,掩映在周围山坡上盛开的烂漫野花中,湖水清澈透底,在雨水和阳光的滋润中处处都体现着豆蔻少女般充满旺盛生命力的肌体。我也见过从初秋到深秋随时节演变的双湖,它周围的树木从秋意微醺到淡装浓抹,再由层林尽染到色彩斑斓,湖水碧绿如玉,彰显出少妇般健康迷人的风韵和妖冶。
现在,我看见了入冬后不久的双湖。在跌宕起伏的林海雪岭中,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深深的谷底,双湖就像一个经历了无数风霜、日渐成熟的中年贵妇,青衣素裹,不施粉黛,雍容而又矜持,华贵不失端庄。她正在用两只乌黑清澈的眼睛,张望着我们生存的这个迷幻世界。
我忽然内心一揪,我的眼睛不再敢和面前的这双眼睛对视。这是一双多么纯洁和明亮的眼睛呵,在它的注视中,我分明看到了自己的一双浑浊无助的眼睛。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我们人类的眼睛看到和经历的东西却太多。这个世界太纷繁,太费神,以至于每个人最终都逃脱不了眼睛会早早地近视了,花了,甚至白内障了,最终什么也看不见了的结局。而双湖呢,它在这深山净土间静静地看世间风云变化了亿万年,亿万年间它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它依旧如出生的婴儿,眸如皓月,天真无邪。
上苍似乎在给我帮忙,在我不敢正视双湖的时候,寒风夹带着雾气又一次弥漫在双湖的山谷中,天空中也飘起了绒毛般的雪花来。
两个护林员早已准备停当,就等我们来接他们下山。几匹马也恢复了原样,刚才还湿漉漉的皮毛已经干透,精神抖擞地嘶叫着要早点下山回家。
从山顶下到湖边,天空开始慢慢地阴暗下来。进到双湖旁边的林子里,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几匹马借助地面积雪的反光,在林中穿行。都说老马识途,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马识归途。马在离开家门远行的时候,大都是不太情愿,有的还会磨磨蹭蹭,故意绕着弯子走,好像这样人们就不再喜欢它,会换一匹别的马来骑。这时人们手中的皮鞭子就会派上用场,在皮鞭的鞭策下,再不情愿出力的马也会一往直前。但只要是返程,再懒散的马也会不用扬鞭自奋蹄,往往是回程的时间只是来时时间的一半,早早地就把主人安全送回到家中。
在阿尔泰山中,马的个体都进化得小巧灵活,无论爬山还是下坡,其速度都是其他地域的同类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在喀纳斯和禾木这个区域,过去马是冬天唯一的交通工具,在一两米厚的雪地里,全要靠马踩踏出一条条通往外界的道路。而在这里,养马却又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马的主人在秋季一般不会给马准备冬草,在长达半年的冬季,马都是靠自己在雪地里刨草吃。如果你冬季到喀纳斯,就会发现在朝阳的山坡上总会有一些马把头埋在雪地里吃草,马吃过草的雪地,像是随意勾勒的一幅幅地图。我时常在想,自然界里,马是最令人尊敬的动物。它忠诚老实,任劳任怨,基本不向人类索取什么,连吃草喝水都全靠自食其力。最后,当马老到不能再干活了,还逃脱不了被人宰杀的命运。仅就这一点,我们人类的贪婪可恶和自私无情是别的动物望尘莫及的。
像是和我有了心灵上的感应,马此刻的心情似乎特别好,在林中的雪地上快乐地奔跑着。天空也彻底地黑下来了,远远的,吐别克村里的狗们又狂叫着出村来迎接我们。散落在四野的木屋透射出微弱的灯光,这里的人们即将结束一天的平静生活。我在想,村民们的一天一定像在过一个世纪,而一个世纪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说,也应该和一天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人们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平静地过着生活。能够在这样的山林中世代居住的人们,他们的灵魂应该早已和山林一样耐得住寂寞。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能耐得住寂寞本身就需要一种勇气。
黑暗中,我们来到四道湾原木搭建的码头边。借助手电筒的灯光,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乘坐的皮艇被波涛打翻在湖水里,如果不是一根绳索拉着,皮艇肯定早就被冲走,不知去向了。舵手和两个护林员跳入水中,将皮艇推到岸边。皮艇在冰凉的湖水中像泥鳅一样光滑,我们几个人费尽周折才把皮艇翻正过来。这时,我们的鞋子都已湿透。被浸泡过的发动机显然是发动不着了,好在我们有个有经验的舵手,在手电筒的帮助下,在皮艇上摇摇摆摆地捣鼓着发动机。
站在湖边,四周漆黑一团。寒风中,只能听到波浪有节奏地拍打着湖岸。用手電筒向湖面照去,只能照到三四十米远的地方,我看到的仿佛是黑夜里波涛汹涌的大海。
发动机最终修好了。登上皮艇时大家的心情和早晨完全不同。早晨是先兴奋后恐惧,现在是大家根本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结局在等待着我们。早晨是天越来越亮,能够看清周围的情况,而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中前行,前路茫然。
早晨的经验告诉我们,皮艇必须沿湖的西岸返回。离开了湖岸,我们就等于丢弃了救命的稻草。发动机突突响着,皮艇慢慢离岸,吐别克村牵马的村民站在岸边,在手电筒的光柱里向我们挥手告别。
皮艇在风浪中摇摇晃晃地出发了。湖面上的风明显要比岸边大得多,皮艇随波浪颠簸起伏,很快,冰冷的湖水淹没了我们的脚踝。我担心皮艇在漏水,用手电筒仔细检查了皮艇的周身,还好,是波浪拍打皮艇后涌进的湖水。我们用所有能舀水的工具齐力向外舀水,皮艇上一时慌作一团。水舀干了,鞋子却再次灌满了冰冷的湖水,我的双脚在灌满冰水的鞋子里渐渐失去了知觉。大家赶忙脱了鞋子,控干鞋子里的水,拧干袜子。护林员告诉大家,脚趾头一定要不停地在鞋子里活动,要保持有知觉,否则脚趾头很可能会被冻伤。
慌忙过后,我们忽然发现皮艇已离湖岸越来越远,大家都惊出一身冷汗。好在我们的皮艇并没有偏离湖岸太远,朦胧中我们几双眼睛都紧紧锁定着岸边的森林和岩石。舵手做出明确分工,一名大个子的护林员坐在船头,负责掌握皮艇的平衡,两个人负责不停地把拍打进来的湖水舀出舱外,另外两个人每人拿一只手电筒,一人照正前方,一人照右侧的湖岸。我们的皮艇必须要和曲折的湖岸保持二三十米的距离才会安全。
手电筒的光柱里,寒风裹挟着雪花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们的脸上和眼睛里。四周漆黑一团,湖岸在手电筒微弱的光柱里若隐若现,稍不留神皮艇便会偏离方向。我想象在夜空中有一双神灵一般安详的眼睛,它能够清楚地看到,我们这只皮艇像是一个气息微弱的幽灵,在波浪翻滚的湖水中无助地摇摆着缓慢前行。
皮艇驶进三道湾处,湖的走向拐向了正南。从南面山谷刮来的山风在这里被山体阻挡,折拐了个方向后加速向喀纳斯湖的上游吹去。由于这里的湖面平坦开阔,为下游的山风提供了畅通无阻的通道,所以比别处更加风激浪高。湖面上掀起的每一个巨浪都会重重地拍打到坐在船头的大个子护林员的背上,使他身上穿的两件棉大衣很快湿透并且结冰。渐渐地,大个子护林员成了一座“冰雕”,端坐在船头。如若不是他不停吸烟冒出的星星火光,我们真的无法判断他的躯体是否已被冻僵。
我的手脚已经有些麻木。双脚像是穿在一双冰鞋里,脚趾头在鞋里已经没有了知觉。风从湖面径直向我们刮来,这时湖面的巨浪不光只是拍打到船头,皮艇的侧面也在经受风浪的冲击。很快,我的后背被湖水打湿,羽绒服被冻成坚硬的冰块。
皮艇这时已经经受不住狂风巨浪的冲击,飘摇欲翻。我们开始恐惧和惊叫,乱作一团,赶快设法将皮艇靠到岸边,再次意识到了大地的可靠。
但已来不及。我听到身后的湖水发出怪异的声音,既不像是风声,也不像是涛声,像是从湖底深处传来的雷鸣的声响。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敢回头去看湖面,只感觉有一个巨大的怪兽在湖水中兴风作浪,随时都会把我们连同这只皮艇吞进它的肚子里。皮艇已无法掌控在舵手手里,在漆黑的湖面随波浪起伏。我们的视线中已找不到湖岸,离开了湖岸就意味着我们很快会迷失方向。此时的我们已无能为力,皮艇在波涛中颠簸旋转,我们像是掉进了茫茫深渊。
一个巨浪打来,皮艇灌满了冰冷的湖水,发动机不再发出突突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在惊呼:皮艇要翻了!我们几人陆续掉入水中,在冰冷的湖水中无望地挣扎。大家都下意识地抓住了皮艇上的绳索,绳索将我们“团结”在皮艇周围。我们在湖水里随着皮艇上下摆动,随波逐流,身上的衣服被湖水浸泡后像灌了铅一样往下沉,大家抓住绳索,像围抱在一个大的救生圈周围。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只要能依靠湖水的冲力漂出三道湾,等风浪小了我们就会重新找到湖的西岸。
在接近冰点的湖水里体温在迅速下降,渐渐地,我的下肢变得僵硬并慢慢失去知觉,意识变得模糊不清。我凭直觉察觉到,一个巨大的黑影在我们附近的湖水中拍打着巨浪,在我们周围来回游动着。
这会不会就是人们传说中的湖怪呢?我惊恐地想。当地的老乡说,湖怪每一次出现,都会有狂风巨浪相伴,今天的天气刚好吻合了这一说法。在这冰冷的湖水中,如果真有湖怪出没,我们几人只不过是湖怪口中的一点零食,它只需要张张嘴,我们便成了它的腹中之物。这个将近两百米深的湖泊,湖怪才应该是它的主人。只要湖怪愿意将我们吞进肚里,我们没有一点挣扎的余地。我脑子里浮现出了常在湖边看到的被遗弃的白色骨头的情景,据说它们都是被湖怪拖入湖水中吃剩下的马和牛的骨头。马和牛湖怪都能够轻易地吞下,我们这些小小的人还算得了什么呢。那么,从今往后,喀纳斯湖边又会多出一些青白色的人骨头了。
想到这些,我努力想要翻上正在跳跃摇摆的皮艇。但我身上像是穿着一身铅做的衣服,任凭我怎样使劲都动弹不得。对面的舵手对着我叫喊,千万不能爬到皮艇上去,那样的话我们立即都会被冻成冰棍。我马上明白了,现在湖面以下是冰点以上,而湖面以上则是冰点以下。如果我们现在离开湖水,不用湖怪来吞噬我们,我们就会被冻死在皮艇上了。
这时,湖面的风浪更大了。浪涛接二连三地劈头向我们打来,使得我们没有喘息的机会。看来,我们真的要葬身在喀纳斯湖底了,我绝望地想。寒冷中我努力睁开眼睛,在汹涌的波涛中,我依稀看见皮艇周围几个若隐若现的身影。在我们的附近,那个巨大的黑影仍在来回游动,拍打出滔天的巨浪。
我们必须要设法回到岸边,否则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回到岸上,我们才有生存的可能。我判断,我们现在肯定离岸边不会太远,体型巨大的湖怪活动的方位应该在湖的中心,而皮艇的另一面,就一定是湖的西岸。于是,我们背对着巨大的神秘的黑影,努力推着皮艇向西岸游动。
我们的努力似乎微不足道,皮艇只是随着波浪来回摇摆。我的身体在冰冷的湖水中已经渐渐失去了知觉,我感觉整个躯体开始向湖的深处慢慢沉去。那个巨大的黑影随着我的下沉也离我越来越远。我真的要沉入湖底了,要离开这我钟爱了一生一世的人世了。我惊奇人之将死心境也开始平静下来,没有挣扎也没有了过多的烦杂。没过多久,我感觉自己喝了许多口冰冷的湖水,胸腔被湖水积压得快要炸开。我在湖水中痛苦难耐,再一次抓住绑在皮艇上的绳索挣扎着冲出水面。这一次,我分明看到了远方一处明亮的灯光在湖面上遥遥闪现。我怀疑自己因过度寒冷产生了做梦似的幻觉,但同伴们的惊呼让我坚定了重生的信念。
是的,湖面上有灯光由远而近向我们驶来。一定是码头上等候我们的人们营救我们来了。我们离开码头太久了,为了寻找我们,他们必定把已经停靠上岸的游艇又重新放回水中。灯光在我们的视线中起起伏伏,但确实是越来越近了。
顿时,哭喊声惊叫声响成一片。我们像一群被丢弃后又重新找到父母的孩童,伤心、委屈、怨恨、惊喜等等各种情绪同时爆发出来,我们只等着父母张开双臂,好让我们能够投身进去。这时,我们的四周忽然变得极度安静,刚才还凶猛无比的湖面这时也变得温情柔软起来。那个一直跟随着我们的巨大黑影,也销声匿迹了。游艇的马达声开始是若有若无,现在由小到大传入我耳中。游艇上的灯光折射到水中,像温暖的晚霞照得湖面波光粼粼。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真实。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额尔德什老人,那个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楚吾尔的吹奏者。他在世时创作了一首《喀纳斯湖波浪》的吹奏曲,曲子虽然苍凉忧伤,但最终阳光下浪花荡漾的喀纳斯湖却温情如上苍的乳汁,让经历了乱世的喀纳斯先民们有了重生的希望。
现在,也是在这样温情的喀纳斯湖的波浪中,我們将同样获得一次重生。
这时的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因为重生的希望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等待游艇上的人们把我们从水中捞出的那一刻,我们会兴奋异常。但当我真正离开湖面时,我的身体开始不停地打着寒战,大脑渐渐变得一片空白。在我彻底失去意识前,我努力回头向喀纳斯湖望去。
我看到的,只是漆黑的湖面和远处隐约模糊的山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