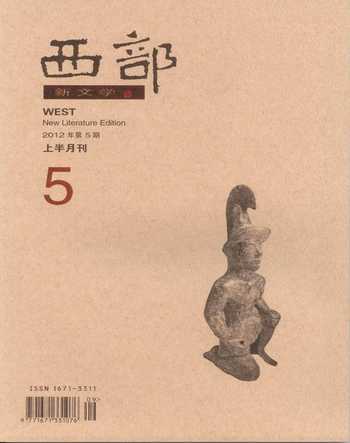原生态及其他
韩子勇
原生态
会议的组织者给我打电话,希望谈一谈木卡姆原生态传承的问题。思之再三,觉得如果不仅仅停留在工作层面,就有更深的理解在里面。
比如,什么叫“原生态”?“原生态”的标准或者“标准的原生态”是什么?“标准”这个词是不是和“原生态”相悖论?到底有没有“原生态”?“原生态”是可以“传承”的嗎?……提出“原生态”,意味着我们所要求的东西已经改变、已经丧失、已经余绪缥缈、烟消云散,意味着那种自由自在、自然而然、未曾扰动和扭曲的过程的结束。
依我看,“原生态”这个词,是对“现代性”的温和提醒。全球化风潮加深彼此联系,改变距离和时间。世界再也没有平静偏僻的角落,撕裂灵魂,沉沦乡土,混淆多样,消磨突起物,抹杀多样性……有一个声音在喊:“集合、立正、齐步走!”
“现代性”在国际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艰深问题。这方面的著作汗牛充栋,莫衷一是,令人眼花缭乱,不胜其烦。伴随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国内始终有一些学者关注这个问题。一段时间,还是学术热点。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现代化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质疑“现代性”,说好听一点是脱离实际,说难听一点是吃饱了撑的、给现代化泼凉水。但这的确不是多余的假问题。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形态,就像万里长城,拉得很长,一头伸进大海,一头蜿蜒消失于浩瀚大漠,几乎可以看到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景致。
不是这样吗?身居上海森林般的花花闹市,很容易忘记地广人稀的边疆农村的袅袅炊烟。我们仿佛站在遥远的两极、时间上的咫尺天涯,眺望这重重关山,层层风景,生生灭灭,真真幻幻,禁不住要喊一句:“好一个大千世界!”各阶段的并置串联、混为一谈,也许,这才是“今天”的原生态呢。
这是一个呼啸前进的大时代。她身躯庞大,欲望强烈,动力强劲,原料充足,不知疲倦,不舍昼夜,一刻不停往前冲……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完成万里长征。六分之一的人类,勤劳节俭的民众,辽阔的城市乡村,源远流长的文化,积压了一百多年的强国富民的梦想,一切的一切都被调动起来,一切的一切都被集中起来,压缩、凝聚、换算、裂变,最后变成简单而又深刻的想法: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于是有了这三十多年爆炸式经济增长:一种东西只要中国开始生产,全世界就降价,再神奇、再贵的东西就马上变得一钱不值,而只要中国购买价格就立马飞涨。中国胃口惊人,吃得下任何东西,中国市场经济的乳牙,已经咬得动资本世界的铜墙铁壁。 而中国才刚刚度过温饱、开始小康,也就是说,才刚刚开始,刚刚发育,如同一个处在变声期的男孩子,刚有那么点儿意思。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三十多年的中国,就是:快。一切都太快了。都说“大跃进”快,“赶英超美”,大跃进是蛮干加嘴快,大话吹破天;现在才真是快,是“不争论”加腿快,基本上是“神行太保”,是“飞毛腿”,千千万万的“神行太保”和“飞毛腿”。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一句好诗,但也可以反思。太快了,有一个缺点,就是只能看清前头,看不清两边,两边齐刷刷往后倾斜,一闪而过,没有细节。太快了,容易拉开距离,距离越拉越大,首尾不相顾,就容易断掉。太快了,灵肉不相依,脑子一片空白,容易失神、失忆。谁是跑着思考的?飞跑的人,脑子变得简单、一根筋。太快了,容易否定“慢”,把身边的“慢”看成已经完蛋的“沉舟”和“病树”。
文化也是一种提醒,“原生态”这个词,就是提醒,不管有没有结论,提醒已经存在了,这就好。
(在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组织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片断)
一沟文明起承转合
昨天上午的吐峪沟之行,我们都有了沉甸甸的收获、沉甸甸的责任。吐峪沟只是一个小沟沟,不算长,也不算深。和新疆大地“三山夹两盆”无数恢弘的大皱褶相比,吐峪沟其貌不扬,甚至过于朴素、狭小和简单了。但就是这么一个小沟沟,竟满满当当地盛满了异常多样的古老文明。吐峪沟,这干焦焦、粗拉拉、光秃秃、一棵树就是风景、一个人就是亲人的地方,当我们吹开时光的灰烬,注视这袖珍的坩埚,刹那间——流淌一沟文明,绚烂夺目,满沟生光。
也许,这就是吐鲁番的神奇之处吧——让你不再轻视普普通通的平凡之物。你得承认,人类的心思,竟这么绵远悠长、复杂精致,比精工细作的瑞士表,还要考究、可靠、结构紧凑。这么一条小沟沟,从古至今,能有几多田畴?能养几多人口?能出几多贤达才俊?能有几多闲钱余财用来打理生存之外的精神文化之事?……但,且慢以寻常之理和实利过度的糟糕心态来揣度前人,就是这么一条地瘠、人少、且贫穷的小沟沟,就是那些土里刨食的粗汉田夫,抱养、收留了远道而来的四大文明。可以想见,那如远途孤旅般满面风尘、踉跄而来的文明余韵,至此地时,早已身覆颓土、气若游丝、形容枯槁,就在这如簇点缀的坎儿井绿荫下,休养生息,缓过劲来,或继续前行,或就此扎根,如此洇染着戈壁沙漠上的文明。荒凉而奢华的西域,不断上演的,正是这样一些文明传播中的经典细节。
也因此,一沟之地,寥寥人烟,竟然风生水起,也有了复杂的插曲、情节、悬念和故事,串缀起大文明之间的起承转合。太阳之下,戈壁之上,一切如此公平、如此悲悯、如此充满灵感的奇思妙想……把更多的呵护给予最羸弱的子裔,把重要的瑰宝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吐峪沟的存在,让我们相信,在荒凉、贫瘠、质朴、弱小的托盘上,可以有奇迹、惊喜和丰盛从天而降。一个个赫赫文明、煌煌巨子,竟被这位名叫“吐峪沟”的普通农妇所收留,并细心哺育。吐峪沟的本质,是包容、开放、谦和、融萃,是认真诚恳的容受消化、兼收并蓄,完美地呈现文明的四季交替、丰富多元。因此,这一角堪称典型的“文化生态学现场”,告诉我们的是:最贫瘠的,有最大的养育;最弱小的,有最大的担当;最逼仄寻常的,有最宽广辽阔的襟怀。对吐峪沟的考古解读,还是留给在座的专家吧!我们这个小小的会议室里,已经聚集了国内、当然是世界上对中亚文明最有发言权的专家。
当前,新疆在中央和兄弟省市的支持、帮助下,在天山儿女的奋力前行中,正掀开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宏伟蓝图,正上演波澜壮阔的时代大剧。自治区党委提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吐峪沟正是一本并非过时的教科书,直接间接地教育我们开放、融合、创新、包容的真谛。因此,保护好这个地方,善加利用、永续利用,就是纪念文明、挽留先贤,就是向文化的致敬。
(在“丝路申遗——吐峪沟大遗址保护筹划会”上的讲话)
中华美术的西北角
借今天“新疆好——新疆美术作品研讨会”这个良辰吉日,我想讲三个词:
“昆仑神话”
占我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也是历史上狭义的西域。西域所涉,绝不仅是个地理概念,它当然也包括心灵文化——中华民族的心灵文化。
中华民族最早最初的精神贡献,当然首推从远古蛮荒流传下来的神话,特别是创世神话。中华民族的创世神话,以昆仑为基石——昆仑创世神话,是中华文化的第一块奠基石。我们的先民在开始构造自己的心灵世界时,选择了一个最接近天宇的海拔高度,选择了这个星球最结实的大块作为她的“发言席”——昆仑参与了中华文化的元叙述,昆仑是真实的世界屋脊,也是中华想象的大块堆垒。
提到古埃及,我们想到沙漠、尼罗河和金字塔;提到古希腊罗马,我们想到地中海、奥林匹斯山和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古希腊罗马神话;提到古巴比伦,我们想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及两岸的绿洲、椰枣树;提到古印度文明,我们想到恒河、印度河蜿蜒流过的南亚次大陆……而中华文明的最早形象,是中华地理三级台地的最高处,是昆仑,是以帕米尔高原为核心的世界屋脊。
河出昆仑。至少在清中期以前的历史中,中国人一直以为“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这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她的子民心中,是发源于昆仑神山的。现实的塔里木河,在历史文献中被误以为是它的上游,注■泽(罗布泊)、潜大漠,又从青藏高原浮出,九曲十八弯,归于大海。
“登昆仑兮食玉英”,除了昆仑、黄河,这一山一河,出于此地的还有一块美石。“玉出昆冈”,我们这个民族,如同“贾宝玉”,是“衔玉而生”。这块中华民族的心灵美石,是浓缩的、佩于胸、悬于颈、饰于腕的和阗玉。这何尝不是对昆仑的纪念,是昆仑的族徽、昆仑的象征物呢。
我很奇怪,深耕于华夏腹地的先民,如此舍近求远,以千里万里之外的昆仑为自己神话的起点、母亲河的起源、中华美石的初始——他们把心中的神灵:盘古、女娲、伏羲、后羿、共工、刑天、西王母……置放于超越自身的地理环境中,这是何等深远的目光,何等大结构的擘划,它又预示一个怎样的未来?
“丝绸之路”
从词到物,从名到实,从昆仑神话而来的,首先是隐现于史前文明的玉石之路。这是一条被文献和考古证明了的真实通道。这条通道出昆仑,一路上北,沿贯通欧亚的北方草原带向东,再向南进入华夏腹地。红山文化出土的最早的玉器虽采于当地,但也同样在这个自昆仑为起笔的“几”字型大路径上。之后,更为著名的“丝绸之路”,更是一条延续千年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干道、大动脉,有力地参与、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合唱与塑造。
关于丝绸之路,中外文献汗牛充栋。这也是世界文明交流史上最美妙、最神奇、最华彩的乐章,是东西文明双璧合体最显著的表证,是东西文明这一隐形伴侣偷情、私奔的秘史、绯闻。在丝绸之路的“婚床上”,那些光明正大的“嫡亲”或“私生子”,无一不是美艳健康的混血儿,披着柔软、华美的丝绸,穿行于沙漠绿洲、草原雪山,至今为人津津乐道:这里是部族迁徙的十字路口,是众神漂泊的宗教走廊,是语言游行的露天广场,是乐舞喧哗的阔大舞台,是植物传递的万千驿站,是技术交流的中继站和变压器……可以想象,人类最早最成功的“全球化”尝试,就发生在丝绸之路上,发生在继之而起的海上丝绸之路上。
“天山画派”
由国家文化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新疆好——新疆美术作品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思的契机:思考中华文化的西北角,思考中华美术的西北角。
这是占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西北角;这是被丝绸之路分三道结实捆扎的西北角;这是由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这三条几千公里的山系依次呈“三”字排列的西北角;这是由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盛满深情厚意的西北角;这是十三个世居民族、四十七个民族成份多彩生活画卷组成的西北角;这是中国史前岩画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内容最杂样的西北角;这是最早出现佛教美术、祆教美术、摩尼教美术、伊斯兰教美术的西北角;这是涌现了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曹仲达、犍陀罗艺术、“凸凹画法”的西北角;这是几乎所有现当代著名画家都曾描绘过的西北角;这是被誉为绘画天堂的西北角;这是馥郁如酪、热烈如诗、一体多元、浓颜明眸的西北角。
今天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近两百幅美术作品,是从两千多幅作品中精选而出的。我以为,它也仅仅是揭开了新疆美术面纱的一角。我几乎走遍了新疆的八十多个县市,我发现在八十多个文化馆的展厅里,绘画在文化馆的文化创造中,都占有绝对大、绝对多的比重。尽管在县市一级文化馆琳琅满目的作品中,多是业余作者的作品,但那些用色大胆、线条奇崛的作品,所支撑的想象、热情与灵魂,甚至要比技巧更令我感动。
借今天这样一个契机,我想提出一个词:“天山画派”。我隐约感到,遥远的中华西北角,正涌动、形成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美术动向。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文化,辽阔的西部边疆火热的多民族生活,壮丽、苍茫、深处于亚洲中央的自然景象,使这里的美术创作具有混血的美、融合的美、野性的美、神秘的美,洋溢着热情、感性、迷醉、欢乐的“酒神精神”,洋溢着热气蒸腾的心灵高温、令人窒息的情感的“沙尘暴”、沙枣花般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灵魂的馥郁、茁壮性感无拘无束的生命意味。
“天山画派”,正从一滴,到汪洋一片。生活在“三山两盆”、绿洲草原的各族画家,正啜饮着、迸发着、创造着,从中必显美之巨子。
(在“新疆好——新疆美术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青草与白雪之歌
此时此刻,旷野安详,群山岑寂。草原上的游牧者,走进白雪世界,在冬窝子安营扎寨。大地屏息、忍耐、克制、积蓄,也更加静思,更加清洁。仿佛孕育中,仿佛藏着天大的秘密,一目了然,又无处倾诉。不经意间,泄出一片喜意……这一切,和今天的画展——《阿曼·穆罕诺夫从艺五十年油画作品展》,多么神似而贴切。
游牧生活是人类最古老的生活之一,是人类对边缘资源的利用。异常的艰辛、孤寂、单纯与分散,始终伴随牧人踽踽独行的脚步。几千年来,这样不变的生活,也无数次锤炼游牧民族对大自然敏锐而细腻的观察力,对内心世界持续的挖掘和表达,从而形成一整套传统知识谱系和艺术世界。
看似零乱、随意,蛛网般密织于大山、旷野的牧道,其实可以提供的生活道路并不多。冥冥之中,有一种迫切而近乎宿命的选择。我们可以想象,1936年出生于新疆伊犁新源县的阿曼·穆罕诺夫,他未来的命运是怎样的?像祖辈和大部分牧人之子那样,做一个一年四季尾随于羊群之后的游牧者?或者灵感从天而降,他开始对着草原歌唱,做一个草原上的阿肯?或者再进一步,追随先贤阿拜的足迹,当一个箴言和诗歌的发布者……苍天之下、群山之上,看似无限敞开、自由散漫的游牧生活,这一刻,又显得那么封闭、偏僻。但,命若琴弦,历史和生活的诱人之处,在于从停滞凝固、冻成白冰的河流中,又总能出现转机。1958年,阿曼·穆罕诺夫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在吴作人、董希文、罗工柳、艾中信、詹建俊等一批名師的指点下,开始接受系统扎实的油画训练。1963年阿曼·穆罕诺夫从中央美院毕业,到新疆文化厅艺术处工作,1981年调入新成立的新疆画院,从事专业油画创作。一个牧人之子,从此改变生命轨迹,如同湛蓝的苍穹,有一颗星突然改变方向,进入新的运行轨迹,加入银河的合唱。
绘画是心灵的手工作坊,艺术家创作时幽微动荡的内心世界不为外人所知。灵光的从天而降如夜幕划过的流星,神秘的创造力属于人类,但又往往无从自知,无法精确计划。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常常是事后的分析与归纳。所谓“恍然大悟”,其实对应着的,正是盲目的经验。
初心便是正觉。作为新疆第一代哈萨克族油画家,阿曼·穆罕诺夫五十年的油画创作,完成了他本人也可能无法预计的艺术道路:将古老的游牧文化的基因,完美镶嵌到号称科学与艺术最完美结合的油画艺术中。在有岩画、毡绣、骨雕、传统纹样的游牧生活中,诗歌和音乐占据了更大的心灵原野,但重要的是,游牧者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之子,游牧生活最大限度地享受到自然的教诲和暗示,自然精神的哺育无处不在,渗透到骨髓和灵魂,成为游牧文化天然的“防腐剂”。
阿曼·穆罕诺夫的作品带给我们最大的震撼,是作品流露出的那种心灵的诚恳态度。在今天这个喧闹浮华的世界,这种诚恳、专注与认真,这种五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是多么的可贵。许多油画家最后的失败,失败在对艺术、对生活、对人类的不诚恳;失败在把专业变成游戏、变成表演、变成偷懒、变成假生活与假创造;失败在那颗脆弱肥厚的心、三心二意的心、东张西望的心、虚情假意的心……真善美是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常识,但要做到、要坚持、要挺住,何其难也?诚恳对于今天的艺术家来说,我以为,是最重要的品质。只有诚恳,才能真实。只有真实,才有力量。
阿曼·穆罕诺夫是个低调的人,沉默寡言,不热闹。在一群七嘴八舌鸣啭的鸟儿当中,常常让人忘了他的存在。安详宁静的他,是众鸟鸣叫中默默的山,是雁行长空时湛蓝的天。这种低调不是压抑克制的结果,而是牧人血中流淌的血红素,他没有背叛自己的血液。熟悉他的领导、同事和朋友,都知道阿曼·穆罕诺夫很安静、不张扬,好像一个自闭症患者,沉溺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艺术世界往往也是熙熙攘攘的名利世界,阿曼·穆罕诺夫是一个远离名利的人,不计较浮光掠影,不计较可能影响生活品质的表面的东西,而是专注于内心世界的艺术表达,专注于对生活、对传统、对大自然的挖掘。
游牧者一年四季逐水草而居,这是一种流动的生活,但却不是杂乱无章的。它和定居者视作难事、手忙脚乱的“搬家”,是两个概念、两种情形。大地无垠,苍天永恒,草原黄黄绿绿,群山起起伏伏,游牧者爬山涉水,随遇而安,但每一条漂泊中的无形轨迹、每一片外人无法辨识的草场,早已熟稔如昨、安放于心,就像他们天天驱使的羔羊,每一只都叫得上、认得出。五十年游牧于画布、放养万千色彩的阿曼·穆罕诺夫,在确定题材、寻找结构、挥洒笔墨时,是否也把谙熟于心的“游牧规则”运用于油画的世界呢?我想,这是肯定的。生活和艺术是相通的,更何况,游牧也好,油画也好,都是个性如此鲜明强烈的品类。把两者放在一起,不是物理的并置,是阿曼·穆罕诺夫那颗心灵的容器。心灵的坩锅的炙烤,一定会产生的新的结晶。
一个同样优秀的汉族油画家曾经问我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新疆,为什么一些优秀的少数民族画家,会把绘画和本民族文化结合得那么好?要知道,架上绘画从无到有,在此地、在此民族中的真正起步,才几十年而已。”这是个好问题,但要回答好却不容易。我想了半天,也许答案就在提问里:“因为‘新,因为是‘第一次,因为游牧和油画是初次‘见面,就像‘初恋难以磨灭,就像嘴唇第一次碰到蜜糖,它会调动全部的感官,这感官当然主要是文化的基因。再加一条,也许,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边界相对清楚,规模相对可控,形态结构相对单纯,更易于个人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短兵相接和‘贴身肉搏。也许,还可以再加一条,因为你是‘旁观者,面对的是‘双重的新,是‘新上加‘新,你所带的文化眼光更易识别这种‘异。”
比如,阿曼·穆罕诺夫的油画作品,那种用色块结构画面的方式,多像无形的草场围栏的划分方式。在漫漶无迹的旷野,游牧生活的“公”与“私”、“统”与“分”、“连缀”与“隔离”,人人心知肚明,是草原上的“习惯法”,都在大家的心里,有着特殊的文化理解。这种微妙的平衡和调适,是否也不易觉察地渗透到画家对作品结构的理解和运用当中了呢?我不得而知,但深信无疑。
阿曼·穆罕诺夫油画的突出特点,是色彩的丰富、细腻、活泼、灵动。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的草原,看到的天空,看到的毡房,看到的生机勃勃的动物,色彩那么丰富,那么干净。我们一些油画家,其作品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里面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混乱和不干净,甚至是偷懒、堕落的痕迹,这样的创作,也叫失败。但在阿曼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纯粹、洁净、简约而丰富的表达,五彩缤纷而不乱一缕,潇洒随意而准确有力。有时我想,阿曼的作品,流露出一种细腻、敏感、隐秘和羞涩的调子,好像永远沐浴在草原母亲爱怜的目光中,干净如处子,沉静如处子,惊人的美把人慑住,神圣不可亵渎,是一种青春生命的颜色和风格。这种品质,源于他的诚恳,源于他扎实的训练和表达,源于他平和、专注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每一个有成就的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好奇、专注、深思是最重要的。而今天的快节奏,往往使人东张西望,往往使人浮光掠影,往往使人步履匆匆,往往使人静不下心来。没有一颗安静、沉思、充满激情的心,很难细腻。如果艺术都不细腻,生活怎么能细腻?如果心灵都不细腻,行为怎么能细腻?没有细腻,就没有亲密接触,就感受不到精神的体温,感受不到心灵的体贴,我们的精神家园就是粗糙、简陋的,就是沙漠戈壁、热风恶鬼。
在阿曼·穆罕诺夫作品的色彩中,我们找到了这种干净的细腻,找到了灵动的丰富,找到沉静和激情的完美结合。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看似细致、细腻的作品其实死气沉沉,板结僵硬的色彩把画面糊住了,窒息了生机和活力。在阿曼·穆罕诺夫这里不一样,是细腻灵动,充满好奇、天真和持续的关注与描摹,流淌着草原的乳香,流淌着青草般的细浪,流淌着变幻的天光云影。牧人之子也是自然之子,阿曼·穆罕诺夫深谙自然的本质是自由的生机,这为他带来健康、向上、有力度的表达。
阿曼·穆罕诺夫今年七十六岁了,除了耳朵有点儿背,眼力还很好,身体还很好,我们相信他还能画出更多、更好、更美的作品。最后我想说,他不愧是新疆哈萨克族第一代油画家的代表性人物,是新疆哈萨克族油画艺术的奠基者。由于他的不张扬,由于他的低调,对他的评价,我以为是偏低的。我们的思维总是跟着热闹走,但大风景在热闹之外。真正好的作品,要沉淀,这种沉淀是心灵的沉淀,是时间的沉淀,审美判断的沉淀。
阿曼·穆罕诺夫的艺术,被时间和心灵沉淀出来。这迟到的礼遇,送给新年,赠予不朽。
(在阿曼·穆罕诺夫先生画展上的致辞)
绿洲,绿洲
《绿洲》出刊一百期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
那是在新疆大学读书时,正做着热烈的诗人梦,每天往本子上抄朦胧诗,抄西方文论和近现代哲学,一年狼吞虎咽能看两百本书——要知道整个高中时期,课本除外,所读“闲书”不超过二十本。除了把自己埋在书的急风骤雨中,就是拼命写诗,而且企图发表。那时候,知道的刊物很少,寄出的稿子很多,一两年也无收获。现在我知道,世人期盼的结果,多在看淡结果后,才不期而至。终于有一日,我的一组、其实也就是三首诗发表出来,得稿费七十余元。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标准,这不算少。要知道当时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的月工资,也就大致这个数。我还记得那组诗的标题是《暑假,我回到农场》,那是我公开发表的处女作,编辑不是洋雨,就是东虹。两位老师都已作古,但我这株三叶草,曾得到他们的雨露,我忘不了。
文学最热的时候,我是初学者。文学似乎末路时,我还是个初学者。这“奖”那“奖”,这“家”那“家”,得了不少,也听了不少,我不习惯,也不真信。只有白纸黑字,是我珍惜的。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叫《铅字》。我们都崇拜过铅字,也就是印刷体的汉字,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接触的印刷体汉字,都是领袖的话。社会的进步,让我们的诗情画意也能变成印刷体,让我们也有了话语权。但电脑普及的时候,也是印刷垃圾开始泛滥的时候,这时我想,我是不是个“污染大户”呢?机会和条件的充足,是不是让我们的心灵能力变得稀薄、像注水和催熟的食物了呢?失魂落魄的铅字,需要恢复混元真气,不上化肥,不打农药,只求真情实感。
在新疆,绿洲是生命的陶器。这个陶器,在锋利的铁器世界没被碰碎,是因为有无数的手的托举。我们应该感谢兵团领导的远见卓识,感谢一代又一代《绿洲》人的细心呵护,是他们保持了这片纯文学的净土。在影像时代、网络时代、读图时代、虚拟时代……一张纸、一支笔、一个字一个字的文学写作,显得落伍了,陈旧了,不合时宜了,和其他优势的、流行的文化样式比,是易碎的陶器。就像我们的记忆,越来越远,似乎是向后走。但不要紧,新与旧,从来都不是判断价值的标准,一册冊的《绿洲》,已经是一部真切的兵团文学史,是一部新疆当代汉文学的历史。这种命运感,细若游丝,却大有深意。
最后,我要说:“接好了,别碰碎怀里的陶器。”
(在《绿洲》杂志出刊一百期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