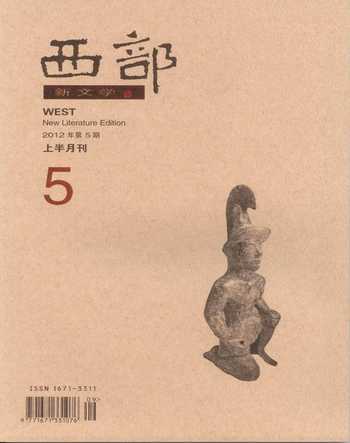“用奴隶的语言开始写作”
杨德友
这本篇幅不大的书是一本强有力的书。即使你只阅读其中最短的两三篇故事,也会立即感受到这股力量。
本書是二战后波兰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波兰诗人、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 1922—1951)的短篇小说集,收入《告别玛丽亚》(1947年)、《某一个士兵》(1947年)和《石头世界》(1948年)中的绝大部分作品。
博罗夫斯基的作品,除了《告别玛丽亚》、《在我们奥斯威辛》和《格仑瓦尔德战役》这几篇,其他的篇幅都比较短小,甚至十分短小。虽短小但充满澎湃的张力。
博罗夫斯基二战时期在沦陷的华沙靠打零工维生,同时在地下大学学习文学,并尝试“用奴隶的语言开始写作”。他活跃、羞涩、抱负远大,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对未来不抱任何幻想。这时,他甚至油印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记录当时华沙犹太人身处的生存环境:灰暗、雾霭、阴冷、死亡……尽管初出茅庐,他却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的作品里没有信仰,但充满勇气,敢于直面悲惨的环境和环境中的自己。他否定世界,否定一切。1943年,他被盖世太保逮捕,成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徒。他在那里苦熬了两年,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战后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他对那段不堪岁月的印象。
博罗夫斯基揭露纳粹集中营人间地狱的小说,被波兰文学界和欧美学者一致认为是描写这一题材的最优秀的作品。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作品的力量,尤其是直接描写集中营囚徒苦难的篇章中蕴含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表现为惊骇和震撼:世上竟然有如此残酷、如此浩大规模的杀人工厂。这不是中外影视作品中的那些血淋淋的、惨不忍睹的场面,观众知道那些是编剧、导演、特技设计者、化妆师和演员在“做戏”,而这些作品里的是百分之百真实的记录,绝无半点“创造”。其次,这里的揭露和控诉随之引起读者的感受是:今后决不允许再度发生这样的事!第三,读者读完作品之后很快会想到和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就像是深不可测之谜,即便是专家学者也无法解释清楚和回答这些问题:一个文明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像德意志这个“优秀民族”的领导人,何以堕落到拿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种族灭绝办法,建立起高效率、高技术的杀人工厂?何以教育良好、纪律严明、工作勤奋的德国人能够集体野兽化,变成绝对的驯服工具,一丝不苟地执行这样灭绝人性的计划?
进一步讲,这是西方文明语境下的奥斯威辛。可“奥斯威辛与西方文明的困境”为什么会发生?西方文明是一种意识,亦即“一朝文明,永远文明” ,这是骄傲自大的西方的静止论的观点。实际上,文明和一切“进程”一样,“需要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否则也会倒退”。(李伯杰:《读书》2010年第6期,第65页)果真如此吗?
德国学者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以后,诗已不复存在。”他还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他的这一名言至今仍未失去鸣声悲切的力量。”(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与爱》,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阿多诺的意思大概是说,西方文明竟然堕落到了开办高技术杀人工厂的地步,再写诗歌颂花前月下诗情画意,沉醉于锦绣辞章文采缤纷,是不合时宜的。如果说诗是呐喊,则遇难者在苦难绝望中的吼声或者呻吟也是诗,因此,诗应该激发人深思、反省。阿多诺这一句微言大义的话本身也像是一个谜,至今有多种解释,争论不休。人和诗,正如人和艺术一样,永远都有不解之缘,而奥斯威辛则斩断了这层缘分,阿多诺如是说。
1951年7月1日,博罗夫斯基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时他还不满三十岁。至于他为什么要自杀,至今没有透彻的解释。博罗夫斯基是一个诗人,在发表散文作品之前,二十岁前后就已经发表诗作。诗人自杀是文坛较常见的现象之一,也许他们太敏感,“一根筋”,遇事不善转弯,对生活的绝望感比常人强烈得多。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终究还是选择了死亡,个中原因也许只有诗人自己知道。
现在来简单地看看博罗夫斯基作品的写作特点。
博罗夫斯基的作品不是旨在全面解释战争后果,而只限于描述集中营;不着重描写某一个人物,而是把囚徒当做一个整体;他表现人物,只限于描写人物的反应、行为、外貌、特殊栖息地,而不深入他的思想或者情感,从而趋向于客观主义;其作品特色是不动声色的冷静到极点——对集中营的描写虽然枯燥,却常常令人不寒而栗。书中人物受到现实的战争的威迫,为了生存不得不使用诡计、行窃……集中营里的囚徒多数丧失了个人的特征,成为“集中营化的人”,没有道德价值观,为了活命不惜任何代价。主要人物青年诗人塔杜施先是在建筑仓库工作,后来成为囚徒,他理解并且接受了集中营的生存法则。作者的叙述语言丝毫不添加感情色彩,常常使用“集中营用语”(见“奥斯威辛集中营专用词汇表”),这一点在原文中尤其突出。
博罗夫斯基也有部分作品是描写集中营外面的生活的。如《告别玛丽亚》写被占领的华沙的日常状态,没有英雄气概或者殉教者事迹。华沙市民只能顺应新环境;全城都在经商,所有人都在交易,交易的“货物”甚至包括人。小说在大背景上还展开了犹太人隔离区的种种悲剧。书中人物塔代克生活在两个世界当中:被占领的世界和爱情与诗歌组成的个人的世界。但是,个人的世界是短命的:塔代克的未婚妻在街道的抓人行动中被捕,叙事人对她的命运表面上显得冷静的推理是她必死无疑,绝无生还希望。这个故事1993年在波兰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导演是菲利普·齐尔伯。
《格仑瓦尔德战役》是一篇苦涩的故事,发生在战后美国人在西德管理的滞留异国人口(波兰语dipis,源于英语displaced persons)的过渡性的集中营。小说情节表明,奥斯威辛迫人遵守的机制战后还在延续。博罗夫斯基描写滞留异国人口集中营时的愤怒,甚至超过对纳粹集中营的愤怒。因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囚徒是没有出路的,要么适应,要么死亡。而在美国人控制的这个集中营里,一切人都在奢谈自由,还举办爱国主义展示活动,但是人们依然被圈在大墙后面,依然在死亡(少女返回集中营遭到荒唐的枪击而横死),大多数囚徒没有感受到处境的巨变——他们已经习惯了。本篇也于1970年在波兰被改编成电影,名为《战后的大地》,导演是著名的安杰伊·瓦依达,电影配乐采用了维瓦尔第的《四季》和肖邦的《波洛奈兹舞曲》。这位名导演近期引起轰动的影片是《卡廷惨案》。
《某一个士兵》、《市场街的毕业考试》和《朋友的肖像》三个短篇记录了少年学生在艰难困苦环境下的学习与奋斗。《石头世界》则描写了集中营解放前后其内部和外部的片段印象。
鉴于博罗夫斯基的全部作品都涉及那个冷酷而艰险的、广义上的“石头世界”——被异化的世界,我们以这一名称作为本书的总标题。
一向以来,揭露和控诉希特勒大屠杀的作家并不少,但博罗夫斯基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20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Imre Kertesz,1929—)曾对博罗夫斯基做出高度评价,他在获奖感言中说:“我全部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写出,皆因我对博罗夫斯基的散文作品着魔迷醉。”凯尔泰斯也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因为写作了关于大屠杀的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下面这些可以看作集中营留给今天的记忆:
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于1947年7月2日成立纪念馆。
美国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于1993年4月21日开馆。
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于2005年3月17日开馆。
德国柏林大屠杀纪念馆于2005年5月10日开馆。
马尔库塞说:“遗忘过去的苦难就是容忍,而不是征服制造苦难的势力。思想的崇高任务就是对抗时间的流逝而恢复记忆的权利。记忆是获得自由的手段。”
本书根据《博罗夫斯基短篇小说集》(1959年,华沙国家出版局)、《博罗夫斯基小说集》(2000年,波兰萨拉出版社)翻译,同时参考了法国巴黎卡尔芒—列维出版社出版的法译本《石头世界》(1964年)和美国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1986年)。
栏目责编:皮皮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