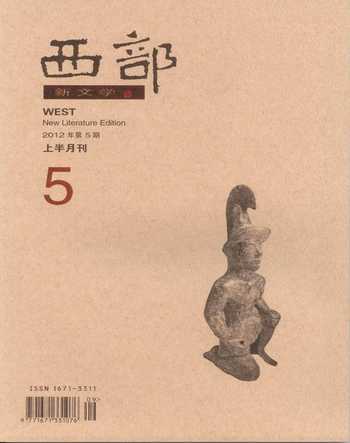少年与芒果
尹德朝
当萧军代的嘎斯69卷着一股蓝色烟尘抵达玛尔图拉的时候,寂静的小镇在秋日的落幕中开始有了一种热忱的喧闹,“芒果来啦——!”孩子们喊,大人们也喊。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玛尔图拉油矿的一个黄昏。那一天,男女老少们都聚集在采油二厂革委会一块灰色土地上,有人开始奏响热瓦甫和羊皮手鼓,没有乐器的人们张开自己的大嘴放声高歌。沸腾圈起了灰色的尘土,使得草绿色的吉普陷入了少有的爱戴之中。人们一边欢唱一边撑大鼻孔,试图从那一屁又一屁的蓝色尾气中嗅出盼望已久的芒果气味。歌声异常粗糙,青客斯山泉颗粒粗大的碱水拉糙了镇民们的嗓门,貌似歌唱的嚎叫,听上去,宛如大锯切石尖利刺耳。人们声嘶力竭着同一句歌词: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面对随车而来的一颗圣果,这句歌词应该是一个欲望的盾牌,人们坚信,这句指意明确的伟人语录一定会压住心头某种欲望的升腾。
最初,人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精神会餐或美丽传说,但当它真的来到的时候,人们如梦方醒,人们不仅感到芒果的真实和存在,更加感到伟人掌控神州大地事无巨细,周到普遍。芒果,伟大的芒果,既不同于往日“最新指示”到来,(虽然热烈却显得空泛和抽象),也不同于食品站拉来一车冻豆腐或羊杂碎,仅仅是一个毫无立场和意义的肠胃填充。芒果,激荡着精神与实惠的双重震撼。
萧军代还没有从车里钻出来,就已经感到,他和他的嘎斯69处于被撼天动地的歌声和喧闹淹没在尘土的危机之中,他发现他与芒果之间有些狐假虎威。他犹疑了一下,没有把芒果抱在怀里,人先钻出车来,他有一点吃芒果的醋。他身穿草绿色军装,斜挎配有烤馕色牛皮套的54式手枪,他踏在车脚板上,面带一副超凡脱俗的当时最为流行的林彪式微笑,他向大家招手致意,笑容可掬。若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他更像一个力夺芳心的车模。那时候,嘎斯69相当于现今的奔驰和林肯。军装、军车、手枪和欢呼让这个萧姓男人释放出了当时最耀眼的炽热光芒。他摆够了Pose之后,才把芒果捧出来。
萧军代的全称为萧军代表。真名叫萧富奎,后改名为萧红军,转业来镇后,相继担任炊事员、保卫干事、民兵连长、人武部长等一系列小镇要职,在将矿长和党委书记统统定罪为走资派之后,他成为玛尔图拉油镇至高无上的当权者。因军装枪械总不离身,便得名萧军代表,简称萧军代。他很瘦,脸很长,酷如鸡爪般的手高举芒果,当他跳入又稠又热岩浆似的沸腾的人群中后,便在鼎沸中煮得不可开交,恐惧向他袭来。
在喧嚣声里,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更为尖细的声音夹杂在声浪里,在众多的眼睛里,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一双更为明亮的小眼睛夹杂在人群中。这个声音是少年匡林的,这双眼睛也是少年匡林的,对于成长在准噶尔盆地深处的孩子来讲,芒果,犹如银河系里的一颗明星,陌生而又亲切。年仅十二岁的匡林从高音喇叭里得知,这颗来自天涯海角的树生果实可以延年益寿,包治百病。也就是说赋予它更多的可贵绝非一个空洞的形式主义,在那甘甜可口的滋味之上,充满了神话般的人性关怀。这分明就是《西游记》里的人参果再现人间。福音,一个老弱病残者和渴望长命百岁者震耳欲聋的福音。
美梦标志性地占据了孩子们最纯真的一块心田的同时,一场灾难,不可避免地走近了少年匡林的幼小生命。
自萧军代掌管了所有权力之后,玛尔图拉便实施了准军事管理制度,为防修备战,石油总局配给的粮油日渐减少,购买食品的队伍越拉越长,少年匡林从他生下来那一天起,似乎就成长在一个暗无天日的购物长龙如海啸般疯狂拥挤的人群当中。小镇看似死寂如水,实则已到了饥寒交迫的边缘。没有食粮,人们便用战备配发的武器疯狂猎杀野兔和黄羊;为抵挡严寒,人们又疯狂砍伐戈壁仅存的梭梭植被;导致饿狼入镇,风沙肆虐。
就在人们所有的信仰即将淡出生命的时候,这颗水果就这样走进了镇民们的视野,其实谁都明白,它什么都带不来。可是萧军代却在高音喇叭上喜传佳话:一滴果汁就能达到百日不饥,千日无寒,食之病除,一食百寿之效果。全镇一千三百二十八人,地富反坏右除外,老少妇孺人均人口一份。”那个荒诞的年代,说什么都有人相信。全镇民众欢腾雀跃,高呼:呜啦——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少年匡林被绊倒在一大堆疯狂拥挤的乱脚之下,就像一块抹布踩踏于黑暗之中,飞起的尘土几乎埋没了他瘦小的身躯,雪崩一般的大脚趟过之后,他爬起来,又急奔而去,他用沙哑充血的语音大声说:“芒果,娘……有救了……”
小镇的天空开始暗淡,人们的潮流涌向一个圆木搭建的墨绿色平台,这里是芒果最终要到达和分割的地方。电线杆上的两盏马奶子灯提前闪烁在灰暗冰凉的空气中,光线异常惨白地铺洒在墨绿色的台子上,使得这个将要针对芒果的手术台更像中世纪的一个断头台。有趣的是,手捧芒果的萧军代走向那个台子的过程非常艰难,失控的局面大有哄抢之趋势。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不该在登上讲台之前就掀开红布露出那个秀色可餐的椭圆体,他两脚已开始离开地面,完全失去了重心和平衡,最后他几乎平躺在了人头之上,如一具供奉的死尸狼狈不堪,完全失去了军威和首脑的尊严。更可怕的是,他腰上的手枪被人拽起,好像还有人抓住枪把抽了一下,他立刻就出了一身冷汗,险些把芒果扔出去。尽管有人不失幽默地高喊:“大家不要挤,让列宁先出去……”惹得一片哄笑,但局面更加不容乐观,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就是在特务说了这样的一句台词之后,列宁惨遭枪杀的。他恼羞成怒,他要拔枪警告,可已由不得他,该死的芒果正满满当当地占据着他的十个手指。不过,万幸,他也只是被人们横着抬起来而已,就向当今的巴勒斯坦人高举着被害兄弟的尸体和棺木那样,人们平平展展地把他放在了台上。萧军代放下芒果便不失时机地把他的手枪从牛皮枪套里拔出来,与枪一起出来的还有一块肮脏的红布,当两发子弹射向天空后,匡林只看到两股淡淡的青烟和红布在充满汗臭的空气中轻轻地淡化和飘落。枪声很滑稽,就像是扔进大海里的两粒石子,红布落在了匡林的脸上,机油和金属气息钻进鼻孔。匡林高举着红布有了向前挤的理由:“叔叔,你的布……”萧军代没有听到一个孩子的叫喊。他看到有许多人正在冲他发笑,他知道这是他微弱的枪声带给他的愚蠢结果,但他还是举着枪,他没有别的招数,军人除了用枪还能用什么?然而他手里的枪一点也不辜负他的希望,枪口指向了两盏闪亮的马奶灯,啪啪又是两枪,很响,不是枪响,而是灯泡爆炸的声音很大,玻璃碎片像雪片那样哗啦啦地散落下来,落在人群的头上脖子里。
灯灭了,场景顿时暗淡,幸好天边还有一丝晚霞撑住了低矮的天空,昏暗世界尚能感到轮廓的残存。人们顿时安静了下来,人们的嘴里一片啧啧声,厉害。萧军代虽然没有杨子荣那样一枪打两盏的神功,但比匪首座山雕一枪只打一盏强多了。而且,那是演戏,这可是真枪实弹。厉害,萧军代人气指数再一次回升起来,酋长般的笑容又回到了他的长脸上。这是他自掌管玛尔图拉以来所展示的第一个军威。不过,与芒果相比,其现实意义还是要远比他的什么破军威大得多。只不过片刻,人们又一次喧闹起来。
作为一镇长官,萧军代是要讲话的,以往,他的每一次讲话都要用掉瑪尔图拉半个白日最廉价的时间,可是今天,他只说了四句话,第一句话:“国家把芒果送给了我们工人阶级,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和鼓舞。”掌声雷动,震耳欲聋。第二句话:“这个芒果百年一果,吃了可以长命百岁。”掌声雷动,震耳欲聋。第三句话:“不过,它还没有熟透,还有一些涩酸,要放一放。”捅了马蜂窝般的叹息代替掌声。第四句是:“瞻仰开始。”
萧军代少有的简单扼要,让全镇人迷惑不解,然而,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
人们的情绪一落千丈,但还是排起长龙,缓步走到芒果面前,吃不到它,看一看也算是个眼福。人们在这颗绿黄粉红四色相间的芒果前停留片刻,与瞻仰一个不朽的死者大同小异。芒果安静地睡在一块枣红色金丝绒里,鲜美水嫩,完全是一副瓜熟蒂落的特征。那妩媚娇嫩的酣睡姿态,那鲜绿、那乳黄、那桃红黯然羞怯的过渡,俨然就是一个刚刚嫁至的美丽新娘。
少年匡林不会为这颗水果附加更多的含意,他最直接的愿望就是尽快得到属于他的那一份。当他走到台前的时候,他的手里还攥着那块包枪布,他仰起头,举手把它送过去,萧军代先是一阵迷惑,低头看枪套,一把就收了过去,他不仅没有一丝谢意反而瞪了少年一眼,他怀疑这个少年就是刚才那个想偷枪的贼。
少年匡林顾不得留意军人的厌恶眼神,他已被那果实牢牢吸引,他自以为做了好事,便具有了对芒果的特权。少年匡林把他的大脑袋探过去,试图想闻到点什么,却没有一点香味进入鼻孔,他想,这一定是玻璃罩阻隔了香味的散發。于是他掀开了罩子的一角,芒果沉重地抖动了一下,使那颗果子变得更为真实,芒果的肉感使得少年情不自禁地将手伸进去,几乎同时,萧军代的拳头重重地打在了这个少年的嘴上。对于一个体形瘦弱的孩子来讲,冲击力是巨大的。少年被打倒在地上,他捂着又腥又咸的嘴痛苦地爬出了人群。他的左门牙已经松动。
夜暗了,芒果被放进厂部会议室里去了,芒果没有被分食,使得这个庆典又落了以往的俗套,它和迎接“最新指示”一样空洞,新瓶装旧酒而已。成年人意犹未尽地散去了,适应和默认那个漫天谎言的年代的每一件事,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可是玛尔图拉的孩子们对大人们的每一句话都坚信不移,他们没有散去,他们不相信芒果会一直放在那里,他们知道食物的最一般规律,时间长了是要烂掉的。他们在路灯下叽叽喳喳,依然热情高涨。只有少年匡林一声不吭地站在一边,用舌尖不停地晃动着那颗松动的牙齿。他对芒果的信心抵触着他对萧军代的仇恨,他发誓,一定要把他应得的那一份拿回去,让病重的母亲吃下去。
温暖在玛尔图拉永远是个奢侈品,一年之中没有几个温热天气,还不到十二月份,天气就像白霜一片寒冷。夜色愈加深厚,寒冷愈浓,路灯下闪烁着纤维般的雪花,孩子们因耐不住寒冷,渐渐也零星离去。只有匡林还呆在那里,他的舌头依然不停地晃动着松动的牙齿。他需要疼痛,疼痛是一台制造热能的机器,他就在疼痛中抵御着寒冷。他跑到革委会的大门前,挤开一条门缝,借着窗外射进来的灯光,他看到芒果安卧在一个讲台上,透明的玻璃罩将它衬托成一幅肖像画,变得陈旧、暗淡,弥漫着一股哀愁的气息。这时,匡林发现会议室朝西的一扇窗子半开着,他就攀爬上去。他并不想做什么,只是想看得更清楚一点,但他听到一声大喊:“谁!”接着是拉动枪械的声音。他几乎是从窗台上掉下来的,他想不到,萧军代就住在一间耳房里,耳房黑暗的窗口正注视着这个少年。远处发电厂的汽笛响起来,这是工人夜班的时间。匡林把两手揣进袖口,舔着他的那颗摇摇欲坠的牙,跑开了。
其实,芒果的序曲早在它还没到来前就在油矿小学开始奏响了,这个具有色香味的消息一下冲昏了孩子们的头脑,在那个年代,普天下所有的孩子们,几乎都在做着相同的水果梦。日子在翘首以待中像蜗牛一样缓慢走过,美梦把玛尔图拉的孩子们几乎都变成了花果山的猴子。
位于小镇西南边的小学,芒果改变了他们的教学大纲。校方在萧军代的敦促下,一直围绕着芒果的生长和成熟做着违背良心的延伸和演绎。老师们说,延年益寿的功能不必多言,医治疑难杂症更是千真万确。在以后的时间里,所有的数学课程都像哥德巴赫猜想那样,分解着一颗芒果如何均等地走进千家万户的胃口。
匡林一直静静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座位上,静默是他的心中挂起的一幅窗帘,窗帘厚厚地遮掩着他巨大的心愿,他要把分到自己的那一份连同他父亲的那份一起让娘吃了,这对他来讲,是生活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他的那双明亮纯净的眼睛平静地注视着眼前的课本,而这样明亮纯净的光泽却看不见一个汉字,这些汉字已被那个神秘的果实冲击得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在心里早已把吃它的工作准备好,甚至把她母亲的病治好后坐火车回老家的事都想好了。
可恨的是,罪恶的数学老师,希望他的学生能表示出较高的革命姿态,要同学们让出自己的那份给萧军代叔叔吃。匡林看见同学们都在沉默。老师不甘罢休,又说,是红小兵的同学应该首先站出来。于是同学们一个一个地站立起来。匡林也是红小兵,他稳稳地坐在他的最后一排椅子上,他不能不要自己的那份,他娘病重。
他的娘已经卧病一年了,医生说是肝病,是要用营养来养的,但是家里连一瓶清油都买不起就别说营养了。娘的病情每况愈下,他曾听到医生对父亲说,准备一下吧,她挺不过这年的春节。匡林觉得很恐怖,他无法想象家里没有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他只有十岁,他需要母爱。现在,这个延年益寿、专治疑难杂症的水果能救娘的命,吃了就能健康地活着,那是他天大的幸福。一想到母亲还能活下来,他就心花怒放。他每时每刻都觉得那颗芒果就在他那幅窗帘的背后浮动着,它孤寂地呆在他心中的一角,发出明亮而寒冷的阳光,它让他警醒,我,就是为你娘的那个病残的身体而来。
玛尔图拉小镇,北靠青客斯山脉,面对准噶尔盆地托里大戈壁,是一个由内地移民而来的油田村落,方圆数百公里,除零星的牧民放牧催马而过,几乎没有人家。这里,埋藏着大海一般的石油,可是油田生产,在那个年代完全瘫痪。听父亲讲,他的老家在安徽,而母亲的老家却在河北,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刚从朝鲜打完仗的父亲,领着匡林的母亲正准备回家收割最后一茬水稻,一阵军号,匡林的父亲被吹上了火车,火车把他带到了新疆这块风沙弥漫的不毛之地。不久他们有了匡林,再不久母亲就得了肝病。肝病使这个三口之家暗无天日。这两天母亲老是在说着一句话:我回不了河北老家了。
芒果来到小镇的第四天,少年匡林对那颗芒果的渴望有增无减。这天早上,他站在他家的门口,抬头远眺青客斯山壁立突起的群山,或高或低的山峦之间,成群的乌鸦盘旋或栖息,一望无际的托里大戈壁几乎终年被大风和沙尘笼罩着,只有西伯利亚的寒流扫荡之后,才可以看到青客斯山脉和大戈壁粗壮的梭梭灌木,灌木中一条石子公路通向远方另一个有人的世界,芒果就是从这条公路到来的。眼下的玛尔图拉油镇,满目一片沙砾的深灰色,十岁的少年匡林踏遍了这里的山川戈壁,除了沙枣树上秋季才能看到的豌豆般大小的沙枣之外,不曾见过任何一颗能够食用的果实。这里的孩子们对水果的陌生,犹如一个天堂之梦。
仅仅过了四天,似乎所有人都不再谈论与芒果有关的话题了。少年匡林依然等待着,他相信大人们不会坐视芒果腐败变质的。他几乎每天都要推开那个会议室的门缝看一看,芒果依然光鲜靓丽地睡在玻璃缸里,他有些纳闷,难道大人们连赶早尝鲜这样的生活常识也遗忘了吗?任何东西都是要被时间给糟蹋掉的。不过,匡林似乎还是能找到答案的,面对全镇一千多号人,也实在难为这颗小小的水果,让它自行消亡也是一个化解矛盾的好办法。但是对少年匡林来讲,就太残酷了。他要进去,拿到它,治好他娘的病。他只拿他和他家人应得的那份,这样是公平的。
窃取芒果的时间定在午夜十二点。一决定下来,匡林就开始坐立不安,这毕竟不是这个少年经常做的事。这个白天,不管他坐在学校里听课,还是坐在他家的床沿边写作业,他的那双不大的小眼睛总是闪烁出透亮饱满的光泽,然而他却看不到黑板上和书上的一个汉字,吃饭时也感觉不到嘴里有一丝味道。那颗芒果覆盖了他整个的生活。夜,终于来到了,他从床上坐起来。家里的人都已熟睡,在这个人人自危的社会,不管明天是不是还有什么荒唐之事,不管能否让病重的母亲吃上芒果,总之他要干一件自认为惊心动魄的事了。
他走出了房门。没有灯亮,这个孤独的小镇早已被寒冷深深裹在了黑夜的被窝里,小镇上的人们都睡得很香甜,他们不愿预知明天,也不再管那个越来越不真实的芒果到底离他们的胃口有多远,能凑合一顿饱饭,再钻进冰凉的被窝里,用身体把暖热的那块地方保住才是最真实的。当然,在自己的体温不再有过多流失的基础上,他们还希望把生活中最需要的猪肉和布票带进梦中。这就是玛尔图拉小镇最美满的夜晚。
少年匡林走到了冰冷夜里,寒风钻进他带伤的牙龈,使那颗活动的门牙在风中战栗,他的左手紧紧握住一把折叠小刀,右手握着一个小药瓶,那是娘吃空的药瓶,他要用小刀切开那个多汁的芒果,不能贪,只要一小块,把它装进小瓶里。他迎着刺骨的寒风摸到革委会门前,耳房的灯还亮着。那个打坏了他牙齿的萧军代,还在为玛尔图拉日理万机。少年匡林知道他的厉害,就趴在一条沟里,静静地等待着那屋里的灯灭,他静静地趴在地上,他知道,如果这样一直趴下去,在凌晨到来之前就会被冻死。他等待着屋里那个令人憎恶的灵魂响起鼾声。夜风刺骨,不時有镇上的民兵,肩扛老式步枪拖拖拉拉地走在沙地里,他们停下来,点着一支莫合烟,再行走,烟抽完了就回家睡觉了。少年匡林仰望夜空,看到一团比黑夜还要漆黑的黑云,黑云就像一群蝙蝠,在空气里翻飞着,翅膀擦着干枯的树叶,掉在了匡林的头上。两小时后,鼾声终于传出来,但是灯却没有熄灭。他是一个谨慎的孩子,他觉得那鼾声有些虚张声势,佯装睡着却像是诱敌深入,他还要等待,他的等待与寒冷在死一样的平静中拼命厮杀,他一次次被寒冷杀死,又一次次被娘温暖的眼睛救活。再一细看,那双布满血丝充满黄胆的眼睛正愠怒地看着他,那惊愕痛切的目光里饱含泪水,娘正拼命在拽他回家,孩子,不要再惹事生非,娘就是死也不要让你这样做……娘知道,这个动荡的社会是顺山而下的洪涛,她的儿子会像一根飘落在河床里的小草,眨眼之间就会席卷而走。可是,少年匡林要救母亲,母亲才是这个破败世界的擎天大柱。黑夜里,他躲避着妈妈那双眼睛的追踪,尽管那是世界上最可依赖的慈爱的眼睛,但他要暂且回避她。
灯也灭了,鼾声终于没有了假寐的成分。少年从雪地里爬起来,在摸到了会议室窗下的那一刻,他又看见了娘的眼睛,像是凝结的冰霜,这是他懂事以来从没有看到过的眼神,他闭上眼睛,他的心里在呻吟,娘啊,你肯定不知道你那惊愕和恐惧的眼神是怎样感动着你的儿子,但是儿子不能没有你,我要救你。他狠狠摇晃着那颗硕大的头颅,聚集着整个生命活力,瞅着那扇半开着的窗口。乌云飘了过去,墨色的天幕,明晰地波动着淡淡的银河。他攀爬上去,一推小窗,开了。他身材瘦小,爬了进去。会议室内不是很暗,窗外被打坏了的马奶灯又装了新的,光线照射进来,芒果照耀在柔和的夜晚之中。他站在室内深蓝色的中央时才真正感到,他的身份变了,他现在是一个贼了,他忽然有些紧张和无策,但是,他闻到了那颗果实的香味,他掀开那玻璃罩,那股香味更加浓烈,但是它的香味好像有些刺鼻,类似于橡胶水或甲醛,这与他的想象出入很大,几天来,无论他怎样幻想这颗果实,随便从哪一个角度来想,它都是那么有滋有味。现在,他将它捧在了手上,却没有感到有什么分量,他掏出小刀,试图将刀刃嵌进果肉割下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可是没有扎进去,刀尖滑向一边,果体却像一个皮球滚向了另一边,这时,窗外巡逻队点烟的火光又出现了。情急之下他放在嘴上狠狠咬了一口。牙齿从芒果上滑了下来。他再一次张开嘴,这一次他咬动了,嘎的一声,牙齿插进了一个空壳之中,嘴里充满了石蜡的味道。上帝,这是一个塑料球体,球体生硬、尖锐,像破碎的玻璃一样,刺伤了他的嘴唇和牙龈、还有他满怀孝顺的心。
他的惊讶突然变成了愤怒,他妈的,骗局,一场骗局。他在心里这样大叫了一声。他再也没有一点胆怯,他是堂堂正正爬出窗外的。他的脸上很潮湿,皮肤上浮着一层愤怒的冷汗。黑夜突然像一个巨大的吸盘,把他的希望、他瘦小的身体和大大的头颅统统吸到了黑夜的肠胃里。他回到家,躺在床上,刚才的事情就像一个荒唐的噩梦划过漆黑的夜。他觉得,舌头的另一半没有任何阻挡地出现在他的左唇边上,舌尖向上一挑,空空荡荡,这才发现,左边的门牙不见了。这一夜,他的思路一直顺着他刚才的行踪寻找这颗失落的牙齿,最后,停在那个芒果的空壳里。他实在不愿让他的那颗门牙定居在刺鼻的塑料壳里,但是思维像一条忠实的狗,找到目标后,趴在那破裂的空壳里,一动不动了。
第二天早晨,学校里笼罩了一层恐慌的气氛,第一节课,数学老师大惊失色地说:“不好了!”话刚开了个头,萧军代就出现在四年级的教室里,他站在数学老师解析芒果的位置上,用一双豺狗的眼睛看着同学们,足足看了十分钟。数学老师站在一边,一下矮了许多,他把脖子像乌龟一样缩进了肩膀里,脸上呈现出一副智障的微笑,这让同学们在自己的身边准确地找到了电影里的“日伪汉奸”。“日伪汉奸”对同学们说:“大家静一静,今天萧军代来给咱们做指示,要讲一讲有关芒果的事,大家欢迎。”同学们掌声雷动。这一下可等来了分吃芒果的消息了吧,芒果再一次唤醒了孩子们的馋涎。
匡林呆呆地坐着,从萧军代的脸上他已经看到了潜伏的危险,这种危险必将以萧军代独特的愤怒方式爆发出来。早晨的阳光穿窗而进,把一身军服的萧军代渲染成一堆巨大的马粪,他一丝不动地站在那里,看着同学们喜形于色。站在那里,把他的凶狠一点一点从瘦脸的皮肤下的显露出来,热烈的空气也一点一点地变冷,他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就那样看着四年级二班的学生们,一直看到同学们疲惫不堪的时候,他突然说:“大家把牙齿露出来。”
同学们被这一句话吓懵了。数学老师立刻说:“大家听话,把嘴张开。”于是同学们都张开大嘴。
萧军代走到匡林的身边道:“你为什么不张嘴?”匡林无动于衷。
“你不张嘴开我也知道,你少了一颗门牙。你的门牙哪去了?”
匡林说:“你打掉了。”
“我知道它去哪里了。它掉在那颗芒果里了。”
“嗷——”全班一下炸了窝。老师挥动两只长臂:“静一静,静一静!”
“你站起来。站上台来!”萧军代说。
全班人都屏住呼吸。匡林从他的座位上站立起来,收拾好铅笔盒和书包,走向前台,他步履缓慢,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走上讲台,晨光照在了他的头颅上,透过窗户,他看到自己家的烟囱上冒出了浓密的黑烟。那是下了夜班的父亲正在为母亲熬药,黑烟是父亲用油渣制造出来的,味道很难闻,比娘的药还难闻,他仿佛又听到了娘的咳嗽声,声音越来越大,之后,他的耳朵就失聪了,他听不到萧军代正在说什么,甚至连全班在冲他喊口号他也没有听到,就在萧军代从腰里拔出手铐向他走过来的时候。他迅速退到黑板前面,绷紧脖颈,突然冲过去,他的大脑袋撞在了萧军代的肚子上,这个高大的男人嗷的一声就倒下了。接着,这个英勇的少年又撞碎了玻璃,像一只扑食的雪豹蹿了出去。
在玛尔图拉的记忆中,萧军代用他亮晶晶的手铐带走过许多人,他从未受到过任何抵抗。他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一个星期零五天,那颗硕大的头颅撞断了他的三根肋骨。
少年匡林从玛尔图拉小镇消失了。人们不知道这个英勇的少年到底去了哪里。人们都说,这孩子饿了就会回来的。这个几乎没有什么交通的小镇,孩子是跑不多远的,他一定就躲在北边的青客斯山上或东面的通古特沙漠里。可是三天过去了,又三天过去了,这个孩子毫无踪影。镇上开始组织人寻找,一百多人一连找了七七四十九天,没有找到。匡林娘握着儿子的照片死了。人人都知道匡林是个孝子,小镇就用高音喇叭,天天对着青客斯山上喊:“匡林你回来,你娘死喽!匡林你回来,你娘死喽。”
四年后的一个春天,有个拾柴人说在北山看到了一个死孩子,匡林的父亲赶到那里,在一个沙沟里,匡林轻飘飘地睡在那里,他轻飘飘地就像一张晒干了的海带,他张着嘴,掉了牙的牙缝里填满了细细的沙。一把小刀和一个小药瓶依然握在已成白骨的手里。匡林的父亲抱着一张干海带,来到玛尔图拉小镇的场部门前,他大声控诉:“萧军代,你出来。你这条吃人不吐骨头的狗!”
匡林找到的消息也如芒果到来一样被疯传开,人们像蜜蜂一样没头没脑地飞过来,愤怒地大喊:“萧军代,你出来!你这条吃人不吐骨头的狗,你为什么拿一个塑料球欺骗我们大家。”
萧军代不知道自己走出来好,还是不走出来好,其实,他也是一个受骗者。四年前,当他在车里发现那是一个假芒果的时候,他也六神无主过,但这是一个遍布全国的真实的谎言,他只有硬着头皮假戏真唱。一排错乱的小牙印和一颗脱落的小牙,让一场火热的尚未落幕的大戏过早穿帮,这使他大为恼火,这是一个政治事件。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了学校,他本想拿着那颗小牙去破案的,可怎么晃动也取不出来。原想堵住这个孩子的嘴,吓唬一下就算了,想不到那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孩子,他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不仅砸烂了那场假戏,还砸断了他的肋骨……
“萧军代,你出来。你这条吃人不吐骨头的狗。”
镇民们也大声喊,很长时间堵在萧军代的门口。他不明白,这个偏僻小镇死的人多了,为什么会对一个死了四年的孩子念念不忘?人们七嘴八舌道出了匡林之死的种种原因,众口一词,是萧军代害死了他,让姓萧的偿命。
萧军代终于走出来了,他依然是一身军装,斜挎手枪,他昂首阔步走出来,背着手站在那里,两眼死狼一般没有光彩。除了匡林爹低沉的哽咽,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了,之后,他穿过人们闪开的小道,消失在风沙弥漫的尘土中,他的背影苍老、孤独。
镇民们找来木匠,为匡林预备棺材。木匠把木料刨了又刨,木头味很快就成了棺材的气味,整个小镇都闻得到。看热闹的人很多,有人嘻笑着说:“归根结底是孩子的嘴太馋……”
一切都来得过于荒唐,小镇上的历次事件总摆脱不了过于荒唐。匡林的死亡连接了那个荒唐年代的天上与地下。
匡林入棺后,铁钉一点一点楔入木头,宛如匡林的牙齿陷入那颗假芒果里,虚拟而不真实。随后整个戈壁旷野响起了棺材的空洞回声。这回声不悠扬,不悦耳,听上去丧心病狂。
若干年后,鎮政府一位女清洁工,把一个落满灰尘的塑料球从某个角落里扫出来,擦掉尘土它依然翠绿鲜亮,放到家里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摆设,可是她发现上边有一个洞,一摇咚咚响,就把它扔了出去。芒果在空中划过一个弧形,在这个过程中,一颗小小的牙齿从里边掉了出来,一阵秋风吹过,树叶和沙尘把它埋在土里,成为它们的一部分。
责编: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