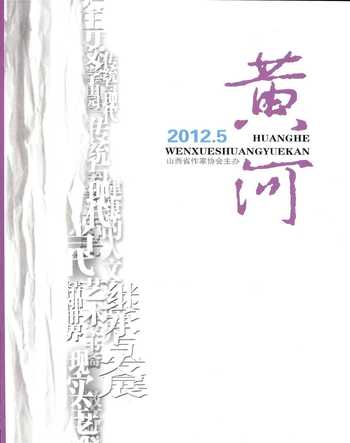那一年,我十八岁
1981年,我18岁,去上雁北师专。雁北师专在一个叫做吉庄的村落里,离市区还远,但大家并不因此而轻看了母校,联想起西南联大时期的李庄,梁思成和林徽因在那里完成了旷世经典《中国建筑史》,想起钱穆先生在昆明郊外就着油灯完成了旷世经典《国史大纲》。我们都叫母校为“吉庄大学”。一半是戏谑,一半则是敬畏。
母校被农村包围着,周围是错落的农舍和茂密的庄稼,校园内则树木参天,高楼三五,图书馆、体育场,书声朗朗,学子莘莘,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但怎么奇异地如此和谐地相处在一起的?想来,这里面肯定是有历史渊源的。
一个18岁的农村孩子,走进一所当时百废待兴之后的高校,其实无疑撞进了一段历史里面了。那是一段历史,是一段国家史,也是一段个人史。我忘不了,那是我的母校。
一、记忆切片
1
吉庄一位老汉,近60岁样子,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胡须浓密,言语铿锵,黝黑的脸膛写满深深浅浅的岁月,开口闭口“扭姥姥吃哇”,像一个从不逃课的学生。他沿着校园叫卖的身影成为学校一道流动的风景,一天不听见他的叫卖声,像一天的戏还没有开场,或者开场之后没有伴奏,心里空落落的。那时候,学校像一个不设防的大港,保卫工作散散淡淡,大家相处都很好,没什么需要管的,不像现在的某些学校如临大敌的样子,撵得商贩没地方跑。他来了,叫卖着,沿着校园走上一圈,然后离开。悠长的叫卖声也渐渐远了。
记得一斤粗粮票换一个煮鸡蛋,二毛钱饭票可买一两猪头肉或熟下水。他原汁原味的吉庄方言常惹得大家鹦鹉学舌,每逢此时,他便会一努嘴翘翘胡子:“看扭哇,张那还像奥大学生赖?”说话唱歌一般。老汉如果现在还健在,今年应该有90岁了吧?
2
学校西墙外,有个小池塘,池塘内芦苇丛生,岸边有几株沙枣树,微风过处,树影婆娑,我总愿将芦苇塘想成白洋淀的芦苇荡,仿佛这样就具备了诗情画意。在干燥的雁北高原,突然有这样一片大水,突然有偌大的芦苇荡,不神奇吗?每到冬天结冰,我总会和同班的宋新海,午饭后越墙而过,在池塘冰面的某个固定点,接力般凿开一个窟窿,日复一日,乐此不疲。
后来我知道,芦苇荡下原来有大片大片不知停歇的泉,水流出来就漫到金沙滩那边,浇灌几千亩土地。民国年间,阎锡山政府为了开垦雁北的土地,曾宴请当时河套地区著名的水利专家王同春来这里勘测过,希望将金沙滩变成肥沃的河套川。
王同春这个人,很难说好,也很难说坏,本事大。他有一只眼瞎掉了。
3
1983年7月15日夜,我曾带4名同学,肩负干柴,徒步10余里攀登学校背面的洪涛山,在峰顶放火烧山,看见火起,我班率先响应,在校园内燃起第一堆篝火。紧接着,其他科级同学也纷纷“起事”,两堆、三堆,一直燃起7堆,颇具神秘色彩的是,站在山上遥望,校园内无意间点燃的7堆篝火,像极了天上北斗七星的形状,将城堡一样独立的雁北师专照成吉庄大地上神秘吉祥的星座,照回吉庄名字的真意——吉祥村庄。
山上举火,在过去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因为山上有长城延宕过去,烽火台一点火,火长烟短,说明着军情的急缓。我们点火时,正在长城边上。
但下面的村庄似乎无动于衷。
4
懵懂好奇的青春期总是和一些荒唐事联系在一起,寻常田野的几次漫步偶尔间发现了新大陆,学校后勤干活的一对中年男女,总会在下午的某个时段,从不同的方向,若无其事地去往同一个地点。有一天,当我们忽然觉察到这就是所谓的“偷情”后,遂待他二人离开后,悄悄摸到校南田边一个土崖下,只见一个放羊倌避雨的小土窑内,躺着块简陋朴素的白塑料纸,像一张孤苦伶仃脸色苍白的面孔。我们揣着做贼的感觉,仓皇逃离,过了好久仍觉得自己非常卑鄙下流。而当事的他俩,毫无疑问看到了我们可耻的行径,自此再没在那里出现过。
多年后翻闲书,戏说孔子便是他父亲与母亲于门外“野合”,才为泱泱华夏诞下这一千古圣人。“野合”,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非正常婚姻关系。但司马迁明确说孔子的父亲母亲却是正经夫妻。那么“野合”呢?当是指这样艰苦的环境吗?若是,孔子出生当属不易。
5
李槟是我发小,晚我一年也来到雁北师专,由于他小巧精致,眼大脚小,踏破铁鞋也无处觅得他那一双38码的小鞋。万般无奈之下,我和谢碧、李清从神头百货门市为他购得一双38女式高跟鞋,回校后由我操刀,花了一个多时辰,用钢锯条硬是将鞋后跟齐生生锯下,锯成平底。由于工艺欠佳,致使李槟穿鞋走路,所踩之处皆坎坷崎岖,这让他小小年纪就过早领略到人生的不平。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尚,跟那个时代迅猛而来的各种思潮一样,生猛如风。
二、老师,是守在我们苍白灵魂边的一捧火
清瘦挺拔的班主任老师郑伯勤,应县人,无论讲课还是说话,总是习惯性以“个呀”作结,亲切温馨又个性十足。
仝祥民老师一副贵妇神态,举手投足典雅端庄,落落大方,她知识渊博,和蔼可亲,毕业10年后我去看她,敲开门的瞬间,她便激动地惊呼“郭虎”,她高兴地说:“前些日子张立波来过,你们班,我只能叫出你和张立波的名字了。”
为我们授课的各位老师,各有所长,每一位都不曾遗忘。杨尚贵老师治学严谨、满腹经纶;左尔忠老师风趣幽默、声情并茂;武世统老师才华横溢、循循善诱;冯巧英老师抑扬顿挫、妙趣横生;刘增寿老师有板有眼、一本正经;曹克明老师不拘言笑、学者风貌……
为我们代写作课时间不长的李新德老师,操浓重的灵丘方言读《阿Q正传》,我等顽劣不恭,下课后一直学他的口音重复阿Q的话:“这个萝卜是你的?你能叫它答应你么?”并将尾音翘得猴子尾巴一样,到收发室取信时仍学个没完。哪曾想,抬头之际,鼻尖几乎与李老师相擦,惊愕得我几乎失声失禁尖叫,那才叫世界上真正的尴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抱头鼠窜,自此,我的我行我素的性格收敛了一半。
杨矗老师的美学课在刚刚拨乱反正的大学里如彩虹仙落,艳压群芳,他一米八的身材清朗俊秀,标准的普通话音质清脆,乐感充沛。他往那儿一站活脱就是一尊美学,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似有迷魂效应,迷倒一大片粉丝纷纷“杨门立雪”,尤以女同学为甚,由于听他课的和做笔记的人多,一度曾造成学校洛阳纸贵。
如果你的一位老师,并且他还是中文系书记,在你的毕业分配上,他比你还着急,那么身为小小的你,除了感激复感激,还能有什么?
像宗志平这样的老师,在中国的大学里,不能说绝无仅有,但多吗?不多。
临近毕业,单纯快乐的我面临人生头一件大事。宗老师亲自带我从神头坐火车,到浑源后又换乘客车前往广灵,去做一个女孩父母的工作,想说服她父母同意她和我一起分配到大同市工作,去为两个刚刚20出头的年轻人圆一个人生大梦。
那个女孩,叫薛建军,像叶芝笔下的末特·岗。我们的初恋无果而终,我们那份宗教般圣洁的爱情,因她父母的反对搁浅,一别成千古恨。此恨绵绵无绝期,生命的月痕,圆明园的疼,我为儿子取名叫郭梦君。
仅仅是为了一个学生,为了一个学生那份神圣的爱情,为了他的工作以及将来,为了不让他的人生落下遗憾的阴影,一个身兼系书记的老师,临近毕业那么忙,却还要亲自出马,这种美好意愿和高尚行为,还有发自内心对学生的呵护负责,纵使亲生父母,也难如此啊!我的生命里能有幸遇到如佛陀般的宗志平老师,真不知是我哪一世修来的福。
三、亲爱的同学们
中文11班50名同学中有8名女生,像当时各系各班一样,男生多女生少,我们那个班只有8名女同学,毕业时居然在本班里连结三对比翼鸟,双宿双飞到今天。如今,三对老鸳鸯,“对镜贴花黄”,相濡以沫,恩爱如故。有必要将他们这种楷模夫妻记录在案,他们分别是引领姐弟恋潮流的常福桃和金利彪,为了捍卫爱情毅然同赴艰苦轩岗工作的马培植和陆静,还有和我同宿舍的于占深与何拥军夫妇俩。
我们宿舍7个人,年龄最大的王长富,常端坐上铺居高临下,从蚊帐缝隙斜眼偷窥于何二人的亲昵之举,一边还朝我们挤眉弄眼扮鬼脸。喜欢“打烂球”的侯学文,因下巴尖瘦,人称“猴头”,毕业后变化最大的莫过于他。10余年未见,有一次我去太原公干,得空去教育学院看他,站在他团委办公桌前硬是不敢确认。他埋头办公,以前的三角猴头完全变成了倒三角,成为下大上小,纵然岁月犀利,也难雕此番沧桑。直至他感觉异样,“你找谁?”一句普通话后抬起头来,立马改为方言:“哎,是这家伙!”我才感叹:人生真是残酷无情!穆献文,这个来自浑源的壮实后生,将他家乡的“国骂”发扬光大到登峰造极,运用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出门进门“百子百子”如嗑瓜子。李善铭和我同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上,又和我同一天走进同一个宿舍,这实属天意,我俩的共同点都是嗓门大,说不了悄悄话。说起同一天生日,颇为蹊跷的是,我和妻子张翠兰也是同年同月同日所生。
睡在我下铺的兄弟高志旺,是个真诚善良的人,寡言,近视。课余,我常看他用尺子打着密密麻麻的小方格,用放大比例法去画一幅人物头像,画出来居然与原像几无二致,很是惊讶他的这一发明:简单实用。分别15年后见到他,听他感悟人生,说一个卑微胆怯的人,就连做梦梦中也是弱者,总是处于被别人追迫的窘境,逆来顺受,不敢反抗。听后哑然。他天性善良,毫无疑问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老师、好公民,他的生活本应该平静祥和,波澜不惊,也不知在这多年的教书生涯中,他受过多少委屈,他一概默默隐忍,独自承受,从不与外人道,想到此不觉为他伤感心酸,只能遥祝他好人一生平安。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上,他是最认真留言的人。他为我写的是一副对联,我至今记忆犹新:“大海蓝天,寄托贤君一世品地,欢聚三载,帮了多少好人坏人,不问个人得失,又有谁不知?僻址寒门,造就不佞半辈生世,痛分两地,盼切几许真友假友,以表众友忘怀,再无人堪忆。”
还有一人,虽不与我同宿舍,但却不能不提,那就是“小脚”张立波,这厮住我隔壁宿舍,自幼学得一些拳脚棍棒,入学后每遇节日庆典,必露两手,一招一式,干净利落,颇像他的为人与说话。这也让我们班集体很为有他而觉得脸面生光。他生性豪爽,声若洪钟,自古英雄出少年,他的酒量入学初即崭露锋芒,现在他是我们班出的最大的官——左云县组织部长,如今喝酒更是如牛饮,酒气豪气冲霄汉。读书时他曾对我说,当初练武功时也练了气功,气进去出不来,鼻口冒血,煞是废人。今天想来,也不知真假?总之他没有让我们失望,无论用拳脚也好,用工作也好,总算打出一片天地来。毕业前他装得人模狗样,看见别人搞对象满脸不屑,嗤之以鼻,毕业后偷偷追下一届美女同学,不期然被我在山阴监考时偶遇。他行踪诡秘,蹑手蹑脚,似又学得武林偷情秘笈,在他的穷追猛打死缠乱磨下,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抱得美人归。他当官后,语气一改往日追人时的温柔,而是眉毛一杨,玩世不恭地调侃:“咋了?叶丽萍,不就是我老婆嘛!”神色颇为自负,好像这世界原本就该是他的。
四、梦起吉庄
学校食堂里最好吃的是猪皮包子,包子刚出笼,黄澄澄的油从白灵灵虚烘烘的包子皮上渗出来,娇艳欲滴,光看上一眼就足以让人为能考上师专而庆幸喝彩,并流口水。雁北师专的包子绝对独一无二,毕业后我走过许多地方,粤菜、川菜、鲁菜,各种菜系也仅仅是个名头罢了,却没有包子,更别提那么可口诱人的包子,那包子真好吃!当时吃包子是男生的专利,每天中午卖包子的窗口万头攒动,熙攘拥挤,女同学挤不上去,只能望包兴叹,思包生津。更有甚者,就有了这样的说法,说是“搞对象就是为了吃包子”,从而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搞对象行列,即使勉强凑合也在所不辞,可见师专包子的魅惑,远胜于女儿国里的唐僧肉。
1982年秋天,曾因为吃了米性猪肉,从而引发的全校学生罢课罢饭大游行,浩浩荡荡直逼火车站,洪水猛兽,势不可挡,学校派出德高望重的老师在半路拦截也无济于事。更有2008级同学在罢饭集会上振臂高呼:“还我生命!还我爱情!”更是震耳发聩,空前绝后,一呼百应,地动山摇。那情景,那阵势,丝毫不逊于“五四”运动,只差没有火烧食堂楼了。
还有,还有女生们住的“大观园”,宽阔平坦的大操场,梦想开花的图书馆,图书馆漂亮的管理员,清凉笔直的林荫道,快乐露天的电影院……记忆的舍利子,粒粒弥贵。1998年,我曾写过一首《途径母校》,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一切的一切,长眠在雪下/我的母校,丝毫不知有一个游子/一种穿透风尘的目光/正向她频频回望……”2004年暑假,毕业20年后同学聚会,旧地重游,物是人非,早已成为朔州驾校的我的母校,像一个破落的贵族,独立吉庄田野上,一任苍老斑驳,风雨飘摇,置身其中,不禁让人心疼落泪……
今天,作为一名诗人,我在杀虎口我的康熙大营门口,虔诚地竖起一块刻有“山西省作家协会创作基地”的巨石,我想为前来这里的所有作家无偿提供一切便捷。我能有今天,都是因为曾经的那个“吉庄大学”。我们青春岁月的精神家园,我的耶路撒冷。我的青春,我的初恋,我的文学梦,都曾在那里盛放。
梦起吉庄,梦回吉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