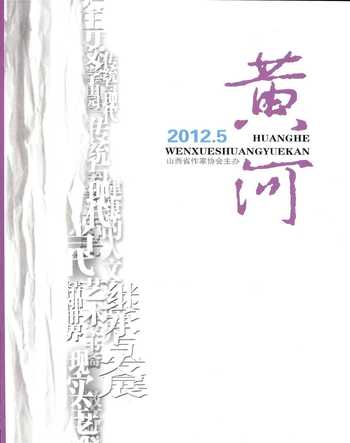读宋杂录六则
蔡润田
避讳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特别的风俗,即在民国之前,凡书写或言说都要避免直接写出或说出君父尊亲的名字,必须用到相关文字时,则以同音或同义字替本字,或者用原字而省缺笔画以避之,是为“避讳”。据说,其俗始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就中,对于孔子及当代帝王之名众所共讳,称公讳。人之避父祖之名,则称家讳。
在宋之问诗文中看到属于“公讳”的有:
(一)“代业京华里,远投魑魅乡”(见《全唐诗》第一函第十册宋之问卷;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下同)。此联见于《桂州三月三》诗中。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世”为“代”。“世业”,世代相传的事业。如《资治通鉴》卷五十六:“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之问这一联说,本来世世代代都在京城做事,可如今自己却被贬到这常有山神水怪出没的边远荒凉之地。
(二)“贤相称邦杰,清流举代推”。此联见于《范阳王挽词二首(其一)》。“举代”:举世,整个人世,普天下。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举世混浊,而我独清。”此处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世”为“代”。这一联,之问称赞追赠为相的范阳王是国中英杰,其德行高洁负有名望,受到天下人的推崇。
(三)“昔者巨浸横流,下人交丧”。此句见于《祭禹庙文》。“下人”:即下民,百姓,人民。如《诗·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此处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民”为“人”。这句话意思是:以前大水泛滥成灾,老百姓处处遭殃。
(四)宋之问有些诗是奉武后(曾自立为武周皇帝)和中宗之命写的,这些诗的题目都缀以“应制”二字。如《幸少林寺应制》、《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等。
这“制”字就是避武后名字“曌”的。皇帝命令,称诏或制。因为武则天,名武曌(音zhao,同照,武则天为自己造的字。另据《资治通鉴》卷二0四记载:为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为武则天选的字,意指日月当空),“诏”与“曌”同音,武则天规定只能用“制”。奉皇帝命写诗不说“应诏”而说“应制”。施蛰存先生说:“‘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唐诗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关于避讳,历史上施行情况并不完全一致。据我有限的阅览,制约施行的大抵有三种因素:一曰礼制(定式);二曰法令;三曰习尚。就礼制层面说,《礼记·曲礼上》:“二名不偏讳。”郑玄注:“谓二名不一一讳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称徵,言徵不称在。”作为一种礼制规定,凡两个字都与尊亲相同的名字,只选择其中一个字予以避讳就行了。不必两个字都一一避讳。但这种礼制实际上大都未能实行,实际通行的是“偏讳”,即每个字都避讳。甚至法令都无济于事。
《旧唐书·太宗纪》:“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以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唐太宗意识到因“避讳”给人们阅读典籍带来的麻烦和混乱,刚登上皇位就立下这个法令,并进而指出“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看来很开明。“据此,唐以前两字兼避,已成风俗,至太宗始禁之。然禁者自禁,唐时二名仍偏讳。《日知录》廿三谓‘高宗永徽初,已改民部为户部,李世勣已去世字单称勣。闫若璩谓太原晋祠有唐太宗御制碑,碑阴载当时从行诸臣姓名,内有李勣,已去世字。是唐太宗时已如此,不待永徽初也。”(陈垣《史讳举例》第四十四)这里,顾炎武说太原考据家闫若璩已发现在太原晋祠,太宗自己立的碑就对自己的名字施行 “避讳”了,这与他“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的政令显然自相矛盾、有些出尔反尔。“可见,法令为一事,习尚又为一事也。”(陈垣《史讳举例》第七十六)
按陈垣先生举“唐讳例”,其中:
太宗高祖子世民 世改为代,或为系,从世之字改从云,或改从曳。民改为人,或甿,从民之字改从氏。
……
武后曌诏改为制,李重照改重润。(笔者按:李重润为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之孙,唐中宗李显和韦皇后长子)(陈垣《史讳举例》第七十六)
太宗当初出于保护文化典籍的考虑,为避免典籍“废阙”(缺漏),免生“讹异”,诏令“二名不偏讳”,但自己就施行不力,别人依然我行我素,照样“避讳”。究其原因,想来,这毕竟是维护皇家面子的事,令是下了,虽不是作秀,也不必太认真的。所以,“避讳”者自不会追究责任。而不“避讳”者,也顺理成章,无可非议。
大概就是这模棱两可的原因吧,宋之问有时避讳有时不避讳。在《始安秋日》诗中有句云:“世业事黄老,妙年孤隐沦。”这里说世代都崇尚黄老之学,自己年轻时候独自过着隐逸生活。其间,却没有避这个“世”字。宋之问因为再度遭贬有意犯讳、以发泄对李唐宗室的不满吗?以之问的畏缩,谅他不敢。只是避与不避当时并非大问题,也不会招致祸患的。事实正是如此。太宗李世民自己也是有时避讳,有时不避讳的。他在李世勣的名字上施行“避讳”,在虞世南的名字上就没“避讳”。在他的诏书中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所以,后唐明宗李嗣源说太宗“自登宝位,不改旧称时则臣有‘臣南,官有‘民部(按高宗时改为‘户部)靡闻曲讳,止禁连呼”(参见《日知录》卷二十三)。“据此,则唐时讳法,制令甚宽。……非如宋之淳熙文书令,广避嫌名;清之乾隆字贯案,罪至枭首也。”(《史讳举例》第七十六)看来各朝讳法宽严不一,唐代比宋、清宽得多了。
才子、才子气
同一题材在不同作者笔下,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格调,这种情况在一些古代同题诗中时有所见。读宋之问的《息夫人》一诗,联想到杜牧、袁枚有关吟咏息夫人的诗作,就有这种感受。尤其是三人同为才子型诗人,其诗作韵味何以大异其趣,个中缘由值得玩味。
息夫人 (即息妫),春秋时息国国君夫人,又称桃花夫人。据《左传·庄公十四年》载:因蔡哀侯向楚王称赞了息夫人的美貌,导致楚王兴师灭息。息夫人被掳进楚宫,后来生二子,即堵敖与成王。但她郁郁寡欢,始终不说话。楚王追问其故,她道答:“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
又《烈女传》卷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虏其君,使守门,将其妻夫人而纳之于宫。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见息君,谓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以身更贰醮,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哉!……遂自杀。息君亦自杀,同日俱死。”
息夫人的不幸遭际及她无言的抗议,在旧时一向被传为美谈。唐时还有祭祀她的“桃花夫人庙”。后人多有咏息夫人的诗文,就我有限的阅读,除以上三位才子之外,还有唐王维《息夫人》,刘长卿《过桃花夫人庙》,罗隐《息夫人庙》,宋钱惟演《无题三首(其一)》;清邓孝威《题息夫人庙》,洪亮吉《题息夫人庙》,孙廷铨《咏息夫人》。
这里,仅就上述三才子的诗略事申说,看该如何评价它们的高下优劣。而这,恐怕首先须有个评判标准问题。然而,文无定法,笔无极诣,诗无达诂。绳墨法度是很难确定的。不过,以愚之见,大略说来,诗文高下,就主观条件讲,至少有两条:一为器识涵养,一为才气性情。二者孰阙孰赡,其作品便会有或深或浅、或文或质、或淳或漓的差殊。
有关息夫人的这个历史故实,宋之问、杜牧、袁枚虽都赋诗题咏,却也因器识、才情的秉持不同,所表现的情感、境界自又不同。
宋之问《息夫人》:
可怜楚破息,肠断息夫人。
仍为泉下骨,不作楚王嫔。
楚王宠莫盛,息君情更亲。
情亲怨生别,一朝俱杀身。
宋之问《息夫人》全用《列女传》之说。之问系初唐才子,一向媚附权贵,品行无足称道。但对息夫人的吟咏,笔调看似平淡,却也寄寓着深切同情。并无逞才使气、乖情悖理之嫌。其识见可谓公允,气度不失淳厚。
杜牧、袁枚的诗都典出《左传》。
杜牧《题桃花夫人庙》云: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
“细腰宫”即“楚宫”,是根据“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翻造的。这一句间接指斥楚王的荒淫。“金谷”,即金谷园,乃晋代豪富石崇的名园。石崇有乐妓绿珠,权贵孙秀求绿珠不得,遂矫诏收崇下狱。石崇临捕时对绿珠叹道:“我今为尔得罪。”绿珠回答:“当效死于君前”,遂坠楼而死。这首诗,以绿珠之死而反衬息夫人之不死,自是意有褒贬。不过在字面上却还不露痕迹。清赵翼《瓯北诗话》说:“以绿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见而词语蕴藉。不显露讥刺,尤得风人之旨耳。”寓褒贬于无形,写得辞微旨婉。这是杜牧的妙处。但是“至竟息亡缘底事?”这一诘问与下句互文,弦外之音是说,息亡是因为息夫人的美色,这就不足为训。到底息亡是因为什么?说穿了,是因为楚国的强暴,息国的软弱。美貌,又何罪之有!诗艺、才情为识见所累,于此可见一斑。傅庚生先生说:“牧之矜才,往往失于轻佻。轻佻则意浅,意浅则濒于漓薄矣”(《中国文学欣赏举隅·雅郑与淳漓》)。
现在来看清袁枚《咏绿珠》言及息夫人的诗句:
人生一死谈何易,看得分明胜丈夫。
犹记息姬归楚日,下楼还要侍儿扶。
这诗仿佛演绎杜牧诗意而来。前两句盛赞绿珠殉节不必说了,后面描摹、嘲讽息夫人的两句,命意、见识自不能与宋之问的诗意淳厚相比。单就艺术表现而言,也不如杜牧的含蓄蕴藉。
袁枚无疑是一大才子。向来才子型的文人大都风发凌厉、心裁别出。鉴于前人对息姬多所同情的态度和杜牧寓讽于婉的诗艺,袁枚自是不甘落入前人窠臼。于是,求新求异,便悬拟出息姬“下楼还要侍儿扶”的矫柔造作之态,从而,极尽揶揄之能事。其笔意不可谓不尖新。然而,生二千载下,以如此尖刻的笔调嘲讽一介“生时蒙辱,死后赍恨”的弱女子,实在有失公允而未免浇薄了。
袁枚《雁宕山卓笔峰》诗云:“孤峰卓立久离尘,四面风雪自有神,绝峙通天一枝笔,请看依傍是何人!”此诗看似状写山峰,实为自况。卓然不群,绝少依傍,确是才子文人的可贵处。但,逞才过甚,失去蓄势,就会显出才子们的负面气息——浮薄与诡异。袁枚咏息夫人诗就有此病。钱钟书先生说:袁枚“论东坡语较平允,然‘有才无情、多趣少韵适可自评。”谈到袁枚批评 “东坡、山谷俱少情韵。藏园、欧北两才子诗斗险争新”时,钱先生说他“蓋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亦拙。”(《谈艺录(六二)》)
袁枚爱“斗险争新”,贯以浮薄小慧自圣,另有佐证。《随园诗话》云:“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诃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日:‘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固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冁然。”乍听,这话确乎雄辩,不能不为袁枚机敏的辩才所折服。然而细味其旨,就觉得很可疑,难道为了“后世之名”就可以将自己的身价系乎一妓女的名下,借以标榜吗?境界如此,实在不好恭维。虽出语新异,小巧小慧而已(参见《中国文学欣赏举隅·雅郑与淳漓》)。
对这位才气横溢的大才子,笔者绝无全盘否定之意。限于识见,这里只是就事论事,觉得他矜才、尚奇,有时就“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至于他文学上的总体成就和影响,岂敢妄赞一辞!
作为对三位才子同题诗(按指题材相近)及相关议论的一则读书笔记,本文不过是想说明这样一点意思,即文人的长处、短处相伏相倚;才情、器识不可偏废。有学有识,无才无情,不免腐儒气;饶于才情,乏乎识见,又难免才子气;而才、识俱无,就只有俗人气了。腐儒气不好,俗人气尤其要不得。才子气呢?看来亦未必佳。清代词学家陈延焯《自雨斋词话》有云:“无论作诗作词,不可有腐儒气,不可有俗人气,不可有才子气。人第知腐儒气、俗人气之不可有,而不知才子气亦不可有。尖巧新颖,病在轻薄;发挥暴露,病在浅尽。腐儒气,俗人气,人犹望而厌之;若才子气则无不望而悦之矣,故得病最深。”
宋之问、杜牧、袁枚同为才子,然而,由于在同一问题上所显示的器识不同,其诗其人的境界就大有差殊,就这一点说,宋之问淳厚,虽系才子而无才子气;杜牧略显刻薄,等而下之;袁枚逞才使性,尖刻漓薄,而尽显才子气,“得病最深”。
逍遥不是适性
“愿与道林近,在意逍遥篇。”这是宋之问在越州长史任上所作《湖中别鉴上人》一诗中的开头两句。此处之问以支遁(道林)喻越州的鉴上人(僧人)。意思是说愿意与像支道林这样的高僧过从,领略逍遥的真谛。这里,之问把道林与逍遥篇并提,其实是在推崇道林,说自己赏识道林对庄子《逍遥游》的释义。
关于道林其人,据记载,支遁,字道林。东晋高僧、名士。世称支公,也称林公,本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人,或说河东林虑(今河南林县)人。约生于晋愍帝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卒于废帝太和元年(公元366年),享年五十三岁。他初隐余杭山,二十五岁出家,他虽为释氏而于“章句或有所遗”。当时名流谢安、王羲之都与支遁过从甚密。后于剡县(今浙江省嵊县)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晋哀帝时应诏进京,居东安寺讲道,三年后回剡而卒(参见《高僧传》卷四)。他精通佛理,有多种佛学著作。好谈玄理,注《庄子·逍遥游》。但著述大都亡佚。笔者所见有限,其生平、学说主要保留在《高僧传》、《大小品对比要抄序》、《庄子集释》和《世说新语》中。尤其后者,刘义庆直接说到与刘孝标注中提到支遁处加起来有五十多处。
宋之问为什么“在意《逍遥》篇”,在诸多注释庄子的著作中如此看重支遁对庄子《逍遥游》的注释呢?其释义有何新颖独到之处?
支遁的注已佚。关于逍遥的释义无从窥其全豹,人们大抵只能从上述有关著述中勾稽其要旨。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即他为《逍遥游》作注的动机是因为不满于西晋向秀(公元227年——280年)和郭象(公元253年——312年)的《庄子注》中的逍遥义。在表示不满的同时也直接道出自己的一个重要观点——逍遥不是适性。
向、郭都是魏晋玄学发展中的重要人物。向秀有《难养生论》(与嵇康《养生论》的辩难文)、《思旧赋》(凭吊旧友嵇康文)传世,郭象有《庄子注》传世。
《世说新语·文学》三十二云:“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 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余嘉錫《世说新语笺疏》第二百二十页)这是说《庄子·逍遥游》向来就是个难以诠释的课题。众贤达名士所能钻研体味到的意蕴都不能超出向秀、郭象两家的义理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与人谈及《逍遥游》,竟别具只眼,超越向、郭,其阐发的新意都是此前一些名流所不曾领略到的。所以,后来人们在解说庄子《逍遥游》时便都采纳了支遁所阐发的义理。
那么,郭象与支遁对《逍遥游》各有怎样的解释,二者有何不同?“支理”何以受到追捧?笔者不学,决非这篇札记能道其详。不过,撮要言之,或许可以透过如下记载窥其梗概。
《世说新语·文学》三十二刘孝标注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曰:‘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鷃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世说新语签疏》第二百二十页)
向、郭认为,大鹏高飞九万尺,尺鷃只低飞于榆木檀木之间,虽有大小的差别,但是都能各自纵任其本性。如果都正好适合各自的性分,则逍遥是一样的。郭象对《逍遥游》的题解说得更明白:“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其间哉!”(《庄子集释·逍遥游第一》见世界书局印行《诸子集成》)这里,郭象强调只要“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就是了,至于大鸟小鸟,是胜是输就不必“曲与生说”了。所以说“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同上)“照郭象看,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以‘自性为根据,……所以事物‘各以得性为至,自尽为极也。就这点看,……‘安命就是‘顺性。”(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二百八十三页)易言之,适性亦即逍遥。
然而,支遁并不这样认为。南朝梁代慧皎《高僧传》卷四《支遁传》:“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按:此人名与《世说新语》所记不同,或许当时二人都在场,二书所记各有侧重)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
关于桀跖,一说桀跖即夏桀和柳下跖的并称。泛指凶恶残暴的人。《荀子·荣辱》:“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淮南子·说山训》:“坏塘以取龟,发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脣而治龋,桀跖之徒,君子不与。”一说桀跖,又名柳下跖,原名展雄,相传是当时贤臣柳下惠的弟弟,为鲁孝公的儿子公子展的后裔,因以展为姓。系战国、春秋之际奴隶起义领袖。在先秦古籍中被诬为“盗跖”和“桀跖”。
这里,支遁因袭旧说,以桀跖为邪恶。说桀跖那样凶恶残暴的人他们也是适性而为的,难道也算是逍遥吗!所以他说:“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鷃。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鷃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遥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世说新语签疏》第二百二十页。并见于《庄子集释》)
这里,支遁在《逍遥论》中说,所谓逍遥,是讲“至人”的精神状态。庄子阐发这方面的大道理,而以大鹏与尺鶠的寓言来说明。大鹏生活的范围辽阔广大,所以在身体之外无所谓适应与否的问题;尺鷃生活在低近处而嗤笑在高远处的大鹏,是由于内心的骄傲。“至人”随顺万物的本性并且有很高的兴味,游历无穷而不受约束,驾驭万物而不执着于万物。这样就可以悠然而不会心为物役,迷惑不会产生,达到不疾而速,优游自得而无所不适。这就是逍遥的境界。如果人所有的欲望都与所能得到的相当,并满足于所能得到的欲望,快乐得有似天然本性,这就如同饥饿的人得到一顿饱餐,口渴的人得到一次痛饮一样,岂不是有点干粮就忘掉了丰盛的祭品,有了口水喝就拒绝了浓醇的美酒吗?如果不是最高境界的满足,难道可称其为逍遥吗?
支遁在此明确提出:所谓“逍遥”,是“至人”的精神状态。并不是任何人所有的精神状态都可以称为逍遥的;这种逍遥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至高境界的“至足”;并不是“有欲当其所足”的“苟足”, 即并不是不管什么欲望,得到满足就是逍遥。“此向、郭之注所未尽。”(同上)是直接针对向、郭“各适性以为逍遥”的。
陈寅恪先生说:“郭象旧义原出于人伦鉴识之才性论。故以‘事呈其能及‘极大小之致,以明性分之适为言。林公窥见其隐,乃举桀跖性恶之例,以破大小适性之说。然则其人‘才藻新奇,神悟机发(世说新语品藻类郗嘉宾问谢太傅条注引支遁传),实超绝同时之流辈。”(《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89页)
无怪乎宋之问“愿与道林近,在意逍遥篇”了。
不向俗人说
宋之问在武后当政初期,曾写过一首骚体诗(或曰乐府诗),题为《冬宵引赠司马承祯》。诗曰:
河有冰兮山有雪,
北户墐(以泥涂塞)兮行人绝。
独坐山中兮对松月,
怀美人(友人)兮屡盈缺。
明月的的寒潭中,
青松幽幽吟径风。
此情不向俗人说,
爱而不见恨无穷。
这首诗是写给他的好友司马承祯的。之问早年向道,寓居嵩山时,与司马承祯同师事道士潘师正。与司马也可谓师兄弟了。大约后来两人不在一处,见面的机会很少吧,之问写了这首景色清幽、情感深挚的怀人诗。诗意大体明白,无须辞费。就中,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句:“此情不向俗人说”。这“不向俗人说”颇耐寻味。于之问,何为“俗人”?在他人,通常指什么人?对此,我想就见闻所及,迻录如左,略事申说。拉拉杂杂,不过是些所谓“獭祭”“丛脞”之类的杂碎堆积而已。
首先,说到俗人,须先释“俗”。《释名》:“俗,欲也。俗人所欲也。”至于“俗人”,通常似乎释义如下:
1.庸俗的人;低俗的人。《荀子·儒效》:“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
2.一般人,普通人;百姓,民众。《老子》:“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3.佛教、道教指未出家的世俗之人,与出家人相对。东晋法显《佛国记》:“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麤。” 宋代洪迈《夷坚甲志·僧为人女》:“汝为方外人,而受俗人养视,如此惓惓,有欲报之意,以我法观之,他生必为董氏子矣。”鲁迅《华盖集题记》:“在和尚是好运……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
以上,是对俗人的三种释义。但从佛、道观点看,教里教外,出处有别,和尚、道士而外,不论雅士抑或凡夫,百姓抑或宰相,都是俗人。即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出家人和俗人两种人。但实际上,“俗”不特与佛、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在儒学传统中亦与“雅”相对。《周礼·天官》:“不雅曰俗”。职此,推及社会人群,俗人而外,也便有雅人。而雅、俗则构成价值判断,意有褒贬,是可轩轾的。而且,单就雅和俗来说,雅有高雅、典雅、儒雅、俊雅、清雅、优雅、和雅、大雅等种种人,似乎各有特征、却无高下,大抵都含褒义。俗则不然,凡俗、流俗、低俗、粗俗、庸俗、鄙俗、恶俗等层次中人,不惟彼此有程度、性质的不同,大凡曰“俗”,都含不同程度的贬义。惟其如此,历史上,不论文人雅士还是仕宦中人,贤与不肖,只要称他者为“俗人”,一般都有清高自重、不屑为伍的意味。贤达、名士、才子、士大夫者流有这个派头,一些势利小人也以此自圣。正因为这样,这“不向俗人说”出自不同人之口,或自重,或自诩,或刺人,或讽世,或扬己抑人甚至荣己而辱人,其意味是不尽相同的。
就宋之问来说,诗中言说的对象为道士司马承祯,俗人当泛指未出家修行的普通人。但普通人与道士价值取向、生存方式或有不同,却难以抑扬褒贬。而且之问诗中所勾勒的情境无关道家宏旨,常人可以领略。不必强调只对道士司马,不向普通人说。所以,这里“不向俗人说”之“俗人”,就不是一般普通人,而是带有不屑与谭的贬义了。但是,之问何人?在武后和中宗朝,他本可以凭自己的非凡才具,有个安定而荣耀的生活和身份的。他却名利熏心,附炎趋势,夤缘幸进,甚至给武则天的嬖臣“捧溺器”,行径如此鄙俗,也还要大言“不向俗人说”,这就嫌矫情,有些崇己而抑人的味道,也多少有点才子气的张狂。而且效仿雅人口吻,也别有作秀和“无疾而颦”的嫌疑。
同样的话,出自另外一些人之口,就觉得信实而得体的多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说自己遭受宫刑还忍辱负重写作《史记》。这番苦衷,只能说给富于超越意识的具有大智慧的人,一般世俗之人是不可理解的。这里,固然有自尊,也未始没有刺人或愤世嫉俗的意味。想到司马迁的身世、遭际,这话就不为夸饰。
有些人并非出于“孤愤”,毋宁说是自重自赏,自标高洁,也说这样的话。黄庭坚《寄题安福李令爱竹堂》:“渊明喜种菊,子猷喜种竹,托物虽自殊,心期俱不俗,……富贵于我如浮云,安可一日无此君。人言爱竹有何好,此中难为俗人道”。在《书赠俞清老》中还说:“陶渊明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夫真处盖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这里的“难为俗人言”云云,是谈他与李令、俞清老在脱俗境界方面的会心、相得,是自尊自赏,自标高洁。其间,惟以俗人衬托自己之雅洁,未必措意于贬抑。俗人犹言普通人。又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瓠子河》:“ 时水又西迳东高苑城中而西注也,俗人遏令侧城南注。”这里俗人亦即百姓,就纯粹是个中性概念了。
自然,也有言及“俗人”而带贬义或略作针砭,谓其低俗或庸俗的。《后汉书·张衡传》:“(衡)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红楼梦》第三二回:“宝玉道:‘罢!罢!我也不过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罢了,并不愿和这些人来往。”鲁迅 《南腔北调集·论翻印木刻》:“中国的雅俗之分就在此:雅人往往说不出他以为好的画的内容来,俗人却非问内容不可。”
不消说,称他人为“俗”,有话“不向俗人说”者,至少须自身先得避免俗气,须不俗或脱俗。而要脱俗,就得旨趣淡泊一些,别汲汲于功名利禄,别太在乎世俗价值。“于世俗事,窥其藩而不入,据其鼎而不尝”(黄庭坚《书枯木道士赋后》赞李长倩)。这说来容易,做到却不易。尤其如我侪血肉之躯、凡夫俗子是很难脱尽俗人味的。但难归难,还是应在俗世中力求少些俗人气。浑浑噩噩,完全随流从俗是可怕的。黄庭坚云:“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书嵇叔夜诗与侄榎》)苏轼《于潜僧绿筠轩》亦云:“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人生活的雅致不容易。跌入“欲壑”,俗起来就很难收拾。
不过,俗与不俗,重在内心修养,并非刻意或时时挂在脸上。有人问黄庭坚“不俗”该是什么样子(“或问不俗之状”)黄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士之处世,或出或处、或刚或柔,未易以一节尽其蕴,然率以是观之。”(《书嵇叔夜诗与侄榎》)不俗的人日常生活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在面临重大考验的关键时刻志向就显出来了。士人在生活中超脱还是入世,刚强还是柔顺,仅凭一次关乎大节的行为是很难全看清楚的,但他的俗与不俗都以这一事关“大节” 中的表现来裁断。黄庭坚认为平素可以同世人和光同尘,重要的是要有不俗的内在心志。“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次韵答王慎中》)。这与老子“常宽于物,不削于人”的涵容心态,与庄子超脱恣纵又不睥睨万物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庄子·天下》有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不谴(拘泥)是非,以与世俗处。”生活中的道家,如何行藏出处、待人接物,庶乎可知大概了。
雅俗问题多半已成为历史话题。古今异势,观念异趣。如今,日常生活中,俗与不俗已界限模糊,很难判断。对此,有所轩轾已属不易,若再求雅,更近讽刺了。
猿、猿声
读宋之问的诗,看到若干咏猿或猿声的诗句。颇也引起我的一些联想。
这里,不妨先对猿这种动物略事申说。
2010年秋,笔者曾到黄河沿岸的垣曲县境游览。在该县参观有关猿的新发现的展览。据云:1994年,中美科学家来到山西省垣曲县考察。在这里,曾发现了中国科学史上第一块始新世哺乳动物化石。1995年5月,他们在黄河北岸寨里时,发现了众多的世界上最早的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特征的猿类化石,主要是牙齿化石和颌骨化石,并且命名为“世纪曙猿”。另据考证,曙猿生活在距今4500万年以前。专家认为,世纪曙猿的发现,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并且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参观了垣曲博物馆 “世纪曙猿”遗址的介绍,似乎使我对这种动物感受更直接、深切。不过,笔者对猿感兴趣倒不在其起源,而是勾起我对猿的“文学形象”、尤其是对古代诗歌中“猿”的意象的联想。
在动物学意义上,猿为哺乳动物,是灵长目动物的总称。这种动物在我国文化典籍中多有记载。我国古代字书中对这种动物的相关阐释大致是这样的:
《尔雅·释兽》:“猱猿擅援”。郝懿行《尔雅义疏》引《玉篇》:“猿似猕猴而大,能啸。”郝又云:“按陆机以长臂为猨”。《说文》:“蝯善援,禺属。”按:经查,蝯、猨、猿。一字异体。“蝯”较古,“猨”、“猿”是晚近出的俗字。
有关典故,如:
貉逾汶则死。——《考工记·总目》。注:“貉或为猨。谓善缘木之猨也。”
毋教猱升木。——《诗·小雅·角弓》。传:“猱,猨属。”
猿狙之便自山林来。——《庄子·天地》
猿猕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鼈——《战国策》
猿之所以寿者,好引其末,是故气四越。——汉·董仲舒《春秋繁露》
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的猨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里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按即“断肠猿”)。——《世说新语·黜免》
又如:猿猴献果(指将人的四肢在胸前捆在一起的姿势;京剧《谢瑶环》来俊臣的酷刑中即有此一招儿)猿狖(猿猴);猿眩(猿临悬崖而目眩。极言险峻);猿臂(臂长如猿,运用自如,亦比喻攻守自如的作战形势)等。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猿”常出现在古代诗人的笔下,尤以“猿声”见著。我在读宋之问诗作时,发现至少有如下几处:
猿躩时能啸,鸢飞莫敢鸣。(《入泷州江》)
沓障连夜猿,平沙覆阳雁。(《自湘源之潭州衡山县》)
破颜看鹊喜,拭泪听猿啼。(《发端州出入西江》)
泛舟依雁渚,投馆听猿鸣。(《发滕州》)
鸟游溪寂寂,猿啸岭娟娟。(《下桂州龙目滩》)
猿饮排虚上,禽惊掠水飞。(《早入清远系》)。
说法初闻鸟,看心欲定猿。(《宿清远峡山寺》)
其实,不自初唐始。魏晋南北朝以来,就有咏“猿”的诗歌。(而咏巫山猿的似乎更多。可能此地多猿)如: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引渔歌。
在唐代,人们耳熟能详的,如: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早发白帝城》
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王昌龄《送魏二》
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刘长卿《重送裴郎中贬吉州》。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杜甫《登高》
为什么古代诗人诗作多“猿声”,以致成为古典诗歌特有意象呢?纵观这些诗文作品,恐怕与猿在典籍中所记载的特性分不开的。其一,作为人类的祖先,与人类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其智能、灵性有相通相近处,故以猿鸣喻人情。其二、猿擅啸、声哀。叫声凄切,悲凉凄清,象征忧愁幽思。《山海经·南山经》载:“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校木,多白猿。”(“发爽之山多白猿”)晋郭璞注:“今猿似猕猴而大,臂脚长,便捷,色有黑有黄。呜,其声哀。” 《水经注》在记述三峡时引用《荆州记》等地记所载,曾先后三次提到了三峡的猿:“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者也”,“此峡多猿,猿不生北岸,非惟一处,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闻声,将同貉兽渡汶而不生矣。”“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诗中之“猿”,大都取“有灵性”与“其声哀”“凄异”这两层意思。刘鹗说:“猿猴之为物,跳掷于深林,厌饱乎梨栗,至逸乐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泣也。故博物家云:猿猴,动物中性最近人者,以有灵性也。”(《老残游记·自叙》)就此,猿的叫声,成了古代诗人们表达悲哀、伤感的特有意象。这是与今人的感受和表达方式所不同的。当然,也有例外。李白《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则突破以前咏猿时的哀愁、悲伤的氛围,将欢悦的心绪和浪漫的情凋融入三峡两岸不断啼叫的猿声之中。成为三峡咏猿诗的另类经典之作,传诵千古。再则,若非与鸣声连属,单独用“猿”字,则可能别有意涵,如宋之问如上的“看心欲定猿”,其“猿”字盖谓人心邪僻,有贬义。《维摩詰经·香基佛品》:“以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法制御其心,乃可调服。”之问此句,意即在此,与表达伤感无关。
缘何乐道王子乔
在唐才子“西河(今山西汾阳)宋之问”的诗作中多所道及王子乔。那么王子乔哪路神仙?何许人也?据《列仙传》和《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载:王子乔,周灵王(公元前571——前545在位)太子,字子晋,或名晋,字子乔。幼好道,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今河南境内)之间,遇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修炼三十年后受书“桐柏真人”。一天,对山中的柏良说:“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缑氏(在河南)山巅。”果然,那天他乘白鹤落在山岭上,人们可望而不可及。于是,他“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列仙传》说人们为他在嵩高山立了祠庙。并有赞词云:“妙哉王子,神游气爽。笙歌伊洛,拟音凤响。浮丘感应,接手俱上。挥策青崖,假翰独往。”宋之问何以对这样一个由人而神的仙人津津乐道呢?
据史书记载,宋之问青年时代师事著名道士潘师正,与其弟子司马承祯、韩法昭及隐士田游岩等交游,出入道观,日后诗文中屡屡提及神仙类人物,容或有其道家人物熏染和信仰问题。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简单,言在此,意在彼, 诗中的“王子乔”是别有所指的。题为《王子乔》的诗作其旨趣就是如此。
且看其诗《王子乔》——或曰长短句:“王子乔,爱神仙,七月七日上宾天。白虎摇瑟凤吹笙,乘骑云气吸日精。吸日精,长不归,遗庙今在而人非。空望山头草,草露湿人衣。”
那么,这首诗究竟为谁而作,是何背景?《资治通鉴》卷二0六记载这样一件事: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六月,武则天“改控鹤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昌宗饮博嘲谑。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鹤于庭中,文士皆赋诗以美之。”原来,宋之问是以王子乔比拟、美化张昌宗呢。这里的 “诸武”即武则天侄子武三思、武承嗣等武氏宗亲。张昌宗何许也?之问何以要如此美化此人呢?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被武后宠爱,被武、宋追捧的神秘人物吧。
据有关记载,张昌宗,神功元年(公元697年),由武后女儿太平公主推荐,与其兄张易之同入侍宫中,为武则天男宠。其为定州义丰(今河北安国)人,行六。美姿容,人称六郎美如莲花。觐见武则天时他们“年二十余,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词”,武则天见后“甚悦”,封昌宗为云麾将军,行左千牛中郎将——即贴身侍卫将领,封易之为司马少卿,不数日又进拜昌宗为银青光禄大夫,配给侍从。从此,二张俨若王侯,每天随武皇早朝,皇帝听政完毕,就在后宫陪侍女皇。二张那时的受宠程度可以从当时权贵们对其吹捧来说明。当时权倾一时的武承嗣等人都甘为二张“候其门庭,争执鞭辔”;甚至武三思还吹捧张昌宗是“王子晋后身”;当有人赞扬张昌宗之美“面似莲花”时,宰相杨思礼却谄媚道“乃莲花似六郎”;甚至太子李显、太平公主等人还两次上表请封张昌宗为王,最后因为不合制度,武则天“乃赐爵邺国公”。长安元年(公元701年),皇太子李显的儿子邵王李重润、女儿永泰公主及其丈夫魏王武廷基暗地里议论二张专政,被二张知道告于武则天,武则天竟然“皆逼令自杀”。因一点小事而逼杀孙子女和孙女婿,可见二张受女皇宠爱之深。武则天为安置二张等宠臣还特意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设立一个新机构控鹤府,以易之兄弟为控鹤监内供奉,后又改控鹤府为奉宸府,又以易之为奉宸令。
张昌宗与兄易之专权乱政,时人侧目。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病,崔玄暐、张柬之等人率羽林兵以谋叛罪诛之。昌宗粗能属文,其应诏和诗,多为宋之问、阎朝隐所代作。武则天以其丑声外闻,欲以美事掩其迹,诏撰《三教珠英》,令昌宗主之。昌宗乃引文学之士李峤、张说、宋之问等二十六人,分门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两《唐书》均著录其领衔之《三教珠英》并《目》一三一三卷,为唐代规模最大之类书,今已佚。《全唐诗》卷八○录存其诗三首。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七八、《新唐书》卷一○四《张行成传》附。
关于宋之问作诗美化张昌宗一事大约发生在武后朝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以后。本年二月,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失宠被杀,太平公主将自己的男宠张昌宗送给母亲解闷。从此,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就成为武则天最心爱的侍寝男宠,每天都跟随在女皇的身边,张昌宗是个男宠,但并不是绣花枕头。他出身名门,精通音律,容貌俊美,也工于心计。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张六郎昌宗远远不如他的五哥张易之出名。但是在则天一朝的宫廷中,张昌宗才是最出色的美男。武则天和所有的帝王一样都追求长生登仙之术,她很羡慕传说中的周灵王太子姬晋(即王子乔),这位王子乔传说擅吹笙作凤鸣,后随浮丘公登仙而去,成仙后还乘白鹤现于缑山,人称“升仙太子”。武则天曾经为这位升仙太子题写过碑文。于是马屁应运而生。武三思想讨姑妈的欢心,便将她最羡慕和最心爱的人扯到一起,说:“我以为六郎之美,已非凡世所能有,他一定是王子乔转世。”武则天很欢迎这个比喻,下令造鹤麾并制木鹤,将张昌宗打扮成她心目中的王子乔模样,果然仿若神仙中人。后来宫中游宴赏莲,马屁又诵道:“六郎似莲花。”谁知高手还在后面,宰相杨再思的发言更胜一筹:“非也,正谓莲花似六郎。”虽是马屁,但也足以证明张昌宗的美色非同凡响,始能先动太平公主,再动武则天,又在传说中被选为打动上官婉儿的人物。但宋之问赋诗“美之”绝非仅因为张昌宗的美色,主要是缘于张宗昌那炙手可热的权势,而这,正是之问一入宫廷就諂附张氏兄弟,并在后来受牵连被贬谪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