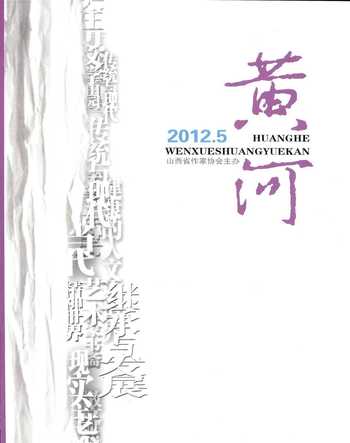短篇小说二题
柳敏
安一刀
——乱世奇人之一
安一刀本姓安,绰号安一刀,是威鲁城的屠夫。城里人之所以这么叫他,是他杀猪宰羊手脚利索,只一刀就能让牲畜毙命。
威鲁城是一座古城,在军阀混战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处处显现衰败的迹象。历史给这座城积累了很多陈旧的东西,破旧的城墙,凌乱的街道,包括各种迥异的人物,安一刀就是其中之一。
安一刀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他很不愿意听到人们叫他安一刀。他常常站在家门口想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绰号有杀性、太狠,人们叫他安一刀时,惭愧怨恨会同时涌入心中。其实,他入屠夫这一行当只是谋生而已。他屠杀利索,是他对牲畜的命脉看得准,他不想让牲畜疼痛的时间太长,不想看到牲畜痛苦的眼神。正因为如此,他练就了一刀毙命的本领。虽然安一刀的职业不足挂齿,但他对自己的衣着却很讲究。没活儿的时候,穿着黑大褂,袖口翻出的里子煞白,在大街上转悠。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很是显眼。城里的人们调侃他几句,安一刀大度地哈哈一笑,挥袖而去,很有风度。
安一刀肚痛的毛病是他老婆生第三个女儿时落下的。安一刀的老婆白凤英是威鲁城的接生婆,四十有余的白凤英在威鲁城接生了无数男女婴儿,但自己总生不下个男孩,为此白凤英受到了安一刀无数次的冷嘲热讽,自己也觉得在安一刀面前抬不起头来,成了白凤英和安一刀的心病。这第三次怀孕,白凤英是怀着志在必得男孩的信念怀上的。而安一刀慢慢觉得这是天命。虽然现在世道纷乱,家里有个男孩能顶挡门户,但自己要了无数牲畜的性命,作孽多,也可能是天谴吧,对妻子生男生女无所谓了。但说归说想归想,安一刀还是心存一丝希望,表面上看他坐在外屋喝茶,心里却急得如火炉上的开水,滚滚翻花。助产的是育婴堂的护工方舟,她在里屋喊道:“安大哥,端一盆开水来!”
安一刀送进开水去,见躺在炕上的妻子目光斜视,怨恨中带着冷漠。安一刀觉得这目光很陌生,心里顿觉不安,肚子也憋得紧,他急急出了家门,到院子一角的茅房解手。站在茅坑旁,他等呀等的,却怎么也尿不出来。
屋里又传来方舟的喊声:“安大哥,草纸!”
安一刀又跑回屋子找出草纸,递给方舟,然后重新跑到茅房,但还是尿不出来。
方舟又喊叫了:“安大哥,开水!”
安一刀再次跑回屋里,提起火炉上的铜壶往水盆里倒。壶嘴里冲出的开水哗哗作响,如小便。这时,肚子忽然开朗,他终于尿了出来,但不是尿在茅房里,而是尿在了棉裤里,裤裆里如浇了一壶开水,热热的,贴肉地热……
“哇哇哇,”随着一声婴儿啼哭,方舟喊道:“生了,是个女儿……安大哥又一个酒壶壶……”威鲁城人把生女儿谓之“酒壶”,意思是以后女婿会经常给岳父送酒喝。
安一刀听见方舟的话,心里凉凉的,木木地端着开水,叉着腿,挪进了产房。白凤英手捂着脸,躺在凌乱的被褥上,无语又无奈。安一刀长叹一声:“命啊!”
白凤英终于憋不住了,失声痛哭,婴儿不解父母的苦衷,也拼命哭起来。哭声回荡在这个昏暗的屋子里……
安一刀很悲哀。虽然他心里早有准备,但面对实实在在的现实,他还是难以接受,心如刀绞。安一刀认命,是缘于一次为骑兵赵司令杀猪的事。赵司令为三姨太过生日,安一刀包下了杀猪宰羊的活儿。杀一头猪时,猪被一群当兵的惊着了,在操场上乱窜。好不容易收拾到屠案上,安一刀一刀下去却没中命门,猪挣脱了束缚,脖子上带着屠刀红了眼乱窜,最后当兵的给了一枪,才解决了几近疯狂的猪。在一旁看热闹的杨疯子喊叫道:“安一刀,你杀生太多,你要断子绝孙!”安一刀拾了块石头朝杨疯子扔去,杨疯子吓跑了,但话刻在了他心里。从此以后,安一刀一拿起刀来,就想起杨疯子的话。他隐隐觉得身后有报应,想扔了刀,另谋一条生路。可从小学了这手艺,再另找个活干,比登天都难。直到老婆白凤英又生了个三丫头,他才彻底认了。
白凤英生完孩子三个月后的一天,后巷李家媳妇生孩子,让白凤英去接生。白凤英走了一个时辰的功夫,安一刀在家里又尿不出来了,尿憋得如一团火烧,烧得他心急如焚,一个劲地叫骂,女人们生孩子与我有球关系?这时灶台上的铜壶响了,忽然间安一刀想到铜壶嘴冲击水盆的声响,他急忙提起咝咝作响的铜壶,冲着水盆倾倒,开水一泻如潮,热气腾腾。同时,安一刀也一下身心舒畅了,裤裆里热辣辣湿乎乎的,憋着的一泡尿一泻而尽。
片刻,白凤英拿着李家给的几包红糖和一篮子鸡蛋回来了,满脸灿烂的笑容:“又接生了个胖小子……”
“人家生儿子你高兴啥了?有本事你也生一个!”
白凤英脸僵了,忽然哭开了:“我命苦哇……上辈子没干人事……缺了德……葬了良心了……让我断子绝孙啊……”
安一刀听明白了,她哭的是自己,骂的却是他,而且骂得很准。安一刀再不敢声张,悄悄溜出了家门。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安一刀心里一直放不下肚痛的毛病。他找到城里有名的医生龚先生,龚先生听了他的病说:“女人生孩子你肚痛,这病有点怪气了。”
“我就是想让老婆生个儿子嘛……”
龚先生打断了他的话:“现在这世道,生儿子是葬良心了!”
安一刀不解地问:“生儿子怎么就葬良心了?”
龚先生硬硬地说:“男孩子们都当兵了,生个男孩就等着当炮灰啊!”
安一刀如醍醐灌顶,忽然明白了。安一刀喝着龚先生的汤药,心里舒畅,日子也过得平静。
这一日,城外晾马台村一双老人意外去世。老俩口只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女儿把老人生前养的两头肥猪杀了,来招待帮忙丧事的人们。杀猪的事安一刀承揽上了,活干得相当顺利。可当收拾完头蹄下水时,一群男女进了院子,跪在棺材前烧纸哭丧,哭着哭着就出了相,什么“盖了烟囱绝了户”,什么“坟头没了填土人”,什么“断子绝孙”……跪在棺材一旁的女婿听不下去了,就站起来和这群人吵闹开了。原来这群人是逝者的本族人,是来闹丧的。一场丧事变成了闹剧,吵吵闹闹,纷纷扬扬,让灵柩里逝去的两位老人作何感想?
晚上,安一刀啃着挣来的猪蹄,喝着烫热的老白干,潸然泪下,感叹人生无常,后事难料,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想想自己三个女儿能否顶得住门户?
白凤英领着三个女儿回来了,她是去伺候方舟了。在育婴堂长大的方舟没名没姓,更没有父母,是教堂的神父给她起了方舟这个名字。方舟性格内向,生性怯懦,如今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婚嫁,一直在教堂生活忙碌,有时当当白凤英的助手。两个女人很说得来,所以方舟有什么事都愿意叫白凤英。前些时,方舟吃不进饭,日渐消瘦,终于卧床不起了。白凤英成天陪在身旁,照顾她,安慰她。
白凤英见安一刀神色忧伤,眼含泪珠,问道:“怎么了?”
安一刀叹了口气:“今儿出活,东家就一个女儿,顶不住门户,让人家欺负的……”
白凤英本来就对方舟的病伤心,现在又见安一刀怨她没生男孩,心里顿感悲伤,眼泪一泻而下:“你又嫌我们母女了……我命苦哇……你嫌弃我们……你拿镜子照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啪,”安一刀拍着桌子,怒目圆睁:“闭嘴!”
三个女儿受到惊吓,齐声大哭……
白凤英拉着三个孩子到了里屋。
安一刀见把孩子吓坏了,忙压下火气,叹息一声,想想白凤英也不容易,因为是个接生婆,三十多岁找不上男人,人们嫌她成天血红溅脸的晦气。自己也是成天血红溅脸的,两个人就凑合到一起了。虽说都是血红溅脸,可白凤英是迎接生命,而他是屠杀生命。唉,这辈子怎么干了这个行当?是命运,还是误入歧途?自己只是喜爱吃肉,做屠工常有肉吃,谁知嘴上享了福,命运上却有了周折。安一刀想着喝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嗵嗵嗵”的敲门声惊醒了安一刀夫妇,是城里有生产的女人,白凤英急匆匆走了。惊了觉的安一刀没了睡意,脑子空空的,他盯着窗外的星星,亮晶晶的星星放着寒光,如一把把利刃。安一刀觉得尿紧,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他急忙穿衣到了茅房,可如前几次一样,又尿不出来了。这次肚痛得厉害,憋得他坐卧不宁,屋里屋外乱转。直到白凤英神色憔悴地回来,安一刀还是撒不出尿来:“怎么今天空手回来了?”
白凤英叹了口气:“孩子死了!”
安一刀的头一下渗出了汗:“死了?怎么死的?”
“上吊!还是三吊!”
安一刀心里放松了,因为“上吊”是婴儿被脐带勒死的,婴儿的死亡与白凤英接生没关系。
“怀上孩子不操心,不知道摔了多少跤,脐带缠了三圈儿,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
安一刀听着,忽然心跳加快,体内如火焚,浑身冒汗。白凤英感觉不对劲:“你怎么了,又肚痛?”
安一刀话语颤抖:“肚痛过去了,现在是身上热啊!”
“快躺下,扎几针,是不是发霍乱子?”白凤英扶安一刀躺下,准备针灸。
安一刀躺下后,浑身松弛,心跳放缓了,体温也降下了,肚子一下不痛了,尿也不憋了。但衣裳湿透了,隐隐散发着尿味。
白凤英准备妥当了:“伸手!”
安一刀说:“等一下,我感觉好多了……”
“好多了?莫不是跟上游魂饿鬼了?”白凤英问道。
“哪有呢,你睡去吧,没事了!”安一刀底气十足地说。
白凤英吹灭油灯睡下。月光静静地照进窗口,照在安一刀脸上。夜静悄悄的,安一刀睡不着,他想不通为什么女人生孩子他急得肚痛?如果是顺产了,他的肚子也没事了,尿也撒出去了。今天孩子夭折了,他的肚子便痛得没完没了,尿也撒不出去,直到憋得从汗里渗出来。安一刀心神不安了,是什么原因呢?他睁着眼,一直想到天明……
从此,安一刀害怕听到白凤英出去接生。每当白凤英外出接生,安一刀就肚痛憋尿,稍有差错,便撒不出尿来,直到痛得浑身冒汗,才能逃过一劫。
无奈之下,安一刀想到了二府巷的大仙爷。大仙爷是威鲁城有名的掐指算命的人。每天只要看看大仙爷门外等的那些手拎礼品的老人和女人,就明白大仙爷有多少信仰者。安一刀看到人们满脸的焦虑与期待,便无心等待,扭头走了。世道乱,老百姓苦,歪门邪道盛行,安一刀边走边想。
安一刀郁闷地往家走,街上有许多搬家的牛车。人们听说又要打仗了,都急着到城外的农村避难。可农村又有土匪侵扰,天下没有平安的地方。在巷口,白凤英正带着三个女儿出门:“我正说找你去,方舟病得厉害,教堂的姊妹们要给方舟祷告,回来得迟一点……”
“病得厉害了?”
“怕是不行了……”白凤英眼睛里浸出了泪水。
“我也去看看方舟吧。”
白凤英急忙说:“不行,你不信基督,去了不合适!”
“我又不是看什么教,我是看方舟,这孩子太苦了,苦得让人心疼啊!”
白凤英还是不同意:“你去不行啊!”
安一刀明白了:“你嫌我是个杀猪的?”
白凤英不说话了。安一刀有些伤感地说:“唉,我这辈子完了!”
他忽然想做点什么事来赎罪。他想起了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安一刀来到城西北的三官庙,庙非常残破,世道乱根本没人修缮。三官庙是威鲁城人为去世的人告庙的地方。告庙告庙,就是告诉阴间,阳世又有人到阴间报到了。许多死无着落的人都停放在这里,安一刀想让他们入土为安。于是,他拉着自己家里的一辆木车,装上一具棺椁,拉到北门外的黄沙梁上,掘墓将棺椁葬于黄土之中。
安一刀彻底放下了屠刀,成了三官庙的守庙人。每天到庙里扫扫院,担几担水,偶然城里有丧事,他也帮着做些杂事。一日,庙里一下涌来很多外地人,衣着破旧,拖家带口往庙里挤。原来是日本人来了,人们都拼命往外跑。安一刀想起西街的五龙照相馆就是日本人开的,掌柜的叫武田一郎,个子矮小,长得敦敦实实,见人就低头哈腰,城里人叫他武大郎。他非常高兴,叫他一次武大郎,他就哈一次腰,满脸堆笑,“哈咦哈咦”地喊,一副卑微相。怎么,日本人会这么厉害?
没几日,日本人真进了威鲁城,个个五短身材,着黄军装,端着七尺长枪,满脸凶狠。明晃晃的刺刀闪着寒光。这是安一刀从门缝中看到的日本人。不一会儿,锣声就响起了,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喊道:“威鲁城的老百姓听着,都到十字街集中了,听皇军训话……”
威鲁城的老百姓也听话,都老老实实地聚集在了日本人端着枪、包围了的城中央十字街。当时天空睛朗,安一刀觉得这么好的天气不会有什么事情。然而,一个日本军官呜里哇啦喊了一阵,提着铜锣操外地口音的翻译,就随两个士兵押着一个中国人站到十字街心。翻译敲了一声铜锣说:“威鲁城的人听着,皇军从今天起接管了威鲁城,你们要听从皇军指挥,白天听候皇军调遣,黑夜不许在外活动,不许点灯,不听话者,就像这个人……”翻译一挥手,两个日本士兵就端起带刺刀的长枪,朝被绑的中国人刺去。
那个人长吼一声,声音如刺刀刺向了所有的人……人群涌动,安一刀闭上眼睛,随人群移动。虽然他见多了血腥场面,可那是牲畜,而这是人!
威鲁城一下子换了一个朝代,街上的人们行色匆匆,变得陌生了。城上的天空也静穆了,没了商贩的吆喝声,没了悠扬的驼铃声。被日本兵刺杀的那个人还躺在十字街心,被反绑着的手一直紧握着拳头,身体扭曲,让安一刀心里隐隐作痛。他觉得应该让这个人入土为安。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安一刀背着这个人,把他葬在了城外的黄沙凹。事后,安一刀还惊奇自己的力量和手段,是怎么躲过日本人的层层岗哨和陡峭的城墙的呢?直到日本人把他抓住,审问他这些细节,他还是稀里糊涂,说得前言不答后语。日本人就觉得这事他一个人干不了,必定有帮手和同谋。但用尽了审讯手段,安一刀还是不说。于是,日本人将安一刀推到院子一角的臭水坑。正是初冬,臭水坑结了一层薄冰,顿时浑身刺骨地疼痛。安一刀实在忍受不住,就往岸上爬。岸上的一个日本兵盯着安一刀看,架着双臂,一副傲慢相,见他爬上了岸边,就用一根长杆把他推下水去。一会儿,缓过劲来的安一刀继续往岸上爬,日本兵又用长杆把他推下水去,并且用劲把他推倒。倒在臭水坑中的安一刀,手碰到了一样硬东西,仔细摸索,竟是他熟悉的屠刀。安一刀脑子一下清醒了,如他过去杀猪时,浑身是劲。他长吸一口气,又向岸边爬去。这一次日本兵先没动手,静静等待着。正午时分,太阳正亮,光芒如刺。当安一刀再爬上来时,日本兵使足了劲,拿木杆向他冲来。这一次,安一刀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身子一侧,躲过杆头,一只手抓住木杆使劲一拉,日本兵就跟着木杆冲到安一刀面前,屠刀便插进日本兵的胸膛……
当天,威鲁城十字街中心,安一刀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中,双手紧握拳头,身体扭曲着……
几天后的深夜,安一刀的尸体消失在夜色中,黄沙凹又添了一座新坟。
官财头
——乱世奇人之二
官财头乃人名,绰号也。此名缘于他长了颗特殊的脑袋,前大后小,上大下小,形如棺材,故名棺材头。
威鲁城算命的大仙爷第一次见了棺材头之后,仔细端详罢他的头,只说了个“好”字,就再不做理论了。事后,人们问其缘由,大仙爷说:“人们说这孩子头像棺材,我看他将来或为官或为财,必有一筹。”此话传开,威鲁城的人们对棺材头就另眼相看了,也不叫棺材头了,改叫官财头。至于官财头呢,也从心里认可了这个名字,官财头从此就成了他正式的名字。
自从官财头在威鲁城叫开以后,城里人或敬或捧,宠爱有加。官财头承受了全城人的宠捧。然而,官财头不识惯,顺着水往下流,如没人修剪的树,蹿天乱长,陋习渐多,直到上房揭瓦,锅里拉屎,在威鲁城声名狼藉。最出名的事,就是黑夜把在威鲁城开照相馆的金捏影家的烟囱盖了,金捏影一家让炭烟闷了一黑夜,第二天人们发现喜欢早起的金捏影没起来,就敲门叫人。敲门人发现金家有事,撬开门,炭烟呛人,金家人都让炭烟闷倒了。多亏金家人命大,让风飕了一会儿,就又都活过来了。金捏影自称是朝鲜族人,在外谋生,势单力薄,虽知道是官财头干的,也咬咬牙忍了。
就是这许许多多的事情,助长了官财头的惰性。
到了二十岁,官财头眼睛开始有些异样,喜欢盯着女孩子看,终于有一天他开始行动了。
骑兵团赵司令有个女儿叫赵婷芳。十六岁的赵婷芳已经出落成婷婷玉立,人见人爱的姑娘了。这时候的赵婷芳在威鲁城的女子学校上学,成了威鲁城的一道风景,城里的人们都说这姑娘长得漂亮。
一天,官财头拦住了上学的赵婷芳:“咱们交个朋友吧。”
赵婷芳问道:“你是谁?”
“你连我都不知道?”
“走开,我要上学去!”
“你不和我说个一二三,你就别想走!”
“我爸是骑兵司令!”
“我是威鲁城二十团司令!”
“什么二十团?”
“威鲁城二十岁的人都归我管!”
赵婷芳笑了:“那我也是你的兵了?”
“可不,你是我的压寨夫人!”
赵婷芳生气了:“你是个痞子!”
“你不要生气,你先上学堂去吧!”
这是官财头与赵婷芳的第一次见面。
从此,官财头经常在赵婷芳上学的路上等她,说上几句话,或送上胭脂之类的小东西。
时间久了,就传到赵司令耳朵里,赵司令一介武夫,非常生气,一个街上的混混竟敢撩戏老子的千金,便派手下教训了一顿官财头,把官财头打得头破血流。性格嚣张的官财头,表现得非常有韧性,任那些大兵拳脚相加,也没有任何反抗之举。事后,威鲁城的小兄弟们叫嚣要复仇,官财头却一笑了之。
第二天,官财头鼻青脸肿地见到赵婷芳,把赵婷芳心疼得泪珠直在眼里打转。
官财头却毫不在乎,一副英雄气概的样子:“为了你,这点苦我能吃下去!”
这句话彻底俘虏了赵婷芳的心:“你要这样把我当回事,我就跟定你了!”
几天后,赵婷芳跟着官财头私奔了。赵司令派了三队快马,追寻赵婷芳,但没有任何结果。赵司令在这件事上丢尽了人,一个名门的黄花姑娘,跟上一个名声狼藉的混混私奔了,赵司令气得又是吐血,又是啪啪吐痰。
官财头就这样失踪了,消失得无踪无影,消失得稀奇古怪。以至于威鲁城的人都感到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围观热闹的机会,没有了鸡飞狗叫的喧闹,直到日本人进了威鲁城,人们才惊奇地发现官财头回来了。
赵司令跑了,官财头回来了。赵司令逃出了赵宅,官财头搬进了赵宅。威鲁城的人还是老样儿,但统治者换了,吃香的喝辣的人换了。
多年后,威鲁城里的人们才知道,官财头领着赵婷芳跑到了北平,在北平从洋烟馆的跑腿儿做起,做到了“看场子”,渐渐又贩卖开洋烟,成为一名有名的洋烟贩子。日本人占领北平后,通过谍报人员找到官财头,携其回到了威鲁城。
官财头是以保安队长的官职回到威鲁城的,一同回来的还有他老婆,也就是赵司令的女儿赵婷芳。
威鲁城的人们见到官财头时,全城人都笑了。原来形如棺材的官财头,戴上保安队的大檐帽,有棱有角的,更像是棺材了。
见到人们别有意味的笑,官财头似乎并不反感,依然沉稳如山,有时还主动和人们聊上几句,说说威鲁城过去的事。是没有看出人们的嘲笑,还是他别有用心?还是在外闯荡几年,练就了成熟的心态?人们以忐忑的心情等待着,等待官财头出什么花样。
事情的变故是一次官财头和日本人出城扫荡,伤了一条腿,成了拐腿。据说,官财头领着保安队走在日本人前面,忽然冲杀来一队骑兵,对着官财头的队伍一阵乱射,把官财头的队伍打得措手不及。这场冲突保安队伤残不少,官财头损失了一条腿,而日本人毫发未损。官财头后悔不迭,直跺那只好脚,想想从北平跟着日本人回来,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倒赔了一条腿。
威鲁城的人调侃道,日本人叫鬼子腿不拐,官财头升了官却瘸了条腿。
官财头只剩下一条好腿后,日本人也不能让他打仗了,就让他到管烟所管了鸦片。这也正是官财头的老本行。这里特别要交代的是,官财头在北平烟行练就一套特殊本事,鼻子灵,眼力准。他能用鼻子闻出鸦片的成色,并能准确地估出分量,十之不离八九。
官财头在保安队旁边的院子为日本人征收鸦片,熬制鸦片。他自己在城里繁华的楼梯坊开了处烟馆,取名逍遥楼。
逍遥楼是座二层木结构楼房,一层为一个大厅,八仙桌摆得满当当,是零散烟民吸洋烟喝茶水的地方。中间是一个天井,抬眼望去,二层一圈包厢,门面都很精制,让人想入非非。包厢里面,木制铺炕,围栏走边,雕花炕桌,白银烟壶,锦的段的铺陈。许多人见了这陈设,都说是个睡觉的好地方。也的确是个好地方,直到今天,威鲁城还有一句名言:逍遥楼里有“三费”,费钱费人费褥子。
官财头开洋烟馆,有在北平城摸爬滚打的经验,可谓是轻车熟路,水到渠成的生意。再加上威鲁城自古以来就是各路商贾或中转或歇脚的地方,逍遥楼的生意很快就火了起来。
逍遥楼每天车水马龙,吸引了威鲁人的眼球,也引来了各色人物。首先是赵婷芳的一个叫赵虎的堂兄,该堂兄从小父母双亡,寄生在赵司令家中。赵司令的太太、姨太太都看不上这个赵虎,赵虎生活得非常窝囊。赵婷芳同情这个堂兄,时时给他些关照。今天来投奔官财头,还是冲着赵婷芳来的。官财头觉得赵家人来求他,是件很光彩的事,便毫不犹豫地收留了赵虎。
没几日,照相馆的金捏影领着一个小伙子也来找官财头:“官掌柜,老家来了个亲戚投奔我来了,我的照相馆现在是勉强维持,多一张嘴实在难承受啊,求官掌柜给他一口饭吃,给他一条活路吧。”
官财头想到年轻时盖烟囱的事,心里有点愧疚,就爽快地点头答应:“叫什么名儿?”
“您叫我小金子好了!”
小金子很机灵,随口就和官财头答上话了:“您以后有什么事就吩咐我,做错了您就指点我,财掌柜!”
小金子有意把官财头称为“财掌柜”,这个名称既好听又受用。
官财头听得高兴:“你是哪的人?”
金捏影忙替回答:“我们那儿的,吉林!”
“我听他说话怎么这么费劲?”
“他也是朝鲜族人啊,刚到咱们威鲁城,没学会咱们这儿的话。”
“他挺像日本人?”
“谢谢财掌柜的抬举,我要是皇军就不用吃这苦了。”小金子小心翼翼地看着官财头的眼睛。
官财头看到了小金子耐人寻味的眼神:“你先干干看吧,这里的事情得慢慢学。”
小金子很聪明,学什么都快,从待客到点烟,从送茶到结账,样样得心应手。连常来抽烟的保安队秦队长,都说官财头招了个好帮手。秦队长河北人,原来是官财头的副官,官财头受伤瘸了腿之后,他就升任保安队长了。两个人都是战场上爬出来的,后来官财头又把官位让给了他,秦队长对官财头心存感激,关系便非同一般了。秦队长经常来逍遥楼蹓蹓,一是关照关照生意,二是给逍遥楼撑个面子。
近来,秦队长常与一个姓常的皮毛贩子来逍遥楼喝茶抽烟。常皮毛的皮毛生意做得大,在张家口、北平、内蒙都有商铺,经常路过威鲁城,找秦队长见个面,吃顿饭,喝壶茶。有时,给秦队长带些外地的新鲜东西。有一次,常皮毛给官财头带来点洋烟。
官财头看过常皮毛带来的洋烟,觉得这烟成色好,又问明产地价格,知道这烟赚头大。官财头就和常皮毛订了口头协议,常皮毛的洋烟有多少要多少。
常皮毛财力大,胆量更大,没几天,他就给官财头送来两骆驼四箱子的洋烟。满满四大箱子洋烟,让官财头又是高兴又是忧,高兴的是这可是滚滚钱财啊,忧的是怎么把它变成银两呢?官财头想,以现有的烟客要吸完这些烟,还得些时日,只有增加烟民,才能快速变现。
可怎么增加烟民呢?这个要紧的事,一直困扰着官财头,他步出逍遥楼,看到了街道对面的蒋客栈。
因为客栈没有客人,蒋掌柜坐在门外,忧郁地抽着旱烟。
蒋掌柜的烟袋非常好看,是用山羊腿骨做的,羊毛发着光,紧紧贴在皮骨上。但那光死板,如僵硬的羊腿骨,没有一点活力。
看着死沉沉的蒋客栈,官财头有了主意。
隔日,保安队的秦队长就来到蒋客栈:“蒋掌柜,你这店开得冷汤寡水的,还尽管开球啥店!”
蒋掌柜恭恭敬敬地说:“周围都在打仗,没人敢做生意了……”
“胡说!你这话让皇军听到,可是杀头的啊!不行的话,你回村种地去吧,省得开店惹事……”
没几天,蒋掌柜的客栈就成了官财头的赌场。
又过了些时日,官财头又用诸多办法把逍遥楼附近的多家店铺据为己有,楼梯坊便成了官财头的天下,赌场、烟馆、妓院、饭店应有尽有,成了威鲁城最繁华的地方。城里的人们说,这里是带着一腰包钱进去,光着屁股出来;红光满面进去,灰头土脸出来;虎背熊腰进去,瘦骨嶙嶙出来。
这些话也传到官财头的耳朵里了,他嗤之以鼻,每天牛气十足地游荡在火热的赌场中。他想,人有时运旺,神鬼不敢撞。
但几天后发生的两件事,让官财头困惑不已了。首先是威鲁城里的英国传教士马神父来逍遥楼传教了。马神父身穿长袍,站在逍遥楼门前,口中念念有词:“阿门!神说了,这样是有罪的,要受惩罚的……”
逍遥楼马上聚集了很多人,看马神父传教。
官财头让赵虎找来秦队长的保安队把马神父撵走了。第二天,马神父又来到逍遥楼门前,还是那几句话:“阿门!神说了,这样是有罪的,要受惩罚的……”
保安队又把马神父撵走了。
可马神父非常执着,头一天给撵走了,第二天又照样来了。官财头知道马神父是英国人,日本人也拿他没办法,自己也不想与这个英国人较真,就让秦队长派了两个人,把守在教堂门口,不让马神父出教堂门。
官财头刚把马神父这头的事安排好,逍遥楼却又出了一件事。这天早晨,官财头还在睡梦中,小金子就来敲门:“财掌柜,快起吧,逍遥楼有事了!”
官财头跟着小金子来到逍遥楼前,只见门前立着一把扫帚,扫帚上挂着一个纸条:“毒赌祸害人,勿发不义财!”
官财头明白,按威鲁城风俗,门前立扫帚是最狠的诅咒。他赶紧让小金子把扫帚火烧掉,把晦气的诅咒烧得一干二净。
官财头从此感到了危机,感到了威鲁城人对他的仇视,同时也感觉到了逍遥楼内部的复杂。尤其是小金子,他觉得不是个简单人物。小金子名如其人,长得短小精干,聪明勤快,是逍遥楼最忙碌的人。官财头见他整日奔忙,总能感觉出他游离于客人之间的神秘目光,或在暗暗观察客人,或在独自思量。官财头心里常犯疑,这小子究竟是个什么人?
还有常皮毛,这个人也有些神秘,从他稍纵即逝的眼神中,就能看出那种游走于江湖的豪爽,以及他言谈中流露出的见识。
被忧虑困扰的官财头,感到危机笼罩着逍遥楼,正在一步步向他逼近。事情终于爆发了。一天早晨,还在睡梦中的官财头,又听到了小金子的叫声:“财掌柜,快起吧,有事了!”
官财头急忙起来,跟着小金子到了逍遥楼,好端端的秦队长死了,死在了逍遥楼的包厢里。
官财头问:“昨天晚上他和谁在一起?”
“和常皮毛啊,您不是也和他们在一起喝茶吗?”
“常皮毛人呢?”
“不知道!”
秦队长死了,死得不明不白,常皮毛也失踪了,失踪得黄鹤杳无。
同日,官财头被日本人带走了。这次他不是座上客,而是阶下囚。
不知何时,赵婷芳和赵虎也走了,小金子也不知去向。
威鲁城的人们传说,小金子是日本人的间谍,是受北平日本间谍机关的派遣,来威鲁城侦察军情的。常皮毛是西山游击队的侦察员,也是来威鲁城收集情报的。至于那赵虎,说是赵司令派来的说客,说服赵婷芳回家去。秦队长的死是游击队干的,是抗日锄奸行动,为的是一箭双雕,把官财头也除掉。不过传说归传说,反正这些人都失踪了,留下空荡荡的逍遥楼,还有无人出入的赌场,楼梯坊一下子萧条了。
大概是冬天吧,官财头被日本人吊死在威鲁城的城门上,寒冷让官财头的尸体冻得硬邦邦的,朔风呼号的时候,悬晃在城门头上,让人看着毛骨悚然。
后来,马神父找日本人求情,才把官财头埋葬了。埋葬时没有棺材,只用一块草席包裹了,安葬在黄沙凹。
事后,威鲁城的人说大仙爷算得不准,而大仙爷却说:“有官有财,荣华富贵;无德官财,早进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