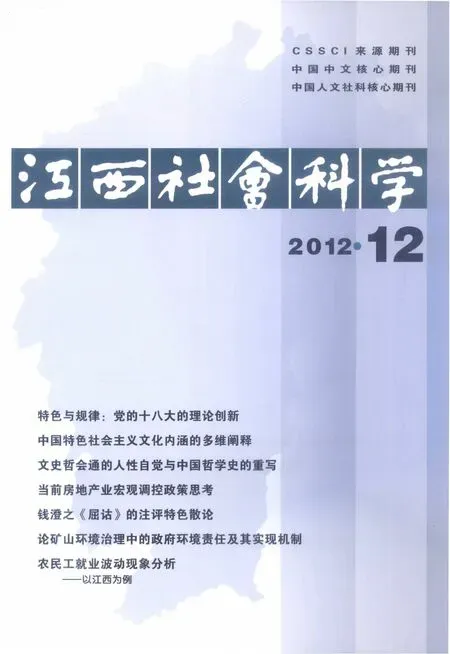从陈寿与傅玄的评语透视曹魏的政治与思想——以魏文帝曹丕为中心
■祝 捷
一、傅玄上疏与陈寿“评曰”语境中的曹魏政局
在三国时代的历史洪流中,曹魏政权率先完成了北方中国的统一。曹魏政权的兴起、发展与嬗替,除了战场中的成败之外,政权内部的政治与思想发展,亦为其过程中不可或缺之历史境遇。对于这一重要发展历程,历经曹魏与西晋两朝的文臣与历史学家傅玄在其“上疏”中有清晰的认识:
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1](P1317)
傅玄将曹魏政权清晰地划分为魏武帝曹操时期、魏文帝曹丕时期与曹丕之后“亡秦之病复发”时期。傅玄上疏对曹魏政权中的三段重要时期的描述,勾勒出了曹魏政权内部的政治格局与政治思想发展,而且表明了政治格局与政治思想的互动影响。
作为政治家与学者,傅玄的认识是精辟的。但在精辟之余,话语之间留存的具体情节与缘由,却又值得读者去深查。“上疏”的第一时期与第三时期分别是曹魏的“兴”与“衰”之期。但是从“上疏”中的“近”与“后”这两个时间副词来看,傅玄认为这“衰”之缘由亦蕴含于魏武、魏文这两个曹魏政权的兴起与发展期。探讨曹魏衰竭与晋朝兴替之由,亦不得不从此前两个时期来透视。“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的话语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魏武帝曹操在曹魏政权初兴之时行“权法之术”,而“天下”臣子遵从的是“刑名”之学,执政者曹操与天下文臣的重要使命都寓存于建设许昌政权之中,曹操以“法术”来掌控天下臣民,天下臣民则通过“刑名”学术来为许昌政权建立制度与规范。
与曹魏初兴之时的“魏武好法术,天下贵刑名”相对立的是,在曹魏政权第三阶段中天下臣民反“刑名”之道而行。“虚无放诞之论”是与“刑名”思想相对立的、不遵守礼节与规矩的言论,也正是“天下无复清议”:朝廷中不再有心系曹魏政权安危的忠心臣子。“虚无放诞之论”与“无复清议”都是针对曹魏政权中的政治思想而言。
曹魏政权的“兴”与“衰”一定有其前因后果。曹丕执政时期的“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在傅玄“上疏”中是最为重要的中间环节。但是傅玄委婉的文字,却给我们理解这一历史线索带来了不少困难:“慕通达”与“贱守节”的用语,看似是形容个人行为,但却深含着政治作为与政治思想。因为在傅玄“上疏”的三个阶段中,魏武与“其他”这两个阶段都渗透着政治思想与政治作为之间的互动与影响。从此看来,理解曹丕“慕通达”与其执政时期的“天下贱守节”之间的政治作为与政治思想,是真正理解曹魏政权兴衰之匙。
正式理解曹丕的政治作为与思想状况,首要的材料是《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按照陈寿撰写《三国志》的手笔,对于其间人物的最为适当的评价,莫过于篇章中的“评曰”。《文帝纪》:
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这段的后半句才是“评曰”的正题,即陈寿认为,曹丕不够“旷大”,不能“公平”,也难以做到“迈志存道”、“克广德心”,这是他为政所不足。
不过问题在于,《文帝纪》“评曰”中的用语,与傅玄“上疏”中的用语,在字面上似乎相互矛盾。傅玄认为曹丕过于“通达”,陈寿认为曹丕不够“旷大”,但曹丕身上的这两种特征都导致了不好的政治结果。陈寿的评价比较委婉,即曹丕不够“迈志存道,克广德心”,亦即“德心”没有能够推广,这与傅玄评价中的“天下贱守节”则为同义,即天下士人不能践履德行(傅玄“贱守节”),不能施广“德心”(陈寿“克广德心”)。
傅玄上疏时间是在晋武帝司马炎初即位时,即大约公元265年。而陈寿写《三国志》大约在280年之后,即晋统一三国后的一段时间。曹丕226年去世。两则材料的撰写,相隔时间不过20年左右,都距离曹丕去世、曹魏覆灭的年月不久。他们应当都可以对曹丕的为政,进行清晰的判断。两则材料又都要顾及晋朝皇室的立场,因此这两则材料在字面上的矛盾就显得难以理解了。但是既然两则材料的结果都是相近的,那么两者对于产生这一政治结果的原因也很可能是了解和一致的,两则材料中的不够“旷大”与过于“通达”就很可能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抑或是一个人(曹丕)的一个问题(思想、性格或者政治策略)两个方面。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需要建立在材料以及事迹的积累之上,我们还是先从陈寿评述所由的《文帝纪》中的具体事迹开始论述。
二、魏文帝为政与《文帝纪》中的“灾异”书写
陈寿对曹丕的“评曰”中有“若加以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的评价,但在《文帝纪》中却鲜有他不“旷大”的直接记载。因为按照正史的书法,不光彩之事则不便直接记载在传记中。而关于帝王的“纪”则尤其如此。但是《文帝纪》中仍然间接地记载了天下臣民对于曹丕的不满。这些不满的情绪主要体现在《文帝纪》灾异中。
正史中的“灾异”记载往往具有特殊的历史记载功能:臣子上报灾异的过程往往也在向帝王传递警诫之信息。臣子上报灾异的政治功能,陈启云在引用毕汉思研究时论述道:
关于儒生官吏对王莽的态度,毕汉思做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分析,他在前引《前汉书所记的灾异试释》的研究,认为汉代的祥瑞灾异,多由地方上报,对朝廷(天子及大臣)有警戒的用意和功能;如果地方人士赞同朝廷的行事,则多报祥瑞,反之则多报灾异。……毕汉思把前汉高、惠、吕氏、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王莽、光武朝的灾异纪录,做成一统计表,显示灾异的次数在成帝哀帝时最高,王莽末年次高,惠帝吕后士气为第三高峰。亦即儒士们对西汉末叶成哀二帝之不满,乃王莽成功建国的明显因素。[3](P37)
“灾异”上报往往并非一定是当时自然现象的突变,因为“灾异”自然现象的发生,在年份上应当是平均的。某一年份的“灾异”突发正表明了臣民对于朝政的意见。
然而,正是在魏文帝曹丕一朝中,“灾异”尤其多见,这使得《文帝纪》渗透着浓厚的阴郁色彩。尤其重要的是,“灾异”往往发生在《文帝纪》中臣子死亡的当月。《文帝纪》中一共有五次臣子死亡 (不包括曹丕之子东武阳王鉴的死亡)。这五次臣子的死亡,“夏侯惇薨”、“夫人甄氏卒”、“大司马曹仁薨”、“任城王彰薨于京都”、“太尉贾诩薨”,均伴有灾异:
(延康元年)夏四月丁巳,饶安县言白雉见。庚午,大将军夏侯惇薨。[2](P59)
(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祀五岳四渎,咸秩群祀。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2](P78)
(黄初四年)三月丙申,行自宛还洛阳宫。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丁未,大司马曹仁薨。是月大疫。[2](P82)
(黄初四年)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贾诩薨。太白昼见。日月大雨,伊、洛溢流,杀人民,坏庐宅。[2](P83)
夏侯惇 (“白雉见”)、夫人甄氏 (“日有食之”)、大司马曹仁(“月犯心中央大星”)、任城王彰与太尉贾诩(“日月大雨,伊、洛溢流”)死亡的当月均伴以灾异,明显地表明了臣民对曹丕为政的不满。
臣民为何将五人之死与对曹丕的不满结合在一起?因为此五人之死并非自然死亡,而正好与曹丕的为政相关。
对于夏侯惇之死,裴松之对其后曹丕的“发丧”行为表示了不满:“《魏书》曰:王素服幸邺东城门发哀。孙盛曰:在礼,天子哭同姓于宗庙门之外。哭于城门,失其所也。”曹丕对于宗族功臣夏侯惇的“丧礼”却表现出“非礼”的态度。实际上,曹丕对于夏侯惇之死应负有责任。因为“大将军”之职为最高军事统帅,夏侯惇担任大将军之职后一个月左右去世,曹丕是在夏侯惇不堪其任的状态下任命其为大将军的。
对于“夫人甄氏卒”,据《三国志·魏书·后妃·文昭甄皇后传》:“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践阼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甄氏因为失宠有怨言,被曹丕赐死。
对于任城王曹彰之死,《三国志·曹彰传》裴注引《魏氏春秋》:“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彰忿怒暴薨。”《世说新语·尤悔》:“文帝忌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加之曹植《赠白马王彪》,这几则材料共同说明:曹彰为曹丕所故意杀害。
曹丕也似意识到自己的作为有问题,在黄初二年六月丁卯,夫人甄氏卒后出现日食灾异,他下诏道:“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但“灾异”发生后往往是地方报告中央,或者下级报告上级,中央和上级如何理解这些“灾异”,则需据实际情况而定。这个诏书在《文帝纪》中记载的意义,还应当联系下诏前的文字:“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而当时的太尉正是贾诩。“有司”敢于奏免位居三公之高的太尉贾诩,也表明了是时贾诩的失势,抑或正是在曹丕默许之下的上奏。因此,曹丕这份诏书的意义,也正在于:其一,承认自己的不足;其二,转移对自己的“谴告”;其三,警告贾诩。曹丕为何要警告贾诩,原因是贾诩在后来对曹丕有不同的意见。考诸《魏志·贾诩传》,曹丕曾问策于贾诩,如果要统一天下,“吴、蜀何为先”。贾诩认为,“建本者尚德化”,“若绥之以文德而伺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当今宜先文后武”。可是“文帝不纳。后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也就是讨伐孙权大败而归。《贾诩传》中紧接着的记载就是“诩年七十七,薨”。也就是说,在“文帝不纳”后的大约三年多时间里,《贾诩传》里已经没有贾诩什么事了。“后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的记载在这里具有两方面意义:第一,贾诩的见识正确,也就是这句话与这句话之前的“贾诩对曰”的意思相连;第二,江陵之役的失败与贾诩之死有关。如果是第二种可能,那么就可以将“后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的前后表述都连接起来,即:贾诩正确→文帝失败→文帝迁怒于贾诩。第二种可能,颇类似于袁绍失败迁怒于田丰。陈寿评袁绍“外宽内忌”与“尝思文帝之宽仁玄默”(外宽)、“若加以旷大之度”(内忌)极为相近。
这场江陵之役还直接导致了上面5人中曹仁的死亡。贾诩对问题的判断是正确的,曹丕对政权的建设还未稳固,对吴蜀作战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贸然进攻,必然会失败。然而曹丕却好大喜功:“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文帝纪》中没有直接记载曹仁是死于该战,而是记载在《蒋济传》中:“仁不从(蒋济),果败。仁薨,复以济为东中郎将,代领其兵。诏曰:‘卿兼资文武,志节慷慨,常有超江湖吞吴会之志,故复授将率之任。’”从“代领其兵”来看,曹仁是死于战争中,而蒋济带领其兵权。曹仁之死,可能是操劳,可能是受伤,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从陈寿的记载角度来看,特别是与“灾异”相结合的记载来看,曹仁之死与曹丕的冒进决策不无关系。
三、曹丕的政治性格
从陈寿的记载来看,夏侯惇、夫人甄氏、曹仁、曹彰、贾诩这几人的死,都是与曹丕有关的,所以均伴随着当月的“灾异”记载。并且陈寿也大概基于此认为曹丕不够“旷大”。曹丕的不够“旷大”,或者通俗来说,比较“小气”,还表现在如下一则字面简略而内涵颇丰的材料。《三国志·曹洪传》:
始,洪家富而性吝啬,文帝少时假求不称,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狱当死。群臣并救莫能得。卞太后谓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废后矣。”於是泣涕屡请,乃得免官削爵土。洪先帝功臣,时人多为觖望。明帝即位,拜后将军,更封乐城侯,邑千户,位特进,复拜骠骑将军。[2](P278)
曹洪家富,曹丕在少年时向他借钱财而不得,于是常常记恨在心,找借口治曹洪死罪。虽经卞太后求情得以赦免,但也免除了他的官职。根据裴注记载,还没收了他的家财。曹丕以此报复,而丝毫不顾曹洪当初舍身救曹操之功,表现出他心胸的狭窄。除此以外,上述材料中卞太后的话语表明曹丕的指令还受到了他的皇后郭氏的影响。《三国志·文德郭皇后传》记载“甄后之死,由后之宠也”,“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曹丕能当上太子,郭氏也有献策之功。郭氏献策除曹洪,大概也有助曹丕剪除宗族势力之目的。与曹操政由己出的为政策略不同,曹丕的政令,受左右影响颇重,表现出他任人唯亲、任政唯亲的一面。
曹丕的任人唯亲,还表现为他对贾诩的任命。《三国志·贾诩传》裴注引《荀勖别传》:“晋司徒阙,武帝问其人于勖。答曰:‘三公具瞻所归,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贾诩为三公,孙权笑之。’”孙权笑曹丕任用威望不足的贾诩为三公之一。曹丕任用他,更多地出于他与自己的亲善。裴松之在《三国志·贾诩传》注中对贾诩还有这样的评价:“且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贾诩的为人远不如荀攸,裴松之认为他不配与荀攸合传。这也说明了贾诩在政权内的威望并不足,能担任太尉之职,仅仅是因为曹丕的任人唯亲。而且,在贾诩不赞成曹丕征东吴,并建议曹丕广播德政后,曹丕很可能也不再多听政于贾诩。
曹丕的任人、任政唯亲,还表现在对夏侯楙和夏侯尚的任用上。夏侯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三国志·夏侯楙传》),仅因年少时与曹王亲密,就被授以重任。夏侯尚因与曹丕亲善而结为“布衣之交”(《三国志·夏侯尚传》),除被授予重任外,还特见宠待。曹丕曾赐夏侯尚手诏云:“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作威作福,杀人活人。”被蒋济称为“见亡国之语”(《三国志·蒋济传》)。曹丕对夏侯楙不因材授职,对夏侯尚以“作威作福,杀人活人”相纵容,都表现了他的“任人唯亲”、“任政唯亲”。
任人唯亲,则难以做到公平地对待所有臣子,加上曹丕因为个人小恩怨或者小脾气而对周围人的生杀予夺,无怪陈寿评曰:“若加以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这四句评语分别点出了曹丕为政上的四个缺点:心胸狭隘,任人唯亲,志向不广,德心不足。
四、傅玄语境中的曹丕与曹魏政治
解读了陈寿的评语后,了解了曹丕的为政后,我们还需要解读傅玄的评语:“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按此句的字面含义,“魏文慕通达”,就不应该是心胸狭隘和任人唯亲。为了进一步解读这句话,我们还是需要结合这段话的上下文和历史背景来理解。
傅玄的这则奏疏出自于《晋书·傅玄传》:
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泳叹而已,又将奚言!锥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悟,臣是以扰敢有言。[1](P1317-1318)
傅玄的这则奏疏是呈递给晋武帝司马炎的。可能鲜为人知的是,这则材料引用了两个重要典故。引出这两则材料,最为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义节”和“守节”这两个用词。这两个用词同时见于《国语·周语》: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内史兴归,以告王曰:“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忠分则均,仁行则报,信守则固,义节则度。分均无怨,行报无匮,守固不偷,节度不携。若民不怨而财不匮,令不偷而动不携,其何事不济!中能应外,忠也;施三服义,仁也;守节不淫,信也,行礼不疚,义也。臣入晋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晋侯其能礼矣,王其善之!’树于有礼,艾人必丰。”王从之,使于晋者,道相逮也。[4](P47-48)
在《国语》的这则材料中,实际表达了一些和傅玄相近的思想,认为礼义是施行德政的根本。这段话是内史兴对周襄王所说的话,话语中称赞了当时的晋文公。傅玄引用这则材料,还有一个隐晦地引典奉上的作用。因为这段话称赞的是晋文公,而傅玄呈递的是晋朝的晋武帝司马炎。“晋文公”的德政与“其君必霸”,也是对司马炎与“晋文公”一字之差的父皇“晋文帝”司马昭的奉扬。
通过《国语》的这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义所以节也”,“义节则度”,“节度不携”。“义”心可以使得臣民行为有所节制(“节”),使得政令法制统一(“度”),臣民不叛(“不携”,“携”字:《国语·周语上》“其刑矫诬,百姓携贰”)。因此,“义节”的意思就是:臣民通过节制自身欲望而达到的对王者的忠心。
“守节不淫,信也”,因此,“守节”一词的含义就是“信”,就是对君主的信用。而“守节”一词正出现于“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一句中。这一句中的“通达”、“天下”、“守节”三个用词同时出现于另一则材料,这是非常罕见的,也足证傅玄此句言论对另一则典故的引用。这则材料出现于《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掌节》:
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以英荡辅之,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於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5](P222-223)
这段话中同出现了“通达”、“天下”、“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即形象意义上的“守节”)。《国语》上说“守节不淫,信也”,而《周礼》中的这段话指明“节”是通关用的文书,其作用也是“信”。从《周礼》中的这则材料来看,“通达于天下”实际上是“亲身赶赴天下”的意思。若要“亲身赶赴天下”则必须带有“节”这一通关文书,以传递信用。因此,如果将“通达”、“天下”、“守节”在《周礼》中的形象意义转化为政治中的抽象意义的话,就可以理解为,“通达”是“亲力传达”,“天下”是臣民,“守节”是保守信用、忠心的意思。如此,再来理解“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就可以清楚了。“慕通达”实际上是指曹丕亲身传达政令,即“任人唯亲”及“任政唯亲”。这与陈寿对曹丕“若加以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的意思实际上是一致的。而傅玄的这句话是说,魏文帝曹丕为政,崇尚“任政唯亲”,因而臣民轻视对君主的信用和忠心。
那么,傅玄为什么说“天下贱守节”呢?原话是这样的语境:“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这段话中,傅玄是说,先王治理天下,通过道德礼仪教化,增长臣民的忠义,如此,君主施行道德教化,臣民奉行清明的政议。君主与臣民相互协作,每人都心怀忠心。秦朝丧失了先王的德政,而施行法术之治,使得忠义之心丧失。魏武帝曹操就是崇奉法术之治,使得天下臣民崇奉刑名之理;魏文帝曹丕崇奉“任政唯亲”。而由于曹操的法术之治也带来忠节的丧失,臣民也如秦朝那样轻视忠心。曹丕为政,正是由于任用了这些无视忠心的臣子,朝廷的法度不能再维持,而虚无放诞之论(即轻视政治道德与忠义的言论)充满朝野,天下不再有清明的政议,亡秦的弊病再次复发。傅玄的这段议论,实际上也是他眼中的一段曹魏政权的政治与思想流变史,他所看到的曹魏的弊端是切实的。按他的意思,曹操引入了各方士人,治御的方式却是法制和权术,而缺少儒家的道德礼仪政教,使得臣子在对君主的忠心上出了问题。但这里对曹丕的为政之失有夸大之嫌,曹操政权的建立是在战争时期,以法术为治政之先是合理的。问题可能在于,他“任人唯才”的战争时期招揽人才政策,使得他的政权内不同背景、不同利益、不同思想状况的人员纷繁复杂,让他们合作共事是不容易的,其后曹丕统治起来自然也更加困难。
[1](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陈启云.代序:我如何研究汉儒与王莽,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黄永堂.国语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5]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