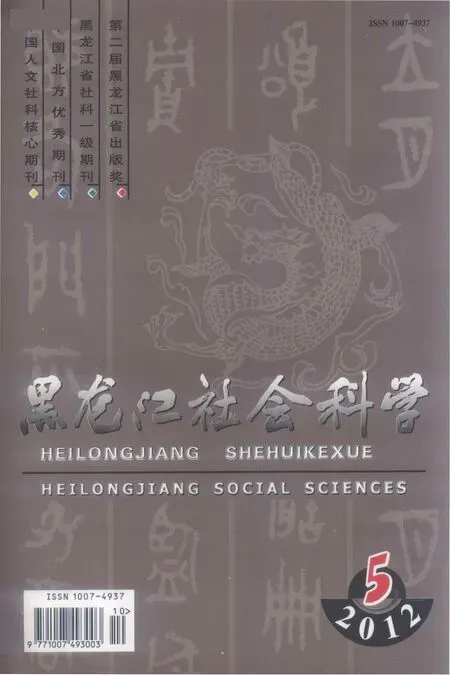齐梁士人的两大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
刘怀荣
(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翻检齐、梁时代的士人传记,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关于士人“博学多通”、“博学多闻”、“博学善属文”之类的记载特别多。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是从齐梁时代才开始的,至少在《后汉书》、《晋书》等史书的人物传里,就已有不少类似的例证。而且到了南朝刘宋时代,士族大家以博学能文相矜尚已经蔚然成风。文化上处于劣势的刘宋皇室,也迫切地希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他们多通过与士族联姻,或组织文士开展各种文学、学术活动来实现这一目的。这种以博学为尚的风气,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元嘉诗风[1]。不过,就齐梁时代士人的趣尚而言,“博学”、“能文”和“以气类相推毂”两点,仍然值得我们关注。
一
盛于宋代的士族博学之风,到了齐梁时期,更为普遍化。特别是在梁代,“博学”、“能文”形成了上至皇室,下及寒门士子,具有全社会性的士人群体特征。以“竟陵八友”及“西邸学士”为代表的一批士人,在其中起了引领风气、推波助澜的作用。翻检史书,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士人的代表,几乎都具备“博学”、“能文”的特点。如王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2]817、谢朓“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2]233、沈约“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能属文”[3]233、范云“少机警,有识具,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稿,时人每疑其宿构”[3]229、任昉“幼而好学,早知名……昉坟籍无所不见”[3]251。他们“博学”、“能文”的特点几乎是天然地相似。
而其他的西邸学士,在这一点上,与“竟陵八友”几无二致。范岫“博涉多通,尤悉魏晋以来吉凶故事。约常称曰:‘范公好事该博,胡广无以加。’南乡范云谓人曰:‘诸君进止威仪,当问范长头。’以岫多识前代旧事也”[3]254、王僧孺“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3]391、柳恽“少有志行,好学,善尺牍”[3]469、谢徵“幼聪慧……既长,美风采,好学善属文”[3]331。诸如此类,比比皆见。
与好学、博学相对应的,是他们对藏书的爱好。沈约、任昉、王僧孺、张缅都是当时一流的大藏书家。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3]718、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3]242、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3]242、张缅“性爱坟籍,聚书至万余卷”[3]474。著述丰富是他们博学的另一标志,据陈尚君先生的不完全统计,《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图书5 242部,其中唐以前人所著为2 918部,唐人所著为2 324部。而唐以前的著作,绝大部分出自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之手[4]。其中,齐梁时代的著述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文人好学深思、勤于著述的风气。这也是各种文献类和文学史著作中常常提到的,我们在此不拟细述。
刘跃进先生曾指出:“王、谢后人在刘宋以后转向文史领域,在政治、军事上的影响越来越小。其它如济阳江氏、汝南周氏等,晋代即属高门甲族,颇有政治势力,但在宋齐以后,其活动也更多地趋向文史领域。”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在齐梁之际,那些勇冠三军的武将后代竟也紧步王、谢后尘,相继加入到文人的行列。”[5]这意味着刘宋以来社会价值趋向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在这一持续的文化发展大趋势之下,刘宋以来的皇族在文化领域获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如果说刘宋皇族在文化上还明显的底气不足,对士族的文化修养充满了欣羡之情,那么,经过齐代的努力,到了梁代皇族,这种明显的差距已经不存在了。皇族在文化上的优势终于在梁代得以确立,以梁武帝为代表的兰陵萧氏家族,在博学能文方面可谓人才辈出,令人叹为观止。《梁书·武帝纪》说萧衍“博学多通”[3]492,在经学、礼学、史学、文学、佛学等多方面均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并都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著作。他还喜围棋,通阴阳卜筮,擅草隶尺牍、骑射弓马[3]2。他的兄弟子侄也大多具有博学能文的特点。
尤其是梁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即学术界所谓的“四萧”,无论是在学术、文化修养,还是在文学创作上,在当时都处于领袖群伦的地位。这固然与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分不开,但客观地讲,在学养和才能方面,他们也的确是当之无愧的。因此,梁代皇室在与文士的文化交流和对决中,已经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由此可见博学能文在上层普及化之一斑。
与以往文化为士族垄断相比,这一时期寒门士子以博学能文著称者也更为普遍化。仅在《梁书》的《儒林传》和《文学传》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大批博学能文的寒士:
司马筠,字贞素,河内温人,晋骠骑将军谯烈王承七世孙。祖亮,宋司空从事中郎。父端,齐奉朝请。筠孤贫好学,师事沛国刘瓛,强力专精,深为瓛所器异。既长,博通经术,尤明《三礼》[3]345。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3]673-674。
臧严,字彦威,东莞莒人也。曾祖焘,宋左光禄。祖凝,齐尚书右丞。父稜,后军参军……孤贫勤学,行止书卷不离于手[3]710。
袁峻,字孝高,陈郡阳夏人,魏郎中令涣之八世孙也。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讷言语,工文辞[3]718-719。
这些士人祖上曾有功名,但到他们出生时,几乎都已经家道中衰,已是典型的寒门,故“孤贫好学”是他们共同的特点。还有些士人则是世代寒贱,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但他们勤奋好学,凭借自己的学术和文学才能,终于跻身于当代名流之中,或成为统治阶层中的中坚,受到社会的瞩目,并在青史留名。
沈峻,字士嵩,吴兴武康人。家世农夫,至峻好学,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麟士门下积年。昼夜自课,时或睡寐,辄以杖自击,其笃志如此。麟士卒后,乃出都,遍游讲肆,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3]688。
孔子袪,会稽山阴人。少孤贫好学,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投闲则诵读。勤苦自励,遂通经术,尤明《古文尚书》[3]678。
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也。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斅之,谓为“吴均体”[3]680。
上述这些士人,虽然其门第略有不同,但都可作为寒门士子的代表。这表明,进入梁代后,兴起于宋代的士族博学之风在庶族寒门也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从仕途利禄的吸引来说,这当然与当时朝廷的提倡有关,《南史》卷四十九《刘怀珍传附刘峻传》说:“梁武帝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6]1219如徐勉“年六岁,时属霖雨,家人祈霁,率尔为文,见称耆宿。及长,笃志好学……勉善属文,勤著述,虽当机务,下笔不休”[3]698。周舍“博学多通,尤精义理,善诵书,背文讽说,音韵清辩”[3]377-387。二人均受到梁武帝重用,《梁书》卷五十《文学传下·何思澄传》即称:“时徐勉、周舍以才具当朝。”[3]375在他们之前还有范云,三人都是博学能文的楷模,且先后为相。因此,梁武帝重文重学的政策,在他们手中自然能够得到更为彻底的贯彻。
但是从更深的层次来看,经过上层社会长期的提倡,好学能文已在社会各个阶层蔚然成风。好学甚至已成为士人本能趣味的一部分。如刘峻与张缵的例子就都很典型。北魏攻陷青州,年仅八岁时的刘峻被“略至中山”,后又被“徙之桑干”,在这种困苦的条件下,却依然勤学不辍,“家贫,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其发,既觉复读,终夜不寐”[3]714,后在齐永明中得以南还,依旧广求异书,终于成为一位饱学之士;张缵任秘书郎后,按惯例“数十百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如此数载,方迁太子舍人”[3]701。如果说刘峻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张缵为读书而不愿迁官,就更能说明这种好学的确是发自内心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博学”、“能文”之风在齐梁时期的深入人心。
二
齐梁文士“以气类相推毂”的特点也非常突出。如果说东汉士人多以名节相互标榜,形成了所谓的“清流”,魏晋士人多以玄谈相互赏识,产生了所谓的“名士”,那么到了齐梁时代,我们看到的则是士人们以“博学”、“能文”相互肯定,出现了一批博学型文人。因为崇尚博学能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旧传统,在齐梁士人中得到了明显的改观。《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陆厥传》曰:“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2]898“推毂”,本指推车使之前进,是古代帝王任命将帅时的隆重礼仪。在这里意为荐举、援引。“以气类相推毂”,实可看做是齐梁士人惺惺相惜的写照。
“竟陵八友”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都曾受到过当时名流硕学的推毂。王俭就是一位代表人物,《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称:“齐台建,迁右仆射,领吏部,时年二十八。”[3]434如此年轻就被任为宰相,他本人又才高学博,尤喜汲引文士。如《南史》卷五十九《任昉传》曰:“永明初,卫将军王俭领丹阳尹,复引为主簿。俭每见其文,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于是令昉作一文,及见,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点正,昉因定数字。俭拊几叹曰:‘后世谁知子定吾文!’其见知如此。”[6]1219又《南史》卷三十八《柳元景传附惔传》曰:“惔,字文通,好学,工制文,尤晓音律,少与长兄悦齐名。王俭谓人曰:‘柳氏二龙,可谓一日千里。’俭为尚书左仆射,尝造世隆宅,世隆谓为诣己,徘徊久之。及至门,唯求悦及惔。”[6]1452因此,任昉在为他的文集所作的序中,也称他“弘长风流,许与气类。虽单门后进,必加善诱。勖以丹霄之价,弘以青冥之期”[8]。“竟陵八友”中除沈约、范云、陆倕之外,其余五人都曾追随于他,得到过他的赞誉和提携。至于齐文惠太子和竟陵王萧子良对“竟陵八友”的援引,更是众所周知,不需多论。
“竟陵八友”能够“以气类相推毂”,无疑也是受了这种时代风气的感染。他们之间大多相互推重,少有相轻之习。这在典籍中多有记载,如任昉“后为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时琅邪王融有才俊,自谓无对,当时见昉之文,怳然自失”[6]986。陆倕“梁天监初,为右军安成王主簿,与乐安任昉友,为《感知己赋》赠昉,昉因此名以报之”[6]1452。不可一世的王融之所以能服气于任昉,年长十岁、成名颇早的任昉却与小友陆倕结为知交,都是为对方的才学所打动。八友中年辈最长的沈约,对其他同仁更是褒扬唯恐不及。如他与范云之父范抗本是同僚,“云随父在府,时吴兴沈约、新野庾杲之与抗同府,见而友之”[3]493。“朓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2]826“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词宗,深所推挹”[3]229。沈约比范云大十岁,比任昉大十九岁,比谢朓大二十三岁,但是年龄和阅历的差距,并没有影响他对这几位文友之才华的衷心赞美与推崇。
“竟陵八友”对于当时其他博学多才的士人,也总是“以气类相推毂”,从不吝惜。如《南史》卷三十八《柳元景传附恽传》曰:“恽立性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为诗云:‘亭皋木叶下,垅首秋云飞。’琅邪王融见而嗟赏,因书斋壁及所执白团扇。”[6]1193《梁书》卷三十六《孔休源传》也说:“孔休源,字庆绪,会稽山阴人也……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荐之于司徒竟陵王,为西邸学士。”[3]253可见“自谓无对”的王融,所欣赏、推重的也不仅仅是他们小圈子里的人,而是见到博学能文者,便会由衷地发出“嗟赏”,与之订交并积极援引。
此外,如谢朓对到洽的“深相赏好”[6]988,及他们两人对江革的“雅相钦重”[3]519,沈约、谢朓等对崔慰祖的“称服”[6]681、萧琛对裴子野的褒扬等等[6]1776,皆可以见出“竟陵八友”爱才惜才的共性。而在这八人中,又以沈约、任昉最具代表性。
沈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天监初,柳恽为吴兴,召补主簿,日引与赋诗[3]522。
子显身长八尺,状貌甚雅,好学,工属文。尝着《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6]866
孺,字季幼,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起家中军法曹行参军,时镇军沈约闻其名,引为主簿,恒与游宴赋诗,大为约所嗟赏[6]。
约为丹阳尹,命驾造焉。于坐策显经史十事,显对其九。约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虽然,聊试数事,不可至十。”显问其五,约对其二……尝为《上朝诗》,沈约见而美之,命工书人题之于郊居宅壁[6]1072-1073。
这些例子远远不是沈约爱才重学、汲引后进的全部,但从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位乐于奖掖后进的文坛长者的拳拳之情。这在他对王筠的一再赞美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天监六年(507)四月,六十七岁的沈约为尚书左仆射,闰十月升为尚书令。二十七岁的王筠则在这一年被任命为尚书殿中郎,成为沈约直接的下属。一经接触,沈约就对这个后生小子却给予了极不平凡的赞誉:
沈约每见筠文咨嗟,尝谓曰:“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自谢朓诸贤零落,平生意好殆绝,不谓疲暮复逢于君。”约于郊居宅阁斋,请筠为草木十咏,书之壁。皆直写文辞,不加篇题。约谓人曰:“此诗指物呈形,无假题署。”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示筠草……筠又尝为诗呈约,约即报书叹咏,以为后进擅美。筠又能用强韵,每公宴并作,辞必妍靡。约尝启上言:“晚来名家,无先筠者。”又于御筵谓王志曰:“贤弟子文章之美,可谓后来独步。谢朓常见语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近见其数首,方知此言为实。”[6]1006
作为长者、上司和成名已久的文坛领袖,沈约对王筠的这种肯定无疑是发自内心的。他把王筠与他极为推崇的谢朓相比,并在梁武帝面前赞美他“后来独步”,是后学中最优秀的一位。既表现出发现人才的喜悦,也毫不保留地尽了“推毂”之力。任昉提携后进的热情也丝毫不减沈约,受到他推举、援引的士人可以列出一大串,如刘孝绰、刘苞、刘孺、陆倕、张率、殷芸、刘显、到溉、到洽等人,均曾游于任昉的门下,常诗酒往来,有所谓“兰台聚”[6]1240,号为“龙门之游”[6],对他不遗余力“奖进士友”[6]的美德,刘孝标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
见一善则盱衡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于是冠盖辐凑,衣裳云合,辎軿击轊,坐客恒满。蹈其阃阈,若升阙里之堂;入其奥隅,谓登龙门之坂。至于顾盼增其倍价,剪拂使其长鸣,彯组云台者摩肩,趋走丹墀者叠迹[3]698。
与此相应,还有两个方面也很能显示出齐梁士人“以气类相推毂”的特点。一是优秀的士人常常会得到一大批名人的推举。如孔休源就先后得到过齐太尉徐孝嗣、王融、梁侍中范云、尚书令沈约、吏部尚书徐勉、吏部郎任昉、太子詹事周舍等一大批朝廷显贵,同时也是学界名流的一致推举,连梁武帝对他都格外重视[3]257。又如刘显也受到王思远、张融、任昉、沈约、陆倕等一批名流的推赏[6]678。二是当时士人之间的相互肯定与称扬。《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记载:“子野与沛国刘显、南阳刘之遴、陈郡殷芸、陈留阮孝绪、吴郡顾协、京兆韦棱,皆博极群书,深相赏好,显尤推重之。”[3]519-522《梁书》卷五十《文学传下·谢徵传》也说:“徵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同官友善,子野尝为《寒夜直宿赋》以赠徵,徵为《感友赋》以酬之。”[3]433从中可见,这批“博极群书”的文士,早已不再“相轻”,而都表现出对朋友真诚的欣赏、推重。《南史》卷五十《刘瓛传附刘显传》还说:“显与河东裴子野、南阳刘之遴、吴郡顾协连职禁中,递相师友,人莫不慕之。”[6]1193所谓“递相师友,人莫不慕之”,正可看做是对当时士人相互敬重、相互学习,“以气类相推毂”之风气的另一种说明。
三
上述士人之“博学”、“能文”与“以气类相推毂”,虽然并非始自齐梁时代,但是在齐梁时期,它已从士族扩展至一般寒族,而且士人之间的相互欣赏与援引,也远远超出了家族的小范围,而扩展至全社会。这两方面的普遍化,不仅为此前所没有,而且从士文化与文学史的发展来说,也有其特殊意义。以往的研究对此虽有所涉及,但因受传统评价的影响,往往语焉不详。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仅拟简要讨论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齐梁士人的两大特点是士人自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余英时先生曾以“士之自觉”为线索,讨论“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以为士之“群体自觉”,始自东汉后期,以党锢诸贤为代表,其根本精神为“以天下为己任”;而士之“个体自觉”,亦始于此时,外在表现为尚名节、人物评论、重容貌与谈论等,内在表现则见于避世思想、养生与老庄、经济丰裕、山水怡情、文学与艺术等多个方面[9]。依余先生的说法,士人群体自觉,主要体现为一种政治层面的集团合作意识,与维护封建政权密不可分;士人个体自觉,则侧重于个体独立或自我心灵追求,而不再以政治之是非为唯一标准,甚至不考虑政治问题。
若以此作为参照,重新审视齐梁士风的两大特点,则士人“博学”、“能文”的普遍化,实为东汉以来士人个体自觉在学识与创作领域的一种具体体现。与此前相比,其变化有三:一是“博学”直接指向“能文”,与文学创作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二是由以往士族大家的家族特征演变为包括寒族在内的全社会士人的特征;三是“博学”、“能文”不再是脱离政治的自我人生寄托,而是再次成为走向仕途的一种特殊能力,许多人凭借“博学”、“能文”的个人素质,得到了重用或获得了升迁。而与此相对,士人“以气类相推毂”则更多地体现了他们在文学领域的群体自觉,他们把“博学”、“能文”作为一种新的价值标准,以此相互肯定,相互欣赏。这种社会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其二,齐梁士人的两大特点,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文人集团与文学流派的形成,乃至唐代文学辉煌期的到来作出了多方面的准备。
以“博学”、“能文”作为衡量士人的重要标准,一方面固然与当时官方选人用人的政策分不开,如梁武帝就喜欢“以文士身份频繁地主持宴会赋诗、隶事活动,以此决定对朝廷文士的任用”[10];另一方面,它也代表了社会对士人的一种理想预期。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两个方面又往往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社会对士人“博学”、“能文”品格的普遍认可,既受到朝廷用人政策的影响,但又会反过来对后者产生制约。与汉代经学及魏晋玄学不同,在齐梁时期,“博学”、“能文”不仅需要在各种宴会、游戏中显示出来,更重要的还要在文学作品中得到确认。如果说与汉代士人重视“博学经书”(《汉书·谷永传》)相关的是章句之学的兴盛,与魏晋士人崇尚“才理”、“异才”对应的是清谈善辩及玄理思考,那么,齐梁士人“博学”、“能文”的最终成果则是文学作品。因此,齐梁士人“博学”、“能文”的普遍化,对文学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或者说,它是文学兴盛的一个必要前提。而士人对同侪“博学”、“能文”的才华,不是嫉妒压制,而是相互欣赏、肯定,“以气类相推毂”,这又与帝王及贵族为招揽人才聚集文学之士、举行文学活动的做法,互为表里,相互促进,从不同侧面共同构成了文学集团形成的必要前提。
作为中国文学发展高峰之一的唐诗,当然继承了前代多种优秀的传统,但唐诗中有几大要素,从继承发展的角度来看,都与齐梁士人的这两大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是用典。建立在博学基础上的逞才炫学的创作风气,在齐梁时代已经以用典的特定方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唐人所做的不过是在此基础上把它更进一步精致化而已。二是格律。永明体的“四声八病”之说,打通汉语声韵与诗歌创作这两大门类的壁垒,在诗歌史上可谓别开生面。到初唐格律定型之后,这一发明为唐代诗人施展才华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而“四声八病”说从本质上说,其实也是齐梁士人逞才炫博的产物之一。三是文学流派的诞生。齐梁文士“以气类相推毂”,虽然产生了永明诗人、竟陵八友、宫体诗人等文学群体,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些文学群体或许未必能算正式的文学流派,但是这种“以气类相推毂”而形成的文学群体,无疑可以看做是唐代及以后更典型的文学流派的前奏。仅从这三点来说,齐梁士人的两大特点,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也可见一斑。
自唐代以来,由于文学的政教功能及士人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往往被作为评价文人和文学的重要标准,故历代关于齐梁文人和文学的相关论述,否定性的意见始终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但从上述齐梁士人的两大特点来看,以往的研究对齐梁士人的贡献及其对文学正面影响的认识,也许与历史实际仍有相当的距离。因此,从多元化的角度对之作出重新的思考,无疑是有必要的,也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1] 陈桥生.刘宋诗歌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136-179.
[2] [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陈尚君.唐研究:第5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36.
[5]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62、63.
[6] [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
[7]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759.
[8] [梁]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656.
[9]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87-400.
[10] 刘怀荣,宋亚莉.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