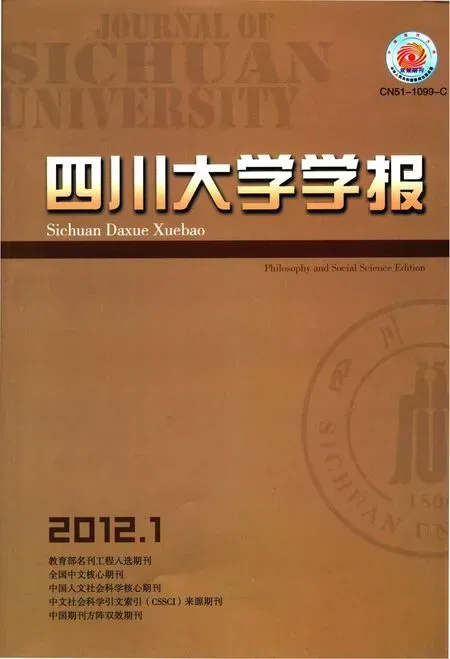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西方政治的启示
李蜀人
(西南民族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近年来,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随着实践哲学的复兴,也成为了当今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话语。然而,在研究政治哲学时,我们也不难看出一些问题,例如,在国家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经常是用社会来取代政治,将政治问题转化成为了社会问题。这就使得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同社会学或社会哲学混淆不清;而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又往往只注意国家权力的运用和限制,而忽视对于公共领域以及公民的相关研究。这就使得政治成为了权力的代名词。这样的研究有意或无意地强调了国家权力在公共领域中具有决定作用这一错误观念。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对于政治与公共领域还缺乏基本的认识,我们还是在日常话语的意义上是来理解所谓的“政治”,而没有将“政治”还原到理论层面进行透视。因此,本文拟对政治与公共领域关系进行清理,从而确定出它们的含义、范围和作用,这或许会对当前政治哲学的研究给出一些启发或建议。
一
在现代汉语里,政治“是指阶级之间、民族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基于各自根本利益所发生的相互关系以及与此有关的活动。”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Ⅱ》,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但是,这一定义的语义不详,我们还是不能从中知道政治是什么。因为所谓的根本利益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政治的,而与此相应,相互关系和活动就不知所云了。
其实,现代汉语中的“政治”这个词是个外来词。首先是日本人翻译西方的politics时用汉字创造了“政治”一词。这样,当这个词从日本传入中国时,孙中山认为其含义是:“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②孙中山:《三民主义》,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这一说法尽管过于简单,但是其影响则是巨大的。因为管理众人的方式在现代主要是以国家形式来实现的,而国家直接涉及到权力。因此,政治的就是权力的,起码就是同国家权力直接相关的,便成为了中文的基本语义。
其实,这样对“政治”的理解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政治”一词最早在《尚书》之中就可以见到。如《尚书》中说:“三后协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①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这里的政治是对某种秩序治理方式的肯定。但是,一般说来,在古汉语里,“政”与“治”是分开说的。如《周礼》上说:“凡事致野役,而师,田作野民,帅而至,掌其政,治禁令。”②杨天宇:《周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这里,“政”表示的是公正,“治”强调的是管理。《说文》解释到:“政,正也。从攴,从正,正亦声。”这一说法有匡定之意。《字彚·攴部》进一步的解释是:“政,以法正民曰正,以道诲人曰教。”③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成都和武汉:四川辞书出版社和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年,第611页这里的“政”也是有公正之意。而治就是治理之意。《玉篇·水部》:“治,修治也。”④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672页。因此,从古汉语上说,“政治”这个词就应该是指某种合理而公正的管理方式。如孔子说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里的“政”指人的公正。其意为,如果管理者自身是公正的,那么,人们还敢不公正吗?他还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⑤金良年:《论语·泰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这里的“政”则是同地位相联系的。显然,这样的“政治”预设了这样的一个前提:人是需要管理的。一些人要管理另一些人。这就是说,在中国传统典籍中,人是有区别,有等级的。管理者就是“君”,被管理者则是“民”。因为“民”总是无助而盲从的,所以,“民”就需要治理。而“君”则天生就比“民”优越,从而从天理上便获得了管理“民”的合法性。但是,“君”对“民”管理则要以政与治的方法才能有效。这样,从一开始中国古代的政治同“国”和“民”相连,都同管理者的计谋和权力相关。所以,墨子也说道:“古者圣王皆以鬼神为神明,而为祸福,执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国安也。”⑥李小龙:《墨子》,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这里, “政治”就是同“国安”相连的,而“国安”又是同“治民”相联系的。
在这些中国传统的典籍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中国传统政治词语所带来的政国治民的语义。其核心是通过计谋和权力对民众进行管理,从而达到“国安”的目的。这就是说,从古到今,汉语政治的含义有着血脉上的相承关系,其基本含义是指对于人民的管理,即政治统治。因此,中国的政治更多涉及的是具有显著等级特征的统治方式,而很少关心人们之间的关系。
而西方的“政治”(politics)一词来源于希腊文polis即public life or affairs,其基本含义是指公共生活或事务。据考证,这个词最先出现在荷马史诗中,其基本的语义是指修建在山顶上的城堡或卫城,即“波里”。城邦形成后,古希腊人就用“波里”来指城邦关系,强调的是在公共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同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相区分。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希腊公民 (不包括奴隶和妇女)是有两种不同的身份:一方面,人是家庭成员,家庭成员之间有家庭的法则和准则;另一方面,人又是公民,在公民之间有作为公民的法则和准则。与公民身份相对应的,就是政治或政治学所包含的内容。因此,对于西方而言,“政治”意指在公共领域里的公共事务。这就意味着,仅仅从词源上考察,中西方从一开始在政治的理解上就有着根本分歧。中文的政治主要是管人理事,考虑的基本问题是统治者如何管理好人民。而西文的政治主要是处理公共事务。考虑的基本问题是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要准确地理解西方的政治,那么,我们首先必须探明所谓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借鉴西方政治思想来构建当代的中国社会,而不至于在借鉴西方政治思想时走向歧途。
二
尽管在日常话语里“公共的”(public)这一词语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例如“公共汽车”和“公共积累”等等。公共汽车是指供公众乘坐的有固定路线和停车站的汽车;而公共积累,即公积金,是指企业单位、生产单位从收益中提取用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01页。。但是,在这些含义中公有公用是其基本语义。“公共汽车”是指公众都可以乘坐的汽车;“公积金”是指为公众服务的资金。因此,“公共的”便是指公众都可以使用的,从而同只能够私人使用的相区别。不过,应该注意,所有的这些公共物品都只能在公共领域才能成为公共的。因此,可以认为,正是公共领域赋予了物品的公共性。正如产品一样,只有到了商品社会,所有的产品都成为了商品。
所以,“公共的”必然会涉及到在公共领域里人与人的秩序、制度和原则以及其规范等问题。也就是说,公共领域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构成了公共领域本身,而且还规定着其中的秩序、制度、原则以及其规范。从这种意义上讲,公共领域并不是像家庭那样自发形成一个领域,而是具有特定内涵的建构性领域。这就是说,同私人领域的自发性不同,公共领域是被建构起来的。因此,公共领域便成为了西方政治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
应该说,西方对于政治的研究有很长的历史。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开始研究公共性这一问题。因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看来,家庭是私人领域,而城邦则是公共领域,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都认为,家庭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的稳定是依靠家庭成员之间自然地存在着的等级制来维持的。而城邦则是以理性为基础,公民之间应该以正义为原则,这样才能保证城邦的正常秩序。因此,公共正义问题则成为了他们政治研究中的基本问题。
其实,苏格拉底早就注意到了城邦问题。他认为,如果要建立城邦,那么就要消除私心,从而保证城邦的稳定和统一。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人有私心,每个人都从自己利益出发,那么,公民之间就不能够团结起来。而如果消除了私心,人们都以公心为标准,那么,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就容易达成一致。这便首次提出了公共领域的基础是公心的思想。但是,人有没有公心,能不能有公心则是一个问题。
而柏拉图则与此不同。因为他关注的是城邦如何起源问题。在他看来,城邦建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个体的自由民是不能自足的。在他看来,个体的自由民有许多的愿望或想法,这些愿望或想法仅仅通过个人的努力是不能实现的。因此,自由民与自由民就必须结合起来,形成城邦。只有在城邦里,个人的许多愿望才能实现②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8页。。不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是不能够自然形成的。因为自然形成的城邦即是现实的城邦,而现实的城邦一定是不完善的,因此,人们必须从理论上提出理想城邦的标准。只有我们知道了这样的标准,才能够建立更加合理的城邦。据此,他第一个提出了正义原则。他认为,只有符合正义原则的城邦,才是合理的城邦。尽管他的正义含义同后来的正义思想有着极大的差别,但是,正是柏拉图首次将正义提高到了社会制度首要价值的高度,从而为西方政治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开启了方向。
接着从城邦的功能和组成上,柏拉图分析了城邦的结构。他认为,任何一个自主的城邦必须由管理者、守卫者和生产者这三类人组成。但是,他又指出,人与人在各个方面又是有区别的。仅仅就公民的构成上说,在他看来,一些人是金子组成的,另一些人是银子组成的,还有些人是铁铜组成的。这些不同材料构成的人,其能力和德性肯定是不同的。因此,他认为,应该根据个人的这些不同,按照城邦的功能,将其分配到城邦的不同位置上。在这些位置上,按照一些法制,让其发挥出最大能力,即各在其位,各尽其职,这就是柏拉图提出的正义原则③柏拉图:《理想国》,第128页,第138页。。因为柏拉图坚信满足这一正义原则的城邦一定是一个和谐而稳定的城邦。
最后,柏拉图分析了现实城邦存在的问题,即城邦的稳定性问题。在他看来,在现实中,正义原则常常遭到破坏。其典型的表现就是管理者、守卫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僭越。生产者变成了管理者,管理者变成了守卫者,守卫者变成了生产者等等,这样,城邦就会产生纠纷,甚至崩溃。而造成这样僭越的原因,在他看来,则“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戚的私有造成的”④柏拉图:《理想国》,第201页。这就是说,在柏拉图看来,财产、子女和亲戚的私有是现实城邦不稳定的原因,于是,柏拉图提出了相关的公有制思想。他认为,只有将财产以及妇女和儿童都共有,城邦才能够统一和稳定。
但是,亚里士多德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尽量趋向统一的城邦最后一定不能成其为一个城邦。因为城邦的本质就是不同的公民在公共领域的集合体,其中就是要表现出每一个公民的个性,其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如果公民的认识与行为都统一了,那么,城邦就将被还原成为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继而被还原成为齐一的个人。这样,柏拉图的理论便会导致城邦等同于家庭的结论,这在理论上便瓦解了城邦。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这种思想或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同时,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柏拉图的共有或公有的思想也是错误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的财产都是属于私人领域的,财产是不能够共有的。如果将其公有,也就是说,将其放到公共领域,则可能将私人领域侵蚀,而又在公共领域里无法扎根,从而混淆两者之间的界限,其结果只能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会被瓦解。所以,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财产是不能公有的而只能私有的。因为一旦公有,人们就不会再关心这些公有财产。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是在自发形成的“村坊”基础上结合而成的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7页。。因为只有在城邦里,人类的生活才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人们才能获得生命和生活的意义,过上他所谓的“优良的生活”。也就是说,人不仅是要生活,而且还要过优良的生活。而优良的生活就只能是在城邦中的生活。离开了城邦,人就只能过自发的本能生活。
虽然人们本能的生活与优良的生活在他看来都是群居的生活,但是,亚里士多德敏锐地发现,人的本能生活就是同动物一样的群居生活。而优良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因为他认为,自然不会造出无用的事物。既然自然造出了人的群居生活的城邦,那么,城邦就应该同动物的群居生活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在城邦生活中人们是通过只有人类才能够具备的言语来交流或沟通的。人类的言语,不仅可以表达生活的悲欢离合,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类通过言语还能够判断生活中的正义与非正义,说明其善与恶。所以,在城邦中,人们是以道理而不是通过暴力来维持人们之间的关系的。因此,他认为,城邦绝不是自发形成的,而只能是以理性为依据,在家庭基础上被建构的。对此,他说道:“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指出,城邦是自然的“村坊”发展的最高产物。从这一最高的产物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本质。在他看来,城邦的本质就是其具有公共性。而公共性,按照古希腊文来说,就是最原始的政治性。这样的原始政治,从本质上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在本性上正是一种政治动物。”同理,人类在本性上也是一种政治动物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8页。。
就城邦与家庭的关系而言,亚里士多德又认为,城邦在形成上是先于个人和家庭的。因为从逻辑上或本性上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只有整体存在了,部分才能存在③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8页。。如果手足脱离了整个身体,那就不成其为人的手足了。同样的,一个孤立的人是不能成为政治动物的,是不足以过上优良生活的。所以,他非常强调城邦的重要性。而在城邦中,公民与公民是要通过语言交流才能形成公共关系,因此,古希腊人都非常重视修辞学,因为言语对于城邦的公民格外重要。言语甚至是决定其生活优良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
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有正义原则。因为在城邦中,人们之间是讲礼法的。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人就会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所以,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 (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④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9页。
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强调的是,城邦要高于家庭,政治要高于伦理,公共领域始终要高于私人领域。因此,他才说,政治学应该是实践科学中最高的科学①亚里士多德:《尼科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页。。
这就是说,从一开始,西方的“政治”就是同公共领域联系在一起的。在古希腊,政治学主要是研究城邦之中的基本问题,考虑的是公共性如何可能的问题。即便在当代,西方政治的这一含义仍然被像阿伦特这样的哲学家所坚持。
三
对于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当代美籍德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Hannan Arendt)有过专门的研究。她基本上赞同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研究的思路。首先,她也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切人类活动都要受到如下事实的制约:即人彼此共同生活在一起。一旦超出了人类社会的范围,行动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并且也唯有行动是如此。”在阿伦特看来,如果一个人只能在孤立状态中劳动,那么,这个人就不能叫人,而只能称为是一种劳动的动物。然而,阿伦特指出,公共的并不就是社会的。因为在古希腊文中是没有社会这个词,也没有同社会对等的思想。社会这个词是来源于拉丁文。根据阿伦特的考证,这个词最早见于塞尼加的书中,后来经过托马斯·阿奎那的阐述,便成为一个指称人类基本状态的标准名词②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见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2005,第57页、58页。。但是,这样的无意置换,在阿伦特看来,却使得古希腊政治的含义基本丧失了。
从词源上说,社会这个词最基本的语义就是指人的群居性。而群居性这个特征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并不是人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因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许多动物也具有群居性特征。因此,在他们看来,不是群居性而是群居的方式才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有很多活动,动植物也有很多活动,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应该有一种不同于其他生物而仅仅是属于人的活动,他将其称为实践活动(praxis)。他认为正是实践活动将人与生物区别开来。而“实践”活动,主要是指人们的政治和伦理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说,阿伦特认为,人们将亚里士多德的“zoon politikon” (政治的动物)一词在最早的时候翻译成为“社会的动物”是不准确的。因为首先是古希腊没有这个词;其次,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只有政治性而不是社会性才是将人同世界中其他物种区别开来的根本性质之一。
而政治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古希腊城邦的公共领域之中。这样的公共领域完全不同于以家庭为核心的自然关系,甚至还直接同家庭关系相对立。这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古希腊公民来说,他们都过着两种生活,即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这两种生活的区别在当时是非常鲜明的,那些具有必然性和实用性的生活就是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它们都被亚里士多德严格地排除在了政治生活之外。就此而言,在古希腊时期,政治生活主要是指城邦中公民之间的生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这种生活才是真正的属人的生活。
阿伦特指出,在公共领域,亚里士多德发现了言语交流的重要性。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会认为,人是一种zoon logon ekhon(会说话的动物)。但是,在拉丁文里,这个定义却被翻译成了“人是理性动物”。阿伦特认为这也是一种误解。因为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人的最高能力并不是理性,而是“努斯” (nous),即静观沉思的能力。所以,他才会提出思辨是最高幸福的思想。而他的这个定义主要是想强调理性在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因此,汉娜·阿伦特认为,亚里士多德这两个著名的定义不过是表明了当时古希腊人对于政治生活方式的主流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城邦之外的所有的人,如奴隶和野蛮人,是不能成为公民的。因为这些人并不是被剥夺了说话的能力,而是被剥夺了这样一种说话的方式:即不能在公共领域言语。而城邦的公民则是可以在公共领域自由交谈的人。因此,阿伦特认为,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在古希腊,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或不同。而所谓的社会领域这一划分肯定是在远离了古希腊公共领域思想后产生的。
作为私人领域典型形式的家庭生活和作为公共领域典型形式的政治生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在阿伦特看来,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因为两者的构成和法则是不一样的。但是,阿伦特又指出,对于两者之间的边界,有时古希腊人也是暧昧的。例如,柏拉图就有侵占私人领域的梦想。因为他提倡公有制,主张将妇女和儿童公有,而亚里士多德好像要清醒一些。他努力维持两者的边界。不过,他更关注公共领域,而对家庭则研究不够。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思想中,两者的边界还不是十分清晰。显然,阿伦特注意到了公共领域这个问题对于人类秩序构建的重要性,并对此进行了她所谓的政治性思考。
在阿伦特看来,家庭的产生主要是为了生活本身,为了满足人的生存和种的延续。在家庭中,男人主要是为了生计而劳动,女人则主要是繁衍后代。因此,家庭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人或人类本能的需要,而本能的需要则受到自然必然性的决定。就此而言,阿伦特认为,家庭领域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具有必然性。从这样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等人所谓的家庭是自然产生的,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是在物质匮乏和人的本能需要的驱使下形成的以血缘为基础,人们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共同体①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见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63页。。
与此不同,城邦这样的公共领域的特征之一则是自由。因为在公共领域中的公民,既不用为生存忧虑,也不受必然性的制约。在公共领域里或在政治领域里,公民都是一些“平等的人”。平等也就成为公共领域的又一个特征。在公共领域,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公民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可以自由地通过言语进行交流,从而突出自己卓越的个性即德行。德行的不同展现了公民之间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是通过言语表现出来的,因此,言语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言语可以增加公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通过言语而不是暴力的方式,以理服人,这是一种文明的标志。这样,“逻格斯”便成为了古希腊政治的中心。因此,阿伦特认为,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政治绝不是维护社会的工具,而其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
然而,到了西方的近代,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民族国家的建立,公共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私人领域越来越小。理性而不是血缘成为那个时代精神的姿态。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因此,平等而自由的思想成为了所有人追求的生活目的和意义。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只有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之上,人的本性才能够得到保证和满足,而只有保证和满足了人的本性,人才能过上幸福生活。甚至在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也要求自由与平等。这就将先前在公共领域中的原则和观念也开始用到了私人领域。在自由与平等名义下,家庭从那时开始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私人领域,而是成为了公共领域的一个单位或部门。这就极大改变了公共领域的功能和范围。这时社会便产生了。
社会不仅将公共领域包括其中,而且也将私人领域吞并。例如,现代家庭的许多日常事务,都必须要一个公共的家政管理机构来管理,人们的婚姻需要到教堂或政府部门去登记,子女的教育要通过学校来完成等等。一些家政工作,也可以用家政公司来打理。如果让一个孩子由家庭来培养,人们马上就会对这样的小孩的未来感到担心,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个小孩缺乏社会性,今后不可能同人正常地交往和生活。从此开始,社会性取代了公共性而成为了从那以后任何时代对人的主要要求。
同时,新产生的社会机构又在担负着这些社会性功能。如社会的民政部门,它既不属于私人领域也不属于公共领域,而只能属于社会领域。甚至学校也改变了它的传统功能,成为了社会机构。这些社会机构既没有传统政治性,更不可能具有传统的私人性。这样一来,传统私人领域里的家庭和传统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共同体,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取而代之的是社会领域的出现。对此,汉娜·阿伦特说道:“一个既非私人又非公共的社会领域的兴起严格说来是一个比较晚近的现象,从起源上说,它是随着近代而开始的,并且在民族国家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形态。”②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第62页。阿伦特认为,现代社会不过是一个在国家基础上形成了既包括家庭、又包括国家在内的人类新型共同体。与此相应,在人类知识体系上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科学。不过,这些社会科学,如果从古希腊观点来看,便是相互矛盾的。如政治经济学,在古希腊人看来,政治的即是公共的,是人的德性自由的展现;而经济的则是私人的,是为人们生计的行动。他们认为,这两门学科是绝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古今的差异,使得阿伦特敏锐地注意到社会领域产生的意义。在她看来,社会的产生完全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她说:“社会从家庭阴暗的内室步入光明的公共领域,它的出现——家政的兴起、它的活动、问题和组织手段——不仅模糊了私人领域与政治领域的传统分界,而且几乎在人们无所察觉的情况下改变了这两个术语的涵义以及对个体和公民的生活的意义。”①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第70页。因为社会最初的含义也是指人的群居生活,但是,它同家庭和公共领域中的群居生活又是不同的。家庭的群居生活是本能的,公共的群居生活是政治的,而社会的群居生活是普遍的。
公共领域现在成为社会领域里的一个部分,与此相应,政治也就成为了社会的一种功能。它涉及到了社会管理问题,而社会中,最基本的管理就是社会成员的管理。这样的管理,从近代以后,主要是通过国家来进行的。因为从霍布斯开始,西方人普遍接受了他的社会契约论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说明了社会起源的原因,赋予了国家的合法性。所以,从近代开始,西方政治也同国家权力相关了,从而丧失了其自由而带有了明显的强制性或压迫性。所以,阿伦特说:“一旦把政治看成是社会的一项功能,人们便再也不可能感到这两个领域之间有什么严格区分了。”②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第66页。而社会领域取代了公共领域,对于社会中的人而言,政治便成为他们在公共领域中的一种社会职责;对于个人而言,社会要求也成为他们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这样,人们在社会中只有社会行为而不能进行人类行动。阿伦特清醒地看到了这样的结果:“社会在其自身的所有层次上都排除了行动的可能性 (而在以前,家庭也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社会期待着它的每一个成员表现出一种特定的行为,它要求其成员遵循无以计数的各类规则,目的是让他们守规则,排除一切自发的行动或杰出的成就。这些规则趋向于将社会成员‘标准化’。”③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第72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要求。按照社会的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会趋同,达到所谓趋同的社会化标准。而这些社会要求和标准又是通过国家这样的形式来完成的。这样社会政治的强制性使人逐渐既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又失去了古典公共领域里的自由。因此,阿伦特认为,按照社会要求和标准,到现在就形成了她所谓的“大众社会”。这个社会,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表示了对如下事实的承认:社会已经完全取代了公共领域。共同性的社会要求将人的差异已经变成了完全私人化的特征,而同公共领域毫不相关。这样的大众社会却是极权主义渊薮。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了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因为一旦社会中的人完全趋同了,那么,社会就等同于人类,这在理论上就说明了这样的社会并不是社会。
四
这就是说,从西方近代开始,由于启蒙运动的影响,人成为那个时代理论研究的主题。无论是霍布斯、洛克、休谟,还是笛卡儿、斯宾罗莎、康德都将个人当作他们研究的基本问题。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们研究的个人已经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公民,而是在社会领域中存在的个人。尽管社会一词突出强调了人们的群居方式,但是,社会并没有将家庭和城邦这些群居方式加以区别,反而是将其统一到社会之中。因为他们都认为,理性而不是血缘应该是人最基本的特征。在他们看来,正是理性的自主性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真正的基础,从而才会产生以自由与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因此,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便成为了人们在理论上关心的重点;到现代,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广泛,不仅是国家之中人与人的交往更为紧密,而且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也更为普遍。这样的社会认同趋势更为明显,对于社会的研究更为紧迫。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在大步前进,而真正的政治哲学却在衰落。
然而,从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上说,一旦公共领域消失了,私人领域便会直接同社会同一。社会原则就会彻底侵入家庭,家庭的作用和意义就会丧失。而公共领域中的自由也会在社会原则的压迫下成为了一种空洞的幻想。人就只能是平均的社会人,而社会人就不是完全的人,因此,社会人已经远离了人的自由本质,而社会就会是一个大众社会。而大众社会是一个为了生计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从本质上说,是同西方传统的政治社会直接对立的。所以,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之中,如果我们要对西方政治哲学有一个透彻的把握,就不得不加强和加深对于西方公共领域理论的研究。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真正要借用西方政治哲学思想来研究中国政治的问题,也不能仅仅从国家权力这样的维度去研究所谓的政治,因为这样的政治仅仅是阿伦特所谓的虚假政治。而虚假政治仅仅是政治的一种形式,甚至是异化的形式。因此,研究当今中国社会的政治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权力的问题,也许中国社会中的公共领域问题是更为根本的政治问题。只有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能真正将政治哲学同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联系起来,从而构建出一个成熟的现代性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