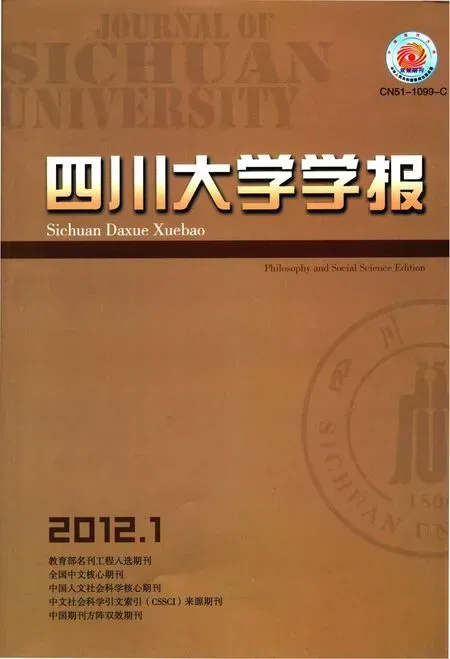左右同源:新文学史上的新写实主义
姜飞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巍巍哉”、“皇皇哉”①邹容:《革命军》,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41页。的鸿图大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且最复杂的革命样本”②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郭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中文版序言 (丘为君译)。,至为深刻而全面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整体命运和个体人生,且如巨海长江,淘洗了旧文化,复如洪炉大冶,炼试过新文学。中国的新文学史,不论如何“重写”,它都不能独立成章,必须还原到中国革命历史和意识形态竞争的真实行程,才能复现本相,获得解释。
革命话语自然不同于文学话语,然而在现代中国,革命话语影响甚至建构了文学话语。革命的征召和文学的应征,制造了一系列貌似缺乏想象力实则别有意味的理论和作品,譬如新文学史上的新写实主义。持续存在于1920年代之后约半个世纪的新写实主义文艺思潮,大抵可以分为左翼和右翼,它们基本不同的立场和政治目标与大致相同的渊源和话语结构,呈现了新文学史上革命思维、文学思维的某种必然性。
一
“新写实”是一个易致混淆的概念,因为在1980年代末期,也有盛极一时的新写实主义,甚至在80年代初期还有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新写实主义③璧华:《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论稿》,香港:当代文学研究社,1984年,序言。。不过,这类“新写实”只是时间序列上的即兴命名,指涉不妨模糊或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要新陈代谢新新不已即可。然而初见于20年代中国的新写实主义,则是一个特定的名词,在当年不仅是时间序列上的新,也是方法论上的新,其所导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三民主义写实主义,更是新文学史上的知名化石。
新写实主义源于苏联。1920年代中期,苏联的列夫派、岗位派、 “拉普”,以及布哈林、波格丹诺夫、沃隆斯基等人的理论表述,错综复杂地塑造了留苏理论家藏原惟人的文学观念。藏原惟人回到日本以后,因应日共政治斗争和日本左翼文艺的需要,遂提出新写实主义理论。秉承苏联影响,在论述无产阶级艺术的时候,藏原惟人认为,“艺术是把感情和思想‘社会化’的手段”,可用于“组织生活”,而“一切的艺术,在本质上,必然是 Agitation,是 Propaganda”,应当以无产阶级的“煽动艺术”、 “宣传艺术”向“意识落后的劳动者,农民,小市民等一切被压迫民众”传播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他也视无产阶级的艺术为现代生活的“记录”,并制定了两条“记录”原则:第一,描写要真实;第二,描写要正确。按理,无产阶级艺术如果旨在“宣传”、 “煽动”和“组织生活”、传播意识形态,则在逻辑上必然是追求效果而非追求真实,但藏原惟人却又要求无产阶级艺术“客观”、“真实”地“记录”,这就暗藏了理论的内在裂痕,甚至使他的“理论”不构成理论。描写的“正确”属于革命话语,而描写的“真实”则属于文学话语,如果遭遇“正确”则不“真实”或“真实”则不“正确”的情形,应当如何处置?对此,藏原惟人只用似乎不证自明的断言敷衍过去: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认识现实”,“没有粉饰现实的必要”,应当“无惧惮地描写”、“无虚伪地描写”①藏原惟人:《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和无产阶级》,《新写实主义论文集》,之本译,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第14页。。藏原惟人关于无产阶级艺术的“真实”和“正确”原则,实际上也是所谓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原则。
在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以前,是“和自然主义一同产生的”以“弗洛伴尔、龚果尔兄弟、左拉、都德、莫泊三”为代表的“布尔乔亚写实主义”或者“小布尔乔亚写实主义”,他们的写实主义可以称为旧写实主义。他们把生活“向人的生物本性,人的性格、遗传等还原”,而社会对人的影响和支配则不予考虑,“社会组织对于个人的压迫”也视而不见,即使有人注意到社会和阶级,也是强调阶级调和而非阶级斗争。与之相对,新写实主义则优先而明确地强调“阶级底观点”,并且是“站在战斗的普罗列塔利亚的立场”,而“普罗列塔利亚作家的主题”就是“普罗列塔利亚的阶级斗争”。藏原惟人也指出,普罗列塔利亚作家要从旧写实主义那里继承“对于现实的客观的态度”。于是,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即新写实主义的写作原则被确定为:“第一,用普罗列塔利亚前卫的眼观察世界;第二,用严正的写实者的态度描写出来。”②藏原惟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路》,《新写实主义论文集》,第33页。然而,“客观”、“严正”的写实态度如何可能?藏原惟人援用了苏联“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文学观念,以唯物辩证法观察世界,区分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表象,认为新写实主义应当把握“复杂无穷的社会现象中本质的东西”,以“前进”的观点去描写③藏原惟人:《再论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论文集》,第42页。——但在写作实践中,所谓“本质”和“前进”的观点,并非经验有限的作家本身所发现的,而是一种政治传达和意识形态规定,从而革命的“政治正确”主宰了“文学真实”。实际上,关于“正确”和“真实”的考察和判断,更多的是依靠意识形态的信仰和革命斗争的成效。
1928年,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述一完成便流入了中国。那时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惨遭曾经“容共”的国民党清洗,劫难之余,正在上海的地下和南方的山上收拾整顿,然而左翼文人却一反肃杀的革命低潮,在文学领域铁骑突出刀枪鸣。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的缔造者与甫从日本归国的冯乃超、李初梨等创造社后期成员编刊作文,鼓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之呼应,共产党人蒋光慈、钱杏邨等也组织太阳社,同样宣扬所谓普罗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人各有观点,忙于论争。然而当年中苏道阻,创造社和太阳社的理论资源大抵不是直接来自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苏联,而是取自日本左翼阵营,福本和夫、青野季吉、藏原惟人等人的观念即在那时被中国的革命文学家一概打包,浮海带回。
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理论最早是由太阳社成员译介的,譬如林伯修翻译的《到新写实主义之路》,便发表在《太阳月刊》 (1928年7月),而当时的蒋光慈、钱杏邨、林伯修等人的文学评论也持新写实主义观点,譬如论及无产阶级文学,林伯修认为“作家自身的生活应该普罗化”,以“把握到普罗的意识”,“应该细心地去接近及观察他所要描写的对象”④林伯修:《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海风周报》第12期,1929年3月。。普罗意识加普罗经验,正是对藏原惟人观念的适当解说。勺水认为“新写实派的作品,应该站在社会的及集团的观点上去描写”,“应该是和廿世纪的无产大众应有的人生观社会观相符合的东西”,“应该是一种光明的东西”①勺水:《论新写实主义》,《乐群月刊》第1卷第3期,1929年3月。——显然也是按照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的原则,以阶级意识的正确性和目的性去选择和展开,着眼未来,追求“光明”。不过,对新写实主义的“光明”追求,同为左翼作家的茅盾深不以为然:“掩藏了现实的黑暗,只想以将来的光明为掀动的手段”,这是“真的勇者”不屑为之的,应当“敢于凝视现实”,“真的有效的工作是要使人们透视过现实的丑恶而自己去认识人类伟大的将来,从而发生信赖”②茅盾:《写在〈野蔷薇〉的前面》,叶子铭编:《茅盾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49页。。坚定捍卫新写实主义的钱杏邨则以针锋相对的反驳回应了茅盾的批评③钱杏邨:《茅盾与现实》,《新流月报》1929年第4期。。
不过,新写实主义文学文本确有先天不足,“真实”受制于“正确”,个体经验服从于阶级观念,常导致叙述无法圆通合理,譬如《太阳月刊》停刊号上被太阳社认为是“很好的无产阶级文学”④《停刊宣言》,《太阳月刊》1928年第7期。,故事却破绽百出。《一尺天》写地下党员萧伯英的狱中斗争,作者似乎忘了小说前面曾说监号里也混有暗探,为了叙述的“正确”、“目的”和“光明”,隆重安排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真实身份犹恐不及的萧伯英串通众多暗藏的同志,在五一节同唱国际歌。诸多描写,向壁虚造不合情理,唯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阶级意识缭绕于字里行间。尽管如此,在整个1930年代,响应新写实主义的文字却越见其繁,有人从世界大格局谈到中国文学史,认为新写实主义是中国文学的必然趋势,有人纵论苏俄新写实主义的发展,有人提倡唯物辩证法指导之下的新写实主义诗歌⑤分别见张耿西:《中国文学的趋势与新写实主义》,《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2期,1930年4月;马仲殊:《苏俄新写实主义的发展》,《灯塔》1934年第1期。欧阳克:《新写实主义的诗歌与生活》,《文学》1937年第1期。,不一而足。
二
太阳社蒋光慈、钱杏邨、林伯修等人的论述,与其后的“左联”、周扬和毛泽东的声音,都处在同一条新写实主义的思想线索之上。“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其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也是在马列主义的框架下表述,有源自苏联和日本左翼的显著胎印,左翼的新写实主义,要求“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同时要和到现在为止的那些观念论,机械论,主观论,浪漫主义,粉饰主义,假的客观主义,标语口号主义的方法及文学批评斗争”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从“左联”认定文学“必须”服从、服务于“革命”、“任务”而论,其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偏重于“正确”,而新写实主义之所以“新”,全在于此。同时,“左联”虽然号召同“主观论”和“假的客观主义”做斗争,但其先验的“正确”规定或许是最大的“主观论”。
在“左联”,最具新写实主义理论家特征的,无疑是年轻的周扬。周扬的新写实主义阐述,深刻影响了左翼革命文艺阵营的风云变幻,并在权力的支持下长期决定着对“真实”和“正确”的理解。周扬对客观“真实”和政治“正确”的处理方式相当明快简洁,他将文学真实与政治真理直接视同一物,最“正确”的也就是最“客观”的。他以马列主义为无需证明的公理,然后在其理论基础上断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党派性绝不会妨碍“客观”,“因为无产阶级是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线,它的主观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行程是一致的”,“我们对于现实愈取无产阶级的,党派的态度,则我们愈近于客观的真理”——这是“拉普”和藏原惟人式的唯物辩证法表述,实际上把对马列主义的信念作为逻辑推论的起点,从而将政治“正确”与客观“真实”等同起来。周扬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阶级社会,在现实的中国,“能够最真实地反映现实,把握住客观真理的,只有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从而“无产阶级文学历史地优于过去一切文学”⑦周起应 (周扬):《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文学的真实性》,《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周扬反复强调的“无产阶级的主观和历史的客观行程一致”,实际上是当时左翼阵营的共识,譬如另一位左翼理论家冯雪峰就曾与之呼应,“要真实地全面地反映现实,把握客观的真理”,“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才能做到”①丹仁 (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和理论》,《现代》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周扬的文学观念是工具论的,认为文学“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同时,要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现实,即阶级斗争的客观的进行,也有彻底地把握无产阶级政治观点的必要”。在无产阶级的文学和革命领域,“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其差别,只是前者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不能代表政治正确的作品,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文学真实”。周扬以意识形态的信念缆绳,将无产阶级文学的真实性与无产阶级党派的政治性、正确性绑在一起,在新写实主义观念史上,看上去依然像是在向藏原惟人致敬。
新写实主义在藏原惟人和钱杏邨那里,除了意味着“正确”和“真实”,也曾意味着以“发展”的眼光看取现实,认为文学叙述应注目于光明的未来而非止步于黑暗的现在。193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亦是要求文学从尚不如意的现实地基上腾空而起,在对未来和理想的描写中展现出真理信念和乐观精神——显得“正确”。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新写实主义,它主张对“未完工的建筑物”做动态的发展的“艺术预测”,要写成“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而不是像“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者”或者旧写实主义者那样“用静止的眼光‘如实地’写”,只是写出一堆瓦砾②卢那察尔斯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5-59页。。在中国,周扬是较早注意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论家,他准确抓住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义,即“在发展中,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周扬认为,“只有不在表面的琐事 (details)中,而在本质的、典型的姿态中,去描写客观的现实,一面描写出种种否定的肯定的要素,一面阐明其中一贯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本质,把为人类更好的将来而斗争的精神,灌输给读者,这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③周起应:《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实际上,在当时的苏联和后来的中国,所谓“本质”和“典型”,都是政治话语,作家体认的“本质”和“典型”需要通过官方认定, “正确”的才是“本质”和“典型”,才能“灌输给读者”,实现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教育人民”的目的,这也正与藏原惟人“组织生活”的新写实主义思路一致。
延安时期,周扬的文学观念与毛泽东高度契合,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基本的理论思路实为周扬和既往左翼新写实主义观念的延伸、展开和深化。毛泽东同样认可“组织生活”的工具性路径,指出文学属于“文化战线”,应当“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既然视文学为工具,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文学是谁的工具?这就引出了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毛泽东不容置疑地认定“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立场问题又带出与之相关的“态度问题”:“歌颂”或者“暴露”。真实的情形是,可以“暴露”国统区,但不能“暴露”延安,“暴露”延安是旧写实主义的遗风,有被整肃的风险。“歌颂”延安则表明作家是以发展和光明的新写实主义态度融入了革命。
延安的作家大抵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于是特别强调让他们“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以此实现政治正确,重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真诚,使之写出“正确”的“真实”。
政治正确和文学真实、文学真实服从于政治正确,这是新写实主义的核心问题,毛泽东曾特别论述“文艺服从于政治”以及“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完全一致”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6页。的问题。毛泽东所谓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完全一致,与周扬30年代所谓的“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是基于同样的先验前提: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许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那个先验的前提似为政治信念而非科学结论。然而新写实主义的理论原则,“正确”、“真实”和“发展”的描写,在毛泽东、周扬等标志性人物的提倡之下,固结为此后数十年中国文艺思想领域不可置疑的天条,衍生出1950年代“新民歌运动”对“发展”和共产主义天堂的无根遐想,以及对“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提倡、对“写真实”论的打击——因为“写真实”不仅不够“浪漫”,而且有忽略“写正确”之嫌,不符合左翼新写实主义的传统。左翼新写实主义的发展渐趋极端,直至“文革”,阶级斗争反复无常的政治“正确”最终扼杀了文学“真实”,同时也扼杀了左翼新写实主义的传统本身。
三
左翼的理论传统告诉我们,新写实主义与旧写实主义的区别在于,它是从“正确”的观点和立场开始,抵达“真实”,然后又通过有倾向和有选择的“真实”叙述,止于“正确”。左翼的文学试验告诉我们,新写实主义并非“通往天堂路一条”。
新写实主义强调革命政治的正确性,以及文学叙述的真实性,“正确”立足于“真实”,“真实”服务于“正确”,呈现为一个“真实-正确”的理论结构,所谓写“发展”、写“光明”的未来,同样可以划入这个结构——因为在新写实主义的观念系统中,写“发展”和“光明”属于政治“正确”。“真实-正确”的理论结构本身是中性的,因此,国共双方,左右两翼,都可以利用,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各有各的“正确”而已。新写实主义的理论结构就是一辆出租车,共产党人去城东可以上,插一面旗子: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国民党人去城西也可以上,另插一面旗子:三民主义、国民革命。
在1930年代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下,两种意识形态的竞争全面展开,双方的战场不仅在江西和福建,也在哲学和文坛。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文学、左翼的新写实主义,必将“召唤”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文学、右翼的新写实主义——稍后的1929年,国民党全国宣传会议,以及胡汉民等,遂倡议建设三民主义文学①刘芦隐:《三民主义的文艺》,《中央党务月刊》第24期,1930年7月。,叶楚伧等人随后提出民族主义文学,以对抗左翼的普罗文学。不过三民主义文学思想的体系建构,直到1940年代才通过王集丛等人的系列论述大致实现。
在三民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相较于抛头露面的张道藩等党国要员,低调的王集丛才是切实研究理论的中坚,而王集丛最核心的文学观念,所谓民生史观的写实主义,便是国民党人的新写实主义。在《王集丛自选集》中,有一则小传写道:“‘九一八’前夜,中日关系紧张,而背叛国民革命遭到惨败的中共,在上海租界里,拉拢‘左翼作家’,搞‘普罗文学运动’,不少青年受其影响”,“王集丛亦注意其活动,但终有自己见地,不接受其宣传、引诱”②王集丛:《王集丛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第2页。。考究史实,小传的说法,或有可议之处。王集丛1930年左右的著译表明,他即便不是左翼作家,也是左翼文学的“同路人”,其辩证思维和文论格局,都有着深刻的左翼渊源和理论印记,而其民生史观的新写实主义,也与藏原惟人唯物辩证法的新写实主义脱不了干系。至于小传宣称的“不接受其宣传、引诱”,正如后来王集丛的选集几不选入其1930年代文字一样,应当是基于时势变易之后的政治考量。
王集丛曾就职于倾向左翼的辛垦书店,并于1930年在辛垦出版了译著《新兴艺术概论》,那是一部论文集,论文作者悉为日共或者日本左翼的理论家,即青野季吉、藏原惟人、田口宪一和本庄可宗。1931年,王集丛参与创办了辛垦书店的月刊《二十世纪》,在创刊号上,用笔名林子丛发表《艺术——其本质、其发生、其发展及其功用之理论的说明》,以左翼的阶级斗争理论批驳国民党人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如今翻检该刊,尚可以看到王集丛的文章中,多处的“民族”二字特意被“纳逊”字样覆盖,而多处的“阶级”字样则覆以“集团”二字,这从历史的远端透露了国民党书报检查制度和当年意识形态战争 (而非一般的竞争)的个中消息。至于王集丛在国共对峙的紧张空气中展开左翼写作,驳斥官方的文艺思想,其思想倾向似非“不接受”左翼的“宣传、引诱”所能解释。在《二十世纪》第二期,王集丛再以同一个笔名发表《艺术与科学》,其所参考的也是藏原惟人《再论新写实主义》等文章,并为新写实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辩护。此后,在左翼与苏汶等所谓“第三种人”的论争中,王集丛更以左翼新写实主义的观点批驳苏汶,认为“在目前,无产阶级是促进历史前进的主动力,他底主观的必要,是最适合于历史的客观的必要的,他不但不‘掩藏现实’,‘粉饰太平’,而且还要阐明现实之一切真伪”,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后的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还要解放全人类,消灭阶级,创造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现在苏联与中国的无产阶级阵营中底一切现象,有没有‘掩藏现实’,‘粉饰太平’,阻碍历史前进的地方,那是另一问题,即或有了,我们也只能说某种策略之不对,绝不能因之说无产阶级在本质上也有问题,拒绝其干涉文艺”①王集丛:《一年来中国文艺论战之总清算》,《读书杂志》增刊,1933年3月。。凡此种种,应当能够证明王集丛“接受”过“宣传”,其文论观念显然是左翼性质。至于王集丛后来提倡的民生史观的写实主义,同左翼的新写实主义比较,其结构上的“影响”关系也彰明昭著。
当然,在生活、时事、师友 (譬如叶青等人)以及自己的阅读和思考②王集丛:《关于青年读书的问题》,《朔望半月刊》第19、20期合刊,1934年2月1日。等的综合影响之下,至少是抗战开始以后,王集丛从左翼文人或至少是左翼的同路人、同情者,改弦易辙,一变而为右翼理论家,否决了他曾运用自如的阶级斗争理论,以三民主义之是非为是非。抗战时期他在《大路月刊》、《时代思潮》等刊物发表了大量有关三民主义文学、三民主义写实主义的文章,后又整理为《怎样建设三民主义文学》和《三民主义文学论》两书出版。遵循孙中山学说,王集丛一反数年前他所抱持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劳资两阶级对立的形势,因而也没有这种对立的意识”,“如果无产阶级文学是表现无产阶级意识的文学,那在中国就没有这种意识可表现,因而这文学也就不能建立”,至于此前中国的“普罗文学”,那是“引导文学走错误路线”。王集丛认为“中国文学需要正确的中心思想”,而在当时的中国,正确的思想“惟有三民主义”③王集丛:《三民主义文学论》,江西泰和:时代思潮社,1943年,第17-29页。。按照王集丛的归纳,在内容上,三民主义文学应有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全民精神和创造精神。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与左翼革命文学的精神类型一样,只是各“革”各的“命”而已。“科学精神”指向写实,“创造精神”意味着“组织生活”或者“创造新生活”——在原则上,大抵左右无别。王集丛特意提出所谓“全民精神”,是为取消左翼阶级斗争的合法性,强调三民主义文学是为“整个的民族”、“全体的人民”而非为某一个阶级服务④王集丛:《三民主义文学》,《大路月刊》第2、3期合刊,1942年5月。。“全民精神”后来成为国民党“文艺政策”的立论基础。
三民主义的写实主义,王集丛又称之为民生史观的写实主义,这既是援用孙中山学说以确立“正确思想”和“正确理想”,也是为了区隔于唯物辩证法的写实主义——同为新写实,有左右之别,国共之别,唯生唯物之别。在论述民生史观的写实主义之际,王集丛采用了与藏原惟人几乎一样的展开方式,只是在批评此前的各种写实主义的时候,特别增加了对左翼新写实主义的挞伐,而左翼的问题也不在其“写实”之“新”,而在其“主义”之阶级论。民生史观的写实主义,是“以写实为基本精神,为现实的人生服务,反对虚空的理想主义”,“由民生史观的见地”,“去描写现实的发展变化,宣传三民主义,奔放革命热情,反对机械的‘再现’观点和绝望的悲观倾向”,“由民生或全民的见地描写事物,刻画个性,反对个人主义和阶级主义”,“鼓吹互助团结以谋生存和促进社会进化的思想”,“反对阶级斗争”⑤王集丛:《论三民主义的创作态度——民生史观的写实主义》,《大路月刊》第1期,1942年3月。。显然,民生史观的写实主义同样秉承了左翼新写实主义的革命基因,持文学工具论,强调“正确”、“真实”和“发展”,只是它的“正确”是以三民主义为衡,它的“真实”是与阶级斗争对峙,它的“发展”则是指向孙中山所谓的“大同”而非马克思所说的“共产”。
抗战期间,三民主义的写实主义逐渐成为国民党文人的群体共识,譬如执笔《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的李辰冬,以及赵友培和刘镇涛,不少文人学者纷纷起而响应王集丛的论述。赵友培重视写实,更重视信仰,他甚至认为三民主义是宇宙间“真理之整体”,“任凭世界如何变动,人类如何进化”,三民主义“这与美相生之情,与善相成之法,与真共存之理,均可放之四海,传诸百世,如帛菽水火,永为人类所享用”,亦即,三民主义是普遍和永恒的真理。这与周扬关于“真理”的论述有相似之处,都是先验地认定各自持有的意识形态为绝对真理,以此断言各自的意识形态文艺理论即各自的新写实主义的绝对合法。在写实的问题上,赵友培主张以三民主义“乐观正直的态度”, “陈列出信仰、希望、幸福”,“运用一切光明面或黑暗面的题材,喜剧或悲剧的手法,表现人生的真实”,“并在表现人生的真实中,消灭苦闷与黑暗,启示快乐与光明”①赵友培:《三民主义文艺创作论》,重庆:正中书局,1944年,第105、114-116页。。这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风格要求几无差别。
刘镇涛提倡所谓三民主义的新写实主义,他认为“有不少人误认为新写实主义文学就是社会主义文学,这是非常不对的”,新写实主义“有其一般性”,本身无所谓左右,“它是一定的历史,一定的社会的产物,只要某个特定的社会到了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有了一个新社会的理想以后,新写实主义自然就依于客观的条件而产生”。刘镇涛参考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炼出新写实主义的一般特征:依照“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观”,写出“事实发展的本质,动的形态”,不仅写现实,也写理想,甚至“提出到达新理想的途径”。在刘镇涛看来,当时的世界上存在两种新写实主义,一是以苏联文学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新写实主义,“已经显示出无比伟大的力量”;一是“将以今后中国文学为代表”的三民主义的新写实主义②刘镇涛:《三民主义的新写实主义》,王集丛编:《三民主义文学论文选》,江西泰和:时代思潮社,1942年,第67-73页。。但他恪遵右翼的传统思维,认为阶级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适合于苏联,至于适合中国的,只能是三民主义的新写实主义——三民主义的正确决定了三民主义新写实主义的正确。
从王集丛到赵友培、刘镇涛,还有李辰冬(“文艺政策”)、张道藩(《三民主义文艺论》)和叶青(《三民主义与文学》)③叶青:《三民主义与文学》,《文艺创作》(台北)1953年第28期。等,关于民生史观的写实主义或者三民主义的新写实主义的论述,无不包括在“真实-正确”的新写实主义的结构之中,而在“正确”这一维度,又无不申说三民主义在当时中国为绝对之真理、唯一之真理,亦无不攻击阶级斗争理论之不合国情——凡此论议,莫不体现当年国共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不稍休息的警戒和竞争。
四
翻检故纸可以发现,中国的新写实主义的确从属于国共两党各自的革命政治话语而大致分流为二。不过也有例外,譬如1930年代一位叫做季权的学者就曾主张调和,企图兼顾三民主义与阶级斗争两种革命话语以及三民主义文学与普罗文学两种文学观念而走中道。只是在立场鲜明的革命时代无人响应,归于沉寂。
季权立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理论,他认为“在社会未到大同以前,阶级未能尽泯时,文学摆脱不了阶级的影响,超阶级的文学与超阶级的政党一样是存在不住的”。三民主义文学“合乎时代合乎社会”,但也不是超阶级的。三民主义文学不能超阶级是因为三民主义的革命及其革命政党本身不是超阶级的。有人坚持三民主义革命最重要的是民族革命,争取民族解放是“全民的”革命,“哪里需要什么阶级基础呢”,季权指出:“试问民权革命是革谁的命呢,封建的军阀和士大夫,那样的不惜卖国弄权,残杀民众,他们的民族意识在哪里呢”——显然,三民主义革命本身也可以包含阶级革命,因为革卖国残民的“封建军阀和士大夫”的命,就是阶级革命。“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不是滴水不漏的全民的革命,而是有阶级基础的”,其阶级基础便是“大多数民众的阶级,即是农工阶级”——在此,季权显然是要调和阶级理论和三民主义,而其观念的来源则是国民党一大宣言以及孙中山1924年之后关于三民主义和“扶助农工”的讲演。既然三民主义文艺的阶级基础是“农工阶级”,自然也不妨说“三民主义的文艺是农工阶级的文艺”,那么这样的文艺有什么任务呢?第一是“把握其正在萌芽的阶级意识,使之发扬滋长,以驱策其阶级意识的完成,而自动地革命,争利益和自由以立于主人翁的地位”,第二是“培植其民族意识,使之认识帝国主义和自己民族在世界所应占之地位及其使命”。“农工阶级的文艺,可立于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之上”,“阶级意识,可说是民权方面的”,“至于民生方面,则分包于民族和阶级意识之内,因为民生的被压迫,亦不外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①季权:《三民主义的文艺之社会的试解》,《夜光》1932年第3期。——于是,三民主义革命包括了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而三民主义文艺,自然便包括了普罗文艺。至于“写实”,自然也是介乎左右之间、国共之间的“新写实主义”。
然而,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兼跨左右的意识形态已无强人愿意维系而迅速崩溃,从此国共两党分别制定革命步骤的先后顺序,并确定各自革命的社会基础。而在社会动员方面,单一、简单的革命宣传自然比既要阶级解放又要民族解放的复杂革命宣传更有效率,而且也不至于让宣传对象一时之间无所适从。作为革命宣传的新写实主义,自然也就不能执两用中,要么是全民互助、三民主义的新写实主义,要么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新写实主义。两种革命的分裂是必然的,两种革命意识形态的竞争也是必然的,抗战时期虽然两党合作一致抗日,但是双方都在准备抗日之后的继续革命,至于抗战期间,虽然不能放手杀伐,但“同志仍须努力”于意识形态的竞争。写实主义的文学就是这样“新”起来的,“新”意味着政治的征召,意味着文学的归附,从传统现实主义描写的个体可控的、经验的、目前的真实,走向新写实主义的政治决定的、抽象的、发展的真实,从飘渺的审美的“无用”, “进步”为实在的、正确的“有用”。在新写实主义的历史上,所谓左右同源,不仅是指左右两种理论的源头都在苏联和日本,而且是指两种理论的表述和竞争都源于同样的革命政治思维和文学工具性思维。如果我们的目光看得更远,则会发现,在中国,“真实-正确”、“经验-政治”的思维路径本是古已有之,传承未绝②姜飞:《经验、真理与路径依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实际上,新写实主义,不论左右不论国共,不仅同源,而且同趋,趋于淡出。从普罗文学的新写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以至“文革”时期的文艺方针,海峡西岸的新写实主义文艺思想经由权力话语而迫使众多的文学从业人员追逐日新月异的革命政治,忙于“赶任务”,最后不知道自由、内心和创造是什么意思,筋疲力尽。海峡东岸在1949年以后,持续提倡“反共抗俄”的三民主义的写实主义、战斗文艺,然而制度不同,大部分作家相对自由,他们纷纷走上了现代主义和乡土文学的道路,导致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家们乏人追随,理论的鼓吹渐若游丝。如今,新文学史上的新写实主义大约是长睡不醒了吧,一时还不至于挺身坐起。革命的声音消散如尘,而图书馆里的《太阳》和《大路》,水侵虫蚀,已渐漫漶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