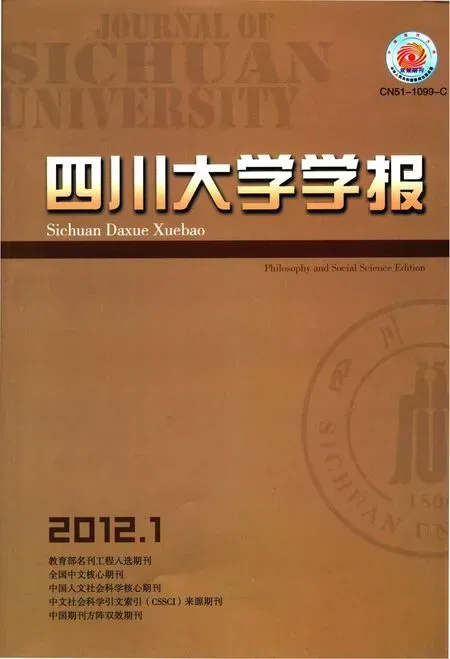中国符号学六十年
赵毅衡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一、中国符号学漫长的黎明
“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他自己参与创刊的上海《科学》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①吴宗济、赵新那编:《赵元任语言文学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78页。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在世界上也没有人做过。虽然索绪尔已经在1913年日内瓦大学的课堂上提出了semiologie,他的讲课笔记要到1916年他去世后才在瑞士洛桑出版,而引起学界注意,则要到1930年代。皮尔斯的semiotics学说生前没有发表,亦是30年代莫里斯进行系统介绍才广为人知。赵元任在此文中说,与他提出的“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词,可为symbolics、symbology、或symbolology,②吴宗济、赵新那编:《赵元任语言文学论集》,第177页。可见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
可能是因为发表于一本科学杂志,而五四中国知识界对文理科学术贯通不一定很敏感,赵元任此文在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要到2002年赵元任的语言学著作结集出版后,才有很少一些学者注意到此文③例如赵家新《赵元任与中国符号学研究》,《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吕丽贤:《赵元任与索绪尔之普通语言学和符号学对比研究》,《宜春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赵元任自己重新讨论符号学,要到四十年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几篇文章④赵元任:《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赵元任语言文学论集》,第877-889页。。只是“符号学”此词在中文中延续了下来,不像中文其他学科译名经常来自日语。日语的译名为“记号学”,至今有一部分中国学者,包括一部分台湾学者,坚持以“记号学”研究“符号”,或“符号学”研究“记号”⑤例如何秀煌:《记号学导论》,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学界做此种区分式定义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西方通用的“符号学”一词semiotics,与符号sign一词词根不同,而西方对符号学的定义就建立在此种不同上: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sign(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问)。实际上西语中此定义是用希腊词源“符号” (semeion)与拉丁词源“符号”(signum)的同义词作循环定义。中文没有必要跟西人转同义词圈子。笔者认为,中文译名为“符号”与“符号学”相当自然,而在中国,符号学完全可以定义为“关于意义的学说”①关于此定义的辨析,见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可惜,赵元任之后,此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最早对“符号学”的介绍,出现在五六十年代的语言学或哲学资料中。第一篇文字可能是周熙良1959年翻译的波亨斯基《论数理逻辑》,发表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59年7月号。1961年贾彦德、吴棠翻译,刊发于《语言学资料》1963年5月号的《苏联科学院文学与语言学部关于苏联语言学的迫切理论问题和发展前景的全体会议》一文,算是把此词正式化了。然而此阶段学界受到政治运动一潮接一潮的冲击,对偶然出现的“符号学”,学界连好奇心都不一定有,此后此词也果然在中国消失近二十年,不为人知。甚至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影响巨大的一些“内部批判材料”,例如1964年的《现代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论文选》,汇集了许多名家译文,却没有符号学的文章,也没有对符号学的批判:学界还没有认为符号学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中成气候的潮流。情况也的确如此:符号学当时在西方也只是在语言学中有一定影响。
符号学这个词再次出现于中文出版物中,要到1970年代末,依然仅仅出现于外国哲学语言学的翻译介绍之中。1978年方昌杰翻译著名学者利科对法国哲学的介绍文章,是符号学重现于中文的第一篇文字②李科尔:《现代法国哲学界的展望——特别是自从1950年之后》,方昌杰译,《哲学译丛》1978年第2期。。真正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的第一批文章,出现于1980年代早期,如胡壮麟、岑麒祥、徐志民、徐思益等学者纷纷著文介绍索绪尔学说③胡壮麟:《语用学》,《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3期;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当代语言学》1980年第1期;徐志民:《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复旦学报》1981年第S1期;潘庆云:《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显然此期的“符号学觉醒”集中于索绪尔语言学,关心者大致上也是语言学界的,这也正常,是在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课。而真正把符号学当作一门单独的学科来讨论,是我国著名东方学家金克木1963年在《读书》第五期上发表的《谈符号学》。这篇文章是印象式的漫谈,论点有点散乱,但却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拿出自己的观点来,不再是仅仅介绍国外理论,所以至今被论者引用。
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热”的迅速升温,国内学界对符号学的兴趣陡增,1985-1987年出现了一系列在各学科中运用符号学的文章④例如,安和居:《‘符号学’与文艺创作》,《文艺评论》1985年第1期;安迪:《短篇小说的符号学》,《文艺研究》1985年第10期;胡妙胜:《戏剧符号学导引》,《戏剧艺术》1986年第1期;艾定增:《运用建筑符号学的佳作:评西双版纳体育馆方案》,《建筑学报》1986年第7期;徐增敏:《电影符号与符号学》,《当代电影》1986年第8期;李幼蒸:《电影符号学概述》,《世界哲学年鉴》1986年第1期;周晓风:《朦胧诗与艺术规律:对于现代诗歌的一个符号学探讨》,《重庆师院学报》1987年第6期;曾大伟:《试论符号学理论与接受理论在教学上的应用》,《外国语》1988年第2期;郑伟波:《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中国翻译》1988年第1期;郭昀:《情报与符号:从大情报观看情报载体》,《情报科学》1988年第3期。,符号学呈现了跨学科的特征,覆盖面之广已经令人惊奇。此时也出现了一些对这门学科作总体介绍的文字⑤例如,毛丹青:《符号学的起源》,《哲学动态》1987年第3期;陈波:《符号学及其方法论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到这个十年将结束的时候,符号学在中国呈现爆发的形态,开始出现综合与汇流。1988年1月,李幼蒸、赵毅衡、张智庭等在北京召开了“京津地区符号学讨论会”,这是中国符号学界的第一次集会;同年12月,李先焜发表《符号学通俗讲座》(最后几讲由陈宗明负责)⑥连载于《逻辑与语言学习》1988年第6期-1989年第5期。。此时中国符号学的最早几本专著开始出版:林岗于的《符号·心理·文学》(1985)可能是我国第一本将符号学应用于文学研究的专著;接下来是何新将符号学应用于艺术研究的《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1987),以及俞建章、叶舒宪的《符号:语言与艺术》 (1988);肖峰的《从哲学看符号》(1989)可能是第一本符号学哲学专著;以后又出版了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 (1989)、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1990)⑦此书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的《文学新学科丛书》之一,1988年交稿后因特殊原因推迟到1990年出版。。
可以说,1980年代中期以后,符号学在中国已经相当繁荣,文科各科对符号学均有所探索。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早期对符号学感兴趣的多半是文学理论家,从上面的扫描可以看出,这个看法可能不够全面。或许我们可以指责说当时的研究深度不够,但不能说中国学界对符号学兴趣缺如。1988年美国符号学界的领军人物西比奥克讨论了世界上27个国家的符号学研究状况,唯独没有中国,他认为中国“缺乏足够的符号学机构和研究活动”①丁尔苏《符号学研究:东方与西方》,《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页。,他的错误判断似源自于信息不对称。
二、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纠缠
1980年代关于符号学的讨论,一大特点是与结构主义混杂在一起,两者不分。这实际上妨碍了符号学在中国的展开,到后来变成符号学界不得不花力气摆脱的一个纠缠。应当说,这种纠缠是世界符号学运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点,只不过中国符号学界认识到必须分成这两个概念时,时间稍微滞后了一点。
结构主义是符号学在学界掀起大潮时采取的第一个形态,中国学界1980年代讨论结构主义的文章,基本上把它当做符号学的同义词,两种文章都是从索绪尔原理与术语开始,只不过讨论范围比符号学的范围广一些,讨论结构主义时论及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拉康、戈尔德曼等人的思想,这些思想家现在不被视为符号学家。这一时期中文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以结构主义为题的文字远远超过讨论符号学的文字。1980年袁可嘉、王泰来等人已经开始相当系统地介绍结构主义。李幼蒸从1979年开始翻译研究结构主义,1981年写了《关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辨析》一文,基本上认为两者是同一个运动的两个不同名称②李幼蒸引用瓦尔的话来说明这两者的关联:“任何学科的任何部分,内容均可看作是结构主义的研究,只要它坚守能指-所指型的语言学系统,并从这一特殊系统取得其结构。”见李幼蒸:《结构和意义:人文科学跨学科认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第130页。。这个局面实际上不是中国学界搞错了,而是结构主义在1970年代尚未充分地走出结构主义阶段,即索绪尔语言学模式阶段。特伦斯·霍克斯出版于1977年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于1987年由瞿铁鹏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因为写得通俗易懂,在中国影响极大。佛克马与易布思同样作于1977年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1988年由林书武等翻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很受欢迎,其第一、二章用几乎占半本书的篇幅介绍结构主义,其中提到了“苏联符号学”,这也给人符号学从属于结构主义的印象。这几本书翻译成中文,比在西方出版滞后了十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1980年代在中国,这两者的确几乎是同义词。晚至1984年,也就是说与符号学在中国兴起大约同时,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大声疾呼要求推翻这个历史陈案:“霍克斯说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围相同,……这种对事实真相的误解大错特错。”③丁尔苏《符号学研究:东方与西方》,第7页。可见在西方1980年代,这种混淆依然是个问题,而且是继承皮尔斯衣钵的一些符号学家在大声疾呼要求澄清。最后是符号学本身的发展,才让符号学最终与结构主义脱钩。
中国的符号学长期搭载在结构主义的车上。这种情况对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很不利:符号学学科长期被结构主义所掩盖,以至于一些重要著作只讨论结构主义而不单独讨论符号学④可以举几本影响最大的书:从1983年第4期开始,张隆溪以“西方文论略览”为总标题,在《读书》上连续发表了11篇介绍现代西方文论的文章,其中以专论结构主义的居多,共有4篇。他讨论的结构主义,包括布拉格学派,也包括符号学与叙事学。王岳川1999年的《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以及他2008年的《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都有一节“结构主义符号学”;陈厚诚、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没有符号学,却有“结构主义”;朱立元、李钧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第一部分为“结构主义、符号学、叙述学”。。更重要的是,当结构主义在西方被宣布“过时”,被突破成后结构主义后,符号学本身的学术承继突然中断,以至于不少人认为符号学与结构主义一起过时了,或是认为皮尔斯的符号学与索绪尔没有相通之处。在追赶学术时髦潮流成为痼疾的中国学界,这个误会是致命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论者詹姆逊多次到中国讲学,在中国影响极大,但是他本人对符号学怀抱热情。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就是用格雷马斯符号方阵来解析《聊斋》中的“资本主义萌发因素”⑤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0-130页。。中国学生觉得是“结构主义残余”,为尊者讳而故意忽略,至今中国讨论詹姆逊思想的人多矣,没有人讨论他对符号学的贡献。
在西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索绪尔语言学模式的符号学,被皮尔斯的逻辑-修辞学模式符号学所替代。有西方论者甚至认为符号学发展到当代,索绪尔对符号学理论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only minor)①Winfried Noth,Handbook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p.64.。“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符号学近年的发展边缘化了,可谓大出意外,也可以看出当代符号学发展之迅疾。不过这种看法可能言过其实:索绪尔的许多观念,依然是符号学的出发原理。
20世纪大部分时期,虽然有莫里斯、米德等人的坚持,皮尔斯模式还是受到冷落。到1970年代,符号学界“重新发现”皮尔斯:西比奥克、艾科等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此种模式考量所有的符号类型,而不以语言学为模式。这个出发点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式、甚至非人类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符号的解释成为进一步表意的起点,由此打开系统,向无限衍义开放。而在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符号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中国成为符号学大国
1990年代的特点,是中国学者们静下心来读书研究,稳步前进。到了2000年后的新纪元,符号学在中国学界换挡加速。这一点很容易用数字证明,当然网上检索是片面的:很多文献实际上在用符号理论,从标题检索上却没有体现,而且符号学理论可以使用不同术语,也是无法简单通过检索数字统计的。如蒋荣昌《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广义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文本形态》,所使用的“广义语言学”,实际上就是“文化符号学”。因此,符号学实际应用面与量,恐怕比下面提供的数字还要大得多。
如果我们大致上把1980-1989算作中国符号学的第一个十年,1990-1999算作第二个十年,2000-2010算作第三个十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十年总共有符号学论文约两千篇,第二个十年大约发表论文近六千篇,而且每一年都在加速,到第三个十年终了的2010年,仅此年中国发表以“符号学”为主题的大约有近千篇,而题目中有“符号”两字的有近万篇,这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学界,每天刊出讨论符号学的论文近三篇,每天涉及符号讨论的论文近30篇②在中国知网 (CNKI)上进行检索:第一个十年,以“符号学”为主题进行检索,结果为277篇,以“符号”为主题进行检索,结果为2844篇;第二个十年,以“符号学”为主题进行检索,结果为863篇,以“符号”为主题进行检索,结果数为7120篇;第三个十年,以“符号学”为主题进行检索,结果为4228篇,以“符号”为主题进行检索,为49759篇。仅2010年一年当中,以“符号学”为主题进行检索,结果为863篇,以“符号”为主题进行检索,结果数为9098篇。参见胡易容:《中国符号学学科发展态势》,四川大学“符号学论坛”,2011年7月25日,http://www.semiotics.net.cn/news_show.asp·id=1326。。另据统计,中国大学近年开出的符号学课程,或是课程中包括符号学部分的,近100门③参见马文美:《中国符号学课程开设现状》,四川大学“符号学论坛”,2011年8月14日,http://www.semiotics.net.cn/news_show.asp?id=1321。。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可以说这是符号学在中国已经成为显学的明证。
1990年代以后的翻译活动异常活跃,索绪尔的《语言学概论》几种版本都翻译过来。巴尔特的著作已经全部翻译,广受欢迎,只是因为版权被不同的中国出版社买到,未能形成一套全集。格雷马斯与艾柯的著作大部分已经出版,有几本遗漏的正在被译出。各学科应用符号学的书籍,尤其是对当代文化进行符号学分析的书籍,翻译数量极大。把大量的翻译与专著一并考虑,这二十年中国出版的符号学著作大约四百多本,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有二十多本,每个月大约出版两本。其实到2010年后,符号学著作以每月三本的速度推出,好几个出版社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等),都在推出符号学翻译或专著系列,可见读者需要量之大。中国符号学运动,就规模而言,的确已经达到世界之最:中国已经成为符号学运动最为活跃的国家,符号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跨学科的显学。由此,本文以下的讨论,主要涉及的是专著。
四、中国符号学传统
我们首先要重视的不是数量,仔细分析一下中国学者在做的工作,在讨论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中国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介绍国外符号学者的说法,至多像1980年代那样点缀一些中国传统的符号学思想,而是开始提出中国学者自己形成体系的见解。我们可以着重讨论几个重要趋势:
首先是中国符号学传统的发掘。1980年代末中国学者眼光已经开始注视到中国自身的符号学传统,胡绳生、余卫国的《〈指物论〉,文化史上的第一篇符号学论文》①胡绳生、余卫国:《〈指物论〉,文化史上的第一篇符号学论文》,《宝鸡师院学报》1988年第3期。,是第一个讨论中国符号学传统的文章,此文对先秦名家的定位也很有意义,虽然准确与否可以讨论。1990年代这个工作就做得相当仔细了。1993年李先焜的《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许艾琼的《荀子正名理论的符号学意义》,1994年周文英的《〈易〉的符号学性质》,1996年李先焜的《〈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1997年高乐田的《〈说文解字〉中的符号学思想》等等,都是重要的开路之作。1995年苟志效、沈永有、袁锋的《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纲要》②苟志效、沈永有、袁锋:《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纲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虽然并不完美,却是第一次以专著形式对此课题作系统的讨论。此后,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的有王明居的《叩寂寞而求音——〈周易〉符号美学》(1999)、詹石窗的 《易学与道教符号揭谜》(2001),朱前鸿的《名家四子研究》 (2005)。2004年陈宗明的《符号世界》对中国符号学传统论述颇详;而张再林的《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2008)则提出独特的见解,把周易解释为身体符号与古人的生殖崇拜遗迹。
另外一个让全世界学者感兴趣,但是只有中国学者能说清楚的课题,是对汉字形成过程的符号学解读。在这个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陈宗明、孟华、申小龙等。陈宗明的《汉字符号学:一种特殊的文字编码》(2001),孟华的《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2004),是这个方面突出的成果。接近这个方向上的另一种引人注目的学术探索,是把符号学用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上,如齐效斌的《〈史记〉文化符号论》(1998),辛衍君的《意象空间:唐宋词意象的符号学解释》 (2007)。文一茗的《〈红楼梦〉叙述的符号自我》(2011)是符号学进入文学经典研究的最新尝试,值得注意。
另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开拓领域,是符号人类学。西方的人类学往往到偏僻的国外进行猎奇式的调查,中国人类学者经常就中国人本身进行研究,应当说中国学者的方向更有意义,更能避免“外来人”猎奇式观察的各种弊病。陈来生的《无形的锁链:神秘的中国禁忌文化》(1993),孙新周的《中国原始艺术的文化破译》(1998),都是早期的例子。文学人类学家叶舒宪的著作借道符号学,深入到中国古代精神世界,例如他的《中国古代神秘数字》 (1996)。当然中国人类学者也有把眼光投向少数民族的,如杨昌国的《符号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2000)。杜勤的《“三”的文化符号论》(1999),是其留日时的博士论文,是角度新颖的中西比较宗教学论著。
在用符号学整理中国思想上做出独特贡献的,是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台湾学者龚鹏程。他的《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2009),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做的北大演讲系列《文化符号学导论》(2005)是对中国传统语文学的一种全新的系统阐释。最近则有台湾学者周庆华的《语文符号学》(2011),在这条路子上继续探索。
就中国面广量大的符号学遗产而言,至今中国学界做的还远远不够。例如佛教 (尤其是唯识宗与禅宗)对中国思想影响极大,现象学界已经对此课题有相当的研究,但是符号学界至今尚未见到尝试;《易》被认为是人类第一个解释世界的符号体系,至今我们的研究远远不足;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式批评,至今尚未见到比较全面的符号诗学总结。
五、符号学理论的发展
19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对符号学理论的探讨更加深入。研读介绍西方符号理论家依然受到重视,但不少著作已经脱离了1980年代以猎奇为主调的介绍。中国学界向来对卡西尔与朗格的符号美学比较感兴趣,这可能是出于美学在中国学界的特殊地位。这方面的论著一直比较多,其成果近年有汇总的趋势,例如吴风的《艺术符号美学:苏珊·朗格符号美学研究》(2002)、谢冬冰的《表现性的符号形式》(2008)。对俄苏符号学的介绍,也有从三篇论文转向专著的趋势:曾军的《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2004),张杰、康澄的《结构文艺符号学》 (2004),王立业《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2006),为这个潮流作了系统化的总结,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依然不够。
介绍西方符号学时,索绪尔依然受到最大推崇,这可能与文献的相对齐备有关,近年专著有张绍杰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探索》(2004)、赵蓉晖的《索绪尔研究在中国》(2005);有些著作已能与国外学界比细究“第一手材料”,例如屠友祥对索绪尔笔记进行细致考证的《索绪尔手稿初检》(2011)。我国西学往往有大而化之不追求细节的毛病,似乎西学是客学,有用拿来即可,不必如中国古典那样锱铢必较地考证校勘。屠友祥的工作细致程度在中国很少见,却是一个良好开端。
对于布尔迪厄、博德利亚等人学说的介绍,一时热闹非常。评价布尔迪厄社会符号学的主要著作有高宣扬的《布迪厄的社会理论》(2004),张意的《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文化学导论》(2005),刘拥华的《布迪厄的终身问题》(2009)。评价博德利亚商品符号学的著作主要有仰海峰的《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2004),戴阿宝的《终结的力量:博德利亚前期思想研究》(2006),高亚春的《符号与象征:博德利亚消费社会批评理论研究》(2007),郑也夫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2007)。介绍这两位法国当代学者的著作之多,让人惊叹。此种巨大兴趣,来自中国学界对“解决”当代社会文化大问题的热衷,而不见得来自对法国符号学运动的推崇。
与此同时,中国符号学家开始有自己的符号学理论体系,出现了一系列符号学理论书籍:首先是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此书初版于1994年,再版于1997年,200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增补的第三版。这本长达八百多页的书,对自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符号学作了最详尽最系统的介绍,其最后一章则对符号学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做出展望。1999年孟华的《符号表达原理》、苟志效的《意义与符号》,2001年王铭玉的《符号学研究》,2004年黄新华、陈宗明主编的由中国符号学界八位学者合作的《符号学导论》,2008年郭鸿的《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等等著作,都在总体介绍的名义下,从不同的方位对符号学进行开拓发展。2011年赵毅衡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则在总结各家学说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个重在接受、重在文化制约作用的符号学体系。同时,符号学理论的建构,也开始落实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2002年齐效斌的《人的自我发展与符号形式的创造》提出了人的生存之符号本质;2006年李子荣的《作为方法原则的元语言理论》发展了雅克布森提出的文本元语言性;2008年韩丛耀的《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在发现》则试图在超越符号学的立场上发展一种图像表意理论。
语言学在中国始终是符号学最重要的基地,也是中国学者做出最多成绩的领域。2000年丁尔苏出版《语言的符号学》,2011年又出版了他在新世纪的符号学论文集《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2005年王铭玉的《语言符号学》被教育部指定为研究生用书。杨习良的《修辞符号学》则用符号学讨论语言修辞问题。语篇研究一直是语言学与符号学共同的领域,陈勇的《篇章符号学:理论与方法》(2010),则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理论符号学还有一个非常必要的方面,这就是对广大公众进行符号学的通俗讲解: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直接显露为符号,但是实际上很大部分由符号组成,人们往往对此不自觉。通俗符号学在这个方面为学者提供有意义的启示,也能帮助符号学拥抱生活。1992年王红旗的《生活中的神秘符号》,在1996年再版时改题为《符号之谜:生活中的神奇符号》;李伯聪的《高科技时代的符号世界》(2001)用符号学讲解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数字革命;有时候,符号学可以与广泛的日常生活相联系,陈丽卿的《职场仪礼:你的成功符号学》 (2010)提供了很有趣的启示:符号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六、应用符号学活跃
很多人认为符号学至今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这个误会来自两个方面:从国外来说,结构主义文学-符号学理论家如巴尔特、托多洛夫、格雷马斯等,都是文学理论研究出身,而他们的符号学影响极大;从国内来说,1980年代的方法论热首先从文学理论开始,当时的一些文科学科 (如新闻传播)尚在起步,正在作职业和技术训练,而中文系与英文系的学术气氛已经比较成熟。但是看一下1990年代以来的符号学专著,可以看到符号学的重点已经转向艺术、传播、影视、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非文学领域。不过,文学作为符号学的传统阵地并没有被放弃。周晓风继续坚持诗歌符号学研究,1995年出版了《现代诗歌符号美学》;2004年有邓齐平的《文字·生命·形式:符号学视野中的沈从文》; 2007年丁建新的《叙述的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模式》分析的对象是英语童话。在文艺学方面,2002年出版了巫汉祥的《文艺符号学新论》,2004年黄亚平的《典籍符号与权力话语》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判,用符号学阐发文学中的权力关系。
但艺术学现在已成为比文学更为重要的符号学领域。黄汉华的《抽象与原型:音乐符号论》(2005)是国内仅有的音乐符号学著作;臧策的文集《超隐喻与话语流变》(2006)是用符号学研究摄影;陆正兰的《歌词学》(2007)则用符号学研究流行歌曲。张振华的《第三丰碑:电影符号学综述》(1991),张讴的《电视符号与电视文化》(1994),袁立本的《演出符号学导论》(2010)则是中国符号学者在影视与戏剧等表演艺术方面的最早努力。戴志中等的《建筑创作构思解析——符号、象征、隐喻》 (2006)表明符号学在建筑艺术理论界受到欢迎。
传播研究领域与符号学的关系极其密切而复杂,甚至有学者认为传播学与符号学同一。翻开任何一本传播学教程,都会辟专章谈符号问题。如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经典之作《传播学概论》中就辟专章写“传播的符号”。目前,国内倾向于认同菲斯克对于传播学研究的二分法:过程学派与符号学派,前者以媒体实践为主要导向,后者则从传播文化学角度引入符号。中国学者对传播符号学贡献良多:李彬的《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2003),余志鸿的《传播符号学》 (2007),胡易容的《传播符号学: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2011),是其中令人注目的成果。
新闻是传播学理论首先必须实践的场所。刘智的《新闻文化与符号》(1999)是符号传播学应用于新闻的最早努力,此后陈力丹在这个领域作了大量工作,在他的传播学著作中,包括《传播学是什么》(2007)以及与闫伊默合著的《传播学纲要》(2007),符号学占有特殊地位。徐建华的《电视符号·广告论》(2004)、崔林的《电视新闻语言:模式·符号·叙事》(2009)则用传播符号学解释新闻实践。
广告是传播学各科目中最迫切需要理论讲解的科目。1997年吴文虎的《广告的符号世界》应当是中国在传媒领域中最早应用符号学的,而在广告分析上做出最大贡献的应当是李思屈(李杰),他的《东方智慧与符号消费——DIMT模式中的日本茶饮料广告》(2003)是做得非常仔细的案例分析和理论推导,2004年他还主持编写了《广告符号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近年来他的符号研究推向广义的文化创意产业,如《传媒产业化时代的审美心理》就是符号学方法论进行的个案研究的对象拓展。
社会学是对符号学适用性的最具体挑战:社会问题非常具体,往往很难容忍符号学的抽象思维方式,但符号学的可操作方式提供了一种比较普泛的理解方式。这方面的成绩,有苟志效与陈创生合著的《从符号的观点看:一种关于社会文化现象的符号学阐释》 (2003),卢德平的《青年文化的符号学阐释》(2007)。台湾学者林信华的《社会符号学》(2011)则试图用中西汇通的方式处理社会符号学问题。
在数量极大的中国符号学著作中,我们还遇到一些“半文科”的科目,如经济、营销、设计、商标、法律、逻辑、计算语言,甚至生物、生理等等,但是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打住,科学和逻辑的符号学,当然是符号学的重要方面,但不是人文社科的符号研究所能处理的,除非我们把它们人文化,例如把生物符号学转化为生态符号学。用符号学把科学技术问题人文化,这方面的工作西方学者做了不少,在中国尚不多见。
七、结语:前程展望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符号学在中国,如同在世界上一样,正在迅速兴起为显学①近年叙述学在中国兴旺,有不少人认为符号学不如叙述学那样容易传开。实际上符号学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规模已经超过叙述学。用“百度”搜索:“符号学”一词达180万条,“叙述学”与其另一种说法“叙事学”合起来626000条,仅为“符号学”的三分之一。用比较学术的“百度文库”搜索:“符号学”近九千条,而“叙述学”、“叙事学”合起来三千多条,比例差亦同。西文方面,差别更大:用Google Scholar,以及Google Books分别搜索Semiotics与Narratology,或搜索Semiologie与Narratologie:符号学始终比叙述学稳定地多八倍。为什么我们感觉上似乎叙述学更普及?可能的原因是叙述学适合中文系与英文系的教学研究,针对性较强,而符号学的应用面遍及整个文科,研习者散于各系科。正因如此,用符号学理论集合这个学科,更为重要。。我们应当说,从数量上看,的确如此:中国目前产生的符号学论文与专著,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而国际符号学学界也日益注意到,世界符号学的重心有可能向东方迁移②Yiheng Zhao,“The Fate of Semiotics in China”,Semiotica,Issue 184,2011,pp.271-278.。只要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即把数量变成质量,把“中文的符号学”变成“中国符号学”。这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问题。纵观中国符号学界三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应当说有几个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本文在此坦白指出,以期引起同行们的讨论。
首先,很多作者总共只写了一本符号学书籍,往往是他们的博士论文 (诚然博士论文是他们写得最用心、最有锐气的著作),许多有才能的青年学者,在写出大放异彩的论文后,再无第二部符号学著作,就此从符号学界消失。这不是因为他们忽然对符号学失去了兴趣,或是不愿意深入研究符号学问题,相当大的原因是到了高校任教后,大部分教师 (尤其是青年教师),不得不教“概论性课程”,例如文学概论、影视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文化批评理论、传播理论,哪怕开出的“概论课”往往无特色,重复过多,学生从本科到博士要反复学几次。学科体制的分割,很难自我突破,不太允许教师开“符号学影视理论”、“符号学传播理论”这样的课。中国的大学完全可以让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有各自不同的教学和研究重点。过于死板的教学和研究分科,严重妨碍了研究人才成长。
第二个大问题是我国高校的学科划分,大半是五六十年代划定的陈旧的条条块块,而符号学的跨学科性质,很难归入任何一块,使他们进退失据。例如中国至今没有“文化研究”这科目,因为这科目“太新”,成为学术重点“不过”二十多年,而文化研究则是符号学最重要的用武之地。学了符号学,写了符号学的论文,进行了这个方向的研究,就业时却被抱怨“不对口”,“没有此专业”而遭拒绝,这已经是全国符号学学生的噩梦。目前符号学的研究分散在哲学、传播学、影视研究、文艺学、语言学、人类学等许多学科,学科多样化本应当是符号学作为文科总方法论的优势所在,但是在科层化的体制中,却落入无所归属的困境。
第三个问题是符号学的专业刊物付诸阙如。中国的刊物之多,为世界之最,但是因为从1950年代继承下来的体制原因,大部分文科刊物是包揽大学文科全部科目的“学报”类刊物,为了照顾各种学科的发表需要,选题极分散。符号学文章得到发表,往往是由于刊物编辑个人的兴趣,成为偶一为之的题目。至今中国只有两个符号学刊物,一是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出版的英文刊物Chinese Semiotics,二是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出版的《符号与传媒》,这两种刊物都没有新闻出版总署给予的刊号,作者在上面发表的文章都不能算“学术成果”。正因为此,相当多符号学的交流活动集中到网上,例如四川大学办的“符号学论坛”。做学问固然要不计名利,得不到承认总是令人丧气的事。
1990年代以来,全国开了近三十次符号学会议。三个符号学学会——全国语言与符号学会、全国逻辑符号学学会、全国哲学符号学学会——基本上每隔两三年举行一次集会。大规模的集会有: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浙江大学在杭州召开的“符号学与人文科学学科方法学术研究会”,同年武汉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东亚符号学国际会议”;2003年四川大学举行的“比较符号学讨论会”;2004年7月在里昂举行的“中西比较符号学圆桌会议”;2005年北京社会科学联合会举行的“符号学与人文科学国际讨论会”;2007年社科院哲学所举行的“全国语言逻辑与符号学叙述会议暨庆贺李先焜教授80华诞学术讨论会”等等。在专业会议上发表的演讲本来是同行直接切磋的成果,但是在中国,大部分这种会议甚至没有兴趣印出会议论文集,因为论文集上发表的文章在目前高校体制中不算学术成果,从而使这些会议重要性大打折扣。不过,这些应当说只是局部性问题,不会成为中国符号学向前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符号学的进展迄今已经取得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1988年在“京津符号学座谈会”上,笔者所做关于符号学运动现状的报告,大致上只能介绍国外的发展①《京津符号学座谈会在京举行》,《哲学动态》1988年第4期。;1994年苟志效写了《中国符号学五年的发展》②苟志效:《回顾与展望——中国符号学研究5年》,《哲学动态》1994年第3期。;2002年王铭玉写了《中国符号学二十年》③王铭玉:《中国符号学20年》;《外国语》2003年第1期。。笔者这篇小文,算是延续他们的努力。从中可以看到,符号学在中国学者们的集体努力下一步步成长起来。
现代符号学近百年来,经过一系列学派的竞争更替,经过各国学者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一门比较成熟而系统的学科。在符号学理论的应用过程中,不断有新的问题暴露出来,新的疆界不断被拓展。中国学者在这个学科中极为活跃,虽然西方符号学界成绩斐然,中国学界并没有“鹦鹉学舌”,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用中国传统的符号学遗产补充符号学理论体系,在符号学发展前沿上提出新的体系。
符号学的繁荣,是当代文化的需要。最近二十多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剧变,当代文化迅速冲进一个“高度符号化时代”:符号生产与消费已经远远超过物质消费。我们对这一局面及其重大历史后果,至今没有充分的理解;我们对当代社会符号生产和消费的规律,至今没有认真的研究和争辩。在社会各阶层的对抗中,在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冲突中,对“符号权”的争夺,越来越超过其他实力宰制权的争夺。无论我们是关心人类的命运,还是只想弄懂我们在各自生活中的幸福与苦恼,不理解符号,就无法弄清我们落在什么境地,就无法理解过去,无法看透现在,更无法把握将来。因此,这个小小的综述有权利,也有必要,以一个乐观的前瞻作结: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将是符号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