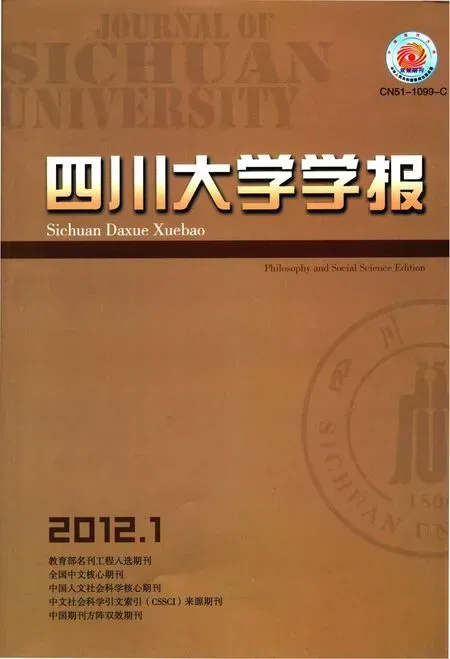韩少功 《山南水北》的乡土世界
魏美玲
(台湾岭东科技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台湾 台中 )
1985年韩少功发表的《文学的根》被视为寻根文学的宣言。寻根思潮的萌发正值西方文化思想、文学作品大量被引进中国之际,作家们急于向西方取经,倾向于横向移植与模仿,有志之士忧心因此丧失民族文化精神,失去文学的独创性,于是兴起文化寻根意识。韩少功强调“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①韩少功:《文学的根》,《在后台的后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74页。。必须扎根乡土,才能写出可与世界对话的作品。出身于湖南的韩少功探寻的文学之根指向绚丽的楚文化,以期将奇丽、神秘、狂放、幽默深广的文化因子融入创作之中②林伟平:《文学和人格──访作家韩少功》,《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收录于廖述务:《韩少功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64页。。认同寻根理念的作家各有不同的文化根基和艺术思维,形成多元的寻根面向③陈思和分析“文化寻根”意识,大致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一,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 (如阿城的《棋王》等);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 (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但也渗透了现代意识的某些特征 (如韩少功的《爸爸爸》)。见陈思和:《当代大陆文学史教程》,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63页。。韩少功“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人的思维和审美优势”,透过寻根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精神,使积弱不振的民族振衰起敝,以期能“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建树一种东方的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思维和审美体系”④韩少功:《东方的寻找和重造》,《在后台的后台》,第279、281页。。韩少功为寻根许下的宏愿,与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遥相呼应。因此其实践理念的《爸爸爸》、《女女女》自然着重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接续鲁迅剖析民族劣根性的启蒙话语。
在《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中,呈现了一个闭塞、神秘、野蛮、荒诞的乡土世界,其间痴呆、愚昧、疯癫、丑怪的人物,打冤、放蛊、唱简、杀牛占卜、吹南风助孕等奇风异俗,营造出由人退化至非人、由文明退化至蛮荒的诡谲怪异气氛。有论者以为在这些“寻根文学”的经典作品中,“读到的不是韩少功所谓的‘绚丽的楚文化’,而恰恰是一个需要被改造的落后的丑陋的文化‘异类’”①杨庆祥:《韩少功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宿命──以〈山南水北〉为讨论起点》,《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2期。。考察韩少功的初衷,“改造”正是其寻根的根源之一,但辽远、荒诞的乡土世界确乎和“绚丽的楚文化”有所落差。在取材和主题上,亦引起“使创作纷纷潜入僻远、原始、蛮荒的地域和生活形态,而忽略对现实社会人生问题和矛盾的揭示”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1页。的质疑。
韩少功1996年发表的《马桥词典》以其知青时代插队的农村为书写原型,采取诠释方言土语的词典方式,铺写当地历史、传说、地理、风俗、物产及各色人物故事,以叙事者插队下乡的年代为主体,向上追溯至明末,向下延伸到改革开放以后,着重描述1970年代的马桥社会,建构一个具体的乡土世界,从而展示民间意识与民俗文化。《马桥词典》及《暗示》(2002)审视民间社会的目光较《爸爸爸》等寻根之作更为温厚,收起冷峻的笔锋,对底层人们的苦难有批判也有同情,有沉思也有欣赏。
2000年,韩少功再度下乡,回到知青时代逃离的农村,在离当年插队的农村不远的汨罗市八景乡安家。他辞去了《天涯》杂志社社长一职,却辞不了海南文联主席的工作,有关单位特别给他安排了每年有半年的创作假③参见孔见:《韩少功评传》,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于是他便如候鸟般,过着半年在汨罗农村、半年在海南海口大城的生活。2006年出版的《山南水北》是其乡居六年的生活随笔,记录了“对乡村新生活的观察、倾听、感受、思考以及玄想幻觉”④韩少功:《山南水北·香港版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为数九十九篇的散文题材涉及山水、草木犬鸟、乡野传说、奇人异事、城乡对比、劳动感悟和个人的生命记忆。韩少功以“阶段性下乡”来界定自己的归田园居,他表示:“阶段性地住在乡下,能亲近山水,亲近动物和植物,……最重要的是,换个地方还能接触文学圈以外的生活,接触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取一些原生性的智慧和情感。”⑤韩少功:《穿行在海岛和山乡之间——答〈深圳商报〉记者、评论家王樽》,最初发表于2004年《深圳商报》和香港《文学世纪》,收录于韩少功《大题小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46页。
《山南水北》是韩少功重新扎根乡土的作品,王尧称之为“新寻根文学”,杨庆祥视之为“再寻根”。韩少功则认为此作是“向更大世界开放,是向生活中更多植物、动物、人物的接近和叩问”⑥王尧认为《山南水北》可以称为“新寻根文学”。他引述韩少功所批评的“史学基本上是帝王史、文献史、政治史,但缺少了生态史、生活史;换句话说,只有上层史,缺少底层史,对大多数人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生存状态,缺少了解和把握”,认为《山南水北》在今天的语境中其重要意义或许就在这里。参见王尧:《〈山南水北〉:新寻根文学》,《错落的时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31页。杨庆祥《韩少功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宿命──以〈山南水北〉为讨论起点》一文认为:“‘寻根’本来是为了寻找一个足够强大的可以救赎整个民族的文化,最后却回到了‘批判国民性’的老路子上了,这些寻根者们对于这些文化的态度却停留在‘五四’的水平上,文化的确认再一次成为文化的批判”,“因为‘寻根’的这种‘未完成性’,实际上可以说‘寻根文学’之后有一个‘再寻根’,而韩少功,无疑是这一个‘再寻根’的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山南水北》只有置于这样一个历史的链条中才凸显出其不一般的意义。”韩少功:《〈山南水北〉再版后记》,2007年11月,《山南水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312页。。从逃离农村到回归乡土, 《山南水北》确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时隔三十年,韩少功体察的乡土世界呈现何种面貌?现代乡村蕴含哪些原生性智慧和情感?这些乡土思维于新时代有何特殊意义?《山南水北》与其过往的乡土书写又有何异同?本论文拟透过文本剖析及作家的书写历程探讨上述问题。
一、朴实中见才智
韩少功曾表示:“因为《爸爸爸》等作品,我被理解成一个批判者,但批判之外的同情或赞赏,可能就无法抵达读者那里。”⑦芳菲:《理想的、或非理想的生活——对话韩少功〉,原载2007年《南方周末》。原载2007年《南方周末》。收录于《山南水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91页。而在《山南水北》里,作者的理性思辨依然不减,但很显然其笔下乡土人物的亮度增加了,农村的色彩丰富了,对于田园的劳动生活更是充满赏爱之情,同情或赞赏超越了批判之声。
《山南水北》里的乡下人,较之韩少功以往所书写的农村人物,毋宁是可亲可爱得多了。例如剃匠何师傅是继承传统技艺的能人,一把剃刀宛如微型的“青龙偃月刀”,在颈部、鼻梁、眼皮、耳窝或刮或弹或剔,“关公拖刀”、“张飞打鼓”、“双龙出水”等寓含历史传说的刀法名目,彰显技艺的精湛与神奇。一套刀法下来,顾客气脉贯通、精血涌跃,俨然有净化身心、康健养生之效。何剃匠不随流俗,拒绝染烫,即使门前冷落,依然笃守古道。他艺高且义重,一生只理光头的老顾客三明爹许久未上门,何剃匠便翻过两个山岭前去探望,发现三明爹仅存一息,于是返家取刀,为老友做最后的服务,使完了全部的绝活,三明爹舒服得长长吁出一口气:“贼娘养的好过呀。兄弟,我这一辈子抓泥捧土,脚吃了亏,手吃了亏,肚子也吃了亏咧。搭伴你,就是脑壳没有吃亏。我这个脑壳,来世……还是你的。”①韩少功:《山南水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以下出于本书的引文页码标于行文中。顶上的舒坦使悲苦的人生有了些许的安慰,粗直的言语是出自肺腑的至高感谢,不但此生受用,还要许来生的脑袋,这无疑是对剃匠最真诚最深切的赞美。
传统技艺之外,新兴的行业更增添农村能人的现代光彩。《卫星佬》里的毛伢子在杀猪的本业之外兼营安装卫星电视天线,杀猪佬成了卫星佬,出入于传统与现代、原始与科技之间,由行业的转换道出乡下能人的识时通变与奇才异能。卫星佬没有监测器、钻孔机、定向仪、译码器、手提电脑等先进设备,也无专家、厂家可供咨询,一辆破旧摩托车载着铝皮锅,深入山乡小径。 “他们既不需要定向仪,也不需要用量角器,只是抬抬头,看看太阳的位置,甚至是太阳在云中可能的位置,把一口铝皮锅左挪一下,右旋两下,再踹它三两脚”(第99页),很快就校准卫星方向;取用断砖废石砌底座,以可乐罐罩住高频头来防雨,在在可见纯朴本色与巧思;对于各种译码参数、卫星名目也烂熟于心,一双巧手让全国各地、港、澳、台,以及东南亚的、中东的、欧美的节目迅速跃上农村的电视屏幕,效率犹胜城里的专业技师团队。科技时代下的草根智慧,着实令人赞叹。同样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炮手华子,只有小学学历,炸石修路,精准过人。“每次打炮眼,他事先围着目标走一走,抠块石头捏一捏,撒泡尿,挠挠脑袋,就能定出最刁的打眼角度,打出恰到好处的深度。……因此他用药少,炸掉的石方反而多,溅出去的石片还不怎么伤田和伤树”(第229页),虽然不用仪器探测,没有精密的计算,却能以朴实的方式评估周围的地质水土,抓准角度,减少炸药,把对自然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
生活越贴近大地、贴近山林,越能体会自然的力量,挖土机师傅老应身上便显现对自然的谦卑态度。在紧临悬崖的坍塌山路赶工,只靠一边履带着地,另一边履带悬空,借挖瓢抓住坡上的树蔸,减轻车体重力,巧妙地保持平衡,宛如表演高空杂技般把挖土机开过险路。尽管艺高人胆大,老应深知自然变幻无常,风险难测,为了表示对山灵的虔敬,他不食山中动物,自觉因此得到感应,一有凶险,则胃痛示警。某次在山里修路,听到奇怪的鸟叫声,眼皮跳,胃也痛,觉得大事不好,示意众人快逃,不一会,土石崩落,山体垮塌,协助修路而置身其中的韩少功,以《也认识了老应》一文记叙这段带着神秘色彩的能人奇事,不可解的超自然现象,使人们对神灵产生更强烈的敬畏心理。
奇诡神秘的楚文化一向为韩少功所津津乐道。《山南水北》中的《村口疯树》和《马桥词典》中的《枫鬼》都描述了成精成怪的枫树。《枫鬼》传说树精喜欢恶作剧,把挂在低枝的竹笠移至树头;树瘤一遇狂风大雨便幻化为人形,暗长数尺;画过这两棵树的马鸣右手剧痛三日不敢再造次。《村口疯树》里,村中有丧事则“树哭”,有人拿斧锯逼近则“树吼”,杀猪的满四爹锯树而死,复原军人则因砍树发疯。二文的枫树最后都在官方破除迷信的指示下被砍伐。《枫鬼》里,被砍下的大树做成公社礼堂的排椅,于礼堂开过几次会后,附近十几个村寨流行起搔痒症,传言是枫鬼发“枫癣”报复。 《村口疯树》则在惊心动魄的人树大战中,一位民兵的右脚被砸成肉泥,“领头的庆长子倒是没事。他事后夸耀,他那天略施小计,穿了个半边衣,有一只空袖子吊来甩去,看上去像是有三只手。树神就算是记恨他,但往后到哪里去找有三只手的人?为了让树神放过他,从那以后,他每次出门还把蓑衣倒着穿,或者把帽子反着戴,让宿敌无法认别。得罪了老枫树的后生们也都学他,后来经常把蓑衣和草帽不按规矩穿戴,甚至把两只鞋子也故意穿反,把两只袜子故意套在手上,把妇女的花头巾故意缠在头上,给这个山村带来一些特殊景象”(第42页)。破除迷信的执行者,反成了迷信的代言人,无力违抗官威,又惧怕树神报复,于是搬演一出与神斗智的闹剧。相较于《枫鬼》,《村口疯树》深化了纯朴的民间思维与活泼的想象力,忧心树神降祸的庆长子,以原始思维观照神的世界,藉变装混淆树神的辨识①高丙中论及:人们砍伐成片树林和大树时尤其慎重。人们相信它们是树神之所在,砍伐它们,就有一个避免树神怪罪自己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仪式大致有三类。其一,通过祭祀讨好神,获得神的宽宥和许可。其二,用巫术对付神,使其不能加害于人。其三,通过转移责任而逃避责任,使树神没有加害伐木者的充分道理,有转移主谋人、造成受人指使的假象两种做法。参见氏著《中国民俗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0-51页。,成功的经验引来许多仿效者,各出创意表演滑稽的变装秀。村民们敬神畏神又欺神,在谐谑的气氛中展现素朴的民间心理,于笑闹中见天真,谐趣中见巧智,反常中见恒常的民间信仰。
二、蛮悍与义理
楚地古有荆蛮之称。《蛮师傅》里参与修路的工人自称“蛮电工、蛮木工、蛮砌匠、蛮司机”,进行工程既无测量也无设计,他们的“蛮”不是漠视科学,对工程设计一无所知,“只是手里少了钱,就没法去懂,只能装不懂”,与其空谈坐等,永远不能成事,不如勇往直前、尽力而为,看似“蛮干”的背后有着缺乏资源的无奈。集合众人的“蛮力”,终于开路有成,这群“蛮人”实亦彰显了强悍的生命力。
蛮气在权威面前则体现出勇于抗争的特性。《各种抗税理由》引出“不服周”一词说明楚地的民风:“‘不服周’,这是流行于湖南、湖北一带的俗语,意思是不服强,不服官,不服权威。‘周’指周天子。当年战国列强当中,惟有楚国未得周天子赐封,也不要周天子赐封,属于自立旗号闹革命,是谓‘不服周’。”违抗权威、抵拒官方的意念化为集体潜意识深入民间,源自祖先的生活经验和思维方式不着痕迹地留存于后人。所以猪婆没阉好要抗税;少分几口救灾矿泉水要抗税;路边茅草太长,野猪闯入猪圈,母猪生了一窝只会捣乱的杂种猪,都成为抗税的理由。面对农民千奇百怪的理由,地方干部大叹:“八溪峒是出‘粮子’的地方,不但出过红军的粮子,也出过白军和土匪的粮子。民性刁滑而且蛮横。不是吃铳药长大的,就是肚子里长了三个脔心,做事总是‘不服周’。”(第252页)
《气死屈原》一文也以古证今。村干部发展观光,设路卡向游客收费,农民未蒙其利,认为干部假富民以利己,千方百计劝阻游客上门,抨击景点不足观者有之,以肉价衬托票价不合理者有之,还有人索性带游客走小路避收费,连乡干部骗钱的话也出笼了,你一言,我一语,以狂欢的姿态对抗权威,众声喧哗的一幕充满嘉年华式的笑闹光影,嘲弄、戏谑的话语表现民间文化的反叛精神,颠覆高高在上的官方权威。外人视此地民风纯朴可爱,乡干部则对此气愤难平:“屈原为什么早不死晚不死,跑到了这个地方就死?”“屈原是个湖北佬,怎么死在这里?他当大官走南闯北,哪里不能死?怎么偏偏在汩罗投江?事情太明白了,他肯定是被这里的老百姓气死的,把八辈子的血都吐光了” (第202页)。把民之刁蛮上溯到二千多年前,以同理心对屈原之死做出新解,足见蛮悍民风之源深流长。面对蛮悍民众向公权力挑战,领导的智慧往往是行政成败的关键。《开会》记叙贺乡长宣布禁止买码(一种类似六合彩的私彩)的政令,民众反弹声浪排山倒海而来,群起拍桌大骂贺麻子,场面失控之际,贺乡长怒气冲冲拍桌责问“哪个骂娘”,由委屈、不平斥责辱亲取得道德形象,进而以正义凛然之姿推动政令,最后赢得群众鼓掌叹服。贺乡长反常而合道的奇智,切合乡人单纯的思考逻辑,孝亲、善道、正义连成一线,由情入理,获得民心的归向,于其中亦可见蛮悍雄强且重孝道义理的民间精神。
有情有义的民风亦见于《老逃同志》。一个战争年代留下来的失忆逃兵,忠厚本分地在村里住了四十年,中风瘫痪后,村长老杨找木匠做了可卧可坐可抬的床,立下全村轮流照顾的规矩,不知乡里、没有亲眷的无名逃兵吃了两年多的百家饭,在村人的服侍下得到善终。村长结合传统的“天道”思想和社会主义精神,带领村人以情义来实现“孤寡残疾都有所养”的大同世界。《非法法也》则由法律之外的“潜规则”呈显民间义理。一场职灾意外死了两名电工,村人咬定供电公司应负全责,实则明白另有肇事者,但追查真相,依法究责,对方无力赔偿,受害者家属得不到实质补偿,肇事者家庭也会陷于苦难。基于“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的信念,“村民不约而同不假思索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何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第179页)。在蛮不讲理的作为中寻出理来,让村人立于义理的一方,理直气壮地在法律之外遵循“潜规则”以安顿民生,维持乡土秩序。
三、神巫信仰
《山南水北》的乡土社会是一个充满泛灵论的世界。仰赖农作维持生计的乡下人,将禾谷瓜菜视为“有情”物。想要谷米质量好,耕耨施肥之外还要唱歌养禾,“尤其是唱情歌,跟下粪一样。你不唱,田里的谷米就不甜” (第249页)。要使每棵桔树都能果实累累,农妇指点着对它们多讲讲话,尤其“要一碗水端平么──你对它们没好脸色,它们就活得没有劲头了”。关怀、赞美的语言化为果树的成长激素,若偏心不公,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果树失去活力,便会降低生产力。还有“对瓜果的花蕾切不可指指点点,否则它们就会烂心;发现了植物受孕了也不能明说,只能远远地低声告人,否则它们就会气死”。孕育新生命的植物宛如娇羞刚烈的女子。另外,植物也会争风吃醋耍性子,“据说油菜结籽的时候,主人切不可轻言赞美猪油和茶油,否则油菜就会气得空壳率大增”。至于“楠竹冒笋的时候,主人也切不可轻言破篾编席一类竹艺,否则竹笋一害怕,就会呆死过去,即使已经冒出泥土,也会黑心烂根”(第52页)。草木皆兵的心理已至杯弓蛇影之境,丰富的联想力令人惊叹。这些来自农家的言说,将喜怒哀乐爱恶欲各种情绪投射到草木身上,坚信它们也是有情识的生命,赖其供养的人类必须善待植物,才能确保劳动过程平顺,获得期待中的好收成。根植于生活经验的生产信念,是源于物我不分的原始思维,于神灵信仰中传达尊重生命的态度。
至于动物与人的互动更是神奇。有能辨明宿敌脚步声的聪明青蛙,听到善捕者靠近就噤声不语(《智蛙》);有比人还要知书达礼的牛,不吃邻家的庄稼,自行到远处觅食(《邻家有女》);有不满主人夸奖狗大哥,急于猎鼠表功的猫小弟(《猫狗之缘》)。狗更是富有灵性,在山村里被叫做“呵子”(《山中异犬》),贤爹家的狗娘翻过两座山到未曾去过的狗崽家送兔肉;茶盘砚的呵子们,见贼就开咬,看见客人则衔树枝表示友善;有福家的呵子不待吩咐,不畏风雨,看守主人的财物,有福在县城遭遇车祸时,家中呵子似有感应,“疯了似的大叫,冲到公路上去见汽车就吠……对一切流动的钢铁盒子大举进攻”而惨死车下,众人认为这只忠义的狗以死挡煞,被汽车撞飞一丈多远的有福之所以没死没落个终身残疾,是因为呵子拿自己的命换了主人的命。有福把呵子葬在山上,说自己以后也要葬在那里。人犬之间的情义,成为山乡的传奇。
万物有灵的信念也包含无生物,甚至人类感官难以辨识的无形生命。例如《寻找主人的船》里那艘老是自行脱锚的船,漂荡在湖心,彷佛在寻找已逝的旧主人;《无形来客》记叙狗儿对着空无一人的院门狂吠,令人思索无形生命的存在;《瞬间白日》则惊见夜晚突然切换成白天,虽然只持续两三秒就消失,难以解释的异常天象,激发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对于贴近大地的乡下人而言,风雨雷电、山林川泽、旱涝无常,处处有不测的凶险,时时存在生存的考验,许多民俗信仰与禁忌因应而生。
即使在现代社会,乡下人仍意识到“既然科学不能管理一切,他们当然就需要科学以外更多的什么”(第88页)。于是入山前要举行“和山”仪式,焚香向山神求恕和感恩。而上山打猎,伤生见血,得在三天前就开始“藏身”,“其具体作法是不照镜,不外出,不见人,不秽语,连放屁也得憋住,连屙屎屙尿也得蹑手蹑脚。遇到别人打招呼,必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决不应答回话。更严格的‘藏身’之术还包括不行房事,不发言语,夜不点灯,餐不上桌……不一而足。其目的无非是暂时人间蒸发,逃过山神的耳目,有点像特种兵潜入伏击区的味道”(第89页)。《藏身入山》里为了避免被山神怪罪,举行特殊的仪式,获得隐身的魔力,这种躲避侦测的做法和《村口疯树》的变装欺瞒十分类近,反映了畏惧神灵降祸的心理及积极的因应作为。对自己施行巫术以得到神秘力量,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原始民族的思维①几乎在所有原始民族中,都有此类的巫术行动。猎人在临近出发狩猎的日子里必须戒房事,留意自己的梦,净身,持斋,或者只吃某些食物,以一定方式来装饰自己和给自己的身体涂色,为的是对所希望捕获的猎物产生神秘影响力。见列维-布留尔 (Lucien Levy-Bruhl):《原始思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37-239页。。
施行巫术的风俗在《船老板》中表现更为具体。李有根是个业余萨满,开船之外兼看风水,还懂一些小方术。为了帮农妇把受惊数日不归的鸡引进鸡窝,便取废纸点火,嘴里念念有词,原本四处奔逃的母鸡竟乖乖入埘。《山南水北》记叙的玄怪奇事多来自乡人的传说,但此段作者以现场记录呈现,并说:“如果我不是在现场目睹,如果这件事只是传说,我撞破脑袋也不会相信。但这的确是事实,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第87页)对于种种巫术、风水、命理,李有根辩说:“你以为这迷信?明明是科学,条条都是有书对的!”民间的巫术或超自然力量,是不是“传统科学所忽略的科学”(第85页),或许还需要人们虚心发掘其中的奥秘。
《山南水北》饱含民间魅力的自然传奇,揭示乡土社会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透过乡下人对动植物的观察、理解与互动,召唤现代人重建人与大地的亲密关系,怀着敬畏自然的谦卑之心,学习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四、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农村
以当前农村作为书写主体的《山南水北》,呈现新世纪农村及农民的新貌。在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下,许多人把西化等同于现代化,等同于进步、富裕的表征,于是有农民穿着西装挑粪、打柴、撒网、喂猪,无视于衣服的剪裁妨碍劳动的灵活度,西装“普及到绝大多数青壮年男人”,成了一种乡村“准制服”。脚上穿的鞋也是如此,“哪怕是一位老农,出门也经常踏一双皮鞋——尽管皮鞋蒙有尘灰甚至猪粪,破旧得象一只只咸鱼”(第25页)。不仅衣着西化,一幢幢矗立在乡间的洋楼,彷佛成为富裕的标志。但是楼房无处烧柴取暖、养猪圈牛、堆放农具和谷物,于是在洋房旁搭个偏棚作为居室,洋房则成为豪华仓库。明知洋房不实用,乡民还是一边抱怨一边盖房,甚至为此背负巨债,因为“新楼至少有一条好处──主人从此做得起人了。按照八溪峒的潜规则,一旦过了温饱线,脸面的幸福就比皮肉的幸福更要紧”(第213页)。因为爱面子,背离实际生活需求与能力,盲目地在形式上追求现代化,产生许多荒诞、变形的怪现象。
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贫富差距拉大,农民劳而少得,为了改善家境,农村劳动人口大量流向城市,许多青壮年外出打工,“去广东、浙江、福建等以前很少听说的地方,过年也不一定回家,留下的人影便日渐稀少。山里更显得寂静和冷落了。很多屋场只剩下几个闲坐的老人,还有在学校里周末才回家的孩子。更有些屋场家家闭户,野草封掩了道路,野藤爬上了木柱,忙碌的老鼠和兔子见人也不躲避” (第16页)。冷落荒凉的景象呈显乡村人口结构改变的严重问题。原本因气候宜人吸引外乡女子嫁入的山峒,也开始“变得白喜事 (丧事)多而红喜事 (婚事)少”,不爱下田、恋慕繁华的女子纷纷离乡进城,性别失衡使峒里的后生人心浮动,于是一些已婚的江西女人来此找男人“寻副业”,彼此“似婚非婚,似姘非姘,似娼非娼,似友非友”(第208页),甚至有“带着老公出嫁”,二夫一妻的怪现象。此外,《天上的爱情》叙述侄儿到广东打工,叔叔与侄媳发生了不伦恋;《寻找主人的船》则是进城赚钱的妻子带野老倌回家,眼看着“那男人替他老婆挑指头里的刺,吹眼睛里的灰”,不知如何是好的丈夫只好去抓鸡杀鸡。村人因此嘲笑他:“丈夫丈夫,起码要管一丈远吧,你如何一条门坎都没守住?”(第155页)城市的恶德渗入淳朴的乡下,尊严尽失的丈夫,在乡里间抬不起头来。而《口碑之疑》里的花花公子式的丈夫,“靠老婆在外打工,盖了全村第一豪宅,还把手机、MP3、数码相机什么的都玩遍了,只是从没摸过扁担和粪桶,从不知自家菜地在哪里”。洋房、手机等文明产物,让贪安好逸之徒乐于出卖妻子,无穷无尽的物质欲望造成人性异化、伦理崩解,在功利思想侵入下,乡下的淳朴之风也大受影响。
结语
农村是韩少功文学的原乡,他在新世纪之初再度回归田园,有人把他比作陶渊明,有人联想到19世纪美国的梭罗,也有人视之为现代隐者①龚政文《从〈山南水北〉看韩少功的人生取向与艺术追求》(《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析论:韩少功批判都市,但不拒绝文明;回归自然,但绝非成为隐者;置身民间,但不认同愚昧。。虽然身居乡村,但韩少功并无隐居之念②韩少功在《〈山南水北〉再版后记》中对于“隐居”、“归隐”、“隐士”之类的评语提出响应,表示自己“只是阶段性下乡,而且有电话和宽带同世界相联,能‘隐’到哪里去?真正的隐士是无法被发现的,更不会出版作品自我暴露”。。他曾比较陶渊明和梁漱溟:“陶渊明为官场不容,只好到农村待一待,但这种挫折也许成就了他。梁漱溟不是这样的。他更有担当,是主动关切多数人的命运。单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梁漱溟更可贵,更应成为我们的楷模。”③芳菲:《理想的、或非理想的生活──对话韩少功》,《山南水北》,第293页。梁漱溟建设乡村的思想与作为,显然是韩少功所要追随的典范。所以在晴耕雨读之外,他参与乡里修路工程,协助地方发展竹业加工、建立绿色瓜菜基地、开发观光旅游,想为农村脱贫尽一己之力。对于半乡半城、阶段性下乡的生活,他在《〈山南水北〉再版后记》中表示:“与其说出世,不如说入世。与其说退避,不如说进发。”其“入世”与“进发”,并不局限于参与农村的事务,最重要的天地当然还是在于创作。
韩少功在《山南水北·香港版序》中说,《山南水北》是他“时隔三十年后对乡村的一次重新补课,或者是以现代都市人的身份与土地的一次重新对话”,既然是“补课”,则显示过往对乡村的认知有所遮蔽或误解。从《山南水北》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作者的理性沉思,也仍存在对现实的批判,但其审视农村的目光更为温厚可亲,批判中隐含理解与同情,以往常见的沉重笔调,也为山水之间的抒情与民间言说的谐趣所取代。其所呈现的乡土社会不再偏重于闭塞、狭隘、愚昧、无知、迷信、丑陋的一面,而是发扬民间朴实中见才智,野蛮中见雄强,狂放中有情义的民族性。此外,“以现代都市人的身份与土地的一次重新对话”的意念,揭示《山南水北》的另一个面向。透过向植物、动物、人物的亲近与叩问,引领读者进入存有原始思维的乡土世界。以“信奉科学的教徒”(第85页)自视的韩少功,意不在呼吁世人回归信神好巫的原始社会,而是由神神怪怪的民俗事象与民间信仰透视民族文化心理,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
现代科技文明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富裕便利的生活,却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面对科技文明所带来的生存的危机,韩少功试图透过与土地的对话,探索原始思维背后的自然生态观,召唤现代人重修自然这门课。将《山南水北》诸多神神怪怪的故事,置于此一架构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现代意义:学习乡下人对自然的敬畏谦卑之心,对万物的尊重关爱之情,人与自然才能和谐共生。1980年代中期阿城即曾以《树王》演绎自然伦理主题,然彼时大陆改革开放方兴,且砍伐山林改造自然仅为“文革”一时之狂举,人与大地的关系未有剧变,自然环境未蒙巨创。由上个世纪末至新世纪初,已然见到工业科技、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之弊与自然生态危机,韩少功以《山南水北》探索原生态文化,既有所承,亦有其独特的时代意义。
寻根时期的韩少功,接续鲁迅剖析民族劣根性的启蒙话语,着重批判闭塞的乡土与传统文化,到了《山南水北》的新寻根,则趋向沈从文发扬乡土人性之美,探求原生态的智慧与情感。韩少功重新贴近大地,扎根民间,于乡土世界补上文明反思的一课,从启蒙批判到向民间学习,或许是全人类应反思的文化课题。
——《革命后记》初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