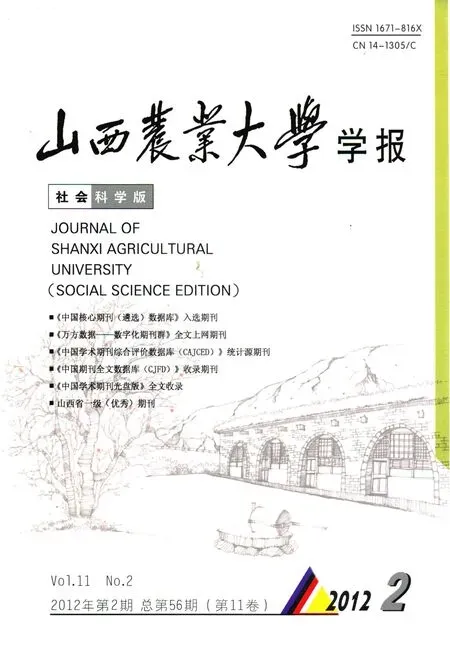《 宠儿》中宠儿的替罪羊形象研究
刀喊英
(厦门理工学院外语系,福建厦门361024)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 《宠儿》诉说的是一个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宠儿免受奴隶制迫害的命运,在看到奴隶主前来抓捕时,用锯子锯断女儿脖子致其死亡的悲惨故事。小说围绕母亲杀婴事件,通过不同人物视角把 “杀婴”事件的来龙去脉层层展开。随着故事的展开,美国奴隶制的罪恶也逐步得到彰显。综观整部小说,可以发现替罪羊机制贯穿小说始终。“替罪羊”一词源自《圣经·旧约》,具有献祭之羊和替罪之羊两个象征意义。“从犹太教祭祀仪式意义上讲,替罪羊是祭祀羔羊的名称,亚伯拉罕将自己的罪孽转嫁到替罪羊身上,由此除去不幸;从社会意义上讲,替罪羊是指为他人的过错承担责任的人。”[1]替罪羊后来泛指替人受过者。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勒内·吉拉尔在他的著作 《替罪羊》一书中精辟地把对替罪羊的迫害归为四类范式:“第一类范式,即一种社会和文化危机的描写,一种普遍的混乱;第二类范式,即 ‘混乱者’①作为认为用 “捣乱者”这个译文化 “混乱者”更适合,故下文都用 “捣乱者”替代 “混乱者”。的罪行;第三类范式,即这些被指控犯罪的嫌疑者是否有被选定的特殊标记;第四类范式,即暴力本身。”[2]用吉拉尔的替罪羊机制分析 《宠儿》,发现宠儿就是奴隶制下黑人社区的替罪羊。小说围绕母亲 “杀婴”事件前因后果的书写便是对吉拉尔归纳的对替罪羊迫害的四个范式的回应。
一、奴隶制——社会和文化危机、社会普遍混乱的导火索
奴隶制导致了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在奴隶制下,黑人沦为终生服役的奴隶,逐步被剥夺了各种权利,并且实行隔离,被固定在奴隶的位置上。“黑人奴隶一无所有,剩下的仅是其作为主人财产的身份,法律地位类似于 ‘物’。”[3]就是说奴隶只被看做奴隶主的 “财产”,而非“人”,只能当做 “财产”才保护,不会当做“人”来对待,而财产又是可以随意支配的,奴隶的命运也如此被随意支配。此外,奴隶身份是遗传的。弗吉尼亚1662年12月通过法律规定:“所有在该地出生的孩子是奴隶还是自由人,仅仅依据母亲的情况而定。”[3]这就意味着,黑奴女性所生的孩子一律沦为奴隶,奴隶制因此可以被奴隶的后代复制而延续下去。1669年以后,在弗吉尼亚,“当被主人纠正或根据主人的命令纠正时如果一个奴隶 ‘突然死亡’不再构成重罪行”。[3]这样的立法很快普及开来。从此,黑人奴隶连最基本的生命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在越演越烈的的奴隶主残酷剥削与奴隶不堪被剥削的社会危机下,无法忍受的黑奴只有逃跑才可能获得自由。但是猎奴者的存在,加上奴隶主有权捉回逃跑奴隶的法规注定了黑奴悲剧命运的不断上演:逃跑的黑人或被虐杀或被转卖,也因此导致黑人家庭妻离子散。
《宠儿》的小说背景是奴隶制肆虐的美国南方社会。奴隶制的暴行在不同章节,经由不同人物视角得到了具体阐释。在 “甜蜜之家”,塞丝他们被当做动物,他们的身体特征被定义为动物属性。保罗·D目睹黑奴 “被租用,被出借,被购入,被送还,被储存,被抵押,被赢得被偷被抢夺”。[4]逃跑的黑奴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他们躺山洞,与猫头鹰争食;偷吃猪食;白天睡树上,夜里赶路;“他们把身体埋进泥浆,跳到井里,躲开管理员、袭击手、刽子手、退役兵、山民、武装队和寻欢作乐的人们”。[4]黑人获得人生自由后,他们不再作为奴隶主的 “财产”受到“保护”,因此白人的歧视和迫害反而加剧。比奴隶制时代更严重的种族仇恨、歧视、残暴的私刑在南方社会弥漫。黑人被禁止使用公共交通,被债务和肮脏的 “罪犯档案”追逐。到了1874年,“白人依然无法无天,整城整城地清除黑人;仅在肯塔基,一年里就有八十七人被私刑处死;四所黑人学校被焚毁;成人像孩子一样挨打;孩子像成人一样挨打;黑人妇女被轮奸;财物被掠走,脖子被折断”。[4]这个种族冲突激烈,奴隶制猖獗的社会时时隐藏着社会危机,这个危机导致黑奴不断伺机逃跑,而白人千万百计残暴追捕。在逃跑和追捕之间的权力冲突中,黑人与白人的矛盾加剧,造就美国南方严重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危机就是勒内·吉拉尔替罪羊机制的第一类范式。这样的社会危机最终导致了塞丝亲手锯断孩子的脖子,以避免孩子遗传其奴隶身份,重蹈悲惨的奴隶生活这样的极端行为。宠儿也就成了种族冲突的牺牲品,奴隶制的替罪羊。
二、还魂报复—— “捣乱者”的罪行
集体对替罪羊的迫害总是基于对 “捣乱者”犯下的罪行的指控,指控的罪状是多种多样的,吉拉尔归纳出如下三类:“首先是指控嫌疑分子用暴力侵犯他人,侵犯最高权力机构的象征人——国王、父亲,或者侵犯手无寸铁的弱者,特别是儿童,这些人是罪大恶极的祸首。其次是性犯罪,强奸、乱伦、兽行,最经常被指控的是那些违背习俗的、最严格的禁忌的行为。最后是宗教犯罪,如亵渎圣物,那同样是违反最严厉的禁忌的行为。”[2]在现代小说中,被指控为 “捣乱者”所犯下的罪行有渐趋缓和的趋势。被选做替罪羊的 “捣乱者”的破坏行为既没有神话中指控“捣乱者”所说的罪大恶极,也不一定侵犯了最高权力机构的象征,或是亵渎圣物,犯了宗教犯罪这样严厉的禁忌行为。然而 “捣乱者”对普通人的报复和破坏行为又是确实存在的,因此说报复塞丝就是宠儿被选为替罪羊的罪状。她的报复和破坏行为具体表现在:她的鬼魂扰乱塞丝的家庭,让124号充斥恶意和她的怨毒,逼走两个哥哥,加速奶奶贝比·萨格斯的绝望和死亡。她在124号闹鬼加深社区黑人对124号的隔离和冷漠。她唤起塞丝对过去奴隶生活的痛苦回忆,导致塞丝终日活在对 “杀婴”行为的不断忏悔中,神志不清,丢掉工作,断了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她在林中空地用手掐住塞丝的脖子,险些掐死母亲。她把母亲的情人保罗·D逼到冷藏室,勾引他上床,犯下了乱伦之罪,最终把他从母亲身边赶走,加剧了塞丝情感上的孤独。这个家庭食物短缺,塞丝和宠儿又处于半疯癫状态,一个拼命赎罪,一个拼命指责,另一个却无能为力,生活和精神几乎崩溃。宠儿的鬼魂侵犯的是已经被黑人社区孤立的可怜的母亲和妹妹,而还魂人身之后试图掐死自己的母亲,并引诱母亲的情人,犯下乱伦之罪。她的这些 “罪行”不仅破坏着塞丝的家庭,还提醒着社区黑人过去那些不堪的奴隶历史记忆,是个十足的 “捣乱者”,足以引起社区黑人的愤怒。
三、黑奴女性——被选定为受难者的特殊标记
对替罪羊的选择存在一定的标准,虽然每个社会选择的标准相对不同,但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在迫害者的选择中,不是罪状起首要作用,而是受害者属于特别易受迫害的种族……人种和宗教的少数派往往引起多数派攻击,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不歧视少数民族和所有不合群、独特的小团体。”[2]种族主义者所宣称的白人优越论将黑人理所当然地圈定在 “异常”的境地。宠儿的黑人身份无疑就是其 “异常”于白人的标志,而她的女性身份又使她成为黑人男性的 “异类”,成为她被选定为受难者的标记。塞丝杀婴其实是将死亡视为彻底解脱宠儿奴隶命运的机遇,杀死宠儿的凶手其实是白人推行的奴隶制,宠儿因此成了奴隶制的替罪羊。
勒内·吉拉尔指出:“社会存在着一种异常……社会的 ‘平均数’被认定为社会的 ‘正常’。从社会最正常的位置朝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的偏离越远,受迫害的危险越大。”[2]所以,“异常”是社会选择替罪羊的首要标准。还魂人身的宠儿身上也具备这些 “异常”特征:她是水中来的外乡人、十八九岁了依然像婴儿一样的举止、没有纹路的手、贪婪、任性和记忆往事的超能力都成为她的罪名。小说中 “黑人社区奴隶制余毒肆虐,黑人饱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像塞丝、保罗·D、贝比·萨格斯、斯坦普等很多前黑奴都无法摆脱奴隶制压迫的痛苦记忆,历史阴影使他们及其后代无法正常生活。无法摆脱的历史重负在黑人群体中转化为内部精神危机。”[5]此时已沦为奴隶制牺牲品的宠儿还魂报复无异于提醒黑人社区,他们所遭受的精神危机并没有化解,还在社区中反复上演。摆脱奴隶制残余的渴望迫使黑人社区采取行动阻止这一切。社区黑人认定宠儿吞噬了塞丝的生命、破坏塞丝的生活,就把他们的精神危机指向宠儿。 “每当发生危机之际,集体或多数派常常对个体或少数派施以迫害,以保护自身的利益并建立新一轮的秩序与和谐,他们或者以集体暴力的形式对替罪羊进行围猎,或者在群情激昂的舆论鼓动下将替罪羊放逐。”[6]于是,社区妇女在艾拉的带领下自发集会,披着救助宠儿和丹芙的正义外衣,30个黑人女性浩浩荡荡地聚集到塞丝家驱逐宠儿。宠儿被当做黑人社区的替罪羊,背负黑人社区的所有苦难,遭到集体的驱逐。替罪羊除了承载苦难,还暗含着救赎的希望。“实际上,是宠儿的出现使塞丝、保罗·D及其他前黑奴直面历史伤痕,最终获得精神上的救赎。”[5]因为身为奴隶制牺牲品的宠儿其实就是她们自己,当她们面对宠儿时,其实面对的也是她们自己不堪的现在和过往,通过这个直面,通过驱逐宠儿,也就驱逐了她们身上的过去,他们像忘记一场噩梦一样忘记了宠儿,也慢慢选择忘记了奴隶制留下的精神创伤,黑人社区在忘记她的同时也慢慢恢复了秩序和平静。
四、杀婴、集体驱逐——暴力本身
莫里森把 《宠儿》置于美国南方19世纪六、七十年代奴隶制余孽尚存,种族歧视与暴力冲突仍然激烈的社会背景之中。林肯宣布1863年1月1日起,奴隶制被废除,奴隶永获自由,联邦政府也承认奴隶的自由。可是到了小说开始的1873年,奴隶制的余孽仍然严重。在莫里森的作品中,种族歧视使人们强烈的爱和扭曲的恨产生碰撞,暴力冲突因此不可避免。《宠儿》中的暴力场面很多,如保罗·D脚带脚镣开矿时经历的种种暴力;西克索逃跑失败被烧烤和枪杀;塞丝的后背硬生生被划开等。可以说,奴隶制就是暴力的摇篮。宠儿沦为替罪羊的暴力场面也由不同人物的视角有不同的描述。斯坦普·沛德认为塞丝像翱翔的老鹰飞起来掠走自己的孩子,脸上像长了喙,手像爪子一样将她的三个孩子抓牢:一个扛在肩上,一个夹在腋下,被她一路吼着地走进了只有锯子的木棚屋,于是惨剧上演。以学校老师为首的白人视角这样描述:“两个男孩在一个女黑鬼脚下的锯末和尘土里流血,女黑鬼用一只手将一个血淋淋的孩子搂在胸前,另一只手抓着一个婴儿的脚跟。她根本不看他们,只顾把婴儿摔向墙板,没有撞着,又在做第二次尝试。”[4]锯子是实施暴力的工具。塞丝锯婴的暴力理由却是:“我不能让那一切都回到从前,我也不能让她或者他们任何一个在 ‘学校老师’手底下活着。那已经一去不返了。”[4]逼近124号枪支武装的奴隶主、猎奴者和警察是塞丝施暴杀婴的导火索。可以说,这些全副武装的白人也是迫使宠儿成为奴隶制替罪羊的暴力本身。而社区黑人驱赶宠儿的场面也充满了暴力:30位黑人女性自发集聚缓缓地朝124号走来,跪下来歌唱、祈祷和吼叫。当神志不清的塞丝手拿冰锥冲向爱德华·鲍德温,以防再次失去宠儿时,几个黑女人都冲上去抓住她,场面混乱。在群情激昂的吼声中宠儿最终消失了。具备 “异常”特质的宠儿作为背负奴隶制和奴隶制遗毒对黑人的精神毒害被选定为替罪羊,最终遭到驱逐,以实现社区黑人的精神净化。
弗莱指出:“替罪羊既不是无辜的,也不是有罪的。说他无辜是指他所得到的报应远远超过他所做的任何过失,好比登山运动员,他的喊声竟引来了一场雪崩。说他有罪则指他是有罪恶的社会的一个成员,或者他生活在一个不公正已成为存在本身无法回避的一部分的世界上。”[7]他还指出:“执著于对某位个人进行社会报复的主题(不管他可能是多么大的一个恶棍)只会使此人显得罪过较轻,而社会显得罪过较重。”[7]莫里森借助替罪羊原型,通过对塞丝杀婴事件的叙述,以及这个婴儿还魂人身对其母亲的报复,最后遭到黑人社区驱赶的事件的描写,塑造了宠儿的替罪羊形象,深刻揭示了奴隶制对黑人的身心摧残和施行奴隶制的美国种族主义的罪恶本质。
[1]梁志健.莫里森 《天堂》中的 “替罪羊”形象 [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151-155.
[2]勒内·吉拉尔著.冯寿农译.替罪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29,18,21,22.
[3]张红菊.美国南部黑人奴隶制的形成及特点[J].广西社会科学,2005(6):137-140.
[4]托妮·莫里森著.潘岳,雷格,译.宠儿[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30,83,227,189,206.
[5]徐颖.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的 “替罪羊”原型研究——译论与实践的关系简论 [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2):62-68.
[6]刘国枝.论福克纳小说中的替罪羊群像 [J].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99-103.
[7]诺思洛普·弗莱著.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批评的剖析 [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