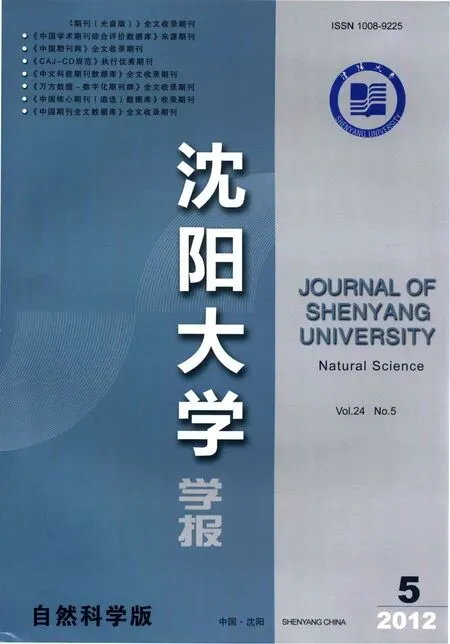苔丝的女性身体意义
张祎贞,李碧芳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身体向来是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探讨的焦点,这深刻地影响到文学批评领域。在柏拉图哲学中,哲学家认为身体束缚着灵魂,他们抵制身体,所以身体处于一种缺席的位置,不被关注。直到尼采提出“一切从身体出发”,身体才不再是沉默者。法国现象学代表梅洛·庞德认为,身体作为一种存在,我们有必要重新挖掘身体上承载的文化意义。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也表明身体是一种有力的象征形式,象征着社会文化。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被规训的身体(docile body)”则表明身体是受到社会文化控制的,身体上铭刻着社会文化,社会体制等。在身体日益受到关注,其地位日益突出的同时,身体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身体带着深刻的文化烙印并具有社会属性。诸如“身体叙事”“身体写作”等成为文学批评者关注的热词。“身体叙述指身体以一种基本的意象存在方式呈现在特定的文本媒介或者语境之中,并且传递出道德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文化信息审美情趣等丰富内涵的叙述行为。”[1]法国文学理论家埃莱娜·西苏提出的“身体写作”成为反抗男性话语霸权的工具,是对父权社会的反抗,也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
过去女性身体常常处于缄默的地位,充当被凝视的客体,也常常被看成男性的附属品[2]。从“身体写作”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身体在文学作品中的意义丰富。本文尝试着从苔丝作为被看的女性身体符号、被规训的身体以及苔丝身体和灵魂之间存在的矛盾三方面分析男性作者笔下的苔丝女性身体意义。哈代在小说中对女主人公苔丝的刻画深刻地体现了哈代对苔丝这类女性的同情,也表达了对社会体制有所改变的愿望,同时也揭示像苔丝这类女性在父权社会里对自由个体地位的向往以及女性自身的反抗精神。
一、被看的女性身体符号
回顾人类历史,在19世纪女权运动开展之前女性都被认为劣于男性并且是男性的附属品。女性身体也一直是男性“凝视”的对象,女性身体就是被男性欣赏、把玩的客体。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大都以男性审美为标准,男人们构建了女性身体美的标准。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作为被看的女性身体符号存在着。无论是德伯亚雷还是安琪,他们都代表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凝视”着苔丝。漂亮的外貌以及姣好的身材,这些成为男性对女性身体的要求之一。此外,女性的处女之身,在男性看来也是极其重要的。在《德伯家的苔丝》中,人物德伯亚雷和克莱安琪儿是父权社会里男性的典型代表。
漂亮的女性成为男性“凝视”对象,所以小说里有多处对苔丝外貌的描写。苔丝是如此漂亮的一位女性,所以成为亚雷的猎物。在第一次遇到苔丝后,亚雷脸上就闪过一道光并且爆发一阵大笑:“啊!该死的,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哈-哈-哈!多丰满的女的呀!”[3]38苔丝漂亮的长相和丰满的体型正符合他对女性的遐想。亚雷自然不会错过如此完美的猎物。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捕获他的猎物苔丝,亚雷让母亲在家禽饲养场给苔丝一份工作。在前往德伯庄园的路上,亚雷甚至把马车赶得全速前进而不顾苔丝的害怕,因为他旨在故意调戏苔丝。最终在他卑劣的手段下,他“给了她含有主人意味的吻”[3]51。
正是由于苔丝的漂亮才招来亚雷的“凝视”——骚扰。就如哈代在小说中所说,“她有着现在看来相当于缺点的特质,正是这个特质使得亚雷的眼光总也离不开苔丝。”[3]37其实亚雷从未爱过苔丝,苔丝女性身体仅仅是“被看的符号”。如果亚雷看到比苔丝更漂亮、身材更好的女性,亚雷一样会不择手段地捕猎到手,去“凝视”,去“把玩”。表面上来看,他对苔丝并不坏。他给苔丝的父亲买马车,还给她的弟弟妹妹买玩具。亚雷想当然地认为在他做了这些以后,苔丝会欣然地爱上他。事实上,在亚雷眼中,女性就是依赖男性的附属品,苔丝作为一个女性,就应该是缄默的一方,她不应该有话语权。他自认为在物质上给苔丝一点帮助,苔丝将顺服于他,他就可以随意占有她的身体,可以拥有她 。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苔丝走时,他对苔丝说:“好吧,你是真的很愚蠢的忧伤,苔丝,现在我并不用奉承你,你不用这么伤心。……我是以一个老实人的身份对你说这些话的,我也是一片好心呀。你若是开窍一点呢,最好不要像现在这样,你应该抓紧时机,趁着你美色尚存的时候大显身手……苔丝,回到我身边来,好吗?”[3]78亚雷对苔丝的“凝视”是父权社会里不足为奇的现象,所以在苔丝生活的家乡,有乡邻议论到:“越是漂亮的姑娘越容易倒这种霉。丑姑娘就挺安全了,根本不用担心会有这种事发生了”[3]106。
除了漂亮的外貌和姣好的身材外,在父权社会里,妻子的处女之身对于丈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德伯家的苔丝》里,安琪和苔丝之间的爱是如此的强烈。他们互相爱着对方,但安琪还是不能接受失去贞操的苔丝。在他们的新婚之夜,安琪得知苔丝不是处女时,他考虑到这对他是莫大的耻辱,安琪佯装和苔丝生活了几天选择了逃避。他还是无法接受苔丝,苔丝的失身成为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苔丝身体上的不一样,导致安琪的离开。“我再重复一遍,我爱的那个女人不是你”,“而是另一个有着你的样子的女人。”[3]231安琪认为他应该完完全全地拥有苔丝。然而在他自己和一个陌生女人厮混48小时这件事上却要求苔丝的原谅。我们可以看到男性的双重性道德标准,男性要求女性恪守贞洁,男性自己却不用。
苔丝作为一个被看的身体符号存在,在男性主导的父权社会里,男性是看的主体,男性的价值取向就是社会的价值取向,男性定义女性的地位,定义女性身体美的标准。在父权社会里,男性可以有双重性道德标准,女性处于被看、缄默的地位,没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女性存在就是满足男性看的欲望。
二、被规训的身体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说到“人体是被操作、被塑造、被规训的。”[4]身体是文化的媒介以及社会控制的反映。规训的身体即受控于文化生活规范的身体。父权社会里,女性身体受到男性权力的规训以及男性霸权话语的控制。在《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的女性身体就是一个被规训的身体,她尝试从父权社会给女性角色的传统定义枷锁中逃脱,但她终究还是被规训的女性身体。
首先,苔丝是被父权社会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规训的女性身体代表。苔丝不幸地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这是宗法制社会衰弱,资本主义社会萌芽的时期。按照宗法制社会习俗,贵族理应得到人们的敬仰。在苔丝的父亲从牧师那得知自己是贵族的后代,有着贵族血统后,苔丝父母就期望着靠卖这个头衔发家致富,或者找个一脉同宗的“亲人”帮衬帮衬。家庭的贫困,社会的传统习俗让苔丝走进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冒牌本家亚雷·德伯家,找亚雷家“认亲”。从这一点看,苔丝身体是被宗法社会习俗规训的。此外,苔丝也受到宗教伦理道德的规训。苔丝一直以来的行为准则和依据都是《圣经》。苔丝希望得到宗教的庇护。所以,她与亚雷的私生子去世时,苔丝希望孩子能接受洗礼,她认为只有这样孩子的灵魂才不会被送到地狱的最底层。因为苔丝的失身,愚昧的父亲阻止请牧师到家里为孩子洗礼,在苔丝父亲看来,苔丝和她的孩子都有损古老高贵的德伯家的名誉。苔丝最后不得不和几个弟妹一起为孩子洗礼。之后苔丝又考虑“给孩子举行基督教的葬仪是否会违反教规呢?”经询问并遭牧师拒绝后,苔丝自己给孩子举行了葬礼。苔丝身体是被父权社会传统习俗和宗教文化烙印操作、塑造和规训的。
其次,维多利亚时期腐朽的性道德观念让苔丝成为被规训的身体。苔丝在失去童贞以后,为维护自身情感上的纯洁回到家,然而,女性贞洁的道德观念还是无形地束缚着苔丝,她的内心害怕乡里人的议论。她问自己:“女人的贞洁难道真是一旦失去就无法找回的东西么?”[3]117她“把时间越来越多地花在那间与弟妹们合用的寝室里。”[3]99苔丝把自己规训在传统习俗所虚构的世界,身上背负着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的双重性道德要求的十字架。失身让苔丝感觉自己与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其实,这个社会本没有什么真正的规范。这样的双重道德观念无非是父权社会里强加给女性的一种规范。女性长期受到把男女有别的社会制度的熏陶和训练,“她们对男女性别角色和男子拥有的权力已经习以为常”[5]203。苔丝的女性身体意义是父权社会文化传统习俗的表征。
最后,苔丝的死则是父权社会通过权力去规训身体的集中表现。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人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他认为法律的惩罚是为了使每一个个体达到掌权者设定的目标。在父权社会里,掌权者就是那些男性,女性是被规训的客体。“男子是权力阶级而妇女是无权阶级,男子依靠各种习俗制度——男性角色的工具——来实行控制”[5]129。惩罚的目的就是让女性身体受到男性霸权话语的控制,苔丝女性身体就是权力规训的对象。因此,苔丝,一个独立而纯洁的女性,当她试图反抗父权社会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杀了亚雷时,苔丝注定受到惩罚。父权社会不容许有苔丝这样的反抗行为出现,但是父权社会容许男性对女性的玷污。在小说的最后,哈代写到“‘公正’得到了捍卫 ”。哈代为什么要在公正上加上引号呢?或许他是想让读者反思苔丝的死是公正还是不公吧。苔丝的死是她生命和身体的终结。苔丝作为被规训的身体,在违反了社会常规时,受到父权规训,受到惩罚,结束了自己存在于世界的基本的形式——身体的存在。
三、身体和灵魂的矛盾存在
在西方宗教里,死就是身体和灵魂的分离。身体或者说肉体消失后,灵魂仍是永生的。The Disordered Body:Epidemic Diseas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一书引用了苏格拉底的话:“一个人的灵魂是身体里捆着手和脚的无助的囚徒,不得不透过牢房铁栅去看现实而不是直接看现实……”(“[A man’s]soul is a helpless prisoner chained hand and foot in the body,compelled to view reality not directly but only through its prison bars…”)这都论证了人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体。当我们关注苔丝时,我们可以发现苔丝的身体和灵魂之间存在着矛盾。
苔丝与亚雷的关系反映了苔丝身体和灵魂的矛盾。苔丝在少女时代时,因家庭的贫困和社会传统习俗走近亚雷,被亚雷这个猎艳高手玷污。苔丝身体完全处于被看、被束缚的处境。苔丝被占据的身体和渴望自由独立的灵魂之间的矛盾不断突显出来。“如果我再像以前那样,我会沦为你的玩物,我才不做这种事……”苔丝一个来自威塞克斯的善良、勇敢、纯洁、淳朴的乡村女孩,当意识到自己不爱亚雷时,苔丝选择了离开,以保持自己灵魂的自由独立。苔丝不愿自己的身体束缚于亚雷而获得物质上的帮助。在父权社会里,苔丝作为被看的女性身体符号存在,身体被亚雷占据。身体的沦陷以及灵魂深处对自由的执著促使苔丝远离亚雷。小说中亚雷多次称苔丝为“独立夫人”。其实,这恰好证明苔丝的灵魂并不会如此简单地束缚于身体。既然她没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她就得保护好自己的灵魂远离这个恶棍。
苔丝内心的苦苦斗争是苔丝身体和灵魂矛盾存在的表现之一。苔丝回家后,身体摆脱了亚雷的占有,但还是处在社会传统习俗和宗教道德观念的规训下。灵魂在习俗和自由两者间苦苦挣扎,没能逃脱贞洁观念的折磨。在传统习俗、宗教道德和伦理道德的压制下,苔丝因自己的失身遭受世人的非议,承受着痛苦。但苔丝开始质疑这些非议。苔丝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个受牧师之托在墙上写圣经句子的人,苔丝问“假设你犯了罪,可你不是有意去犯的呢?”[3]94,“呸——我才不相信这些话出自上帝之口呢!”[3]95当牧师拒绝给她的孩子主持基督教的葬礼时,苔丝说:“今后我绝不会到你那个教堂去了。”苔丝想要自己的灵魂不被亵渎而离开亚雷,但自己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却被认为是一个犯了奸淫罪的人,她不被那些为维护女性贞洁观念的人所接受,不能被原谅。她开始怀疑信仰的宗教。简而言之,苔丝身体处在男性话语里,被规训着,苔丝的灵魂深处开始对这种规训产生怀疑,有了反抗情绪,苔丝女性主体意识在不断地苏醒。被规训的身体和渴望打破规训的灵魂开始了一场持久战。
安琪的抛弃,家庭的贫苦,亚雷的软硬兼施,面对残酷的现实,苔丝的灵魂妥协了,不再追求自由和幸福。她成了亚雷的情妇。苔丝灵魂的抗争在强大的父权社会里,传统习俗,宗教道德的力量前显得那么微弱。但是当安琪最后原谅了苔丝,并且回来找苔丝时。苔丝的内心深处对安琪的爱,以及灵魂对自由的向往再一次被激活。安琪的归来,说明她的“不洁”的身体被接受了。这说明代表男性之一的安琪也挣脱了传统习俗的束缚。这个事实对苔丝来说是个福音,它重新激发了苔丝灵魂对幸福和自由的渴望,同时也让苔丝鼓起勇气杀了亚雷,这个禁锢她身体和折磨她灵魂的父权社会的男性代表。苔丝在她短暂的生命里,灵魂做过苦苦的挣扎,面对现实也有过妥协,苔丝最终杀死亚雷,以生命或者说身体的代价,追求灵魂的自由。她的身体和灵魂终于永久地统一于自由和幸福。
四、结 语
身体是文化的文本,我们可以挖掘女性身体承载的文化意义。分析《德伯家的苔丝》后,我们不难看出在父权社会里女性身体就是被看的身体符号。苔丝作为被规训的身体,她的身体上铭刻着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传统习俗、宗教道德和父权社会的男性话语。就像Beauvoir说的,社会习俗要求女性安分守己地遵照“女人”的历史概念。苔丝的女性身体则像是一面镜子反映出男性对女性的霸权与控制。苔丝的死是父权社会权力对女性违反常规的惩罚的结果。通过分析《德伯家的苔丝》中女性身体的意义,我们发现在父权社会里女性的地位低下。然而,小说的副标题“纯洁的女人”以及安琪最后醒悟并接受苔丝,苔丝最终杀了亚雷追求自己的自由幸福,这些反映哈代对生活在父权社会里的女性的同情,以及对一个和谐平等社会的期望;同时也反映人们对社会性别不平等观念的改观,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1]刘立辉.变形的鱼王:艾略特《荒原》的身体叙述[J].外国文学研究,2009(1):50-59.
[2]刘波.西苏的“身体写作”在中国的实践及变异[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11):15-16.
[3]哈代.德伯家的苔丝[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54.
[5]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