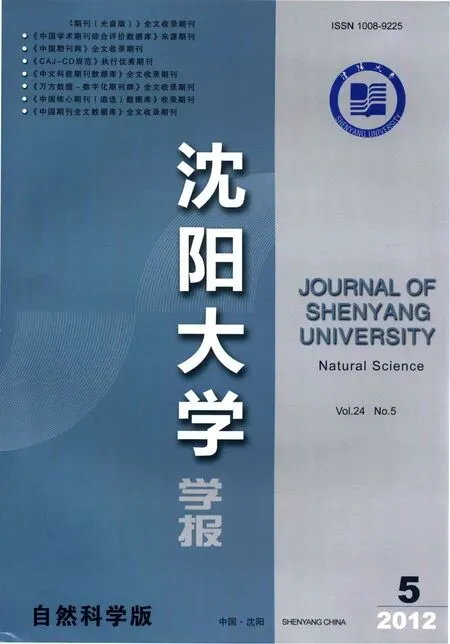论双重叙事对小说《围棋少女》主题的构建
禹 霓,张捷频
(1.沈阳农业大学 外语教学部,辽宁 沈阳 110161;2.大连外国语学院 法语系,辽宁 大连 116044)
200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部获得2001年法国龚古尔中学生奖的小说《围棋少女》,小说的作者山飒便是一位有着独特文化身份的法国华裔女作家。正是借着这部代表作她叩开了法兰西文学界的大门。同时,随着该小说在中国的出版,国内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围棋少女》的评议风潮。
在探寻《围棋少女》的成功因素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作者在小说中为凸显主题所采用的双重叙事加以研究。山飒在《围棋少女》中刻意借助独特的双重叙事,谱写了一曲从敌对到因爱赴死的爱情悲歌,意在触动现代人生存与情感的危机,引起人们对黑与白、罪与罚、忠诚与背叛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思考,寻找一种由对立到共存的可能。因此,本文旨在叙事学视阈下从叙事线条、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三方面共同挖掘受中国围棋文化影响的叙事模式对小说主题的构建。通过对小说叙事模式的解析,层层深入地挖掘主题是如何借助叙事形式而彰显的。这种基于中国文化的双重叙事形式,从叙事学角度来看,无疑是作者山飒具有创新意识的写作尝试,令其成为“中国文化式”小说的旗帜性人物。
一、《围棋少女》中黑白并置的复线叙事
叙事线亦即情节线,实际上也就是按因果关系安排故事发展变化的进程。在《围棋少女》中,小说整个故事由两条同时发展的叙事线组成,围棋少女的独白是一条线,日本军官的独白是另一条线,两条线的叙述完整而连贯,甚至可以成为两部独立的小说。一部是围棋少女在战争年代的成长;一部是日本军官在战争中的心灵救赎。但正如米兰·昆德拉与萨尔蒙的谈话中所说:“假如我可以写出七部小说,我就无法奢望通过一本书来把握‘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1]同样如果将《围棋少女》故事写出两部独立的小说那就无法通过一本书来透视现代世界中既矛盾又依存的关系。在《围棋少女》中,这两条线都是明线,在文中并置叙述。而叙事线并置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并无直接联系但有类似性或对比性的两个或两组人物以及由他们构成的事件,就某种情况交替着写;另一类是两个或两组人物发生某种联系,甚至共处于一个故事之中,那就是同一件事、同一个过程变换着角度交替着写。在这部小说中,山飒对情节巧妙的安排使这两类情况同时存在。前44章中围棋少女与日本军官没有交往,未曾谋面,他们的世界生活轨迹平行而无交集。少女在学校、家庭、千风广场之间往来,在业已千疮百孔的满洲悄悄长大;军官随着日军侵略部队离开家乡,带着军国主义思想踏上了满洲土地,开始了他即将沦为炮灰的命运。从第45章开始,虽然大多数章节两人仍无直接的关联与接触。但因围棋他们有了共处于同一故事情节下的机会,即处于相同的故事空间,在同一时刻经历相同事件。这正是“谁要同时布置两套情节就必须负责把它们在同一时刻里解决”[2]。在小说整个的叙述中,这两条叙事线或是反向对比或是同向映衬,下面举例为证。第27、29、31、33、35章为围棋少女按照故事时间讲述她与两个青年之间的暧昧情缘和她与其中之一敏辉的初恋。第28、30、32、34、36章为日本军官倒叙自己与日本艺妓光的初恋。男女叙述者同叙“初恋”,一个正叙,一个倒叙,在现实生活和往昔回忆中来回穿梭,形成反向对比。现实在往复间照亮了记忆,而记忆也完成了对现实的感悟,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意义张力,从而给读者带来更大的心灵感触。这样一来,借助两者由对立到相交的关系共同指向了小说由对立到共存的主题。
为了更加明晰地展现情节对比映衬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小说《围棋少女》故事情节对比映衬关系
二、《围棋少女》中的双重人物视角
聚焦的基本建构机制是:小说中借谁的视角来讲述故事,由于叙述者与故事的距离不同,由远而近,小说的艺术结构相应地发生着变化。“视角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自西方现代小说理论诞生以来,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一直是叙事研究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学者们发现,视角是传递主题意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3]它从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着作品的整体结构和艺术审美。因而它逐渐得到现代作家的重视与青睐。有着双重视角的小说多见全知视角与第一人称视角相结合或全知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相结合。这样结合主要是用全知视角来弥补人物视角缺陷同时又用人物视角来完善传统全知视角的不足。
在《围棋少女》中山飒却将围棋少女与日本军官双重人物视角巧妙结合,以各自的视角观察“自我”与“他我”。不断交替变换的视角,使故事同时呈现两个世界,这应该算是《围棋少女》对传统小说聚焦模式的一种创新。同时,现代小说一反传统线性小说对故事因果逻辑的严密铺排、对外部世界的精心刻画的传统格局,转而注重捕捉人物的心理和情感思绪。“作家的兴趣集中到了人物内部心理,现代小说大规模地实现了‘向内转’”[4]。所以双重人物视角结合的方式比照传统视角结合方式更凸显现代小说的这一特性。当然人物视角也存在一些缺点,如视野上的局限、主观色彩浓重等。但正是借助人物视角的这一普遍缺点而创造的双重人物视角成了《围棋少女》叙事艺术特色的法宝。因为在少女与军官二者多次相互“观察”与“被观察”中,更突出了黑白对照,形成单一视角无法企及的叙事效果。而且从读者角度来看,仿佛被置于观棋者的位置,随着围棋少女与日本军官如下围棋般交错的双重视角叙述,读者由远及近逐渐进入人物复杂的内心,不仅感觉到男女主人公的呼吸和心跳,还听到他们的心声,更走近了他们的思想。可以说,山飒用双重人物视角引领着读者去“观棋”,搭建一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棋局效果,使读者能参与到文本主题的阐释中来,引起人们对现实的担忧与思考。如山飒序言中所说:“《围棋少女》是一场梦,希望梦中的沉沦与爱情能带来现实的清醒,能让人对幸福对未来有一种特别的追求和信心。”
三、双重叙事结构
结构一词并不陌生,不是为小说专设,而是先于艺术世界存在。现代科学也不断揭示,结构在自然、社会、思维领域都普遍存在。“正所谓‘万物皆有结构’。结构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构成要素的性质;二是构成要素的数量;三是构成要素的联结和相互作用的方式。所以结构与事物的性质特点密切相连。”[5]因而对一部小说作品的结构分析,并不仅仅是形式的分析,同时也意味着解读隐藏在结构背后的深层内涵和艺术魅力。正如杨义先生所说:“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由于它以复杂的形态组合着多种叙事部分或叙事单元,因而它往往是这篇作品的最大的隐义之所在。它超越了具体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6]这里我们将根据结构的第三个决定因素,并借鉴热奈特结构主义叙事学和现代电影叙事理论,分析《围棋少女》双重叙述的联结和相互作用方式,也就是分析它们以何种形式组合在一起以凸显小说对立中求共存的主题。
1.断裂的结构——电影平行蒙太奇剪辑的借用
《围棋少女》中作者把围棋少女和日本军官的叙述分别拆分成46个短章,共92章,章节多而短小,多如棋盘上排兵布阵的棋子,短小如落子瞬间的干脆利落。其中奇数章节为少女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偶数章节为军官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以下围棋的方式拼贴在一起形成一个文本,展开无声的对话。这种拼贴方式可以看作小说对蒙太奇剪辑的借用,它使整部小说呈现出非线性的拼贴画风格。蒙太奇剪辑是现代小说非线性叙事赖以完成的必要技巧性元素之一,时空的转换,线索的交错并行,都需要通过蒙太奇剪接来完成。在《围棋少女》中作者主要借用了平行蒙太奇剪辑,这种手法常以不同时空或同时异地发生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情节线并列表现,分头叙述而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结构之中。匠心独具的平行式蒙太奇打破了传统小说以情节的因果链和时间轴为主的结构模式,形成了现代小说叙事的破碎与断裂,这种断裂感正与主题中的对立有异曲同工之妙。
乍看《围棋少女》中迅速切换的章节似乎彼此无关,阅读的连贯性不断受到破坏,发生断裂,这种断裂在前46章尤为明显。下面略举一列。小说开篇第一章少女讲述千风广场棋盘前第一百次连续胜局,最后一句写道:“我满足,我骄傲。今天,是我的第一百次连续胜局。”而第二章则突转到军官自述离家赴战场前后的情景,沉重而忧伤。第三章又轮到了少女,她在这一章又倒叙了向陆表哥学棋的往事。第四章则为军官叙述部队的生活。这四章的叙述使小说初看起来有些松散,甚至略显混乱。然而通过情节的间断跳跃,片段之间的断裂,作者创造了独特的审美空白。但继续读下来,读者会将故事情节按现实逻辑重构,故事仍旧是完整而有序的,主题思想非但不支离破碎而且表现得非常有力。这就要归功于作者巧妙地设置每章的故事内容、章节之间结构的安排。细读这些似乎毫无联系的章节会发现其中有着作者巧心安排的叙事结构,而正是这些结构上的关联使叙事在形式上有了彰显主题的功能。如果照前面论述,作者借助平行蒙太奇来实现叙事上的对立的话,那么同样,存在于对立之中的重合与共融也可以在叙事结构上有所表现。下面我们从同时异空、情节重复、叙事的接续三方面来解析双重叙事结构上的重合与共融。
2.重合与共融的结构
同时异空,即几个事件在同一时间但不同空间内发生。这几个发生在不同空间的事件被置于同一时间内,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悬念和想象空间。现实生活犹如多棱镜,是多面而各异的。这就意味着会有多种事件同时出现在共时性的时间里。例如,在小说的开头,男女叙述者分别讲述故事,一个在“千风广场”,一个在“东京”的家中,情节没有任何的交叉,乍看故事完全无关。但通过叙述,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暗示共时性的时间标记,如:第一章中“棋手们身上罩着一层薄霜,口鼻中呼出白气,一个个俨然成了雪人。”又如:“我握紧了手中的暖炉,用脚敲击着地面,试图融化凝固在体内冰冻的血液。”第二章中“今天早晨,东京下了第一场雪。”“我掉头跑掉了,母亲情不自禁,在雪地中追我。”我们可以从上面的例子中发现二者的叙述其实都是发生在 “冬季”这一相同的时间里,即为同时异空。这既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悬念和想象空间,同时也暗示了少女与军官看似无关且对立实则牵绊纠结的命运。
“一部像小说那样的长篇作品,不管它的读者属于哪一种类型,它的解读多半要通过对重复以及由重复所产生的意义的鉴定来完成。”[7]同样,法国新小说派的主要作家罗伯·格里耶也特别强调重复。他认为对同一场景或事物的重复描写能产生奇特效果,它能使场景或事物成为各种散乱片断的凝聚点而形成一种网络。基于这些关于“重复”的论述,我们发现《围棋少女》叙事情节上也存在着复现。全书92个章节中,有几个情节被男女叙述者分别叙述一次,因而构成了情节上的重复。如二人第一次交手下棋(第45、46章分别叙述);日本军官应约等待围棋少女下棋(第50、51章分别叙述);二人去七韵山坐在黄包车上的场景(第76、77章分别叙述);二人最后一次下棋(第84、85章分别叙述)。对二人的整个叙述而言,这样几处重复占的篇幅甚少,但是它们却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们是多数对立和看似无关的情境中唯一几个有少女和军官共存于一个时空中的场景,二人的重复叙述更说明了由对立到融合的大趋势。可以说,这不仅作为叙事手段在小说中出现,而且已经深入文本,成为叙述结构之元。更是小说主题意义不断增值的过程。通过重复,作者山飒将叙事结构进一步推向主题构建,使小说蕴含一种强大的艺术张力。
小说最后两章中,作者山飒用独创的叙事技巧将围棋少女和日本军官的叙事在经历了由平行蒙太奇构建的“断裂”到同时异空中隐含的“重合”再到四个场景的“重复”之后重新“缝合接为一体”,创造了双重视角与情节下的叙事的接合。第91章少女所有的故事在第92章军官的叙述中有了结局,二人“共享”的结局。日本军官最后的述说为全书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至此,他们的命运融和在了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叙事结构也完成了它一步步构建着小说由对立到共融这一主题的历程。
《围棋少女》的创作背倚着中国围棋这一古老的文化意象,这是一个无不蕴含着关于对立与共存深刻哲学思辨的象征物。山飒创造出仿围棋的叙事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为突出《围棋少女》的主题打造了独特的叙事,使双重叙事在不断从“断裂”走向“接合”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小说主题的层层构建,步步为营,最终使小说的主题借助叙事形式而完美彰显。而且可以说阐释《围棋少女》这部小说背后的主题深意对当今充满矛盾与对抗的世界中人的际遇有着普遍的现实意义。
[1]Milan Kundera.L’art du roman[M].Paris:Gallimard,1995:90.
[2]狄德罗.狄德罗美学论文选[M].张冠尧,桂裕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43.
[3]申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8.
[4]杨世真.重估线性叙事的价值:以小说与影视剧为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97.
[5]吴效刚.现代小说:叙事形态与人本价值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5.
[6]杨义.杨义文存:第1卷:中国叙事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39.
[7]米勒.解读叙事[M].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