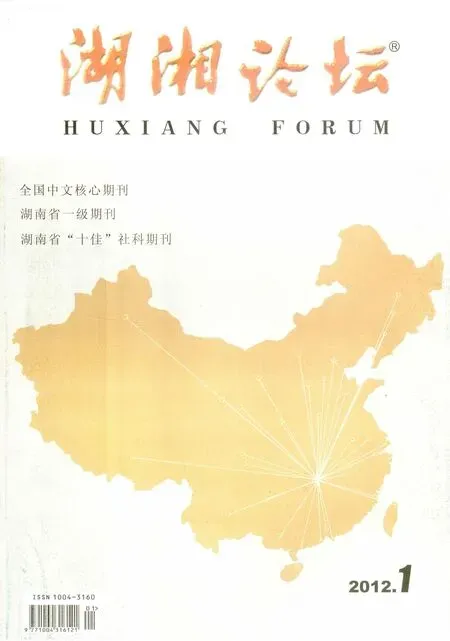经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传统认定及其反思
陈锦宣
(成都理工大学,四川成都611745)
经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传统认定及其反思
陈锦宣
(成都理工大学,四川成都611745)
在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上,自中国哲学学科建立时起就形成了中国哲学需于经学中求的传统思维定势,并且大多数研究者认同并采用了这种观点。这种定位是奠基在上世纪初对“什么是哲学”和“什么是中国哲学”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西方的学科分类标准对其亦产生重要的影响。当前随着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合法性”等问题的深入反思和对经学地位的重新认识,先前的这种定位需要加以认真思考和重新认定。
经学;中国哲学;关系
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从中国哲学学科建立时起就存在,但是对此问题的探讨和挖掘还不够。中国哲学学科建立之后,形成了中国哲学需于经学中求的传统思维定势,研究者们大多认同并采用了这种观点。如果对二者关系的传统定位加以进一步认真反思的话,会发现其定位是奠基在上世纪初对“什么是哲学”和“什么是中国哲学”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西方的学科分类标准对其亦产生重要的影响。当前随着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合法性”等问题的深入反思以及对经学地位的重新认识,先前的这种对二者关系的定位需要加以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并予以重新认定。
一、传统认定:中国哲学需于经学中求
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是伴随着“哲学”概念传入中国、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而产生的。众所周知,明治初年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造“哲学”一词翻译西方的“philosophy”,后经我国学者黄遵宪传入,“哲学”此译名最早出现于1887年黄遵宪所撰就的《日本国志》一书。在此之后,中国思想界即有了“中国哲学”概念的提出,在胡适之、冯友兰等人的努力开创之下,中国哲学更演变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可以说,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是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冯友兰等人通过引进西方的哲学观念及其学术研究范式完成的,创立中国哲学学科的过程,其实就是经学研究的退场过程,就是经学研究模式向现代哲学研究模式的转换过程。因此,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从中国哲学学科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了,但是这个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忽视,学人们对之鲜有论及,或有论及而语焉不详。
冯友兰是少有的论及此问题的人之一。他于1931年发表专文《中国中古近古哲学与经学之关系》,探讨了中国中古近古哲学与经学的关系,他认为:
“中古近古时代之哲学,大部分须于其时之经学中求之。在中古近古时代,因各时期经学之不同,遂有不同之哲学;亦可谓因各时期哲学之不同,遂有不同之经学。大概言之,其中有哲学成分之经学,为今文家之经学,古文家之经学,清谈家之经学,理学家之经学,考据学家之经学,经世家之经学。”[1]P196-197
分析冯友兰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第一,他认为经学与中古近古哲学关系密切,经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紧密相关,有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就有什么样的经学思想,有什么样的经学思想就有什么样的哲学思想。第二,中古近古哲学思想存在于经学思想之中,中古近古哲学家们大多没有独立的哲学体系,而有完整的经学体系,因此探求中古近古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需要到他们的经学思想中寻求。第三,中古近古哲学广泛存在于经学之中,几乎可以说所有的经学中都包含有哲学。冯友兰对经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认定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中国哲学需于经学中求。
冯友兰的这种对经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认定影响了后来大多数学者。比如这种思想就典型地反映在王葆玹先生对经学派别的划分之上。他在《今古文经学新论》中谈到:“我以为,历史上的经学可归结为三大派系,即今文经学的系统、古文经学的系统和形上学化的经学系统。”[2]P17对于“形上学化的经学系统”他作了如此的解释:“所谓形上学化的经学,包括魏晋玄学、隋唐经学、宋代理学及明代心学等等,其特点是注重于形上学而轻视礼乐,或者说重视哲学而轻视类似于宗教神学的东西。”[2]P17可以看出,王先生实际上就是从经学中把他认为属于哲学的部分单独划分为一个派系,而这个划分的标准就是哲学的标准。事实上,他的这个划分标准的前提就是承认中国哲学存在于经学之中,中国哲学需于经学中寻求。
时至今日,人们对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认定趋向基本定位于中国哲学需于经学中求,因为他们认为古代思想家的学术活动大多以经学研究为主,在众多的经学论著所阐发的经学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哲理,中国哲学即是通过注释儒家经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中国哲学需要到经学中去寻求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
需要提及的是,章太炎在此问题上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经学中鲜有哲学。在其《国学概论》中,他提出:“讨论哲学的,在国学以子部为最多,经部中虽有极少部分与哲学有关,但大部分是为别种目的而作的。以《易》而论,看起来像是讨论哲学的书,其实是古代社会学,只《系辞》中谈些哲理罢了。”[3]P30笔者认为章先生所持的是“中国哲学需于子学中求”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虽然经学中有哲学,但是相比于经学,哲学思想的精华却在子学中。章太炎曾把哲学分为四类:“以哲学论,我们可以分宋以来之哲学、古代的九流、印度的佛法和欧西的哲学四种。”[3]P47在这四类哲学中,他认为宋以来的哲学不如“九流”之哲学,故推重“九流”,以之为最。他明确提出:“宋以来的理学和九流比较看来,却又相去一间了”,“‘九流’实远出宋、明诸儒之上”。[3]P47-48所以说,章太炎持有的是经学与中国哲学关系不大的观点,这也代表了一种认定的趋向。
二、传统认定的原由探析
为什么冯友兰等人在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上会做出中国哲学需于经学中求的认定呢?探讨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如何界定“什么是中国哲学”,因为对于“什么是经学”在学界是有共识的,而对于“什么是哲学”和“什么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对经学和中国哲学关系的认定相异。因此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着重注意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种认定是建立在对“什么是哲学”和“什么是中国哲学”的认识基础之上;二是其认定与西方学科体系的传入和全盘接受紧密相关。
“哲学”是西方传入的概念,一直以来,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都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进行界定的,因此在“哲学”一词还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自我意识”形成“自觉”之前,对“中国哲学”的定义也只能够按照西方哲学的标准进行界定。所以当我们以西方哲学的问题域来划定哲学的研究范围时,中国哲学也只能以“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冯友兰之所以对中国中古近古哲学与经学的关系做出以上的认定,根源在于他认为哲学就等同于“西方哲学”,他对“中国哲学”的界定采用了西方哲学对哲学的定义标准。他在其所著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4]P1他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即是用中国历史上的材料来套西方哲学的标准。所以,他如是界定“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家”:“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4]P8他用西方哲学的标准来判定“什么是中国哲学”,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之下,他对经学进行了裁剪,符合者选取之,不符合者抛弃之,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他不能看见存在于中国哲学中的“形式上的系统”,而只能努力地“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4]P14因此,冯友兰的认定只能说是在西方哲学视野下对经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认定,这种认定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故胡适之、冯友兰等所创建的“中国哲学”只能称之为“中国现代哲学”,他们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只能称之为站立在中国现代哲学角度去重新审视现代之前的哲学文本所重新构建的“中国哲学史”,因此,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只能称之为“现代中国哲学家眼中的‘中国哲学史’”。
另外,我们都知道,“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门类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学问,按照现在的学科标准,“经学”包括的范围很广,涉及哲学、宗教、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等诸多学科,事实上在西方近代学术门类中,并没有一个与“经学”相对应的学科。其实,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就传统来讲,中国只有典籍分类法,后来这种典籍分类法不仅成为了图书典籍的分类标准,而且也成为了学科的分类标准。中国传统典籍分类标准经历了从刘歆的《七略》之“七分法”向纪昀主持编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之“四分法”演变的过程。在《七略》中,刘歆把典籍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七大类。在这七大类中,最重要者为“六艺略”(即六经),儒家之六经处于独尊的地位。《四库全书总目》将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最重要者亦为经部。按照这种典籍分类,自然就形成了相应的以典籍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西方学科体系传入之前,中国无“哲学学科”,中国哲学还没有经历从传统的“经学”、“子学”等中分离出来的过程。
但是这种以典籍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与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学科”是完全不同的。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被中国学术界所认识并全盘接受,近代中国开始沿用这个学科体系。在晚清吸收西方的学科体系实现学科体系转型的过程中,经学的学科定位呈现的是逐渐下降的并最终被“消融”的过程。因为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经学”难以在其中找到相应的学科位置。按照西方的学科标准,“经学”涉及了哲学、宗教、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等多个学科,所以如何将经学纳入新的学科体系中,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人们采取的是“解构”之后重新“建构”的方法。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先加以拆散,将其完全打破,然后再重新按照新的学科标准归并到新的体系中去。可以说,在这个所谓的现代知识分类框架中,经学是被完全“分解”了的。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标准,《周易》、《论语》、《孟子》、《公羊传》、《孝经》等被划归到了哲学学科;《尚书》、《左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等被划归到历史学科;《诗经》被划归到文学学科;《尔雅》进入到语言文字学科;等等。
事实上我们知道东西方文化是不同的文化,西方的学科体系是在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它是为了解决西方自身的问题而设计的,不是为了东方文化而设计的,所以说这种学科体系并不一定就适用于我们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我们只能在学习和引进西方学科体系的过程中经过对它的消化,充分兼顾我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使之有机结合,而不能全盘地不分清红皂白就加以吸收。当然,这个形成过程是清末中国积贫积弱,西方占据了各个方面的话语霸权,中国在此话语霸权下完全“失语”的反映。
综上所述,这种传统关系的认定原因就是中国学者在创建“中国哲学”学科的过程中全盘吸收西方的学科分类标准,以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一认定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在经学与中国哲学关系上的反映,它是西方哲学语言和学科体系在中国占据话语霸权的结果。
三、对传统认定的反思
如前所述,对经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传统认定是建立在对西方学科体系的引进和以西方哲学的标准来界定“什么是中国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在此我们需要反思两个问题:一是西方哲学是否就等同于哲学,西方哲学的标准是否能全世界通用;二是西方的学科标准是否适应于中国,这种现代的学科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兼容”。
首先,哲学是否就专指西方哲学呢?上个世纪末,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访问上海,与王元化先生谈话时提出中国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这个谈话引起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有无哲学”问题的重视,此后,我国学者郑家栋先生在1999年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就引发了学术界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等问题的深入讨论。时至今日,这场讨论正逐步深入,所讨论的问题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入到对《中国哲学史》写作方式的反思,再进一步深入到探讨“中国哲学”是否需要重构及如何重构的问题。这场讨论富有成效的成果之一就是中国学者对“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各自的定义和研究范围有了更加清楚的把握,对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宜用“共相”和“殊相”(或“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来把握,哲学既具有普遍性之“共相”,而这种“共相”具体表现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哲学之“殊相”。所以说“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都只是哲学这一共相下的殊相之一。
既然“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是不同的殊相,那么二者就是不同的哲学,西方哲学的界定标准是不能够用到中国哲学之上的。关于这一点,金岳霖先生早就有主张:“我们可以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来写中国哲学史,我们也可以不根据任何一种主张而仅以普通哲学形式来写中国哲学史。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5]P6其实,金岳霖对胡适之的批评也适用于冯友兰。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问世之后,牟宗三更是指出:“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6]P3因此,“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在中国哲学里选择合乎西方哲学的题材与问题,那将是很失望的,亦是莫大的愚蠢与最大的不敬。”[6]P6在这个方面,当前学界更是达成广泛的共识,如宋志明先生就认为:“西方哲学只是一种哲学,并非哲学的范本。照搬照抄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不可取,卖弄西方哲学的新名词更不可取……”[7]P105龚隽先生也强调:“我的主张是借用西方的叙述来激活中国哲学的问题,而不只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柜架来剪裁中国哲学的史料,决定中国哲学的问题,使之简单地成为对栽种哲学的说明。”[8]P43
在第二个问题上,现代的学科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兼容”,已经表现在作为整体的“经学”已被肢解上。而恰如汤一介先生所言:“对我国的‘经学’研究,可能综合性的研究更有必要。”[9]P3-4因为经学是一个整体,传统的经学思想认为各经有各经之功用,如荀子认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儒效》)所以,在培养人方面,孔子曰:“文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汉书·滑稽列传》)经书构成了一个系统,只有集中在一起才能发挥经学的整体功能,产生效应。用西方的学科标准来僵硬地划分中国的传统学术,将经学“肢解”成各个部分,这是非常不恰当的。如彭林先生就对按照西方的学科标准来“分解”经学的传统做法表达了自己强烈的不满,提出“我们应当重新检视百年以来盲目追随西方大学文科体系的迷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消极后果,给经学以应有的学科地位和必要的尊重”,并建议“在有条件的重点大学中设立经学系或者经学学院”。[10]P10-14事实上,西方的现代学科分类有其严重的局限性,正如尼采所嘲讽的:“因为我们现代人自身内毫无所有;我们只由于使我们填满了,并且过分地填满了陌生的时代、风格、艺术、哲学、宗教、认识,而成为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成为走动的百科全书,一个误入我们时代里的古希腊人也许将要这样称呼我们。”[11]P25西方的学科分类只能导致人的个性的缺失,使人成为“走动的百科全书”,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宗旨相背离。
既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区别,西方哲学的标准不能够运用到对中国哲学的界定之上,加之西方的学科标准与中国是不相适应的,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兼容”,那么对经学与中国哲学关系需要重新思考和重新认定。而笔者认为重新思考和认定二者的关系需要把握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重新定位要以对“中国哲学”的定义为基础,而对“中国哲学”的定义要从中国传统、中国哲学自身出发,找准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找出自身特有的问题域,而不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二是重新定位要把握经学和回归经学的整体性,从整体上理解和研究经学,而不能肢解经学。
[1]冯友兰.中国中古近古哲学与经学之关系[A].三松堂学术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2]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7.
[3]章太炎.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5]金岳霖.审查报告[C].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宋志明.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几点看法[J].中国哲学史,2005,(4).
[8]龚隽.再论中国哲学史作为“学科”的合法性危机与意义[J].哲学研究,2005,(8).
[9]汤一介.中国经学与传统学术[J].中国文化研究,2006,(春之卷).
[10]彭林.论经学的性质、学科地位与学术特点[J].河南社会科学,2007,(1).
[11]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B2
A
1004-3160(2012)01-0086-05
2011-12-10
陈锦宣,男,四川宣汉人,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曹桂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