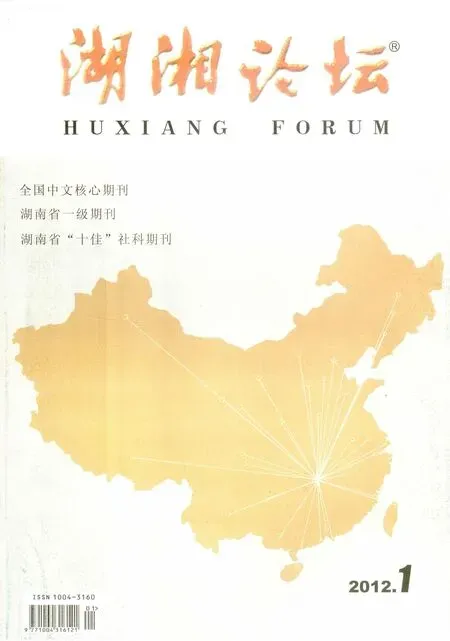胡寅、胡宏为湖湘学奠基
张立文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胡寅、胡宏为湖湘学奠基
张立文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湖湘学的奠基者是胡安国的儿子胡寅、胡宏。胡寅儒佛邪正之辨,是从道学家道统论立论而辟佛的,他守儒家三纲五常而辟佛不忠不孝,违背伦理道德;不穷理尽性而至于命,而以万物皆空;反对佛教三世轮回说等。胡宏思想路线,是其对父兄胡安国、胡寅“心与理一”思想路线的继承和阐扬。正由于胡宏的道性形上学的本体学的哲学个性和特色,而为湖湘学奠基,并为湖湘学与程朱道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奠定基础,与其学生张栻哲学思想发展开出新的精神路向。
湖湘学;胡寅;胡宏
一、辟佛以崇正
湖湘学的奠基者是胡安国的儿子胡寅、胡宏。全祖望说:“武夷诸子,致堂(胡寅)、五峰(胡宏)最著,而其学又分为二,五峰不满其兄之学,故致堂之传不广。然当洛学陷入异端之日,致堂独皭然不染,亦已贤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衡麓学案》,《宋元学案》卷41,《黄宗羲全集》第4册,第641页。)朱熹说:“胡致堂说道理,无人及得他。以他才气,甚么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检点。”(《朱子语类》卷101,第2581页。)赞扬其议论英发,人物伟然。胡寅著《崇正辩》和《斐然集》。所谓《崇正辩》,是指“辟佛之邪说也”。(《崇正辨序》,《斐然集》卷19,《崇正辩斐然集》第390页,两处“辨”、“辩”有异。)为什么说佛为邪?胡寅认为佛教“沦三纲”、“绝四端”;不言生而言死,不言显而言幽;河山大地未尝可以法空而佛空之等。“是故仲尼正则佛邪,佛邪则仲尼正,无两立之理,此《崇正辨》所以不得已而作已。”(《崇正辨序》,《斐然集》卷19,《崇正辩斐然集》第393—394页。)据此,胡寅将佛儒的差分概括为五点:“道德之本,性命之正,幽明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永州重修学记》,《斐然集》卷21,《崇正辩斐然集》第435页。)胡寅儒佛邪正之辨,是从道学家道统论立论而辟佛的。黄宗羲说:“吴必大问《崇正辨》如何?朱子曰:‘亦好。’必大曰:‘今释亦为所辩者,皆其门中自不以为然。’曰:‘吾儒守三纲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谓吾儒自不以为然否?’”(《衡麓学案》,《宋元学案》卷41,《黄宗羲全集》第4册,第660页。)守儒家三纲五常而辟佛不忠不孝,违背伦理道德;不穷理尽性而至于命,而以万物皆空;反对佛教三世轮回说等。
胡寅理论思维继承胡安国的“心与理一”说:“天地之内,事物众矣。其所以成者,诚也。实有是理,故实有是心;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实有是事,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衡岳寺新开石渠记》,《斐然集》卷20,《崇正辩斐然集》第417页。)诚,实也。由实理——实心——实事——实物——实用的过程,是一从形而上理心到形而下事物、功用的“一以贯之”的实践;又从“物无不可用,用之尽其理,可谓道矣乎。”(《衡岳寺新开石渠记》,《斐然集》卷20,《崇正辩斐然集》第416页。)由物的外度越而尽理,而至形而上的道理。由此胡寅批判佛教“以心为法,不问理之当有当无”而辩曰:“理与心一,谓理为障,谓心为空,此其所以差也。圣人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以一贯之,莫能障者……夫又何必以心为空,起灭天地,伪立其德,以扰乱天下哉。”(《崇正辩》卷2,《崇正辩斐然集》第69页。)圣人理与心一以贯之,两者不可离,既然理是实理,心也是实心,理心都是实存的有,而非空无。如飞走动植的并育而不相害,仁义礼智并行而不相悖。因此,佛教“皆以心法起灭,幻术隐显,非道之正。”(《崇正辩》卷2,《崇正辩斐然集》第61页。)道学家的道与理两个概念异名同实。非道之正即非理之正。道(理)均具有实存性。“道一而已,亘万古而无弊。得之者,或先百世而生,或后百世而出,其言得行,若合符契。盖至当归一,而精义无二也。”(《崇正辩》卷2,《崇正辩斐然集》第66页。)道(理)作为实存是永存永继的,是与言行活动、历史实践归一无二的。
胡寅从实理实心批判佛教空寂的“了心”。他说:“佛氏所谓了心,异乎圣人所谓尽心也。举心之所有者皆归之空,了心也,举心之所包者各臻其理,尽心也。了心之弊,至于一身亦不欲存也。若非自绝于人伦之类,则刳剔焚灼,餵饲饿虎,无所不至,要皆空而后已。空虚寂灭,莫适于用,道之弃也。”(《崇正辩》卷2,《崇正辩斐然集》第96页。)了心与尽心的差分是,一是“了心”,举心的所有都归于空;尽心,举心所包涵的万事万物各渐通达其理;二是“了心”的空虚寂灭,以至于受之父母的身体也不欲存,以身餵饲饿虎,这有违于人伦道德,有逆人理。“尽心”是讲人伦物理。圣人之道乃天理之自然;“先王之道,送终追远,奉承祭祀,以时思之,修身慎行,不敢伤父母之遗体,恐辱先也。”(《崇正辩》卷2,《崇正辩斐然集》第75页。)人的行为活动要与三纲五常相契合。
二、道性本体学
胡寅承胡安国的“理与心一”思想,批判佛教之邪,以立儒教之正;立儒教之正,以明理心的一以贯之。但于道学哲学思潮的理气心性核心话题,并无智能创新,而未能彰显湖湘学派的理论个性。其弟胡宏(1198-1161)贴近道学核心话题理气心性,体现其重建伦理道德,重塑价值理想的时代精神,为湖湘学的立派奠基。全祖望说:“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五峰学案》,《宋元学案》卷42,《黄宗羲全集》第4册,第669页,因胡宏长期寓居湖南衡山祝融、天柱、芙蓉、紫盖、石廪五峰之下,故学者称其为五峰先生。)此评公允。吕祖谦称誉《知言》超过张载《正蒙》,而见其书在当时学术界、思想界产生了效应。真德秀在看了《知言》的稿本后,作跋说:“孟子以知诐淫邪遁为知言,胡子之书以是名者,所以辨异端之言与吾圣人异也。杨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书于诸子百家之邪说,辞而辟之,极其评焉。盖以继孟子也。”(《宋真德秀跋胡子知言稿》,《胡宏集·附录二》第340页。《孟子·公孙丑上》:“‘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知言》既批判诸子百家的邪说,又批判佛老异端的言辞,通过与圣人之言的比较,以继孔孟的道统心传。从吕祖谦和真德秀的评《知言》中可察,《知言》是归于理学主流派的著作。但亦引起主流派、非主流的论争,而扩大了其影响。朱熹作《知言疑义》,将其内容作了概括:“《知言疑义》,大端有八:性无善恶,心为已发,仁以用言,心以用尽,不事涵养,先务知识,气象迫狭,语论过高。”(《朱子语类》卷101,第2582页。)此八端疑义,也是朱熹有不同见解的所在。正由于引起朱熹、张栻、吕祖谦等人辩析,使《知言》在理学中影响升温。
胡宏在其家学文化思想环境中,接受其父兄的“理与心一”的主张,同时亦吸收北宋道学家张载、二程等思想,他将家学、道学和传统儒家孔孟之道相融突,在思议现实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精神的实践中,把心性话题转换为道性话题。道作为自然宇宙和社会生活的客体与作为性的心性主体,是“一以贯之”的,这种道性的圆融,是道性本体学向伦理学和伦理学向本体学转化的圆融精神的表征,这对于朱熹的心与理、道与器、太极与阴阳、天理与人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是一个突破,这也是为什么引起朱熹激烈批评《知言》的缘由所在。
胡宏道性本体学是一个开放的生命化的实践,这个生命化的实践是穷理尽性,“务晓人以生生之道”。(《周易成书》,《皇王大纪论》,《胡宏集》第277页。)来建立一种主体我与天地万物、人与我之间共存并行不害不悖的圆融关系。所谓道性本体学,是指胡宏哲学逻辑体系,道与性两个概念具有名异实同、内外合一的性质,故称之为道性本体学(朱汉民、陈谷嘉著:《湖湘学派源流》中认为胡宏哲学为“性本论—新本体论诠释”,同上书,第116页)。向世陵认为,“胡宏从北宋诸家中选择出五子理论,并以性为基线将它们贯穿起来”,建立性本论(《宋明理学分系概说》,《湘学》第266页)。这是湖湘学在本体学上的表述。
道在胡宏哲学逻辑结构中是一个至高的、普遍的、通贯天、地、人三极之道的范畴。其一,道为太极。他说:“道谓何也?谓太极也。阴阳刚柔,显极之机,至善以微,孟子所谓可欲者也。天成象而地成形,万古不变。仁行乎其中,万物育而大业生矣”(《汉文》,《知言》,《胡宏集》第41页)。胡宏将《周易·系辞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改换为道谓太极,立天之道阴阳以成象,立地之道柔刚以成形,立人之道仁行其中,万物育,大业生。道度越天地人三道,而又使其成就天象地形和万物大业。作为太极的道既具有形而上本体性,又是其生命化文化流行的实践性。“天道保合而太极立,氤氲升降而二气分。天成位乎上,地成位乎下,而人生乎其中。故人也者,父乾母坤,保立天命,生生不易也”(《皇王大纪序》,《胡宏集》第163页)。这种生命化大化流行的实践,是阴阳二气氤氲升降的差分比,而贯通于天地人整体世界之中,生生不易,显著天地人三道。“阴阳成象,而天道著矣;刚柔成质,而地道著矣;仁义成德,而人道著矣”(《修身》,《知言》,《胡宏集》第6页)。由道的生命化流行,才使天地人三道著明起来。
其二,道塞天地。作为形而上本体性的太极的道,便要求一种既度越于天地万物,又具有统摄天地万物的功能,而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普遍地充塞天地人。“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于驱者不见其大;存乎饮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诸子百家億其以意,饰之以辨,传闻袭见,蒙心之言”(《天命》,《知言》,《胡宏集》第3页)。道由已及物,由身及天地,道充塞身而推及充塞天地万物,以及人的日常生活活动之中,无不由道来统摄和主导。正由于道具有度越性,形上性,因此,道与物不同。“形形之谓物,不形形之谓道。物拘于数而有终,道通于化而无尽。”(《纷华》,《知言》,《胡宏集》第26页)物有形象而拘泥于数,是终始、有限度的,道无形象而通化,是无始无终的、无处不在不有的,所以能充塞天地,而具有普遍性、度越性、形上性。
其三,道外无物。道的生命化大化流行于天地万物之中。无天地万物,道的生命化流行便会窒息。所以“道不能无物而自道,物不能无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犹风之有动,犹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间之?故离物求道者,妄而已矣!”(《修身》,《知言》,《胡宏集》第4页。)正由于道不离物,道便主导、支配物。故此他把道喻为风和水,物喻为动和流,风为动之源,水为流之本。有风和水,才有动和流,动和流是风和水的一种表现形式。换言之,道是本源,动和流是末流。由于道与物之间存在这种体用关系。这是其对二程“道外无物,物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河南程氏遗书》卷4,《二程集》第73页。)的理解。道贯物中,天地万物之间,都普遍存有道,受道的主使。道外无物,道在物中,亦在事中。“事本乎道,道藏乎事,天生人,人成天。”(《西文佛教》,《皇王大纪论》,《胡宏集》第223页。)事以道为本根,而藏隐于事中,犹人与天一样,相互相成,道与事亦相辅相成。
其四,道为仁义道德。“道非仁不立。孝者,仁之基也。仁者,道之生也。义者,仁之质也。”(《修身》,《知言》,《胡宏集》第4页。)仁为道之所化生,道由仁而能站得住。孝与义是仁的基础和性质。仁是道在生存世界人际间所体现的道德规范和原则。道生命化流行,不受时空的限制。“道无不可行之时,时无不可处之事。时无穷,事万变,惟仁者为能处之,不失道而有成功。”(《修身》,《知言》,《胡宏集》第5页。)道不被时所限,也不被事所限。时间和事物都是变化无穷的,但仁者能掌握时间和事物的变化,而能取得成功。
仁是主体人的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仁也者,人也。人而能仁,道是以生。生则安,安则久,久在天,天以生为道者也。人之于道,下学于已,而上达于天,然后仁可言矣。”(《求仁说》,《胡宏集》第196页。)仁的本义是亲的意思,“从人二”,即两个人或两人以上的互相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讲仁是人,人之所以能仁、能以仁来处理人际关系,就产生道德价值,由生——安——久——天,天以生为道。人的道的培养,需要由下学到上达、推已及天的修养工夫;又要向圣人学习。“学圣人者,以仁存心,以义处物,相时而动,亦岂必于进退哉!……以圣人之道为必可行,以圣人之政为必可复,以天下之衰为必可振。”(《上光尧皇帝书》,《胡宏集》第82页。)提升人自身仁义道德的修养素质,以仁爱之心出发,恰到好处地处理各种事物,如此圣人之道、之政、天下之衰就会得到可行、可复和振兴。
仁能贯合天地之道。如何贯合?他说:“其合于天地、通于鬼神者,何也?曰,仁也。人而克仁,乃能乘天运,御六气,赞化工,生万物,与天地参,正名为人。”(《邵州学记》,《胡宏集》第150页。)仁具有度越功能,能与天地参,这便是“仁之道”。仁之道可一以贯天下之道。“唯仁者为能一以贯天下之道,是故欲知一贯之道者,必先求仁;欲求仁者,必先识心。忠恕者,天地之心也。人而主忠行恕,求仁之方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即主忠行恕之实也。”(《论语指南》,《胡宏集》第305页。)胡宏在评各家解《论语》吾道一以贯之的孔子忠恕之道时,认为体知—贯之道,必先求仁,求仁先识心,以忠恕之道就是天地的心。主体人主忠行恕,这是求仁的方法,已所不愿,勿施于人,这是主忠行恕的实践。批评有的学者以人与心为二,心与道为二的支离的观点,认为“忠恕即道……夫人心忠,则为忠;恕,则为恕。今曰:‘忠之为心’,‘恕之为心’,似以忠恕又自有心。”(《论语指南》,《胡宏集》第305—306页。)忠与恕不是二个心,也非二个道。忠恕只一心,忠恕即道。这是因为“圣人与道一体,故不用学。学者,学道者也。若体与道一,则更何用学。惟未能与道为一,故须学也。学道,便是行仁义也”(《论语指南》,《胡宏集》第315页)。这是胡宏对孔子所说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的评论。圣人是生而知之者,已与道一体,学而知之者就是学道,学道的内容就是践行仁义,达到与道为一境界。
其五,道合体用。“道者,体用之总名,仁,其体;义,其用。合体与用,斯为道矣。‘大道废,有仁义’,老聃非知道者也。”(《阴阳》,《知言》,《胡宏集》第10页。)又说:“圣人仁以为体,义以为用,与时变化,无施不可。”(《上光尧皇帝书》,《胡宏集》第82页。)仁体义用,道合仁义体用。批评老子把大道与仁义二分,而未明其体用关系。“中者,道之体。和者,道之用。中和变化,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往来》,《知言》,《胡宏集》第14页。)《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以性情解中和,胡宏以道的体用解中和,中和变化,各正性命,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道之明也,道之行也,或知之矣。变动不居,进退无常,妙道精义未尝须臾离也……参于天地,造化万物,明如日月,行如四时。”(《往来》,《知言》,《胡宏集》第15页。)中和体用,参天地,造万物。道合体用,妙道精义须臾不离。仁义体用,亦可与天地参。“仁之为体要,义之为权衡,万物各得其所,而功与天地参焉,此道之所以为至也。”(《与原仲兄书二首》,《胡宏集》第121页。)这种与天地参的过程,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体用合一,未尝偏也”(《与原仲兄书二首》,《胡宏集》第122页。)的实践。
道体具形而上学的度越性,而道用则有形而下的现实性,于是涉及现实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各层面,如圣人之道、先王之道、学问之道、修身之道、为政治国之道、王道、霸道等。圣人之道要学习,“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井田、封建、学校、军制,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与张敬夫》,《胡宏集》第131页。)要学得圣人之道的体和用,不可偏,有体无用,与异端佛教思想就无分别了。圣人能竭心思考致用的大的方面,这也是圣人与佛教思想的分歧所在。“若讲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国,为万世之人君乎”!(《文王》,《知言》,《胡宏集》第20页。)如此,便是明君。“学问之道,但患自足自止耳。若勉进不已,则古人事业决可继也。”(《与彪德美》,《胡宏集》第136页。)作学问患在自满自足,自满自足,就不会继续艰苦的坚持学习,就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其六,死生之道。孔子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胡宏认为人的生死与道的关系,犹如鱼与水、草木与土地的关系。“鱼生于水,死于水;草木生于土,死于土;人生于道,死于道,天经也。饮食、车马、衣裘、宫室之用,道所以有济生者,犹鱼有蘋藻泥沙,草木风雷雨露也。”(《仲尼》,《知言》,《胡宏集》第17页。)生从何来?死从何去?这是人的终极关切的大问题,也是形而上的哲学话题,人生于道,死于道,这是“天经”的合理性、自然性。饮食、衣裘提供了人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是用而不是体,不是之所以生死的本源和根据。换言之,道是生的源头,死的安顿,精神的寄托。这种精神的寄托,不在乎老病之人,不是老病之人亦然。“老人、病人、衰人有死之道,然以目前观之,死者亦未必便是老人、病人、衰人。”(《与彪德美》,《胡宏集》第137页。)道是每个人的归宿,精神的家园。
就人生的具体过程而言,“天地之间,有气化,有形化。人之生,虽以形相禅,固天地之精也。”(《姜嫄生稷》,《皇王大纪论》,《胡宏集》第225页。)人的生是天地精华的结晶。如此,作为天地之精英的人,“生不为名利累,死不为儿女悲,临大变,质诸义,无愧辞,全天归之,可谓仁矣。”(《彪君墓志铭》,《胡宏集》第186页。)合乎仁道,即合乎天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合天地之道者也。”(《西方佛教》,《皇王大纪论》,《胡宏集》第224页。)这样,人的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便是度越现实人的生死的形而上的终极关切的道体。
统观上述,道是度越形而下现实生存世界器物活动、日用活动的所以然者,是对道的道的追究,道是实存的,人只能陈述它,而不能造作它;道是参天地,育万物,与日月并明。“道参天地,明并日月。”(《天命》,《知言》,《胡宏集》第3页。)道是万世长存的,“斯道也,与天地相并,造化相关,亘万世而长存。”(《邵州学记》,《胡宏集》第157页。)道与天地相并存,造化相关联。道是外度越的形而上实存,又是终极关切的精神家园。.
三、性与心情
“天命之谓性”,“天者,道之总名”(《知言》,《胡宏集》第42页)。道之在天为天道,在地为地道,在人为人道。“人之道,奉天理者也。自天子达于庶人,道无二也。得其道者,在身,身泰;在家,家泰;在国,国泰;在天下,天下泰。失其道,则否矣。”(同上。)天命犹天道,天命在人为人的天性,犹道之在人为人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为人的仁义德性。“天命为性,人性为心。不行己之欲,不用己之智,而循天之理,所以求尽其心也。”(《知言》,《胡宏集》第4页。)胡宏把作为时代理论思潮的理气心性核心话题,疏解为天——性——心的逻辑结构,这也是对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逻辑次序的倒置。一是由外向内推演,一是由内向外推演,但其联接天和心的中介环节是性,性是天心内外的之所以构成整体逻辑次序的关键,凸显性的价值和地位。“万物生于天,万事宰于心。性,天命也。命,人心也。”(《修身》,《知言》,《胡宏集》第6页。)万物生于天,万物之性是天命的;万事由心主宰,万事的命令是心主使的。构成天、性、心、命与万物万事的关系。在这种错综关系,胡宏对性的规定是:
其一,性为形而在上者。“形而在上者谓之性,形而在下者谓之物。性有大体,人尽之矣。一人之性,万物备之矣,论其体,则浑论乎天地,博浃于万物,虽圣人,无得而名焉;论其生,则散而万殊,善恶吉凶百行俱载,不可掩遏。”(《释疑孟》,《胡宏集》第319页。)《周易·系辞传》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胡宏将其诠释为形而在上与在下,在上与在下是位置的差分,而非哲学逻辑意义上的体与用、本质与现象、本体与表现的差分。并以性与物替代道与器。在这里性与道相圆融,器与物相融合。所以《知言》器物连用:“无德,则器物而已矣。”(《天命》,《知言》,《胡宏集》第2页。)道性与器物相对应、相贯通。形而在上与在下的性与物虽有此分,然分而不离,上下相依,互相包涵,“性外无物,物外无性。”(《修身》,《知言》,《胡宏集》第6页。)凡物都有物性,无无性之物;凡性体现在物中,无无物之性。性与物互渗、互济。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故万物生于性者也,万事贯于理者也。”(《皇王大纪序》,《胡宏集》第165页。)万物生于性,性为万物的化生者,理贯通万事。
其二,性具万理。“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类指一理而言之尔,未有见天命之全体者也。”(《一气》,《知言》,《胡宏集》第28页。)性广大而具万理,由于天地万物各具其性,所以由此而立得住。世儒往往以一理而言性,而不见天命之谓性,是指全体万理者具有性。譬如“夫人目于五色,耳于五声,口于五味,其性固然,非外来也。圣人因其性而导之,由于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阴阳》,《知言》,《胡宏集》第9页。)目、耳、口对于五色、五声、五味的分辨,是目、耳、口的本性,不是外来的。这种种万物的性,都是性所本来具有的,犹如性具万理。“天命不已,故人生无穷。具耳、目、口、鼻、手、足而成身,合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而成世,非有假于外而强成之也,是性然矣。”(《修身》,《知言》,《胡宏集》第6页。)成身成世、肉体自然之身体与社会伦理之世界,不是假外力而成,是性的使然,性便成为身体与社会的根源。
其三,性为气本。“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其气之本乎!”(《事物》,《知言》,《胡宏集》第22页。)无物没有性,即凡物皆有性,性是气的本性。“气之流行,性为之主。性之流行,心为之主。”(《事物》,《知言》,《胡宏集》第22页。)性主使气的大化流行,心主使性的大化流行。因为“气感于物,发如奔霆,狂不可制。”(《事物》,《知言》,《胡宏集》第22页。)气与物相感应,就会出现狂不可制约,所以需要性主使制约其大化流行。这是因为气有性。“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气有性,故其运不息;德有本,故其行不穷。孝悌也者,德之本欤。”(《好恶》,《知言》,《胡宏集》第11页。)水流不息,木生不穷,是因为水有源,木有根。气运不息,与水木一样是气有性。犹德有孝悌之本,从自然万物到社会伦理,其活动运行,都有其根源,而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性之气,无本之行。
其四,性有质用。“子思子曰:‘率性之谓道。’万物万事,性之质也。因质以致用,人之道也。”(《往来》,《知言》,《胡宏集》第14页。)万物万事者具其本性,这种本性即其本质,是天赋予的,使其本性、本质发生作用,那是人道。为什么人能使万物万事的本性致用?是因“人也者,天地之全也。而何以知其全乎?万物有有父子之亲者焉,有有君臣之统者焉,有有报本反始之礼者焉,有有兄弟之序者焉,有有救灾恤患之义者焉,有有夫妇之别者焉。”(《往来》,《知言》,《胡宏集》第14页。)人之所以能致用,是因人是天地之全体,有父子之亲、君臣之统、报本之礼、兄弟之序、夫女之别、救灾恤患之义。这就是说,人具全体的智慧,而禽兽不得其全。虽然禽兽目可视,耳能听,与人同,但“视万形,听万声,而兼辨之者,则人而已。覩形色而知其性,闻声音而达其义,通乎耳目之表,形器之外,非圣人则不能与于斯矣。”(《往来》,《知言》,《胡宏集》第14页。)人能辨别万形万声,这是禽兽所不能的。若能看见形色而知道其性,听见声音而通达其义,这就是圣人了。意谓万物万事都有其本性,也各有其用。人性与兽性不同,其用亦不同。人之所以与禽兽性异用异,是因为人能各正性命,“人也,性之极也。故观万物之流形,其性则异,察万物之本性,其源则一。”(《往来》,《知言》,《胡宏集》第14页。)从源头上看,万物的本性是一,这就是说,性的质一,而用的流形是异是多。
其五,心性之性。心性是道学家哲学的核心话题,他批评佛教徒,“曾不知此心本于天性,不可磨灭,妙道精义具在于是。……今释氏不知穷理尽性,乃以天地人生为幻化。此心本于天性不可磨灭者,则以为妄想粗迹,绝而不为,别谈精妙者谓之道。则未知其所指之心,将何以为心?所见之性,将何以为性?言虽穷高极微,而行不即乎人心。”(《与原仲兄书二首》,《胡宏集》第120—121页。)“心本于天性”,即心以性为本,性本永远不可磨灭,妙道精义都在这里。但佛教徒不知穷理尽性,以天地人生都是幻化,执着识心见性,而不知心以性为本的性本是不可磨灭的,又别谈精妙为道,是不知何以为心、何以为性。
胡宏在心性关系上,主张性本心用。这就与程朱等所说“心统性情”有异。胡宏说:“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情犹水之澜,欲犹水之波浪。”(《往来》,《知言》,《胡宏集》第13页。)他把性喻为水,心、情、欲都是水之下、水之澜、水之波,这是水所表现的不同状态。心、情、欲之所以具有不同的状态,其根源、根据是水,无水哪里有水之下、之澜、之波。换言之,无性,心将不存。心以性为本,是性所表现的一种状态。虽然“性主乎心”,但是“性定,则心宰。心宰,则物随。”(《义理》,《知言》,《胡宏集》第30页。)性定以后,心便具有主宰功能,物随心主宰。
尽管心本于性,心是性表现的状态,但是性必须通过心,才以彰显其价值,这就是心体现性。“曾子、孟子之勇原于心,在身为道,处物为义,气与道义同流,整合于视听言动之间,可谓尽性者矣。夫性无不体者,心也。”(《仲尼》,《知言》,《胡宏集》第16页。)认为曾子、孟子的视听言动合于礼(理),穷理(礼)尽性,原于心之勇,心的行为活动体现了性。“命有穷达,性无加损,尽其性则全命。”(《中原》,《知言》,《胡宏集》第46页。)胡宏认为,“命,人心也”,人生的穷与达关乎心的正邪,人的本性是固有的,不可加减。穷理尽性,才能使天命得以保全。
由心性而推及性、心、情。“探视听言动无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视听言动不息之际,可以会情。视听言动、道义明著,孰知其为此心?视听言动,物欲引取,孰知其为人欲?是故诚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动,心妙性情之德。”(《事物》,《知言》,《胡宏集》第21页。)视听言动是性本表现的一种形式,探究视听言动表现形式的本源,可以知道性;观察视听言动活动不息之际,可以与情相会。然而,视听言动作为外在表现,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道义明著,视听言动合乎道义;二是被物欲所蔽,视听言动为人欲所累。据此,必须诚意正心,以成就天下的性,情效法性诚而动,心妙用性情的德性。“义理,群生之性也。义行而理明,则群生归仰矣。敬爱,兆民之心也。敬立而爱施,则人心诚服矣。感应,鬼神之性情也。诚则能动,而鬼神来格矣。”(《义理》,《知言》,《胡宏集》第29页。)义理与道义意思相通,是众生的本性。义理著名,民众便有敬爱的心,这样众生归仰而人心诚服,就可与鬼神的性情相感应,而来格。
胡宏天——性——心的逻辑结构而开出性是形而在上者、性具万理、性为气本、性有质用,心性之性等内涵的规定,是一贯通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范畴,与胡宏所说的性相应的是道,他将道规定为道为太极、道充塞天地、道外无物、道为仁义道德、道合体用、死生之道等义理,也是形而上与形而下圆融的范畴,且是一终极关切的精神家园。基于此,胡宏往往道性连用。“命之理,性之道。”(《天命》,《知言》,《胡宏集》第3页。)“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德合天地,心统万物,故与造化相参而主斯道也。”(《往来》,《知言》,《胡宏集》第14页。)穷理尽性,由尽人性推及尽物性,参天地,育万物,而主于这道。这道为性之道。他批判佛教徒穷理与尽性、道与性的不能合一。“释氏见理而不穷理,见性而不尽性,故于一天之中分别幻华真实,不能合一,与道不相似也。”(《往来》,《知言》,《胡宏集》第13页。)这就是说,心、性、情都不能离道,由道统摄,一以贯之。“昔孔子下学而上达,及传心要,呼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曷尝如释氏离物而谈道哉?曾子传子思,亦曰:‘可离,非道也。”见此,则心迹不判,天人不二。”(《与原仲兄书二首》,《胡宏集》第121页。)佛教离物讲道,道就不能贯通形而上下、内外、主客。道被悬置而失去其价值。心是内,迹是外;心是主体,迹是客体;天是外在客体,人相对天而言是主体。心迹不分判,天人不二,即言内外、主客不判不二,而为一。换言之,道外性内,道客性主不判不二;胡宏这一思想路线,是其对父兄胡安国、胡寅“心与理一”思想路线的继承和阐扬。(张栻说,胡宏“自幼志于大道,尝见杨中立先生于京师,又从侯希圣先生于荆门,而卒传文定公之学。”(《胡子知言序》,《南轩集》卷14,《张栻全集》第755页。)可见是继承胡安国之学的。心理为一与道性为一的形而上学本体学,是对于程朱心与理二分与陆九渊“心即理”的心理为一的融突和合的实践。这一实践既体现了两宋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又凸显了湖湘学哲学理论思维的个性和特色。正由于胡宏的道性形上学的本体学的哲学个性和特色,而为湖湘学奠基,并为湖湘学与程朱道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奠定基础,与其学生张栻哲学思想发展开出新的精神路向。
B2
A
1004-3160(2012)01-0072-07
2011-12-01
张立文,男,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国学研究院院长、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
责任编辑:叶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