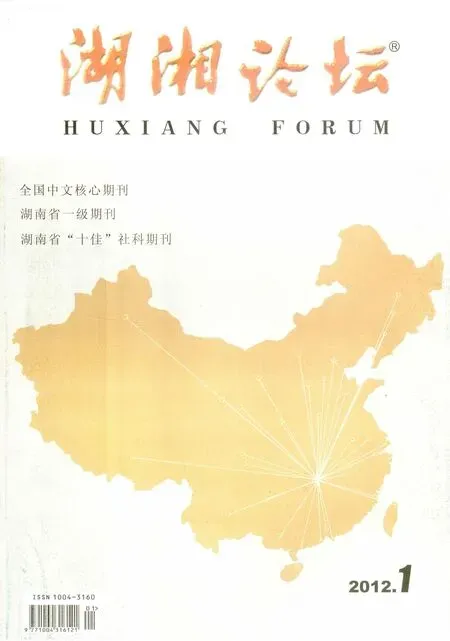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儿童形象的比较研究(1860-1879)*
夏益群
(湖南商学院,湖南长沙410205)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儿童形象的比较研究(1860-1879)*
夏益群
(湖南商学院,湖南长沙410205)
基于美国学者费伦·詹姆斯分析人物模式的理论,比较分析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儿童形象三方面的不同表现:儿童故事;诗化与悲苦的交织、观念儿童;纯朴与神圣的象征、儿童建构;展示与讲述的同构,从中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笔下如白昼般快乐、光明的儿童乐园转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如地下工厂般阴森、悲苦、阴暗的儿童世界,从而领略两位艺术大师的艺术魅力。
儿童故事;观念儿童;儿童建构
梅烈日科夫斯基说,“在俄罗斯文学中,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更为内在地近似、同时又更为对立的作家是没有的。”[1]P39梅日烈科夫斯基这一论述是从二位大师源于普希金这一基点出发的。事实上,两位大师在生存信念、艺术手法于迥异中又有类似之处。这时期两位文学大师笔下没有出现以儿童为主人公形象的小说。在其宏篇巨著中,儿童形象只是成为小说的一个极不起眼的部分。也就是说,十九世纪六七十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中都出现了大量的不成其为主人公的儿童形象,而在对儿童的认识理解上、儿童形象塑造上有着各自的特点与侧重。
这两位大师笔下的儿童形象虽说只是一种“浅吟低唱”,但在小说叙事中不仅承担各种功能,带动情节的发展,而且本身是具有行为心理可信度的孩子,是关于某种现实生活的一组象征性图示。
申丹教授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一书中将叙述中的“功能性”人物观和传统批评中的“心理性”人物观进行了详细地对比分析。她认为,“功能性”的人物观是把人物看作是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而“心理性”人物观是把人物看成是具有心理可信性和心理实质的人。不仅如此,她在分析查特曼、米克·巴尔等国外学者人物叙事特点的基础上,指出应注意这两种观点适用范围、局限性和互补关系。刘为钦在《“功能”与“审美”:人物解读方法的可行性研究》中提出了将“功能性”分析方法和“审美性”分析方法有机结合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美国学者费伦·詹姆斯在分析人物模式时将人物的“功能性”和“心理性”相结合,提出了分析人物模式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模仿的(作为人的人物);主题的(作为观念的人物);综合的(作为艺术建构的人物)。[2]P4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形形色色的孩子们,既可从叙述学的角度被视作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也可以从传统的批评理论中出发被视作具有某种“心理”现实的人。这两者无法截然分开。
笔者认为,费伦·詹姆斯的这种分析方法能有利于在两位大师宏大的叙事进程中,将处于小说文本“边缘”处的儿童形象塑造的策略与观念更好地表达出来。下文试以这三个因素为依托,分别分析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儿童形象在这三个方面的不同表现。
一、儿童故事:诗化与悲苦的交织
费伦·詹姆斯提出的第一个分析人物的因素为模仿因素,是作为人的人物,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模仿。具体到儿童形象而言,是指作为儿童的儿童,儿童的故事。托尔斯泰笔下的儿童故事多集中于贵族孩子或物质生活条件较优越的孩子的故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儿童多是一些穷苦孩子苦难的故事。各色儿童形象都是在两位伟人的宏篇巨著中部分地展开叙述。
卢那察尔斯基称,“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你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抽象概念或幻想,他的作品表现真正的生活。”[3]P338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托尔斯泰小说中多是些充满生命力的、家庭富足的孩子们。托尔斯泰贵族家庭孩子的故事多是些日常化的生活情境的描写,从而再现俄国社会贵族孩子们诗意化的生活状况和教育状况。《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家有两个可爱的孩子:黑眼睛、大嘴的娜塔莎,胖男孩彼佳。娜塔莎的故事是从其命名日大笑声中开始的。小彼佳却一心想去当骠骑兵,结果牺牲在战场上。安德烈公爵的孩子尼古卢什卡,从一出生就没有了母亲,七岁时父亲也去世了,他是由姑姑带大的。他想象皮埃尔那样聪明有学问,在彼埃尔和尼古拉争论时,他总是站在彼埃尔这一边。这是一个内心型的孩子。《安娜·卡列尼娜》中奥勃朗斯基一家的孩子们热热闹闹,有互相间的关心与争吵打骂。在母亲的管理下,他们的生活充满诗意与快乐:母亲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森林采蘑菇,一起去河边游泳,一起游戏;当格里沙被罚坐在客厅角落不准吃甜饼时,丹妮娅借口给娃娃过家家把自己的甜饼和格里沙一同分享;当丹妮娅和格里沙为了一只皮球,竟然两小孩发生你扯我捶的打闹。安娜的儿子谢辽沙因为和母亲的分开,这个无比幸福的孩子却变得忧郁而沉静,所有的功课都学得不太好,但他却并非是个无能力的孩子,不幸的孩子一直在期望见到母亲,从来都未曾相信母亲已死的谎言。托尔斯泰关于孩子们日常生活的故事,生气盎然,极富情趣。托尔斯泰以极其细腻凝炼的笔法描绘了孩子们日常生活的图画。梅烈日科夫斯基评价托尔斯泰,说其感染力的秘密在于“他能发现不明显、过于平凡的事物,但在意识的照明下,正是由于这种平凡性,那平凡事物才显得不同凡响”。[1]P186托尔斯泰笔下的贵族孩子们零星地散落在他的作品中,这些具有勃勃生机的孩子们,他们平淡日常化的生活无疑给小说增添了许多生趣。在他们幸福的童年生活当中,托尔斯泰寄托着对孩子们成长的理想的家庭模式和教育模式的关注。
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同,他笔下孩子们的故事多带上悲剧的色彩:出生的贫苦,人生路上的艰难,病态的性情,过早地离开人世。这些饱尝人世间苦痛生活的孩子们,大多是体弱多病。《被侮辱与被欺凌的》中的孤儿涅莉患有神经性疾病,无依无靠的她却被迫承担生活的困苦;《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为维护尊严、奋起反抗的伊柳沙,却因贫病交加走向了天国;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借伊万之口大量地书写了儿童的苦难:那些饱学的先生和夫人将孩子关在又冷又暗的茅房实行虐待,一大群狗将一个砸伤主人狗的孩子撕成碎片;《鬼》中斯塔夫罗金对一个十一岁少女玛特廖莎进行强暴;《小小图景》中那些病恹恹地散步在彼得堡大街上的孩子们个个东倒西歪;《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那些在伦敦草市的小女孩却被迫卖身;《罪与罚》中马美拉多夫家的孩子们骨瘦如柴,常常恐惧地哭泣着;《永久的丈夫》中八岁的丽莎衣衫褴褛,神经质地啜泣,等等。这些苦难孩子的故事是对这个黑暗社会最强烈的控诉。
“所谓‘模仿性’,是指这些小说中的孩子多多少少都是对现实中可能有的儿童的‘写实’。”[4]P14同是在十九世纪六七年代创作的小说,在对现实模仿之下小说儿童形象的再现在两位大师笔下截然不同,这与两位大师自身的人生经历与创作取向有关。托尔斯泰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贵族地主家庭,而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大量田产的贵族地主,对贵族孩子真实地、细节性地、诗意地生活地再现,也是托尔斯泰自身生活的一种写照。此外,“托尔斯泰表达每件事的时候,能使你看见书本,忘掉作者,——而这正是人所设想的最高艺术。”[3]P339托尔斯泰将对贵族孩子们的叙说完全把读者带入了一个单纯的孩童世界。孩子们的哭与笑,打与闹,悲伤与忧郁,都是一幅幅无比生动的生活场景画。托尔斯泰笔下儿童的“既非生活在过去,又非生活在将来,而是生活在现时”的生存方式也是托尔斯泰所向往的。在他看来,儿童的童性特征是与年龄无关的,“这种特征的不可磨灭的痕迹终生都陪伴着他”。[1]P4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一个军医的家庭,阴暗的童年生活、生活的艰辛与困苦以及其长年的疾病缠身,也使他笔下的孩子带上了更多阴郁的色彩。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到当时俄国文学表现贵族生活的倾向,在他看来那只是俄国社会中的一个偏僻的角落,贵族生活的图画已经是属于历史,他着力表现的是处于混乱和变动中的现实。因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更多的是关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们的故事。
二、观念儿童:纯朴与神圣的象征
费伦·詹姆斯作为主题的人物类型,是一种作为观念的人物。小说文本中儿童形象因为自身的弱势地位和无法言说性,始终只能让成人成为其代言人。小说家在为儿童代言之时,始终无法摆脱成人的观念,也就是说儿童始终是成人笔下的一种观念的表达。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儿童形象常常是作为一种高于成人的观念化形态得以表现的。但是两位大师又各有不同的侧重表现。托尔斯泰强调的是儿童那种怡然自乐、超乎于俗利之上的淡泊之心。儿童之高于成人正因为其生活的单纯、纯朴。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力图表现的是儿童作为成人的拯救者的观念,以及儿童的神性与圣性观。在他笔下,儿童是人间天使,是至纯者基督,是未来的希望。
托尔斯泰在其长篇小说中对高于成人的孩子们的童稚之心常有表现。《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率领军队从斯摩棱斯克撤退,觉得一切都暗淡悲惨,来到度过童年的田庄童山,看到两个姑娘用衣襟兜着从暖房采来的李子跑过来。这两个小女孩因为突然看到主人而慌忙地躲起,更来不及拾起地上掉下的青李。在这样一种兵荒马乱的时候,这两个小孩如若生活在世外桃园,享受着采摘果子的情趣:把青李带走,吃光,而不被抓住。正是孩子这般逍遥于尘世之外的生活和性情,使安德烈的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欣慰感。因为安德烈从孩子们身上看到了“世上还有另一种对他完全陌生的、然而是他同样感到兴趣的、合情合理的人性的存在。”[5]P139从这里可看出,托尔斯泰从安德烈于孩子身上得到的启示的叙述,将孩子置于成人之上,以孩子的诗意生活观带给成人的存在更大的启示。《安娜》中安谢的儿子谢廖沙尽力想去弄清母亲和伏伦斯基间微妙的关系,但却始终也没弄懂,但是孩子却对于安娜和伏伦斯基来说却好象在大海航行中的“罗盘”,因为孩子有他对人生天真纯朴的看法,“因此他就好像是一个罗盘,在给他们指出偏离正路的程度,他们知道正路是什么,但是却又不愿意知道。”[6]P162《家庭幸福》中的玛莎抱起自己的孩子,孩子虽无法开口说话,但是孩子那一双闪现着思想火花的小眼睛盯着她,脸上浮着微笑。而在之后,玛莎结束了与丈夫的恋爱关系,开始了一种崭新的幸福生活。从托尔斯泰小说中可以看出,他把孩子当作成人生活的“罗盘”,能指出成人生活是否偏离了方向,因为只有孩子才是世上最纯洁的人。正如丰子恺曾说,孩子具有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从孩子眼里我们能透过尘世的烟雾看到生活的真谛。因为孩子能诗意地存活于世,他们喜欢春色迷人的早晨,以及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的美。而成人欣赏的只是自己统治人的手段和权利。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儿童与已经世俗化的成人保持着距离,是天堂的光芒,是人类的未来。他笔下那些因受尽人世苦难而贫病交加进入天国的孩童躯体上,没有暴力和血腥的痕迹,却发出神性之光。“小小的涅莉置身于鲜花丛中的小棺材里,消瘦没有生气的小脸,却有着凝固的微笑,两手交叠在胸前。”[7]P376走入天国的伊柳沙也是如此消瘦,尸体没有异味,表情严肃如在沉思,小手一样交叠在胸前。地下室里的小男孩和那些冻死在襁褓里,寄养在育婴堂被折磨而死以及闷死在车厢里的孩子们一块参加天堂耶稣的圣诞晚会。虽是作者的一种虚构,也是作者对儿童生命的理想化和神化。小说中的孩子往往以天国的主人,人间基督的形象出现,来拯救成人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己的苦役流放经历创作的《死屋手记》中,一位如天使般的小女孩出现在“我”沉闷阴郁的死屋生活和在那些忧郁狠毒的苦役犯当中,她请求“我”看在上帝的面上收下一块铜板。这块铜板长久地保存在“我”的身边。这位纯朴的小女孩是“我”在死屋黑暗生活中的光亮。《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中小涅莉被“我”称为小天使,成了大人世界中的救星。她向娜塔莎的父母讲述了自己和母亲的苦难生活,唤醒了老人因自尊而埋藏于心底的父爱,让娜塔莎一家幸福地团圆了。《白痴》中和梅斯金公爵一起在瑞典的孩子们帮助患肺病的玛丽忘却了自己悲惨的厄运。《一个荒唐人的梦》中的“我”,在生命百无聊赖之际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街上一位八岁光景的小女孩悲切地呼唤我去救救妈妈,此事唤起我心底的恻隐之心,“我”热切地想去帮助那个小女孩。事实上小女孩真正成为了“我”灵魂的拯救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篇著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也对孩子们作了更精彩的描写。小说中作者借伊万之口说道,即使肮脏、难看的孩子也可爱。小说中的伊柳沙是一个被人瞧不起,但是人格高尚的贫民孩子,九岁便知道什么是世上的真理,勇敢地维护自己的父亲。小说中和郭立亚一起的这帮小孩子们对病榻前伊柳沙的关心与爱护,与尔虞我诈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间的成人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辽沙和孩子们才代表着一种人类最高的理想,一种孩童式的、基督式的美好理想。
孩子们使人们的生活在最高意义上富有人性,只有在孩子们的身上,我们才能发现人类生存之美。我们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圣洁的儿童形象中看出其是把儿童置于一种高于成人的地位,儿童成为作者言说自我理想的一种“符号”。
普世教会的“最高祭司(真正的、永恒的父辈的代表)只是在孩子的生命里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命。”[8]P206两位大师同样如此,以儿童形象来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认识。托尔斯泰从儿童日常生活琐事之中,以儿童道德感情的纯洁为出发点,表达一种超乎世俗的、自然的童真生活。在托尔斯泰看来,“人的童年,比后来处于教育腐化影响下的生活更和谐。”[9]P294托尔斯泰在其小说儿童形象上也试图表达这种自然、和谐的生活理想。故而其对儿童是一种基于和谐现实之上的儿童纯真观。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高度颂扬儿童的天真和纯洁,而且将神性赋予儿童,儿童成为拯救世人的基督的化身。
三、儿童建构:展示与讲述的同构
费伦·詹姆斯分析人物时的第三个因素是综合的人,即作为艺术建构的人。儿童作为小说中的一人物形象,因为其自身的独特性,它在艺术建构方面有着独特的艺术特点。
儿童形象在小说中被建构,有两种方式:展示与讲述,它们是叙事文学塑造人物形象最基本的方法。讲述是作者在作品中有明确的讲述人身份,以全知性的整体通观而展开的对人物的叙述方式。展示则是一种倾向于让人物直接站到读者面前,对之进行叙述的方式。它偏重的是对人物的心理和动作进行展示性的描述,而不要经过作者间接的讲述。[10]P151-154但事实上,小说就是一种讲述方式,在小说文本中我们不能把展示与讲述截然分开,而只能说,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时对使用这两种方式进行故事讲述时各有偏重和特色。
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儿童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法来看,托尔斯泰注重的是展示与讲述儿童日常生活相结合的手法,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注重的是以讲述的方式戏剧性地展示儿童纯洁的或梦幻的、病态的、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
托尔斯泰笔下的孩子的出场是往往是先闻其声再见其人,而后再做进一步深入的描写。《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儿子谢廖沙的出场是在他大叫着“妈妈,妈妈”声中出现的。作者展示了谢廖沙出场的场景:从楼梯上一下子跳过来,双手吊在母亲的脖子上,而后托尔斯泰描写了这个孩子的外貌:“淡黄色的卷发,天蓝色的眼睛,裹着紧身长统袜的两条结实挺拔的小腿。”[6]P106接下来作者又以讲述的方式描写了谢廖沙对于母亲和伏隆斯基关系的感觉。在小说接下来的章节中,托尔斯泰展示了在谢廖沙过生日的前一天和看门人之间的对话,他们对一个缠绷带的小官员的共同关心。在此之后,托尔斯泰又加入了几句谢廖沙对帮助小官员和收到礼物心情的评述:“谢廖沙觉得今天是一个人人都应该快乐开心的日了”。[6]P516托尔斯泰又以“展示”的形式叙述阿廖沙的学习情况,天性好奇的孩子总是提出许多与学习无关的问题,却得到的只是“我不知道的”回答。父亲和老师对他的学习都不满,但是作者并不是如此看待孩子的成长的,小说中加入了作者的一段评述:“他现在九岁,他还是个孩子;但是他知道自己有—颗怎样的心,他珍惜自己这颗心,他保护这颗心,就像眼皮保护眼珠一样,没有—把爱的钥匙,他是不会让任何人进人他心中的。教育他的这些人抱怨说他不愿意学习,但是他心中充满着求知的欲望。于是他跟卡彼托内奇学习,跟保姆学习,跟纳金卡学习,跟华西里·卢基金学习,可就是不跟教师学习。父亲和教师期望那股水流进他们水磨上的轮子里,可是这股水早就漏掉了,流到别处去发挥作用了。”[6]P521托尔斯泰认为,儿童与农民一样,是心灵尚未腐化者。从对谢廖沙的教育中,也可看出,托尔斯泰从儿童的身份出发极力地反对所谓破坏纯真的教育,在托尔斯泰看来“真正地教育须是儿童与尚未世故机巧的无知之人能顺遂地、渴切地吸收的一种教育。”[11]P286托尔斯泰惯常的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就是“从可见到不可见,从外在到内在,从肉体到灵魂,或者,至少,到‘精神’”。[1]P174托尔斯泰笔下的谢廖沙形象也正是从外在形貌、平凡生活到内在精神气质逐一加以表现的,并从儿童身上更进一步体现出作者自身的教育理念。“托尔斯泰在小说创作方法上带来了一个改变,他从旧有的、戏剧式的方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的还是这种旧方法)跳上了一个新方法——‘有观点的方法’。戏剧的方法只表现人物的行动和语言,不予以解释。托尔斯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从没有在表现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时不予以解释的。在他看来,心理上的解释是一件重要的事。重要的不是人物做什么,而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12]P413-414托尔斯泰在塑造儿童群像时既通过生动的戏剧化的描写来赋予人物形象以生动性,同时也以直接地分析、说明和评价,或者讲述,来实现与读者进行的精神交流。
不仅如此,托尔斯泰在讲述儿童故事的同时,通过儿童的“观看”来展示成人的生活,表达某种思想观念。《战争与和平》中彼佳对皇帝游行队伍的观看,小姑娘对来到童山庄园的安德烈公爵的打量,六岁玛拉莎对在自家开的军事会议目不转睛地“瞧”,尼古连卡对皮埃尔与尼古拉的观战,以及《安娜·卡列尼娜》中奥勃隆斯基家的孩子们对姑姑安娜的诸多看法,谢辽沙对母亲安娜和伏伦斯基的认识,《家庭幸福》中玛莎的孩子用那双闪耀着思想火花的小眼睛对“我”的盯视,甚至在托尔斯泰晚年的作品《复活》中也有诸多儿童观看的描写:孩子们对女强盗(玛丝洛娃)的恐惧地望,牢狱中一个犯人七岁小女孩对监狱生活的看与学,豪华马车里的小女孩和小男孩对犯人不同的看法等,表明了孩子是成人世界中的一个“罗盘”,托尔斯泰借儿童之眼看成人世界,在孩子纯真的眼眸中,表现的是作者的观点和看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孩子们的故事常常是作者讲述故事中的一个部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孩子们的故事又常常是以展示的方式出现的,即作者让孩子们以自己的方式展示在读者面前,通过自己来显示自己的“性格”和“品行”,而没有任何附加的评论或说明,与此同时又将小说儿童的故事戏剧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戏剧诗学中‘示’的概念引入小说诗学‘述’的概念之中,从而一改传统小说对全过程的娓娓而徐然的叙述,开创了直接切入过程的剖面来淋漓地展现的先河,并由此导致了小说的风格不再是生动而是紧张。”[13]P1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悲剧性的孩子们的故事也往往是关注的“一个切面或点”,而不是儿童故事发展的全过程,不是全面地、巨细无遗地加以描写,而是直接切入、开门见山、突然展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儿童故事常常是扣人心弦的紧张的烘托,其往往是从“一个顶点转入另一个顶点,从一种迫切情势转入一种急切境况”[13]P13。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中小女孩涅莉的出现是出人意料的:“我”搬到已故老人叶列米亚·斯米特的寓所,当我产生出门回家后又会见到老人的奇怪想法时,一个小姑娘推门而入来到“我”的房子,向“我”打听外公和狗阿佐尔卡,孩子的神情是木然而病态的。在她惊叫一声后,匆匆离去。小女孩就以这样直接地方式而突然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在这之后,小说又停止了对涅莉的叙述,只到小说第二部涅莉重新出现,我跟踪她并把她从火坑里救出,带到我的家里。小女孩由冷漠地拒绝“我”到真心地热爱“我”,其多疑而有点变态的性格一点点得以呈现。小女孩的悲惨的身世也是在叙述中得以逐层展现,最后可怜的孩子被伊赫缅涅夫一家收养。当伊赫缅涅夫老人为涅莉的故事而感动原谅了自己的女儿,一家人团圆时,涅莉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随着涅莉的离开人世,她的人世之谜也得到了最终的揭开。小女孩涅莉的故事不是以讲述的方式按人的生命时间发展的顺序展开的,而是以空间的骤然转变而展开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小男孩伊柳沙的故事也是以如此的形式得以呈现的,由我路遇一群放学的孩子和伊柳沙的石头战开始,伊柳沙的身世得以缓慢呈现,而当孩子们之间变得互相关爱时,伊柳沙却已经病入膏肓,悲惨地离开人世。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儿童形象时,并不是以一种慢条斯理地、含蓄地方式加以叙述的,而是以儿童出其不意地出场展现其个性,又以情节的陡然急转来展开孩子的身世,孩子的一切不是以生动来形容,而是紧张而又充满激情,孩子的生活逐层得以展现。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托尔斯泰塑造笔下的儿童形象是富于诗意的,就如一个人淋浴在春风里,慢慢地与你一同回忆着无比美好的童年往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儿童形象却仿佛把人引入了一个神奇的迷宫,在对孩子命运的好奇与担忧之下,读者迫不急待地要将故事读完,终不忍释卷,而为孩子的生命慨叹不已。两种建构儿童形象的不同方式,带给我们的却是不同的审美感受。
四、结语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高尔基誉为“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艺术力量使整个欧洲都转而注目俄罗斯。他们笔下的儿童形象只是他们艺术特色的一个方面的体现。儿童或作为长篇巨作中的一个小小的故事,或作为作者观念化的一种表达,或作为文本的一种艺术建构技巧,在文学大师的长篇小说中扮演着“边缘化”的角色。
威廉·白瑞德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到托尔斯泰,有点象从某个地下工厂的阴森气息走进光明的白昼。”[14]P141我们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儿童形象在小说文本中的“浅吟低唱”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出,我们是从托尔斯泰笔下如白昼般快乐、光明的儿童乐园转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如地下工厂般阴森、悲苦、阴暗的儿童世界。我们无法评析其优劣,更无法对之做出高下之分。艺术的丰繁复杂,为我们领略艺术的多姿多彩提供了一个天地,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为之流连忘返,也可为之扼腕长叹,这都是艺术的无穷魅力所在。
[1][俄]梅烈日科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M].杨德友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美]费伦·詹姆斯.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伦理、意识形态[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倪瑞琴.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何卫青.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儿童视野[Z].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4.
[5][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M].刘辽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6][俄]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M].智量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6.
[7][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M].娄自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8][俄]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M].张百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9][英]以塞亚·伯林.俄国思想家[M].彭淮栋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0]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1][俄]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M].智量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6.
[12][英]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
[13]季星星.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化[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4][美]威廉·白瑞德.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根源[M].彭镜禧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I1
A
1004-3160(2012)01-0091-06
*本文系2010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儿童形象研究和儿童教育》[编号:2010WLH27]的阶段性成果。
2011-09-02
夏益群,女,湖南益阳人,湖南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俄苏文学。
责任编辑:秦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