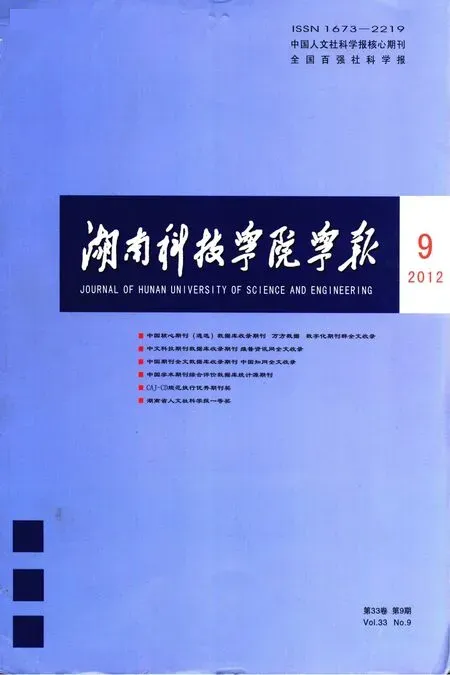单向度的叙述
——论《中国在梁庄》兼及叙事伦理
陈桃霞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单向度的叙述
——论《中国在梁庄》兼及叙事伦理
陈桃霞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为近两年受众面较大的一部非虚构文本,《中国在梁庄》的价值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虽然具有口述实录性,但因作者极力规避又无法消除的先入之见与抒情性话语使文本呈现出较为单一的声音,浅尝辄止的分析使其深度不够,同时也违背了基本的叙述伦理。
《中国在梁庄》;非虚构文学;单一话语;叙事伦理
2010年末沉寂的文坛因梁鸿《中国在梁庄》的出现而热闹起来。该书最初以《在梁庄》刊于2010年第9期《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并于当年1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以《中国在梁庄》出版。自2011年4月出了2版并第7 次印刷,成为畅销书,其影响力亦可由它所获得的奖项验证。它获得当年《人民文学》非虚构作品奖、《新京报》十大好书、《亚洲周刊》非虚构十大好书和新浪网十大好书。作者亦先后接受国内三十多家媒体的采访。在社会思潮多元化、众生喧哗的当下,该书能够超越不同意识形态,获得广泛的认同实属不易。同为非虚构文学,上世纪80年代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的杨显惠就无法享受这种殊荣了,他的《夹边沟纪事》在本世纪初的印数还不到万册,两相对比,引人深思。《中国在梁庄》赢得了普通读者与评论界的极大关注,李敬泽认为,“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阎连科、温铁军则分别从文学、社会视角对本书做了高度评价。本书以一个村庄为个案,通过梁庄近半个世纪的变迁折射出共和国一个群体的流变史,作者对乡村社会改革与市场双重侵袭下满目疮痍的面貌表示了担忧,而这种担忧在很多乡土作家与三农问题研究专家笔下都有呈现。
一
“非虚构文学”与“问题报告文学”近似,后者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后成为文学史上的一种强势存在,形成一股报告文学热,这是启蒙思潮下作家们社会责任感与现代反思意识的回归。新世纪以来,国家、精英与消费主义等多元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得报告文学作为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文种开始受到争议,尤以商业消费为目的的报告文学的喷涌使得人们冷落了这一文体。在此背景下,非虚构文学作为一个大的文类出现,并以其中立的价值立场与阔大的思想视野得到了越来越多批评家与读者的推崇和认同。新世纪以来各类文学期刊的口述实录栏目几成重镇,在挖掘历史、反思当下中,读者可以从众多历史幽深处获得自己的审美认知,这也是受众对各种虚构艺术疲软的一种反拨。作为口述实录性的非虚构文学,《中国在梁庄》由村庄一个个讲述人构成,作者努力贴近村庄,关注乡村的各种特殊群体——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村庄存在的紧迫问题——环境恶化、宗教信仰混乱,每章都由若干故事组成,使农村的各种问题感性鲜活,作者在每阙故事后面发表个人看法。“作为田野调查方式之一的口述实录,往往接近于口述历史或回忆录的形式,它本身有其局限性——例如,口述材料难免带有一种事后认识的因素,受访人的感情、态度、兴趣会导致记忆被有重点地选择和剪裁,这往往属于事后经历的形塑,并不能完全呈现访谈内容发生当场的情景。”[1]P78这也是该类文学的局限性,它一般只能表达历史性存在,而对共时性的社会现象的本质揭露则比较乏力。除“事后形塑”外,作者写作中的先入之见也会影响文本的真实,同时如何突破众多的口述材料,深入理解使文本向深度拓展也是对作者的严峻考验。
知识分子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他们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2]P4作为一名乡村知识分子,《中国在梁庄》是作者在离家近二十年后的还乡之作,是一次学者由书斋走向田野,饱含社会责任感的书写。作为土生土长的梁庄人,20岁离开家乡,这种回乡的念头在远离故土,旅居京城,从事大学教师工作后更为强烈。讲台上的高谈阔论与为写论文夜以继日地查阅资料构成了作者的日常生活,她由此怀疑其学术价值与生存意义。在无根的悬浮中,这位外省人渴望以一种回归重新融入故土,于是她利用2008、2009年寒暑假五个月回乡访谈完成了此书,当然相关精神上的准备则更久。知识分子还乡的主题在近现代作家笔下多次出现,从鲁迅、师陀到路遥、贾平凹、魏薇(其《异乡》、《回家》、《乡村、穷亲戚和爱情》通过一位女性离家后回家的种种际遇,进而书写了一个时代不断变迁着的人际伦理。)等,作家们对农村痼疾的揭露、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与农村一地鸡毛的现实都有生动而无奈的呈现。梁鸿师从鲁迅专家王富仁,她对鲁迅作品及其启蒙意识不会不熟悉,《中国在梁庄》以重回故乡的方式进入,以离开故乡收束,典型的归去来模式。与鲁迅相比,事隔近一个世纪的返乡,她所看到的景象竟与鲁迅惊人的一致。读师范时回家,“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常常的沟渠,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在沟渠边蔓延,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有着难以形容的清新与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然而,“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3]P6。肮脏的坑塘、废弃的砖窑、颓败的农舍让念兹在兹的家乡累累伤痕、盲目疮痍、物是人非,家乡在高歌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日益边缘化,并最终沦落为一个社会的病灶和整个民族的累赘。作者是这样评价自己的书写的:“我不认为这部书的内容有多深刻,文学性有多高,它的价值可能更多在于启发性。”“我的目的不在怎样表现出我的文学能力,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呈现他们的存在。”在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农民一直作为被牺牲和被忽视甚而漠视的对象,这些我们不难从各类媒体中获知,农村的衰败、农民工的迷惘、农村留守人员的伤痛已然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然而其呈现远不如作者这样集中,也未能表现得如此鲜活,唯此,才能产生一种事实上的震撼。如此触目惊心的农村图景,文学的表现却相当乏力,近年来这方面优秀的文本却不多,较有代表性的有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与贾平凹的《秦腔》,喧嚣的文坛似乎被消费主义浪潮裹挟得失去方向,世纪初以来争议纷纷的底层写作似乎也未能对此进行深刻的书写。在此情况下,纵观对《中国在梁庄》的评论,可以发现持高论者居多,论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肯定了作者对现实的介入意识。而“知识分子无论如何的平民化,都具有某种精英意识,在大众面前以启蒙者自居”[4]P234。因而梁鸿所说的“启发性”、“呈现他们(可以狭义地理解为梁庄民众)的存在”就显得虚妄,文本中充斥的多是作者个人的声音,而这种启蒙也未到达一定的高度。
二
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事实”的虚构性,这种“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决定的。如何悬置“我”先验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因为“我”的价值观将引导着“真实”的走向。梁鸿在写作中表示要过滤各种先入之见,尽量摈弃学术论文的语言,回归乡村的本真,尽量以客观冷静的写作呈现自己的对象。在回乡的火车上,作者翻阅的是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亨利·贝斯顿《遥远的房屋》,这本书是他1920年在人迹罕至的科德角海滩居住一年后写的散文集。作者被亨利·贝斯顿精湛的抒情所吸引,这似乎注定了她以一个外来文明的闯入者的姿态介入曾经的家乡。她倾心的是科德角的大海、海鸟、海滩与变幻莫测的天气,沉迷的是亨利·贝斯顿所描述的那种展示自然世界的神秘与美丽。“我不禁对即将展开的故乡之旅充满了向往。我的村庄、我的亲人、我的小河,还有小河中那刻有我青春记号的大树……我想象它们也有如是壮丽的风景,能给人带来如此庄严的思考。”[3]P3然而下车看到却是雨后泥泞不堪、垃圾随处可见的景象,以致儿子不敢下车。强调在叙事中抛开先验的作者,立刻以小见大,进行议论,定义县城的落后、脏乱。李敬泽表示,“非虚构”与某些纪实文学相比的优点在于,作家是怀着敬畏、谦卑的心态而接近真实,而不是“习惯了下车伊始,哇啦哇啦,真理在握,比谁都高明”,可是作者返乡的第一反应似乎与李敬泽的观点相左,她尚未进入村庄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对喜欢显示自己优越感的从部队复员回来、在西安蹬三轮的堂哥,对城里卖菜堂嫂的普通话及表现欲,作者明确表示出对其强势和自鸣得意的不满,“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常年的城市生活及对自己生活的满意使她产生了一种自信”[3]P219。这些在她所理解的乡村思维之外的已然在城里生活数年的梁庄民众,因不能纳入自己对乡村的理解范畴,作者也就直言不讳地以拒绝表现了自己的立场。恩格斯在给敏娜·考茨基的信中讲到,作者的政治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5]P385—386。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含蓄地表达思想,从而激发读者找出背后普遍性的东西。非虚构文学应以其客观的展示表现出作者的行动力,从而带动读者极大的阅读与探究的兴趣。相比于杨显惠作品以节制冷静的叙述和真实的力量来打动人,揭开回顾历史的盖子,激发读者重新反思苦难,反思人性,梁鸿的先入之见带来的是文本内涵的缺失与思考的乏力。
如果说诸多先入之见使原本饱含鲜活的细节与故事的文本呈现裂缝,作为文本叙述者也即梁庄现代历史的一个参与者,作者也很难保持对叙述对象的客观。“我”的一家20多口人温煦和睦,而梁庄中则或者如昆生一家寄居在墓地中、光河的丧失儿女之痛、菊秀那样的漂泊着永远生活在理想之外、清立那样的以恶抗恶、精神崩溃,此外还有姜疙瘩、五奶奶、清道哥,他们的个人与家庭生活都是不幸福的,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触目惊心地构成了农村的病灶,是农村形形色色问题的感性显现,而在梁庄生活的“我”的一家似乎独立于村庄之外。用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那段话所说的那样,非虚构文学并不应该抛弃而且也没有抛弃思维着客体的思维,尽管它看起来是那么的想隐藏住它。如果客体的思维带有偏见,是否会影响文本的客观呢?通过一个个梁庄的叙述者,作者为我们展示了梁庄近半个世纪来的变迁,提升了文本的历史感,然而,在记录这些被正统的历史叙述所忽略的声音之外,作者缺乏进一步的提升。在《今天的“救救孩子”》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启蒙的努力,这无疑是沿着五四启蒙的道路对历史与现实的追问,然而面对杀害八十二岁老奶奶的王家少年时,“我又能问些什么呢?一切的询问都是苍白的……”就轻松地卸下了启蒙的重担,展现给读者的只是一个“看”的场景与对象,这比现代文学作家笔下的“看”还要无力,使原本可以深入下去的话题戛然而止,文本成为个人的村庄见闻录,成为一地鸡毛。同样面对此案中的老单身汉钱家豁子、梁家光义,他们为何因被反复审问而神经错乱?可怕的真相同样在官民对立中神志不清的清立那里,作者没有进一步探究,使文本缺乏一定的深度,也即放弃了古尔德纳所谓的“批判性话语文化”,只剩下“黯然”。
三
作者在前言中表示要对语言进行编码、隐喻,表明自己的叙事只能是文学的,或类似于文学,而非彻底的‘真实’。由此可发现虽然作为非虚构文学,但作者的旨归更多在文学性上,文本随处可见的抒情性话语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本书更能为大众接受的原因。“从村庄后面常常的河坡走下去,是大片大片浓密的树林,林子里有养鹿场,还有一个小湖洼,湖上有成双成对的野鸭。一下雨,整个河坡青翠、深绿。少年时代,这条河陪伴我度过了孤单而又悲伤的初恋,也见证了我少女矫情的眼泪和自怜。”[3]P39文本这种充满个人情感的话语俯拾皆是。当然也有对历史的致敬,那就是对乡村半个多世纪的苦难史进行回溯,文本中充斥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官方到民间,从老人到同龄人,从回乡闰土到精神异常者,最后统领这一切的却是作者的话语。
黑格尔称中国历来就是一个“灾荒之国”,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农民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凄惨。《中国在梁庄》以一个村庄为摹本,通过其人事变迁,揭示现代化潮流下个体不同的悲剧命运,希望通过书写梁庄而达到描摹乡村中国的野心。不同于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非虚构文本的口述实录特征使其注意通过对个体的细致描摹来书写历史。而要了解历史,了解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应该关注“公共舞台后的私人空间,追寻迅速和动荡的历史脚步下深深埋藏的生命痕迹,去揭示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视、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6]。无疑,《中国在梁庄》为我们展现了真实生动为民间理解的历史话语:为现代化叙事所遮遮掩掩的三年自然灾害,通往死亡之路的养老院,“1960年都是贼,谁不偷饿死谁”,“咱们梁庄的梁家人1960年前有两百多人,1960年饿死六七十人,几乎是挨家挨户都有人死”。1962年的“四清”,重大历史事件折射到民间只剩下衣食温饱的奢求,清理贪污,浮夸风,“没胆量,没产量”。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以塞亚·伯林认为,历史的“内在事件”而不是公众事件,才是人类最真实、最直接的经验,因为生命过程是由而且只能由“内在事件”所构成。在作者笔下,我们看到的正是一个个卑微的个体参与了历史的建构,他们使一个村庄鲜活生动起来,这也是在全球化时代以地方性知识来抵抗遗忘、同化命运的尝试,当然他们多是以悲剧的无名者的形式存在。梁庄的韩、梁、王三大姓在父亲梁光正的叙述下娓娓道来(梁光正、七十岁,瘦骨嶙峋,颧骨高耸,双颊下陷,两眼混浊,佝偻在圈椅里,连轮廓都有些模糊了。这正是一位饱经沧桑的梁庄或者中国半个多世纪乡村历史的见证人,这种人在每个村庄或者中国的每个角落都有。)通过他与梁庄的各色人物,如老贵叔(对使百姓遭殃的砖厂三十多年历史的讲述,吊诡的是,八十年代路遥笔下的砖厂却是孙少安实现个人理想的途径)、建昆嫂(八十二岁的老母亲被王家少年残忍杀害及她诉诸法院寻找正义的经过,从中可以获得民间与庙堂的交接、乡村道德感与法律意识的博弈)、芝婶(留守老人抚养孙儿的艰辛、与子媳关系的新变迁、农村养老体系的阙如)、梁万明(八十年代红火、村人敬畏的基础教育在市场环境下折戟沉沙、丧失殆尽,小学从教育圣地变为养猪场的荒诞而沉重的现实)、毅志(八十年代的孙少平,在流浪中的种种坎坷,农村青年男女的婚恋,收容所、黑砖厂等历史黑暗的一角,农村知识青年的文学理想)等等,这些讲述在文本中这些讲述还有很多,组成了文本中不同的声音,构成巴赫金的多声部效果,这些民间声音使文本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一种可以经由个案进入一个村庄、分析一个群体进而分析一个阶层的脉络。然而,通过审视这部文本,我们发觉在非虚构文学的外壳下,纵然充斥着众多民间的声音,但是否达到众声喧哗的效果依然值得怀疑,因为文本最终呈现的只有作者的声音,其它的叙述话语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声音,伴以作者文学性极强的抒情话语与浅尝辄止的分析。如对好友菊秀未实现个人理想的悲剧作者没有进行分析,只能是她太理想主义化了,只是个人的悲剧,“这条路似乎被我们遗忘了,这是它必然的命运,就像菊秀也有着她必然的命运一般”[3]P96。多是以反问句结束一个故事,“农村人的想法很现实,人死了,剩下最重要的就是钱的问题……似乎他们把钱看得比人重。但是,谁又能看到他们心里面的深流呢?”[3]P111谈到农民工“性”的问题,“可是,难道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又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3]P103除了无力的反问外,作者未能提供一种更有深度的思考,而所有的故事最后都成了作者个人观点的依据,在思考之外,她只能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将其统摄起来,形成个人的声音,即一种抒情感伤的声音。这使文本从沉重处生发,最终却是“不可承受之轻”,弱化了非虚构文学的文本特性,除了一地鸡毛的农村现实和留给读者一堆浅显的喟叹外,作者无力得出更深的结论。
四
不同于虚构文学较为自由的写作姿态,非虚构文学的叙述者、角色及作家本人三位一体,其本质在于行动,将真实展现给读者,同时表达个人的叙事伦理。《忏悔录》中,卢梭因袒露自己与华伦夫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将自己的子女送进福利院并致其夭亡的私隐,遭到了不少批评家的批评。“虽然叙事伦理是一种虚构伦理,与现实理性伦理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经由叙述者的价值偏爱而构建的虚构伦理会在与受众的互动中对现实伦理产生不可回避的影响。”[7]李敬泽认为报告文学的根本症结是其在叙事伦理上不成立,由此他推崇非虚构文学能够清晰完整地表达个体情感,然而从《中国在梁庄》中,我们却看到了这个观点的虚妄。这也引发了对非虚构文学叙事伦理的思考,文体的尴尬带来了价值的尴尬,如何形成阅读期待?如果这种叙述违背了叙述伦理,作者又该如何规避?
女作家李林樱曾动情地娓娓倾诉这种叙事伦理上痛苦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我常常接触到许多重大的矛盾、激烈的冲突,由于和被采访者交了朋友,他们也常常推心置腹地把人生历程上的苦难和坎坷告诉我,往往使我震动、使我骇然当然有时也令我欢欣。于是我常常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某些矛盾、某些事件、某些任务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如实地加以暴露。有时我甚至想,只有这样,才能写出“轰动一时”的、坚持真理的“名篇”。
然而,我终于痛苦地克制住了自己,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必须为被采访者、被报道者负责,为社会负责,而不能仅凭自己一时的感情冲动。[8]P62—64
而《中国在梁庄》中,当好友菊英在说到帮砖厂拉砖那段生活时,“她反复告诉我,这是她的秘密,不能写出来,不能让别人知道”[3]P95。“我”虽然明白了她的意思,但为了故事的震撼性,还是写了出来,这无疑带着我们鉴定甚至是玩赏了别人的羞愧与痛苦,是对讲述者承诺的违背。采访到春梅的死时,堂嫂说,“我只给你说这些,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说起来,春梅的死也怨我,与我有关”[3]P98。然而为达到戏剧性效果作者还是将她们如实地写出来,明显违反了叙事伦理规范。由此出发的那些看似饱含深情的抒情话语就显得苍白无力,在作为看客的过程中对读者的情感伦理产生了不言而喻的影响。
[1]周淼龙.非虚构叙事艺术:报告文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2]余英时.自序[A].士与中国文化[C].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7.
[3]梁鸿.中国在梁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4]林贤治.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札记(节选)[A]沉思与反抗[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5]恩格斯.给敏娜·考茨基[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许钧.关注公共舞台后的私人空间[N].文汇报,2005-06-06.
[7]伍茂国.欲望叙事·伪欲望叙事·叙事伦理——从电视剧《蜗居》说起[J].中州大学学报,2011,(2).
[8]李林樱.矛盾与探索:采写报告文学的反思[J].当代文坛, 1989,(2).
(责任编校:周欣)
I247
A
1673-2219(2012)09-0048-04
2012-07-02
陈桃霞(1981-),女,湖北咸宁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商业服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