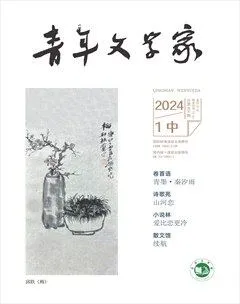论梁鸿返乡书写的新变
林贤丽


故乡梁庄是梁鸿十余年来持续追踪、观察、书写的对象。2010年和2013年,梁鸿根据回乡见闻相继创作了《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十年后,梁鸿再一次将眼光投向故乡,书写故乡十年间的沉浮变化,于2021年出版了新作《梁庄十年》。至此,梁鸿为读者奉献出了厚重的“梁庄三部曲”。与前两部作品不同的是,《梁庄十年》消隐了强烈的整体意识和问题意识,作者不再执着于对深度意义的挖掘和分析,而是聚焦于对故乡日常生活的书写,并在书写的过程中强化了文学性。文本的叙述者也从强势介入转变为温和融入,写作姿态的调整使《梁庄十年》的总体基调发生变化,形成一种悠长的叙述并内蕴着对故乡更好的未来的期待和信心。基于此,本文以《梁庄十年》为例,探究梁鸿返乡书写的新变。
一、从整体性观照到日常化书写
《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之所以会诞生,源于梁鸿对学院生活的厌倦、怀疑而做出的返乡行动。梁鸿曾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中国在梁庄·前言》)基于这样的精神困境,梁鸿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沉浸式观察、感受、体验,记录家乡在时代剧变中的无序、撕裂与疼痛。在这一过程中,梁鸿的书写携带着整体性的视角和强烈的问题意识,试图通过梁庄的种种状况以小见大地折射当代乡土中国,从而窥见一个时代的病症。例如,在第一部梁庄作品《中国在梁庄》中,作者就通过描写家乡的外在环境和家乡内部不同年龄阶层的人的经历、命运,直指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在《出梁庄记》中,漂泊在他乡的梁庄人的种种遭遇则映射出尖锐的城乡对立问题、打工人的精神危机问题等。梁庄为千万个乡村代言,是乡土中国的缩影。但到了《梁庄十年》,梁鸿整体把握对象的勃勃野心明显消退,她放弃了先入为主的框架设定,不再执着于对深度意义的探究,而是展开对乡村点滴与日常的书写。比如,作者写梁庄人,有的人仍活跃在这片土地上,有的人却已经被浩浩荡荡的时间之河带走。活着的人们吃饭、打牌、钓鱼、上学、理发、跳舞……生活一天天地行进,日子如流水一般前行不息。作者还写梁庄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梁庄有了更多的高楼和别墅,但破败的老屋也顽强地显示自己的生命力;梁庄有了新的美丽景观—大胜的花园,在大胜的精心打理下,花园繁花盛开,雍容华贵……《梁庄十年》呈现更多的是生活常态、生活细节,以及一些乡村景观。一切都是那么日常,有悲有喜,有变与不变,字里行间散发出恒久、平静、温暖的气息。
从容的日常化书写也使《梁庄十年》与前两部书写梁庄的非虚构作品相比起来更有文学性。《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由于作者在语言表达和情感流露上过于直接,作品的文学性偏弱。但到了《梁庄十年》,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对虚构艺术的回归,最明显的表现是作者在部分章节的写作上使用了小说笔法。例如,《小字报》一节,作者先是在韩家媳妇发现小字报一事上设置悬念,接着慢慢引出小字报主人公张香叶的一段风流往事,以及与之有关的矛盾恩怨。悬念的巧妙设计,细节的有意描摹,人物神态的传神刻画等都把读者带进了当时的八卦现场,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充满好奇与紧张感—小字报里写了什么?小字报是谁贴的?为什么要贴?可以说,《小字报》作为《梁庄十年》全书第一章里的第一节,给了读者完全不同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阅读感受,引起了读者新的阅读期待。
从整体性观照到日常化书写,可见梁鸿创作理念和创作心态的变化。这种变化让《梁庄十年》“虽借用社会学主题,但更偏向文学的创作”(《十月·卷首语》),作品的文学性得到加强。这是梁鸿在创作上的自我突破,对非虚构写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别样的阅读体验。
二、从强势介入到温和融入
《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带给读者的最大感受是,两部作品字里行间都涌动着“我”各种激烈的、复杂的情绪。面对家乡的现状和梁庄人的各种遭遇,“我”是愤怒的、痛心的。文本中随处可见作者激烈的诘问、控诉和评论。例如,当“我”在监狱里见到奸杀了村里八十二岁的刘老太的王家少年时,“我一下子崩溃了”,随之是一连串反问:“谁能弄清楚,那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在少年心里郁结下怎样的阴暗?谁又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而又有谁去关注一个少年最初的性冲动?”(《中国在梁庄》)当“我”看到贤义在都市从事算命工作时,“我”对此评论道:“不管贤义如何努力去理解人生,其内在的荒谬性还是一眼可见。”(《出梁庄记》)由此可发现,“我”是一个强势的介入者,“我”时时在场,观察、倾听、反问、评论,文本处处有“我”的痕迹。
而在《梁庄十年》中,叙述者强势的介入姿态明显发生变化,“我”不再高高在上地评判审视,不再任由情绪泛滥决堤,而是融入梁庄,融入那些日常,见证时间对每个人、对整个村庄的洗礼。无论是写儿时好友们坎坷悲惨的经历,还是写村庄老人们如吴桂兰、福伯、明太爷的令人无奈心碎的故事,“我”都不再是那个狂妄自大的介入者、批判者了,“我”消隐在故事之后,以一个“内部居民”的视角呈现一切,留给读者自行感受和思考。诚如作者所言,十年后的“我”是“消融在梁庄,和梁庄人一起,站在时间的长河之中,看历史洪流滔滔而来,共同体味浪花击打的感觉”(《梁庄十年·后记》)。
写作姿态的变化使《梁庄十年》和前两部作品的基调有明显不同。《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总体基调是悲哀的、疼痛的。因为当“我”强势介入时,“我”是焦灼悲愤的。“我”在梁庄的目之所见是一幅乡村末日图—梁庄生态环境恶化,人的道德沦丧、精神萎靡,乡村空心化……当“我”出梁庄时,“我”的目之所见是身处他乡的梁庄人过著脏乱差的生活,他们为了生存拼尽全力却仍然得不到尊重,到处被歧视,被驱赶。作者仿佛写了一个悲情剧本,被现代化无情冲击的梁庄和梁庄人是剧本的主角。到了《梁庄十年》,虽然梁庄仍有那么多令人无奈和忧惧的地方,但因为“我”融入了村庄而非俯视它,“我”经过了十年的成长,不断自我纠正和反思,在岁月的洗礼下领悟到日常的珍贵和生命的浩荡,所以十年后的“我”再次书写故乡时,则对故乡充满了温情、敬畏和包容,作品的基调由此也变得悠远、绵长。《梁庄十年》让读者感受到一份释然,这份释然不是简单的、一时一地的,而是历经时间冲刷和沉淀之后独有的温和、喜悦和平静,是真实的时间长度和情感厚度共同作用而出的。
三、从“我终将离梁庄而去”到“我也继续往前走”
如果要寻找文学传统的话,可以发现《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明显受到鲁迅的乡土小说的影响,字里行间有着鲁迅式的乡愁和哲思。鲁迅写故乡,写了凋零、破败的村庄,写了在其中生活的麻木愚昧的人们,写了游子回乡后所生发的种种复杂的人生况味。鲁迅最后告诉读者,故乡是离开后归来但终究还是要再离开的地方。诚如钱理群所指出的,“‘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的永远的漂泊者”(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也表达了这种相似的回乡感受。《中国在梁庄》继承了鲁迅《故乡》中“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写作模式,长大后的“我”离开故乡求学工作,后因倦于书斋生活而回到故乡,试图通过与广阔的天地和现实建立联结来缓解自己的虚无感。当“我”雄心勃勃进入梁庄时,“我”却发现“我”并不了解它,“我”始终融不进它。一方面,是因为“我”已离乡多年,接受了现代教育,习惯了城市生活,当“我”重新进入、观察梁庄时,“我”无法避免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视角和启蒙的姿态,“我”也失去了“对另一种生活的承受力和真正的理解力”(梁鸿《历史与我的瞬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瞥到“背后那庞大的时代映像和不可告人的动机,那深渊之深让人莫名心惊”(梁鸿《历史与我的瞬间》)。无论是蓬勃的废墟村庄、守在土地上的成年闰土还是青岛电镀厂的雾气、少女眼里蓄满的泪水……一切都让“我”感到窒息和无力。作为已经中产化了的、习惯了安稳和退守的知识分子,作为热爱叙事但无力解决现实问题的写作者,“我”的逃跑成为一种必然。最终,《出梁庄记》以“我终将离梁庄而去”一句收束全书,留下了深深的叹息。
与终将离开的痛苦、无奈相反的是,十年后的《梁庄十年》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也继续往前走。”短短的一句话让读者能充分感受到作者内心充满了明亮和希冀。全书最后一章最后一小节为《少年阳阳》,写“我”请梁庄的一群小孩子吃饭,写“我”和少年阳阳的对话,最后写到阳阳和他的朋友们往前走了,“我”也继续往前走。如此书写是出乎意料的,因为这一章的标题是“生死之谜”,前面几个小节里密集地写了各种死亡尤其是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在最后一小节却笔锋一转,写年轻阳光的孩子,写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姿态,前后反差形成巨大的张力。这样的结尾透露出“我”对故乡未来的期待和信心。梁庄虽然仍处在无序之中,但毫无疑问梁庄还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它会发展,会变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像那条曾经破坏生态、吞噬孩童的湍河,十年之后复归平静,波光粼粼。作为梁庄的母亲河,湍河的这种变化或许是梁庄的某种隐喻。
另外,从“我终将离梁庄而去”到“我也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出“我”与故乡的情感关系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回到梁庄之前的作者是虚无的,在两度回乡写出了《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作者是更加困惑和无力的,那么写完《梁庄十年》的作者则实现了最初与故乡、与现实联结的梦想。十年的沉淀、省思终于使她在将近知天命的年纪和故乡共振起来,她不再是出走的、与故乡充满隔阂的女儿,而是与故乡血肉相连的赤子。正如作者在《梁庄十年》的后记里所说的:“我就像一个孩子,蹦蹦跳跳的,依赖梁庄,喜欢梁庄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我的爱多得我自己都兜不住,要溢出来。”十年后的“我”面对故乡,已经对它有了皈依感,有了深深的眷恋。
1921年,鲁迅的《故乡》发表;2021年,梁鸿的《梁庄十年》出版。这一百年来,乡土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如今的乡村与百年前的乡村仍有一些地方是那么相似;这一百年来,不同年代的作家也在孜孜不倦地书写着乡土中国的悲与喜、苦与难,但无论怎么写,好像总逃脱不了那几种模式,如归乡模式、田园模式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庄十年》对乡土书写的贡献或许就在于作者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乡村的视角和心态,即乡村虽然不是世外桃源,但也绝不是“十恶不赦”之地,它虽没有如诗如画,但也没有全然破败、无可救药。面对乡村不应该焦灼地“恨铁不成钢”、远远逃离,而应该尽力地为乡村的改变做些努力—梁鸿对梁庄的“长河式”书写便是其中一种,同时怀有期待和信心,目送和祝福乡村更好地前行。
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相比,《梁庄十年》在写作内容、写作姿态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使《梁庄十年》获得了不一樣的艺术魅力。作者梁鸿也在这个返乡书写的过程中与故乡真正和解,获得了面对故乡的踏实感和力量感。《梁庄十年》作为梁鸿最新的返乡书写的代表作,它与其他两部书写梁庄的非虚构作品之间仍有诸多不同的地方等待挖掘和分析。另外,作为非虚构作品的“梁庄三部曲”与其他书写梁庄的虚构作品《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四象》之间也值得作比较研究。梁鸿的书写新变不仅折射出梁鸿创作的心路历程的变化,也对当下的非虚构写作、乡土写作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