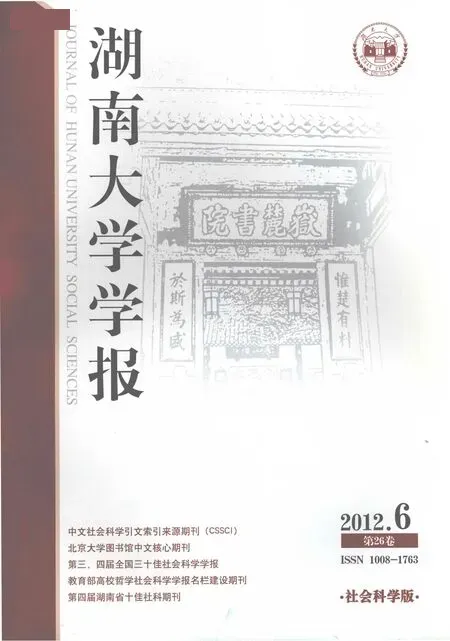论朱子对《中庸》“致曲”的诠释*
郭晓东
(复旦大学 哲 学学院,上海 200433)
一
按朱子《中庸章句》所厘定,《中庸》之第二十三章为“致曲”章:“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①朱子与《礼记正义》对《中庸》之分章多有不同,但两者都将从“其次致曲”至“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断为第23章。本章承上章“天下至诚”章而来,朱子以为“天下至诚”章论“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1](P32-33)即圣人之至诚尽性而与天地同流,故朱子于此下一按语说“言天道也”[1](P33)。而未及圣人者,即于二十三章之论“其次”者,朱子称“其次,通大贤以下凡诚有未至者而言也。”[1](P33)既然“诚有未至”,则必须有学者之工夫,故朱子之按语称“言人道也”[1](P33)。就此章而言,由“致曲”,而有形、著、明、动、变、化之功,从而上达天道至诚之妙。故这里论工夫之关键,便在“致曲”两字上。那么,“致曲”之作为学者之工夫,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工夫呢?学者论朱子之工夫,似乎较少有关注到这一点,故本文拟从朱子对“致曲”的诠释入手,从一个侧面来看朱子之工夫学说。
二
朱子在《中庸章句》中说:
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其次则必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也。[1](P33)
就这里而言,要点显然有二:其一之作为工夫本身的“致”,朱子训为“推致”,《朱子语类》卷六四称“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极”[2](P1574),说得更为清楚,这与朱子之训“格物致知”之“致”为“推致”是一贯的;其二,则训“曲”为“偏”,此“偏”为“善端发见之偏”。不过,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何为“善端发见之偏”?这一“善端发见之偏”之发生是如何可能的?进而如何推而致极此一“善端发见之偏”?或者说,“致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工夫?对于这几个问题,在《章句》中朱子似乎语焉不详,不过,在相关的《朱子语类》、《中庸或问》以及朱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我们还是可以梳理出其中的脉络所在。《中庸或问》曰:
人性虽同而气禀或异,自其性而言之,则人自孩提,圣人之质悉已完具;以其气而言之,则惟圣人为能举其全体而无所不尽,上章所言至诚尽性是也。若其次,则善端所发,随其所禀之厚薄,或仁或义,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发见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于乎其极,使其薄者厚而异者同,则不能有以贯通乎全体而复其初,即此章所谓致曲,而孟子所谓扩充其四端者是也。[3](P92-93)
《语类》卷六四亦论之颇详,我们这里略选数则来加以考察:
1.曲,是气禀之偏,如禀得木气多,便温厚慈祥,从仁上去发,便不见了发强刚毅。就上推长充扩,推而至于极,便是致。气禀笃于孝,便从孝上致曲,使吾之德浑然是孝,而无分毫不孝底事。至于动人而变化之,则与至诚之所就者无殊。[2](P1571-1572)
2.刘潜夫问“致曲”。曰:“只为气质不同,故发见有偏。如至诚尽性,则全体著见。次于此者,未免为气质所隔。只如人气质温厚,其发见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那义底分数;气质刚毅,其发见者必多是义,义多便侵却那仁底分数。”[2](P1572)
3.问:“‘其次致曲’,注所谓‘善端发见之偏’,如何?”曰:“人所禀各有偏善,或禀得刚强,或禀得和柔,各有一偏之善。若就它身上更求其它好处,又不能如此。所以就其善端之偏而推极其全。恻隐、羞恶、是非、辞逊四端,随人所禀,发出来各有偏重处,是一偏之善。”[2](P1573)
4.元德问“其次致曲,曲能有诚”。曰:“凡事皆当推致其理,所谓‘致曲’也。如事父母,便来这里推致其孝;事君,便推致其忠;交朋友,便推致其信。凡事推致,便能有诚。曲不是全体,只是一曲。人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极,则能通贯乎全体矣。”[2](P1574)
从朱子的以上论述看,“致曲”之“曲”,是人的“善端”之“偏”,而人之“善端”之所以有此一“偏”,其源头在于人所禀的“气质”。在朱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所共同禀有《中庸》开篇所说的天命之性,此为人性善之保证,亦即伊川所谓“性即理”意义上的性。就此天命之性或本然之性来说,是人所共有,即每一个人都具有仁义礼智之性,那么理论上讲,每个人在现实中就应该是善的,所以孟子道性善,亦即上引《中庸或问》所说的,“自其性而言之,则人自孩提,圣人之质悉已完具。”但这仅仅是从“理”上讲。从另一方面看,对朱子来说,人除了禀有作为“理”之“性”之外,人之有肉体生命,则由于人所禀的“气”,即《大学或问》所谓“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3](P2-3)此说亦承之于伊川,在伊川看来,人之所以有不善,即是因为此“气禀”的原因,①如程颐说:“人之禀赋有无可奈何者,圣人所以戒忿疾于顽。”(《遗书》卷三,《二程集》,第65页。)又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遗书》卷三,《二程集》,第66页。)朱子亦然,其以为人在现实层面上之所以有善恶贤愚之区别,即在于所禀之气: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恶底,此是气禀不同。[2](P69)
在这一意义上,所禀之气对朱子而言必然对成德具有一种负面的限制性意义,《大学章句》章首注“明明德”曰: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1](P3)
在《大学或问》中,朱子则进一步申明此说曰:
况乎又以气质有蔽之心,接乎事物无穷之变,则其目之欲色、耳之欲声、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岂可胜言也哉?[3](P4)
由此可见,人之有善有不善,实为其气禀所致。那么,既然如此,当朱子释“致曲”之“曲”为“善端发见之偏”,而这一“善端”之“偏”又如何可能本之于一种近乎可善可恶的“气质”呢?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朱子而言,纯粹的“性”与“气”都是从理论上必须的设定,正如程明道所说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4](P10)朱子亦然,对于具体的每一个人而言,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既不是纯粹之理,也是不纯粹的气,而是所谓的“气质之性”。“气质之性”这一概念本于张载与程颐,但在张、程那里,“气质之性”即是“气质”或“气禀”,而朱子则赋予了新的内含。
在朱子看来,人既在本源上禀有天命之性,但这一本然的天命之性一旦要落实在每一个具体的人物身上时,这一“本然之性”就必须有一个安顿的地方,这一安顿处即是人之气禀。而此本然的天命之性既安顿之后,其落实于具体的人身上便被朱子称为“气质之性”:
问气质之性。曰:“才说性时,便有些气质在里。若无气质,则这性亦无安顿处。”[2](P66)
问“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一段。曰:“人生而静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时。人物未生时,只可谓之理,说性未得。此所谓在天曰命也。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者。言才谓之性,便是人生已后,此理已坠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谓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是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才是说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也。然性之本体,亦未尝杂,要人就此上面见得其本体元未尝离,亦未尝杂耳。”[2](P2430)
可见,朱子所谓的“气质之性”,是人物在既禀之后“本然之性”安顿于“气质”之中的一种形态,它不能简单地视同于“气禀”或“气质”,而是“本然之性”在夹杂气禀以生时,这一“本然之性”即成为“气质之性”。在朱子看来,明道讲“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那是指人物既生之后才有性之名,然而,有性之名的同时,“本然之性”即已安顿于气质之中,因此“本然之性”亦即失去了原初“本然”之纯粹性,即所谓“不全是性之本体”。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当“本然之性”杂夹着气质而成为“气质之性”时,虽然它“不全是性之本体”,但毕竟没有离开“本然之性”来讲“气质之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气质之性”还是“本然之性”,只是形态发生了转变而已。①故朱子说:“气质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这个天地之性却从那里过。好底性如水,气质之性如杀些酱与盐,便是一般滋味。”(《朱子语类》,第68页。)陈来先生亦指出:“天命之性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气质之性则是天命之性受气质熏染发生的转化形态。”见氏著:《宋明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这样,在每一个具体的人物身上,虽然其所禀受的气质会对其本然之性有所限制,但同时其“气质之性”实是本然之性的转换形态,故本然之性亦可透过其夹杂之气质而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来,这正如朱子的日光之喻所说的:“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窍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质局定了,也是难得开广。”[2](P58)
尽管所受之光会被形质局定,但其光多少总是能漏得下来。故朱子于《大学章句》中一方面称那种“所得乎天”的“明德”会被“气禀所拘”,但同时又认为“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此即《大学或问》所谓:“是以虽其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矣。”[3](P4)可以 说,所谓“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即本然之体或多或少的呈现,正是朱子论“致曲”所谓的“善端发见之偏”。此“善端发见之偏”,是因为“气质”的原因而有一偏,又因为它是本然之性在气质上的呈现而有善端之发见。因前者之故,常人不同于圣人②对朱子来说,圣人即便是所禀的气,亦“能举其全体而无所不尽”,因而有第二十二章“至诚尽性”之说。,故“致曲”属于“其次”之工夫,即次于圣人者,皆有下“致曲”工夫之必要性;而此所“致”之“曲”,即“善端”之发见,实源之于本然之性,故“致曲”之工夫方有可能由此一偏之善而推致其全体,是以《中庸》下文才有所谓的形、著、明、动、变、化之效验。
三
从上可知,对朱子而言,所谓“致曲”之工夫,即是将人因气禀而有的“善端发见之偏”推到极处,亦是将人那种“未尝息”而随时可能呈现之“本体之明”推到极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一种工夫,亦即是朱子释《大学》所提及的“明明德”之工夫,《大学章句》曰:
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1](P3)
我们在此可与前引《中庸或问》中朱子所说的做一对照:
自非各因其发见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于乎其极,使其薄者厚而异者同,则不能有以贯通乎全体而复其初。[3](P92)
这两种表述虽然一正一反,但其内容可谓如出一辙。《大学章句》之“因其所发”,即《中庸章句》之“善端发见之偏”;《大学章句》之“遂明之”者,即《或问》这里所说的“一一推之,以至于乎其极”,而最终的目的,则都是“复其初”。
而对朱子来说,《大学》所谓“明明德”之工夫,具体来说,则分格、致、诚、正诸节目,①《语类》卷十五:问:“《大学》之书,不过明德、新民二者而已。其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乃推广二者,为之条目以发其意,而传意则又以发明其条目者。要之,不过此心之体不可不明,而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乃其明之之工夫耳。”曰:“若论了得时,只消‘明明德’一句便了,不用下面许多。圣人为学者难晓,故推说许多节目。今且以明德、新民互言之,则明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然则虽有彼此之间,其为欲明之德,则彼此无不同也。譬之明德却是材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却是下工夫以明其明德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际,要得常见一个明德隐然流行于五者之间,方分明。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时加拂拭耳。若为物欲所蔽,即是珠为泥涴,然光明之性依旧自在。”见《朱子语类》,第308页。而在此格、致、诚、正诸节目中,在笔者看来,所谓“致曲”之工夫,亦即表现为“格物致知”之工夫。朱子对“格物致知”工夫的论述,可谓随处可见,其中或不失有相互扞格者,但最具代表性的论述,亦是他最正式且最审慎的论述,则莫过于《大学章句》之《格物补传》: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1](P6-7)
就格致工夫本身上看,《大学》文本称“致知在格物”,也就是由“格物”而可“致知”,即《格物补传》所谓“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就此而言,“致知”似乎是“格物”的效验。然而,朱子又说,要格物,则要“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则其所谓“已知之理”又成为格物的前提,这两种论述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对此朱子与其弟子也曾讨论过:
任道弟问:“致‘知章’,前说穷理处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且经文‘物格,而后知至’,却是知至在后。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穷之’,则又在格物前。”曰:“知先自有。才要去理会,便是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着,便是知之端未曾通。才思量着,便这个骨子透出来。且如做些事错,才知道错,便是向好门路,却不是方始去理会个知。只是如今须着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头万绪,无有些不知,无有毫发窒碍。孟子所谓:‘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扩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2](P324)
又:
问“致知在格物”。曰:“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虚明广大,无所不知,要当极其至耳。今学者岂无一斑半点,只是为利欲所昏,不曾致其知。孟子所谓四端,此四者在人心,发见于外。吾友还曾平日的见其有此心,须是见得分明,则知可致。今有此心而不能致,临事则昏惑,有事则胶扰,百种病根皆自此生。”[2](P293)
由此看来,朱子之论格物致知,工夫的落脚点还是在“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上。其实朱子之训“格”为“至”,训“物”为“事”,因而“格物”就是到事物那里去。而之所以要到事物那里去,则是要“致知”,即推极我本有之知。故所谓格物致知,工夫落实处实是在致知上。其实对朱子而言,格物与致知两种工夫,并没有被严格地区分开来,格物本身的目的就是致知,而要致知则离不开格物。②朱子曰:“格物、致知,彼我相对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于这一物上穷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穷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于物之理穷得愈多,则我之知愈广。其实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所以大学说‘致知在格物’,又不说‘欲致其知者在格其物’。盖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别有致处也。”又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见《朱子语类》,第313页。又曰:“致知、格物,一胯底事。”《朱子语类》,第290页。但这里最关键的字眼还是在《补传》中所谓的“因其已知之理”,这是整个格物致知工夫之前提,不论是要到物上去推致的“知”,还是要到事物上去穷格的“理”,都要从这“已知之理”出发,而格物致知便是“因其端而推致之”。《语类》卷十八载:
若今日学者所谓格物,却无一个端绪,只似寻物去格。如齐宣王因见牛而发不忍之心,此盖端绪也,便就此扩充,直到无一物不被其泽,方是。致与格,只是推致穷格到尽处。凡人各有个见识,不可谓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以至善恶是非之际,亦甚分晓。但不推致充广,故其见识终只如此。须是因此端绪从而穷格之。未见端倪发见之时,且得恭敬涵养;有个端倪发见,直是穷格去。亦不是凿空寻事物去格也。[2](P402-403)
因此,对朱子来说,格物并不是凿空地在物上盲目地格,而是有一个“端绪”或“端倪”,否则就如钱穆先生所批评的王阳明之格庭前竹子一般。[5](P631)很显然,这里所说的“端绪”或“端倪”,即是《补传》中所说的“已知之理”。然而,这种“已知之理”又从何而来呢?朱子说:
穷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达而及其所未达。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穷理者,只是足于已知已达,而不能穷其未知未达,故见得一截,不曾又见得一截,此其所以于理未精也。[2](P392)
可见,所谓“已知之理”,其实就是“本所固有”的“良知”。对朱子而言,它是本然之体在“介然之顷一有觉焉”时的呈现,也就是《中庸章句》“致曲”章所谓的“善端发见之偏”,同时还被朱子认为就是孟子所谓的“四端”。朱子训“致知”之“致”为“推极”,训“致曲”之“致”为“推致”、“以造其极”;朱子又称“致知”之“致”为孟子对“四端”之“扩而充之”之扩充,而《中庸或问》也称“此章所谓致曲,而孟子所谓扩充其四端者是也”。可见,无论是《大学》之“格物致知”,还是《中庸》之“致曲”,朱子都把它理解为对人呈现在外之善端的扩充,且由之而推到极处。
在朱子看来,对格物之工夫而言,必须是“至于用力之久”,必须是“积习既多”,所谓“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2](P392)。如此才能豁然贯通。而对“致曲”工夫来讲,朱子称是对“善端发见之偏”推而致极,但亦不是“止就其发见一处推致之也”[2](P1573),而是“须件件致去,如孝,如悌,如仁义,须件件致得到诚处,始得”[2](P1572)。可见,不论是格物之工夫,还是“致曲”之工夫,都是一种渐进之工夫,就源头上看,基本上都承之于伊川的“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思想。[4](P188)
进而从工夫之后的效验上看,《格物补传》称“豁然贯通”,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样一种表述,与前引《中庸或问》所说的“致曲”工夫之后的效验,即“贯通乎全体而复其初”,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语类》卷六四论“致曲”时亦说,“人能一一推致之,以致乎其极,则能贯通乎全体矣。”[2](P1574)可见,从效验上看,“致曲”工夫所达到的效验,几乎可以认为等同于“格物致知”工夫之效验,这亦本之伊川的“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的说法。[4](P188)
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第一,朱子在《中庸》诠释中所提到的“致曲”工夫,应当可以视同于其在《大学》诠释中所提到的“明明德”的工夫,若更具体地说,即是“格物致知”之工夫。由此我们可以见朱子《学》、《庸》诠释的会通处,或者也可以说,朱子是以《大学》“格物致知”之工夫来诠释《中庸》之“致曲”工夫。
第二,对朱子而言,无论是“致曲”之工夫,还是“格物致知”之工夫,其必要性都建基于人之构成肉体生命的气禀本身,也就是说,正是气禀对人的局限,使得修德之工夫成为必要。从另一方面说,本然之性在每一具体人物之上虽表现为为气禀所拘的气质之性,但其本然之性之本体宛然具在,它总会有“介然之顷一有觉焉”的时机,人得之于天的明德总会有所发见,即人总会有“善端发见之偏”,这使得工夫具有了可能性。无论是“格物”还是“致曲”,都致力于将此善端之发见推到极处。而这样一种“善端发见之偏”被推到极致,那么其工夫相应的效验,即《格物补传》所谓的“豁然贯通”,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亦即《中庸或问》所说的“贯通乎全体而复其初”。
第三,通过对上述两种工夫的讨论,我们可以认为,简单地衡定朱子之工夫论,特别是其“格物致知”理论,认为它是一种由知识而进入道德的工夫路径,恐怕有所偏颇。①其实朱子本人亦对此颇有警惕,也自知其学有可能会遭此误会,故其于《大学或问》中就假设而问曰:“然则子之为学,不求诸心而求诸迹,不求诸内而求诸外,吾恐圣贤之学,不如是之浅近而支离也。”而朱子就此回应说:“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矣。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以圣人设教,使人默识此心之灵,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为穷理之本;使人知有众理之妙,而穷之于学问思辨之际,以致尽心之功。”见《四书或问》,第24页。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 朱熹.四书或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4]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二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