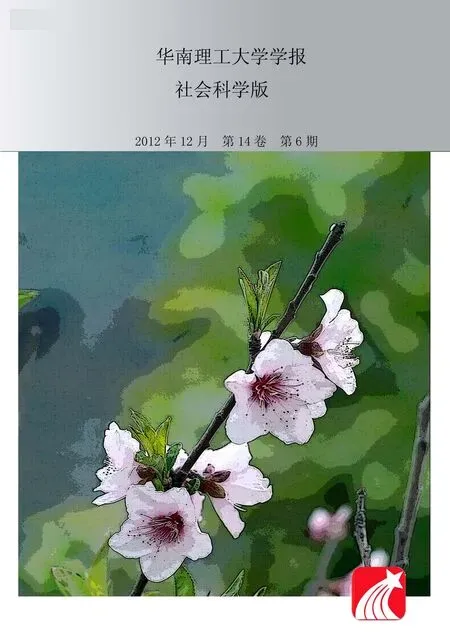碎片化社会与碎片化传播断想*
彭 兰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一
微博的普及更加突显了网络传播的碎片化特征。所谓碎片化传播,主要体现为事实性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和意见性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两个层面。前者指信息来源的多元化、观察视角的分散化、信息文本的零散性以及信息要素的不完整性; 后者不仅指意见的零散性,更指意见的异质性、分裂性。新媒体平台上意见的形成,其实是各种“碎片意见”碰撞、冲突的过程,这与传统媒体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意见的相对一致性迥然有别。
对于碎片化传播,人们关注的重点通常是事实性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但如果观察新媒体传播的长远影响,我们尤应关注意见信息的碎片化及其传播效应,因为它反映了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
除了上述两个层面,整个传播格局也会显现出碎片化的特点: 过去专业媒体所构建的“传播中心”受到冲击甚至可能被“去中心化”,每一位用户可以构建起自己的传播中心,某些经过努力获得强势话语权的个体也可能以“意见领袖”的方式演变成为新的话语权力中心。相对专业媒体而言,他们是碎片式的传播者。
二
碎片化传播常常被认为是新媒体传播的“原罪”,但新媒体只是碎片化传播的一个促成因素,碎片化传播本身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碎片化或者说多元化。
这个“碎片化社会”出现的基础是价值体系的多元化。随着中国社会的持续开放以及现代化转型,长期被边缘化或被抑制的某些价值观开始受到关注,甚至赢得了广泛认同。譬如对个体价值的重新认识,个人的尊严、权利、利益、财产等观念开始受到重视。价值观的选择与表达,也成为个体权利的一种表现。这是社会价值多元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而人们对主流价值观的态度也变得复杂而多样化。简而言之,整个社会已不再被一种价值体系所垄断。
社会价值多元化在更高层面上表现为对文化、制度等层面的重新思考。譬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反思,对个体与集体关系、公权与私权关系的重新认识,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探讨等等。在这些方面价值观的差异开始显现。
社会价值体系分化,也是因为受到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中国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是一个基本事实,无论从何种角度或者以何种方式去划分(如经济分层、社会声望分层、阶层意识与社会态度分层、消费分层等)。不同社会阶层群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利益诉求、对社会关注的重心以及所面临的矛盾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价值观自然会发生分化。与此相应的是自我权利意识的萌生和成长,以及对传统权威所产生的怀疑或抗拒。尽管不能断言主流价值观已失去生命力,但其内在感召力确已相对弱化。
价值观分化和社会碎片化趋向导致的“后果”是,在意见的表达方面人们不再千篇一律,在事实陈述方面,由于观察和思考角度的不同,人们的描述也会不尽相同。
三
碎片化传播的凸显与Web2.0时代的传播模式密切相关。以门户网站为中心的互联网1.0时代,基本沿袭着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但随着数字化和网络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融合、优化(如RSS、Widget、Application、SNS、微博等),整个互联网传播模式的“去中心化”和“分裂”特征日趋明显。
基于RSS 、SNS或微博等技术,网民可以构建起一个自己的“个人门户”。这个个人门户既是他们与外界进行双向信息交换的“窗口”,也是他们构建自己社会关系的平台,个人门户为人们的个性化的信息获取提供了可能。
在个人门户模式支持下,未来越来越多的网民可以以自己的社会网络为桥梁,通过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渠道进行信息发布与接收。人们获取的更多地是来自于各种不同信息源的碎片,而不再是来自几个“权威”媒体的“统一口径”。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对信息碎片进行筛选、组装与解读。这意味着绝对的“权力中心”可能会减少,甚至不复存在。相对统一的媒介市场也因而将演变成分裂的、碎片化的市场。
由此可见,碎片化传播与个性化传播是相互关联的,而个性化传播意味着个体对公共信息的接触量或接触面可能会相对减少(当然,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人们仍然会保持对公共信息的高度关注)。如果人们越来越多地将自己封闭在个人化的信息天地里,他们对社会整体的感知则会受到削弱,社会公共价值的形成也会出现更多的障碍,其结果可能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碎片化。
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之一唐纳德·肖几年前提出过“水平媒体”(Horizontal Media)和“垂直媒体”(Vertical Media)这两个概念。他认为,水平媒体是某些小众的媒体,而垂直媒体是大众化的媒体,它贯穿社会各个阶层和人群并将他们整合在一起。在他看来,水平媒体与垂直媒体的交织可以创造一个稳定的“纸草社会”(Papyrus Society)。个性化的、碎片化的传播扮演了水平媒体的角色,但即使水平媒体充分地发展了起来,这个社会仍然需要垂直媒体。专业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垂直媒体,在未来,它们在社会整合方面的责任无疑将更加重大。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正视碎片化社会的出现及其挑战,承认碎片化传播的价值,并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实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