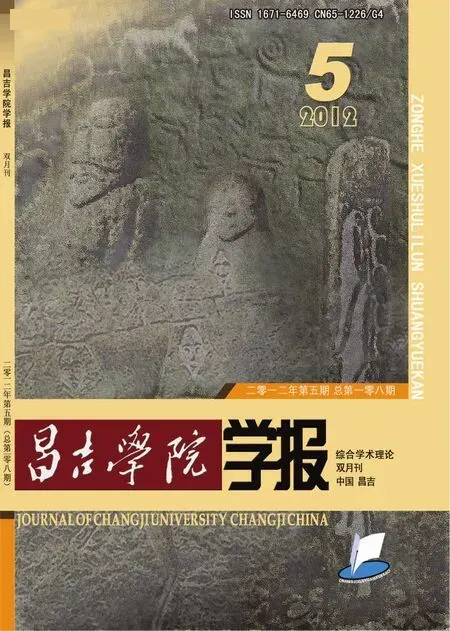论福柯的权力观
苏姗姗
(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北 恩施 445000)
福柯曾说过:“不要问我是谁?”是的,由于福柯思想的宽度和广度,我们无法把他真正归入到一个单一确定的领域。他的作品横跨哲学、历史、社会学和文学理论,他的著作“深入研究了心理学、临床医学、精神病院、现代刑罚制度以及古代希腊和罗马道德的发展历史,并且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进行了结构分析。”[1](P1)因此给他任何一个单一的头衔都显得有失公平。在福柯的研究生涯中,他一直信奉不断将自己从自己中分离出来,他要求自己的作品中绝不允许出现重复的思想,因而在他的一生中,他的思想一直处在不断的变更与发展中。
一、权力意识的发展历程
权力意识的发展进程也是随着福柯思想的发展进程而不断成熟和完善的。在其关于疯癫的早期作品中,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在这一阶段“处理的权力关系的模式是否定的,在这种否定的模式中,权力总是表现在压制和排斥的战略之中。”[2](P3)在“考古学”(archaeological)时期,他重点寻求揭示“支配思想的深层构成规则”,[3](P3)因此权力的问题仍很少被直接提到。但相对于前一阶段的观点,他的权力观有所发展。此时他将话语当作一种相对独立的事物对待,而不再“被一种僵化、还原论的社会控制逻辑所限定。”[4](P3)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即“谱系学”(genealogy)时期,权力就以相当持续的方式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此时他的权力观进入了成熟阶段。他对其进行了本质上源头性的重新阐释。福柯认为“权力构成了从制度到主体间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从而基本上是一种能动的力量,”[5](P4),因此要全面的理解权力,就要“分析它最复杂多样和最具体的表现,而不仅仅关注其最集中的形式,这种对权力关系的侧面或日常生活的关注,称之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以对应于‘权力的宏观物理学’”。以下将重点阐释在20世纪70年代后,成熟时期福柯的权力观。
二、福柯的权力观
㈠本源与来源
提到福柯的权力观,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尼采的谱系学。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非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且福柯关于权力的研究都源至这种方法。对于尼采来说,“本源”(Ursprung)指的是“先于世界历史而存在的存在者”[6](P247),这个存在者创造了这个世界,决定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规定了世界运行的轨道以及世界的终结。即使世界消失了,这个存在者依然存在。“这个存在者既在世界之外创造了世界,又在世界之中支配着这个世界。”[7](P247)“本源”就是一种形而上学、超越历史的存在。尼采不相信任何“本源”的存在,存在的只有世界历史本身,于是他提出“上帝已死”。福柯继承了尼采这一观点,相信“一切事物只有世界之内和生命之内的‘来源’(Herkunft),而没有什么世界历史之外和生命之外的‘本源’。”[8](P247)
“来源”类似于“血缘”和“谱系”,它是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存在于历史之中的,与“本源”的唯一性和神圣性不同,“来源”是多元的,细微的。在“谱系学”的研究时期,福柯就是从权力、知识、主体等多来源的角度入手研究问题。
㈡何为权力
权力一词的定义,在西方由来已久。福柯将中世纪以来支配我们的传统权力观称为经济主义的司法权力论,这种理论将权力看成是根据某种契约关系而由法律赋予某人的权力,人们可以像买卖商品一样对它进行交易,也可以像剥夺非法财产一样从人们手上夺走。显然,这种权力的模式是带有浓厚经济色彩的。福柯认为这种权力关系最多只能说明传统的君主权力的模式,是不足以说明现代社会的权力模式的。因此,福柯根据自己的研究,总结出现代社会权力是“一种松散的、非中心的多级对抗网络,其权力的运作方式细微而多变”[9](P266)这种权力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权力是一种关系。以往人们将权力看成可以被给予的、可转让的、可交换的、可分享的东西,其性质类似于商品。而在福柯看来,可以将权力理解为多种力量关系的“复合”(the multiplic⁃ity of force relations),它存在于各种不平等的力量关系之中。这些关系是相互作用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们在各自的位置上与他人接触、交往,从而使各自的位置发生相互作用,发生变化。其次,权力的运动方向是自下而上的。以本源为主导的权力思想认为权力是自上而下的,由代表本源的存在者自上而下的赋予人民,他的权力笼罩一切,统治一切。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应将权力看成自下而上的过程。最下层变化的权力关系是在社会生产、团体和机构中形成、变化权力关系的基础,也是社会整体冲突的基础。第三,权力运作的匿名性。权力的运作拥有自己的指向性,即明确的对象;同时也拥有运作的目标,即具有清晰的运作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权力的运作过程中,我们找不到一个绝对的指挥者。虽然权力的运作全过程看似对象明确,目标清楚,但是追根溯源,谁给出了对象,谁指定了运作过程是不得而知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权力的运作是匿名的。第四,权力是支配与反支配之间的斗争。哪里有权力,哪里就会有反抗。事实上,权力关系就是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这种反抗不仅仅表现于充满硝烟的战场,同样也可以隐藏在日常生活中。但这种斗争绝不是权力之外的斗争,权力同样也离不开各种力量的抗争。“只有在支配与反支配的实际冲突中,权力才会存在。”[10](P267)第五,权力的非中心化。在君权制的社会中,权力与君主这个特殊身份的人是紧密联系的,君主个人就是权力的化身。他可以在“社会权力系统之外支配这个系统,社会的权力运作成了一种派生于君主意识的行为。”[11](P268)在这个权力模式中,君主的地位相当于“本源”,独立于权力系统之外。而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存在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人的。现代权力关系是一个没有中心,且处于“不断变化的力量对立的网络”。[12](P268)在这个网络中,没有特殊人物的出现,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位置,并且这些位置都处于流动状态,因而每个位置都不固定属于一个人。因此,福柯提出了抛弃代表形而上学权力模式的大写权力(Power),而应推崇具有多重来源的小写权力(pow⁃er)。
福柯对权力的定义中,最重要的突破在于他彻底拒绝了形而上学的权力模式,在没有绝对权威的世界中去研究、分析权力,注重权力来源的多元化,强调了权力的关系性,明确其自下而上的运动方式,更注重了权力运作中的匿名性、斗争性和非中心性。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对传统权力模式的挑战、颠覆和解构,以微观的权力代替宏观权力。
㈢权力的技术
根据福柯的观点,现代社会的权力具有多元化,分散性,非中心化等一系列特征,那么面对这种新的权力特点,应该如何来运作和维护这些权力呢?由此福柯转向了“广泛散布在社会机体各个层面、各个方位的非统治性权力的研究,并由此重新考察整个现代社会权力网络的运行机制。”[13](P249)
对福柯而言,现代权力可概括为“生命权力”(bio-power)或“管制生命权力”(power over life),并将其分为两种技术:“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和“调节权力”(regulative power)。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举了两个反差很大的例子。一个是对“酷刑”场面的描述:“1757年3月2日,法国激进分子达米安(Damiens)因谋杀国王在巴黎被公开审判,审判的广场上树立起了刑架,刑吏用烧红的铁钳撕裂他的身体,将熔化的铅以及滚开的油脂、松脂、蜡和硫磺的混合物浇入被撕裂的伤口,要求他坦白自己的罪行,最后才被五马分尸加以处死。”[14](P250)另一个则是 20 世纪80年代后列昂·福歇(Leon Faucher)为“巴黎少年犯罪监管所”制定的作息时间表,表中细致地规定了犯人每天起床,穿衣,劳动,吃饭,上床就寝的时间,甚至精确到了分钟。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看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力模式。福柯认为,第一个模式从“司法”的角度看权力的实施,起作用的是“法律”(Law);第二个模式中,从“规训”的角度去看权力实施,对犯人起作用的是“纪律”(discipline)。第一个例子清晰地体现了在传统权力模式中,其目的是对肉体的摧残和消灭;而第二个例子表现的却是肉体被纪律规范化的过程,它的目的不是消灭肉体,而是要规训犯人的肉体与生命,使之能重新回到社会并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这第二种模式,福柯称为“规训权力”。他认为规训权力形成于17—18世纪以来的欧洲,它与当时的刑罚改革有关,由于刑罚改革,才使得“纪律”而非“法律”成为了刑法实施的真正基础。在此次的改革中,将“纪律作为新型的权力核心而形成‘规训权力’是18世纪的重大发明。”[15](P253)。“所谓的规训权力就是为了特定目的对人这部机器进行拆解、改造、重新组装的技术。”[16](P254)因此对于规训权力而言,纪律和人的身体都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福柯认为区分纪律和法律对理解规训权力非常重要。在传统的权力理论中,纪律是法律之中的事物,即“一种将法律的一般形式扩展到个人生活的细小层面上去的方式,或者是将一种法律具体化和细化的方式。”[17](P253)而在福柯眼中,纪律在本质上是“反法律的。”[18](P253)“司法体系根据一般规范来确定一般的司法对象(人人必须这样),而纪律则对对象进行区分、归类、分等并对他们作出不同的具体规定。”[19](P253)此外,法律的目的是要消极禁止,而纪律更多是积极规范。“规训”可理解为“规范化”(normalize),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权力不仅仅起到压抑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生产性,……生产了大量‘驯服而有用身体’”。[20](P253)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再将身体视为威胁权力的东西,而是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这种资源一经开发就能成为促进生产发展的生产力。惩罚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消灭身体,而是要对身体进行驯化和加工,此时的身体已被视为可为各种不同目的而改造的机器,而非一个有机整体。在17、18世纪的欧洲,规训权力是纪律和身体的结合产物。纪律作为一种特殊的人体支配技术,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两者之间和谐的关系:“使人在变得有用时变得更驯服,在变得更驯服时变得更有用。”[21](P254)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提出了规训权力的两种模式,即瘟疫模式和圆形敞视监狱模式,更生动地说明了规训权力如何对人进行监视和管理。而在这两种模式中,其中瘟疫模式是非常规的规训权力模式,圆形敞视监狱模式则为真正正常的规训权力管理模式。
瘟疫模式借用的场景是瘟疫时期,发生瘟疫的地域会与其他地方隔离起来。但这些隔离区域仍然是社会性的空间,没有被社会完全否定和抛弃。瘟疫模式的目的是将所有的人“禁闭”起来进行“监视”,隔离在瘟疫区的人群被仔细地分割和相互隔离,以免在游离、移动中将病菌传染给别人和被别人传染,同时也便于监视。瘟疫模式并不是将人驱除出社会以保持社会的纯洁性,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将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固定和包容在社会空间的某个可近距离监视的位置,从而以特定的纪律规范之,其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增进个人的健康、生命、寿命和力量,……这种权力模式是一种类似于毛细血管的组织,它能深入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节并在那里发挥规训的作用。”[22](P256)在福柯看来,瘟疫模式对付的只是异常情况,真正使规训权力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的模式是圆形敞视监狱模式。
圆形敞视监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思想家边沁(Bentham)的一种设计。这种监狱“四周是一个环行建筑,中心是一个嘹望塔。嘹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行建筑。环行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小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亮光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安排一名监督员。”(余红,2005,P257)圆形敞视监狱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使得中心塔上的监督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囚室里犯人的一举一动,而被监视者即犯人是看不到塔上的监督者的,因此无论塔楼里是否有监督者,监督者是谁,被监督者都只知道自己正处于被监视的状态。只要犯人看到了代表权力的塔楼,只要这个权力位置被看到,权力就会自动生效。因此福柯评价这种模式是“一架不依赖某个监视者而只凭借某种虚构的视觉关系来运作的权力机器,一架最终被监视者自己的观看所造就的自己对自己进行持续不断监视的机器。”[23](P258)这种代表规训权力的模式,像一张从不间断的,无形的,最终转化为自我监督的权力网,被福柯誉为最经济的模式。
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就是国家权力和规训权力相互交织、作用的产物。但是,与国家权力相比较,规训权力拥有更隐蔽和更广泛的基础,通过这些细如毛细血管的密集网络,社会才得以组织起来,国家的权力才会找到支撑点。
除了规训权力以外,生命权力的另一技术为调节权力(regulative power)。如果说规训权力是以“作为机器的个体身体”为中心而形成的,它侧重于“根据不同的需要而对个人身体进行仔细的解剖、分类和分解式规训,从而矫正他们的生理心理,提高他们的体能和功用,目的是培养“有用而温驯的个体身体”,使之成为积极的经济与政治要素,其主要手段为纪律,福柯称为‘身体的解剖政治’。”而调节权力是以“作为生命载体的全体身体”为中心而形成的,它的侧重点是根据国家和民族整体的经济发展与国防需要而对全体国民的生命状况进行管理,…通过有规则的积极干涉和控制来合理地调控一个国家的整体生命,其主要手段是总体的调节机制,福柯称之为‘人口的生命政治’。”[24](P262)虽然这两种技术有所差别,但他们并不是毫不相干的,而是相互交接的。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每个人都处于各种规训机制的监视、控制和规范之中,另一方面,社会中的公共机构又对人们进行了整体生命的宏观调控和管理。
无论是规训权力还是调节权力,对于福柯来说,都是一种“积极地让人‘生’的权力,”现代规训权力促使人‘生’为‘服从而有用的身体’,现代调节权力促使人‘生’为‘整体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25](P264)
在福柯的权力观中,他的先进性是不容质疑的。他指出人们以往将权力视为商品的错误观念,并提出现代社会的权力是一种关系,是一张大网。每个人在这张网里面都有自己的位置,并且这些位置都是处于不断地运动和变化之中的。因此,权力是没有中心,没有主体的,具有明显的分散性。
然而每一个理论家的理论都不是十全十美、毫无瑕疵的,福柯也不例外。在福柯的权力观中,规训权力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他过分强调了这种权力技术的重要性。事实上,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为了维护良好的秩序,国家权力,规训权力以及调节权力是缺一不可的。在福柯看来,规训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国家权力得以发挥都是由于规训权力的作用。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国家权力,特别是国家的政治体制、法律系统对维护社会秩序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权力作为基础发挥作用,规训权力的作用是得不到发挥的。另一方面,调节权力涉及的是国家、社会的总体规划和布局,因此也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合理有效的总体布局,个体和部分又如何能得到规范呢?再者,在福柯的表述中,规训权力似乎仅仅是起到压制的作用,按照同一规范来培养和塑造人,支配人的行为,抹杀了个体的个性。事实是规范权力在实施过程中是会产生一些积极影响的,而福柯完全忽视了规训权力的优点,因此他的批判是带有片面性的。当我们在承认和学习福柯的理论时,也不能忽略其理论中的瑕疵和不科学之处,这样才能真正运用福柯的理论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1][2][3][4][5][9][24],路易斯·麦克尼·福柯[M].贾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6][8][10][12]18][19][20][22]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11][15][23][25]梯利,伍德.西方哲学史[M].商务印书馆.1995.
[13][16][17]汪民安.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J].外国文学,2003,(1).
[14][21]马歇尔.米歇尔·福柯:个人自主与教育[M].于伟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