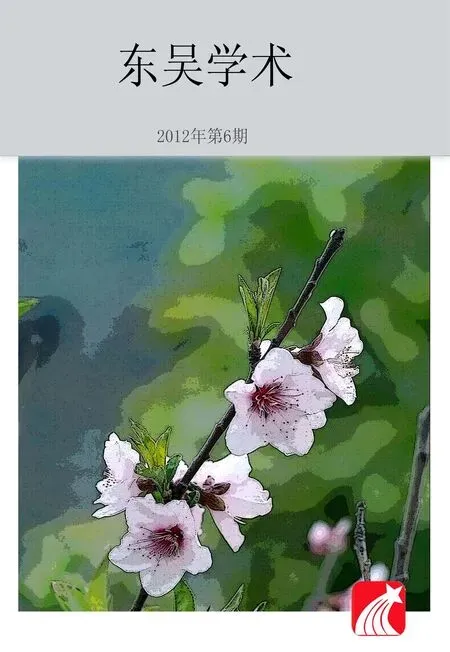从《白夜》到《雨夜》
——一种“萨米兹达特”(Samizdat)式的新抒情主义
柏桦
现代中国文学
从《白夜》到《雨夜》
——一种“萨米兹达特”(Samizdat)式的新抒情主义
柏桦
何谓“萨米兹达特”?马克·斯洛宁对此有详尽叙述:
二十年代,自由刊物遭到禁止,革命前的一些出版社都被封闭;从此以后,国家对文学艺术所施加的压力就逐年加强。结果,许多诗歌、文章和短篇小说都因有 “颠覆性”或暧昧的内容而没有获得在“合法”刊物上发表的机会;于是它们开始以打字稿的形式在主要是知识分子中间流传。但直到斯大林逝世为止,这种“刊物”只是偶然出现,范围很小,地区也很分散。不过,从那时起,它就具有广泛而有组织的活动的特征,成为自由发表意见的一种出路,并获得“萨米兹达特”(俄语的意思是 “自发性刊物”)的名称,这一著名的名称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西方也使用了。“萨米兹达特”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中心,并小范围地在一些省城逐渐扩展成为打字的、油印的,以及照相复制的一种真正的地下刊物…… “萨米兹达特”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也成了使保安机构伤透脑筋的侦查对象。“萨米兹达特”的活动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后来,它不仅涉及到诗歌和小说,而且还涉及到政治、哲学和宗教。一九五七年,帕斯捷尔纳克那部长达五百六十多页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遭到禁止,在西方却以原文和多种译文出版,这时,该书被偷偷地带进苏联,由“萨米兹达特”翻印了其中大量章节。这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开端:许多最初由“萨米兹达特”传播并秘密送往国外的作品,印成书后又被作为走私品、“违禁品”运回苏联,再由国内翻印流传。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由“萨米兹达特”有计划地加以翻印。作家们也经常通过迂回的途径把自己的作品送往国外出版……约瑟夫·布罗茨基早在他流放前很久就在“萨米兹达特”上发表诗歌,虽然这些作品在苏联从未正式出版过;他的诗集《长短诗》于一九六五年在纽约出版。①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395-39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从上可知“萨米兹达特”就是苏联出版的地下刊物。而《今天》的出版模式与苏联的地下刊物的运作过程极其相似。不过此文不讨论两者的运作模式,只是从两首诗来谈一种共通的抒情强力,即一种新抒情主义(对抗式的或“民族寓言”式的)。
此处所谓“新抒情主义”,大致可以这样理解:它是一种对抗式的强力写作,即个体之情对抗极权之情的写作。需知,极权主义本质上是一股巨大的集体情感力量,反抗者必须有足够强大的个人情感力量,才得以与之抗衡,这是一种以个人之情反抗集体之情的激烈、强力的抒情,这种抒情,我将之命名为新抒情主义。由于新抒情主义产生的文本因其特殊的政治原因,往往被迫以非公开的地下方式秘密流传。新抒情主义成为一个时代(国家)一部分写作者的共同写作模式(我将在下面通过对《白夜》和《雨夜》的讨论,对这种写作模式进行阐释),并具有思潮的性质和特点。在这个意义上,亦可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特殊时期的极具悲剧色彩的民族寓言,这种激烈、强力的抒情在整个国家范围内秘密地进行,它不同于既往出于对时间“惘惘的威胁”而产生的抒情,而是以一种对抗的方式尖锐地存在,它的写作对抗的对象具有虚妄、乌托邦性质。随着国家生活相对正常化,以及个人主义获得的存在空间的相对拓展,这种对抗美学(以个人之情反抗整个社会)也随之淡化,逐渐减弱。从地理覆盖范围看,新抒情主义包括苏联和东欧的地下文学,以及中国“文革”以来的地下文学,其代表性作品主要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及其抒情诗,在中国主要是北岛的诗歌,诸如《回答》、《雨夜》等。
俄罗斯的白夜,帕斯捷尔纳克(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的白夜,是“清晨的寒意侵袭着我们”,是单薄的两个人在“涅瓦河边一间楼房”与国家机器相抗衡,那是怎样一种惊世骇俗的力量。帕斯捷尔纳克在此将这种“白夜”式的私人爱情叙述转化为了一种宏大的俄罗斯式的对抗美学姿态,一种我们才能理解的“民族寓言”(相关阐释见后文)。现将全诗录下,以供参照:
我见到遥远的往昔:
彼得堡涅瓦河边一间楼房,
你,大草原里一个小地主的女儿,
从库尔斯克来读书。
美人儿,你赢尽男子们的倾慕。
但在这白色的夜里,你和我
舒适地坐在你家的窗前
从高楼向下俯视。
像下面那蝴蝶似的煤气街灯,
清晨的寒意侵袭着我们;
像那沉睡中的远景一般
我柔声和你长谈。
我们,仿佛是沿着无际的涅瓦河
延展出去的彼得堡,
在怯羞的虔诚之中
被一个神秘的谜笼罩。
野外,远处,在密林中,
在这白色的春夜,
枝头夜莺千折百转地高唱,
咏叹的歌声震动着林野。
夜莺的高歌激越入云,
这细小而平凡歌手的歌声
在那迷乱的树林深处
挑逗着、唤醒了欢乐的心。
夜,像赤脚的朝圣妇人,
徐徐地挨近围墙,
从窗棂跟踪到她的背后的
是我们细语的声响。
在这些被她偷听的细语的回声中,
在围墙里边的园榭里,
苹果和樱桃在枝上
开着美丽的白花。
这些树,像白色的幽魂
从园里挤出到外面的路上,
如同挥手告别
这白色的夜,和整夜里的见证。
作为地理学意义上的“白夜”,是指大气光学作用(大气对阳光的折射和散射)导致的夜晚天空明亮的现象。即: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之后到第二天日出前的这段时间内,天空通宵处于“晨昏朦影”的状态。它又被称为“曙暮光”,日出前叫“晨光”,日落后叫“昏影”。这种夜晚,人们可以不必借助灯光而跟白天一样从事各种活动。白夜出现在夏季的高纬度地带,其发生范围,可以由南、北极点(南、北纬90°处)外延至南、北纬48°34′地带。在我国最北端漠河附近,接近夏至日时,会发生白夜现象。而帕斯捷尔纳克所书写的彼得堡的《白夜》(见前),也同样因为处于高纬度地区,每年夏季也都会出现白夜现象,无昼无夜,通体光明。曾经的彼得堡诗人布罗茨基对此更是深有体会。
正因为白夜是俄罗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所有的文学家都乐于书写这个主题,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帕斯捷尔纳克是,甚至那些没有直接以此为题来书写的作家都在秘密进行着这样一项事业。因为“白夜”已成为一个象征,它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寓言”,是俄罗斯式的激情对抗美学。①见柏桦、余夏云《“今天”:俄罗斯式的对抗美学》,《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版)2008年第1期。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描绘了这样一种具有国际胸怀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说:
除了这些极其重要的任务——代表自己民族的集体苦难,见证其艰辛,重新肯定其持久的存在,强化其记忆——之外,还得加上其他的,而我相信这些只有知识分子才有义务去完成……我相信,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结上其他人的苦难。②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41页,单德兴译,陆建德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显然,萨义德描述的这个形象并不适用于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着太过鲜艳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以至于他们只强调和关注自己民族的苦难,他们书写的是“今天”,而非“未来”。赫鲁晓娃(Nina Khrushcheva)说:“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才是俄罗斯的未来。”因为: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里的大多人物都很典型——苦难、悲惨成了共同的前提意识,从来没有好结局。俄罗斯人在现实中不顺利,就从这些人物身上寻找安慰。我们安慰自己:没有洗衣机、食品店,可是我们有俄罗斯精神,这就能构成一个大国。而纳博科夫一生都没有这样的主张,他自称从来没有社会目的,写作只为自娱。可如果你看他的作品,尤其是一九四○年代后用英语撰写的作品,他基本上是在为俄罗斯人改写俄罗斯文学。③赫鲁晓娃:《纳博科夫才是俄罗斯的未来》,《南方周末》2007年3月29日。
赫鲁晓娃的指认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属于俄罗斯的昨天,他们镌刻了体制生活下鲜明的时代印记。尽管他们最终将走向世界,但他们首先只属于俄罗斯。换言之,他们是在书写一种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意义上的“民族寓言”。而这种“寓言”的关键词就是“白夜”。
正是出于这种民族受难的考虑,俄罗斯的现代诗与西方的现代诗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帕斯捷尔纳克、曼杰斯塔姆、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yeva),他们写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世界主义诗歌”,而是有一个鲜明的苏联社会主义背景。他们首先要用诗歌解决个人生活中每天将遭遇的严峻现实政治问题,为了突破“政治”、歌唱自由,他们不惜用尽一切“细节”、一切“速度”、一切“超我”,像一只真正泣血的夜莺,如帕斯捷尔纳克的《白夜》便是最好的证明,他以私人的爱情书写来对抗一个公开的国家,而西方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超越了政治而专注于最普遍、最基本的人性本身。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的作家。而索尔·贝娄(Saul Bellow)不仅仅是美国作家,也是全人类的作家,他越过了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在作品中表现了对全人类的所有人性问题的关注、理解和同情。”
但是,俄罗斯式的美学,在对抗中生成,也惟有在对抗中才有存在的意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些事件统统使得对抗在瞬间瓦解,“白夜”的意义在顷刻湮灭。所以,九十年代以后,昆德拉(Milan Kundera)之类失效了,纳博科夫才预示着一个国家民族未来的展开。
顺便说一下 (以散文式口气并有意逸出主题):一九八七年我写《琼斯敦》,那是另一个“白夜”。那时我无意中卷入了西洋式的加速度,青春的胸膛再次充满渴望爆炸的军火,现实或理想的痛苦在撕咬着愤怒的眼泪,热血的漩涡如疾雨倾泻于玻璃,感情在突破,性急与失望四处蔓延,示威的牙齿漫骂着、啃着一排排艰难时日,“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对于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已经混淆了、厌恶了……我在酒精的毒焰中挺身代替曼杰斯塔姆 “残酷的天堂”,我宣告:
孩子们可以开始了
这革命的一夜
来世的一夜
人民圣殿的一夜
摇撼的风暴的中心
已厌倦了那些不死者
正急着把我们带向那边
幻想中的敌人
穿梭般地袭击我们
我们的公社如同斯大林格勒
空中充满纳粹的气味
热血漩涡的一刻到了
感情在冲破
指头在戳入
胶水广泛地投向阶级
妄想的耐心与反动作斗争
从春季到秋季
性急与失望四处蔓延
示威的牙齿啃着难捱的时日
男孩们胸中的军火渴望爆炸
孤僻的禁忌撕咬着眼泪
看那残食的群众已经发动
一个女孩在演习自杀
她因疯狂而趋于激烈的秀发
多么亲切地披在无助的肩上
那是十七岁的标志
唯一的标志
而我们精神上初恋的象征
我们那白得炫目的父亲
幸福的子弹击中他的太阳穴
他天真的亡灵仍在倾注:
信仰治疗、宗教武士道
秀丽的政变的躯体
如山的尸首已停止排演
空前的寂静高声宣誓:
度过危机
操练思想
纯洁牺牲
面对这集中肉体背叛的白夜
这人性中最后的白夜
我知道这也是我痛苦的丰收夜
——《琼斯敦》
北大的钱文亮在解读该诗时也曾注意到了“白夜”这个词,他说:
这是柏桦非常喜欢的一个意象,在他的诗中多次出现。很明显的,它标示了柏桦诗歌资源中的俄苏文学因素,那种理想主义的、幻美的、苦难中超越的、带有宗教性的献身激情与净化功能的、个人倾诉性的对青春与爱情的想象与表达。它是贯穿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和《猎人笔记》、果戈理的《狄卡近乡夜话》、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等等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影响深远的精神传统,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白夜》里更具有深刻的表现。《白夜》写的是一个孤僻成性的“梦想者”与孤女娜斯晶卡邂逅的故事,在四个白夜里,两人互诉衷肠,并且“梦想者”爱上了娜斯晶卡。但是娜斯晶卡的情人突然归来,“梦想者”虽然很痛苦,却仍然怀着感激之情向她祝福……“梦想者”身上的这些美德——精神的纯洁和爱情方面的自我牺牲,曾经深深影响了北岛、柏桦他们这代人。与此相关,柏桦特别喜欢白色、白银、白马、白夜,尤其是白夜;这是一个美妙的情境,这样的夜晚,“只有在我们年轻时才有。星斗满天,清光四射”,与柏桦热爱旧时代的自然风物的情怀正相契合……因此,“白夜”在柏桦那里成为一种超现实之美的象征……是一种 “飞翔”的激情,“爆炸”与“燃烧”的激情,或者说“革命”与“毁灭”的激情……而激情式的抒情则是要以“抵抗”为前提……①钱文亮:《在记忆与表象之间——解读柏桦的 〈琼斯敦〉》,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第277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尽管不可否认,我们那一代深受俄罗斯的影响,而且我本人也沉迷于俄罗斯诗歌,但是我想说的是,这首诗写在我的青春飞行期,那是一个充满躁动不安和波德莱尔式的“恶之花”的时代,它更多的是一种热血和燃烧,是一首极端个人化的诗,暗藏了许多个人情结与私人象征,其中有对抗的力量,但也有超越对抗的莫名的力量。它一方面代替了曼杰斯塔姆“残酷的天堂”在发言,另一方面它又属于我个人的经验,而不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二○○七年六月我写 《水绘仙侣:一六四二-一六五一——冒辟疆与董小宛》一诗时,我又一次注意到并有意使用了“白夜”这个词:“富贵人生映照着这依旧夺目的白夜”。在离开《琼斯顿》整整二十年之后,我想我这一次是获得了一次胜利。因为它无关对抗,也没有白热的个人情结。我在这个西方语词中容纳了一个古典的语境,它仅仅是指一个明末夜晚的华贵画面,在江南,在水绘园,繁华与清安并在,古典与现代互现。它复现了晚明王朝最后的风华声教,追忆了一个永世不再的以精致闲雅为时尚的遗民世界。
水绘园的白夜,是花前月下,一对神仙眷侣及一群好友轻轻地生活,不打扰人家,亦不回应时事。他们只为自己的似水流年、如花美眷而生活着,做一份人家。尽管贵重,却绝不是王侯将相的霸气,睥睨一世的孤高,而仅仅是一种安闲的风日无猜,细水长流。
这里没有对抗,只有隐逸。孤云独去,众鸟高飞,这是中国的语境,中国的感觉。尽管冒辟疆年轻时为着家国抱负彻夜不眠,英雄煮酒,但是在与董小宛相携而伴的九年里,他显得优游自足,认为一生的清福即在其中。
每花前月下,静试对尝,碧沉香泛,真如木兰沾露,瑶草临波,备极卢陆之致。东坡云:“分无玉碗捧峨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
——冒辟疆:《影梅庵忆语》
忆年来共恋此味此境,恒打晓钟尚未著枕,与姬细想闺怨,有斜倚薰篮,拨尽寒炉之苦,我两人如在蕊珠众香深处。令人与香气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扃室中也!
——冒辟疆:《影梅庵忆语》
这长久的中国古典式的白夜里有爱情,有回忆,有隐逸(虽暗含政治),更有日常。它是我对一个西方语词的中国化理解,它代表了一次转化。
如下再返回主题:
北岛的一系列抒情诗最能代表那个时代年轻的心之渴望。他安慰了我们,也焕发了我们,而不是让我们沉沦或颓唐。“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仅这《雨夜》中的两句就足以激起几代人的感情波涛。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当时的“伤痕文学”,这两句不但足以抵上所有的伤痕文学,而且是更深地扎向伤痕的最深处。它的意义在于辛酸中的欢乐之谜,只有辛酸(或伤痕)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辛酸中悄悄的深刻与甜蜜,个人的温柔与宽怀,甚至要噙满热泪,胸怀欢乐去怜悯这个较为残酷的世界。《雨夜》又一次体现了北岛抒情诗的伟大性之所在,它与俄罗斯式的抒情是相通的。《雨夜》寓意了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平凡而真诚的人的故事,一个感人而秘密的爱情生活故事,当然也如同帕斯捷尔纳克的《白夜》一诗那样是关乎对抗的故事。这故事如一股可歌可泣的电流无声地振荡了每一个读者的心,唤醒了他们那沉睡已久的麻木生活。《雨夜》当之无愧是七十年代的“娜娜之歌”,是中国的《泪城》。
相比之下,毛泽东时代越消解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就越强大,个人生活的核心——爱情就更激烈、更动人、更秘密、更忘我、更大胆、更温情、更带个人苦难的倾诉性、更易把拥抱转变为真理。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吟唱的“天色破晓之前已经记不起,我们接吻到何时为止”。“拥抱永无休止,一日长于百年。”以及他在《日瓦戈医生》中所塑造的娜娜,这一完美女性的真理形象,那近乎圣母玛丽亚的形象。在娜娜身上,他倾注了他所有的理想、抱负、热血、眼泪和美。他对娜娜所进行的无限的幻美使他摆脱了可厌又可怕的人间生活。这一点似乎证明了杰姆逊所说的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寓言”的文学,即爱情这个很私人的题目变成了对极权的反抗,对压抑的突围。这里的娜娜如此,《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萨宾娜如此,北岛《雨夜》中“血的潮汐”亦如此。
而另一些话,另一些黑夜中的温柔细语,另一些乌黑的卷发和滚烫的呼吸在北岛的“雨夜”中歌唱,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念出这些我们记忆中的诗行(而不是戴望舒的《雨巷》):
当水洼里破碎的夜晚
摇着一片新叶
像摇着自己的孩子睡去
当灯光串起雨滴
缀饰在你肩头
闪着光,
又滚落在地
你说,不
口气如此坚决
可微笑却泄露了内心的秘密
低低的乌云用潮湿的手掌
揉着你的头发
揉进花的芳香和我滚烫的呼吸
路灯拉长的身影
连接着每个路口,
连接着每个梦
用网捕捉着我们的欢乐之谜
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
沾湿了你的手绢
被遗忘在一个黑漆漆的门洞里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出奇不意的“铁条”,我们生活经验中一个熟悉而“亲切的”词汇,在这里,它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极乐(beatitude)刺入我们欢乐的心中。
“爱情”作为一种“民族寓言”在此昭然若揭。公与私,艺术与政治在此融为一体,不分彼此。联系到中国文学的传统,“爱情”一直是一个“民族解放”的关键点,明代的汤显祖写《牡丹亭》如此,苏曼殊写《断鸿零雁记》如此,周瘦鹃缠绵地纠缠这“情”字发力,连严峻的鲁迅也会在《伤逝》中以“情”来探讨中国的命运与前途。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曾在他的讲演录里多次征引安德森“想象的社群”理论,来讨论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是如何借小说叙事来传播民族国家崛起的“大叙述”想象。尽管安德森的这一理论偏重于媒介——小说、报纸——研究,但是显然故事的内容也为这类政治小说起了关键作用。显然,《新中国未来记》可以看作这种“浪漫的建国小说”,因为它模仿了日本小说《佳人奇遇》,而这个名字本身就说明了它的“才子佳人”模式。李欧梵说,在中国这类的建国小说只有《新中国未来记》能勉强算一部,而这种“中国爱情”模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如“革命加爱情”的小说就特别引人注目 (这方面刘剑梅有专书讨论,《革命加恋爱:文学史、女性身体与主题重复》)。为此,我们也应将北岛的《雨夜》放入这样一个“爱情中国”传统或王德威所说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连环中去考察。
“铁条”和爱情和受难和我们日常性的束缚和“伟大的”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样的抒情诗(或爱情诗)当然会在人们的心中一石激起千层浪。这“雨夜”中的“铁条”正好就是人们内心珍贵的铁条、幸福的铁条,它已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英雄象征——当一个人即将成为烈士时,他会含着这个象征(或这个崇高的微笑)从容地面对死亡。
“娜娜式的”爱情或“雨夜”式的爱情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被压抑的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偶像(这压抑指六十-七十年代),一个我们自己才能理解的神话。即便像赵一凡这样研究西方后现代的学者,也会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咖啡厅里,随着“娜娜之歌”的插曲开始他“昔日重来”的精神漫游或“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的漫游。①赵一凡:《埃德蒙·威尔逊的俄国之恋——评〈日瓦戈医生〉及其美国批评家》,《读书》1987年第4期。但这个神话,宇文所安认为是应当避免写出的。他说:“这种伤感正是现代中国诗坛的病症,较古典诗歌中令人窒息的重荷更为不堪忍受的欺骗。在现代中国,这种病症出现在政治性诗歌中,也在反政治性诗歌中出现。”②宇文所安:《何谓世界诗歌?——对具有全球影响的诗歌之期望》,《倾向》1994年第1期。真的应当避免写出吗?其实这是一首具有典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现代性经验的诗歌,它有着十分特殊的中国语境,而这个语境是宇文所安绝对不能理解的。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必须指出,即“政治性”是中国文学和诗歌自古以来的一个深远传统。吉川幸次郎也反复说过:“中国文学以对政治的贡献为志业,这在文学革命以前,即在以诗歌为文学中心的时代就已是这样。诗歌的祖先《诗经》是由各国的民谣及朝廷举行仪式时所唱的歌组成的,后者与政治有强烈的关系,自不用说,前者也常常有对于当时为政者的批判,这成为中国诗的传统被一直保持下来。被称为伟大的诗人的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也是因为有许多对当时政治持批判态度的作品才成为大诗人的。一般来说,陶渊明、李白对政治的态度比较冷淡,但大多数的中国评论家又说,其实两人都不是纯粹的不问世事的人,他们也有对当时政治的批判或想参与政治的意图,这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只写个人情感的诗人,但这些都是小诗人,不会给予很高的地位,这是中国诗的传统。”③吉川幸次郎:《中国的文学革命》,《我的留学日记》,第218-219页,钱婉约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因此,我认为,讨论北岛早期诗歌的政治性,应该将其置于这个伟大的中国传统中来进行,而非简单的否定。
今天派的诗歌形式与俄罗斯的现代诗歌形式更相契合 (虽然也受了一些西方诗歌影响)。俄罗斯的现代诗与西方的现代诗是不同的,帕斯捷尔纳克、曼杰斯塔姆、茨维塔耶娃,他们写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世界主义诗歌”,而是有一个鲜明的苏联社会主义背景。他们首先要用诗歌解决个人生活中每天将遭遇的严峻现实政治问题,为了突破“政治”、歌唱自由,他们不惜用尽一切“细节”、一切“速度”、一切“超我”,像一只真正泣血的夜莺。西方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超越了政治而专注于最普遍、最基本的人性本身。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的作家。而索尔·贝娄不仅仅是美国作家,也是全人类的作家,他越过了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全人类的所有人性问题的关注、理解和同情。”而今天派的背后同样有一个社会主义背景,俄罗斯诗歌自然而然成了它的姐妹。从这一点上说,今天派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毋用置疑,同样的内容、同样的背景,当然就采用同样的形式。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柏桦,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