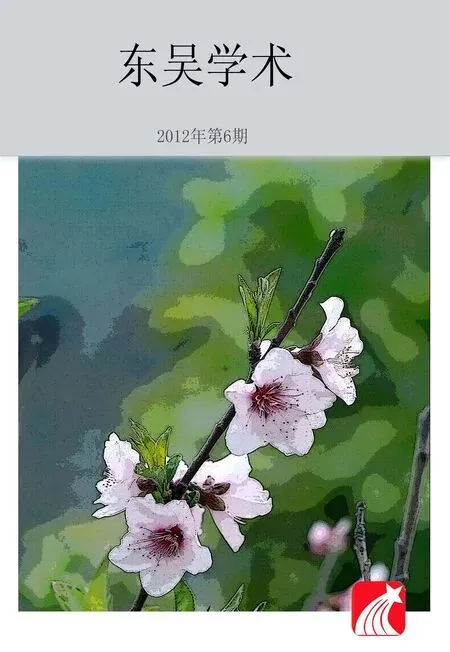闯入者、误-会、身体的焦虑
——从让-吕克·南希的《闯入者》谈起
郭建玲
随笔与书评
闯入者、误-会、身体的焦虑
——从让-吕克·南希的《闯入者》谈起
郭建玲
别人的心脏成为我的闯入者
“事实上,没有比这个叫做心脏的器官更卑鄙、更无用、更多余的东西了,它是人所发明的最肮脏的工具,砰砰砰地将生命注入我里面。”①〔法〕让-吕克·南希:《闯入者》,郭建玲译,《东吴学术》2012年第4期。让-吕克·南希引用阿尔托的诗句,开始思考“别人的心脏成为我的闯入者”。一九九一年,南希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二〇〇〇年,他写出了《闯入者》。南希写这本小册子,是以他者之心来思考本己之心,他把心脏移植的经验,身体的感觉,转变成了对主体和他者、接纳和排斥、生和死的“会”与“误-会”的思考。
“我自己的心脏和我发生了误会!”早在一九九一年之前,南希已经知道自己得了心率不齐,有心悸,并且知道这并非一件小事情。“我专有的心脏实际上已经不能用了。”通过背叛,心脏成为一个对主体而言陌生的东西。这个暗红色的、上面布满了突起的血管、依然跳个不停的“我的心脏”,已经离开“我”,“我的专有的心脏放弃了我”,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我的”器官,“我的专有的”器官?然而,此刻,反思和动作都失去了意义,只有身体,身体的知觉和痛苦,成为首要和最高的思想。“爬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每一次不连贯的多余的心跳紧缩都好像一块小石子掉入了井底。”面对事实,为了活命,南希必须接受另一个人的心脏。
移植一个心脏?这在二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二十年后,借助环孢灵素——一种新发明的药物,这成为可能。“一个人的偶然性与另一个人的偶然性在技术的历史中相遇了。”于是,“其他人”,一堆陌生人介入进来,包括医生。在个人最私密的领域,他们会,会救活南希的命。他们将南希的名字登记在等候名单上,等待在夏末动手术,等候会有一个心脏,一个O+型血的心脏。也许是一个在高速公路上不幸遭遇车祸的二十五岁少女的心脏,也许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变态杀人狂的心脏,谁知道呢?僧多粥少,供不应求,这谁都知道。(Sylvie Blocher曾经给做完心脏移植手术的南希画过一幅像,题目是《带着女人心的让-吕克·南希》。南希自嘲说,“我接受的可能是一个黑人妇女的心脏。”)据说,只要血型相合,心脏移植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尤其是不受性别、民族的限制。在生与死被分享的网络中,“捐献者”与接受者之间没有任何神秘的亲密关系,他们不可沟通地沟通着。
一种空的生理感觉打开胸腔,伴随着一阵呼吸的暂停,“一颗砰砰跳动的心”闯进身体,管子、钳子、缝线、探针,血液在体外循环,血管被绕在一起的线缝合起来,身体走进一条通向虚无的通道,“感觉好像一口气息,穿过不易觉察却早已半开的奇怪洞穴,好像参加一次展示,感觉走过小桥,却仍留在桥上”。这颗闯入的心脏,它是没有权利的,没有实现征得身体的同意,便进入了身体。但是,因为活命,闯入者已经获得进入并居留身体的权利。闯入者的通行法则是,一旦闯入,它便复多化自身,通过不断更新内在差异来认同自己。它是主体所期待的,等候的,但它仍然不为主体接受。
闯入都是凭强力发生的,只要有闯入,就会有误会;只要闯入者依然保持陌生性,误会就将继续下去。然后,排斥发生了。那个成为“我的心脏”的闯入者,它排斥“我”;它来救命,却将致命。闯入构成了双重的陌生:一方面,主体识别出外来的心脏,攻击它;另一方面,药物治疗为了保证移植的心脏不受排斥,降低主体的免疫能力,以便使主体的身体更好地接受,医学操作使接受移植心脏的主体成了自己的陌生人。一具身体,两个主体,“我”究竟是谁?
一个偶然性和另一个偶然性在科技的历史中相遇了,会合了,起初的会是否本来就是一场误-会?像买鱼挑选的时候,我们不能先尝后买,谁知道哪条鱼更好?谁来决定选择?谁来保证这不可沟通的会不是误-会?一个误-会,或一串误-会?如果不是,为何带来更多的闯入者,更多的陌生?南希回顾八年来他的身体所遭受的痛苦:首先是一种从兔子身上提取出来的免疫球蛋白,减低排斥,身体开始痉挛地颤抖……然后,是每天必须接受仪器和医生的监控、测试、评估,不停地将我驱赶到陌生中去,身体疲惫不堪,腹部引起带状孢疹,产生令人嚎叫的疼痛……然后,一个新的陌生者闯入进来——癌症……然后,一大堆陌生的化疗和放射线治疗,它们攻击咬噬着、消耗着我的身体的淋巴瘤,一方面缓解痛苦,另一方面又引起其他痛苦:眩晕、神志不清……然后,“干细胞移植”,把我从我的身体里抽取出来,引起高烧、霉菌病、全身失调……最后,我不再“认识”自己:我成了一个松松垮垮、漂浮不定的陌生者,悬浮在难以辨明的状态之间,悬浮在痛苦、无力、衰弱之间。要与这样的一个自己建立联系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一个缺乏确定性的困难:经历过痛苦和恐惧,任何东西都不再是直接的——协调把人折磨得筋疲力尽,即使自己成了自己的外来者,也并没有使主体与闯入者协调起来。从痛苦到痛苦,从陌生到陌生,不过是缝合两个相互接触却彼此陌生的“我”的一根脆弱的线。那个绝对专有的主体,退到了无限遥远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它要去哪里,要消失在哪个“我”还能声称这是“我的”身体的点上。吊诡的是,如果没有痛苦,如果主体不能宣称“我痛苦”,主体又如何借以感觉 “我自己”?误-会外展 “我”,剥夺“我”,带出两个“我”;尽管这种外展是过度的,但身体的痛苦,使主体感觉到“我”的在场。正如鲁迅所言,“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①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第1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痛苦成为交织着陌生人和陌生性的过程,这个过程铭写了主体的幸存,既是生命的幸存,也是“我”的幸存。
痛苦是闯入与拒绝的关系,是会而不合的误-会。生为了远离痛苦缺席的临界,必须以痛苦为代价吗?在现代科技的拯救下,身体成为铭刻痛苦的一个杂交体,一个“会合”:我是疾病和药物,我是癌细胞和移植的器官,我是免疫能力抑制剂和治标剂,我是缝合胸骨的一段段线和锁骨下面一直疼痛的注射位置,我是臀部上早有的螺丝钉和腹股沟里的托盘,我成了科幻小说里的机器人,一个活-死人。手术后的照片上,南希微笑着,这个带着一颗女人心的南希,这个被救活的哲学家,是否在“会心一笑”?
我闯入了别人的国家
一个女人,带着天鹅,离开中国,到美国去。望着滔滔的海面,她许下一个心愿:“到了美国,我就要生个女儿,她会很像我。但在美国,她却无须仰仗丈夫鼻息度日。在美国,不会有人歧视她,因为,我会让她讲上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①〔美〕谭恩美:《喜福会》,第3、59、20页,程乃珊、贺培华、严映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然而,当这个女人的脚一踩上美国的土地,移民局便把她强令带走了,她手里只抓住天鹅的一根羽毛。这是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的题引。
《喜福会》讲述的是四对母女的故事。小说中的母亲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移民”美国的,她们没有合法的身份,带着中国苦难留下的伤痛,她们“闯入”了别人的国家。她们是固执的、没有权利的闯入者,面对一个国家,梦想中的天堂,她们只能通过“去过去”的策略,消除陌生,实现合法化。她们的语言夹杂着蹩脚的英语和中国各地的方言,她们的名字是中国名字和美国名字的杂糅,她们的服饰由原先五光十色的丝绸,换成了“淡蓝色聚酯纤维长裤,红色围领毛衣,和一件小孩子穿的绿色短夹衣”,她们加入教会,读《圣经》。在同一张脸上,她们有两副面孔:一张中国人的,一张美国人的;她们知道什么时候用美国的那张,什么时候用中国的那张。然而,两副面孔如何在同一张脸上会-合?如果露出一张面孔,就必须牺牲另一个。
最大的误-会在母亲和女儿之间,她们互相依靠,又彼此折磨,结果两败俱伤,谁也不是赢家,谁也走不进对方的内心。母亲一方面希望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能讲流利的英语,有体面的职业,进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她们又希望女儿能继承自己从中国带至美国的那一套准则和处世方式:孝顺、谦虚、温和。在两种文化的拉锯中,那个长着中国脸的美国人,“我是谁?”如何在这个我的/别人的国家认同作为他者的母亲?女儿选择了“去文化”的策略。她们憎恶与母亲的相像;她们用母亲看不懂的文字书写日记;逃避、违抗母亲对自己成长的规划;她们甚至用夹子夹住鼻子,试图改变中国人的身体特征。
坐在桌子的两端,母女相隔如重山。“我们彼此失散了,她和我。我们互相间见不到,听不到,互不了解。”②〔美〕谭恩美:《喜福会》,第3、59、20页,程乃珊、贺培华、严映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在女儿面前,母亲没有过去;在母亲面前,女儿没有未来;在别人的国家,她们是彼此的陌生人。没有融入,只有井水与河水相望而不相会的痛苦和焦虑。
来吧,女儿,来我给你讲讲我在中国的故事,用夹杂着汉语的英语。“我要告诉她,我爱你的方式是你所看不到的。也许你不相信,可我从内心深处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你伤透了我的心,说不定我也伤透了你的心。”母亲从旧衣箱捡出一件毛衣,拆开底边,从中抽出根线头,随后,以一种破竹之势,毛线衣很快化成一根弯弯曲曲的毛线,而她的故事,也以同样的节奏倾泻出来。犹如一道浓重的阴影,它渗入母亲的生活,也渗入到女儿的生活中。女儿回到了母亲曾经坐的麻将桌的东首,“万物起于东方:日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③〔美〕谭恩美:《喜福会》,第3、59、20页,程乃珊、贺培华、严映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语言无法到达的地方,身体召唤身体
在语言无法到达的地方,只有身体占有身体,身体召唤身体,身体是最有力的思想。就像闯入“二十九棵棕榈树小镇”的一男一女,只有焦虑的身体才能消解语言的误-会。
男人叫大卫,只会说英语,女人叫加茜娅,只会说法语。他们似乎是一对恋人,又似乎不是,他们去“二十九棵棕榈树”拍摄外景照片。这两个身体构成了世界(大卫的橙色T恤上正印着醒目的GLOBE字样),这个世界是他和她的身体的展示,也是他和她的冒险:冒着不可渗透、相互抵制的危险,也冒着相遇和相互溶解的危险。
“二十九棵棕榈树”,一个名字毫无意义的小镇:荒芜的沙漠,没有人烟的道路,裸露的山石,高大的仙人掌树,满身芒刺,向天空伸展,冷清的商店,漠然的人。他们闯入了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封闭闯入另一个封闭,语言无法到达,撕裂的切口在哪里?身体!
汽车在大路上奔驰,窗外是白炽的烈日下旺盛的沙漠,车内是听不懂的音乐,他们没有交流,也没有接触,只是向前开去。这里没什么可讲的,也没什么可沟通的,两个身体不可能同时独自占领同一个空间。①让-吕克·南希:《身体》,陈永国译,《解构的共通体》,第359页,夏可君编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加茜娅由漠然,抽搐,最后哭泣起来。最后,汽车停在一片无人的荒漠,矗立的裸露的山石,绵延开去,他们赤裸的身体,爬上山峦的顶处,像造物的孩子,仰脸躺在蓝天下,灼热的阳光下,“我们要燃烧了”。裸露的沙漠。裸露的石头。裸露的天空。裸露的太阳。裸露的男人。裸露的女人。如此众多的身体,融入了自己一无遮碍的条目,在语言不能渗透的地方,他们发现了裸露的真理——身体。
一旦语言闯入,误会便发生了。在冰淇林店外,看到邻座的水手,大卫和加茜娅有这样一段对话:
大卫:如果我把头发扎成这样,你会甩了我吗?
加茜娅:果真如此的话,我会……
大卫:我认为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你又说法语了。
加茜娅:果真如此的话,我会离开你。
大卫:你不喜欢水兵吗?
加茜娅:喜欢。他们真的很帅。
大卫:也不见得吧。
加茜娅:正如我说的那样。
大卫:你在说什么呢?
大卫:好吃吗?
加茜娅:不好吃,但还是很棒。
大卫:我也不知道,我不明白。你说些让我不能领会的话。
加茜娅:没有可以领会的东西。
大卫:很好。
加茜娅:很好。你生气了吗?
大卫:没有,我没有生气。
加茜娅:没错,你生气了。
大卫:我们会话的时候会产生诸多障碍,有时你这样说,有时那样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会话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功能……
加茜娅:我爱你。
大卫:我需要你。
加茜娅:我也需要你,亲爱的。②《29棵棕榈树》(Twenty-nine Palms),导演:布鲁诺·杜蒙(Bruno Dumont),法国,2003。
身体占有了语言不能渗透的地方,无法沟通的两个人之间,身体是唯一的通道。身体召唤身体,成为一个没有精神的身体的共通体。给予与被给予,离弃与被离弃,身体从全部符号的游戏中撤离,只留下一个触摸和被触摸的轨迹:摩擦、拥抱、吸吮、穿透、颤抖……
他们闯入别人的小镇,身体的重量和释放,将封闭打开一个缺口。闯入者其本身构成了小镇封闭的正确性的侵犯。一切始于路上,止于路上。又一次外出拍景的路上,他们被小镇的三个男人追击,加茜娅被剥光衣服,大卫被打,被鸡奸,鲜血残酷地洒出,从棍棒击打开的伤口残酷洒出,这个被驱赶、被抽打、被折磨的身体,半张脸贴在地上,露出惊恐的眼睛,看着加茜娅赤裸的身体。闯入者本身被闯入了,闯入撕裂了他和她之间的亲密关系。从现在起,不再有产生意义的身体,身体不过是伤口。受折磨的身体的痛苦始终存在着,伤口是痛苦的符号,标志着一个被剥夺了身体的遭禁的身体。
经过了岩石地带的悲痛以后
又是叫喊又是呼号
监狱宫殿和春雷的
回响在远山那边震荡
他当时是活着的现在是死了
我们曾经是活着的现在也快要死了③T.S.艾略特:《艾略特诗选》,第78页,赵萝蕤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最后,杀戮和自杀,分解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身体创造的“世界”。“世界、我和声音都消失在强烈的痛苦的折磨之中。”
也许,你们听入耳的比我说的内容要多得多,也许,你们听入耳的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也许,在这次会面中,我们已经产生了误会。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我们已不再陌生。
郭建玲,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