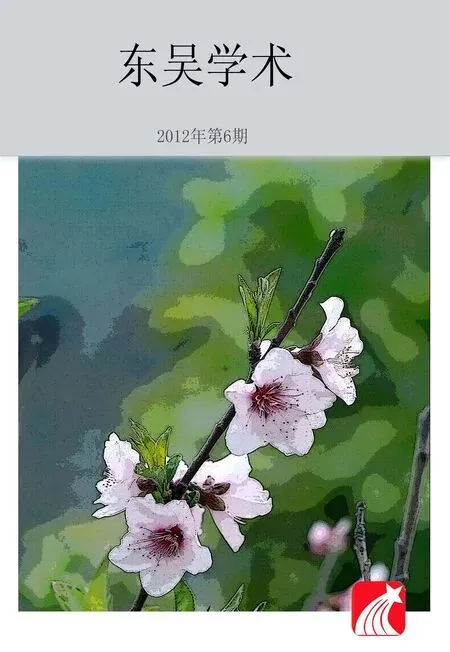海外中国研究的冷战与东方主义余绪
——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王斑
东吴讲堂
海外中国研究的冷战与东方主义余绪
——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王斑
主持人 傅大友 丁晓原
丁晓原(常熟理工学院教授):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下午好。今天,我们举行第二十次东吴讲堂。东吴讲堂是一个高端的、开放的、国际化的讲堂。此前,我们邀请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康奈尔大学等海外高校的著名学者来校讲学。今天到讲堂担任“堂主”、“版主”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王斑教授。我们热烈欢迎王斑教授光临我校。下面我向各位简要介绍王老师的学术情况。王斑教授祖籍山东,出生在福建厦门。一九八二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学位,一九八五年于该校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一九八八年旅美留学,先于爱荷华大学读比较文学,后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园,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园任教,一九九八年聘终身教授。二〇〇〇年转新泽西罗格斯大学,二〇〇四年聘正教授。二〇〇七年聘为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二〇〇二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系任客座教授。二〇〇九年聘为华东师大长江讲座教授。学术写作涉及中西文学、美学、历史、思想史、国际政治、电影及大众文化等。下面我们就请王斑教授作学术讲演。
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到常熟理工学院来,我也感到很荣幸。我是去年到苏州的时候,才知道有常熟理工学院,非常孤陋寡闻。来了以后才发现这不仅是一个训练理工的人才的基地,而且是一个人文学科的重镇,这令我非常惊讶。丁晓原、林建法先生还有学校的领导班子非常重视人文科学的发展,投入很多资本,花很大心血搞这个规模很大的基地,现在已经名声在外了。我在海外已经听到不少人提到这里的文学发展,一个是苏州大学,一个是你们这里,两个地方,靠得很近,相得益彰。中国文学已造成很大的气势,搞得有深度,我非常高兴。今天到这来还有另外一件令我非常激动的事,是今天早上林建法先生带我去参观了沙家浜这个景点。沙家浜使我想起我中学读书的时候,刚好赶上“文化革命”的尾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父母讲过,那时中学小学人人都得参加演出革命样板戏。可以演出的剧目很多喽,有的人演白毛女,有没有看过《北风那个吹》那个电视剧?就是讲知识青年演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我当时演沙家浜的一个唱段,下完课就得在教室或外面去练练。我演的是郭建光,是正气凛然、不屈不挠的一个形象,唱段是“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去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开了一个会,讨论重新发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美国学者还试图发现“文化大革命”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还让我去讲讲,当中还邀我唱了一段京剧“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这次来沙家浜,感触非常深。这跟我们今天这个讲座有什么联系呢?我想说,对于沙家浜这样的文化遗产、文化记忆,我在美国学生中,一百多人中恐怕没有一个人懂,这包括中国留学生,因为在他们记忆当中,中国的历史,“文化革命”,改革开放前的这段历史,三十年以前的历史意义是空白。“文化革命”那更不要说了,是一团糟,是动乱,文化荒芜,十年动乱,所以他们都不知道。这也使我益发对沙家浜那么憧憬,那么钟情,而我的学生对此有隔膜,认为是非常遥远的事。这反映了一个问题,学生是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以什么历史背景来了解、理解、接近、走近中国文化的,沙家浜与我今天讲的题目有点关系,知道沙家浜以后你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会改变,不会像那些没有历史记忆的人,觉得中国以前就是非理性的、黑暗的、动乱的,到后来想开了,搞经济,搞改革,然后才取得了中国的崛起,才让人家看得起,其实不是这么简单。我要从沙家浜谈起,作为一个跳板、一个切入口来谈。我想谈谈,在国外传播和教授中国文化,会有什么样的隔膜、误解和偏差。缺乏类似沙家浜的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深厚了解,我觉得会带着各种不同的有色眼镜看中国。有人会反驳说沙家浜很商业化,只是为招揽游客赚钱。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沙家浜有很多很可贵的精神,阿庆嫂是一个非常机智的地下工作者,是抗日英雄。但她带有很多的民间文化的因素,她伶牙俐齿,能够舌战刁德一等一些非常狡猾的人。而且沙家浜的成功依靠有深厚的草根传统的群众,这说明革命者改变历史、改变社会、改变世界、打败外国的侵略,种种努力都离不开身后的群众,依靠民间的、老百姓的才智。但是这种观点在国外的讲坛、学术研究上比较少见。国外的学生、老师、学者比较短视,他们认为最近改革开放三十年,像上海浦东的发展、深圳的发展,才是最有意思的,而从这三十年往后推就黯然失色。这样切断历史我们就失去了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外教学和研究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有色眼镜。第一个有色眼镜就是冷战,第二个就是东方主义。什么叫冷战?要想知道冷战先要知道什么叫全球化、国际化。
全球化以为,全世界的人,不管什么样的肤色,操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国家,都可以有机会汇聚一堂。可以跨越国界,用一种世界语言在一起交流、沟通,谈论学术,互通有无。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纪》一开篇就描绘了一幅全球化的景象,描写了世博的盛大场景,全球的商人都来中国做生意,各国学者汇聚一堂,共同商讨学术,梁启超称之为大同。康有为的《大同书》曾有这样的理想:天理相通,四海同心。大同即世界各国人可以互相交流对话,没有太多的隔阂,虽然我们的衣着、种族、语言不尽相同,虽然我们来自五洲四海,但最后仍能齐聚一堂。所以全球化有些类似于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大同和全球化在我看来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在当今列国纷争的情况下,却是一个迷雾或是一个迷失(myth)。中文把myth翻译为迷失很有意思,即失掉方向,不辨东西。所以完全陷入全球化迷雾中的人,看不到事实上世界仍然被分割成民族国家的几大块。民族国家、国势的对峙还在持续,没有被全球化的力量推倒。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曾讲过:资本主义全球化会把中国的长城推倒。因为地球平了,没有隔阂和壁垒。可是前几天我个人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在美国生活很长时间,也拿了美国护照,到欧洲,到台湾,到香港,没有必要去办签证。美国的护照使我中了美式全球化的毒,全球化的背后其实是美国人对世界的想象,觉得全世界畅通无阻。《纽约时报》专栏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为人津津乐道的书 《地球是平的》,说地球平了,没有隔阂和壁垒,大家是自由的。所以持美国护照者可在全世界一马平川,畅通无阻,出门不用到旅行国家的大使馆去办签证。可是我差点没来成常熟。我在走的前一天晚上,看了护照,发现新换的护照,页页是空白,这能去中国吗?绝对不行啊。所以我就在最后一刻跑到大使馆去办了个签证,如果不办的话,根本就不能来。你要跨过国界,你还是需要得到这个国家的许可,你并不是一个世界人。这个护照并不是全球人的通行证,什么门都可以打开。世界人这种定义,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你还得要有国家,身份还是由国家来界定的。所以这一点就使我想起了我自己深陷其中,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一个世界人呢,还是一个美国人,或是一个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要把全球化看得这么乐观。专家学者在谈全球化的时候,没有看到全球化底下还有冷战的暗流。什么叫冷战的暗流?我们说中国、美国或者中国、西欧等,我们经济都融合到一起去,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那么既然一体化,你干嘛一天到晚穷兵黩武?你干嘛在黄海做各种各样的军事演习?干嘛挑动越南等中国的周边国家纠集起来围堵中国?现在美国在砍军备,可是在亚太地区从来不会砍军备,只会增加军备。在太平洋,他们的军事基地到处都是,台湾是永远不会沉的航空母舰,日本的美军基地也很多,韩国也是。我在韩国时发现,英文电视好多是美国军事基地的电视。到处是老美势力范围,你谈什么和平地做生意,谈什么大家都共赢?什么叫冷战?冷战并不仅仅是过去美国和苏联对峙,冷战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国势的发展而超出自己的国界,来重新调整、部署一国在海外的势力范围。苏联倒了,并不说明冷战的格局已经结束,还要重新来调整大国、强国在世界经济领域,能源需求的势力范围。所以冷战仍然要军备竞赛、强弱相争。其实我们中国也是这样,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们知道,中国在发展航空母舰,还有各种各样的超音速飞机。前两天我看到美国还打了一个超音速的导弹,可以打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这就跟谷歌找地理位置一样,一下击中目标。
全球化了,可是原子弹各国都在搞。世界根本不平静,太平洋从来都不太平。稍稍注意新闻就知道南海硝烟弥漫。而且奥巴马来亚洲的时候,也一直说要“返回亚太”。但他们从来都未离开过,却说要回到亚太。这就像在冷战初始的时候,说美国失去了中国。他们从来都没有拥有中国,却说他们未曾拥有的东西失去了。新的亚洲政策要加强对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这个军事部署大概占他们全球军事的50%,他尽管打过伊拉克、阿富汗,等等,但是真正的重中之重是太平洋,在关岛和澳大利亚部署重兵。当我们为经济、文化全球化侃侃而谈的时候,冷战却是埋藏在全球化迷雾中的危机,是一股冷流,仍然在地下窜动。而冷战类似过去的殖民,是某些强国想保持不平衡。美国外交家乔治·柯南在一九四八年提出冷战理念就认为,冷战是要维持美国与世界的不平衡的关系。他们5%的少数的人却占有60%的世界资源财富,那多数人不会心甘情愿的。所以冷战的理念是靠军事威慑你。据说,美国在全世界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美国人的军备预算比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军备预算之总和都要多得多,所以冷战是一种保持新的殖民范围的办法。
殖民霸权会不会摧毁你的文化呢?这就涉及东方主义。什么叫东方主义?日本人在侵略中国的时候,表面还把中国的文化束之高阁。西方在两百年多中也是这样。东方一直都是他们的殖民对象,掠夺资源的地方。他们当老大,但老大不见得要把你的文化扫除一边去,他反而会欣赏你这种东方的色彩,一些优雅的东西,这就是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可以把你捧得美轮美奂,欣赏你的“慈禧太后”、“小脚女人”,欣赏你的东方美人、东方佳丽。它还把小脚女人搬到大博物馆。你们可曾看过《雪花秘扇》?《雪花秘扇》主要是讲两个女孩子,在封建家庭的女孩子裹脚,把脚弄得像三寸金莲,这样才能嫁得出去,才能有好日子过,才能有前途。同时她们两个女孩子在男权高压专制下,在摧残妇女体制下,继承了一种只有她们能懂的语言——女书。她们通过女书的沟通交流,来产生一种自由开放的空间,求得自己的生存。这个故事所渲染的是东方主义。小脚女人,在五四时代都是在批判之列,很残酷,摧残妇女。康有为、梁启超很早就在搞去缠足会,废除裹脚。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化把这个东西搞得很臭。这部电影由小说改编,作者有些华裔血统,她某个祖先可能是五、六代以前的中国移民。小说非常欣赏中国很远古很腐朽的糟粕,能让凄惨的事变得非常精美,三寸金莲看上去很精巧,整个电影和小说都是往那方面下功夫。把它变为艺术,要达到三寸金莲,要怎么样去裹脚,血淋淋的,但它把血淋淋变成审美之物。演员一定要东方佳丽,一个是李冰冰,另一个是韩国巨星全智贤。全智贤演新婚之夜那个女孩子。她很早就听从媒婆的劝告,忍受很多痛苦,把脚弄得非常小,新婚之夜,有一个很长的戏。她坐在炕上,然后镜头就是特写照那只脚。穿了很漂亮的绣花鞋,这个夫婿端起这个脚,先把玩一下,然后把非常细致漂亮的镶金绣花鞋摘下来,再去把玩,当作恋物。最后人头从画框外凑上去,kiss那只小脚。我看到这幕,非常难受,我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化长大的人一定会不舒服,可美国观众却不觉得难受,认为这是最精彩的。我座位后面有个从大陆来的女学生脱口而出:This man is sick,这个新郎很病态。我说不是新郎病态,我觉得是这个电影变态,但是这部电影特别火,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榜首。如果你要写祥林嫂,控诉中国妇女被压迫,控诉摧残妇女,绝对不会走红畅销。这就是东方主义。另外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秋瑾,秋瑾参加救国运动,是巾帼英雄。但是一谈到秋瑾跟民族解放,跟孙中山的关系,在美国观众看来就有问题,因为妇女解放怎么能跟国家联系起来,妇女解放就是妇女解放,好像个体的问题,别牵扯到政治。这是东方主义的一些表现,东方主义并不想贬低或者说摧毁东方文化,因为它可以拥他人文化为己有。在博物馆、在拍卖艺术的场所,东方文化、东方艺术价值不断攀升。就像鲁迅讲过的,殖民主义者最欣赏我们的国粹,所以鲁迅非常反对国粹这个词,很讨厌国粹。因为主子拥有你奴才的东西。你到美国很多大庄园里头,在加州的铁路大亨豪门,他们家的庸人都是中国人,他们家里的起居室、客厅,挂的中国满清一些大画,而且还有很多小玩意儿,都是东方的。他们非常直率,有种自豪感:我拥有你的东西。
大亨们的儿子可能会在远东前线作战,是远征军;或者做生意,到中国冒险家的乐园,然后把中国的这些有东方色彩的玩意儿拿回来,放自己家里做展览,很牛气很光彩,有老大的感觉。所以冷战的权利、势力不平等,实际上和东方主义有内在联系。以这种思想和情感和有色眼镜作为背景,美国学生和学者走进中国的路径有三种,第一种是审美,到中国走马观花地看看,读中国的文学和诗,都找一些觉得契合自己口味、很抒情诗意的这样的小片段。另外一种就是功利的态度,我学中文能够跟中国人交际,知道过年过节在干什么,待人接物交际怎么办,这是功利性。第三种是疗治性,以医生自居,说中国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不符合我们的标准,你不能靠工人去管理,你得靠我们外国管理人员去管理,你人民币的价值太低了!应该升高这才符合国际标准。中国到底怎么走?在他们眼中,要跟他们普适标准接轨而不是你自己按你自己的想法去创造你的未来。中国必须走到我们的这个模式,所以要用休克的疗法来给你诊断治疗。
因为有这三种态度,一般美国人不把中国的文化当作一件有主体判断的有理性价值对象。他们觉得对中国人就是教小孩,站在很高的道德制高点上,来评判中国的不足。他们不把你当作一个有血有肉有头脑的人,而当作一个物,把一个人完全当作一个审美对象。这是一种对物的态度,而不是对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态度。
我现在来讲一下我教学的经验。我除了教文学以外还教过很多电影课,每年都会上一次电影课。在中国电影课上,不知你们想看什么样的电影,你们喜欢看什么王小帅、张艺谋、贾樟柯,或是比较新近的电影。我认为,上电影课,不仅是看电影娱乐,更是教文化。文化就是一种历史,不只看最近的二十年,应该往前回溯历史。所以可以放一些像《神女》的早期电影,从三十年代走到四十年代,走到五十年代,看《青春之歌》,然后还有一些像六十年代的《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然后再往前走就是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国经历变革,这么多的风风雨雨,电影反映了这种坎坷这种奋斗。总之,你要有历史的长河,历史轨迹,用不同时代的电影。可是我的学生比较喜欢九十年代以后《十七岁的单车》和《饮食男女》,越新近学生越喜欢,因为可以认同自己的经验,比如说少儿犯罪、都市伦理剧、都市情爱戏,有关吸毒的,有关犯罪,逆反心理啦,不听父母教育之类的电影。这类电影反映了新一代人在新的环境中不爱上学读书。这类电影在西方,反映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艺术上也是陈词滥调,可是他们一看到中国新新人类跟他们同样地生活,忽然化腐朽为神奇,很快认同吸毒、犯罪、反抗性、逆反心理等影像。他们是从个人角度,而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
在中国的ABC,就是美籍华人,很喜欢有中国气派,特别爷儿们、有帝王气派的电影,最喜欢功夫片。他们来找我,说:“你要多放功夫片,武打片。”我纳闷你们为什么喜欢功夫片、回答是,我们要让白人看看,我们中国人过去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就可以拳打脚踢就把你们打得屁滚尿流,非常厉害的。中国移民,即使历经几代人,在美国还是受歧视,黄种人受白种人歧视。你看,不得不谈到种族的问题。不是说全球化吗?全球化超越种族,可是在这个时候你不得不谈种族问题。美籍华人要我放功夫片,就是要让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是不好欺负的。中国人同样可以有扬眉吐气的时候,同样可以打败他们。最近有几个香港片,像《叶问》这样的,可以增强民族气概的这类电影,他们就非常非常喜欢。在加州这样的地方亚裔占百分之二三十,像伯克利,亚裔都能占到百分之五十,可是还是有种族歧视。
这就使我想起在海外华人文学里,有两个非常醒目的形象,一个是花木兰,第二个是关公。他们都是有武功的人,而且是能够匡扶正义,道德非常完善的。花木兰是替父从军,忠孝两全。关公也是匡扶正义,刚直不阿。这两个形象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美籍华人总是觉得他们是被压着,所以他们不断地在追求这两个形象。他们写的剧本,拍的电影,还有他们写的小说也经常会让这两个形象出现。Woman Warrior——像花木兰这样的女战士是榜样。前几年有迪斯尼拍的一部花木兰的动画片叫《木兰》。那部电影是东方主义加上西方主义色彩的一部电影。因为它并不是把花木兰作为一个替父从军的形象,而是发展成一个追求爱情的形象,一个女权主义者,为女孩子争取权利的这样一个形象。她跟我们历史上的花木兰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你要把花木兰替父从军从忠孝两上去讲的话,会符合中国人口味的,但不符合西方人的口味。西方人喜欢个人主义的英雄,追求爱情,追求自己的独立。但美籍华人都非常喜欢这种电影,因为他们看了这种电影很解气。他们觉得在白人当中他们可以昂起头来,给他们争光,给他们解气。
中国在办奥运会的时候,在美国好多大城市,中国的学生保卫火炬,跟好多美国的民众发生了冲突,甚至流血受伤。火炬代表什么?火炬代表奥运。但是中国人去拿这个火炬,中国人原来是被殖民的,连老二、老三都算不上,西方是老大,你怎么能拿奥运火炬来走街过巷,招摇过市,不行。你中国人凭什么拿着火炬到美国这种西方的地界招摇过市,不行。然后很多人就围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在巴黎发生的很惨的事情。很多人想抢火炬,要把火炬扔掉,然后有一个大陆去的残疾的女孩子,为保护火炬,被推到喷水池里,还抱着火炬不放。当时在旧金山我也看到了这个视频。显然是他们觉得你没有资格拿着世界性、全球化的火炬在街上来表示你已经走上国际舞台。他吃不消你这个。奥林匹克实际上是有大同精神的,其实梁启超、康有为讲的大同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人家不愿意你参加大同。因为有东方主义,还有冷战这种思维,就是说,全球化要在我们的名下,不能在你们的名下。中国能否走上世界,在美国的民众中产生很大争议,中国的美籍华人,虽然世世代代远离中国,已经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叫香蕉,皮黄内白,可他们还是觉得,中国的崛起,他们脸上有光。中国的崛起是势力上的崛起,军事上、经济上的崛起。实力的崛起对文化有很大影响。
再谈谈我在教学上碰到的问题。我有一个博士生毕业后,在德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学院当教授。她开的中文课的学生里,十八个人中有十四个学生都是豪门世家,石油豪门,就是开采石油致富的。每家都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他们学中文干嘛?——做生意,或是当外交官。当外交官干什么?就是怎么样去对付中国。外交,就是怎么样去保持我们的霸主地位。外交实际是诱饵,所以“弱国无外交”。外交是要靠实力操作的。他们这样富豪的子弟,走进中国的动机是很功利性的,他们要在中国的地域上发挥他们的才能,他们要成为权势阶层的接班人、太子党,接他们父母的班。另一个功利意图就是做生意,做石油生意或者做其他的生意。
由于这种功利态度,他们把老师当佣人一样,认为你过来教我中文,我们学中文来对付中国,这是非常老大的态度。比如明天要考试了,他们就赶紧复习,半夜十二点,凌晨一两点给老师电话说:“这个问题怎么做?”这样半夜惊扰的事,频频发生,老师若拒绝,那家长就会向学校问罪。他们把老师当保姆一样,非常牛气,认为自己是未来权势阶层的接班人,所以把我这个学生当贵族使唤的保姆,他们实际上并不把中国人,中国的老师当作平等人来看,没有一点师道尊严。面对真正的中国人,能把他们当作学习的对象吗?来中国,真的想学中国人值得学的地方吗?很多人不是真的想学,只不过想了解中国的一些东西以对付中国。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下面我想用一段电影来解读一下,什么叫做用冷战和东方主义这种心态来呈现中国。这段电影选自《小裁缝》,是根据戴思杰小说《巴尔扎克和小裁缝》拍的。小说原是法文写的,后来翻译成英文。在法国是畅销书,英文版在美国又是畅销书,电影也是畅销片。这个大概的情节是这样:两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湘西凤凰山深山老林里,参加劳动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个叫马剑铃,刘烨扮演;另一个叫罗明,陈坤扮演。他们在深山老林里生活非常艰苦,没有文化学习机会,农民很愚昧。有一个知青带了一箱书,其中有巴尔扎克的小说。他们如获至宝,两人就虔诚地读起巴尔扎克的小说。读着读着突然觉得启蒙了,在这非常落后的深山老林里突然找到了光明,体验了文明。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发现了性爱、爱情、个人奋斗、个人解放,懂得了女人的美,一个很崇高的、一系列的价值发现。他们开始用女人的魅力来教育小裁缝。小裁缝是一个村妞,他们向她灌输小说中性爱、美、爱情、浪漫等思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巴尔扎克的书就是再教育,带来了真理启蒙光明,带来了他们的解放。之前他们好像被禁锢在一个铁屋子里,整个乡间的生活就是监狱。做农活外还要挑大粪,浇地,要挖矿,犹如地狱。可是有了对巴尔扎克的阅读,就如换了一个人,焕发了新生。
我在文学课上用过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像鲁迅、丁玲、沈从文,乃至张爱玲、余华。但是没有一部作品像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和电影《小裁缝》那么让他们那么激动。美国媒体也非常激动。当时在美国国家广播电台还做了一个讲座,请美国专家来讲这部电影。他们最喜欢的一个片段,就是 “莫扎特想念毛主席”的一段———莫扎特是十八世纪奥地利的一位作曲家,你们也许听过一些他的作品——这个片段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视频。两位知识青年来到山村,在黑暗局促的小屋里,队长严厉审查他们的东西。村人发现有个小提琴,要把这个“资产阶级的破玩意儿”付之一炬,但罗明说这是一个优美的乐器,可发出很美的音乐,队长就要马剑铃试试:(视频播放,其中一段的录音)
队长:“……来一首试试。”
马剑铃:“队长我不行。”
队长:“我让你试,你就给我试。”
罗明:“剑铃给队长拉一段莫扎特的奏鸣曲。”
队长:“奏鸣曲是啥东西?”
马剑铃:“奏,奏鸣曲是一种山歌。”
队长:“歌名是啥子?”
马剑铃:“像歌,但不是歌。”
队长(很不耐烦):“我问你歌名!”
马剑铃:“歌名叫莫扎特……”
罗明:“莫扎特想念毛主席。”
队长:“莫扎特永远永远想念毛主席。”
“对!”
“开始!”
“队长叫开始就开始嘛。”
名不正“乐”不顺。罗明急中生智忽悠队长,说曲子名为“莫扎特想念毛主席”。村长面有悦色,欣然应和:“莫扎特永远永远想念毛主席”。命名通过,山野农人便开始欣赏莫扎特奏鸣曲。音乐优雅柔和,若潺潺流水,从黑暗狭窄的陋屋里流淌而出,飘流向岭头山谷。先前不知小提琴为何物的野人,却立马无师自通,洗耳恭听,本能地被莫扎特的西洋乐所征服。电影用镜头将听音乐写得很有诱惑力。摄影机随着音乐缓缓退出陋屋,用长镜头、大远景展现郁郁葱葱、沉睡的山岭,并缓缓摇拍,盘桓其中,最后定格在“天眼”这个怪石之上,似乎开了天门,开了天眼。这远离文明的荒村野岭,破天荒第一次聆听了西方天籁,实为盘古开天地。这种普适的高雅文化,蒙昧的野人都能欣赏。
野人开化,回到文明的怀抱,是构成“莫扎特想念毛主席”这一片段的基调。难怪美国电台的专家和我的学生,都对此赞不绝口。他们之所以喜欢这部小说及电影,是因为作品表现了中国人受赐开化启蒙,领教了自由、个人幸福、爱情、女性美,还有违背礼教的性爱。这些似乎是任何一个文明、自由人都应该具备的素质。他们乐意看到落后的中国人被莫扎特音乐和巴尔扎克所征服。讽刺的是,这些堂皇的艺术家名字,对于我的学生来说,已经十分陌生,已被遗忘。大部分学生不能指称一部莫扎特的奏鸣曲,不知巴尔扎克为何许人。没有一个人敢说读过巴尔扎克。我相信,在电台上奢谈的专家们,也好不到哪去。对自己的文化一无所知,回头又把自己的优越文化摆在他人面前,让人敬仰,凭什么那么地自豪?难道对自身文化没有自知之明,而看到别人拼命追求自己的文化时,也会欢欣鼓舞?也许文化是什么并不重要,知不知也无所谓,关键是享有什么权威、权势、优势,以自己的“优势”觉得高人一等,但优势优在何处?没人去过问。只要看到那些中国人,那些原始村落里的未开化的“土著”拼命追求“我们”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我们”的优势和正当性便得到了肯定。这证实了“我们”的文化是现代性的标杆、旗帜,历史进步的航标。这些话不是来自媒体,而是学生说的。这个航标向全人类指出了走向未来的道路,不论你是什么种族、地域、性别、文化,都要走上这必由之路。
在他们看来,莫扎特、巴尔扎克代表的文化并不是多元的文化中的任意一种,不是“一夷”,西方文化似乎不受历史地理的因素所限制,它是普世文化,人类文化,它最终是一切地方色彩的底色。在地缘政治权力不均的关系中,文化和启蒙,也成了优胜劣汰的游戏,成了进步、强势的代名词。小说中的一段,抄写在羊皮袄上的巴尔扎克的文辞使一位医生如得天启,热泪盈眶。另有一段讲述受迫害的中国基督教牧师,在弥留之际,所有语言记忆都失去,惟有过去学的拉丁语还在,口诵拉丁语去见上帝。在学生看来,这些情节再自然不过了,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的。这些中国人,受苦受难,愚昧无知,成为自身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受害者。要解放要翻身,就必须彻底脱胎换骨放弃落后的文化,皈依巴尔扎克,皈依拉丁语,小裁缝最后离家出走,漂流世界,到香港或出国,便是自然的结局。
自己都不知道莫扎特是何许人也,连巴尔扎克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可是他们都非常喜欢看到中国人那么蜂拥地在巴尔扎克的影响之下突然觉醒,有了人格、有了人样、有了自信,说起来,这部电影对于历史的表现确实有真实的地方,其魅力是政治讽刺、意识形态针砭。可是我又一想,那年轻人偷来的那箱书里头,不仅仅有巴尔扎克的书,还有鲁迅的书,还有其他好多作家的书,可他非要找巴尔扎克的书来说事。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一直很流行,也不是突然从天而降。你凭什么觉得你的文化是优越的,那别人的文化就是落后的。你优越你文明,你高雅,别人就是落后愚昧。学生说这是灯塔,巴尔扎克、莫扎特是灯塔,照亮黑暗。“灯塔”这个词是帝国的心态对其他民族国家常见的修辞。我们是别人的灯塔,你必须跟我们接轨。这样的优越感,会影响很多人。不管学生还是教授还是专家对中国的看法带有很大的成见,很大的优越感。我们西方创造历史,创造文明,而你们跟小孩一样,蹒跚学步慢慢跟上来,跟上我们。反过来,我要问,你对自己都一窍不通。连巴尔扎克是谁都不知,你凭什么来把人家看扁了?我经常百思不得其解。
我把它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在传播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的时候,有各种阻力,各种各样的东方主义偏见,冷战遗留下来的余绪,影响着美国人对待中国的态度。我想你们也想将来有机会到国外求学,学到先进的知识。我当学生时也有这个良好愿望。但是不能把西方学术文化想成一个非常公平的平台。它不是平的,有各种各样的陷阱,各种各样的暗礁,有冲突。我们不能受主流媒体,受主流的观念的支配。不能没有自己的思考,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是我留给你们的一点个人的体验和忠告。谢谢!
丁晓原:王老师以他的亲身的观察感受,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海外对于中国形象的一个塑造和解读。王老师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就是冷战,还有一个就是东方主义。刚刚王老师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些理论的知识,同时还给大家看了一段电影,尽管电影的效果不太好,但是毕竟看到了。而且小说也好,电影的故事也好,都是很有意思的——《小裁缝》——刚才画面都是非常美的。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看今天因为时间比较紧,就提两个问题吧,跟王老师请教一下吧,好不好?
王斑:我希望就是你们有时间能找机会找这个电影看一看。
丁晓原:这个网上有吗?
王斑:这个网上有。
丁晓原:那上网看。
学生:首先我要感谢王教授今天的讲演。我觉得你刚才说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中国人在外国的处境,与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东西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种感觉是,中国人在国外,其实就算是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么高,还是受到很严重的歧视,不知道“严重”这个词儿是不是有点过分。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他们国外人对中国人的了解是很片面的,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了解就没有那么全面,我们现在就无法,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无法进入到自己的历史中去反思、去认识,那么我们的年轻人跟他们进行对外交流的时候,他们的年轻人或者他们的成年人又怎么通过我们走进我们的历史呢?我们现在中国存在的现象,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吧,蜂拥崇尚国外,比如说对英语的那种疯狂的的学习,然后又把汉语忽视了,不知道你怎么看这种现象,就这样。
王斑:我先说后面一个问题吧。学英语,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有的人认为学英语,是拜倒在他人的脚下,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这是荒谬的想法,施行真正的大同,一定要有一种语言,不管是世界语还是什么——过去世界语,流行了一段时间——当你把大同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做时,就有了世界语这样一个理想和实践,但是世界语是凭空造出来的,没有历史深度,没有文化积累支撑这个语言。学英语跟这不一样,我不认为学英语就是说等于拜倒在所谓霸权话语之下,因为英语本身它有存在的自我批评、自我克制、自我翻新的这个能力。要看谁去用,克服英语霸权的那一面,批评霸权的理论、话语,经常地从英语中迸发出来。反过来,很多外国人学中文,也有这种相似的看法,觉得学了中国话,你就变成中国人,变成中国人的奴隶了。所以很多人抵制孔子学院在国外的教汉语的活动。这也很荒谬。鲁迅曾说过,吃了牛肉不一定长成牛啊,对不对?外国语言是为我所用,应用英语可以增长你的自由度,支配一种语言,使你更有力,更给力。用英语来进行操作,用英语跟汉语进行对话,我觉得对研究文学好处很多,能够加强语言和其本身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解构能力,语言是人去操作的东西。你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受歧视的问题。中国人被人尊敬与日俱增,因为国力在改善嘛,中国人也有提升。歧视我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害怕、恐惧,因为他觉得中国崛起就像过去大国崛起一样,威胁别人安危,而我们中国政府的、某些组织的一些做法也给人家感觉咄咄逼人,反过来,我们如果跟别人平等地交往,不那么牛气,会减少别人的疑虑和恐惧。
学生:王老师,中国的经济现在发展很快,成为世界工厂。在国际上,我们中国的经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肯定,而美国人对我们的了解局限在清朝。清朝时的一些文化,比如裹脚,用现在中国人的观点来说应该是一种腐朽的文化。但是我想问一下王教授,我们中国要提升哪个方面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先进?
王斑: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很难回答。我们不能把裹小脚这种文化放在台面上津津乐道,不断地去渲染它,这样提升不了中国文化。但是我觉得像阿庆嫂代表的文化,是很值得去提升的。为什么呢?并不是阿庆嫂嘴巴厉害,也不是因为阿庆嫂这个人长得像中国非常朴实善良的乡镇妇女形象。她更多的是中国人怎样在自己的传统和意识上不断地再造传统,再造生活,再造自己的世界。不管在经济、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是如此。中国人应有自信的能力,像阿庆嫂这样的,我非常喜欢维新时代、戊戌变法时代仁人志士反省儒家几千年的传统,形成一种新的儒家大同的学说,这说明中国人能够古为今用,能把中国的古传统、看起来很衰弱的传统革新,推到前台,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也能够欣赏,这是完全能做到的。
学生:首先感谢王教授的讲演让我受益匪浅。在很多影视、书籍,包括王教授您刚刚讲述的事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外国人在关注中国文化的时候,并不是把中国文化放在一种对等的地位,他们骨子里还是对本国文化惟我独尊,非我族类,其形必诛的思想。所以我想问一下中国文化在对外宣传的过程中是不是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或强制性的措施?
王斑:我觉得文化的问题跟武力是不同的。我觉得可口可乐文化、星巴克文化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侵略。它们的后盾是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霸权造成的媒体话语权的强大。媒体的话语权对他在整个亚洲的霸权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用比较强硬的手段来推销自己的文化,这是不可取的。过去,大清王朝推行他的文化,但是他也吸收被他征服的汉文化,通过汉文化改造满族人的文化,他仍然用中国文化的礼仪的方法而不是暴力的方法,或少用暴力进行治理。全球互相沟通,你看我我看你,在这种密切的情况下,直接用武力或强制性推行自己的文化,别人不会接受,硬塞给别人,中国人千万不能做。你要让人家相信,一定要循循善诱,用礼仪的方法让人家慢慢相信你,人家不相信你也是可以的,不能非我族类其形必诛。我觉得儒家的教育方法是超越这种强制,比较放松、开放。
丁晓原:刚刚三位同学提问都提得很好,王老师的回答也非常到位。互动环节把今天的主题解析得更加到位。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要在世界上取得重要的地位,最后应该落实到文化上。在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作为中国来说,在走向世界的同时要注意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另外要在传承中创新,做到文化的自觉、自新、自强。今天的讲座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王斑,现为斯坦福大学William Haas中国研究讲座教授,东亚系主任、教授,兼任比较文学系教授。二〇〇二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系任客座教授。二〇〇九年聘为华东师范大学长江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