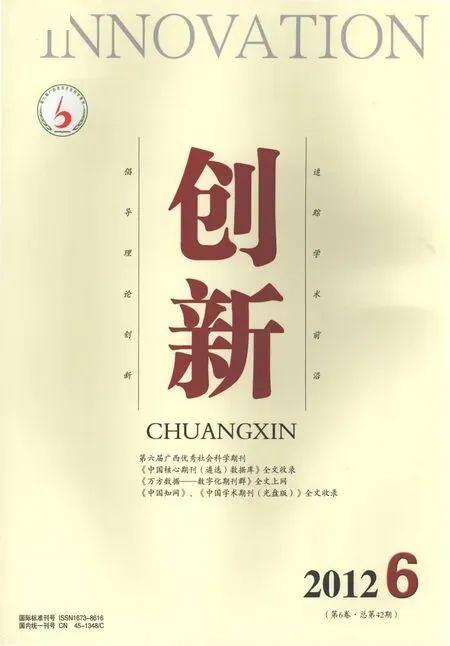追求个性自由独立 彰显崇高人性理想
——从普希金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探究其人生价值观
倪思然 常瀚文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在群星闪耀的俄罗斯文学史上,是一位享有崇高声誉的伟大作家。他不仅以“诗圣”的美誉闻名于世,还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别尔金小说集》等杰出的小说作品蜚声世界文坛。通过对普希金笔下一个个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独特艺术魅力的女性形象进行解读,可以洞悉这位艺术天才他广博而深邃的人生价值观。
毫无疑问,普希金对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倾注了复杂的情感和思想观念。在理解和分析这些情感、观念时,必须注重联系当时俄罗斯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及其特定的时代精神。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善恶观、爱情婚姻观和幸福观三方面,对普希金在创作中显示出的人生价值观进行辩证的剖析,试图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
普希金的小说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倾注了他本人的善恶理念,这里主要选取作家颇具代表意义的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形象,来对普希金的善恶观进行阐释。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普希金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塑造了光彩夺目的完美女性形象——达吉雅娜。作为普希金小说中较为少见的理想化女性形象,她身上显然承载了普希金本人心目中完美的人性标准。应该说,她头上那光辉灿烂的人性光环是富有强烈浪漫色彩的。这点从作者本人赐予达吉雅娜的称号——“我的可爱的理想”[1]前言中就可看出。
尽管达吉雅娜是个浪漫色彩浓厚的理想化形象,但她的美好情操与道德闪光点是普希金思想观念中至善人格经过外化的产物。她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始终坚守自己的独立个性,维持高尚的道德标规。婚后两年,面对无意中邂逅的奥涅金的求爱,她没有被心中旧日的激情搅乱理智,而是严肃而不无痛心地责问奥涅金:“为什么凭您的心灵和才气,竟会成为浅薄情感的奴隶?”[1]274在奥涅金轻薄浮躁行为的反衬下,达吉雅娜的人格彰显出极大的思想艺术魅力。她与《上尉的女儿》一书中矢志不渝追求爱情的玛丽亚一样,不但拥有淳朴善良的天性,更拥有在人生的重大关口能坚守自己独立人格的品质。显然,这种品质在普希金的思想道德体系中是占据崇高地位的,也是他在塑造这两个女性形象时着力突出的美好人格特质。
在普希金之前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女性形象多为男性的附庸和陪衬,而普希金“第一次将众多颇具个性的美丽女性带进了文坛”。[2]在塑造达吉雅娜等具有美丽人格的女性形象时,普希金倾注了他自身不拘流俗、追求人生自由、坚持独立人格的人生价值理念。
与对达吉雅娜人性美的描述迥然不同的,是作者对小说人物奥尔加的艺术展现。可以注意到,在整部小说中,作者“对于徒具美色的、浅薄的奥尔加一直采用一种贬抑的笔调进行叙述”。[3]然而,作者所展示出的奥尔加性格中潜在的消极因子,并不像小说《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贪婪的渔夫之妻那样单一和彻底。首先,在达吉雅娜人性光辉的映衬下,奥尔加贫瘠的精神世界及缺乏自主意识的性格显然与作者理想世界中的美好人性相去甚远。当然,这还不足以被视作严格意义上的人性之恶。其次,作者对舞会上奥尔加拒绝连斯基的邀请作了极尖锐的评价:“乳臭未干的她,轻浮的小丫头,竟会是水性杨花!她已经在玩弄狡猾的手段,她已经学会变心和背叛!”[1]172不仅如此,奥尔加的“变心”还成为了奥涅金和连斯基决斗的导火索,并间接导致了连斯基的死亡。从这里不难看出作者潜意识中存在男权思想。
透过普希金对奥尔加性格中恶因子的描写,读者可以洞悉普希金那颇为复杂的人生善恶观念。先看奥尔加的“变心”:一方面,作者对女性“水性杨花”的品性和轻佻浅薄的举止予以否定,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当时的俄国上流社会,泛滥着法国路易十四时代遗留的轻佻浮躁风气。而普希金人生价值取向的一大可贵之处在于摒弃流俗,坚持女性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作者在《彼得大帝的黑奴》一书中对情感不专一的D伯爵夫人的贬抑,亦有与对奥尔加的否定相似的突出意义。另一方面,作者通篇对奥涅金那具有同样性质的轻浮行为却并未予以指责。再看奥尔加带来的“祸害”:从表层看,是奥尔加导致了连斯基死于决斗;而从深层看,奥涅金邀请奥尔加跳舞的行为带有引诱与挑衅的性质——正是它激起了连斯基的愤怒与仇恨。作者在作品中对这一事实是有所反思的,具体体现在第六章后半部分对奥涅金负疚心理的细腻刻画上。可见,在奥尔加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普希金既流露出追求独立个性、排斥轻浮浅薄之世风的价值立场,又能够从自己的思想观念出发,对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根源予以恰当地剖析。此外,作者不经意间仍流露出男女有别的男权思想——这显然与当时俄国的具体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普希金怀着追求个性自由独立、反对轻浮浅薄世俗的敏感心灵,以深邃而缜密的创作思想塑造出一系列善恶分明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也因而获得了鲜活的艺术生命和较为广阔的解读、阐释的艺术空间。
二
普希金在小说创作中以自己饱含浪漫情调的创作,展现了一个个意蕴深长的爱情与婚姻的故事,其中,《叶甫盖尼·奥涅金》、《村姑小姐》、《上尉的女儿》等作品情节一波三折,尤为引人入胜,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作者的婚姻爱情观也在这几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上得到具体体现。
就故事中爱情与婚姻的关系而言,普希金的爱情婚姻题材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爱情与婚姻完美统一的,女主人公在经过一系列波折之后与心上人喜结连理。这类作品以《上尉的女儿》、《村姑小姐》为代表。第二类是爱情与婚姻相分离,即女性出于传统或现实的种种原因不得不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此类作品以《叶甫盖尼·奥涅金》、《杜布罗夫斯基》等为代表。第一类作品《上尉的女儿》中,在农民起义的时代背景下,女主人公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坚强不屈,坚持操守,为了替格里尼约夫澄清所受的怀疑,只身谒见女皇,最终使格里尼约夫得以释放。《村姑小姐》中的莉莎亦是充分调动自己的聪明才智,排除种种外界干扰才与心上人亚历克赛结合。反观第二类作品,无论是《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达吉雅娜还是《杜布罗夫斯基》中的玛丽亚·基里洛夫娜都出于父母的要求与现实的压力,违心地嫁给了自己不爱的男人,可见在普希金看来,以甜蜜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纵观普希金的小说作品并联系当时俄国的社会环境,不难看出,由于传统观念的深远影响,长辈的权力(尤其是父权)对女性的婚姻常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现实中的种种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女性的婚姻命运。总之,珠联璧合的“有情之姻”是颇为难得也弥足珍贵的——这正是普希金爱情婚姻观的一大要素。
普希金笔下的女子面对爱情婚姻问题时,并不是一味地顺从父权的摆布。她们中的玛丽亚·基里洛夫娜(《杜布罗夫斯基》)和娜塔莎(《彼得大帝的黑奴》)都曾为争取自由自主的婚姻对抗过专制父权。但最终,她们仍妥协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现实的巨大压力,屈从于父辈安排的婚姻命运。由于时代和文化环境的局限,她们面对人生重大关卡时,惟有退回到传统观念的藩篱之中。而一旦回到了传统,玛丽亚便拒绝了前来抢婚的杜布罗夫斯基:“已经晚了。我已经结婚了,我是威列伊斯基公爵的妻子。”[4]普希金的婚姻观念是现代与传统因素的统一体,他十分赞许女性为拯救爱情而抵抗父权、抵制“无爱之姻”的进步观念,但同时他也认为,美好的女性在婚后都应当无条件地忠于家庭、忠于丈夫,作者在达吉雅娜这一承载着美好人格理想的形象身上,亦寄托了同样的理念。达吉雅娜在婚后邂逅了奥涅金,心中的渴慕之情也曾重新点燃,但为了家庭,她不得不掐灭爱情的火种,回归传统的好妻子道路。她的行为显然代表了普希金心目中的理想婚姻状况。
可见在普希金看来,以爱情为根基的婚姻是弥足珍贵的;女性追求个性自由和纯真爱情的进步观念是值得肯定的;婚后的女性则应当忠于家庭,以贤妻良母的一切美好品行作为自己行动的标规。这大致就是我们从作者笔下女性形象解读出的爱情婚姻观内容。
三
除了善恶观、爱情婚姻观之外,普希金小说中在女性的形象塑造上,还展现出他本人对人生幸福的洞见。与前两者相比,作者关于人生幸福的观念、看法表现得较含蓄和隐晦。读者需要在熟悉文本的基础上反复咀嚼、涵泳和品悟,方能领略个中真意。
首先,普希金在自己崇尚的自由理念基础上,发展出其独到的幸福观:女性为了追求自己心中所向往的幸福,可以抛弃世俗观念中的美好事物。普希金认为,只要是追求自由心灵所向往的人生幸福,必要时付出昂贵的代价也毫不吝惜。最典型的例子是《驿站长》中冬尼娅的人生追求。尽管作者分别用同情和贬斥的笔法来描写驿站长维林(冬尼娅之父)和带走冬尼娅的骠骑兵明斯基,但毫无疑问,冬尼娅本人是向往与明斯基在一起时富足的生活和甜蜜的爱情的。为了追求自己真心向往的幸福生活,冬尼娅抛弃了家庭和父爱,投向了明斯基温暖的怀抱——这在普希金看来显然是无可厚非的。崇尚个性自由、向往豪放不羁的人生气魄的俄罗斯文化传统,哺育了普希金以热爱自由、崇尚独立个性为思想根基的幸福观。冬尼娅式女性做出的人生抉择,可看作作者的这种幸福观的折射。
其次,普希金小说《村姑小姐》、《上尉的女儿》中的戏剧性结尾,则为我们打开了解读他的幸福观的另一扇窗。《村姑小姐》中的莉莎一直扮作村姑与亚历克赛交往。小说结尾,当亚历克赛发现心上人莉莎恰恰正是父亲让其娶的那位小姐,于是胸中块垒顿消,他们两家之间的矛盾也终于完全冰释并顺利结为姻亲。《上尉的女儿》的结尾显然也具有类似的艺术效果。只身一人来到彼得堡的玛丽亚向一位端庄典雅的夫人倾诉自己拯救格利尼约夫的坚定决心,恰巧这位夫人正是当朝女皇陛下。于是女皇赦免了格利尼约夫,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带有如此戏剧性巧合的结局中,女主人公都在不经意间获得了孜孜以求的幸福,但倘若没有莉莎精心构想的“爱情游戏”以及玛丽亚忠贞不二的爱情信念作铺垫,幸福怎能翩然而至?普希金通过两位女主人公的幸福结局,不经意间流露了自己的幸福观,也向读者传递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再次,普希金认为,追求幸福的同时必须坚守自我的独立人格。面对奥涅金的求爱,达吉雅娜坚持自己的独立个性,抛开了曾经令自己梦寐以求的那份爱情,无悔地追求更高层次的人生幸福;身处战争环境中的玛丽亚不屈从于希瓦卜林的淫威,并小心珍藏着自己心中那份真爱,最终得到了希冀的幸福。文章笔触中普希金以闪耀着崇高人性光辉,向读者描述了女性们追求美好的人生幸福的过程。
通过普希金小说中一系列具有鲜活艺术生命的女性形象,读者可以感受到普希金追求个性自由独立、彰显崇高人性理想的思想观念,领悟出令人颇受启迪的人生哲理,并解读出作家那传统与现代因素交融并蓄的人生价值观。
[1][俄]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M].智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张铁夫,等.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26.
[3]周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从《叶甫盖尼·奥涅金》看普希金的女性观[J].江西社会科学,2004,(8).
[4][俄]普希金小说集[M].戴启篁,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246.
——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