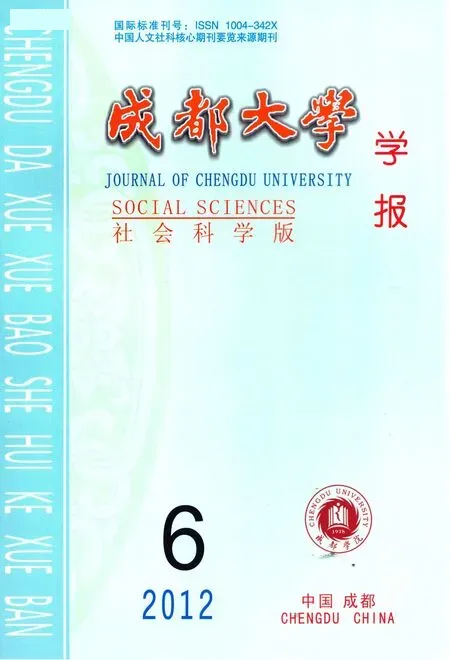从“神女”到“女神”
——试析郭沫若《女神》中女神形象的转型
粟 斌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在对于郭沫若诗集《女神》的意象进行研究的论文中,关于其中诸如凤凰、天狗、煤、太阳、大海以及其他个体性意象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对于作为中心意象的“女神”的关注明显逊色,所据往往是郭沫若在《女神之再生》中所引用歌德的诗句“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作为有关的说明,还有一些研究将女神意象与其他意象放在并列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作为中心意象的重要意义。今天,重新回顾九十年前由《女神》所带来的这一场新诗风暴,探索《女神》得到时代认可的原因,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诗集中作为中心意象的“女神”,在贯连起新旧文化之间的联系,并诱发时代性的诗情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 唤起新诗与古典文化精神的联系
文学意象的审美接受,首先是对其载体也即文学语言符号进行的认知活动,这也是一个从词语的表层线性结构中探索深层命意的充满着积极思维特征的心理活动过程。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作品的生命体现在意象层中,接受者在阅读中的审美对象,不仅仅是白纸上的黑字,也是“呈现在自己感觉中的、由作品三个语言学层次激活的意象。”[1]经由词语表象的刺激,语言描绘能够对词语的接受者唤起相应的想象,进而呼应起接受者的深层语言心理结构,使该词语与有关意象发生相互的作用。在“女神”一词中,“女”与“神”两字都具有单独表意功能,可以组合为“女神”,也可组合为“神女”。尽管各自表达的意思不同,但由于字面上的相似性,其词语表象所刺激和引导的功能仍然存在。
众所周知,在一个文明自成体系的社会中,语言表达总是以某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为基础。某一类型的形象总是带有该文化土壤中强烈的集体情绪记忆色彩。以“女神”(女性的神祇)为例,在汉文学关注过的所有女神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为充满了浪漫情色因子的巫山神女系列。尽管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女神数量众多,其形态、功能、精神类型各异,但在文学创作中,像女娲那样的原始古老的创造神,享有神仙世界崇高地位的西王母,以及在地方民间传说和各类祠祀中出现的务于传统生育事务或各类世事的女神,则很少被选择为诗人们浪漫情怀倾吐的对象。
自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以来,“神女”作为汉文学史上最为经典的感性形象之一,她(她们)不但有美好的形象,而且还有不同时代版本的浪漫的故事,以及伴随着诱发欣赏者联想和想象的情感因素。这种影响还波及到其他类似对象,像曹植的《洛神赋》写的是宓妃,却是“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而来。由于宋玉、曹植的艺术成就,高唐神女、洛神几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女神的代称。以至于类于母亲型神祇的西王母,尽管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许多诗人的关注视点却不在于西王母,而在于她座下的侍女。这个有趣的文学现象,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来说,是创作主体在尊重古老而崇高的人神关系时意图拉近彼此情感距离的一种方式,但另一方面也可谓是神女型故事在文学中的变异处理。
从郭沫若诗集《女神》推出的时代而言,用“女神”一词能呼应起新诗与古典文化精神趣味的联系,得到更多的关注及认可。这正如台湾学者叶维廉《秘响旁通》一文指出:“打开一本书,接触一篇文章,其他的书的另一些篇章,古代的、近代的、甚至异国的,都同时被打开,同时呈现在脑海里,在那里颤然欲语。”[2]接受主体已有的心理经验和情绪记忆,不但是理解、体验外来情感和审美信息的基础,也左右着人们的行动和思想。尽管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文化水平和心理基础上的差异,将不同程度地影响接受者根据自己的文化信息网络和情绪记忆所获得的审美体验。但阅读中的审美接受体验,仍然需要在接受主体的文化积累基础上,进行主客体的融合、再创造,才能得到新的审美体验。
二 郭沫若新诗中女神形象的时代转型
前文已指出“女神”一词意在唤起知识群体对于传统文学意象“神女”的记忆和情感体验,但是在《女神》诗集中,诗人笔下的女神形象并不唯传统是继,而是出现了明显的转型。这种转型首先表现为阅读者看到的是女神形象由神女型转向创造性的女神。
宋玉笔下的神女,是一位姣丽迷人,主动荐枕席的女子。尽管闻一多先生以为神女乃是在原始宗教和生殖崇拜意义上的高媒女神[3],但这并不影响后来的写作者,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无论是欣赏艳羡还是其他角度,几乎都把与神女有关的事归入艳情。这种创作倾向在汉魏六朝以来,又与当时的求仙方术结合,将神女作为男性作家编织艳遇类白日梦的故事原型。诗人们笔下的“巫山云雨”专指风流韵事。唐代杜甫极其精练地创造了“峡云”、“行云”、“神女雨”、“巫山雨”等等词,而李商隐则移植了这批词,……《花间集》的作者又把李义山的手法移植了这批词,成为以写爱情为主要内容的表现手法[4]。在这种创作思维的影响下,宫体诗中用“巫山女”、“洛川神”、“姮娥”、“弄玉”等指称美人,是十分常见的用法。至以陈寅恪言“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録华之世缘,流传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娼伎者。”[5]无论是作为理想寄托还是情欲之思的对象,在历代文人的创作中,神女型的女性神祇多是无所事事型,或清新孤远,或放荡游佚,都没有表现出对现实世事的明显关注。而郭沫若新诗中的女神形象明显超越了传统艺术视野所凝固的神女的层次,不但与创造大神(女娲)的使命结合起来,而且也不仅仅局限于女娲神话中运用五色石修缺补漏的内容,而是坚定地主张“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神。”“我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好同你新造的光明相结。”“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这些语言突显出女神形象在新时代的转型。
当然,这种转型在诗歌史上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比如苏轼有一首吟咏巫山神女的《神女庙》,其形象就迥异于过去文人诗中的神女形象。“大江从西来,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环拥,恢诡富神奸。深渊鼍鳖横,巨壑蛇龙顽。”在这猛兽横行的环境中,“上帝降瑶姬,来处荆巫间。”而且该女神造福人间建不世之功的方式也很令人叹服。“神仙岂在猛,玉座幽且闲。”其结果是“百神自奔走,杂沓来趋班。云兴灵怪聚,云散鬼神还。”[6]这一混乱世界的秩序整顿者的形象,使文学史上的神女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总的说来,这一形象的文学影响与传统视野所凝固的神女形象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与女神形象的转型密切相关的,是其精神状态上的重要转变。在传统文学中,神女系列形象的精神状态明显地集中于个体的情怨之思,集中于表现缠绵悱恻的情感,人神之间无可奈何的殊途以及由此而来的不绝如缕的精神痛苦。在苏轼的《神女庙》诗中,即使是作为一方生灵的掌控者,似乎也看不到她的情绪变化。反映在与写作主体的关系上,神女系列形象在传统的求偶型、艳遇型等人神关系中,始终是一个“他者”的形象。而在新诗中,女神的精神气质转而变为充满崇高的宇宙大爱的积极乐观型。她们与新诗中出现的诸如凤凰、天狗、太阳、大海等意象所反映的内在精神几乎处于同一位置,并且与写作主体实现了自我内化,成为了一体。
比如在《日出》、《浴海》、《太阳礼赞》、《新阳关三叠》、《金字塔》等诗中的太阳,就是一个充满了破坏力和再创造神力的意象。比较其中的诗句,如《浴海》中,“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我的血和海浪同潮,∕我的心和日火同烧,∕我有生以来的尘垢、粃糠∕早已被全盘洗掉!”“太阳的光威∕要把这全宇宙来熔化了!”“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社会的改造∕全赖吾曹!”很明显,抒情主体“我”和诗中的“太阳”实为一体。《天狗》中也是如此。“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大量强烈力度性动词的使用和急促的排比句式,又不断肯定着创作主体意欲抒发的内在情感。诗人使用的“太阳”、“天狗”等意象与抒情主体之间,不分彼此,并不存在着“他者”的关系。
回首再比较《女神之再生》与《凤凰涅槃》二诗,也可以很明显地认识这种意象之间的同一性。在它们的开篇,前者有共工与颛顼的争帝,传来不和谐的喧嚷之声;后者凤凰出现时的背景则是梧桐枯槁,醴泉消歇,大海浩茫,平原阴莽,冰天凛冽,都呈现出一个黯淡晦冥、秩序混乱的背景。传说中修炼五色石补天的女神(女娲),在汉民族文化中象征着吉祥、高贵、神圣的凤凰,都具有作为中心秩序的整顿者的身份。只是前者在新诗中是以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神祇的面貌出现,而后者在新诗中是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实现新世界(包括自己)的光明、和谐、欢唱。从这一意义上说,阅读者所接受到的“女神”意象和“凤凰”意象,其内在的精神气质不分彼此,都充满了对世界更新的强烈的意愿。从词语使用情况来看,在《女神之再生》中,女神的歌咏中“我”和“我们”共出现16次,在凤凰的歌唱中,则共出现49次。无论对于阅读接受者而言,还是作为吟咏的表达者而言,“我”、“我们”这类带有强烈集合性及呼唤意义的词语,在使用中不断淡化着写作主体与他所借助的表达对象之间在空间上、心理上和情感上的距离,与写作主体实际上合而为一。
杨胜宽先生曾就《女神》中出现的文学意象进行分析,指出“女神”作为诗人自我的化身,也作为人格的象征,被诗人赋予创造太阳、创造宇宙的能力,在天、地、人的三维结构中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他还结合郭沫若在解释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时的话,指出《女神》中“我”与天地万物平等如一,而且天地宇宙为“我”所用。女神创造太阳、凤凰“火便是我”的高唱、对地球“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的比况,都是其泛神论思想中“我即神”的艺术体现[7]。这一分析也充分说明学术界对女神这一中心意象与写作主体的关系的认识。
三 渗透着新文化思想的诗性必然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理解当年郭沫若在选择新世界的破坏者和创造者时,使用的是女神的形象,这固然如他在《女神之再生》的前言中引用歌德的诗句“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将女性视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过程中精神指引的崇高力量有关,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创造的神,诸如女娲、苏轼《神女庙》中的形象的继承,但更多的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过程中,对传统女神文学在题材和主题上的革新。这种革新究其原因,极具时代色彩。除了与“女神”相似的“神女”形象能够唤起汉文化群体共同的情感和文化记忆,满足新生的民国国民对于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忆与梦想以外,新的“女神”形象也开启了二十世纪20年代受新文化思想激励,渴求新时代精神的文化阶层,在中华文明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对于文明引导力量的文化想象。
这种想象,在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一方面表现为“对过去的新发现”,即赋予女神创造者的身份,并在诗中加以不断的强调。这一认识,即颠覆、重塑世界的力量向女性转移,是与时代的认识潮流相呼应的。民国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变化对于时代的心理冲击力尤为强烈。今天的研究者往往可以很轻易地在当时的各大报刊上发现男女共同发布的同居的声明、解除同居关系的声明,说明至少在社会的某一阶层或某一类群体中,已经越来越将女性视为平等的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对于女性的重新发现。那么,在文学领域,英雄神祇的形象也由原先更多地由男性的、外在的、力量性的,开始转化为女性的、社会内在的、精神性的形象。因此,带有明显古典人文色彩的女神形象的转型,在“五四”时期的话语方式中能够表现出非常的时代性号召力量。这印证了接受美学的观点,“新的文本为读者唤起熟知的早先文本的期待视野和规则,那样,这些早先的文本就被更动、修正、改变,或者甚至干脆重新创作了。”“这种文学—历史参照系的客观能力的理想范例是那些唤起读者期待视界的作品,这种期待视界仅仅是为了一步步地打破它自己……能够自身重新产生诗的效果。”[8]这也是在“五四”时期,用中国传统的神话资源贯连起这一时期的转型话语的重要原因。包括郭沫若在内的许多文学创作者有意识地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文学的现代化叙写。无论是郭沫若其后的系列历史剧创作,还是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朱湘等人对于古典诗风的继承和发展,都反映出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想象的倾向。
另一方面,这种想象还表现为在诗歌中“对西方文明的引入”。这种引入在女神形象的塑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女神的数量为例,在汉民族的文化记忆中,不论是神话传说中作为创造神的女娲,还是后来通过文学创作而流传的神女形象,在其流传的经世文本中,都是以个体的形象出现。(六朝以来的女性游仙形象时常群体出现,但从其神性、功能及地位上看,都不具备前二者那样的典型意义。)在郭沫若的《女神》中,女神出场之初,则由单一之数转为群体性形象。“女神各置乐器,徐徐自壁龛走下,徐徐向四方瞻望”。面对共工与颛顼争帝的乱局,是集体性的思索及行动。“姊妹们呀,我们该做什么?”出现三个女神分别说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其他全体随之共同呼应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从诗歌场境来看,这些女神彼此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种神性上的平等及数量上显而易见的变化,极易让人联想起以希腊神话为中心而雕塑的面貌相似,体态、服饰差异不大的众多女神群像。
另外,关于女神口中“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之语,也泄露出这种将西方文明因素与中国古典神话相结合的倾向。众所周知,葡萄从西而来,其引入是在西汉时期,酿造葡萄酒,以及以皮囊作酒器都不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代表性生活内容。将西方诗歌中常见的“葡萄酒”引入新诗,除了受20年代前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将中华文明的起源附于西方的文化影响以外[9],应该也有诗人郭沫若顺应阅读接受群体对于诗歌内容明显的心理取向和强烈的时代需求,有意识地将以“葡萄酒”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符号放入诗句中,在阅读者中激发起关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向西方文明靠拢的诗性想象。
也就是说,女神形象的转型,对于受单一审美惯例影响从而形成相对凝固之势的艺术视野并培植出比较固定的心理结构的接受主体来说,其“再生”的意义非常明显。
比如,在《女神》诗集中,对熟悉事物的陌生化体验,以及对新世纪新事物的吸收,成为这一创造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有关“科学”用语及西方现代文明意象频频出现,如“振动数”与“燃烧点”等用语[10],《天狗》、《光海》等诗中有关天文学、现代物理学、现代医学所反映出的现代科学意象,轮船、火车、摩托车等工业文明的意象,闪耀着开放眼光的世界性人名、地名意象[11],甚至有对工业港口“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笔立山头展望》)这样的深情吟咏,都反映出20年代的文艺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时代主题之一——“科学”紧紧呼应。用“女神”这一语言符号构筑的带有“群”的意义的中心意象,迥异于古典文学中的自然意象和人文社会意象,正是新文化思想渗透的诗性必然,反映出当时的诗歌创作者与接受群体之间对中国向现代文明国家快速转型的共同的热切渴望。
综上所述,郭沫若新诗集中女神这一“新”的形象,既如诗歌文本中所表现的那样,承载着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时代使命,也为熟知传统女性神祇经典形象的文化阶层建立起一个承载抒情记忆与浪漫梦想的诗歌通道,更通过女神“新”的转变,表达出受新文化思潮影响下的20年代的社会群体对于现代文明国家的企盼情绪。
:
[1]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73.
[2]温儒敏,李细尧.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68.
[3]闻一多.神话与诗·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A].闻一多全集(一)[M].北京:三联书店,1982.
[4]钟来因.《高唐赋》的源流与影响[J].文学评论,1985,(4).
[5]陈寅恪.读莺莺传[A].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111.
[6]苏轼.苏东坡全集·续集·第一卷[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7]杨胜宽.太阳 大海 女神——《女神》文学意象分析[J].郭沫若学刊.2007(1).
[8]尧斯.文学史向文学理论的挑战[A].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480.
[9]顾颉刚.古史辨[Z].北平:朴社印行.1926.
[10][日]横打理奈.《女神》中含有诗意的科学用语.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1).
[11]张建锋.郭沫若《女神》意象体现的文化精神[J].成都大学学报.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