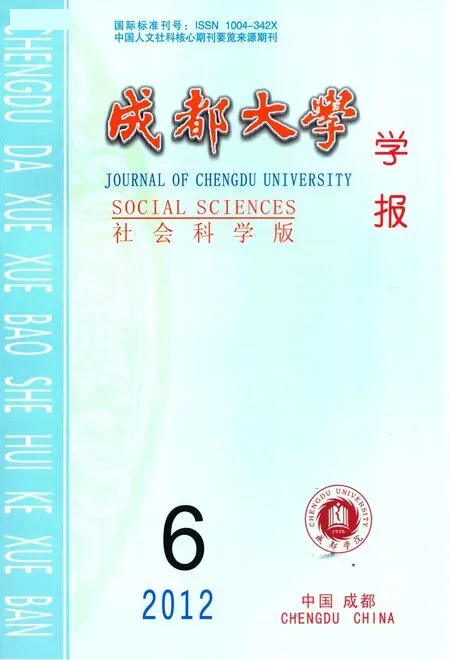汉兴一百年蜀地民众国家认同的发展和深化
王 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巴蜀文化在战国秦汉之际的转型,是“由一种作为独立王国形态和民族性质的文化,向作为秦汉统一帝国内的一种地域形态和以秦汉文化为符号的中华文化的亚文化的转化。”[1]当然,这个转化完成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以秦灭蜀的公元前316年起,至学界一般认为的公元前100年左右基本完成,即有二百余年之长。对蜀地民众的国家认同而言,在这段时期里,他们至少经历了从本土国家认同到异族国家认同,再到大一统国家认同三个阶段的递变。本文要讨论的是第三阶段,即蜀地民众对大一统国家认同的情况。
秦汉都是大一统国家,但还是有着很大不同的。简单地说,秦的大一统主要是政治上的大一统,而汉的大一统则已深入到精神层面。而大一统秦的存在只有短短十五年(公元前221~前207年),且在这十五年里天下汹汹,其治下民众,几乎是每个阶层,都疲于奔命。身为“罋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的陈涉,[2]281愁苦无聊之际在大泽乡登高一呼,天下却风起云从,秦始皇去世不到三年,大一统的秦帝国就土崩瓦解了。如此之短而又如此不得人心的大一统国家,不仅无法在国家认同上有所建树,甚至“大一统”国家存在之是否必要也成了令时人怀疑的问题。对此,汉文帝时的一件小事更使之清晰呈现。文帝六年,其弟淮南王刘长因反叛事败,流放蜀地,至雍而死。文帝十二年,民间有“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的歌谣为淮南王鸣不平,文帝得知后颇为不满,说“天下岂以我贪淮南地邪?”[3]2144可见,在时人观念中,哪怕高至皇帝,其与诸侯王在土地上还是各有所属的,“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当然,秦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秦灭后项羽以“霸王”而众建封国,以及汉初实权诸侯王的分封等,也都是这方面的证明。
正如王子今先生所指出的,伴随着“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巩固,以及汉武帝时代大规模版图扩张活动,促使汉文化共同体内聚力的显示,汉代人的国家意识才逐渐形成。[4]405显然,对大一统的国家认同也就是伴随着这种国家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不过,在汉代大一统国家外在与精神都没有成形时,蜀地民众对汉国家的政治认同却已开始发生。
一 汉兴之际蜀地民众的国家认同
蜀地自入秦以后,虽然随着秦移民的进入,秦制度和物质文明的引进推广,开始了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且在秦朝时代已显示出具有明显融合痕迹的文化面貌,但说到对大一统的国家认同,其实与关东地区并无二致。蜀地纳入秦的统治远远早于关东地区,而秦末之乱,也没有波及蜀地,但在秦亡之际,蜀地并没有表现出对秦的留恋,而是很快地几乎和平地转入对汉统治的认可和配合。①对此,汉元年刘邦由汉中入平关中时“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食”[5]30,汉二年(公元前205 年),以“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租税二岁”[5]33,以及同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5]38,都可看出。在常璩的记载中,蜀地民众对汉的支持,还不止于后勤供应,还有直接的兵员提供,如“收其精锐,以补伤疾”[6]141。
但是为什么初兴之汉,由关东而来,从无与蜀地民众相处的经验,却能够迅速获取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呢?其原因,除了秦政治对附合民心极度失败外,大约还有二点。
其一是刘邦政治声誉的传播和政治作为的得宜。刘邦初兴之时,在项梁军中,即以义行长者而知名,在选定由谁西行入关定秦的商议中,怀王诸老将以“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从而选择了刘邦。[5]16-17而刘邦入关中后,不杀子婴,且“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以及废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还以“仓粟多,不欲费民”为由拒绝秦民自发对其军士的献享,而这些不仅换取了关中民众的“安堵如故”,还令他们“大喜”、“益喜”。[5]23刘邦的这些政治行为,在项羽入关后“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的行径对比下,[7]315其政治声誉就会更加高涨而四处传播了。虽然没有直接材料表明蜀地民众受到了刘邦政治声誉的感染,但是《华阳国志》所载“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8]14,刘邦王巴蜀,范目主动“说帝”等行为无疑暗示出他对刘邦的作为早有耳闻,巴蜀同域,阆中人知道,蜀人也应当知道,可见刘邦的声誉是较早流播于巴蜀的了。刘邦为汉王后,由于要再定关中东向战楚的缘故,对巴蜀民是必须利用的,但其利用却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一体现在“抚而用之”,即“汉王引兵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9]2014“使”的前提是有“抚”有“谕”,所采取的是一种柔性政策而不是暴力威逼。另一体现在适可而止、及时回报。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当刘邦入定关中,军队给养可以由关中支持后,他就下令“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了。[5]33初兴的汉政权,对蜀民的这种态度,必定会换取蜀民的更大认同和支持。
其二是蜀地民众民族构成的影响。由于秦灭蜀后,不断往蜀地移民,蜀地民族构成主体发生变化,成为由开明氏蜀国遗留的本土蜀民与“秦之迁人”两部分组成的新蜀民。对本土蜀民而言,终秦一代他们也还没有完成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从考古文化上看,秦朝时期也不过是中原文化特征加强,蜀文化特征削弱的阶段。[10]223也就是说,在汉初兴之前,本土蜀民还较多地保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但在政治上却要接受异质的秦文化的统治,而秦在政治上的失败,导致秦并没有获得本土蜀民足够而持久的认同,这就使得秦在灭亡之际,本土蜀民呈现出冷漠的态度。而且如果我们注意到,本土蜀民的原开明氏王朝,其建立者本是来自楚地的荆人鳖(鄨)灵,开明九世仿中原建立礼乐制度时“乐曰荆。人尚赤”[6]122,而终结秦统治的刘邦也是楚人,其起事后是“帜皆赤”[5]10,因此当刘邦入汉中王巴蜀时,本土蜀民看见他飘展的红色旗帜,未必不会生起故国之念,从而在刘邦身上寄予复兴的念想,快速地转入对刘邦汉政权的支持。而“秦之迁人”,“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7]316,迁徙入蜀的人基本都是被迫的,还带有惩罚性质,所以才会有“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的现象[11]3277,因此蜀地大部分“秦之迁人”作为被秦“惩罚”的群体,对秦的认同在短期内是不会有多高的,在天下起而诛秦的形势下,他们即便不会有幸灾乐祸的报应欣喜,对于还懂得体恤百姓的刘邦汉政权却也更不会有所抵制。因此,可以说,在面对秦被汉取代的问题上,新蜀民的两大主体在历史情结之下达成了一致的态度。
明白这些因素,蜀地民众未遭秦末战乱而快速转向对汉政权的配合和支持,生发出对初兴之汉的认同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这种认同或许有着心理与意识方面的色彩,对汉家政治措施应激的政治认同才是更为根本的。这种暂时的政治认同能否转化为对汉的国家认同,就要看汉家后续统治者的表现了。
二 汉初蜀地民众国家认同的发展
汉代建立后,连续几代统治者都推行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并发展,蜀地也不例外,至景帝末也是“世平道治,民物阜康”[6]141的景象了,蜀地的生养之饶获得了更高实现。
不过,由于蜀地本无如中原般的文教的历史基础,汉廷初兴文官教育和选拔制度也未建立,所以景帝末来任蜀郡太守的文翁,“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采取了政府自筹资的方式,送学生到长安学习,又在蜀地开办学校,为学生免除徭役,学优者随带出巡,有的还授以郡县荣耀吏职,蜀地民众大为羡慕,数年之间,蜀地民众便“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蜀地“由是大化”[12]3625。
从这里看到的除了蜀地文教的兴起景象外,也呈现了正是在文翁的“诱进”之下,蜀地民众才感受到汉国家对民众的好处,才开始乐意进入国家统治机构服务。但事实却并不如此,向权力接近虽然对蜀地民众来说并不具有先天优势,汉国家却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蜀地人物的选拔与任用。
智能分析仪表端能产生的预警信号包括: 计算出试剂等消耗品余量值、余量不足、消耗品用完。例如硅表试剂还剩3 d的余量时,产生预警信号,给予用户充足的时间增补试剂。系统能给用户提供相应的处理参考方法。
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高帝诏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5]33,其中包括的“巴蜀材官”至少表明了汉廷平等对待巴蜀民众的一种态度,相信他们愿为国家所用。而且,若是注意到汉初大臣基本是开国功臣,且当时尚未建立文官选拔制度的背景,那么以士兵被抽调中央“为皇太子卫”的荣耀和个人命运改善机会显然是增大了很多的。对汉文帝的宠臣,被《史记》、《汉书》视为佞幸的蜀人邓通,“无伎能”,“以濯船为黄头郎”[13]3192,让司马相如得以知名于汉武帝的蜀人杨得意,是上林苑狗监,一以擅划船为水兵而进,一以擅调教狗进,而他们都还能接近皇帝,邓通更是宠幸无比,这至少表明汉廷愿意进用蜀人的态度,哪怕没有治国之才,也要也“低贱”技能拔擢他们。后来,司马相如得以赋进,开西南夷、上《封禅书》,一度进入参与到国家权力中枢中。文翁兴学,培养出一批具有职业官僚技能的人士后,他们或者“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或者“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或者“传教令,出入闺阁”,汉国家对蜀人完全是量才授用了。[12]3625-3627可见,汉国家在休养生息之余,对蜀人进入国家机构的上升通道也是完全打开的。
因此,在汉国家提供的这种“生息与上升”的通道中,蜀地民众获得了远比秦时更为令人逸乐振奋的生活,他们对汉的国家认同也必定会随之日益增强。但是若以此断定蜀地民众对汉国家认同的最终生成,则可能是比较草率的,因为他们的认同程度、认同层次尚没有经受过检验。而这个检验在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政治军事活动中才终于来临。
三 武帝时期蜀地民众国家认同的转变
蜀地之西、之南,一直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司马迁以蜀地为方位坐标,把他们统称为西南夷。西南夷,在秦代已经开始开发,但秦末大乱,到汉兴之时又与中原文明中断官方联系。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东越(《汉书》作闽越)攻南越,南越王求救汉廷,汉遣大行王恢等率汉军平定东越,事罢,王恢遣唐蒙出使南越。在南越番禺(今广州),唐蒙发现了来自蜀地的枸酱,回长安后,唐蒙建言武帝,开通由蜀郡直通番禺的道路,从而引出汉廷开发西南夷的长期活动。
汉武帝时期开发西南夷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唐蒙引起的,第二阶段是张骞引发的。不过本文的讨论背景只在第一阶段。虽然第一阶段开发西南夷是由唐蒙首先建言引发,并且由他亲自施行的,但司马相如在开发西南夷中的定策以及施行作用却在他之上。而司马相如在开发西南夷中两篇文章《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更是为我们考察当时蜀地民众的国家认同提供了重要材料。
由于《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所载开发西南夷事件、时间等的混淆,兹先参考熊伟业先生的研究成果,[14]并结合《史记》、《汉书》相关记载,列开发西南夷诸重要事件及时间于下,以为后文论述之便。
至武帝元光五年,汉廷开始把开发西南夷的计划付诸实施后,蜀地民众的休养生息就宣告结束了。由于蜀地处于汉西南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位置,整个活动的物质和人力支撑就基本落在蜀地民众身上了。
当蜀地民众得知这项活动任务之初,是积极配合的,毕竟在汉国家里,他们已经过了七十余年太平逸乐的日子,为国家做些事也是他们的愿望。所以唐蒙到蜀地后,虽然只“发巴蜀吏卒千人(巴蜀各五百人)”,但是地方却私自增发了后勤保障人员,“郡又擅为转粟运输”,“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15]3044-3045,显然,蜀地民众的热情为郡守的擅自行为提供了支持。但是,蜀地民众对这项活动的政治严肃性和艰巨性在思想认识上是完全不足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唐蒙以“军兴法”管理这项开发工程意味着什么,在作业中仍然保留了长期太平生活养成的散漫态度。所以,当唐蒙用军兴法“诛其渠帅”以保证作业纪律和工程进度时,便出现了“巴蜀民大惊恐”的现象,以至于惊动了远在长安的皇帝。[15]3044汉武帝派遣蜀人司马相如使蜀,进行安抚,司马相如因之发布了著名的《喻巴蜀檄》。②
对于前者,司马相如指出了三点。其一,汉国家是一个维护民众利益的国家。如其中所云“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是先担负起了养民职责的。其二,汉国家是威德强盛的国家,如其所云“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其三,汉国家是一个有责任主持正义的国家,所谓“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
对于后者,司马相如也指出了三点。其一,要尽人臣之道,急国家之急,不惜牺牲性命。他举现实例子说“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其二,在为国家立功的过程中,成就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最终达到“有剖符之封,析珪之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的境地。其三,应具有成忠君爱国、孝亲悌长的伦理操守。开发西南夷活动中逃亡、自相贼杀的民众是“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地方上应该“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从而培养出好的风气。
当然,本文告的重点是后者,即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汉国家的子民。司马相如所讲的道理,应该是被蜀地民众接受了的,因为唐蒙的开发工程得以继续,而且“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15]3046,蜀人在大惊恐之后,不仅继续为国家服役,服役人数也成倍增加了。这似乎暗示出,在司马相如的告喻之后,蜀地民众已颇为接受作为汉国家子民对国家所具有的义务了。
但是,行为上的接受不一定表示心理上的理解和认同。就在这数万人二年的辛苦劳作后,结果却是“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虽没有停工、造反,但无法理解这项活动和希望停止的心声还是不断地释放出来。以至于汉武帝派遣时为待诏博士的公孙弘入蜀考察,公孙弘回长安后可以“盛毁西南夷无所用”[16]2618,“盛毁”一词说明公孙弘虽极为夸大其辞,但蜀民中的劳怨之声也是不可谓小的。
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蜀西之夷“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15]3046,汉武帝犹豫未决而询问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确认了通蜀西夷的可行性和优势,于是汉武帝再次派遣司马相如使蜀,负责开通西夷。
司马相如此次入蜀的规格是比较高的,“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不仅是二千石钦差,还有三个驰四乘传车的副官,而“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这样盛大的迎接场面蜀民应该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他们不仅“以为宠”,而且曾经因为百般无奈才把女儿卓文君嫁给司马相如的卓王孙也“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15]3046-3047。作为蜀人的司马相如在蜀地得到的荣耀,给蜀地民众造成的心理震撼无疑是巨大的。而司马相如之所以得到如此荣耀,显然,这也是因为他得到了皇帝的赏识,而皇帝就是汉国家的代表。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实际上是用自己的事迹为蜀地民众树立了尽人臣之道、急国家之急,为国家立功从而成就自己的鲜活榜样。
司马相如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尽管通西夷是“因巴蜀吏币物”,人力、物力都由巴蜀提供支持,而且还是在唐蒙以数万人通南夷二岁和“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的劳苦背景和心理背景之下,司马相如还是很快“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马龙、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然后“还报天子,天子大说”。[15]3047
不过,尽管司马相如得到了蜀地吏民实际行动的支持,但是他们在支持之下仍然对开发西南夷的政策表示了不解。司马相如完成使命返回成都时,蜀地父老就向他表达了不解。对此,司马相如在其“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的《难蜀父老》中作了回答(其实这也是对汉武帝开边政策的辩护)[15]3048;③。
蜀父老对开发西南夷的不解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违背传统华夏蛮夷相处原则“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其二是开发活动本身得不偿失,“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
对于第一个疑问,司马相如巧妙抓住蜀地民众在疑问中以华夏自居的立场,聪明地暗示出蜀地曾经也是蛮夷之地,如果不赞成开发西南夷,那么巴蜀之地就会仍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的落后景象,从而先声夺人地确立开发西南夷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同时故弄玄虚地指出,民众不理解属于正常,因为开发西南夷是“非常之事”,而“非常”的特性是“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对于开发西南夷这样的非常之事,开始时民众是会感到害怕的,但成功后就能享受一片祥和了。
对于第二个疑问,他用夏禹治水的故事指出,要想获得安宁逸乐的生活是要先付出极大辛劳的,“当斯之勤,岂唯民哉。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胝无胈,肤不生毛。故休烈显乎无穷,声称浃乎于兹。”因此,为开发西南夷而付出辛劳也是必然的。
然后,司马相如指出贤明君主的目标,不是“委琐龌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时取说云尔”,而是“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贤明君主就要“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还要发扬《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精神,让“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衍溢”,“怀生之物”皆能“浸润于泽”。而当时的汉国家“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但是“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向而怨”,他们“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以至于“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因此,汉天子才大出兵,“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开发西南夷也是为了“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提福”。当时汉天子的急务就是“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汉天子确实承担起了这项使命,所做的正是这些伟大的事业,但这些事业的成功需要汉家子民的支持,民众的辛劳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因此当下的辛劳是值得的,一旦成功天子就要“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宣告一个盛世的来临。
最后,司马相如再次强调民众要保持思想上和国家的同步,如果还不理解,“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那就“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无比可悲了。
由此观之,《难蜀父老》实际上是在用国家理想来感召民众,希望民众在精神上理解并保持与国家步调的一致,把个体的生命同化到国家的生命之中,为国家大一统理想的最终实现贡献自己的才干、牺牲自己的利益。
如果说《喻巴蜀檄》是强调合格国家子民的要素,并诱以在为国家尽义务的过程中,利用国家提供的平台来实现个人和家族的成就,显然这是一种理论上必须做到的外在要求,那么《难蜀父老》就是利用宏大的国家理想来感染民众的精神,使之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从而实现大一统国家在精神上的同一。
道理讲了,效果如何呢?据他自己说,“于是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完全是受了教,立马就树立起大一统国家的观念了。当然,这是文学家夸张的笔调,观念的转变不会是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但也不可否认,从此之后,蜀地民众对汉国家确实也明显地向其大一统精神认同上转变了。
就普通民众来看,在汉武帝第二次开发西南夷中已能看见他们对汉国家的认同是远胜于前了。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反,汉因犍为发南夷兵征讨,但是南夷且兰君担心出师远征遭到旁国侵掠而杀犍为太守造反,“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17]2996,会南越破,又“引兵还,行诛头兰”,“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17]2996,“并杀筰侯,冄马龙皆震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犂郡,冄马龙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17]2997;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等[17]2997,这些活动对蜀地人力物力的调发都是远大于第一次的,但是并没有蜀地民众造反抱怨的记载留下,这显然表明蜀地民众在整体上对汉国家的认同已经更深一层,已经能够理解汉国家的开疆政策并牺牲自己的利益积极投身到其中了。
就蜀地士人而言,也有直接材料表明他们的精神是受到了司马相如感染的。成帝时牂牁郡夜郎王等“蛮夷”相攻击,牂牁太守建议兴兵平乱,汉廷“以道远不可击”,决定遣使“持节和解”,汉廷派的使者是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18]3844。但是和解失败,汉使者还受到侮辱,于是汉廷决定军事解决。这时汉廷又任命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主持平乱。陈立也是蜀人,曾在西南夷连然县、不韦县为令长,“蛮夷畏之”[18]3845,在为国家治理边疆上他是积极作为而颇有成效的。陈立到任后,也果然很快将动乱平息。在这件牂牁事务的处理上,和平调解与武力平定,汉廷派出的都是蜀地士人,可见蜀地士人在为汉国家留意西南边疆事务上是比较用心的,这种用心只能来自于对汉国家边疆开发政策的认同。而陈立显然又是这方面的杰出分子了。由连然县、不韦县的令长,到西羌边地的金城司马,再到牂牁太守,陈立以在边地建功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成就,这便是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与《难蜀父老》精神的生动实践。对此,作为纯文人的扬雄,在这点上也不例外。
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匈奴单于上书请求次年到长安朝拜天子,考虑到匈奴朝拜使团人员众多,国家接待与赏赐开支巨大,汉诸用事大臣皆认为是徒费国家财物而建议拒绝,哀帝同意。这时向来自得在著书立说中,不以官场上进为意的蜀人扬雄却上书谏止,深切讲述应该接受单于朝拜的道理。在上书中他盛赞汉武帝伐匈奴是“规恢万载之策”,不是“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而是有着“不一劳者不久佚,不蹔费者不永宁”考虑的正确决策,现在为了省却一笔接待赏赐开支而得罪单于重开边衅,汉家历代君王的苦心和国家曾经的付出就白费了[19]3813、3814。哀帝看到上书后,幡然醒悟,立即追回已经派出的拒绝使者。“不一劳者不久佚,不蹔费者不永宁”,这与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中谆谆教诲的“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在精神上是没有区别的。
结 语
汉代大一统是儒家文化对民众精神的大一统,实际上就是发展后的传统诸夏文化(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在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势推广下,成为汉国家意识形态,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20]3620,使之成为域内民众的“禄利之路”,为之提供稳定而持久的上升平台,从而激发域内民众的认同,获得长久的统治利益。武帝的开边政策,实际上也是以武功的形式,通过为武人提供“禄利之路”来推广文化的“禄利之路”,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推广并以之整合同化武功所及的地域文化,通过文化同一和核心文化的扩张来确保国家认同的同一,最终实现大一统国家从外到内的“大一统”。因此,说蜀地民众国家认同转变最为根本的原因,还当在于儒学在蜀地的推广和汉国家政治军事的强大,这与传统诸夏地区并无区别,只是蜀地较为后进而已。
司马相如是有着浓郁儒家精神的士人,他的作品“突出地表现出儒家思想的浓重痕迹”[21],即便他在仕途上并不热心,“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15]3053,但在为国家大事考虑上并不逊色。他临终特意写《封禅书》于武帝,建言仿古圣王封泰山、禅梁父、勒功中岳。司马迁在其传末特意写道“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先礼中岳,封于泰山,至梁父禅肃然”[15]3072,以此来看,说司马相如是以其作品“代天子立言”并不为过[22]。
《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实际上也是司马相如站在“天子”立场上积极推动蜀地(当然也包括整个汉国家域内)民众国家认同层次深化的努力,使之融入到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之中,上下同心,最终达到儒者所追求的国家境界。当然,正是在司马相如两次出使蜀地发布了这两篇“代天子立言”的文告后,我们看到了蜀地民众国家态度的新面貌,因之,将之视为蜀地民众国家认同深化的标志也是得宜的。
注:
①《汉书》卷16《高恵高后文功臣表》载平棘侯林挚“以客从起亢父,斩章邯所置蜀守”,亢父在今山东济宁南,可见对蜀地控制权的争夺,不在蜀地而在关东,战火未及蜀地。
② 全文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44-3046页,下文引用其中片段不再具标。
③《难蜀父老》全文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49-3053页,下文引用其中片段不再具标。
:
[1]段渝.论战国末秦汉之际巴蜀文化转型的机制〔J〕.中华文化论坛,2005,(3).
[2](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汉)班固.汉书·卷44·淮南衡山济北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王子今.“汉朝”的发生:国家观念的历史考察〔A〕.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汉)班固.汉书·卷 1·高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汉)司马迁.史记·卷 7·项羽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汉)司马迁.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11](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汉)班固.汉书·卷89·循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汉)司马迁.史记·卷125·佞幸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熊伟业.西汉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年代辨正〔J〕.贵州民族研究,2008,(3).
[15](汉)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6](汉)班固.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倪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汉)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8](汉)班固.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9](汉)班固.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0](汉)班固.汉书·卷88·儒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1]李凯.司马相如与儒学〔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22]程世和.代天子立言:司马相如文本的精神解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