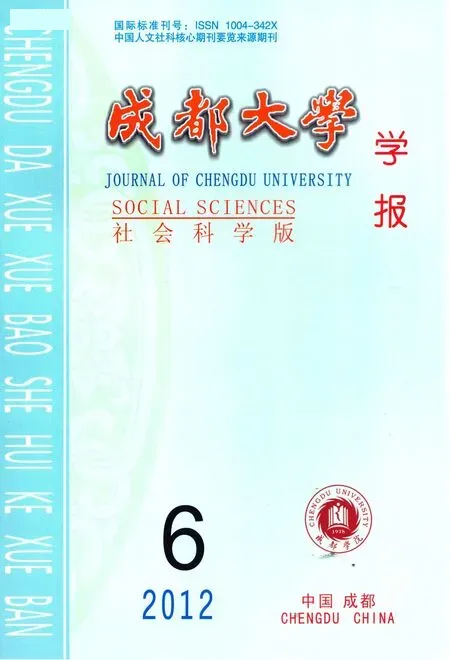乌托邦、非理性、历史与个人
——格非小说“人面桃花三部曲”主题分析
梁 仪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1)
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以《追忆乌攸先生》、《迷舟》等中短篇小说闻名,并以其叙事技巧和存在探索上的先锋姿态而被文学史归为“先锋派作家”的格非,近年陆续推出《人面桃花》(2004年)、《山河入梦》(2007年)及《春尽江南》(2011年)三部小说,构成长篇小说系列“人面桃花三部曲”。
与80年代先锋时期中短篇创作以形式技巧探索为主以及90年代转型时期初作长篇小说时的生涩迷惘不同,“人面桃花三部曲”无论其艺术技巧还是思想主题都较为成熟。尤其是作为对内容厚度和思想深度有更高要求的长篇三部曲而言,这三部作品中显现出来的对人性、历史、乌托邦、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大命题的思考,是我们探讨其得失成败的重要关注点。
三部曲讲述的三段故事,在时间上有承续关系(辛亥革命前后、五六十年代、当下),在空间上有重叠关系(地处江南邻近的普济、梅城和鹤浦,“花家舍”),在人物上有血缘关系(陆秀米、谭功达、谭端午),结构上有回环照应关系(秀米临终所见、谭功达听到的戏文、谭端午的创作等),这些都是三部曲作为整体的宏大建构。而更为重要的是三部小说在思想主题上的逻辑统一关系:乌托邦、非理性、历史时代与个人内心是一以贯之的主题,这些主题依托三个不同时代的不同故事反复地被探讨,不断被深化,形成三部曲的核心主题,值得探究。
一 乌托邦的精神追求与局限失败
“人面桃花三部曲”概括而言就是发生在不同又相关的三个时空对乌托邦精神追求与局限失败的故事。“乌托邦”是古今中外文学文化的重要母题,西方有柏拉图《理想国》、莫尔《乌托邦》等,中国有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及近代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等,不胜枚举。格非在三部曲中强烈地体现出对这一母题的高度关注和思考,不同于前述作品的是,格非的这种思考既不是一相情愿的求索,也不是具体而微的实践方案,而是表现出一个现代作家对古老绵延的“乌托邦”精神既追怀赞美又质疑反思,既孜孜以求又无奈叹息的复杂心态。
格非在三部曲中设置了一块“乌托邦”的试验田,即三部小说中都出现的地名“花家舍”。可惜这块负载了乌托邦梦想的土地却都走向了它的反面,露出或狰狞、或阴森、或淫邪的面目。《人面桃花》中王观澄满腔抱负,试图建设一个世外桃源,结果只成了争权夺利相互残杀的土匪窝,花家舍外表一派安逸祥和,其实暗藏权欲邪念。《山河入梦》中郭从年建设的“花家舍人民公社”物质丰美、井然有序,但是社员却大多畏畏缩缩、战战兢兢。其背后是社员相互监督的“匿名信”制度和神秘间谍机构对人们精神的禁锢和摧残,花家舍的空气中布满了阴森恐怖的窃听和偷窥。《春尽江南》的花家舍从理想主义者王元庆的手中败落给商人张有德,最终成了一个充满物欲肉欲的“销金窟”,成为现代消费社会人们放纵声色的众多消遣去处中的一个。对于精神沦落、物欲腾升的部分现代人而言,他们的桃花源就是这样一块“花家舍”。从花家舍在三部小说中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对桃花源的向往与曲解、追求与失败。要么成土匪窝,要么成集中营,要么成销金窟,都是桃花源的反面教材。
作家格非对于“花家舍”流露出痛惜又讽刺的态度,也是对盲目追求乌托邦的一种警醒。在这里格非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桃源梦的探索与失败过程,而是潜伏其中的人性悖论:苦心孤诣追求梦想的人们最后却在背离梦想的路上越走越远,或曲解或遗忘或丢弃了最原初的梦想。无论是秀米、谭功达,还是谭端午,乌托邦的精神追求都潜伏在他们心底或付诸行动,但最终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他们热切甚至不惜代价、不顾后果地追求心中的桃花源,而这样的完美追求注定在现实里频频碰壁。他们身上都兼具了理想的可贵与理想的失落,二者之间构成强烈的人性悲剧张力。格非对此既有痛惜怀恋的感伤,更多更深刻的是对理想追逐中人性变异的思考和警惕。
有意思的是,这种乌托邦精神是与知识分子精神融为一体的,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其后都是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和追寻路上的思索。其中包含着知识分子如何参与现实、如何安顿灵魂、如何在理想幻想与现实实际的落差里反思自身与反思人类等重大问题。对于从理想主义大行其道的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格非这一批作家,乌托邦色彩在他们作品里并不少见,如阎连科《受活》、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废都》、王安忆《乌托邦诗篇》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角度或深或浅地思考着乌托邦。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格非对此有一种强烈的偏好和执著,三部曲不仅仅是乌托邦的故事和思考,小说本身也带上了浓厚的乌托邦气质,即对完美追求的幻想和追求而不得的失落。这种幻想性和失落感可以说贯穿格非从早期《迷舟》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到现在的三部曲创作,构成格非小说的独特气质。只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正由于这种对乌托邦的偏好和执著,三部曲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理念先行、图解思想的痕迹,这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作家的幻想性和失落感特质也往往掩盖了更深刻的理性挖掘,尽管有一定的思考和警觉,但小说深度仍有所欠缺。
二 非理性:理解的同情与警惕
“人面桃花三部曲”中的乌托邦探索体现在人物身上便是富含激情的狂热的非理性特征。三部曲中的“非理性”最集中的是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疯癫来表现的。这种疯癫往往与小说人物的乌托邦追求有关,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认为激情本性是疯癫妄想的基础,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因此它既带着浓烈的激情和狂热,又因其不切实际幻想性异质性而与众人产生紧张关系。
这点在第一部《人面桃花》中最为明显,书中凡有乌托邦情结的人物无不带有疯癫气。在小说开篇就有详细记述父亲的发疯。母亲和仆人不知就里把父亲发疯归于“天底下的读书人,原本就是一群疯子”[1];而迂腐先生丁树则嘲讽父亲“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也不无道理,在这里格非借丁先生之口点出所谓桃源梦背后恐怕也只是官场功名的失意又不甘心。中国古代文人自来有隐逸之风,其中多少人不过是如父亲陆侃一般在桃源梦乡里安顿功名利禄之心罢了。此外,革命与情欲糅为一体的张季元、“活死人”王观澄、冷漠绝情的“校长”秀米等,他们身上都带着强烈的“非理性”特征,在众人眼里也无疑都是“疯子”。有意思的是作家格非对笔下的这些疯子,既寄以同情理解甚至流露出赞赏,又不时地通过疯子与实际的脱节与众人的紧张来揭示“非理性”因素的危害和悲剧。
再如《春尽江南》中王元庆并不是主要人物,但他却是全书精神的一个缩影和隐喻。他曾是80年代理想主义的热血诗人,90年代下海的成功商人,然而最后他却沦为了精神病人。他那些箴言式的信往往直切现代社会精神弊病“我们其实不是在生活。连一分钟也没有。我们是在忙于准备生活而提心吊胆。”[2]“如果一个人无法改变自己受奴役的事实,就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去美化它。”[3]这里,从80年代走过来的格非既有对曾经理想主义的追怀和反思,又有对商业经济控制下人性变异的担忧和警惕,作为疯子的王元庆承担了这两方面的寓意。相比前两者,格非对《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则寄予更多的喜爱和同情。与陆侃和王元庆的“真疯”不同,谭功达只是带有“呆气”,这一方面体现在他身为县长却不懂官场斗争,一心只想实践自己的桃源梦,最后落得百姓受灾官位不保;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女儿家”的态度,一如宝玉式的花痴,可惜后来错过与姚佩佩的爱情却落入了虎妞式的张金芳手中。即便是作者自己喜爱的人物也难免悲剧的结局,这便是格非对“非理性”理解的同情和警惕。
这种对“非理性”的暧昧态度其实表现出曾经历过70年代文革癫狂、80年代理想主义激情和90年代商业社会热潮的作家格非面对“非理性”的复杂心态:既一次次深陷“非理性”的热潮不能自拔,又在退潮后清醒与感伤交织。如格非自言:“作家的重要职责之一,在于描述那些尚处于暗中,未被理性的光线所照亮的事物,那些活跃的、易变的、甚至是脆弱的事物。”[4]对于“非理性”(如疯癫、偶然、卜卦、预感等)的表现一直潜伏在格非创作中,无论是早期短篇《迷舟》《褐色鸟群》《傻瓜的诗篇》还是长篇《敌人》《欲望的旗帜》,到了近几年的三部曲,可以看出格非对“非理性”因素的把握已经更为纯熟。这种非理性特征与小说虚构艺术结合构成了格非创作的一大特色,有论者将其归为“格非的神秘主义诗学”[5]也不无道理。
三 历史时代与个人内心
格非在“人面桃花三部曲”中表现出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有趣的是他把这种历史思考与个人内心融合在一起,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雕刻人物的细微心态,既写历史时代风云变幻中个人的心态命运,又写个人内心激荡中折射出来的历史时代影子。“动荡年代里挟在革命浪潮中的卑微的个人,尤其是个人被遮蔽的自我意识——不论它显得如何脆弱、如何转瞬即逝,但在我个人的记忆和想象中,却显的不容辩驳。”[6]从中可见,格非创作三部曲的初衷之一便是这种历史与个人的纠葛,历史中的个人、个人内心的历史形成三部曲的另一个核心主题。
《人面桃花》中秀米是个秋瑾式的女革命者,全书四章就是她从“闺女”到“女人”到“校长”再到“禁语人”的人生经历图谱。其中具体记述革命行动的只在“校长”这章,而且采用旁人的视角叙述,看到的只是秀米的侧影。重心放在革命前后,重点写初潮来临惊恐羞涩的少女“秀秀”、出嫁被劫伤心的女人“秀米”和革命失败后黯然沉默的“禁语人”。这样的秀米一改革命者的刻板印象,他们不是癫狂冷漠或热血正义的形象,而有脆弱纤细的神经,有情欲冲动的折磨,有失败后落寞感伤的隐退。这也是作家格非在“革命外衣”之下,试图引领读者深刻反思:知识分子们一直试图干预现实,可是他们孜孜以求的惊天动地的“革命乌托邦”为什么一碰到现实就破碎,要么软弱逃遁(陆侃),要么面目狰狞(小驴子、张季元),要么失败而归(秀米),何处才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所?
《山河入梦》同样表达了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思考。作为县长的谭功达却常常沉浸在“花痴”的神游里,在白小娴、姚佩佩的爱情里举棋不定,在桃花源的梦境里痴想不已。作为五六十年代国家初建时期的县长,历史赋予他的任务是建设,尽管他也参与其中,但他所梦想的不过是一个桃源胜境,这与历史任务是相冲突的,因此后来他在官场斗争中落败下台。小说中对历史时代与个人内心冲突的表现形成巨大的张力,尤其最后一章在“花家舍”的背景下,命运的感伤和错过的爱情交织把全书推向高潮,这便是历史风云里个体生命的悲欢,所以能够深深地打动人。
《春尽江南》不同于前两部有历史背景而主要记叙当下生活,它同样折射出时代与个人的隐秘关系。诗人谭端午和律师庞家玉构成小说中两种气质的分裂与交融:在物质时代,一方面文弱清高的诗人不断逃避现实企图回归性灵而不得,另一方面世俗功利的律师不断迎合现实却又陷入精神痛苦之中。他们及周围一批人都是时代的“失败者”,勾勒出时代风云里种种个人无奈。由此思考集中在当下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和心态、物质消费时代的人性扭曲两大方面。前者集中体现在谭端午身上,尽管他是小说主人公,但其言行思想无时无刻不处于“边缘状态”。工作上,他所在的地方志办公室只是个清闲部门;家庭生活中,经济收入高的妻子处于绝对领导地位;朋友圈子里,他犹犹豫豫,总爱说“也不妨试试”这样无关痛痒的话。在周围人忙着升官挣钱、纵欲狂欢时,他始终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沉浸在书本和音乐里。实际上,在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地位的失落是必然的,最可怕的是知识分子精神的失落,幸而格非始终为谭端午把持着这条底线,可想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格非对这个群体的喜爱和希冀吧。后者则是通过多人来表现:在现实里摸爬滚打的庞家玉却始终参不透现实的game,她瞧不起自己的丈夫而肉体和精神双重出轨;在官场上呼风唤雨的陈守仁最后死于不明不白的谋杀;徐吉士混迹烟花柳巷放纵肉体;年轻女人小史借自己的肉体来换取金钱和梦想等。这些在我们当今社会见惯不惊,可是被格非放置到小说里,不禁让人讶异:人们精神中那些梦想的激情和力量到哪儿去了?难道都化作了或肉体或金钱或权力的欲望?这些欲望又如何扭曲了人性?这些都是《春尽江南》带给我们的思考。只是这样的承载太多,太贴近现实真实而损伤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和想象力,这也是第三部的缺憾。
“人面桃花三部曲”在艺术技巧上也许还值得商榷,但其主题选择却体现了作家一定的眼光和勇气。一方面是三部曲勾勒出20世纪初至今的时代风貌,故事背后既是历史和现实的隐喻,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精神状况的探析。“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人已经生活得相对比较猥琐了,不太会想乌托邦的问题或者是做白日梦。其实文学的职能之一就是白日梦,在现实生活重压之下给我们提供一丝喘息。”[7]对乌托邦激情的呼唤同时又有对乌托邦背后非理性的警惕,这是时代精神建构的难题,也是三部曲努力探求的问题。小说不一定能给出答案,重要的是它给人以警醒。另一方面从格非小说的主题探索之路来看,自80年代先锋的存在思考到90年代转型的迷惘与阵痛,再到近年的三部曲,作家对这些主题始终在关注,且不断在成熟。从三部曲可以看到格非面对乌托邦和非理性的暧昧态度,这种暧昧态度也普遍代表了时代风云里的知识分子复杂心态。与别的作家不同,这种复杂心态下形成的幻想性和失落感一直贯穿格非小说,成为其独特气质。
综上所述,格非“人面桃花三部曲”既有宏大建构又着力表现人类精神细微的颤动,既在虚拟时空里驰骋想象又关涉当下生存实际。三部曲在乌托邦、非理性、历史时代与个人内心三个核心主题的统摄下叩问时代精神,可说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一次较为成功的主题探索。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物质至上的消费时代、娱乐至死的戏谑氛围里,像格非的三部曲这样比较纯粹的人性精神思索,也许可以给人们日渐麻木的精神一些刺激。正如格非在一次接受访谈时所说“文学叙事是对生命和存在的超越”,这种力图超越的精神力量对作家而言是十分宝贵的,对于当下日渐泛滥的文学创作也具有某种借鉴意义。
:
[1][6]格非.人面桃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8,1.
[2][3]格非.春尽江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72,175.
[4]转引自刘伟,格非的神秘主义诗学[J].文艺评论,2009(1):64.
[5]刘伟.格非的神秘主义诗学[J].文艺评论,2009(1):62-67.
[7]格非.《山河入梦》书封[A].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