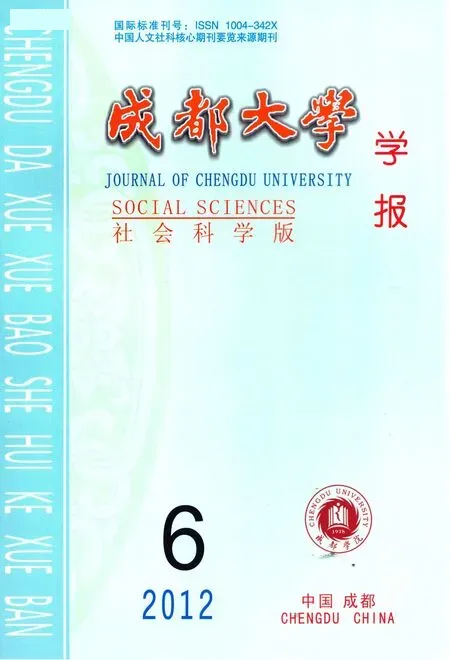宣泄与补偿:虹影小说的“弑父”书写及其心理机制
秦香丽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3)
叶舒宪先生在《文学与治疗》一书中将文学的治疗分两种:治疗他人和治疗自己。治疗自己,即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将苦闷情绪在作品中宣泄出来,克服自我苦闷和心灵的错乱,达到精神上的健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鲁斯特才说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厨川白村才认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川端康成才将文学视为“拯救人生的大道”。“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尼采的这句话道出了无数作家走向写作的不二法则,那就是通过创作来缓解、消除自己的精神症结。
“宣泄与补偿”是文学治疗最基本也最常用的功能,虹影的创作也印证了这一点。对她而言,内在的心灵创伤(这里的创伤绝非一个,私生女身世、18岁时与历史老师的不伦之恋,第一次的婚姻等均在其中,但究其根源则是“私生女”的身世。因此,本文的创伤特指“私生女”的身世创伤)是激起创作冲动的基本原因,而写作则是医治创伤的表意符号系统。作为一个“私生女”,她饱受边缘身份之苦,以“原罪”之身应对这个世界,这使得她对自己的“父亲”心生怨恨,拒绝承认他的存在。此种隐秘的心理体验体现在小说中就是“弑父”,藉此宣泄自己的压抑情绪;但是,“缺父”也使她产生了强烈的补偿愿望,为此她迫切地需要父亲或者父亲的替代者来纾解自己的精神苦闷;历经几段不彻底的“爱情”之后,在“寻父”与“弑父”的矛盾中挣扎的虹影终于认识到必须回到自身,审视自己才能真正获救。
一
熟稔文学创作的人大概不会否认此种观点: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乃作家的宣泄之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证明文学创作的纾解苦闷与压抑的功能,他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旨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正是借助文学创作这种特殊的宣泄渠道,作家才得以保持心态平衡和身体健康。
自西方的“原罪说”诞生以来,很多哲学家如叔本华将人的灾难追溯到“原罪”。“人之大孽,在其降生”,虹影一直强调这一点,但显而易见,一开始这个“罪的源头”的特指对象是父亲(当然,也指向母亲等人,就其本质而言,还是父亲),而不是自己。在《饥饿的女儿》中,“饥饿”有三重意蕴:食饥饿、性饥饿、精神饥饿。这三种饥饿中,笔者以为最重要的是“精神饥饿”[1]。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伦理国家,“私生女”的身份烙印注定虹影无法得到生父的爱,即便他是那么含辛茹苦地爱着她,也终为世情所挟持;养父对她的爱尽管也不乏伦理基质,但始终未能走进她的心……而哥哥姐姐、同学、社会上的人则以集体共谋的方式将她放逐,使她饱受“边缘人”的切肤之痛。《饥饿的女儿》中,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
“我无法忍受委屈,我总没能力反抗;退让,反使我情绪反应更强烈:我会很长时间不说话,一个人面对着墙壁,或是躲到一个什么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想象我已经被每个人抛弃。我的自怨自艾会变成愤怒,刺刺冒火,心里转着各种各样报复的计划,放火的打算,各种各样无所顾忌的伤害仇人、结束自己的计划。总之,让亲属悲痛欲绝悔恨终生,我却不给他们任何补救赎罪的机会。”[2]
由此可见,虹影心中的怨愤之情已有火山爆发之势。可以这样说,释放缺乏父爱的痛苦,既是主观情旨的使然,又是她写作的最直接的目的和动因。事实上,小说叙事和她的心理构成了一个系统:“弑父心理——作品表达——精神疗伤”,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心理宣泄的自足系统。
虹影小说有关“父”的宣泄叙事虽形态各异,但基本模式却有章可循,大致呈现这样的叙事流程:主人公(以女主人公为主)身陷“无父”的囹圄——主人公为了摆脱困境开始寻父并遭遇一段恋情——由于种种原因,爱情破灭,主人公“自食其果”,开始反省爱情,对“父亲”的认知也随着加深——主人公审视自己的隐秘心理,自省与忏悔,重新承认自己的父亲。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心理原型”叙事,换句话说,在虹影这里,写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写作,她通过写作来宣泄自己的“无父”怨愤。
“弑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否认父亲的存在,将人物处理为“孤儿”。虹影小说中一个重要的人物谱系便是“孤儿”,小六(《孤儿小六》)、少年圆号手小罗和玉子(《绿袖子》)、筱月桂和余其扬(《上海王》)、于堇(《上海之死》)、兰胡儿和加里(《上海魔术师》)等人无不是孤儿或半孤儿。即便主人公有着如常人般的家庭,虹影也刻意强调他们形同孤儿,甚至干脆宣称这是一个“无父”的世界:
“三个父亲,都负了我:生父为我付出沉重代价,却只给我带来羞辱;养父忍下耻辱,细心照料我长大,但从未亲近过我的心;历史老师,我情人般的父亲,只顾自己离去,把我当作一桩应该忘掉的艳遇。”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父亲。”[3]
由此可见,在虹影这里,“父—女”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对位空缺”。她用人物晦暗不明的身份及其艰难的生存际遇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父亲”。但虹影又意识到她不可能否认生理学意义上的父亲,她也没有选择父亲的权力:“你能对自己的父亲有选择吗?包括他的习性长相爱好,绝对不能。退一万步讲,只要他不弃你而去,他就是一个杀人刽子手,他还是你的父亲。”[4]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弑父”几乎不太可能,合理而又安全的方式必须予以重视。这就涉及到“弑父”的第二种方式,“残父”形象的刻画。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虹影作品中几乎没有正常的父亲形象,要么身体残缺、要么父性残疾:《饥饿的女儿》中养父双目失明,不得不由母亲承担整个家庭的责任(这其实是以“母强父弱”的转喻显示父亲的被阉割境遇)。大姐的生父是个流氓头子,在外花天酒地,打跑老婆女儿。被捕后,经他招供的人全被抓获,他才得以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孔雀的叫喊》中,柳璀的父亲具有严重的人格缺陷,他蓄意冤枉玉通禅师和妓女红莲,诬陷他们为通奸犯,用两个冤魂谋取平步青云;在柳璀母亲难产,母女只能保存一个的两难选择时刻,他却有违常理,毫不顾惜柳璀母亲哀求的目光,断然选择了要孩子。《鸽子广场》中的父亲不但没有对为了救他而委身他人的妻子表示丝毫的感激与愧疚,反而还不断地打骂她。《康乃馨俱乐部》中的父亲竟然强奸自己的亲生女儿,还恬不知耻地说“我养女儿就是为了我喜欢,我养儿子就是为你妈高兴”,完全丧失了父性……正是借助种种不称职的父亲形象,虹影才达到了精神弑父的目的。
从前面所总结的叙事流程可以看出,“男人”的出场实际上是一场预谋:通过爱情来“杀死”父亲。无论对虹影还是对其笔下的女性而言,男人不过是“父亲的替代者”。他们多以老师、长者、引路人与保护者的身份出现,给女主人公父亲般的温暖,不管这种温暖是否持久可靠。换言之,爱情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父亲,弥补女主人公的“缺父”遗憾。虹影坦言自己的“缺父情结”,她说:“我以后与男人的关系,全是建立在寻找一个父亲的基础上,包括我的婚姻”,“我非常尊敬我的养父,但因为我是私生女,他没有给我一个完整的父爱。生父也是。他们都没有给我一个完整的父亲形象。所以,会有‘历史老师’的出现,会有我和前夫的结合。”[5]我们知道这些男人不管如何努力都是不能替代父亲的位置的,他们的“被弑”也就在所难免。最典型的如《好儿女花》中,六妹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一生的男人,到头来却发现这是一场幻梦,不由得心生怨恨:
“……在我最后一次发现他与别的女人,比以前走得更近,仍在忽悠我时,我想对他吼叫,把积压在心中的愤怒喊出来,我要告诉他,他这个父亲是如何失去了尊严,如何亲手把他这棵大树,从我的土地上连根拔起,他有多残忍、冷酷,我是多么恨他,我今生今世都不要原谅他!”[6]
由此可见,虹影小说中的弑父书写很大程度上脱胎于她的现实境遇。正是基于这种现实的苦闷,在拒认父亲的存在之余,她设置了一系列的“弑父”场景。最典型的是《康乃馨俱乐部》,一群复仇女神组成俱乐部专门阉割男性生殖器。《好儿女花》中,几个姐姐剁掉小唐的小拇指也极具隐喻性,同样意味着对男性的阉割。根据弗洛伊德的“性欲说”,女性将曾经艳羡的“生殖器”割去以后,阳物崇拜自然也就消失了,也即意味着对男性特别是父亲的崇拜与依靠消失了。
“文学是人类独有的符号创造的世界,它作为文化动物——人的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园,对于调节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与张力,消解内心生活的障碍,维持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培育和滋养健全完满的人性,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7]弗洛伊德称作家为“神经官能”者,他们和常人一样,也有种种不得不排遣的压抑,只是他们能够从内在的情感状态出发经由创作活动的中介,实现了以“文学对抗精神疾患,排遣、释放”被压抑的苦闷,达到了以文学治疗心灵、走向健康的效果。而虹影正是通过“弑父”书写,发泄掉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隐秘愿望,才不走向死亡的幽谷。
二
写作在宣泄的同时,也具有补偿作用。弗洛伊德的“作家与白日梦”、“作品是改装的梦”、“文学是性欲的升华”等文艺思想则是其体现。在他看来,作品无非是作家们经过乔装改扮、经过“投射”和“文饰”过滤掩盖的“未得满足的”“欲望”的陈列。作为一群文学患者,作家需要通过文学创作来维持他们的精神平衡。如同美学家阿恩海姆在《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中指出的:“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疗救人(包括本人)的实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艺术本身的要求,而是源于病人的要求,源于困境之中人的需要。”[8]在《饥饿的女儿》中,虹影处于怎样的精神状态呢?
“母亲从未在我的脸上亲吻,父亲也没有,家里姐姐哥哥也没有这种举动。如果我在梦中被人亲吻,我总会惊叫起来,我一定是太渴望这种身体语言的安抚了。每次我被人欺辱,如果有人把我搂在怀里,哪怕轻轻拍拍我的背抚摸我的头,我就会忘却屈辱,但我的亲人从未这样对待过我。这里的居民,除了在床上,不会有抚摸、亲吻、拥抱之类的事。没有皮肤的接触,他们好像无所谓,而我就不行。我只能暗暗回忆在梦中被人亲吻的滋味。”[9]
……
“他就是那样的男人!我在回家的路上把他恨死,决定今后再也不理他了。但在晚上躺上床时,我禁不住又想着他,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逃跑。是我不对。我抚摸自己的脸,想象是他的手,顺着嘴唇、脖颈朝下滑,我的手探入内衣触到自己的乳房,触电般闪开,但又被吸了回去,继续朝身体下探进,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传遍全身,我闭上了眼睛。”[10]
……
此时此刻的虹影,基本上处于一种“病态”,如果找不到精神的出口,后果难以设想。她既是患者也是医生,拯救她的只能是自己。在《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中至少呈现了两种拯救方式:爱情和写作(《好儿女花》中还提到六妹曾经求助于心理咨询,但这并不占主要方式,所以本文忽略不计)。在这里,我们重点考察的是写作对虹影的精神补偿作用。
“文艺家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失去家庭的幸福时,这种缺失叫他们痛苦,但同时也激发着他们的创作冲动。这种创作冲动往往促使他们通过文艺创作冲动去努力换回一个逝去的世界,或重建一个新世界。也就是说,文艺家的缺失性体验成为他们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11]“缺失性体验与创作动因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缺失带给人痛苦,但也唤起他们力图重新得到缺失对象的顽强意志。”[12]“私生女”所经历的痛苦、失落、尴尬、挣扎等童年的缺失性体验,给虹影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但她同时又意识到,她必须拥有一个父亲。尽管,她自始至终没有写出一个完整的父亲形象,但她一直渴望能找到他:
“我想我是天生的女权主义者,我从小就在寻找父亲,我特别需要父亲,我的生命里面不能没有父亲,但是实际上在现实世界里,我没有得到父亲的爱。包括我自己,比如说找男人也是找父亲那样的人。我觉得这就完结了我的一个情结。但也是我的一个失败,我不可能找一个父亲,在我童年的时候命运就注定了,我不可能有父亲。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和写作过程当中,我想找到这个人……”[13]
创作是一种“替代的满足”,它成为心灵上需求的、不能满足的一种意志“转移”。对于虹影来说,她一直强调可以没有婚姻的爱,并称爱对她是至关紧要的,她要的就是这么一丁点东西。实际上,她需要通过爱情来转移与弥补自己“父爱”的匮乏。一方面,虹影在小说中设置一种追寻结构,在时空的跨越中凸显人物的身份悲剧和漂泊心态;另一方面,虹影一再强调性爱的和谐,写出性的奇妙,以狂欢叙事的手法在释放压抑的同时想象性地补偿自己匮乏爱的灵魂。
“追寻结构”是在时空的腾挪中寻找身份,也即寻找自己的父亲。虹影写作一个的最大母题是“创伤”,它有两个子题:出逃和性爱。出逃是为了寻找爱,这种心理动机虽说可以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援引证据,但它更多地得益于虹影的生命体验。在《饥饿的女儿》、《阿难》、《绿袖子》等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家庭到社会,还是从中国到外国,故事总依附在“追寻结构”中。寻找父亲,邂逅男人,弑杀男人或父亲,再次寻找,这种无穷无尽的寻找,使得人物永远呈现出一种“在路上”的漂泊心态。显而易见,此种寻找绝大多数以失败而告终,但毕竟在这个过程中,虹影找到了一系列父亲的替代者,体会过父亲之爱。
同样的,不管是基于书写策略的考虑,还是内心真诚表达的需要,我们都能发掘出“性爱叙事”与补偿心理的隐秘关系。赵毅横在《唯一者虹影与她的神》中说“虹影描写性的焦烈渴望,爱的沉醉升华,中国作家几乎无出其右”,并称《K》乃“性爱主题之登峰造极”。林一直处于性的压抑之中,无法纾解内心的孤独感。朱利安的出现,让她找到了一个摆脱庸常压抑生活的突破口,在她的引导下,两个人的性爱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文中大量直白的性场面的描写,不过是女性渴望爱、实现自我的直接表露。正是在性描写的狂欢化叙事中,虹影完成了情感表达的本能宣泄与补偿。她的书写证明的是女性也可以爱,可以在一次次的创伤之后,仍然拥有爱的能力,只有抓住爱,才能获得拯救。在《阿难》中,“我”的丈夫艳情不断,使“我”深受精神折磨,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去爱。小说如此写道:
亲爱的苏菲霏,我活过来了,在男人把我扔掉以后,你看我还可以爱人,不在乎他爱不爱我……[14]
正是大不断寻找爱的过程中,她们才拥有一种替代性的满足。赵毅横曾用“女性白日梦”来形容虹影的小说,确实如此,虽然她知道自己不可能真正拥有父爱,但她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写出爱的极致,从而获得一种象征性的满足。
三
虹影小说关于“父”的叙事基本上遵循这样一个模式:寻父——弑父——认父。而与之相应的创作心理却远非那么简单,并不能将“宣泄”与“补偿”视为某个阶段的对应物。也不能说,通过这样的写作,艺术治疗的目的就完全达到了。不过,总体而言,到了《好儿女花》时,虹影基本上抽离了对“父亲”的仇恨,写作心理发生了很大转变。
在前期,虹影的写作是心灵的大活跃、大解放,是情感的涌现,是想象力的活跃。它强调情感的一泻千里、激情澎湃、心力张扬、癫狂恣肆、震撼淋漓。它必须伴随着音乐的喧嚣、“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将心中的怨愤、不平之气喷射出来,将痛苦倾力释放……总之,她的写作一味尊崇“感情的本能宣泄”,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尽管“私生女”是她一生的心理创伤,始终贯穿于写作的各个阶段,但在写作治疗的前期,她基本上将矛头指向父亲,并未审视自己。她用一种叛逆的反抗精神来对抗整个世界,她不仅恨自己的父亲,也恨自己的母亲。她离家出走,选择流浪和写诗,孤注一掷。“疯狂约会,疯狂写作,疯狂做爱”,唯有“疯狂”、“惊世骇俗”才能概括该时期的写作心理。
虹影一再声称:“《饥饿的女儿》只是我重要的作品,但不是最好的作品,它是一把可变幻的钥匙,掌握得好,可打开我其他的作品。”[15]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她所有关于“父亲”的叙事也必须回到这里来。这个追寻身份的悲剧故事是虹影小说中的父亲叙事的底本,按照此底本演绎而成的其他小说都弥漫着一种怨愤情绪;到了《好儿女花》这里,虹影的“父亲叙事”有了较大转变。尽管我们仍然可以窥到一个压抑灵魂的释放欲望,但总体而言,狂飙式的宣泄不见了,其叙述也呈现出隐忍的风格。她第一次将苦难的根源指向自己,剖析自己的“缺父情结”,并对“既往之我”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作为自我治疗的写作,是否实现它的初衷,能否让作家走出精神的困境,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的写作发生了什么变化。众所周知,成功的心理治疗,必然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过程。治疗师所扮演的不过是一个引导者的角色,他诱导患者倾诉自己的故事,重组自己的故事。我们会注意到故事的底本基本未变,变的只是讲述的角度和看待故事的方式。但恰恰因为这“角度”的转换,患者才有了某种重生的感觉。源于文学治疗的特殊性,特别是治疗者和被治疗者的合一性,注定了写作既是一个涅槃重生的过程,也是一个反省自我的过程,只有完成这个过程,治疗才算完成。
以续篇面目出现的《好儿女花》,主旨就是“回家”,其隐现的前提就是回到“女儿”的位置,重新审视既往的一切,与“父亲”和解。笔者将该部作品视为重建记忆、重建自我的努力,是“饥饿的女儿”归家的一次尝试。从弥补缺失到承认缺失,从“寻父”到“弑父”最终到“认父”,虹影借助小说完成了自己的归家之旅。尽管,小说的主线是母亲的故事,但里面关于“父”的叙事仍占了相当比例。仍然是那个带给她生命的生父,其形象却不再苍白猥琐,一再强调他对女儿的想爱又不能爱的孤苦与无奈。正是基于这样的写作心态,虹影与生父和解了:
“生父与我在梦里和解了,他像一个严父那样打我,以此来处罚我对他对母亲做的所有不是。生前我从未叫过他,我恨他。可是在梦里,在我陷于绝望之中,我走向他的怀抱。”[16]
对“父亲缺失”的认知与对“爱情”的认知原本是一对双生儿。虹影是抱着“寻找父亲”的心态去寻找“男朋友”、“丈夫”的。《饥饿的女儿》中的六六在得不到父爱,甚至得不到任何来自亲人的关爱时,开始寻找一种“叛逆的快意”,她总想“把自己交给一个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当作一件礼物拱手献出”。而在《好儿女花》中,在写到六妹和前夫的爱情时,虹影的文字客观冷静,不带有任何怨恨的笔调,而是将笔锋指向了自己的“原罪”——私生女。它抛却了《饥饿的女儿》中的那种“这个世界本来没有父亲”的“弑父”心态,并正确认识到“亲情之爱”与“爱情之爱”的区别,“只想找个爱人,而不是一个父亲”,以一个正常女人的心态开始了新的婚姻,并有了自己的女儿。
就连对背叛自己的“丈夫”与小姐姐,虹影也有了比较冷静的态度。“丈夫”和“小姐姐”,都是她至亲的人,对她的打击可想而知。但在处理这一情节时,虹影摈弃了过去那样的“怨毒”情绪,选择了理性的节制,既同情小姐姐将她视为受害者,又怕小姐姐报复“小唐”,处处为他着想。更难能可贵的是,虹影将这场悲剧归咎于自己:
“我、小姐姐和他,只是我们三人遇在一起,悲剧就发生了,我们在不该遇见的地方时间遇见了。要说有罪,那就是我,我是罪的源头。”[17]
此时此刻的虹影,带有深刻的自省与自审,对自我的拷问已经超出了此前“忏悔”的意味,走出了“缺父”记忆的沉疴,用最真实的自我赢得了对自己的尊重,达到了自我疗治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在《好儿女花》中,虹影的小说第一次出现了家人团聚、和睦融融的场景:兄弟姐妹亲密无间,他们相约做一道父母生前做过的菜,像正常的家人一样团聚在一起吃着晚饭。这一场景告诉我们,“饥饿的女儿”终于回家了。
结语
对于虹影而言,其独特的成长经历,那些充满了痛苦和矛盾的生命记忆,那些边缘人晦暗不清的惨痛的生命表象,迫使她一次次追问,她的痛苦来自哪里?当“私生女”成为一个坚定而又不可抗拒的答案时,虹影认识到自己带着“原罪”而来,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不得解脱。在这种情况下的虹影和许多作家一样,选择了“自救”。“谁也无法剥夺我最后一个选择——写作或自杀”[18],写作承担起灵魂救赎的重任,她说,“我觉得自己曾经被毁灭过,曾经走到了绝境,曾经进入了死城,但后来又重生了。我确实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这真是个奇迹……”[19],“我把这些不堪回首的过去写下来,就是要把自己送上审判台,进行一次寻找自我救赎和忏悔之途!因为一切的悲剧因缘都在于我,在于我的私生女身份,在于我隐藏在血脉深处的原罪!反过来说,把这些命运的残酷写出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我放下了,释怀了。我坦然,淡然。”[20]
她的写作始终绕不开“父亲”,正是通过“父”的叙事,虹影才完成了对自己的治疗,以及重返家园的路。
[1]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两种“饥饿”不重要,而是因为“食饥饿”在虹影的生命历程中是间接而又短暂的,而“性饥饿”是“精神饥饿”的衍生物。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饥饿”才是最根本的。
[2][3][9][10]虹影.饥饿的女儿[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33,254,108 -109,113.
[4][6][16][17]虹影.好儿女花[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89,89,185,223.
[5]虹影.今天,我要把自己送上审判台[EB/01].信报独家专访披露《好儿女花》背后的心路历程.http://www.cq.xinhuanet.com/news/2009 -10/30/content_18096562.htm.
[6]虹影.好儿女花[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7]黑格尔.朱光潜译.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8]阿恩海姆.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A].郭小平等译.艺术心理学新论[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1]张佐邦.文艺心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2]童庆炳,程正民主编.文艺心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3]王红旗.难在道“女人”之所未能道[A].爱与梦的讲述:著名作家心灵对话[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4]虹影.阿难[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
[15]止庵.关于海外文学,泰比特测试,以及异国爱情的对话——虹影与止庵对谈录[J].作家,2001,(12).
[18]虹影.饥饿的女儿(附录)[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19]孙康谊.虹影在山上,女子有行(附录)[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
[20]信报独家专访披露<好儿女花>背后的心路历程[EB/01].http://www.cq.xinhuanet.com/news/2009 - 10/30/content_1809656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