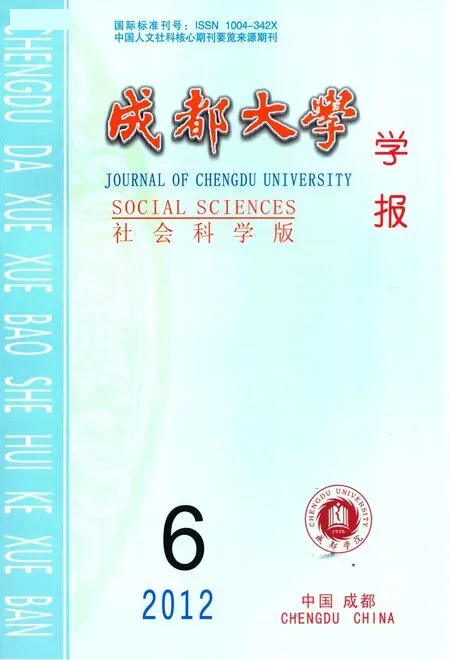新生代文学中的“血”
——当代文学的意象研究笔记
樊 星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新生代文学中的“血”
——当代文学的意象研究笔记
樊 星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新生代文学对人性的探讨常常深入到血缘、血型的深处,体现了“60后”、“70后”作家人生观、文学观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也显示了新生代作家重新认识民族性的可贵努力。而姚鄂梅的《像天一样高》、张广天等人的《切·格瓦拉》、丁三的《我在图书馆的日子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等作品也表明:在新生代作家中不乏“为民请命”、“批判现实”的热血之士。
新生代文学;“血”;人性探讨
在读当代文学作品时,常常会与“血”的意象相遇。是因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血写的历史的原因,才使得当代作家在描绘历史中常常会有意无意地渲染血的氛围?还是因为在久远的古代,“血流漂杵”的恐怖记忆就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以至于中国历代政权的更迭史一直充满了血腥的气息,一直到“文革”那样的“内战”也血光四溅?中国文化的词汇中有许多与“血”紧密相连的成语——从“呕心沥血”、“满腔热血”、“热血男儿”、“歃血为盟”、“血脉相连”、“血浓于水”、“血亲复仇”、“血海深仇”、“浴血奋战”、“碧血丹心”、“甘洒热血”、“血肉丰满”、“杜鹃啼血”到“刺刀见红”、“一针见血”……是否也与我们这个民族有太多痛苦与感人的血泪记忆有关?
那么,“血”意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大量涌现又具有怎样的文学与文化意义?如果说,在参与过“文革”的作家那里,郑义的《枫》、顾城的《永别了,墓地》、老鬼的《血色黄昏》、都梁的《血色浪漫》、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等作品是浪漫青春、革命激情与牺牲悲剧的集中体现,那么,到了新时期,当革命已成往事,世俗化浪潮高涨,当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时,更年轻的一代作家在书写自己的血色记忆时,会表达出怎样的人生感悟?
新时期作家在冲破了“阶级斗争”的思想牢笼以后,回归了人道主义的传统。对人性的探讨成为许多作家的自觉追求。这样的探讨最终导向了神秘主义,因为人性实在是个深不可测的话题。
1980年代,日本电视剧《血疑》在中国的风靡一时更开启了从血型、血缘的角度追问人性与命运的思路。当代人已经习惯从血型、血缘的角度去猜想人生之谜了。“新生代”作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因此引人注目。
苏童:对血气的感悟
苏童是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这一代人普遍具有相当浓厚的神秘主义倾向。他们一方面相信算命、预感、求神、拜佛之类传统民间迷信,另一方面对“血型与性格”之类来自海外的神秘学说也笃信不移。这股神秘主义的思潮一方面是现代社会人们在变化万千的生活中感到惶惑、企图把握自己命运的心态显现,另一方面对于探讨人性的神秘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不妨将苏童小说中对神秘血气、血缘的点化看作新生代作家走近神秘主义思潮的证明。而苏童的上述猜想也的确开阔了读者探讨人性的思路。
苏童在他的中篇小说《1934年的逃亡》开篇,就有主人公“我想探究我的血流之源”的主题。祖父陈宝年是地主,祖母蒋氏是长工,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陈宝年的性欲。而蒋氏生下的孩子也继承了陈宝年的残酷暴虐,使她“顿时联想到人的种气掺满了恶行,有如日月运转衔接自然”。而小说中描写陈宝年进城靠经营竹器发迹时,也点化了事业与血缘的神秘联系:“我只是想到了枫杨树人血液中竹的因子”。此外,小说中还有关于地主陈文治有一白玉瓷罐,专采少男少女的精血作绝药的描写,也进一步渲染了小说的神秘意味。到了中篇小说《罂粟之家》中,作家更描写了恣意纵欲的地主刘老侠“血气旺极而乱,血乱没有好子孙”,结果几个后代都是畸形儿。“传宗接代跟种田打粮不一样。你把心血全花在上面,不一定有好收成。……人的血气不会天长地久,就像地主老刘家,世代单传的好血气到沉草一代就杂了,杂了就败了,这是遗传的规律。”这样的议论表达了作家对神秘血气与家族命运的思考。中国从来就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不过三代”等说法,昭示着宿命的难以抗拒。而苏童的《罂粟之家》则将这宿命论与血气之思联系在了一起:难道血气真的也有盛衰的节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那节律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与纵欲有关(纵欲足以戕害生命)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那些显赫一时的大家族会很快败落,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奋斗终于成为赫赫有名的豪门,除了政治谋略、军事实力、经济原因以外,有没有血气方面的因素?……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人的命运与血气的神秘有关。这是苏童在探索人性之谜方面得出的结论。
另一方面,苏童的“文革”记忆也不同于参与过“文革”的那一代人。在他一系列追忆“文革”的作品中,都记录了在“文革”主流的边缘,那些懵懵懂懂的孩子浮躁又无所寄托的残酷青春。他有一部小说集《少年血》,就是残酷青春回忆的真切写照。其中,《刺青时代》就记录了少年帮派之间一场“大规模的血殴”,“疯了,那帮孩子都疯了,他们拼红了眼睛,谁也不怕死。他们说听见了尖刀刺进皮肉的类似水泡翻滚的声音,他们还听见那群发疯的少年几乎都有着流行的滑稽的绰号,诸如汤司令、松井、座山雕、王连举、鼻涕、黑X、一撮毛、杀胚。那帮孩子真的发疯了,几个目击者摇着头,举起手夸张地比划了一下,拿着刀子你捅我,我劈你的,血珠子差点就溅到我们砖窑上了。”一拨斗殴者被一网打尽后,另一拨又在那里歃血结盟了。《回力牌球鞋》也讲述了少年之间为了一双球鞋而发生的“血祸”。《午后故事》还记录了一场少年之间的打斗与凶杀,少年血“是紫红紫红的,又粘又稠,颜色异常鲜艳”。这些关于少年斗殴的故事与王朔在《动物凶猛》中关于少年斗殴的描写一起,写出了“文革”中的社会的另一道伤痕:不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武斗,而是为了少年懵懂、无知、争强好胜的血性而斗殴。少年之间绵绵不绝的斗殴在今天也常常发生。这样的斗殴是人性恶的证明。
余华:血腥故事与民族性之思
余华也曾经是“文革”的旁观者。他的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就散发出浓烈的血腥味: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在“文革”中失踪。当他在“文革”结束十年后重返故地时,已经精神失常。他的自残显然出于精神病人的妄想,可他却在阴差阳错中起到了提醒世人,勿忘“文革”的作用!因为,“十多年前那场浩劫如今已成了过眼烟云,那些留在墙上的标语被一次次粉刷给彻底掩盖了。他们走在街上时再也看不到过去,他们只看到现在。”余华显示了将精神病人的奇特感觉文学化的才华:在这位精神病人的眼中,太阳是“一颗辉煌的头颅,正在喷射着鲜血”;路灯里也“充满流动的鲜血”;燃烧的垃圾是“一堆鲜血在熊熊燃烧”;他“用钢锯锯自己的鼻子,锯自己的腿”,在疯狂地自残中把自己伤得“满身都是斑斑血迹”……这些文字,读来令人感到惨不忍睹,又惊心动魄。
他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则是一部描写当代社会底层平民靠卖血为生的艰难生活的力作。在卖一次血就抵得上种地半年的贫困年代里,在“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的生存环境中,人们不得不去巴结血头,去争相卖血。虽然小说中许三观的老婆许玉兰牢记父亲的教导:“身上的血是祖宗传下来的,做人可以卖油条、卖屋子、卖田地……就是不能卖血。就是卖身也不能卖血,卖身是卖自己,卖血是卖祖宗”,但许三观“除了身上的血,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将自己身体里的血当成了“摇钱树”。在这样的描写中,作家揭示了老百姓因为生活所迫对于传统禁忌的远离,因此也就写出了生活的无情,生命意志的强大。为了尽可能多卖血、多挣钱,他甚至不顾卖一次血要休息三个月的禁忌,不怕“把自己卖死了”。这样,小说又将一个自身生命意识淡漠的可怜人对于家庭的悲壮责任感写到了感人至深的境界。读这部作品,使人不禁对中国的民族性产生新的思考:在社会的底层,有些看似活得浑浑噩噩的人,其实是有着不为人知的坚韧意志的;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生命的可贵,但他们知道自己应当承担起的对于亲人的责任,为此,他们可以牺牲自己。这样,《许三观卖血记》就还原了民族性的混沌状态,写出了麻木与坚韧、可怜与顽强、卑微与伟大的水乳交融。比起那些常常以“勤劳、勇敢”或“麻木、卑怯”去以偏概全的空洞议论,《许三观卖血记》显然更富于生活的混沌感和深刻的哲理感。
一直到今天,还有一部分没有脱离贫困的人在靠卖血为生,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此感染了“艾滋病”。因此,《许三观卖血记》也具有关注底层社会弱势群体的深刻意义。余华在为这部小说的英文版写的前言中就告诉读者:“在中国,这只是千万个卖血故事中的一个。……卖血在很多地方成为了穷人们的生存方式,于是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卖血村,在那些村庄里几乎每个家庭都在卖血。卖血又带来了艾滋病的交叉感染,一些卖血村又成为了艾滋病村。”①因此,《许三观卖血记》就成为“底层”叙事的一部经典。由于作家在作品中融入了对于国民性的重新认识,所以作品中同情、理解、悲叹、肃穆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也明显不同于那些一般常见的“为民请命”之作。《许三观卖血记》因此能够成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重新思考“国民性”问题的杰作。
血缘之谜与自虐心态
林白的中篇小说《子弹穿过苹果》是一个“暴力故事”,而这个故事与恋父的苦闷有关。主人公在苦闷中产生了自虐的妄想——
……我开始拿起那片刀片,我已经睁着眼在黑暗中看了很久了,我把那刀片看得成了精,紫莹莹地闪着薄薄的光,很妥帖地游到我的手上……
只要把刀片压住。
再一拉。
腥红的血就会很美丽地飞到白墙上,中间一道流星般奇妙的弧线,又灿烂又优美,足以消解所有痛苦……
虽然是妄想,却写出了女性的痛苦:“爱情能要了女人的命。”恋父,当然是不伦之情。可它却在相当一部分女性心中根深蒂固。这不能不说是血缘之谜。
到了长篇小说《守望空心岁月》中,林白也写到了女主人公在公园里凭对于血缘的信念寻找亡父墓地的体验:“我是否在繁茂的草木中感到过血缘神秘的亲和力?”(但结果却不得而知。)一切都不那么虚无缥缈,但也同样不那么切实可信。
陈染的《私人生活》中的女主人公倪拗拗也自认为自己强烈叛逆的个性来自于“血液中那种把一般的对抗性膨胀到极端的特征”。在这样的描写中,不难看出女作家从血缘中寻找命运的谜底的神秘之思,不过,神秘的信念与现实的纷乱之间的出入又使她们常常陷入惶惑与迷惘。尽管如此,她们也似乎无意因此而放弃对于一切神秘现象的猜想。这,也是一种难以理喻的宿命吗?
再来看看另一种变态的情感:自虐。
2002年,“70后”作家盛可以发表了小说《快感》,相当生动地写活了当今一部分年轻人的变态心理。小说开篇写“我”“对利刃莫名其妙地兴奋”——
利刃划过肌肉,就像农人犁开泥土。肌肉绽开真实的花瓣,就像恋人表露心怀,袒露鲜红的本质,毫无疼痛感,有的只是极度的灼热到极度的冰凉的转变。多年前我试过用锈钝的裁纸刀对着手腕磨来磨去,也试过用自己的肌肤尝试新刀子的锋利。我看到鲜血首先像豆子一样蹦出来,冒着热气……汩汩流淌并大面积地漫延。专注于血液的审美,脑海里稀奇古怪的沉重如云絮轻悠,这是妙不可言的……我说不疼,你肯定不信。
这段文字,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的无聊、苦闷、嗜血、变态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与女友的争吵与打斗中,女友挥刀削去了“我”的小拇指,“我”却感到:“鲜血滴答滴答往地下掉,节奏无比优美,像远古传来的跫音,冲击耳膜,产生不逊于交响乐狂轰的巨响。”甚至,“我缓缓地接过剁骨头的刀,在灯光下晃了两晃,像在鉴别某类古玩,几行红色的血迹像蚯蚓一样在刀面上爬行,它们是刀的血管。”“我”甚至不急于去医院,而是乘兴与女友做爱!小说最后写他的“命根子”被女友割掉,将女友的变态也写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
2004年,“60后”作家艾伟发表了短篇小说《迷幻》,生动刻画了几个少年自残的悲剧:先是小罗“经常有一种毁坏自己的欲望”,额头被父亲砸出血以后他“竟然感到畅快。当血液从身体里出来的那一霎,他没感到痛苦,不,痛苦也是有的,但幸福竟然从天而降,他感到饱胀的身体有一种释放的快感,快感过后,身体变得宁静如水。”“他很想让血液从身体里喷涌出来。他闭上眼睛,幻想着血液从肌肤里喷射出来的情形,血液会在阳光下闪耀。”他因此而烦躁,继而咬自己的手臂,“尝到了咸咸的温热的味道,他知道,那是血。快感和幸福感又一次降临……”。他藏有三把刀。他用刀自伤。“血像是有自己的欲望,它迅速把刀子包围了,那一瞬间,像火吞噬易燃物,热情奔放。他感到他的身体是那么渴望刀子,对刀子有一种无法遏制的亲近感。……刀子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血液因此在欢呼刀子的光临。”他后来在同学中找到了知音。他们在打架中体会着变态的快感;在自伤中体会那快感,甚至“把彼此的血滴入瓶子里,再分成两份,然后把血喝了下去”,然后体会“灵魂好像已升上半空,在微风中飘荡”。他们陷入了“对血的迷幻之中”,他们甚至“开始强迫另一部分人自残”。他们还彼此“炫耀着伤痕”。而在疯狂过后,他们仍然感到空虚。
这样的作品发人深省:现代化在改善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莫名其妙地扭曲了人们的心灵,使人们或者感到压抑,或者渴望疯狂;或者易怒,或者自虐。
这也是一种异化:生命被虚无主义、莫名苦闷扭曲的异化。
冷血与犯罪
新时期小说已经产生了许多犯罪的故事。这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因为社会失范而产生的犯罪剧增的体现。刘恒的《杀》、《黑的雪》,余华的《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王安忆的《遍地枭雄》,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等都是证明。
“60后”作家须一瓜是报社记者,在了解到许多“罪与罚”的悲剧以后,写下了一批有影响的剖析犯罪心态的小说:《蛇宫》、《雨把烟打湿了》、《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淡绿色的月亮》、《第三棵树是和平》、《太阳黑子》……她擅长写犯罪题材,通过写犯罪剖析剧烈社会矛盾冲击下普通人心理的扭曲与变态。像《第三棵树是和平》就剖析了一个性工作者杀夫的心态:孙素宝的丈夫生性脾气暴躁,因为失业而虐待妻子,不仅砍烂了妻子的二十条内裤,而且常常在痛打妻子后泄欲,甚至用刻刀在妻子的腹部刻字,甚至咬掉了妻子的半只耳朵!在这样的刻画中,一个虐待狂的变态灵魂惊心动魄地暴露无遗。而他的妻子孙素宝在饱尝了虐待之苦、忍无可忍的压力下突然一时性起,杀死了虐待狂丈夫——
血喷到了孙素宝的下巴、脖子和前襟。这三个地方都感到了杨金虎的血有点烫。杨金虎站不起来,因为他的一只胳膊被孙素宝绑住了。孙素宝看到他被绑住,忍不住笑了,拣起掉在地上的剃刀。杨金虎想用手来抓,但是,手伸了一半,就软了下去。血啊,非常多的血像山泉一样带着泡泡,从杨金虎的脖子里噗噜噗噜地冒出来。整个床马上就湿透了。孙素宝有点困惑,没有想到一个人有这么多的血,这使她有点不耐烦。但后来想到,只有血流光,杨金虎才会彻底死去,所以,她就心情比较愉快地等那些血噗噗噗地往外冒。
以暴抗暴——这,也是底层生活的一部分:那些心理素质糟糕的人渣,常常在虐待弱者中宣泄着疯狂的罪恶能量。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许多人因为心理失去平衡铤而走险。须一瓜写出了这一点,写出了家庭暴力对女性的戕害,也写出了弱者在忍无可忍中犯罪的无奈,读来令人叹息。类似的悲剧,在生活中经常上演。
尽管在须一瓜的作品中,常常回响着对罪犯未泯人性的理解情感,可在实际生活中,冷血罪犯数不胜数。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是人性恶的无情证明。
新生代文学:热血的证明
其实,新生代文学中不乏热情谱写的篇章。
“60后”作家姚鄂梅就写下了许多热切关注现实的作品。中篇小说《女儿结》通过一位连续遭受丧母、婚变、重病打击的女青年叶小昭突发奇想,在报上刊登征母广告,并奇迹般顺利赢得了新的母爱的故事,相当集中地刻画了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传统的伦理亲情在巨变中失去平衡的社会现实(例如“空巢”家庭、“单亲”家庭、“丁克”家庭的大量出现,以及由传统的“尊老”传统向“重幼”风气的演变,等等),同时又意味深长地揭示了在传统伦理亲情遭遇危机时新的人伦关系的产生,这样,就在呼唤人间真情的同时也产生了对于建立新型人伦关系的独到思考,在悲凉与悲凉的“相濡以沫”中升华出温馨的主题——母女情深,深就深在血缘亲情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但《女儿结》中因为亲生女儿出国而独守“空巢”的秦爱霞和因为亲生儿女不孝而寂寞独居的唐世芬,却集中体现了血缘亲情在社会变动中常常难免的分离隐痛,体现了母爱的无所依托。二人争当叶小昭的义母,直至在看护叶小昭时争相表现又彼此调侃,正是渴望亲情、母爱伟大的证明,同时又何尝不是母爱具有排他性的心理流露。而农妇张妈与叶小昭的邂逅、对叶小昭的关爱则显然具有更普泛意义上的同情与关爱的色彩,从而成为人间自有真情在的证明。因此,《女儿结》中对于非血缘的母女亲情的描绘,也显得不拘一格了。另一方面,叶小昭虽然渴望母爱,却在发现自己得了重病之时而不愿给义母添麻烦的心态,以及两位义母为了看护叶小昭不辞辛劳的描写,也使新型的母女之情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情感寄托,而在互相体贴、“相濡以沫”的精神层面上得到了升华。作品颇有些传奇色彩,但也折射出当代生活中奇事、奇人层出不穷的现实。
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有一个令人心动的副标题“谨以此篇献给80年代”。小说描写了几个因为纯洁而向往自由、独立的生活的青年诗人的浪漫生活:小西、康赛、阿原。他们在父母的眼里,是“长不大的孩子”。他们没有钱,却浪漫而快乐;他们清高,却不狂妄。他们生在都市,却去新疆寻找自己的生活。他们追求“精神的高贵,内心世界的高贵”,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诗歌爱好者”,在“那样一个乱糟糟的环境里,却写出了纯净的诗歌”。他们的“天真无邪”,与许多同龄人的世故、颓废、狂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热爱《吉檀迦利》和《瓦尔登湖》,向往梭罗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就像小西所说的那样:“我从来没有对生活采取消极的态度,我只是喜欢躲到一边去独自逍遥,所以我不仅不消极,我甚至是积极的。”他们因此“能把贫穷无奈的生活升华成悠闲”,一边劳动,一边写作。他们在那片土地上找到了自由的乐园。然而,作家好像无意重建一个“乌托邦”。小说后半部讲述了自由乐园的瓦解:他们之间也常常会发生不快;他们中有人终于没有抵抗得了功利生活的诱惑(如阿原,他终于发现“不堕落就无路可走”;而康赛在经历了婚姻的失败和自杀的体验后,也被迫承认“诗歌其实跟诗人一样软弱无力”,然后心灰意懒地回归了世俗化的生活),甚至连小西也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坚守乐园的生活。但她不断走向内蒙古、东北的人生足迹,还是显示了精神的力量。小西是当代文学中不多见的理想主义流浪者的形象。她不像张承志笔下的理想主义流浪者那么愤世嫉俗,她显然更多一些长不大的阳光少女的单纯色彩。作家以这样的形象为世纪初的文坛、为当代的青年文学,增添了一抹可贵的亮色,也足以使人想起英国作家毛姆的长篇小说《刀锋》和《月亮和六便士》那样具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的杰作。
还有一位“60后”作家、音乐人张广天。在1980年代的大学生活中,他曾经热衷于学习嬉皮士,酗酒、玩恋爱游戏,直至配制兴奋剂。后来,经过三年的劳教农场生活,他变了。他说:“我开始告别与我们的处境无关的各种西方理念,在情感上越来越靠近劳动阶层。”他谱写了一些“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和抗议的必然性”的歌曲,流浪、卖唱,“和知识分子的阶层告别,为精英的躯体默哀”,“在人民中间,开始了自觉的文艺劳动”,并“下定决心去做一个永远在人民中歌唱的歌者”②。他参与策划的现代史诗剧《切·格瓦拉》因为缅怀革命在世纪末的剧坛引起了聚讼纷纭。他对格瓦拉的怀念与当年的老红卫兵对格瓦拉的怀念颇有相似之处:“格瓦拉为弱者拔刀为正义献身的精神在世界各地点燃了一颗颗心灵。剥削压迫社会的长夜已经在酝酿下一次革命。”③且不谈这样的预言与世俗化的社会怎么格格不入,它至少表明:民粹主义的精神在“新生代”这里并没有被世俗化浪潮窒息。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张广天的深入民间与当年“右派”、“五七干部”、知识青年的深入民间很不一样——他的采风性质的流浪与创作、他在充分利用现代文化传媒传播自己的文艺作品方面取得的成功,都是当年在文化专制主义高压下沉默的“右派”、“五七干部”、知识青年所不可能做到的。他表达了当代底层人民的不满情绪,以“新生代”特有的方式。对于他,民粹主义是与标新立异的个性紧密相联的。在这方面,他与张承志的特立独行颇有相通之处。而他们之间的区别则在于:他不似张承志那么绝望。《切·格瓦拉》与《左岸》、《圣人孔子》共同构成了张广天的“理想主义三部曲”。《左岸》讽刺了“肉身比理想要坚强得多……可是金钱和权势的力量比肉身还要坚强”的世风,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当集体理想主义缺失的时候,个体的爱情实践是否可以给自由的理想主义一次启示?‘爱情是如今通向真理的唯一出路’。”④这样的思考显然已经离正统的理想主义相去甚远。剧中一句“之所以会疼痛,是因为还有血有肉”令人感动;还有“在我里面,血液的更里面,∕红的光芒正向外飞旋”的歌声一再响起,也进一步凸显了真诚之爱的主题。“《左岸》讲情爱主义的实践,《圣人孔子》讲亲爱主义的实践。都是理想主义”。“儒家希望从小家到大家,描绘一幅有可行性的理想主义蓝图。你爱你的血亲,这是天性人道,无须论证,于是,你爱血脉相连的全人类,也是顺理成章的天经地义。这就是亲爱主义。”⑤这样的主旨使《圣人孔子》汇入了当代儒家文化复兴的文化热潮。
张广天是“新生代”中少见的具有革命倾向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民粹主义者在“新生代”中,显然是凤毛麟角。不过,张广天能在世纪末的音乐界、戏剧界成为一个聚讼纷纭的人物,似乎也隐含了这样的意义:尽管民粹主义已经式微,但时代还需要这样的声音。在多元化的思想格局中,民粹主义不应缺席。一方面,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呼唤着民众不断提高参政意识和自身的素质;另一方面,民主化的时代潮流也呼唤着民众的代言人。因此,民粹主义具有卷土重来的相当潜力。张承志、张炜、张广天等人拥有的文化空间就是证明,虽然他们常常显得不合时宜。
《天涯》杂志曾经开辟过“1970年代人的底层经验与视野”的专栏,发表了一批“70后”作家关注底层的作品。其中就发表过历史纪实文学《蓝衣社碎片》的作者丁三的文章《我在图书馆的日子里》。作者失学以后开始了在图书馆的自学之路: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读鲁迅,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并开始思考国家的命运:“一个后来席卷了一个古老国家,并且改变了这个国家几乎全部面貌的运动,在其崛起时,居然是那么弱小!这当中,有什么规律?而新社会出现后,又迅速地回到旧世界曾经有过的最可怕的方面,旧世界以新世界的名义还魂,这背后,有什么必然?”他由此走向“认识真实社会,追求理想社会”的道路。⑥
“70后”作家梁鸿博士在“非虚构文学”《中国在梁庄》中通过大量事实记录了故乡的颓败现实——乡村已成废墟,环境已被污染,少年犯罪,青年背井离乡,乡村政治深陷困境……作家把故乡当作了“中国的病灶”、“中国的悲伤”去剖析,揭示了被遗忘的底层、不为人知的苦难。另一方面,作家也在书中表达了一个“70后”学者对于乡土的真挚情感:“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乡土中国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是我思考任何问题时的基本起点,它决定了我的世界观中有土地与阔大的成份。这是我的村庄赋予我的财富。我终生受用。”⑦读着这样的文字,是很容易使我们想到当年梁漱溟先生“救活旧农村”的呐喊⑧,想到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于乡土社会流弊的剖析。《中国在梁庄》曾获2010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十大好书、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书和《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好书,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评论道:“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⑨
还有“70后”作家慕容雪村揭露传销的纪实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作家以一个身家百万“老板”的身份,潜伏在狂热而扭曲的地下传销世界中达二十多天。据此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协助公安机关捣毁了这个团伙,解救出157名传销人员。然后,写出了《中国,少了一味药》,揭示了传销狂热深处的国民性病灶:“这就是一片适合传销的土地。所有传销者都有相同的特点:缺乏常识,没有起码的辨别能力;急功近利,除了钱什么都不在乎;他们无知、轻信、狂热、固执,只盯着不切实际的目标,却看不见近在眉睫的事实。这是传销者的肖像,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肖像。传销是社会之病,其病灶却深埋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在空气之中,在土壤之中,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它就会悄悄滋长。”⑩作家的这一经历足以使人想到当年的“体验派”报告文学作家贾鲁生混入丐帮,写出《丐帮漂流记》的往事,还有作家邓贤揭密一群炎黄子孙漂泊异国他乡的惨痛历史的纪实力作《流浪金三角》,也是作家“以生命做赌注换来的作品”(11)。
《像天一样高》、《切·格瓦拉》、《我在图书馆的日子里》、《中国在梁庄》和《中国,少了一味药》足以表明:在新生代作家中不乏远离了颓废、冷漠的浪漫之士,不乏“为民请命”、“批判现实”的热血之士。也许,在新生代中,他们的上述作品的名气远远不如那些渲染颓废、冷漠情绪的作品大,但它们的问世毕竟是热血的证明。中国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一向有弘扬正气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一部分新生代作家那里也已经开花结果了。
注:
①余华:《这只是千万个卖血故事中的一个》,《读书》2002年,第7期。
②《行走与歌唱》,《天涯》2000年,第5期。
③《切·格瓦拉》,《作品与争鸣》2000年,第6期。
④⑤《先锋导演手记》,《人类的当务之急》,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179页;第185页。
⑥《天涯》2003年第6期。
⑦《中国在梁庄》(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210页。
⑧参见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第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⑧引自王海圣,《〈中国在梁庄〉:梁庄是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河南商报》,2011年1月25日。
⑩《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
(11)解玺璋:《〈流浪金三角〉问世之日访作者邓贤》,《北京晚报》,2000年6月29日。
I206.7
A
1004-342(2012)06-44-06
2012-05-16
樊星(1957-),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