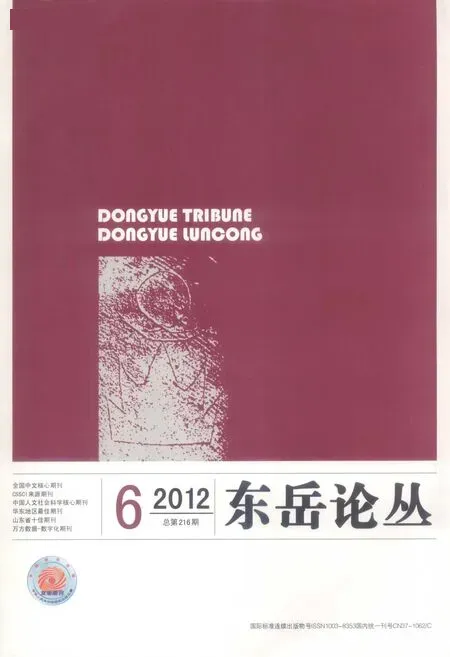四书五经融通视域下的罗汝芳心学易学
张沛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四书五经融通视域下的罗汝芳心学易学
张沛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四书五经通而为一”是罗汝芳跟从胡宗正学《易》获得的重要结论。近溪心学易学的总思路是:先以太极生生为画前本旨,进而以乾坤相涵论心性,最后再以复卦统言功夫。四书五经的相互融通乃是作为诠释的总原则,始终贯穿在“生生(本旨)——乾坤(心性)——复(功夫)”的理路演进之中。近溪所欲达成的,是一个建立在彻底打通、彼此开放的四书五经基础上的一体圆融之学。由是,近溪之论《易》多与其它经典相联,其易学亦呈现出不拘一格的浑融气象。
罗汝芳;易学;融通;生生;乾坤;复
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门人私谥明德,为王门后学的重要人物。在易学方面,罗汝芳虽无解《易》专著,却留有相当丰富的论《易》之语。迄今为止,学界对罗汝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心学思想上,关于其易学思想并无太多讨论。鉴于此,本文即对近溪心学易学的思路与特点进行一简要的梳理和分析。
一
罗近溪三十四岁学《易》于胡宗正①旧说误以胡宗正为胡清虚,二者实非一人。参见彭国翔《王龙溪与佛道二教的因缘》,载《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4期;《王畿与道教——阳明学者对道教内丹学的融摄》,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1期。一事,后人在罗氏传记、年谱中多有记述。其中,尤以曹胤儒《罗近溪师行实》所载最为详尽:
宗正乃言曰:“易之为《易》,原自伏羲泄天地造化精蕴于图画中,可以神会,而不可以言语尽者。宜屏书册,潜居静虑,乃可通耳。”师如其言,经旬不辍。宗正忽谓师曰:“若知伏羲当日平空白地着一画耶?”师曰:“不知也。”宗正曰:“不知则当思矣。”次日,宗正又问曰:“若知伏羲当日凭空白地一画未了,又著二画耶?”师曰:“不知也。”宗正曰:“不知则当熟思矣。”师时略为剖析,宗正默不应,徐曰:“障缘愈添,则本真益昧。”如是坐至三月,而师之《易》学,恍进于未画之前,且通之于《学》、《庸》、《论》、《孟》诸书,沛如也。②曹胤儒:《罗近溪师行实》,《罗汝芳集》附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835页。
胡宗正指出,易之精髓只能神会、不可言传,故其既不言象数图书、卦爻符号,又不言卦爻辞义、文字训诂。他对近溪的易学传授,仅是以略加点拨的方式促使近溪自我致思穷索而得悟。从对罗近溪“最初一画”的提问来看,胡宗正颇重“画前易”之旨。“障缘愈添,则本真益昧”,更透露出胡氏是以画前为易之“本真”所在,故主张放下典籍破除障蔽、静中思虑直达“本真”。这一思想对近溪影响至深:
“盖‘易有太极’,是夫子赞易之辞,非易之外又有个太极悬在空中也。即如周子云‘无极而太极’,又以赞太极之辞,亦非太极之外又有个无极悬在空中也。”曰:“易之外固非别有太极矣,然易何以便谓之太极也耶?”罗子曰:“窃意,此是吾夫子极深之见、极妙之语也。盖自伏羲、文、周三圣立画显象之后,世之学者观看,便谓太虚中实实有乾坤并陈,又实实有八卦分列。其支离琐碎,宁不重为斯道病耶?故夫子慨然指曰:此易之卦象,完全只太极之所生化。盖谓卦象虽多,均成个混沌东西也。若人于此参透,则六十四卦原无卦,三百八十四爻原无爻,而当初伏羲仰观俯察、近取远求,只是一点落纸而已。……要之,伏羲自无画而化有画,自一画而化千画,夫子将千画而化一画,又将有画而化无画也已。”①罗汝芳:《近溪子集》卷礼,《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此乃是罗近溪从学胡宗正的得悟之语。近溪以为,伏羲、文王、周公创设卦爻,目的只在符示太极的创生大化。因而,从未有一画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成,是太极生化之功的全然展现;《易》虽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齐备,究其本根又在未着一画处。此未着一画处,即有即无、虽混沌却不妄。可惜三圣之后,学者便胶着卦爻,以为乾坤六十四卦皆是实存,全然不目易之原旨,因而孔子才拈出“易有太极”一句,使人明彻唯有归于画前方能寻得易之“本真”。
有学者认为“从易学史的角度看,宗正所谓‘伏羲泄天地造化精蕴于图画中’,这表明其所擅长的是‘图书易’而非义理易”②吴震:《泰州学派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此说略显武断。尽管胡宗正易学我们已不得而知③据罗汝芳说,胡宗正自言其易学得于异传,故不轻易授人:“楚中一友来从某改举业,他谈《易经》,与诸家甚是不同,后因科举辞别……得因遣人请至山中,细细叩问,始言渠得异传,不敢轻授。”见罗汝芳《近溪子集》卷乐,《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但他在与近溪的问答中并未言及图书。且就上下文语境来看,将“泄天地造化精蕴于图画中”的“图画”理解作卦爻符号比视为河图洛书更为切当。即便胡氏所言“图画”确指图书,也不能由此断言其擅长图书易④认肯图书者未必擅长图书易。如阳明、龙溪都曾谈及河图洛书,但二人皆不长于图书易学。。至于“画前”易旨,可以是图书,也可以是义理。所以,我们只能说胡宗正强调“画前易”,却不可妄言其“擅长图书易而非义理易”。在这一点上,受《易》于胡宗正的罗近溪纯然取道义理,在其存世文献中亦未有关于图书之学的只言片语,可作旁证。
罗近溪从学胡宗正,不单使其“《易》学恍进于未画之前”,更重要的是,他由是得以将《易》“通之于《学》、《庸》、《论》、《孟》诸书,沛如也。”亦即五经、四书之间彼此通贯、互诠互显:
降古圣神,序之以六十四卦,分之以三百八十四爻,演之以《系辞》十翼,布之以《洪范》九畴,至于极力显著,则又是《中庸》此书。⑤罗汝芳:《近溪子续集》卷乾,《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
先儒谓《易》为五经祖,则《书》之政事、《诗》之性情、《礼》之大本、《春秋》之大义,言言皆自伏羲画中衍出,非《易》自为《易》,各经自为各经。总之,皆自身心意知,通之天下国家。⑥罗汝芳:《旴江罗近溪先生全集·语录》,《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四书五经通而为一,是罗近溪跟从胡宗正学《易》获得的重要结论。这一结论不单是我们理解近溪易学的前提,也是我们全面把握近溪思想的关键。
二
因乎五经、四书相互敞开、彼此融通,则近溪之解读某一儒家经典常常与其它典籍相联系,自然就顺理成章。近溪并不强调各经、书之间的分别和界限,而是着重开掘儒家经典中“一以贯之”的精蕴。他认为:“一切经书皆必归会孔孟,孔孟之言皆必归会孝弟”⑦罗汝芳:《近溪子集》卷乐,《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儒家经典之旨不外乎“仁”,究其本,“仁”又源于“生生”:“孔门宗旨,止要求仁,究其所自,原得之《易》,又只统之以‘生生’一言。夫不止曰‘生’,而必曰‘生生’,‘生生’云者,生则恶可已也。”⑧罗汝芳:《近溪子续集》卷坤,《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77页。近溪强调,“仁”是贯穿一切儒家典籍的核心思想和内在精髓。这一思想精髓是孔子从《周易》的“生生”中体悟出来的。我们知道,“仁”作为儒家一贯秉承的人文精神,原本是对人与人之间真实情感的凝炼;而人对他人的情感,无疑又是由生而皆有、无一丝虚伪造作存乎其间的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等自然情感引申推及的。所以,“孝悌”为“仁之本”,正根缘于父母生命赐予的“生”与孝悌之“仁”存在着的密切关联。有见于此,近溪便将《易》之“生生”与孔孟之“仁”融会贯通。其晚年的“孝悌慈”宗旨,亦是对此见的推进延伸。
父母赋予生命与子女孝父悌兄,固然是“生”、“仁”相通最为亲切的展示。若以宏大之整体宇宙视野审视,更可觉悟到“天地之心”的“生生”乃是作为宇宙法则的“大德”之“仁”:
孔子云:“仁者人也。”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无尽曰“仁”,而人则天地之心也。夫天地亦大矣,然天地之大,大于生;而大德之生,生于心。生生之心,心于人也。①④罗汝芳:《旴坛直诠》,《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88页,第388页。
此段文字中,近溪打通经典阐述己意的诠释方式表现得分外明显。在这种诠释下,《易传》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礼记》的“人者,天地之心也”、《中庸》的“仁者,人也”都为“生”与“仁”的相互诠显提供了经典支撑。从天地创生万有、造化万物中流露出的无穷“生”机“生”意,最好地体现了大德之“仁”作为宇宙法则贯通古今、处处俱在的品格。因而“在他看来,孔子所谓仁、孟子所谓性善、《中庸》所谓天命之性、《大学》所谓明德亲民,《周易》之‘生生不已’就可包括无余。生生之仁统摄宇宙,世间的一切,都是生生之仁的体现。”②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罗近溪思想中“生”与“仁”的贯通,显然又与从学胡宗正的经历有着重要关联。在谈及学《易》经过时,近溪曾言:
其时孔孟一段精神,似觉浑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横穿直贯,处处自相凑合。但有《易经》一书,却贯串不来,时又天幸,楚中一友来从某改举业,他谈《易经》,与诸家甚是不同,……某复以师事之,闭户三月,亦几亡生,方蒙见许。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时孝弟之良,究极本原而已。从此,一切经书皆必归会孔孟,孔孟之言皆必归会孝弟,以之而学,学果不厌;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万物一体、而万世一心也已。③罗汝芳:《近溪子集》卷乐,《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可见,未能将《易》与孔孟精神相贯,是近溪拜师学《易》的起因。这一起因,已然设定了其用力方向和最终目标。因此,认识到《易》之宗旨“不外前时孝弟之良,究极本原而已”既是其学成的收获,也是其原本的期望。在胡宗正穷索易之“本真”的点醒下,罗近溪经由熟思静虑最终觉悟到的不过是他预期获得的内容而已。由是推断,所谓“画前易”之“本真”,大抵就是“生生”一旨。以“生生”融汇孔孟,则《易》可“通之于《学》、《庸》、《论》、《孟》诸书,沛如也”。
既然天地之大德的“生”亘古不息,永恒地创生运化着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故宇宙间时时、在在皆是“仁”的显现。顺循此一识见,便可达至“万物一体”之境:
圣门之求仁也,曰“一以贯之”。一也者,兼天地万物,而我其浑融合德者也;贯也者,通天地万物,而我其运用周流者也。……天地万物也,我也,莫非生也,莫非生则莫非仁也。夫知天地万物之以生而仁乎我也,则我之生于其生,仁于其仁也,斯不容已矣。④
我们知道,“万物一体”是宋明理学的传统之一。之前横渠、明道、阳明、心斋都颇重此一境界,明道、上蔡更有“以生言仁”之说。在宋儒当中,近溪首推明道。其基于“生”、“仁”相贯的万物一体论,亦与明道颇多类似之处⑤关于二人“万物一体”思想的同异之辨,可参看周群《论近溪对明道‘一体论’的远祧与变异》,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此处不论。。不止一体论,近溪的其它思想亦对明道多有所取。不过,与明道“更多地强调个人的感受体验”⑥陈来:《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不同,近溪还为其“万物一体”思想提供了一个气本论的说明:
实一元之气,浑沦磅礴,浩渺无垠焉尔。是气也,名之为天则天矣,天固乾之所以始乎坤者也;名之为地则地矣,地固坤之所以成乎乾者也;名之为我则我矣,我固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夫合天地万物,而知其为一气也,又合天地万物,而知其为一我也。⑦罗汝芳:《近溪罗先生一贯编》,《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49页。
此是以乾坤二卦论天地人物一气化生。《周易》以乾坤为首,近溪尤重此二卦之义。
三
我们知道,易学史上的诸家曾结合各自易学对“易”之义有过多种训解。在这一问题上,近溪借鉴了“日月为易”①“ 日月为易”之说见于《易纬·乾坤凿度》、郑玄注、《说文》、《参同契》、《经典释文》等著作。刘大钧先生认为这一说法与《系辞》相符。可参见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3页。说进行了新的诠释:
明字与易字,皆用日月二字为之。明以日月相并,正显阴阳之体;而易以日月相函,却显阴阳流行之用也。故天以日月,时时尽卦爻,而人莫知;圣人以卦爻,时时象日月,而人莫测。卦爻者,日月运行于天上之度数也。十一月中,日在地之极下处,月在天之最上处,冬至一复,则日从地而渐上,月从天而渐下,日上一百八十遭,而五月中,则阳不得一百八十爻耶?其时月在地之极下处,日在天之最上处,夏至一姤,则月从地而渐上,日从天而渐下,日上一百八十遭,而又十一月中,则阴不得一百八十爻耶?②罗汝芳:《近溪罗先生一贯编》,《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24页,第323页。
他认为,“易”、“明”两字皆由日月构成,故“易”字需与“明”字相参。日月即阴阳,则“明”之左右结构,代表阴阳并具之“体”;“易”之上下结构,象征阴阳流行之“用”。以《复》、《姤》两卦具言之,《复》符示着日上月下即阳气渐息始于十一月中气冬至之时;《姤》符示着月上日下即阴气渐消始于五月中气夏至之时。自十一月冬至到次年五月夏至为阳息、五月夏至到十一月冬至为阴消,各历一百八十天;以一爻一日计,则五月夏至时阳得一百八十爻,十一月冬至时阴得一百八十爻。由此可见,天之日月运行,与《易》之阴阳卦爻一一对应;《易》的阴阳消息,亦是对天之日月往来的拟照。近溪更以日月之义论乾坤:
此只看一“易”字,则即得“乾”“坤”二字之意矣。盖“易”是日月相函而成,且日居上而月居下。函月而居上,则尊而善于统矣,尊统乎阴,则阳非专阳,而阳不足以名之也;函阳而居下,则卑而善于从矣,卑从乎阳,则阴非独阴,而阴亦不足以名之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统而从,从而统,则日月虽两体而合一体,阴阳虽二用而成一用,造化自此而可成,鬼神自此而可行矣。③罗汝芳:《近溪子集》卷礼,《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可见,乾坤二卦亦应从“易”字象征的日月相函、阴阳流行中寻求理解。“易”字日上月下,根据居上为尊、处下为卑的原则,“易”本有阳贵阴贱、乾尊坤卑之义。然而,日月相函、阴阳流行本为天道,故二者虽有贵贱之分,但并不分立隔绝,而是以尊统卑、卑从尊的方式交感互通着。所以,尽管纯阳之乾与纯阴之坤体现着天尊地卑的宇宙秩序,却并不妨碍彼此合二为一、涵摄融通。他认为,邵子“天根月窟”说的深意正在于乾坤互涵、阴阳相摄:“尧夫先生一生学问,得之《易经》,而其学问根源,则见之复、姤,故曰:‘一动一静之间,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④罗汝芳:《近溪子集》卷射,《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近溪反对以动静解《复》、《姤》、把“一动一静之间”视为《复》《姤》之际的观点。照他的理解,邵子之意是《姤》《复》的外卦乾、坤各出自其内卦巽、震,从而以阴巽生阳乾、阳震生阴坤体现出阴阳相摄不离。因此,在阴阳互涵的意义上看,乾统坤、坤从乾,乾为坤之始、坤为乾之终,二者不必分疏而论,言乾则坤已在其内,指坤则乾亦存其中。“大抵学《易》,先须乾、坤二卦识得明尽。”理解乾坤是明悟《易经》的前提,而理解乾坤首在领会二者交互涵摄之旨。
尽管近溪对邵雍易学有所推崇,但从他对“乾遇巽”、“地逢雷”的解释来看,其意与邵雍“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看天根”的本义相去甚远。同其他心学解易者一样,他所在意的只不过是如何以邵雍之说来阐释自己的思想⑤王龙溪亦曾以己意论邵子天根月窟说,其解说亦有违背邵雍本意之处。可参见本人硕士论文《王畿心学易学思想研究》,山东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应当引起注意的是,由上述内容可知近溪曾受到过象数易学的影响。除天根月窟外,近溪还曾谈及卦气:
或曰:“何卦气、岁功之数不同?岂岁功之外又有卦气耶?”罗子曰:“乾、坤主体,坎、离主用,然统总只显出一个阳之纯处、知之明处,则前四卦之二十四爻,皆当主体,而流行化生,亦止三百六十爻,正所谓三百六十日也。”⑥罗汝芳:《近溪罗先生一贯编》,《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24页,第323页。
乾坤坎离四卦每爻各主一节共二十四节、余六十卦每爻各主一日计三百六十日的卦气说,本于宋代先天六十四卦圆图。二十四节为体流行化生三百六十日,隐含着六十卦皆本自乾坤坎离四卦的结论。又,据“乾坤为体、坎离为用”①此可上溯汉易,王龙溪亦主是说。见拙文《王畿心学易学思想研究》,山东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则各卦皆由乾坤二卦所生。此更见乾坤的地位之重②近溪并无系统卦气思想。今本《罗汝芳集》中卦气之论唯此一见。显然,其着眼点在强调乾坤的根本地位,而非热衷卦气和其它象数思想。。
四
同其他所有讲《易》的心学家一样,近溪的易学亦与其心学思想密不可分。尤其是四书五经的彻底打通,更为易学与心学之间的相互诠解提供了学理基础和具体方法。既然“一切经书归会孔孟”,那么以易言心、以心解易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比如,近溪将《孟子》的“良知良能”与《周易》的“易知简能”互训就是一例:
知者,吾心之体,属之乾,故“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属之坤,故“坤以简能”。乾足统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该能,言知则能自在其中。如下文:孩提知爱其亲,知敬其兄,既说知爱亲、知敬兄,则能爱亲、能敬兄,不待言矣。③罗汝芳:《近溪子集》卷射,《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第81页。
在近溪看来,《系辞》“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一句中的“知”和“能”,即是《孟子》所讲的“良知”、“良能”。良知为心之本体,良能是良知的发用,二者的体用关系正如同乾坤二卦的尊卑统从,故《系辞》以知属乾、以能属坤;另一方面,由于乾坤相互涵摄,相应地,言良知则良能亦被包举其中,故心学只言良知即足。
事实上,良知学发展至泰州一脉,学者谈及本体时颇多新论。其中,近溪尤为强调“赤子之心”:
此“知能”二字,本是《易经》精髓,然晦昧不显,将千百年于兹矣。古今惟是孔孟两人,默默打得个照面,如曰不虑而知,其知何等易也。然赤子孩提,孰知之哉?天则知之尔;不学而能,其能何等简也,然赤子孩提,孰能之哉?天则能之尔。④罗汝芳:《近溪子续集》卷坤,《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
近溪对“赤子之心”的提示,极好地体现了其涵化融通四书五经的能力。由于“赤子之心”与仁、孝悌、性善、本心、大人、天命之性等儒家经典中的观念范畴有着先天的紧密关联,故他特将此四字从《孟子》中点出。所谓“赤子之心”,既表现作咕咕坠地即知爱母,又体现为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就《易》而言,一方面,生而爱母体现了“生”与“仁”的通而为一;另一方面,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知能”,即是乾坤的“易知”、“简能”。由此可见,“赤子之心其实就是良知良能,亦即‘孩提良知’。这表明近溪是用赤子之心这一描述性概念,来指实孟子的本心、阳明的良知。”⑤吴震:《泰州学派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页。如同良知即使被蒙蔽亦不曾失却一样,赤子虽生长为成人,但其心从未丧失。《易》云“百姓日用而不知”,即是现实中的人尚未觉察到自我怀具着一颗同于赤子的心。然只一觉悟,便可发现良知原本时时完备、在在俱足:“天下之人,只为无圣贤经传唤醒,便各各昏睡,虽在大道之中,而忘其为道,所以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则许多道妙、许大快乐,却即是相对立谈之身,即在相对立谈之顷,现成完备,而无欠无余。”⑥罗汝芳:《近溪子集》卷御,《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与阳明“心即性”的心性浑一不同,近溪除以“赤子”论“心”外,亦专论“性”。近溪之论性,仍本于其融通经书的一贯诠释思路。在解《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时,他说:
盖伏羲当年亦尽将造化着力窥觑,所谓:仰以观天,俯以察地,远求诸物,近取诸身。……浑作个圆团团、光灿灿的东西,描不成,写不就,不觉信手秃点一点,元也无名、也无字,后来却只得叫他做乾画,叫他做太极也,此便是性命的根源。⑦罗汝芳:《近溪子集》卷射,《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第81页。
近溪认为,不悉心理会得画前之旨,就无法将性命在源头处看个分明。在卦爻皆本于浑沌不妄之太极、太极运化展开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意义上,太极符示着“生生”之源。因而,是太极在创生天地万象、宇宙万有的过程中赋予了人以性命。太极为性之源,即“天命之谓性”。在近溪“生”与“仁”贯通的视域下,人与万物的造化既是“生生”的成果,又是“仁”的呈现。所以近溪认为,谈“性”不可“生”、“仁”相分:
学者读书,多心粗气浮,未曾详细理会,往往于圣贤语意,不觉错过。即如告子此人,孟子极为敬爱,谓:能先我不动心。夫不动心,是何等难事!况又先于孟子也耶!想其见性之学与孟子未达一间,止语意尚少圆融,而非公都诸子之所概论也。今且道“生之”为言,在古先谓太上,其德好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而乾则“大生”、坤则“广生”、“人之生也直”,生则何嫌于言哉?至孟子自道则曰:日夜所息,雨露之养,岂无萌蘖之生?“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是皆以生言性也。嗜则期易牙,美则期子都,为人心之所同然。“目之于色,口之于味,性也有命焉”,是亦以食色言性也。岂生之为言,在古则可道,在今则不可道耶?生与食色,在己则可以语性,在人则不可以语性耶?要之,食色一句不差,而差在仁义分内外,故辩亦止辩其义外,而未辩其谓食色也。若夫“生之”一言,则又告子最为透悟处,孟子心亦喜之,而犹恐其未彻也。①罗汝芳:《近溪子集》卷乐,《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第50页。
在“生”、“仁”相贯的前提下,近溪消解了告子“生之谓性”与孟子性善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的紧张对立。经近溪的重新诠释,告子“生之谓性”的“生”等同于《易》之“生生”;孟子所言“目之于色,口之于味,性也有命焉”,亦与告子“食色,性也”无甚差别。如此,孟子则成了告子性论的支持者。应当注意的是,将“生之谓性”的“生”转义为“生生”,尚不有违于孔门精神;而近溪直下认肯“食色”为性,毕竟在儒家学者中极为罕见。其所以如此,可能是看到了“食”和“色”既是生而即有的先天本能,又是维持和传衍生命的必要手段。因而在关乎“生”的意义上,“食色”便与“仁”一起成为了“性”的内容。当然,近溪的“生之谓性”论一方面是受明道思想影响的反映,一方面是泰州学派重“身”传统的接续,但更多地是其心学特殊旨趣的显现:“重视生机的近溪,不像宋儒那样以天命之性为相对于气质之性的东西,而是以天命之性为虚气之合,即当作与气质浑一的存在。……如果不这样看,那就会失去生机之感通而陷于玄虚。”②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五
上文已言,在近溪看来,学《易》须先明乾坤大义。因乎乾统坤从、相涵互摄,要之,则《易》统于乾卦:“盖《易》之卦,虽六十有四,而统之则独在乾坤,乾坤虽云并列,而先之则又在于乾。”③罗汝芳:《近溪子续集》卷坤,《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第251页,第281页。在四书五经融通的视域下,“乾以易知”的“知”即“良知”、“赤子之心”。《易》以乾为首,正对应心学以“良知”、“赤子之心”为本。所以,近溪多以乾坤二卦和生生之旨论心性。当然,亦偶有以乾坤论功夫之时。如“自然却是工夫之最先处,而工夫却是自然之以后处,次第既已颠倒,道蕴何能完全?故某尝云:为学必须通《易》,通《易》必在乾坤,若乾坤不知合一,而能学问有成者,万万无是理矣。”④罗汝芳:《近溪子集》卷乐,《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第50页。此即是以乾坤合一言自然与功夫之关系。
不过,一如此前心学易的传统,近溪更多地是以《复》卦论功夫:“《易经》一书,只一复卦,便了却天地间无限的造化;颜子一生,只一‘庶几’,便了却圣神无限的功夫。”⑤罗汝芳:《近溪子集》卷数,《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心学以本心、良知为人人皆有、不可泯灭,以去除障蔽、复还本体为功夫,故心学易皆从“复还本体”的角度解《复》,近溪亦如是:
谓之《复》者,正以原日已是如此,而今始见得如此,便天地不在天地而在吾心,所以又说:“复以自知。”“自知”云者,知得自家原日的心也。”⑥罗汝芳:《近溪子集》卷射,《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原日的心”即“赤子之心”。赤子之心生而皆有,成人之后亦未丧失。所以,功夫之要便在于知晓体察到原本生而即具的赤子之心。在近溪看来,《系辞》三陈九卦的“复以自知”,旨在点示“复还本体”的功夫不过是让百姓“自知”其原本“日用而不知”的赤子之心而已。这样的功夫,显然是以良知现成为基础的。在赤子之心时时俱在、良知现成完备的前提下,近溪并不以事事物物上为善去恶或归寂主静中涤除障蔽为功夫大要,他强调由自知而达本体的“觉”、“悟”。有如一阳初动即纯阳之始,一旦觉悟便浑然皆是: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然则圣人性反之觉,又不总是《大易》之逆知也耶?⑦罗汝芳:《近溪子续集》卷坤,《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第251页,第281页。
复之为卦,学者只一悟透,则此身自内及外,浑是一团圣体,即天地冬至阳回,顽石枯枝,更无一物不是春了。⑧罗汝芳:《近溪子续集》卷坤,《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第251页,第281页。近溪解《复》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从五经四书的互训出发对《论语》的“克己复礼”予以了新的阐释:
曰:“‘克去己私’,汉儒皆作此训,今遽不从,何也?”
罗子曰:“亦知其训有自,但本文‘由己’之‘己’,亦克己‘己’字也,如何得做“由己私”?《大学》:克明德,克明峻德,亦克己‘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峻德’耶?况克字正解,只是作胜、作能,未尝作去。今细玩《易》谓‘中行独复’,‘复以自知’,浑然是己之能与胜处,难说《论语》所言,不与《易经》相通也!”①罗汝芳:《近溪子集》卷礼,《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第26页,第28页。
近溪认为,观《大学》文辞可知“克”应作“能”,而非“去”义;“己”也非“己私”,否则“为仁由己”便讲不通。从《易经》“复以自知”、“中行独复”明示出的人之昂然主体性和充足能动性来看,所谓“克己复礼”,应解为“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以达到复礼的目标。”②吴震:《罗近溪的经典诠释及其思想史意义——就“克己复礼”的诠释而谈》,载《复旦学报》2006年第5期。显然,此一训释是以“《论语》与《易经》相通”为前提的。若究其源,《论语》“克己复礼”之“复”亦本于《易经》:“复本诸《易》,则训释亦必取诸《易》也。”③罗汝芳:《近溪子集》卷礼,《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第26页,第28页。
顺着以《复》为“复”的思路理解,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无疑点明了《复》与仁、礼的紧密联系。近溪指出,孔子一生最重“仁”、“礼”二字,细论起来,“仁是归重在《易》,礼则归重在《春秋》。”④罗汝芳:《近溪子续集》卷坤,《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页。在总体上,“仁是归重在《易》”可以通过“生”、“仁”相贯获得理解;具体而论,又以《复》卦对“仁”的开示最为生动、最具代表性:“《易》所以求仁也。盖非易无以见天地之仁,故曰:‘生生之谓易’,而非复无以见天地之易,故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⑤罗汝芳:《近溪子集》卷礼,《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第26页,第28页。在《复》为功夫的意义上,“复”的核心在于自觉“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与生俱来的孝父爱母是仁,而赤子之仁性又源于天地大德生生之仁的天命。所以,《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一句最好地概括了《复》卦“仁”的内蕴。因为“天地之心”,既是现实人生当下觉悟到的赤子之心,更是接通上达的宇宙法则和天地之德。
至于《复》与礼,近溪云:“《礼》曰:‘天地之节文。’而又曰:‘礼时为大,顺次之’。夫复则天,天则时,时则顺而理,顺而理则动容周旋,四体不言而默中帝则,节而自成乎文矣。复在乎己也,夫安得不动之而为礼也耶?是以孔孟立教,每以仁礼并言。盖仁以根礼,礼以显仁。”⑥罗汝芳:《近溪子集》卷射,《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人一旦复其赤子之心,则良知时时见在、处处显用,自然便会趋时而作、依理而行,在不思不虑间契合天地之文、自然之则。所以,“仁”、“礼”皆在《复》卦之中,二者亦可互诠互显。
六
自《周易》经传问世起,“时”就成为了易学的重要概念。近溪不但继承了言《易》重“时”的易学传统,更将“时”涵化于功夫之中:
易也者,变通以趋时者也。六十四卦,圣人示人习时之大纲,三百八十四爻,则其节次也。……其初则观天之时,以通吾心之时;其既则以吾心之时,而希天之时;及其终而纯且熟也,则天之时即吾之时,吾之时即天之时。……善学《易经》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学论语者,先《时习》一章。⑦罗汝芳:《近溪子集》卷数,《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185页。
《易经》“所谓‘时的哲学’,乃是以一种特殊的‘时’的智慧和视野,观照、理解乃至回应大宇宙和现实社会人生的哲学。此所云‘时’,不可简单理解为时空之时”,而“是一个在实然世界基础上,着重指涉价值世界的范畴;简言之,它指涉着人所值的特定时空下,大宇宙和社会人生中各相关因素互动消长的总体格局与情状,及在此总体格局与情状下的事事物物。”⑧王新春:《〈周易〉时的哲学发微》,载《孔子研究》2001年第6期。以此观之,“变通以趋时”即是指人应在宇宙、社会、人生的当下格局中定位自我,从而使一己之行为全然契合于“时”。这便要求人对当下所处的“时”有一清醒认知,继而见几而作、相时而动。这样,“时”就具有了功夫的意义。近溪更将“习时”二字相连,以凸显“时”的功夫义。在他看来,《易》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是圣人对“习时”之功的展示。因生熟不同,此一功夫又分三层渐进:最初着眼于知时而后行,宛如深渊薄冰;其次则用力于我行以合时,仍有自我提撕之意;待功夫达至纯熟之境后,便可在不思不虑中时我无间。
基于对“时”的这一理解,近溪重释了“学而时习之”:
圣人之学,工夫与本体,原合一而相成也。时时习之,于工夫似觉紧切,而轻重疾徐,终不若因时之为恰好。盖因时,则是工夫合本体,而本体做工夫,当下即可言悦,更不必再俟习熟而后乐也。①罗汝芳:《近溪子集》卷射,《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近溪不以《论语》首章之“时”为“时时”,而取“因时”义。在他看来,二者颇为不同:“因时”是良知自然完备,功夫只在当下顺适、肯认本体;“时时”则未免过于把捉,而不知“即本体便是工夫”。
由此可知,近溪对“时”的理解亦是在五经四书的融通下获得的。一方面,他以《易》“时的哲学”观照《论语》而论功夫;另一方面,他又以功夫主张诠解《易》之“时”义。此外,他还将“时”与“复”相联:“复而引之纯也,则为时;时而动之天矣,则为复。时,其复之所由成,而复,其时之所自来也欤!”②罗汝芳:《近溪子集》卷礼,《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在近溪的心学易学中,“时”、“复”皆言功夫。“复”必由“时”而成,唯“时”方可达“复”。二者亦是融通的。
结语
以上就是近溪心学易学的主要内容。《一贯编》中的如下文字,颇具概括性地提示出近溪心学易思想的内在逻辑,可视为近溪易学的总纲:
易以乾为体,乾以复为用。夫乾纯粹以精,而天地人之性之至善者也。……夫子五十学《易》,继乾坤资始资生,而昌言曰“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谓易”。夫子以易为学,以学为教,易则生生,生生则日新,日新则学不厌,学不厌则教不倦,不厌不倦则其德曰仁。夫唯仁,斯其人曰圣乎!故夫子示天下万世求仁之旨,必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要之,孩提知爱,少长知敬,未学而嫁知养子,是人人能仁者也。人人能仁,是乾乎乾而机自不息,性乎性而生恶可已。所谓万物皆备,我可人,人可天,不越一己而天地人物一以贯。故己能己焉,是谓“中行独复”,中行独复,惟颜氏之子庶几。夫子所以语之曰“克己复礼”,又曰“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信哉,复其见天地之心矣乎!③罗汝芳:《近溪罗先生一贯编》,《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325页。
近溪在延续此前心学家“以心解易、以易论心”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心学易学的总思路,是先以太极生生为画前本旨,进而以乾坤相涵论心性,最后再以复卦统言功夫。其最具特色之处在于:他将此前学《易》悟得的“四书五经通而为一”作为诠释的总原则,始终贯穿在“生生(本旨)——乾坤(心性)——复(功夫)”的理路演进之中。可见,近溪不同于程朱“理学”重分疏辨析的路数,而与明道、阳明重收摄统合的风格相类。如果说阳明学因从朱学中流转而出,故意图以心学融通《大学》三纲八目的话,近溪则不止于此。他欲达成的,是一个建立在彻底打通、彼此开放的儒家四书五经基础上的一体圆融之学。正是这一背景,使近溪论《易》多与其它经典相联,其易学亦因此而呈现出不拘一格的浑融气象。
从留存的资料来看,近溪多有论《易》之语。然而,其中绝大部分不外乎“生生”、“乾坤”、“复”三义。至于《易》的其它内容,皆被近溪舍略。因其易学论述着眼于阐发宏观意义的儒家精蕴,所以近溪虽言卦,却不以明象训辞为的;虽论《易》,然不以解《易》为归。通观近溪论《易》之语,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能够概括其心学易学思想的代表命题。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近溪的心学易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心”有余而“易”不足。
[责任编辑:杨晓伟]
B221
A
1003-8353(2012)06-0010-0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易学研究”(07JJD720041)。
张沛(1983-),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