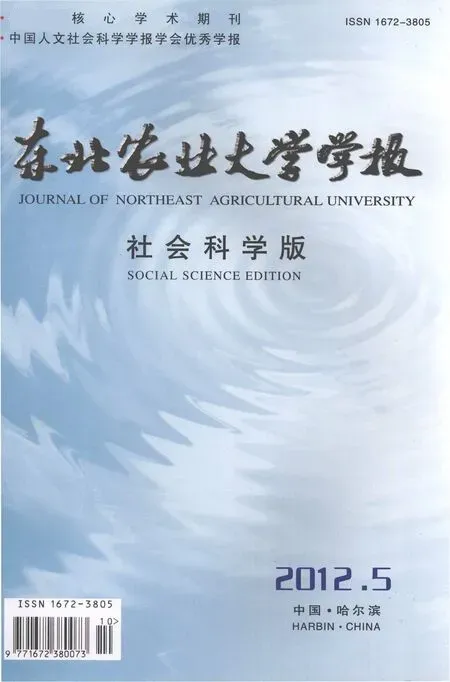认知诗学视域下的文学阅读
李良彦
(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认知诗学的产生为跨学科的文学文本研究和语言心智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认知诗学理论力图避免割裂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批评理论中“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者关系,而从整个文学阅读的过程来重新审视并评价。
一、文学阅读认知诗学分析的理论基础
文学阅读分析在过去的理论研究框架下主要侧重于审美效果的分析,侧重于反应作者的写作意图、作品文本的自身意义以及读者对作者和文本知识的机械反映。从认知诗学的角度理解,文学阅读的具体过程恰恰是研究的主体对象。利用一些研究方法和相关理论对阅读的心智过程进行研究,通过对过程的分析来展现作品文本的意义,这是认知诗学视域下文学阅读分析的重点。何为心智?心智即指人们对已知事物的沉淀和储存,通过生物反应而实现动因的一种能力总和。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不是被动的刺激物接受者,人脑中进行着积极的、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这个加工过程就是认知过程。”文学语言对现实的表征上依赖于大脑对现实的表征,通过认知过程,语言中的表征延伸了心智表征中诸如信念、愿望和意向等基本表征。对阅读的心智过程分析可以跳出传统文学阅读分析的藩篱,将分析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综合以上对认知诗学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作者心智的产物,对作品文本的理解是读者心智的产物,这两者都与彼人所处的客观世界和彼时所感的社会文化紧密相关。认知诗学简化了阅读的推理过程,澄清了文学的内容和结构。
二、以认知诗学理论分析文学阅读过程
在解析文学阅读过程时,认知诗学的几个主要理论框架,包括图形—背景理论、概念隐喻和图式理论,成为分析认知方式对文学阅读影响的主要工具。
1.以图形—背景理论分析文学阅读过程
心理学家认为,图形指认知概念中突出的部分,具有完整的形状和结构;背景是为突出图形起衬托作用的部分,细节模糊且结构未分化。当我们在观察某一物体时,会把这个物体作为知觉上的突显,即图形;而把物体所处的环境当做未分化的背景,这就是突显原则。研究表明,确定一个物体为图形应遵循“普雷格朗茨原则”。图形必须恰当地包含在背景中,图形通常是具有完形特征、面积或体积小,容易移动或运动的物体;而背景则相反,面积或体积大,位置不易移动,较为固定。图形没有已知的空间和时间特征可确定;背景具有已知的空间和时间特征,可以作为参照点用来描写、确定图形的未知特征。这是图形和背景的定义特征。运用到语言学领域中,图形—背景理论表现为一种空间组织原则,比如“桌上有本书”和“书从桌上掉下来”两句话中,书是图形,桌子是背景;书与桌之间的空间关系是通过介词“上”和“下”体现出来的。图形—背景理论之后的研究则深入到对复杂句的分析,逐渐表现为一种语言组织的基本认知原则。图形及背景的定义特征和特点,在我们解释语言现象时可以提供很好的辅助工具。在分析文学阅读的过程中,图形—背景理论也可以应用于对语篇语境、文化语境等要素的辩证分析。下面运用图形—背景理论来解读美国表现主义画派的著名画家、诗人和散文家麦克司·威伯(Max Webber)的著名短诗《夜》(Night),试图通过对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来探讨该理论在文学作品解读中的应用。
麦克司·威伯创作的诗歌数量并不是很多,却都明显带有生动形象的画家风格。1914年,他的诗歌集《立体派诗篇》问世,《夜》(Night)便是其中的一首。原文如下:Fainter,dimmer,stiller,each moment,/Now night.诗作篇首的两个单词fainter和dimmer,遵循了诗歌简洁明快的原则,最简化地处理了“it’s getting fainter and dimmer”的含义,最大化地凸显了比较级形式中所体现的事物的逐步变化的功能,通过凸显,产生了图形的特征,进一步刺激读者的知觉,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结合了每个人自身的认知经验,将栩栩如生的夜幕降临的镜像投射到读者的大脑中。第一行诗中描绘夜的特征的几个形容词的比较级的并置使用,既描写了夜之属性不断向最高级进行推演的过程,又为读者营造了夜色逐渐凝重的背景,为第二行诗作对图形进行凸显做好了铺垫。
“Now night”看似突然的结尾,却正是诗作运用“图形—背景”理论的点睛之处。诗作的第一行用 fainter,dimmer,stiller来刺激读者的视觉和听觉,用each moment描写夜之降临的动感过程,Now night再次重新刺激读者的视觉知觉,同时用词的最简单的形式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凸显于听觉,这种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再次赋予night图形的意义。根据“图形—背景”理论,人们将易移动的物体视为图形,比较级产生的动感过程为读者阅读第一行诗时确定图形创造了条件;而相对不动的night易被视为背景,在背景下感知光的暗淡,周遭静谧的景象。而第二行诗的听觉凸显,又使第一行诗已经产生的“图形—背景”顺序具有了可逆的特征,通过图形和背景的重组,读者认识的范围被扩大,夜和其特征的“图形—背景”相互转化,进一步表现了诗人的认知经验。
2.以概念隐喻理论分析文学阅读过程
作为一种认知工具和认知资源,将概念隐喻应用于文学阅读的分析中,既可以通过分析隐喻机能来理解阅读对象,又可以具体地研究阅读过程。诗歌作为文学作品中较多地运用隐喻的文学形式,为此类认知工具的具体应用提供了适宜的载体。因为诗人需要通过短小的篇幅将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表达出来,对隐喻的使用便成了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之一,可以说,诗歌和隐喻几乎是不可分离的。
以美国诗人艾米莉·迪金森为例,她所创作的诗歌很多是以死亡为主题的,她也因此被称为“美国诗坛上的白衣修女”。在其最著名的《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这首诗中,诗人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神秘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她用丰富的想象和深邃的思索对死亡这一主题进行分析,并且用到了很多概念隐喻来对死亡进行独特的阐释,所以要想理解这首诗就必须理解其中的隐喻。
第一诗节中,“Death is departure”这一基本概念隐喻首先被表达出来。由于死亡被比作离开,所以“离开”这一概念域中马车、车夫等工具和方式的延伸则为死亡提供了表达。读者通过对离开这一概念的原始认知,理解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即便在第一诗节中并未提及死亡的字眼。
第三诗节中体现的基本概念隐喻有两个:“people are plants”和“life is a day”。人们对植物生命周期里发芽、开花、结果、枯萎的循环和每天黎明、中午、傍晚、深夜等渐变过程的认知经验,使读者非常自然地理解了人类童年、青年、中年、暮年和生命的诞生、成熟、衰老、死亡的过程。诗人也是依赖类似的认知经验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读者与诗人类似的认知体验为读者文学阅读的过程建立了互通平台。
诗作的最后三个诗节继承并发展了之前的概念隐喻。根据“life is a day”的概念隐喻,死亡被表达为夜晚,夜晚露水的寒意反映了对死亡的恐惧。人们认知过程中的寒意彻骨和毛骨悚然在知觉层面达到统一。对“death is departure”这一概念隐喻的发展是“death is a destination”。人的一生最终都将归于死亡,就像回家一样,归宿是最后的目的地。与此类似,“house”,“roof”,“cornice”等意象均可以通过读者的认知,在阅读过程中被解读为墓室、坟冢和墓碑。这也正反映出作者认知过程中叶落归根,人生最后的归宿是泥土的体验。
以上从认知诗学的角度,对《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一诗中的概念隐喻进行了认知分析。通过研究可以看出,文学作品中许多看似新奇的隐喻,其实背后隐藏的都是我们已经常规化了的概念隐喻的衍用,这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有着重要的作用。
3.以视点为代表的图式理论分析文学阅读过程
在解析文学作品产生的原因和背景的同时,认知诗学更侧重于从深入阅读者心智的角度探察读者如何理解文本。认知心理学中图式的概念也被运用于认知诗学讨论并研究的过程中。Stockwell认为,文学具有“图式”,具有增长性、调节性和重构性。其理论应用于文学领域时,可分为三类图式,即世界图式、语篇(文本)图式和语言图式。通过图式的建构,有助于解释不同的读者对同一文本做出不同的解读的文学阅读现象。在认知诗学领域里,视点是一种特殊的图式,是制约语篇深层机构(即语义)的一种图式,反映人们看待对象世界的角度和态度,支配着对象的选择与组合,从而又影响语篇表层结构的组织。视点可分为时空视点、观念视点、叙述视点和知觉视点。作为认知处理过程中的一个要素,视点在认知处理过程中反映着认知。在文学阅读过程中,视点的选择和处理是一种认知过程,它涉及脚本、图式、框架等多个认知方式的交叉运用,阅读者对视点的把握程度影响着其把握作者或叙述者观点和态度的精准性。因此,解读以视点为代表的这一类图式对文学阅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认知处理的过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公认的20世纪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在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中,作者通过独特的叙述技巧,通过视点的转换、选择和安排,体现出了叙述者和作者的心理认知过程。《洛丽塔》选择主人公死囚亨伯特第一人称的叙述视点,将其作为作品通篇主要的叙述者,以其入狱后的自白为叙述载体,令读者必须通过亨伯特的思维,才能了解到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亨伯特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和参与者,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能够掌控其所见所想,随意地控制叙述的时空视点、观念视点和知觉视点。而另一主人公洛丽塔由于没有出现在叙述者的地位上,只能作为亨伯特的叙述对象而处于被动位置。这种处理方法使读者只能听到洛丽塔被亨伯特思维过滤后的言语,比如洛丽塔勾引了亨伯特,只能通过亨伯特的叙述间接地体会洛丽塔的感受。这种叙述被称为不可靠叙述,因为读者无法听到洛丽塔自己真正的声音,无法直接深入其内心世界。使读者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不得不跟随叙述者视点的转变,适时调整自己的阅读视点,揣摩亨伯特言语的真实性,用谨慎、怀疑的眼光去分析文中所提供的信息,去解读悬念,使读者达到审美目的。
三、结语
认知科学包括与认知有关的各个方面的科学,如最基本的记忆、情感、创造力、模仿、投射以及中枢神经对运动的控制,当然还包括较高级别的语言运用、文字表现和逻辑推理等活动。认知诗学观点认为语言与现实世界没有传统的直接的映射关系,每一种情景都可以根据不同的图形—背景、概念隐喻、脚本与图式、框架与文化模型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认知诗学理论正处于不断走向成熟的时期,其理论系统逐步发展完善。认知诗学将逐渐成为语言学家研究文学阅读过程的工具之一,为语言学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平台。通过认知诗学进行文学阅读分析,是对阅读心智过程的分析,进而展示出文学文本的意义。同时,利用认知科学有关的研究方法,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在传统文学阅读中审美地分析文学文本的基础上,为文学阅读提供一条新的分析途径。认知诗学对文学作品的全新解读方式不但会丰富文学和语言学理论,还将把全方位、多层次的视角引入到文学欣赏中去。
[1] Tsur,R.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M].Amsterdam,London,New York & Tokyo:North Holland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1992:35-36.
[2] Stockwell P.Cogni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M].London:Routledge,2002: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