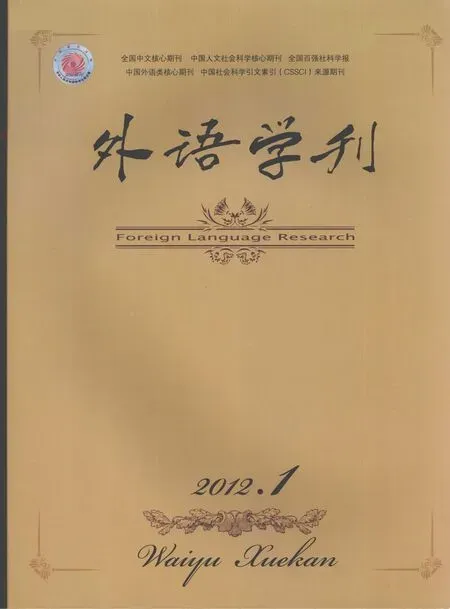论“第三空间”翻译文化资本运作*
曾文雄
(广东商学院,广州510320)
1 引言
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发挥着多重功能:第一,作为殖民化的工具,构建殖民者的文化身份,这与市场、机构的显性和隐形控制相关联;第二,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之后,成为维护文化不平等的“避雷针”;第三,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过程的工具,翻译成为被殖民者用来抵抗殖民、摆脱殖民者的枷锁和削弱文化霸权的途径。(Robison 1997:31)后殖民翻译理论代表人物尼兰贾娜等持“翻译作为帝国的殖民工具”的观点(Niranjana 1992:21);代表人物巴西坎波斯(Haroldo de Campos&Augusto de Campos)兄弟的食人主义(cannibalism)则持第三种观点。面对上述殖民与反殖民的双峰对峙,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探索民族文化融合的途径。有学者指出,未来翻译研究“应重视各文化资本构成的文本,把握克服文化融合障碍的方法,”“必须找到一种如何翻译它者文明中文化资本的途径,”“调查不同文化资本跨越文化疆域的模式”。(Lefevere& Bassnett 2001:10-11,138)本文试图结合“第三空间”,考察后文化资本的流通方式及其制约因素,探索去殖民化和文化资本跨越疆域的运作方式,进一步拓展文化构建、文化融合与发展的途径。
2 “第三空间”与翻译文化资本的本质
后殖民代表人物霍米·巴巴曾指出,“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会打开一片‘填隙式空间’(interstitial space)、一种填隙的时间性,它既反对返回到一种始源‘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也反对放任于一种‘过程’中的无尽的分裂的主体”(Bhabha 1994:112)。这里的填隙的、杂合的(hybrid)和居间的空间(in-between space)也就是“第三空间”。巴巴指出,文化的“我者”与“他者”需要通过“第三空间”来实现交流,这个“第三空间”不仅反映语言的一般条件,也反映了话语的特定内涵,而这个内涵囿于自身所无法意识到的。(Bhabha 1995:207,孙会军 2005:175)“第三空间”是文化异质得到传播的前提,它可以化解冲突和不稳定因素,并瓦解两极对立的政治壁垒。根据巴巴的观点,所谓“文化定位”,“既不是定位在后殖民地宗主国文化的普遍性上,也不是完全定位在弱势文化的差异性上,而是定位于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第三空间’”。(孙会军2005:176)第三空间“既非这个也非那个(我者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它致力于突破种族差异、阶级差异、性别差异和传统差异中文化认同的“阈限”(liminal)。这个阈限是一个杂合的场所,它见证了文化意义的生产,并与杂合共存。“文化活动的条款,不论是对抗性的还是契合性的,都是在演现中被生产出来的。对差异的表述决不能被草率地解读为固着于传统中事先给定的种族或文化特性的反映。从少数族裔的视角来讲,差异的社会发声是错综复杂、流动不居的协商,它寻求授权与出现于历史转型时刻的文化杂合性”。(Bhabha 1994:2,生安锋2004:28-29)第三空间正承担着协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以及因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对抗,为跨语际的异质文化间的争夺提供可对话的“居间”。
显然,第三空间中的文化既不是原语文化也不是译语文化,而是融合两种文化的杂合体,而且,强调殖民文化与被殖民文化相互渗透的特征。换言之,翻译是一种文化间性(in-betweenness)的行为,这种间性不是简单的将两种文化或语言相加,而是在杂合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文化形式。第三空间承担这种间性功能,它“既不是自我文化,也不是它者文化,既不是‘原语’,也不是‘译语’。……它将翻译活动看做是互动的过程,是矛盾凸显和寻求合作空间的交汇处。在第三空间中的协商被看做是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译者和其他委托人对译文的接受进行讨论和处理翻译的场所。……被看做是跨文化和社会互动的潜在形式,这个空间以启发式手法形象地演示翻译的转换过程以及与相伴着的语境和这些转换涉及的条件所发生的变化”。(Wolf 2002:188-190)显然,“第三空间”不仅仅作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场所和条件,还是促进特定文化的非同质性(non-homogeneous)交流的策略。
翻译作为文化资本运作的主要途径,是一种跨文化行为,不仅构建自身话语而且传播文化资本、建构文化资本和民族文化,进而促进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与创生。文化资本包括体化文化资本(embodied)、物化文化资本(objectified)和机构文化资本(institutionalised)三大类。(Bourdieu 1986:47)体化文化资本指一套内化的语言、技能、情趣、行为和知识系统,通过生物体本身表现出来,如知识、技能、语言、情趣等;它包括语言资本(linguistic capital),即掌握某一种语言,作为一种交际手段和表述方式。物化文化资本指可传递的、以实物形式体现的物品,如译作、图书、各类媒介。机构文化资本指学术资格、奖励等各类机构认定的资格证书。(刘永兵 赵杰2011:123)换言之,文化资本主要存在于精神、文化及机构等领域,体现文化的主体化、客体化与机构化等特征,是社会体系中的一种存在形式。我们认为,翻译文化资本指翻译、翻译行为与译作所承载的隐形或有形的资本,包括翻译自身及其载体,且应在人类生存的社会里得到正确的流通。
“就翻译文本而言,无论其目的是为了提供信息、娱乐,或者兼顾两者,或者实施劝谕等功能,它均被看作是某一文化或‘世界文化’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可以通过翻译的方式在各民族文化之间以及某一特定的文化当中得到交流、传播与接受。”(Lefevere&Bassnett 2001:41)“翻译文本一旦被看做是文化资本,它将以多种形式不断影响其他类型的文化资本。”而且,“正是文化资本使翻译明显地被看做具备建构文化的功能,它可以通过文本间的文化资本的协商来实现这种构建;当然,也可以借助翻译策略,使一个文化语境中的文本渗透到另一文化文本中,并在它者文化中发挥文化构建的作用。”(Bassnett&Lefevere 2001:5-7)文化资本在跨越民族疆域以及流通、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1)需要,指读者需要或听众需要;2)翻译的赞助人或发起人;3)原语和译语文化、语言所拥有的相关声望”。(Lefevere&Bassnett 2001:44)当然,诸如译者动机、规范、诗学、意识形态等因素以及各种翻译选择均可能影响文化资本的运作。后殖民语境、文化帝国语境中的翻译活动更显著地受到文化霸权、文化帝国等因素的干涉,致使翻译活动中出现了不平等的语言、文化交流。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文化构建要求我们思考文化资本运作的有效方式。
3 “第三空间”作为文化资本实施文化构建的场所
翻译在文化构建的过程中受到诸如主流文化、主流规范、意识形态、赞助人等翻译主客体代理的干涉,因此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各具特色的文化资本运作模式,以及多样的文化构建目的。就中国翻译传统而言,粗略地看,文化资本运作的动机模式可以归纳为“弘扬宗教型”、“科技会通型”、“兴国启民型”等,并采用“文化顺应型”和“文化会通型”、“借题阐发型”等翻译模式。西方翻译史也证明了各时期文化资本的运作方式和目的具有共性、异性或多样性。例如,爱尔兰文学的后殖民翻译在殖民主义时期,译作以英国规范为指向,迎合殖民者的文学规范和品味,删除和压制那些不符合英国规范的但具有爱尔兰特色的文化。在民族主义时期,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认为,爱尔兰文化完全符合英语文学的规范,并非如殖民者所贬低的那样庸俗不堪。在非殖民化时期,力求以真实的面目展现爱尔兰文学和文化,拒绝以任何理由对原语文化进行删改。(Tymoczko 1999)显然,在不同的翻译语境有相同的、相似的或各异的翻译选择或文化取向。就殖民文化话语构建而言,翻译是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被强权者所利用,其运作方式是多样的。根据尼兰贾娜的举例,英译作品通过改写来构建“东方”形象,并以之代表“真实”(reality),将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于人。(Niranjana 1992)以上表明,一方面殖民者在实施文化资本运作时要求被殖民者学习或模仿帝国文化,遵循殖民帝国的价值观、诗学、规范等,翻译成为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统治工具。另一方面,被殖民者在模仿或吸收殖民者文化的同时,以“本土”文化抵抗殖民者的主流文化,丰富自身的文化构建。
若将翻译作为“去殖民化”的文化资本运作工具,其目的是消解他者文化带来的显著冲击,且在妥协、吸收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本土文化。例如,巴西坎波斯兄弟的食人翻译理论将翻译视为食人的方式,视翻译为一种获取力量的行为,通过吞噬自己的敌人或尊敬的人,从中获取力量;一种滋养行为,即生命力量源于“吞噬”原文,使译文从中获取语言和文化营养;一种积极的行为,原文通过翻译后得以重生;一种输血行为,译文从原文中吸取血液,使原语文本注入新的活力。(Munday 2001:136-137)在这场后殖民世界的变革和斗争中,被殖民者通过翻译的创作使自身从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改变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为建立新的世界和变革注入源泉,不断构建和丰富自我文化身份。
上述表明,文化资本的输出与输入具有操控、压制、抵抗、妥协、顺应等特征,其文化构建并非是机械地和简单地进行。面对语言、文化不平等的两极,针对如何使各民族的文化资本运作获得互动与交流的场所,实施文化构建并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一些学者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基于欧美的翻译语境,韦努蒂提倡“异化”或“抵抗”式的翻译方式来处理民族中心主义等问题;尼兰贾娜试图通过“重译”(retranslation)的方式翻译印度人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文本,以改写殖民主义的“属下”形象,以推进去殖民化的进程。(Robinson 1997:89-92)巴巴则将“第三空间”引入文化资本的运作中,致力于推动“他者”与“我者”的文化融合。“第三空间”的翻译具有“可翻译的”(translational)和“跨民族的”(transnational)特征,文化资本的高效流通要求灵活地运用杂合等翻译策略。
“杂合”是“殖民权力生产力的标志,表现它不断变换的各种力量和稳定因素,作为一种策略性的方式抵抗压制的过程。”(Bhabha 1994:112)杂合的过程是“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合的过程”(Bhabha 1994:55),是殖民地和弱势文化颠覆、瓦解文化霸权的一种抵抗性策略,不过,这种抵抗并非是直接的简单的否定或拒绝,而是一种话语、文化的杂合,它赋予新的内涵,成为意义与表述的新形式。显然,它是两种文化或多元文化的妥协结果,也是跨文化障碍的自然结果。杂合的新内容也许不可辨认(unrecognizable),以至模糊了宗主国的语言、文化与殖民地语言文化之间的界限。由杂合构建起来的第三空间,动摇关于“霸权”、“始源”(originality)的信念,旨在瓦解帝国主义话语所隐含的优越性。文化资本正是借助一个模糊的、发声的“第三空间”,依靠多样的翻译策略或形式来跨越民族疆域,使各民族文化资本拥有可沟通与传播的场所。
广而言之,翻译常被看做是杂合认同的过程,或者说,所有的译作都是混合体,因它保留原语的一些或全部特征,另外,它经历多方的合力书写,是赞助人、读者、译者、代理人、交际双方的语言和文化地位等因素共谋的结果。因此,文化资本运作不仅要求顺应性地使用翻译策略,还应关注其他的互文关联层面,包括语言、文化的差异、读者的接受性、赞助人、意识形态、权力、诗学、规范等对文化资本构建的影响。在第三空间的观照下,意识形态、赞助人、语言等翻译层面的重要性已被重新分配。落实在语言层面,语言的重构旨在为深层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重建,因为“语言就是人,人就是语言”(李洪儒2007:11);语言必然具有民族性和社会性,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心理等各个层面相关联。翻译中的语言民族主义不利于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不利于本土语言和本土文化的丰富与发展,并威胁到语言与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后殖民的语言民族主义表现为过分地强调本民族语言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以及优越性,因此,文化资本的运作必然要改变本土语言和后殖民世界强势语言(例如英语)的不平等状况。西方强势文化方输入弱势文化的行为中应保持原语文化资本的语言异质;而对殖民地输入强势文化资本而言,则应对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文化进行理性处理,使西方语言或文化适当“本土化”,使两种语言达成融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殖民化的冲击。
翻译长期被置于西方文化中心(Occidentalism)的框架中,在实施民族文化构建的过程中,文化资本运作要求剥去民族中心主义的标签,双方展开协商与对话。“其结果既可以避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吞并,还可以避免弱势文化变成新的强势文化”(孙会军2005:176),避免形成新的殖民语言和文化帝国。在这样的理念观照下,同样可以避免强势文化资本吞并弱势文化资本。即使在文化帝国或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资本的运作要求冲破固有的文化霸权或文化封闭,防止“民族中心论”或者“单一文化论”,避免“一种文化控制它者文化”,倡导多元文化共存。文化“全球化”时代促使文化及文化资本不断走向国际化,这并非意味着文化的单一性或一致性。“第三空间”本来就隐含介入(intervention)的角色,要求两极之外他者的介入;同样,文化资本的运作也要求两极之外的他者介入,以消除文化的二元对立(cultural binarism)。而且,文化资本是翻译多元主客体声音的混合体,要求翻译的主客体超越巴巴的“第三空间”,进入更高层次的和合文化空间,消解文化异质在接触与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一致性。
在后殖民的自然产物“第三空间”的启发下,当代的文化资本运作应打破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与观念,削弱边缘-中心文化的相互渗透,要求在原语文化资本和译语文化资本之间构建和合的文化生态空间,使“他者”与“我者”文化实现协商式翻译。这种和合文化生态理念具有文化交互性(interculturality)的特征,让各民族文化资本既是给予者又是接受者,指向文化资本运作的终极目的,即通过翻译作为文化资本的运作,使各民族文化通过翻译达成会通、融合与创新,实施文化构建,甚至超越自身或他者文化。对中西文化资本融合的途径与目的,徐光启是这样论述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转引自陈福康1992:64)。因此,在推动文化资本跨越民族疆域并实施文化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应站在沟通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立场,遵循“谐同和异”的翻译原则,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对待各种异域语言和文化。(朱安博2011:120-123)值得重视的是,实施民族文化构建的文化资本运作必须有翻译伦理的介入,即翻译主体应遵循各种翻译伦理或翻译行规,并对翻译主客体代理或代理人负责,合理实施互文顺应的翻译选择,使翻译文化资本在实现最大化效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满足各翻译主、客体的期盼。
4 结束语
“第三空间”一方面帮助弱势文化或边缘民族摆脱身份压制和文化遏制,另一方面惊醒强势文化意识到其自身文化的异质性;促使文化资本跨越民族的疆域,使文化协商与文化融合获得发生的场所。虽然“第三空间”是殖民地语言和文化与宗主国主导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对峙的结果,但是这种观念启发当代文化资本如何在不平等或不平衡的文化、经济、权力关系中实施文化交流。在当代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资本的理想运作与流通不仅要突破二元对立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模式,还应超越译语文化语境的读者需求、语言和文化的地位、赞助人以及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等因素的制约;要求各文化实体持开放的胸怀,本着平等的、相互尊重的文化态度,共同构建相互共存、相互协商的空间。当代的文化构建必然要求我们以超前的文化意识、文化政策来引领翻译文化资本的输入和输出,以和合的语言生态和文化生态理念引导多元文化的世界,寻求和合发展的空间,合力创出一条通向各民族文化融合、创生与发展的大道。
李洪儒.意见命题意向谓词与命题的搭配——语言哲学系列探讨之六[J].外语学刊,2007(4).
刘永兵赵 杰.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外语教育研究与理论建构的社会学视角[J].外语学刊,2011(4).
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4.
孙会军.普遍与差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朱安博.翻译中的“同”与“异”之辩[J].外语学刊,2011(5).
Bhabha,H.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4.
Bourdieu,Pierre.The Forms of Capital[A].In J.G.Richardson.Handbook for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C].High Wycombe:Greenwood Press,1986.
Lefevere,A.& S.Bassnett.Where are we in Translation Studies[A].In S.Bassnett & A.Lefevere.(eds.).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Shanghai:SFLEP,2001.
Munday,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1.
Niranjana,Tejaswini.Sitting 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and the Colonial Context[M].Berkeley&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Robinson,Douglas.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M].Manchester:St. Jerome,1997.
Tymoczko,Maria.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M].Manchester:St.Jerome,1999.
Wolf,Michaela.Cultural as Translation — and Beyond Ethnographic Models of Represent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A].In T.Hermans.(eds.).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C].Manchester:St.Jerome,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