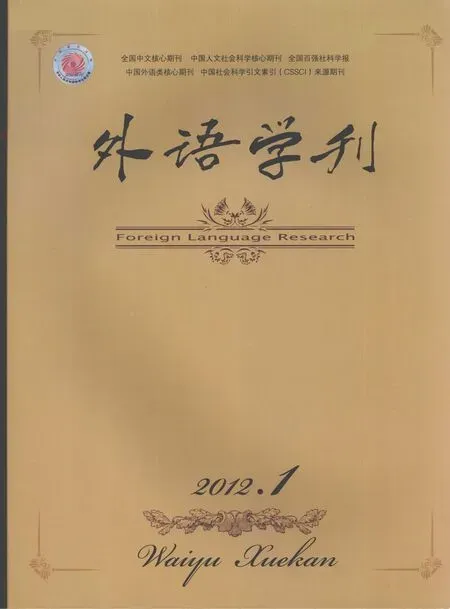从述谓观看中西语言哲学的研究路径*
——从蒯因的述谓学说谈起
霍永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
1 引言
述谓(predication)是由命题的主项和谓项构成的结合体。自柏拉图起,命题述谓结构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传统课题。哲学关注命题述谓结构,原因在于:1)命题的述谓结构反映语句的使用以及人类语言表达(最为简单的)思想的过程(Davidson 2005);2)命题的主项和谓项在述谓组构过程中结合为一个统一体(Gibson 2004,Gaskin 2008,Searle 2008);3)述谓的命题统一体在心智层面上体现为人类特有的一种形成判断的心智能力(Bogdan 2009:xi);4)述谓在形而上学层面上体现实体(主项)和属性(谓项)的联系(Bogen 1985)。
语言哲学作为哲学中专注意义问题的基础学科,自然离不开对命题述谓结构的考察。这一方面是因为语句命题的述谓结构本身就是一个表达意义的、有真假值的语言单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语词意义的确定,无论是外延意义的确定,还是内涵意义的确定,都要参照语词在相关命题述谓结构中的功能。在语词意义的确定过程中,同一性述谓起着基础性的参照作用。语词的意义在同一性述谓结构这个维度上呈现出多种样态,考察这些样态不但有助于深刻把握西方语言哲学的本质特征,还可以给中国语言哲学带来新的洞见。
有鉴于此,本文先考察当代哲学家蒯因的述谓学说,进而回顾西方近现代哲学对同一性述谓的关注,然后通过对言语的分析考察中国先秦语言哲学的述谓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语言哲学①研究进路。循此思路,本文力图说明,中西语言哲学对述谓结构的定义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两种不同的语言哲学研究进路和传统。
2 蒯因的述谓学说
2.1 述谓的性质、结构和功能
蒯因(Quine 1960:§20)在讨论词项(terms)的指称问题(语言哲学核心问题)时发现:适应对象的单复数不是单称词项(singular terms)和通称词项(general terms)的有效区分标准。原因在于,比方说,Pegasus(神马)是单称词项,但却无指称对象,因而其意义需借助描述才能获得。而与此相反的是,natural satellite of the earth(地球的自然卫星)是通称词项,但却只指称一个对象(月球)。显然,仅仅依赖单复数概念无法区分单称词项和通称词项之间的差异。要厘清二者的不同,只有另寻他途。
蒯因的思路是借助上述两种词项的语法功能来讨论二者的差异。具体作法是:引入述谓概念,在语句述谓这个维度上解释二者的意义特征。什么是述谓?从区分上述两种词项表义方式的需要出发,蒯因认为,述谓是体现单称词项和通称词项功能性差异的基本组合。就其性质而言,这种组合是在日常语言的句法维度上实现的。从功能的角度来看,述谓的作用是把两种词项合并为一个语句,语句的真假值取决于处于主语位置上的单称词项所指称的对象(如果单称词项有指称对象)与处于谓语位置上的通称词项是否适应或满足。关于述谓结构的格式,蒯因区分三种:①a is an F(如Mama is a woman);②a is F(如Mama is big);③ a Fs(如Mama sings)。三种格式中,a所代表的Mama由于处于主语位置而成为单称词项,而①中的woman由于处于谓语位置而成为通称词项。蒯因还发现,物质名词(mass terms,如lamb)的意义对语句述谓结构的二分法也极为敏感,其在句中主、谓语位置上的出现也构成其单称、通称语义功能分类的标准。他认为,上述语句中作为前缀的系词(is/is an)不但连接两种词项而构成述谓结构,还使(由名词或形容词充当的)通称词项成为动词,从而进入谓词位置。与此相关的是,动词(如sing)对述谓结构的构成具有基础性,因为动词无须借助上述系词形式便可进入述谓结构,并充当谓词(如 Mama sings)。
显然,语词的语义功能并非完全由语词与其指称对象决定,还要参照语词在语句述谓结构中的具体位置。这是蒯因经验主义语义取向的结果。
2.2 述谓结构的同一性问题
作为一种述谓结构,同一性(identity)述谓(又称同一性陈述)是蒯因借以讨论语词指称现象的一种句式(Quine 1960:§24)。同一性述谓指由系词或同一性符号(数学等号“=”)连接两个单称词项而构成的语句,如Mama is the new treasurer等。如此构成的语句为真,当且仅当作为其构成成分的两个单称词项指称同一对象。而且,在蒯因看来,语句述谓结构的同一性是英语语言及其概念图式的基础特征。
同一性述谓与语词指称的确定关系密切。在蒯因的述谓学说中,同一性述谓结构中的语词指称问题首先表现为指称的分离。指称分离(the dividing of reference)是根据个体事物的同异确定其类别的手段。用蒯因的话来说,就是:在何种程度上你拥有的是同一类苹果,而什么时候你又发现你所拥有的是另一类苹果了。由此确定为同一类型的事物,才可进入同一性述谓结构。在蒯因看来,儿童是通过这种手段将事物个体分离为不同的类,进而在语言使用中用语词(如前述的通称词项)对其加以指称的。
显然,述谓结构是蒯因思考语言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维度。本节的分析和讨论表明,语词的指称这个语言哲学基本问题并非是由语词与世界的对应关系单方面确定的。相反,语词指称的确定还要考虑语词在述谓结构中所实施的语法功能。在这个层面上,语词指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得以显现。就语词指称问题而言,同一性述谓是最为基础的一个维度。指称的分离性以及指称所预设的概念图式等指称的基础问题在这个维度上显现出来。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明白蒯因的断言:语句述谓结构的同一性是英语语言及其概念图式的基础特征。
但何以说同一性述谓是英语及其概念图式的基础呢?在指称问题乃至语言哲学理论建构中,同一性述谓的基础地位何在?本文力图回答上述问题。本文的研究来自于这样的基本认定:对同一性述谓的关注不但是英语语言及其概念图式的特色,也是西方哲学问题思考的进路;西方语言哲学这一思考问题的路径使其迥异于中国传统语言哲学的研究进路。
3 西方哲学对同一性述谓的关注
西方哲学讨论的同一性可作两种解释:跨时间的单一性(singleness)和差异中的同样性(sameness amid difference)(Bunnin&Yu 2001:466)。前者考察对象在跨时间的条件下对自身同一性的保持(如赫拉克利特关于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断言可以看成对事物如何经由时间变化而保持自身同一性的思考),后者涉及一类事物在其他类型事物中如何保持自身类型或某一个体区别于同类其他事物时所依赖的同一性。在逻辑研究中,同一性表现为一种等值关系,其确定须要借助莱布尼茨不可分辨物同一性原理(principle of indiscernibles)。按照这一原理,若一事物的每一个属性都属于另一事物,则二者同一。在莱布尼茨逻辑体系中,同一律与矛盾律、排中律并列为西方哲学三大基本定律。与本研究相关的是,逻辑学对同一性的关注是在命题述谓结构维度上进行的。具体说来,就是命题述谓结构中的主项与谓项有相同的指称对象。
3.1 从近代哲学说起
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后着力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知识的表征形式和有效性。这样一来,对命题的考察成了哲学家的研究课题。命题因其内部的述谓结构而成了有真假值的,因而是有效的基本知识单元。有趣的是,对知识的讨论是在命题述谓的同一性维度上展开的。发起这个讨论的是促成近代哲学语言转向的霍布斯。
霍布斯将命题定义为“由系词连接的两个名称构成的言辞”(Hobbes 1839:30)②。其中,前一名称与后一名称指称同一个事物,且后者在概念上包含前者。具体说来,就是在命题man is a living creature中,由系词is连接的名称man和living creature共指一个对象,且living creature在概念上包含man.
霍布斯的命题观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首先,命题是一种实施断定或否定、表达真值或假值的言语(speech)。虽然名称的组合可构成多种言语(如疑问、祈祷、承诺、威胁、愿望、命令、抱怨等),但在他看来,命题类言语是唯一可用于哲学研究的言语(同上)。其次,从上述结构分析来看,霍布斯的命题也是一种述谓。(Tanesini 2007)由于构成述谓的两个名称均指同一对象,因而可以说霍布斯的命题性述谓也是一种同一性述谓。
但霍布斯上述命题述谓观与其哲学体系建构有何关联呢?考察霍布斯(1839)的著作,可以看出,作为近代认识论哲学的重要奠基人,霍布斯的哲学是知识的学问。但霍布斯的知识是来自形式推理(ratiocination)或计算的知识,而不是来自感觉和记忆的知识。这种来自推理的知识以逻辑(主要包括名称、命题、三段论和推理方法)(Hobbes 1839:5)为基础,其内容包括基本认识范畴(如量值、物体、运动、时间、质量等级、活动、概念的形成、比例、言语和名称)以及物理学基础。这样一来,霍布斯的命题述谓观对于哲学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就好理解了。名称作为概念的体现,只有在命题层面上才能构成有效的知识,同一性命题述谓便是有效知识的基本单元。以此为基础,可以构成三段论和逻辑推理的基本方法,并在上述基本认识范畴的基础上建构起物理学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可以说,霍布斯的哲学是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起点。
莱布尼茨的述谓学说源自其形而上学。和亚里斯多德一样,莱布尼茨也认为世界由实体(substance)和属性(property)构成。与此对应的是主谓式命题,如“水是湿的”。(Thomson 2002:29)莱布尼茨认为,命题的主谓形式是其基础形式,所有其他类型的命题(如假言命题、关系命题等)都可以还原为这种形式。在这样一个命题结构中,主项(指称一个实体)的一个属性(谓项的指称对象)被肯定或否定(如“水是/不是湿的”)。这样一来,通过对命题主谓结构的分析,就可以对实在进行描述,从而回答世界本体和形而上学的问题。
对命题真值的分析构成莱布尼茨命题学说的重要内容。命题因何而具有真值?在莱布尼茨看来,命题为真当且仅当命题的谓词概念包含在其主词概念中。(Thomson 2002:30)由此而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所有为真的命题都是分析性命题。不过,在莱布尼茨命题学说中,并非所有的命题都具有同样的分析性。在其区分的三种分析性命题中,“一个男子是一个男子”在结构上符合“A是A”类同一性陈述的格式。这类命题的分析性不须要证明,其否定必然会出现自相矛盾。第二类命题(如“一个三角形有三条边”)通过一定分析可证明为与“A是A”相同的同一性命题。第三类命题(如“裘力斯·凯撒死于公元前49年”)表面看来不是上述恒等陈述,但若对其主词(裘力斯·凯撒)的概念作足够(甚至是无限)的分析,便可证明其分析性。前两类命题可称为显性分析性命题,后一种命题为隐性分析性命题。
显然,与霍布斯的命题一样,莱布尼茨命题也是一种同一性述谓。所不同的是,莱布尼茨的同一性表现为主词概念对谓词概念的包含,而霍布斯的同一性则体现为谓词(构成命题的第二个名称)对主词的包含。但莱布尼茨同一性述谓对其哲学体系的建构是否也有基础性作用呢?
回答是肯定的。其实,上述讨论就已经暗含这样的一个思路,即命题述谓结构同一性本身就已经论证命题的真值。以此为基础,可以论证(比如说)充足理由律的合理性。按照这一定律,每一事物之所以如其所是(而不是以另外的方式存在)必有其原因,而且这个原因是先验的。这种先验性,在他看来,就存在于命题述谓结构中主词与谓词的逻辑关系中。命题谓词代表的属性作为主词概念的构成要素是不证自明的,因而是先验的。这样,体现为命题述谓结构的实体存在方式便是先验的,因而其如此存在的理由是充足的。
与此相关的是,贯穿莱布尼茨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研究的一个主题是力图找到一个真正表征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以及操纵这些符号的计算工具,即莱布尼茨之梦。(Davis 2000:14-15)简单说来,这个方案包括三部分内容:1)一部涵盖人类知识全部范围的百科全书;2)一个为百科全书的观念提供符号的符号系统(普遍文字);3)一个由规定符号操作(推理)方式的演绎规则(或推理演算)构成的符号逻辑系统。这里,人类思想活动(推理)成了计算活动,所不同的是推理活动被描写为上述有意义的文字,而代数演算活动则体现为无意义的数字运算。在推理演算中,作为逻辑关系的同一性在计算、推理公理化的过程中被看成逻辑公理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基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茨哲学体系为现代逻辑创始人弗雷格所继承,前者命题述谓结构同一性的学说也在弗雷格数理逻辑体系中得到继承,从而引发并推动现代逻辑、现代语言哲学的研究与发展。
3.2 弗雷格的述谓学说
弗雷格对莱布尼茨哲学的继承表现有二:1)为数学(尤其是数的哲学性质)寻求一个逻辑根基;2)使人类思维摆脱日常语言的控制(Hill 1997),为思维过程的形式化(数学化、逻辑化)奠定哲学基础③。循着路径一,弗雷格试图为自然数的理解建立一种纯粹的逻辑理论,从而证明数学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具体说来,就是用纯逻辑术语来定义自然数,然后再用上述逻辑导出数的性质。其结果便是现代数学的基础——集合论。(Davis 2000)这种作法后来也称为逻辑主义(logicism)。循着路径二,弗雷格创立和设计出一种由概念文字构成的符号逻辑系统,并借助该系统的逻辑符号对人类思维(具体为弗雷格基于真值函项的命题演算,或莱布尼茨的“推理演算”)过程进行符号化。思维过程的符号化便是借助逻辑符号对思维过程的明确、客观的描写。
值得注意,无论是逻辑主义的尝试还是符号逻辑系统的设计,命题述谓的同一性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④。就逻辑主义而言,这种基础性表现在数的定义中。在弗雷格看来,数这个概念只有经过数的等式的定义才能成为确定的概念。(Frege 1953:74)具体作法是构造一个判断,该判断为一个等式,等式的两边各有一个数。这样,借助于等式(当然也是命题同一性述谓),数这个概念可以得到明确的定义。何以如此?在霍布斯和莱布尼茨的逻辑体系中,语句的真值来自于主谓项中两个名称的共指和包含。在弗雷格的命题同一性述谓结构中,处于主项位置上的主目和处于谓项位置上的主目都是带定冠词的单称词项,都指称一个(当然也是同一个)对象。(Frege 1953:77)这里,数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自于包含数的同一性陈述的意义。这体现出弗雷格的语境原则。
与此相关的是,命题述谓结构的同一性也是弗雷格符号逻辑系统的基础。借助逻辑符号描写思维过程的第一步是把日常语言的语句改写为符合符号逻辑要求的语句,这样一个语句便是一个同一性陈述。如语句Jupiter has four moons可改写为 The number of Jupiter’s moons is the number four.(Frege 1953:69)这样,原日常语句的主谓结构(也是述谓结构)就改写为同一性述谓结构,其中两个名称均为带有定冠词的单称词项,这样的结构和要求使名称的意义在语句或命题中表现为概念的外延,即对象。在上述主谓结构中,使二者得以结合成为一个统一体的是系词is.改写过程既反映一个定义的过程,也反映一个基本的推理过程。
4 中国哲学的述谓观
和西方哲学一样,中国哲学也关注述谓结构,所不同者则在于关注述谓的类型不同以及述谓结构中关注部位的不同。由于先秦古汉语中与“语句”或“命题”大致对应的语言单位是“辞”,我们的考察就从“辞”开始。
4.1 辞(述谓)的功能性定义
先秦哲学研究中对辞的定义首先表现为功能性定义。功能性定义的特点是定义只参照辞在具体语境中的用途进行。如《周易·系辞》将辞定义为“辞也者,各指其所之”。这里的“辞”显然是指《周易》中的卦辞或爻辞(上文“其”的指代对象),其功能是指明所述事件的发展趋向(上文“之”即意为事物发展的趋向)。然而,辞的功能是否仅限于此呢?考察《周易》的卦辞和爻辞部分,我们既会发现像“乾:元,亨,利,贞”、“蒙:亨”、“师:贞丈人吉,无咎”这类实施定义功能的卦辞,也会发现诸如“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六四,师左次,无咎”这类表明事件发展趋势的爻辞。从结构来看,实施定义功能的卦辞就类似于上述同一性述谓,如“乾:元,亨,利,贞”、“蒙:亨”、“师:贞丈人吉,无咎”的“:”均可由“=”替换。爻辞的结构则表现为“动+名”或“谓+主”格式,如“见龙在田”为“龙出现在田野之间”(杨天才 张善文 2011:3),“师左次”为“军队驻扎于左方”(同上:86)。显然,《周易·系辞》的定义只涵盖《周易》辞(卦辞和爻辞)在某些语境(如“指其所之”)中的功能,而未考虑其他功能(如上述卦辞的定义功能),更未涉及辞的结构。
《周易·系辞》关于辞的学说虽不完善,但却开创了辞的哲学、逻辑学考察。在辞的功能性考察中,墨家的辞说不可不察。墨子(前468-376)对辞的定义见于《墨子·小取》,即“以辞抒意”。在墨子的辩学体系(“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中,“辞”作为介于“名”(名称、概念)和“说”(辩说、推理)之间的辩说单位用于表达(“抒”)意图。在《墨子》中,辞体现为不同类型的判断,包括肯定、否定和全称、特称、直言判断以及假言、选言判断(姜宝昌2009:461),其所表达之意也随其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和《周易·系辞》一样,墨子也未对辞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但从其辩学体系可知,“辞”作为介于“名”(名称、概念)和“说”(辩说、推理)之间的辩说单位是由名称或概念构成的。然而,名称或概念是如何构成辞的呢?
4.2 荀子的述谓(辞)学说:结构与功能
荀子对辞的考察集中于《荀子·正名》。和墨子一样,荀子也是在思考辩学问题时涉及辞的问题,即“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荀子·正名》,见方勇李波2011:364-365)。而且,从上文叙述可以看出,“辞”作为辩说的构成单位本身又由下位构成成分——名称或概念构成,并在辩说过程中用于表达或论述说话人的意思或意图(“一意”)。
荀子对辞的定义还涉及到构成辞的名称的类型和名称的组合方式。在荀子的定义中,构成辞的名称指称不同的实在对象。对于哲学研究来说,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哲学中,体现辞的述谓结构不是同一性结构,至少不是诸如“乾:元,亨,利,贞”、“蒙:亨”或其他类似于西方哲学中体现为同一性的命题或语句。于是,荀子定义中的“兼”就好理解了:组成辞的名称经过“兼”而合为一个辩说单位(“辞”)。但“兼”这个动作是由何许成分实现的呢?这个问题荀子并未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成分至少不是西方哲学中连接同实异名构成同一性述谓的“是”。
这样,哲学研究中围绕着系词“是”(to be)而产生的种种疑问就可以得到清楚的回答:西方哲学以作为同一性述谓结构的命题或语句作为其分析对象,因而系词“是”作为连接同实异名的纽带必然成为语言分析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以异质性述谓结构作为语言分析的对象,而且这样的结构不需要系词“是”作为连接名称的纽带。因而,即便汉语中有“是”,“是”也不会成为哲学分析的对象。
5 述谓观与语言哲学
西方哲学对同一性命题述谓结构的重视以及中国哲学对辞的异质性述谓结构的关注引发的结果是,二者在研究的基础层面或(更为确切地说)语言哲学致思路径上存在差异。
5.1 西方语言哲学的研究路径
上述对霍布斯、莱布尼茨、弗雷格、蒯因哲学理论建构过程的分析表明,西方哲学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不但把同一性述谓结构作为有效知识的语言表征方式,也将其作为讨论语言意义的基本单元。在语言哲学层面上,同一性述谓结构的基础作用表现为:语词意义(语言哲学核心问题)的定义和区分需在同一性述谓结构内进行。在逻辑方法论上,同一性述谓结构的基础作用表现为在描写语词意义时对外延逻辑或语词外延义的重视。在研究目标上,重视同一性述谓结构的意图是建立符号逻辑以使思维形式化。这一路径对语言学的影响就是语言研究中对句法(尤其是形式句法)的偏爱。
以弗雷格语言哲学为例。《涵义与指称》集中体现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思想,也是现代分析性语言哲学的开山之作。论文的思考是由The morning star is the evening star这个同一性陈述或等式引出的。在弗雷格看来,由这个等式(或者更为确切地说,体现这种等式的系词)所反映的是否是一种关系?如果是,那么这种关系是对象间的关系还是语言符号间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弗雷格引入两个数学等式,即a=a和a=b.在符号指称对象层面上,上述同一性陈述体现为等式a=a:the morning star和the evening star指称同一个对象。但这样一来,陈述便没有意义(未提供任何新信息),而实际上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语句,这个陈述是有意义的。在弗雷格看来,这种意义是由述谓结构中名称的符号引发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引入上述第二个等式,即a=b.这个等式说明,上述语句在符号层面上存在差异,即the morning star和the evening star并不等同。差异何在?弗雷格的看法是:由不同的呈现方式(modes of presentation)引出的认识价值(cognitive value),即涵义(sense)。当然,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不止于此,上述分析也只是该文的起点,但正是这一路径及其引出的理论发现促成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而促成这一转向的是弗雷格在同一性述谓层面上对语词意义的思考和讨论。
5.2 中国语言哲学的研究路径
和西方哲学相似的是,先秦哲学也把辞的述谓结构作为讨论哲学问题的一个层面。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先秦哲学家并未把同一性述谓结构作为语言分析的对象和维度。这或许和荀子对辞的定义有关。在理论上,由此引发的结果可能是:哲学研究虽然涉及语词意义的探讨,但未必把语词意义的思考定位于辞的述谓结构。在语言哲学层面上,这进一步体现为哲学研究对分析性、同一性述谓和意义不感兴趣。在语言分析实践上,这一倾向表现为哲学家不是从对同一性述谓结构中语词的意义和关系入手思考哲学问题,建构哲学体系,而是从违背常理的表达方式(“辞”)入手,提出并阐述哲学问题,建构哲学体系。在这样的语言哲学背景下进行的语言研究难以形成较为系统的句法理论,遑论形式句法理论。
考察先秦语言哲学,会发现这样的断言并非空穴来风。最为著名者当推“白马论”的辩说方式。“白马论”又可表述为“白马非马”,为先秦哲学家公孙龙语言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为《白马论》(公孙龙5篇论文之首)中客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白马非马,可乎?”),“白马非马”构成论辩过程中主客互动的核心内容。以此为基础,论主(公孙龙)借助客方的问题和质疑(白马何以非马?),逐步推进,阐述“白马非马”的种种情形(如“坚白”情形下的“白马”),开始其语言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其实,围绕“白马非马”这样一个分析性述谓的否定式,在公孙龙论著中我们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辩说方式,如:“牛羊足五,鸡足三”(《通变论》)等违背常理的言辞。必须指出的是,从本文的角度看,这些辩说方式(当然就辞的结构而言,也体现为述谓结构)恰当地阐述了公孙龙的语言哲学思想。
循此思路,也可发现,先秦哲学论辩中类似的辩说方式并非为公孙龙所独有。惠施“历物十事”、“二十一事”就有“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南方无穷而有穷”、“火不热”、“目不见”等说法。即便是在坚守“白马,马也”、“盗,人也”的《墨子》中,也可看到“杀盗,非杀人也”(《墨子·小取》)这样的辩说方式。和“白马非马”一样,这些方式(当然也是辞的运用)从各自的角度有效地体现和阐述惠施、墨家的致思路径和哲学思想。
6 结束语
本文从蒯因的述谓学说出发,分析、考察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述谓观,以此为基础思考中西语言哲学的研究进路。研究发现,西方语言哲学重视语句、命题同一性述谓结构的分析,并以此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考察知识的有效性和语词的意义,从而建构哲学、语言哲学理论。而中国哲学虽然关注并思考过辞的述谓结构,但其兴趣并不集中于对辞的同一性述谓结构的分析,且不以此作为理论和建构语言哲学的基本语言单元。这一差异决定中西语言哲学研究进路的不同,并由此决定两个语言哲学体系在本质上的差异。
研究表明,中国语言哲学有其固有的问题和辩说方式,这些问题是由汉语的特性和中国哲学的本质所决定的。因而,从这些问题和辩说方式入手,同时吸收西方语言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啻为在目前情况下继承和推进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一条路径。
注释
①正因为如此,若无特别注明,本文中“中国语言哲学”、“先秦语言哲学”和“中国先秦语言哲学”同义。
②但霍布斯同时也认识到,没有系词的语言可用语序等方式来连接名称,构成命题。(Hobbes 1839:31)
③这一路径的结果之一便是为图灵通用计算机的设计奠定了数学、逻辑学的基础。(Davis 2000:53)
④不过,弗雷格的命题和莱布尼茨的命题不同:后者表现为主词和谓词的结合,而前者则被定义为函项和主目的组合。本文认为,后者是前者的一种情形,前者是后者的抽象和概括,二者的差异不影响本文的论述。
姜宝昌.墨经训释[M].济南:齐鲁书社,2009.
方 勇 李 波(译注).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1.
杨天才 张善文(译注).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1.
Bogdan,R.J.Predicative Minds[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9.
Bogen,J.Introduction[A].In J.Bogen & J.E.McGuire(eds.).How Things Are:Studies on Predication[C].Dordrecht: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5.
Bunnin,N.& J.Yu.Dictionary of Western Philosophy:English-Chinese[Z].Beijing:People’s Press,2001.
Davidson,D.Truth and Predication[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Davis,M.Engines of Logic[M].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2000.
Davis,M.,R.Sigal & E.Weyuker.Computability,Complexity and Languages(2ndedn.)[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94.
Frege,G.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M].New York:Harper& Brothers,1953.
Gaskin,R.The Unity of Proposi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Gibson,M.I.From Naming to Saying[M].M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
Hill,C.O.Rethinking Identity and Metaphysics[M].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
Hobbes,T.Elements of Philosophy[M].London:John Bohn,1839.
Quine,W.V.O.Word and Object[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60.
Searle,J.R.Philosophy in a New Centur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Tanesini,A.Philosophy of Language A-Z[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
Thomson,G.On Leibniz[M].U.S.A.:Wadsworth,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