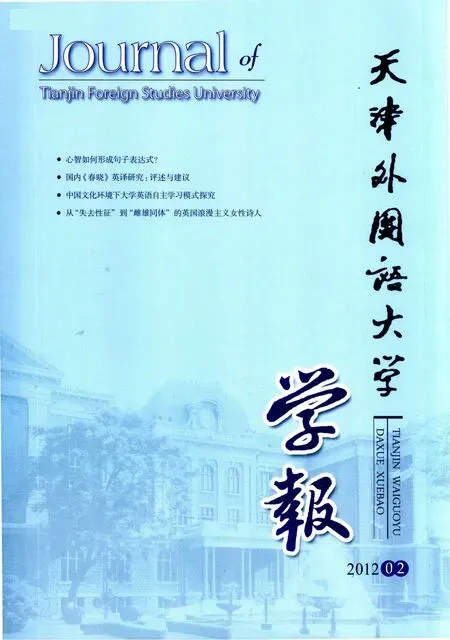心智如何形成句子表达式?
徐盛桓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一、引言
本文从意识(consciousness)的涌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y)探讨句子表达式(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的形成。语言表达式有一个重要的外在表征,就是它的不可预测性(nonpredictability)。但我们并不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只是从语言表达式的不可预测性之所以会出现研究句子表达式是如何形成(shape)的。
二、句子表达式的不可预测性
先从哥尔德博格(A.Goldberg)的一个重要说法说起。Any linguistic pattern is recognized as a construction as long as some aspect of its form or function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its component parts or from other construction recognized to exist;In addition,patterns are stored as construction even if they are fully predictable as long as they occur with suff i cient frequency.(Goldberg,2006:5)①这就是说,哥氏认为,对于构式,可以它的特性“不可严格预测”(not strictly predictable)来认定,即对被认定为构式的语言构型(linguistic pattern)是不可从其组分或从其他已存的构式对它作出严格预测的。但是,哥氏也认为,有些构型即使可充分预测,只要它们有足够的出现频率,也可以认定为构式。她的这些论述蕴含这样的观念:从可预测性角度说,有些构型多少可以预测,有些构型却难于预测,这就是说,从整体来说,语言构型的可预测程度是一个连续统。本文认同这一看法,并试从意识的涌现属性论证这一看法,进而谈一谈由此得到的一些启示。本文没有拘泥于“构式”这个术语,而是用了比较常用的“语言句型”和“句子表达式”,这是因为哥氏所说的构式包括非句法层面的语言单位,而我们的研究只关注句法层面的句子表达式;同时,构式是“构式学研究”(constructionist approach)的一个专门术语,不借用这个术语,可以避开某些关于构式说法的枝节争论。
“句型”是由一类在句法层面其形式—意义(或功能)相关的语言表达式集合体。“句子(法)表达式”是用以表达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用例事件”(usage event)的句法层次语言单位。“事件”泛指自然或社会存在的一切自在事件,这时的事件是以它的自然形态出现的;一个句子表示、描写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简单或复合的事件,而“用例事件”是特指话语主体用一个特定的句子表达式所表示的那一事件。有些句型的概括可能涉及一个很大的“家系”,如SVO;有的句型可能只有个别成员,如“多Adj的NP!”the more … the more(less)…,let alone等。大“家系”里可能包括若干其形式或功能以及规模各异的中小“家族”、“家庭”;从规模来说,至少可粗分为概括程度不同的句型、句式、表达式等。在本文,(构式)、句型、句式、表达式的区分,大体是前者可以按不同标准分类为后者;而表达式可看作是某类句型的单个运用。所谓可预测性,哥氏指的是构式义的预测。但是,既然构式的概括可能涉及上述一类形式—功能以及规模各异的结构,它们都可能抽象出其概括程度不同的结构义,那么预测也可能是在这些不同的层次的结构进行。本文关注的是语言表达式的预测。
作为构式语法的研究,习惯上是从具体的表达式展开的。例如:
(1)a.The chicken cooked all night.(intransitive inchoative)
b.Pat cooked the steaks.(transitive)
c.Pat cooked the steak well-done.(resultative)
d.Pat cooks.(deprof i led object)
e.Pat cooked Chris some dinner.(ditransitive)
f.Pat cooked her way into the Illinois State bake-off.(way construction)(Goldberg,2006:3)
对于预测来说,对这样具体表达式的观察可能比较直观,所以我们的研究也拟从表达式层次开展;当然,需要时还可以进行必要的概括和抽象,如(2)。试比较下面的表达式或句型:
(2)NP1是NP2(如“张三是学生”)
(3)IS THAT an NP? (如Is that a computer?)
(4) (SVO运用时变为)OSV[adv]表达式(如Edison gave his mother part of the money he made from selling newspapers,and)the rest he spent on chemicals.
(5)The wall paints easily.
(6)They killed John a duck.
(7)Sue kissed him unconscious.
(8)素肌 (喻梨花)应怯余寒(周邦彦《梨花》)
对于只有一点点汉(英)语言知识以及日常常识的人,能 “猜”出以上表达式意义的难度,或曰其可预测的难度,可能自上往下增大。光就语言表达式(而暂时不管运用表达式的主体)来说,这里直接涉及的有两个方面:表达式的自身和表达式所要表征的客观现实。“预测”意味着能从表达式自身的形式“看到”它准备表征的内容、意义、功能,说到底就是看表达式的结构及有关词语所表征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贴近客观现实。这就是哥氏所说的,简单句式是与反映人类经验基本情景的语义结构是直接联系的(Goldberg,1995:39)。
从表面上看,语言表达式在语法书上作为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好像是人为地编造出来的,表现为比较系统的语法规则。但是,人工“编造”的表达式其实并不是任意编造的,它们实际上是根据表征客观现实的需要总结出来的。那么,它是如何表征客观现实的呢?在语言研究的心智哲学视野中,对语言运用有三个假设:语言运用是基于心智的,语言所表达的基本内容是话语主体的感觉和感受,语言表征的是心理表征(徐盛桓,2011:10)。这表明语言表达式其实是联系着人的心智的,人们正是根据心智里所反映的人类经验基本情景的概念结构才“编造”出某一特定的语言表达式。以上那三个假设表明,语言的运用可能是这样的:在心智的参与下,客观外界由心智摄入后加工加以表征,心智表征才由语言表达式加以表征。帕维奥(Paivio,1986:53)的“双代码理论”(dual-coding theory)假设了一个“双代码表征系统”,认为人类的感觉系统联系着两个过程:言语过程和非言语过程,它们可以双向互为表征,从而把言语过程和非言语过程连接起来。客观现实中各种可视可听可感等等的现象通过身体感官摄入,在大脑中成为“表象”(imagen)储存;各种杂乱原始的表象经过筛选、去留、分类、合并、整理,抽象成为一个个的“单位”,这就成为大脑里以表象储存的一个个的概念。用有声有形的符号分别指称它们,就成为“语象”(logogen),即成为大脑里概念的“语言外衣”,即语言概念。大脑里的概念是整理过、提炼过、抽象过的表象,语言概念则是大脑里的概念的外在表征。表象可以由语象表示;或者反过来,语象可以唤起表象。语义结构是用概念结构对外部世界作出的表征,是运用语言符号来表示的人类经验的基本情景;语言表达式就是按一定的规则串连起来的这样的语义结构串。所以,实际上,语言表达式不是真的由人工自由地编造出来的,而是要受到用语言概念符号所表示的人类经验的基本情景的规范,这种规范就是用以编造语言表达式的语言知识,就是一个语言共同体所大致达成一致的那些语言“规则”。语言要以人类经验为基础,意义是人类意识的基本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说,“经验就是我们通过语言来识解的现实”(Halliday & Matthiessen,2008:108)。这整个过程就是心智表征外部世界而心智由语言表达式表征的过程。
上文提到“语言所表达的基本内容是话语主体的感觉和感受”。感觉是人们的眼、耳、鼻、舌、身(下文统称“身体”)对客观现实的各种事件的摄入,得到感官意象,这是“最初意识体验”;感受是“通过回忆、联想和想象所呈现出的相关意象”,这是“扩展意识体验”,或称“反思意识体验”(李恒威,2011:95),即“反思”为已裁剪成上文所说的用例事件。根据李恒威转引埃德尔曼和达马西奥的说法,人们的意识包括“身体”的一切级别、一切类型的体验(同上:96),包括最初意识体验和反思意识体验(同上:99,100)。所谓“反思”,就是“在记忆和语言等能力的襄助下,后一个意识事件将前一个意识事件的已沉淀为记忆的意象作为体验内容的一种能力”(同上:102)。“意识的涌现”在这里指的就是从最初的意识体验 “涌现”出扩展的意识体验:客观现实“沉淀为记忆的意象”,并经过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格式塔转换的“反思”。“涌现”为感受的体验内容:梨花可以“感受”为“素肌”,人们行贿官僚可以“反思”为“[ 官僚+(行贿行为+ 状态)]”(bureaucrats bribe easily )。这些例子表明身体对客观事件摄入后所得到感官意象,同沉淀于记忆里的反思性扩展意识对成为用例事件的感受可能是不同的。梨花不同于“素肌”、人们行贿官僚不同于“官僚+(行贿行为+状态)”。因此就有心理感受是不是贴近客观现实的问题。
之所以会有不同,是因为意识有涌现属性,就是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涌现”出了新的质。霍兰 (J.Holland)在他那本被誉为“对涌现现象进行深入探索的第一本著作”《涌现:从混沌到有序》曾经作出这样的提示:“我们是否能将人类的意识解释为某种物理系统的一种涌现属性?”(霍兰,2006:3)本文就是试图从心智哲学视角,从涌现的角度展开研究。
感受是个人的“第一身”的感受,外人难于知道。为了表征心理对客观现实的感受,人类创造了上述所提到的可视可听的语言符号,使心理表征可以由语言表征出来即语言所表征的是心理表征。这样,我们的研究就可以将目前无法现实地有形地把握的心理感受问题转换成可视可听的语言表达式的问题。心理感受和语言表达式可视为是异质同构的:内容一样,载体的物质不同,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互为表征、相互印证。可以从语言表达式印证心理感受,或者反过来。我们都有这样熟悉的经验:一个语言表达式有可能引发一定的心理感受;反过来,一些心理感受可以凝固为一定的表达式。表达式是模拟、象似(iconize)、表征心理感受的,亦即将人们的心理感受是不是贴近客观现实的问题转换为语言表达式是不是贴近客观现实的问题。我们就是准备这样来探讨语言表达式的形成问题。
三、对意识涌现的一般说明
上一节的讨论告诉我们,沉淀于表达式里的内容是沉淀于记忆里的反思性的扩展意识体验,是涌现事物及其涌现的新质。各种意识活动都是不同程度的复杂系统,而“涌现”是复杂系统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和属性。复杂系统关于涌现的研究认为,一个事物或一个事件作为一个系统,它的一组相对完备的成分以某种方式结合并相互作用,就会涌现出一个新的“涌现事物”(emergent substance),这样的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属性,称为“涌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y);涌现事物及其涌现属性是具有一定自主性新质的现象。物理世界以及意识活动都是如此。
目前,学界较普遍认同的关于涌现最基本的特征是本格(M.Bunge)给出的较为宽泛的说明:每一个系统都具有某些从它的组成成分(组分)涌现出来的而为它们原先所不具有的性质(本格,1989:31),而且涌现出来的这些新质是宏观性、全局性的( Bunge,2004:14-15)。这个新系统是由系统内部各组分的作用和各组分间的关系综合构成,构成新系统内部相对稳定的各部分的结合方式和整体的组织格局,这就是系统的整体性(wholeness),是整体的宏观的序和系统的新行为,是一种全局性的新模式。
就这里所讨论的意识的涌现来说,可以表征为从主体对一个事件的感觉意识涌现为对一个用例事件的感受意识的过程。事件可以是任何自然形态的事件,而用例事件是语言主体主观地剪裁、分割为一个语言表达式所涉及的事件,有可能不同于自然事件的结构和形态。一个用例事件对应一个可长可短、可简单可复合的语言表达式,这是建构在心理活动和一定的语言内外知识结构基础上的反思性的思维活动,以建立一个针对某一特定活动域、概念域的临时性的表征结构,是人们在进行思考、交际时为了达到某一局部行动之目的而构建起来的表达这一用例事件的语义结构串。这一意识的涌现可能涉及一连串复杂的心智活动,主要包括意向性(徐盛桓,2011)、注意(Deutsch & Deutsch,1963:80-90;Treisman& Gelade,1980:97-136;Lavie et al.,2004:339-354;Knudsen,2007:57-78)、心—物随附性(McLaughlin,2001:1142-1147)、选择、外延内涵传承(徐盛桓,2009)、联想、想象、格式塔转换以及整合等。这些心智活动可分三个阶段: (1)开始阶段,包括意向性、注意、心—物随性、选择等,以心智主体的特定意向性的建立与行使为统制,通过注意的过滤、衰减、反应等过程,在心—物随附性的主导下进行选择,目的是对事件的感觉作出符合用例事件的意向性的认定;(2)传承阶段,在上述对感觉选择认定的基础上,将定向了的最初感觉意识“反思”为扩展的意识体验,这样的过程是通过包括联想、想象和格式塔转换(主要是相邻、相似转换和/或显隐、凸现转换),将事件所体现的外延和内涵“输传”出去,涌现为用例事件的过程;(3)整合阶段,用语言符号表征用例事件,固化为语言表达式。涌现涉及两个主要的现象:层级性和新颖性。
1 层级性
心智哲学认为,世界涉及三个大的层次:物理层次——生命层次——心智层次。没有心智是不包含生命的,没有生命是不包含物理实体的。每个层次又都涉及若干层级,高层级是从低层级来的,低层级是高层级的“根源”。心智哲学用随附性说明高层级的心智现象与处于较低层级的物理事实的关系:前者是随附于后者的,由后者涌现出来。例如,意识的表征是分层级组织起来的,人的感官作用于物理事实获得感官意象,若干感官意象连通为大一点的意象单位,并可能进入上位的层级,成为上一个层级的成分;这样,下位层级单位依次地连通,成为一个又一个更大的上位层级单位,直至由最初的意识转换为或涌现为反思性扩展意识。这在语言表达中体现为词、词组、小句、句子、语篇等层级单位,后者是由前者涌现而成。涌现涉及上向因果关系(upward causation)和下向因果关系(downward causation),上下向因果关系的发生是以系统的分层级特征为依据的,涌现发生在跨层级的进程中,每一次的涌现至少涉及一个跨层级的转换。
2 新颖性
新颖性(novelty)表现为涌现事物具有原来事物所没有的新质,新质具有一定的新颖性,是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例如,从生化现象来说,本身并没有咸味的“氯”和“钠”化合在一起,就涌现出有咸味的“氯化钠”(盐)及其“咸味”的属性;本身没有生命迹象的氨基酸、核苷酸可以组成体现出一定生命活力的实体,表现出一定水平的新陈代谢、变异遗传、自我修复等的生命活动功能。从人的意识来说,感官作用于物理事实所获得的感官意象涌现为反思性扩展意识,也发生了新质性的质变:涌现出来的新整体是一个全新的实体,它形成了新的宏观规律,这样的宏观规律对它的各组分施加约束,使之改变原有的功能和行为而服从于整体行动的需要同外界发生互动。例如,视觉器官作用于红领巾,在记忆储存下来以后,经过联想和想象,发生格式塔转换,可用“红领巾”转喻为以佩戴红领巾为标志的“少先队员”,这就发生了涌现,这就是新质。表达式“我看到前面来了个红领巾”就是涌现的产物。从这里也看到了宏观规律对各组分施加约束:“红领巾”作为感官所作用的事物,它的数量表达通常是用“一条”,如“我看到树枝上挂着一条红领巾”。“红领巾”的转喻用法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它已涌现为思维中的转喻现象,受到转喻宏观规律的约束,服从于转喻表达整体行动的需要而同外界发生互动,适应转喻表达外部环境(语境)的需要。涌现现象的新颖属性具有对比的特征,新颖性的呈现常常是同个人原来大脑的储备知识相比较而发生的,就像生活在热带的人冬天到了北国初见大地被冰雪覆盖成白茫茫的一片,觉得很新奇,但这种现象对于一辈子就在北极圈生活的人早已习以为常,一点也不觉得新颖。
为什么会发生涌现现象?从根本上说,涌现现象可由自然界中存在的上向因果关系和下向因果关系说明(Campbell,1974: 179-186)。心智哲学把世界现象看作具有依附性关系的层次结构,心智实现智力功能,身体的眼、耳、鼻、舌、身等身体感官是实现心智功能的物质基础。功能层次处于较高层,物质实现者处于较低层。低层级的一些单位以化合或组合的方式构成较大的单位,成为上一个层级的成分,这样就形成一种趋势,好像上位单位是由下位单位“涌”出来的,被“涌”出来的单位所获得的新特性,是由“涌”它出来的那些下位单位共同负责的,所以这样的新特性必然统制着下位的那些单位。上下向因果关系就是这样表现为事件之间的“引发和后承”的链效应。上向因果关系是沿着由下而上的方向发生的“引发和后承”的效应,这时的因果关系的状态和结果表现为下位层级的组分涌现出上位层级的较大的新实体,如上文所说的由想象、联想和格式塔转换将若干实体“反思”为上位层级的较大的新实体。下向因果关系是沿着由上而下方向发生的“引发和后承”的效应,这时的因果关系的状态和结果表现为涌现出的新实体显现出对组成这个新实体的下位层级的组分的全局性约束。以隐喻 “怒涛卷霜雪”(柳永《望海潮》,据柳永词意,“霜雪”喻波涛的白色的浪花)为例,波涛的浪花在进入心理状态之前本身是物理性的,在它们被摄入成为感官意象之后,通过想象和联想,主要是受相似律的作用而发生格式塔转换,在微观进化的基础上实现系统上的性能和结构上的突变。浪花一项项分开来不见得会带来像“霜雪”那样的感受,但当这些组分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对心理施加想象和联想的影响,就可以涌现出“霜雪”那样的心理属性,而在大脑里产生出把白色的浪花当成是白色的霜雪的意识。在隐喻操作过程中,从身体感官的感知觉开始,然后由心智功能加以整合,获得一个隐喻的认识,涌现出隐喻表达的宏观结构,成为一个由智力整合的非实在存在的思想观念。在这样的过程中,隐喻的反思性扩展意识由下而上地涌现出来,高层内容依赖于低层对象,但高层内容不能还原为低层对象。在“怒涛卷霜雪”中,怒涛是感官感知的实在,“霜雪”是依赖波涛白色的浪花的意象得出的扩展意识。“霜雪”不是真正的霜雪,也不能还原为事实上的“浪花”,是涌现出的一种新质,是大脑神经系统所造成的心智过程的产物。这种“霜雪”是意识范畴里的联想和想象,是反思性扩展意识体验,不可还原为物理现实,在隐喻中要由语言加以表征。据涌现的新颖性的特征,涌现出来的隐喻表达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
四、语言表达式的涌现属性
上一节的论述表明,表达式所表征的反思性扩展意识是涌现出来的,涌现出来的新质具有新颖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这一节的讨论要回到语言表达式上来,从反思性扩展意识的涌现说到表达式的涌现。
语言表达式用以表征大脑里这样的意识涌现,二者是异质(物质)同构的。前者模拟、象似后者,是以不同的构造材料表征大体相同的结构内容,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客观外界由心智加以表征,心智表征由语言表达式加以表征。语言表达式将表征有关意识内容的词语以最大限度的近似排列,模拟有关意象出现的先后、显隐、突出、转换等,仿佛表达式就是从这些词语“涌现”出来的。例如,心智把梨花感受为“素肌”,表达式就表达为相同的概念;人们行贿官僚可以“反思”为“ [ 官僚+(行贿行为+状态)]”,表达式也最大限度地以概念的排列模拟这样的意识状态:bureaucrats bribe easily。这就是说,扩展意识把自己的涌现状态以“转录”的形式“复制”在异质同构的语言表达式里,以不同的构造材料体现大体同样的涌现过程,用后者模拟、象似前者。正是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表达式是“涌现”出来的,就像反思性扩展意识是从感官意识中涌现出来的一样。这就像我们对语言的意向性研究,语言是物理性的,不会有意向性。但心智哲学的研究假设人的意向性可以“寄生”在语言里,没有意向性的语言也就被看成是有意向性的了。同样,我们把象似反思性扩展意识的语言表达式看成是模拟了意识的涌现,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反思性扩展意识的涌现说到表达式的“涌现”,把表达式看成是构成表达式的词语“涌现”出来的。下文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直接说语言表达式具有涌现属性。
句子表达式的形成一般经历三个阶段:(1)面临一个新的事件,为表达这一事件做出反应;(2)把它转化为用例事件,形成社会性表征,并赋予语言符号形式;(3)通过交际将这一符号形式转化为语言共同体的共识,在社会群体获取最大的认同,形成一个语言表达式。涌现属性有新颖的新质,这是语言表达式有不可预测性的最根本的原因;不可预测性表现为一个强弱的连续统,是因为不同的涌现会表现出不同的涌现强度。
有些涌现现象的涌现强度在没有特殊的观测手段情况下是不易容察觉出来的,如氯和钠化合涌现出盐,我们看到的是一粒一粒的盐的结晶,一般人没有想到是怎么“涌现”出来的;雪花的小结晶粒聚合涌现出六角形的雪花晶体也是这样。有些涌现是人们凭自己的感受可以进行对比而察觉出来的,如语言表达式,人们可以从对表达式的内容“猜测”的难易就能反观其涌现强度。有人可能不一定懂得说这是“涌现”现象或说其涌现的强度如何如何,但可以感觉到句子同心目中认定的某些句式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使表达式不好“猜”了、越来越难弄懂了,这其实这就是涌现的强弱使表达式的可预测性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些涌现,人们可以凭已有的体验感受到它的强弱。那么,我们怎样刻画和表征语言表达式的涌现现象及其强度呢?
语言表达的组织形式是人们在长期运用语言的过程中约定俗成固化下来的,它们都已经语义化和语法化,成了一种语言的语法语义规则。严格的无标记的语法规则语义规则可称为“律则”(f i at)。以现代英汉语来说,最常见的“律则”是SVO的排列,而语法主语、逻辑主语、话题主语三者重叠,语法主语通常是“人”([HUMAN+])的表达式。这样的律则是这些语言表达式组织的基本格局,有关表达式通常是最常用的,在长期运用中已为该语言社区的人们所耳熟能详,成为该语言社区人们语言运用的定式。对于已经在下意识中熟习了这些符合律则的语言表达式的语言运用者来说,这些表达式的新颖性已经被很大程度地磨蚀,常常呈现弱涌现的态势,甚至因有足够的使用频率而成了哥氏所说的“可充分预测”。反过来,一些对无标记的语法语义规则有所突破,但又保留了规则的某些基本的格局,而其突破又可以从某个角度、某些方面进行逻辑推理、语用推理从而作出认定以获得相关认识(简称“逻辑认定”,事实上,许多句子表达式的格局是由逻辑认定确定下来的)的表达式,就呈现不同程度的较强的涌现态势,表现出一定的新颖性,这时表达式的组织形式也会呈现一定的不可预测性。例如,以“NP1是NP2”句式来说,所用到的NP是如实的指称有关的事物,其可预测性就要比非如实的指称的要高(试比较“张三是学生”和 “张三是‘红领巾’”)。从句式来说,所用到的句式是“如实”地指称所表征的事件的要比非如实指称的要高(试比较SVO和OSV(Edison gave his mother part of the money he made from selling newspapers,and he spent the rest on chemicals.同…the rest he spent on chemical),NP+V+NP2+for+NP1和 NP+V+NP1NP2(如They killed a duck for John.同 They killed John a duck.),People painted the wall easily.同 The wall paints easily.),每一对句子是前面一个比较“如实”,因而涌现强度弱一些,可预测性要高。这就是说,有些涌现强度弱一些,离开“如实”地指称有关的事件较近;有些涌现强度大一些,疏离“如实”地指称有关的事件较远。实际上,各种表达式的涌现强度正是游离于弱—强连续统之间;与之相对应,它们的可预测程度则处于大—小的连续统之间。
判断是否“如实”地指称所要表征的事件,以英语、汉语为例,主要有六个维度:(1)从事件叙述的安排来看,SVO句子的语法主语、逻辑主语、话题主语三者重叠的越是“如实”,如People bribe bureaucrats easily>Bureaucrats bribe easily (重叠>不重叠)(>表“越 ‘如实’于”); (2)从事件叙述的先后次序看,按S-V-O的越是“如实”(S-V-O>非S-V-O);(3)从事件叙述的详略来看,越是详细的越是“如实”(正常句>省略句);(4)从事件叙述词语的选取来看,越是写真的越是“如实”,如上面的“学生”和“红领巾”(写真>不写真);(5)从事件叙述词语的规范来看,越是规范的越是“如实”,如“敌人被包围了>村里的人都被高铁了”(规范>不规范);(6)从相邻的词语搭配来看,越是合理就越是“如实”,如John gave Jack a book>John baked Jack a cake,因为give-jack比bake-jack合理(合理>不合理)。我们可以用以上这六点来帮助判断表达式是否“如实”地指称所要表征的事件,也就是是否运用严格的无标记的语法规则语义规则。同时,对一个表达式的涌现强度的感受是会因人而异的。刚学汉语的外国人同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中学生看到汉语的句子“一锅饭吃十个人”,对其涌现出来的新颖性的感受是不同的。因此,表达式的涌现强度是个人感受的函数。
一个人对表达式涌现强度的感受函数决定于他的律则知识库的认定和他对表达式的运用是否 “如实”地指称所要表征的事件的置信概率。一个人的律则知识库就是他相信为真的、作为“律则”的语法规则语义规则的集合,即其置信概率为1的全部语法规则语义规则的知识。设对律则的语法规则语义规则的“如实”置信概率是无条件置信概率,那么发生了上面这几项变异的语法语义规则的置信概率就是条件概率。无条件置信概率可表示为P(A)=1。
对无标记的语法规则语义规则有所突破的那些表达式仍然可以认为其置信概率为1,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就成了条件置信概率。这里的条件就是:保留了规则的某些基本的格局,而其突破又可以从某个角度、某个方面进行逻辑推理、语用推理作出认定以获得相关认识;这可简称为 “逻辑认定”。设这样的条件为B,则条件置信概率可表示为P(A/B)=1。
对以上的说明可小结如下:一个涌现e是弱涌现,当且仅当,e是由律则缔造的;一个涌现E是强涌现,当且仅当E是由逻辑认定引发的。若一个表达式是由弱涌现所涌现出来的,它的可预测程度就较高;反过来,若一个表达式是由强涌现所涌现出来的,它可预测的程度就比较低。既然语言表达式的涌现强弱会同个人对律则知识库的掌握和对表达式是否“如实”地指称所要表征的事件的置信概率有关,那么,语言表达式的可预测程度是个人有关感受的函数。
五、涌现研究的启示
我们先是研究了意识的涌现,说明对用例事件的感受的反思性扩展意识是从原初的对事件的感官意象意识涌现出来的,并认为语言表达式是模拟、象似、表征涌现出来的反思性扩展意识的,从而把语言表达式看作是由有关的词语“涌现”出来的。由于涌现现象具有新颖性,涌现出来的语言表达式也就有是不是“如实”地贴近客观现实的问题。这就同哥氏所说的构式的不可预测性联系起来了。
研究表明,涌现的新颖性具有对比的特征,语言表达式的涌现强弱不但同表达式自身排列的独特性有关,也同个人对律则知识库的掌握和对表达式是否“如实”地指称所要表征的事件的置信概率有关,因此,语言表达式是否可预测就不完全是语言表达式的问题,也同个人的认识和运用的不同经验有关。这就联系着表达式出现的频率。
从感官意象意识通过联想和想象并经由格式塔转换而涌现为反思性扩展意识是经常发生的,这一过程就是句子表达式形成的过程。从这一视角揭示语言现象的机理,是一条可以考虑的新进路。表达式内容其实是有关事件的感官意象通过联想和想象或经由各种类型的格式塔转换而涌现出来的反思性扩展意识,并经“转写”成为语言符号就成为表达式,那么,新词语和新表达式就可以通过其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来研究。这应了法国哲学家莫兰(2004:64)所言,未来的某些现象的名字叫“不确定”。语言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总有不确定、不可预测的因素存在。因此,语言学研究的发展空间必须是包容性的,给不可预测性留下空间,把考虑如何应对不可预测性作为研究工作的一种常态。不可预测性带来语言运用新的可能性,新的可能性带来语言选择的新自由,语言选择的新自由带来语言研究的新前景。
* 本文初稿曾在全国认知语言学会第三次暑期讲习班(2011.7.5-7,上海)以“语言表达式的涌现属性”为题宣讲,这里作了一些改动。
注释:
①哥氏这段话上文用“(不可)严格预测”((not) strictly predictable),下文用“充分预测”(fully predictable)。在我们看来,“(不可)严格预测”的说法不科学,而说能不能“充分预测”可能较为合理。“严格”预测表示的是预测的质,预测准不准确、到不到位。作为对构式的研究,对它的构式义的预测不准确,这样的预测是没有意义的。“充分”预测可以从量来说,可能充分预测、部分预测、不可预测。由于我们研究的不是构式的可预测性问题,这里不展开讨论。
[1]Bunge,M.Emergence and Convergence: Qualitative Novelty and the Unity of Knowledge[M].Toronto :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4.14-15.
[2]Campbell,D.T.‘Downward Causation’ in Hierarchically Organized Biological Systems[A].In F.J.Ayala & T.Dobzhansky(eds.)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C].London:Macmillan Press,1974.179-186.
[3]Deutsch,J.A.& D.Deutsch.Attention: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J].Psychological Review,1963,(70):80-90.
[4]Goldberg,A.E.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5]Goldberg,A.E.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6]Halliday,M.A.K.& C.M.Matthiessen.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M].Beijing: World Publication Cooperation,2008.
[7]Knudsen,E.I .Fundamental Components of Attention[J].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2007,(30) : 57-78.
[8]Lavie,N.et al.Load Theory of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Cognitive Control[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2004,(133).
[9]McLaughlin,B.P.Supervenience[A].In N.S.Smith (ed.)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C].Elsevier,2001.1142-1147.
[10]Paivio,A.Mental Representation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1]Treisman,A.& G.Gelade.A Feature-integration Theory of Attention[J].Cognitive Psychology, 1980,(12):97-136.
[12]本格.科学的唯物主义[M].张相轮,郑毓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3]霍兰.涌现:从混沌到有序[M].陈禹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14]李恒威.意识、觉知与反思[J].哲学研究,2011,(4):95-102.
[15]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6]徐盛桓.话语的意向性[R].认知语言学会全国第七次研讨会,2011.
[17]徐盛桓.外延内涵传承说——隐喻机理新解[J].外国语,2009,(3):2-8.
[18]徐盛桓.语言研究的心智哲学视角[J].河南大学学报,2011,(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