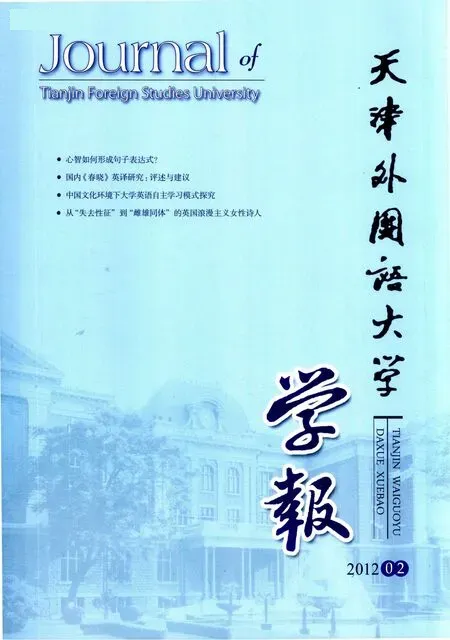多元理论视域下的语言与性别研究
张荣建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47)
一、研究回顾
Jespersen(1922)认为,女性本能地排斥粗俗的语言表达而偏好优雅和间接表达,从而对语言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和普遍的影响。Jespersen代表了20世纪初的性别语言意识,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的女性特质观点,即男女使用语言的差别,女性语言的特征是沉默、谦虚、顺从、礼貌、移情、支持性和合作性,这种差别被看作是自然的和合理的。但复杂的现实表明,女性语言并非如Jespersen所说的那样,所谓的本能因文化而异,性别语言的文化表现随时代而变化,存在各种变异(Cameron,2003)。
语言与性别的系统研究开始于1975年,代表作是Key,Lakoff和Thorne的论著。当时的主流观点包括Lakoff(1975)的缺陷理论(def i cit theory),认为女性语言低劣于男性语言;Thorne(1975)的支配理论(dominance theory),认为女性语言优越,男性语言是缺陷。Cameron (2003:458)认为,女性语言优越的观点实际是女性语言被表现的方式的转换:女性比男性更善于和他人分享情感或倾听。20世纪90年代的论著则强调女性更善于使用语言来维系人际关系,从而有Tannen(1990,1994)和Gray(1992)的差异理论(difference theory),强调性别是“有差异但平等的”,需理解差异、避免误解。Lakoff和Tannen将男女作为研究对象,Lakoff提出了标记某些社会身份和立场关键的语言形式,Tannen则提出了协商权势和亲密关系的重要性的一些交往事件,但都没有讨论性别的相关性,或没有讨论性别和其他社会身份如何交往以构建话语风格,因此,和“交往语境脱离”(Freeman,2001:242)。上述三个理论都关注女性的语言特征,都使用“两性对立的性别概念”(Freed,2003:702-703),在强调语言反映男女本质不同的同时,忽略了男女差异之所以不同的社会、历史、语言等意识。上述理论的结果导致了对不同群体的分类给予了某个群体某种优势,如某一群体语言是标准或规范的,另一群体语言是变异的、缺陷的和边缘的。在实践中普遍采用的是男性语言规范,并根据此规范评判和确定女性语言的差异,最终形成差异是自然的、静止的和不变的定型。
20世纪末出现了语言和性别的意识转换,语言与性别研究受女性主义语言观影响,挑战传统观点,将学术探索和社会生活密切结合,同时出现大批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如Gender and Language,Gender and Society,Gender and History,Feminism and Psychology,Gender and Education等)。学界曾经关注性别包括语言中的性别差异,如社会语言学关注男女话语差异,将“差异”作为出发点。但随着对性别概念的复杂性和变异性理解的加深和意识转换,不再将男女差异作为语言行为解释的起点和归属。这种研究的转向,是“离开性别的本质主义和两分概念,转向有差异的、语境化的和表演的模式,质疑概括化的性别观”(Holmes & Meyerhoff,2003:7)。
性别概念被看作在日常语言实践活动中被自然化和规范化。语篇或各种形式的语言产出,都是性别建构的主要场所。性别是社会建构的,通过语篇来研究(Freed,2003:704)。各种语言特征如话语量、叙述结构、不同句式、话语风格、威望语言形式、不同语音和韵律模式、土话话语形式、词汇选择、沉默、打岔、称呼语、礼貌形式等,并不是以一致的模式与性别对应的。使用者以创新和不同的方式使用语言,依赖场景、语境、活动类型、社会和个人身份、话题、交际方式、实践社区、观众、各种语言能力、经济和象征资源、政治目的等而异。语言是变化的、灵活的和创新的,女性语言有变异,男性语言也不是单一风格或形式。基于这样的认识,语言与性别研究出现新理论视域下的不同研究范式。
二、语言和性别研究的新视域
1 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多个范式
性别是社会关系中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变量之一,在社会权势和不平等的研究中,性别被认为是多面的和变化的。语言和性别研究的交往和社会身份分析范式强调通过分析书面语篇或通过家庭交往、礼貌观点、媒介特别是网络交往,讨论女性和权势的关系,揭示传统话语模式因为女性进入传统男性领域而带来的变化。语言本体规范的研究范式,则关注性别歧视的语言用法和提出改革建议。变异研究范式将性别作为特定的社会范畴或社会变量,关注个体性别和语言特征,研究与性别这种社会范畴相关的话语模式。社会建构研究范式认为,社会和语言范畴同等重要,社会身份特别是性别身份是社会建构的而非天生的社会范畴。性别是社会交往的实现和产物,语言是不同时间交往中实现社会身份不同方面的资源。所以,人们不仅在不同社会环境使用不同语言或文体,也创造不同文体,并建构不同社会环境和社会身份。“实践社区”模式就是根据社会建构框架提出的。以民族志为基础的后现代方法和多种方法的结合,也都认为性别身份是社会身份的一部分。Wodak(2003)使用了批评话语分析来揭示语言、权势和意识的关系,描述了话语建构权势和支配方式,其他还有认知方法、关注定型和交际顺应论。语言和性别研究的新视域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如工作场所、广告和教育,同时,考虑各种研究范式的整合。
2 整合与冲突
2.1 新生物主义
语言和性别研究社会建构观的目标之一是揭露和挑战男女差异所隐含的不平等关系和意识形态,进而反对不公正的和受压迫的性别关系,而生物决定论则与其对立。近年来,生物决定论或新生物主义在语言和性别研究中的影响颇有增大之势,该观点坚持认为,女性言语能力强于男性的原因是生物基础,并以此解释男女语言差异是生物决定的,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使得两性在身体、认知、心理特征和行为的习惯都出现差异,该观点质疑男女语言行为差异是社会文化过程的影响。
语言和性别研究中的新生物主义是人类行为、思维和文化研究中的“达尔文转向”(Cameron,2009:173),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等新科学的发现成为生物主义研究范式的“锐利武器”。女性言语优越性的观点被引入科学话语的解释,即人类进化的达尔文主义的“宏大叙事”。新生物主义的观点不仅影响学术界,也影响语言政策和语言实践。在美国,男女生的内在差异观点支持了单一性别课堂的运动,男女不仅应分别教学,还应分别教育,课程内容和教学法应适应不同的智力和学习风格。因为女生天生的语言优势,强调语言和读写的现代教学对男生不利,男生需不同的语言教学和更少的语言中心的课程。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发现,老师和学生都使用生物的性别差异和“大脑性别”观念来解释女生在语言课程的优势(ibid.:174)。
新生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人类思维、感觉和行为的理论解释来自进化论和进化心理学。进化心理学被称作是新的“人类本质的科学”(science of human nature),其中心是人类心智和身体一样,是进化的产物,而非在出生时是“空白板块”(blank slate),通过经验和社会化填写。相反,它认为,人类具有“被适应的心智”(adapted mind),是预设的,以特定方式发展,我们的祖先使用了这些有利于生存的方式。
进化心理学强调的是“自然” 因素(即遗传基因)而非“培育”(环境/文化影响)因素。生物机制的关键因素是自然选择,是具有生存优势的遗传特征向人类下代传播。进化心理学认为,对人类本质理解的相关历史条件是我们的物种数百万年前进化时的条件:人类祖先在非洲平原以狩猎和采摘生活,现代人类的本质就是继承了适应那种生活方式的基因。这样,不同性别适应了不同技能和特征(如女性的情感移入,男性的侵略性)。进化心理学的这种推理支持男女认知和心理差异(包括语言差异)是生物现象而不是文化现象的假设。而当代语言和性别研究的两种方法:实验室基础的神经和心理语言学和社会或应用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前者调查男女语言能力差异及大脑中语言的功能组织,后者研究自然发生的语言社区中男女语言行为。研究结果大多是证明女性天生有语言优势和语言交际的特质;男女语言交往方式有别,男性是竞争性的,女性是合作和移情的。这些研究被生物主义用来支持其遗传观点:成功的古代女性有高度的社会(包括交际)技能,天生的抚养特质和合作能力;成功的古代男性是有力的竞争者,具有实践的和非语言技能,并传播到现代人类。
生物主义论对女性语言优势的一个解释是劳动的性别分工,人类早期的女性是抚养、采摘、家务促成了大脑语言区的功能进化。男性的狩猎阻止了该进化(采摘和母亲角色可以在工作中“闲谈”,狩猎者则必须安静),这样,狩猎活动开发了男性的视觉—空间能力,减弱了语言上的神经能力。对此,Cameron (2007:18)驳斥说,即便存在劳动的史前性别分工,其解释的也是人类语言的起源,而非语言能力的性别差异。如果女性真的具有语言优势,就必须证明她们在百万年前就具有这种优势;或者是因为史前劳动的性别分工给了她们先机,让她们现在才表现出语言优势,而上述观点只是假设。Cameron(2009:178)说,现代人类学研究已经证实了所谓人类早期劳动的性别分工是简单化的概括,社会语言学研究也驳斥了女性话多的观点。根据不同社会交往环境,在非正式的交往中,不存在性别差异;而在正式的环境,男性谈得更多。即使存在语言的性别差异,根据Tannen(1990)的观点,会话风格的性别差异并未反映能力和技能的差异。Tannen的“文化差异”观认为,男女语言交往的不同话语风格,是来自儿童期的交往习惯而非生物现象或天生特征:男孩是等级制的大群体;女孩是松散平等的小群体。这些不同的群体结构和活动形成了成员使用语言的不同方式。
因此,生物观存在诸多局限,其一,认为与性别相关的语言行为变异可以通过遗传的生物特质解释。但这里涉及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人类话语的产生来自大脑机制的生物基础,但很难将这些机制的应用,如将闲谈、讲故事等本身也看作是遗传的特质。其二,生物观认为,女性比男性语言更礼貌,男性存在“交际技能”缺陷,并解释是未能充分发展移情和社会意识能力,但该观点忽略了语言行为的环境制约性。Cameron(2007:20)认为,男性不是不能使用,只是使用频率较女性低,因为男性的社会支配地位,使用礼貌语言的必要性更少,问题的关键是动机而非能力。其三,生物观认为女性语言比男性更接近威望语言规范,女性语言更标准,从而反映女性具有更多语言能力。对此,Labov(2001:293)提出了“性别悖论”: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服从显性的社会语言学规范,比男性更少服从隐性规范”,而生物观很难解释为什么女性语言具有这两种相反的趋势。其四,生物观认为女性的语言优势是遗传的结果,如果真是那样,就应该在不同文化和时期,特别是在生活方式与古人相似的社会中发现证据。可是,民族志研究恰恰是在现代西方语言社区发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在西方现代女性话语社区中,女性语言才是或者看作是有等级意识的、合作的、间接的、礼貌的、有技能的和文体灵活的,而传统社会是男性掌握这些语言技能。
因此,尽管新生物主义或达尔文主义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弱点,但它在语言与性别研究中具有的相当影响力,说明“新生物主义和其相对的宗教正统派的出现,表现了西方社会和学界对过去50年性别关系变化的现实和深奥的文化焦虑”(Cameron,2007:20)。男女性别从来没有如此难以区分,难以被生物范畴管辖。随着社会的变化、科技的进步和随之而来的性别身份变化,21世纪仍将继续各种思潮的整合和冲突。我们当然不能否定男女生物基础的差异,但是,作为文化构成部分的性别意识对人类理解自己和理解社会关系的方式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2.2 实践社区
实践社区这一理念是Lave(1991)和Wenger(2000)提出的,其定义是共同参与某种行动的人群的聚集,是做事方式、交谈方式、信念、价值观、权势关系等实践在这种共同参与中的出现(Freeman,2001:246)。实践社区关注的是“成员”和“共同实践”而非空间距离。强调实践社区对社会意义、社会身份和社区成员身份持续的共同建构、争辩和强化,而非强调固定的和被给予的社会身份。实践社区关注的是经常参与共同实践的人群,强调人们所做的社会意义,而非个体行为和活动。
实践社区的理念被用于研究语言和性别的当地建构,提供实践如何与更广泛的世界、参与者和社会结构相联系,从而在话语层面更深刻理解性别是如何产生和再产生的,人们的观察和性别顺序有什么有机联系,如社会权势和社会价值是在实践中建构的。Eckert和Mconnell-Gine(2007:29)从两方面研究语言和性别与实践社区的重要联系,研究不同但相似的实践社区类型,以探索实践对性别的语言建构的影响;关注实践社区和其他社会结构的联系,如社会网络、机构(如学校、教堂、监狱等)及更广泛的全球社区(如国家、女性)。将实践社区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研究中发现,人们参与多种实践社区:家庭、工作、体育、教堂、课堂、好友等。对不同实践社区的不同参与形式,所使用的不同语言资源的研究,创造和揭示了实践社区之间的联系及语言资源之间的联系。Holmes(2006)对工作场所这一实践社区的交往研究表明,交往中产生作用的不仅是不同性别的参与者,还包括产生“性别化工作场所”的特定机构文化,如开会时使用定型的男性“公事公办”(all-business)方法,以强调效率,或强调更“女性化”的工作场所,以突出交流、合作和情感支持。
实践社区表示意义建构的场所,它们不是随意的和独立的,结构多样的实践社区联系着个体之间及个体和政治经济。研究不同实践社区的异同,研究其在社会组织的地位,也就是研究实践社区的相互关系,并在其他理念的背景中进行。“这种分析社会单位的视角提供了在日常生活中研究性别和性相的有用方式”(Eckert & Mconnell-Gine,2007:32)。
2.3 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社会语言学
社会建构主义也称“后现代”,以与本质主义相区别。但所谓“现代”和“后现代”女权思潮是重复的和交叉的(Cameron,2005)。社会建构主义将男女性别看作是话语和实践的结果,而非独立于话语和实践的实体,因此,质疑性别的本质主义观点,质疑性别的社会概念的二元特征乃至生物性的二元特征的主观性,如男女语言的不同、女性比男性更有礼貌等。性别语言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研究的重点不是可识别的男女语言特征,而是探讨语言作为重要资源在建立性别角色和性别化的社会身份中的作用,并强调不同文化对不同生物范畴,社会文化和语言范畴的不同认可,人们以不同的、动态的和环境相符的方式在不同环境中“完成性别”(do gender),研究关注的是话语、性别和语言的接口(interface)(Holmes,2007:52)。
当代女权主义被看作是 “社会建构主义”,是女性社会语言学受后现代主义的认同和主体性理论影响,也受民族志方法的社会现实建构理论的影响(Cameron,2009:190),赞同性别差异是社会和文化产物,非生物的观点,强调语言在实现性别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在职业场所。女性社会语言学研究强调有效的社会建构的路径和方法的使用。根据语境化线索推断社会和语用意义,语言会系统地引发语境假设,包括性别规范。通过使用文化特定的当地推理,女性社会语言学认为性别是通过各种实践中的语境而社会建构的。所以,当今的实证研究多是“人们在日常书面和口语中如何建构世界、自身和他人,包括可识别的、自然的和性别化的”(Holmes,2007:54)。这是研究性别如何被镶嵌在语境中的日常谈话中被建构的动态方式的强大工具。说话方式与特定角色、立场(如权威、商讨、尊重、礼貌)、活动和行为相关。它们是“性别的文化编码……和成为性别指示的其相关的说话方式”(Cameron & Kulick ,2003:57)。
女性社会语言学普遍反对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方法,强调对女性的系统歧视,歧视既出现在制度层面(机构组织),也在当地层面(人际关系和家庭)。所以,他们把女性这一词汇看作是覆盖了不可固定归纳的范畴,如果把女性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范畴,则掩盖它的变异性和多样性。语言和性别研究丰富了性别概念的复杂性和流动性,丰富了我们对男女语言实践差异的理解,社会建构主义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
根据实践社区概念,需要关注工作场所的特定社会、种族群体、社会背景、话语风格等。例如,在对工作场所的性别交往和话语行为中,发现存在普遍的和系统的限制和阻碍女性在权威的和领导性职务的表现,特别是性别定型和对行为的正常期望上。有权势的男女使用不同的话语资源,包括正常的男女话语风格,但有的女性不得不使用男性风格。为了处理这种双重约束(女性如果模仿男性,就是跨越了女性界限;如果使用女性风格,就不像领导),女性采用各种策略,包括男女风格混合(Holmes,2007:57-58)。又如,对黑人英语语法和语音特征研究要考虑社会和会话背景,即考虑黑人祖先语言的影响。而女性语言研究同样依赖交往和其出现的社会背景,但在西方语言与性别研究中,一个潜在的假设认为,黑人女性语言因为黑人英语的存在而被认为和其他女性语言有别,是女性语言的低层部分,而非平等部分。尽管黑人和白人女性生活在相同的社会体系,种族和性别变量都是社会建构的,但是,黑人女性语言涉及种族和性别变量,白人女性不涉及种族变量,与好的和正常的女性语言相对的是工人阶级语言和有色人种女性的语言。这种观点反映了性别对白人和黑人的不同建构 (Morgan,2007:122)。因此,语言和性别研究应该考虑影响性别因素的社会背景,思考话语在建构身份和协商权势中的重要性,否则,孤立地认为女性语言应该是柔和的、关心他人的和好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Cameron(2003:459)归纳了导致当代社会生活变化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全球经济性质的变化,产品制造让位于销售服务,服务业凸显了语言的人际功能,而这些是女性语言的特征;其二是个人生活的变化。现代人生活在比以往更复杂的、更流动的、变化频繁的和具有个体取向的社会中,其身份认同意识依赖的是能够将人生经历各种片段进行连贯持续的自我叙述和对自身经验的反思。例如,当代社会改变或削弱了社会网络,个体需重建个体关系,需和他人分享经验,自我开放,自我不再是隐秘,而是与他人交流。语言意识或交际意识是保持个人身份和人际关系的技能,它改变着传统的语言技能,如公共演讲功能的重要性减退。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情感表达和倾听在当代语言表现中的重要性。“为什么交流就成为自我了解和维系人际关系的方式”(Cameron,2003:460)。在某种意义上,交流是女性的领域,这些有利于女性的语言变化,是价值观和公共话语的女性化。所以,身份被看作是可以在交往过程中定位或使用的资源,而不是人们拥有的静止东西(Wodak,2003: 671)。这也是女性社会语言学或后现代女权主义从二元对立的性别差异转向性别多样化的标记,多种性别身份影响到并被其他社会身份影响,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在社会实践中人们用语言做什么涉及交际能力观点和意义建构的权力。
三、结语
面对任何一个语言建构的文本和实践,我们不能停止和放弃使用语言的思考。为避免本质主义方法,认为将个体分类为男女就能够决定言语和语言交往的特征,我们需要从本质主义观点转向“人们对直接的和最显著的社会群体的参与”(Holmes & Meyerhoff,2003:10)。
[1]Cameron,D.Gender and Language Ideologies[A].In J.Holmes & M.Meyerhoff (eds.)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ender[C].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3.447-467.
[2]Cameron,D.Language,Gender,and Sexuality: Current Issues and New Directions[J].Applied Linguistics,2005,(4): 482-502.
[3]Cameron,D.Sex/Gender,Language and the New Biologism[J].Applied Linguistics,2009,(2): 173-192.
[4]Cameron,D.Unanswered Question and Unquestioned Assumpti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Gender: Female Verbal Superiority[J].Gender and Language,2007,(1): 15-25.
[5]Cameron,D.& D.Kulick.Language and Sexualit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6]Eckert,P.& S.Mconnell-Gine.Putt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in Their Place[J].Gender and Language,2007,(1): 27-37.
[7]Freed,A.F.Epilogue: Ref l ections on Language and Gender Research[A].In J.Holmes & M.Meyerhoff (eds.)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ender[C].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3.699-721.
[8]Freeman,R.& B.McElhinny.Language and Gender[A].In S.L.McKay & N.H.Hornberger (eds.)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10-280.
[9]Gray,J.Men Are from Mars,Women Are from Venus[M].New York: Harper Collins,1992.
[10]Holmes,J.Gendered Talk at Work: Constructing Gender Identity through Work-place Discourse[M].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6.
[11]Holmes,J.Social Constructionism,Postmodernism and Feminist Sociolinguistics[J].Gender and Language,2007,(1): 51-65.
[12]Holmes,J.& M.Meyerhoff.Different Voices,Different Views: An Introduction to Current Research in Language and Gender[A].In J.Holmes & M.Meyerhoff (eds.)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ender[C].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3.1-18.
[13]Jespersen,O.Language: 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Origin[M].In J.Holmes & M.Meyerhoff (eds.)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ender[C].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3.
[14]Key,M.R.Male/Female Language[M].Metuchen: The Scarecrow Press,1975.
[15]Labov,W.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Vol.II):Social Factors[M].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1.
[16]Lakoff,R.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M].New York: Harper & Row,1975.
[17]Lave,J.& E.Wenger.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18]Morgan,M.When and Where We Enter: Social Context and Desire in Women’s Discourse[J].Gender and Language,2007,(1): 119-129.
[19]Tannen,D.Gender and Discours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20]Tannen,D.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M].New York: William Morrow,1990.
[21]Thorne,B.& H.Nancy.Language and Sex: Difference and Dominance[C].Rowley: Newbury House,1975.
[22]Wodak,R.Multiple Identities: The Role of Female Parliamentarians in the EU Parliament[A].In J.Holmes & M.Meyerhoff (eds.)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ender[C].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3.671-698
[23]Wenger,E.Communities of Practic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